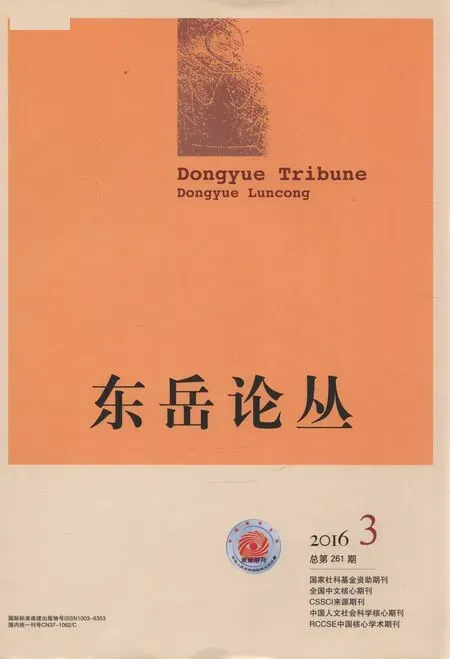中国山水画论笔墨说的形而上底蕴
——以唐岱的天地观与笔墨说为考察核心
赵 卿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山水画论笔墨说的形而上底蕴
——以唐岱的天地观与笔墨说为考察核心
赵卿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唐岱在《绘事发微》之《自然》篇中提出了“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思想,表明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使笔墨之自然能够合于天地之自然。这一共同性关键在于对自然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自然即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天地之自然”指的是天地化育万物时那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笔墨之自然”描绘的是天地中那处于生命的自然状态的山水,也因此笔墨成为绘画显现天地生生本体的载体,二者相合于体现自然状态的生命境域。但是,唐岱并没有详细解释二者的根本差异与相合的方式。从当代自然美学的视野来看,天地之自然是自然审美对象,而对应于西方自然观的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观,“天地”近似于自然美学中“自然”,“笔墨之自然”所描绘的应是形而上的天地观。“相合”思想折射出的重大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贯通自然美学与艺术美学。而笔墨为何能描绘山水生命的自然状态,完成与天地之自然的相“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唐岱;《绘事发微》;笔墨之自然;天地之自然;天地观;中国山水画
引言
提及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的关系,历代山水画论家普遍认为,笔墨之自然是天地生生之德的形而下落实。画家通过描绘“元气淋漓障尤湿”*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的笔墨自然,使天、地、人三者相合归一,“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清代画家唐岱提出的“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清)唐岱:《绘事发微》,周远斌注,济南: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思想,正是对二者关系的集中概括。
当代环境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发掘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很多自然欣赏理论的更多价值与意义。唐岱在《绘事发微》中提出的“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思想,就带有明显的自然美学色彩,这种异于西方自然审美的理论思路能够为当代环境美学体系的完善提供有效因子;并且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概念,才是环境美学语境中最接近于当代西方“自然”的概念,这种概念上的梳理和辨析是清晰准确地理解中国自然美学的前提,也是沟通中西自然美学的一个重要契机。因此,本论文将集中观照充分展现山水审美意识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论,并在当代环境美学的视野中,对唐岱提出的这一思想进行初步的分析,以期探索中国山水画论中的笔墨说所具有的形而上的哲学、美学底蕴。
一
本文的核心论题是“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笔者简称之为“相合”思想,这一思想的关键点是一个“合”字。笔者认为,要准确地理解这个论题,至少应该回答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1、什么是“自然”?2、什么是“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3、二者相合的原因与途径是什么?4、相合之后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与审美特征又是什么?而对于“自然”的理解,对“自然观”的把握,笔者认为,是解决其他问题的逻辑起点,因为在中国哲学与美学语境中,与西方自然观相对应的应该是“天地观”。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点,需要先从“自然”的含义说起。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其中似乎并没有西方“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一般是形容词或副词,不是西方语境中的名词,它形容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或状态。最早提出“自然”观念的老子,他用“自然”形容道的运行方式,说明一种无目的、无意识的化生万物的过程,如“道法自然”*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9页。。重视“自然”概念的还有庄子,他基本继承老子“自然”思想,提出“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1页。,以“顺物自然”表示人应顺应事物自然的本性,而不应掺杂私念。这里,事物“自然”的本性即是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发展特征。“自然”概念由老庄提出,历经魏晋玄学、汉代到宋明理学,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含义基本上都是“自然而然”。
中国古代画论受到《易经》、《老子》、《庄子》三大典籍的巨大影响,与中国古代文化盘根错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的很多概念范畴都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自然”概念也不例外。反映在山水画论中,其意涵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作为形容词,指“自然而然的”,表达不假乎人力,未经雕琢的山水天然样态,诸如:“非积习数十年妙出自然者,不能仿其万一。”*唐志契:《绘事微言》,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页,第319页。一类作为副词,指“自然而然地”,诸如:“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集·画意》,金沛霖等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看得多自然笔下有神。”*唐志契:《绘事微言》,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页,第319页。不论“自然”用作形容词还是副词,都旨在强调一种对“天成自得”艺术境界的表达,获得一种对生命“自然而然”生发的审美体验,这便是天然之妙有。张彦远在对绘画进行品评时,就将“自然”列为上品之上,即作为绘画的最高品评标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之中,妙品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贯众妙。”*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16页。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画家追求的正是对“自然而然,浑然天成”生命状态的呈现。
当代环境美学讲的“自然观”,是按照现代学术的思维方式去建构的,因此,一旦提及要立足现代学术这个角度,那人们必然会考虑到中西文化间的比较问题。显而易见,中国山水画论中的“自然”不能望文生义地混同于自然美学中的“自然”二字,因为在西方,当人们说到“自然”时,特别是将它作为名词使用时,指的是“自然界”以及“自然界中的事物”;这两种意义上的自然,对应于中国哲学的,分别应该是“天地”以及“天地中的事物”,或称为“天地万物”。与自然美学中名词性的“自然”真正对应的,应该是中国哲学中的“天地”概念。
在西方,Nature一词的含义,不仅可以解释为自然物或自然界,并且还可以抽象地解释为事物的性质、特性、本质。在西方,大自然是一切具象化的自然物的总称;通过具体的自然事物深入研究它的客观属性与本质特征,是西方比较普遍的思维方式与学术研究模式。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哲人看待自然界时,是以一种具象思维的方式去把握、欣赏它的:他们利用眼耳鼻舌身这五大感官,将那些可视、可听、可闻、可味、可触的自然物,通过向上玄思体悟的方式获得它们抽象的本质特性。自然物本身因此被抽象为具有某种价值或意义的审美对象,并被赋予了某种形而上的抽象观念或原则。其中道与器的关系可以作为对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呈现。《易经》言:“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哲人的思维向度。
那么,根据中国古人的具象思维模式,“天地”作为大自然是可以感知的,从天地的形状与颜色上讲:中国古人用“天圆地方”、“天玄地黄”等可感知的特性来描绘“天地”,如《庄子·说剑》中说:“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931页,第650页,第623页。《周易·坤》中说:“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刘勰:《文心雕龙》,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天地”成为最大的“法象”:“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同时,从天地的功能与特性上讲:《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生生之谓易。”*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意味着天地具有生生不息地化育万物的德行,一切东西都是由天地所生,即所谓“天地絪缊,万物化醇”*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然而,面对这种造化万物的功德,天地并不言说,并不夸耀,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931页,第650页,第623页。,这也近似于孔子说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来可泓:《论语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页。并且,“天地之大美”的展现是通过自然而然的运行方式而进行的,这就涉及到天、自然、万物三者的关系,郭象注《庄子·齐物论》中对此有论述:“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郭象注《庄子·齐物论》。
可见,以“天地”来对应现代自然美学中“自然”,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纵观古代文献,“天地”有时用一个字来表示,那就是“天”,有时则将“天”“地”分别论述。天地化育万物的神奇的力量,中国古人称之为“道”,具体的例证就是“道生万物”以及“道法自然”思想。所以,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的代名词,也是“天地”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比天地更加抽象。因此,中国古人又提出了“天道”、“天地之道”等重要概念:“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248页。“《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等等。这里的“天道”或“天地之道”都可视为“天”或“天地”的近义词。除此之外,阴阳与天地、阴阳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不能忽视的。《周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第44页,第627页,第582页,第647页,第598页,第611页,第593页,第598页。,将阴阳对立又统一的性质作了哲学意义上的概括,以说明“道”本身及“道”的特征,老庄及以后的学说思想,都是继承这一思想并发展起来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天地如何运用阴阳二气化育万物?“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931页,第650页,第623页。从中可见“阴阳”与“天地”的关系:它发乎天地,上下交媾,周流六虚,无形却充满化生的能力,是天地中确实存在的东西。并且,阴阳之气充斥于天地之间,成为天地之间唯一的本源物质,所谓“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同时,“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王充:《论衡·自然》。这从本体论上论证了“气”的运化特性是自然而然的。以此解答阴阳与自然的关系,如郭象言:“谁得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然尔耳。”*郭象注《庄子·知北游》。可见,自然的性质规定了阴阳运化的方式。因此,不难看出“阴阳”与“天地”、“自然”的紧密关系,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为:“阴阳”是对天地之道的体现,是天地造化万物的根本物质媒介,是万物的生成与变化的物质基础,它在“自动自休,自峙自流”(《非国语·三川震》)的运化中显现着“道”的特性与功德。
深入剖析了天地观的概念问题,梳理了天地、自然、阴阳之间的关系之后,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唐岱所提出的“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从而尝试揭示中国山水画美学的形而上理论底蕴。
二
《绘事发微》一书,是清代画家唐岱对山水绘画之画理与画法的经验总结。它以论列章节,有二十四篇,在第二十篇《自然》中,唐岱提出:“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墨之静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体阴阳以用笔墨,故每一画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树石沙水,无一笔不精当,无一点不生动。是其功力纯熟,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唐岱:《绘事发微》,第104、105页。其中隐含了唐岱山水画美学的核心观念,涉及四个关键词以及两个重大问题。这四个关键词分别是笔墨、阴阳、自然、天地。关于后三个词的涵义与相互关系,笔者已经在第一部分做了分析,所以不难得出“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的具体内涵——指笔墨的自然状态与天地的自然状态。两个重大问题,分别是“画什么”与“怎么画”。“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实则是关于“画什么”的问题:用笔墨去体现生生本体的天地观,描绘天地之自然。“体阴阳以用笔墨”,实则是关于“如何画”的问题:作画就是“用笔墨”的过程,而“用笔墨”的前提却是“体阴阳”,也就是说,理解“体阴阳以用笔墨”这句话的前提就是准确把握“阴阳”说。而要论述“怎么画”的前提则是解决“画什么”。
《周易·系辞上》有:“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39页。,根据这句话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是“天地”与“笔墨”,都包含有“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而“形上”层面正是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思想精微之处。程相占教授曾借鉴傅伟勋教授提出的“一心开多门”*程相占:《文心三角文艺美学——中国古代文心论的现代转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理论,说明中国古代心性论的理论模式。笔者也借鉴这一理论,为中国古代画论中的笔墨与天地关系找到一个便于把握的理论模式:“一心开二门”。“一心”指“文心”,即为文之心。“文”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术语,可以指山水自然的形貌,所谓“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刘勰:《文心雕龙》,第1页,第608页。;也可以指对艺术作品形象的描写,即指代绘画,所谓“故立文之道,一曰形文,五色是也”*刘勰:《文心雕龙》,第1页,第608页。。“二门”指事物之形而上之显“道”与形而下之为“器”两个层面。因此,结合山水画论,“一心开二门”包含两个意思:当“文”指自然山水之风采时,“文心”指“天地之心”,所开之二门,一门是形而上的天地生生本体,即天地之自然,另一门是形而下万物的形质样貌;当“文”指绘画作品时,“文心”指反映在作品中画家的言说之心,所开之二门,一门是由心挥洒出的形而上笔墨之道,另一门是形而下的笔墨技法。笔者认为,形而上层面的笔墨之道正是中国古代绘画所要“画出”的东西,也正是“画道”的深意,相比之下,笔墨技法只不过是停留在形而下层面的“器”。也就是说,“用笔墨”的终极目标是显现形而上的天地生生本体,描绘出天地之自然的境界。“天地之自然(状态)”,是历代画家以之作为理想的本体和各门艺术追求的最高对象,它既是画家应去深入体察的真实“自然”,也是笔墨要描绘的真实“自然”,用庄子的话说,它就是“天地之纯”*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984页。,近似于“天地之美”*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984页。。“天地生生本体”作为中国山水画的描绘对象,回答的正是“画什么”的问题。
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是“相合”的?笔者认为,二者相合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即一片化育生命的自然境域。“自然状态”正是笔墨与天地二者相合的关键。为了论述这一点,要从生命之基本物质“气”说起。
“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王廷相:《慎言·道体》。这说明“气”是天地造化的橐钥,万物皆是“气”,故绘画是表现物之“气韵”的,这就为天地之自然与笔墨之自然间找到了共同性,即“气”也。“气”是道之根本,万物之本源,它并非静态凝止,而是在不断变动的,所以相合的境域是一个活泼泼的境域,“生命状态”的性质亦是活泼泼的。同时,物之“生”依赖于气之“动”,如《说卦》讲:“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第717页。有了“气”之“动”,万物得以生,并且“气”之所向即物之所成,这倒非常类似“随物赋形”的意味。“境域”是张祥龙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现象学分析时所用的术语,笔者运用“境域”一词来形容气化流行的整个天地,可以比较生动的展现天地的博大与无穷的化生性。在张祥龙看来,“境域”指存在本身,具有相互构成性,即是说,存在于境域中万物的“存在形态或构成形态,不是任何现成的形态……是正在‘化生着的’……”,“总有正在当场实现之中的流动和化生”*④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8页,第185页。。也就是说,“任何‘存在’从根本上都与境域中的‘生成’、‘生活’、‘体验’或‘构成’不可分离。”④这段话说明,万物从根本上与境域是统一的,这一切都尽在气化流行之中。而所谓“元气淋漓障犹湿”,即是对生命境域之活泼泼状态的艺术写照。“相合”问题借助现象学的“境域”的“构成”洞见与识度,能够开辟中国古代思想对生命的“原发”理解,即对天地生生本体的体验。有了“气”的贯通与契合,笔墨就可以将天地中生命的自然状态描绘出来,恰当地表现出物之真实情性,“自然耳,故曰性。”(《庄子·山木注》),并且能够体现出物象中所蕴含的道之特性,即所谓“道法自然”*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169页。也。
但不能忽视的是,画家描绘天地中的山水物象,必然要依托于物象中反映道之特性的审美特征。根据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笔者认为,“虚”是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者,即是对道之特性恰当的体现者。画家观物就是欲观物之“中虚的灵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93页。原文是“天地之间,其尤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守中”即“持守中虚”。以得其妙。在这注重“虚”的山水审美意识下,物象的审美特征可以总结概括为六个字,即山光、水态、物致,因为它们集中显现“虚灵”特性——对“光”、“态”、“致”的体验带有强烈的形而上色彩。诸如,唐岱在《绘事发微》中,就以“凌云之致”形容“松”,以“探水之态”*唐岱:《绘事发微》,第71页,第79页,第107页。形容“柳”,以“沄沄之态”*唐岱:《绘事发微》,第71页,第79页,第107页。形容“波纹”,以“润泽之气”*唐岱:《绘事发微》,第71页,第79页,第107页。形容“石内发出的腾腾欲动之光”等等。其他画论家的论述也有以“云收天碧”*王维:《山水论》,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259页。形容“雨霁”,以“返照之色”形容“远峰之顶”*沈括:《梦溪笔谈·论画山水》,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271页。。笔者认为,这些画家所审美体验到的都是不孤立的“物象”形质,而是描绘出超出物象的那个“境”。比如画松,依靠其“似龙形,环转回互,舒伸屈折”的审美特征,意在描绘其“致”;又如画山水,要以描绘出具体“山石”之内的“光”为先;再如画水,通过波纹要显现其“态”。“光”、“态”、“致”是物象有形与无形、虚实结合中的一种“境”,即司空题所言之“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司空图:《与极浦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境”也正如司空图所说的,它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03页。是对“道”的一种显现。
总之,“画什么”的答案,其实是“天地之自然”这个总括的具体化。那么,如何画出这些东西呢?答案是笔墨说,即体“阴阳”而用的“笔墨”。“说”一字,直接规定了笔者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并非针对形而下的笔墨技法,而是针对笔墨“道说”生生本体的形而上理论层面。
三
“一阴一阳之谓道”,笔墨与阴阳的关系,反映的也是笔墨与道的关系。笔墨是如何表现“相合”思想的?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另一问题的分析得到解决,即笔墨如何显现天地的自然状态,归根结底,这是由笔墨自身性质决定的。笔者将从三个层次分析:一是笔墨能够显现阴阳的道性;二是笔墨山水是对天地“道性”的“道出”;三是笔墨山水使大道流行的“化机”得以显现。
首先,笔墨能够显现阴阳之道的特性。“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墨之静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唐岱:《绘事发微》,第104页。阴阳作为化生万物的介质,笔墨承接了这一作用。唐岱从两方面论述了笔墨的阴阳性:一是从动静的角度,将笔墨与阴阳自身特性联系了起来。笔在造型中发挥着“阳”的功能,墨在皴染立形中发挥着“阴”的作用,犹如“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静一动,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太极说》。,笔墨二者相依互立,和生万物,具有了阴阳般“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周敦颐:《太极说》。的能力;二是从笔墨显现物象生命层面,笔墨具有传神的能力。唐岱认为,笔法关乎物象之“生动气势”,墨法关乎物象的光彩,合理运用“墨之六彩”,可以使物象“气韵得全”“本乎自然”,而不损其“真体”。“气”与“彩”的笔墨功能,在体现神韵的机能层面与阴阳联系了起来,所谓“阴阳,气也;变化,机也,机则神。”*王廷相:《慎言·道体》。由此,唐岱为“阴阳”这一哲学范畴转化为中国画学中的笔墨语言提供了形而上的合法性,为笔墨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与理论基础——阴阳交感化生为天地间的自然万物,笔墨并用成就了画面上能够体现天地化机的各种事物。
唐岱以阴阳论笔墨,将笔墨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如同阴阳互为本根,二者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笔墨的目的是使物之神韵得以显现,而阴阳造化赋予物各自的神采,在呈现生命的自然状态上,二者意义上是统一的。神之所成,出自阴阳,亦出自笔墨,笔可呈物之气,墨可生物之彩,笔墨圆满后神韵自生,正所谓“夫神必藉形气者,无形气则神灭矣”*王廷相:《内台集·答何柏斋造化论》。,形气乃笔墨所具,神的完备也需要笔墨的有力传达。周敦颐提出:“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周敦颐:《通书·顺化》。,由此可把“笔”看作是赋予物象生命的“生者”——“生者”必有其气,是生命之根本,比如当代画家黄宾虹深谙笔墨功能,在笔法与墨法之间,提出了“墨法尤以笔法为先”*黄宾虹:《黄宾虹谈艺录》,南羽编著,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之说;同时,可把“墨”看作是展现物象“质彩”的“成者”——“成者”有圆满之意,倘若没有本乎自然之华彩的墨法,再精湛的笔法也是“有笔无墨”之流,所谓“有笔无墨”,用石涛的话说,便是“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原济:《苦瓜和尚画语录》,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62页。。“蒙养”,指的是墨法对宇宙中元气淋漓状态的显现功能,传达的是宇宙化生万物的氤氲感受。而缺少墨法来蒙养的山水,犹如只有筋骨,失去了血肉的滋养。相对于形质,山水的深意更在于显现宇宙氤氲的生化气象。所以,“生者”与“成者”可以视为从阴阳角度,对“有笔有墨”境界的再次肯定,一幅优秀的山水作品,不仅要有“笔”对生动的山水形态的体现,又要有“墨”对天地气象的皴染。只有笔墨结合,才能显现天地化生万物之功。这必然符合唐岱对笔墨功能的设定。因此,作为互不相离的笔墨,正如氤缊相揉、相兼相制的阴阳,发挥着一动一静,一取一生的作用,肯定了笔墨具有“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宗炳:《画山水序》,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252页。的能力。
其次,笔墨是对天地“道性”的“道出”。谢肇淛在《五杂俎·论画》指出:“人之技巧至于画而极,可谓夺天地之工,泄造化之秘,少陵所谓‘真宰上诉天应泣’者,但不虚也。”*谢肇淛:《五杂俎·论画》,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53页。这句话揭示了,相比其它艺术门类,如诗歌,绘画中的笔墨有着超凡的艺术功能,即有“泄造化之秘”、将天地的“幽微玄奥”呈现出来的能力。从历代画论对山水的论述中可知,画家没有停留在对山水表面形质样貌的描绘,而是关注其显现内在生命特质的诸多特性,这些特性即美学中的“审美特性”,比如,其体势、气象、气势、意态*倪瓒:题《树石远岫图》,原话为:“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尘之格,而意态毕备”。、性灵等等,对于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特性来说,笔墨却能将它们呈现出来,使画家在笔墨描绘的山水中,也可以欣赏到天地自然状态中的那种造化生机,正所谓“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宗炳:《画山水序》,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252页。笔墨之自然既然能够与天地之自然相通,就意味着它达到“上通天地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境界,那么,也就可以说,笔墨语言“道出”了天地的生命特征与意义,笔墨依靠对天地特性的理解,成为替天“道言”的“言道者”,彰显出一个原本的、纯粹的“道言”之域,使观者“游居”画中而得笔墨之大用。
这一内容涉及三个问题,即天地的“道性”是什么?“道言”有哪些特点?以及笔墨何以成为“言道者”?笔者认为,道自身的性质是“惟恍惟惚”,它是万物的本根,具有使万物生生不息的能力。并且,“惟恍惟惚”并非一片空洞、无有所出的混沌,而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6页,第226页。在“道”的恍恍惚惚中,能够认识万物本始的情形,这就是“道”的特征。至于“道言”,即道之言说,它是指一种自然而然相互引发的道的状态,反映“道”,有“惟恍惟惚”、“有无相生”、“正言若反”等体现“玄”的特点,是一种“大言”,绝非那些具体的、概念性可表述的“小言”,如人言、可道之言等。同时,“道言”具有可“道出”性。张祥龙在《从现象学到孔夫子》中提出:“老庄著作中讲到‘无言’、‘无名’主张之处,究其实都是在否认概念表象的小言或人言能达到至道,并非完全否定言与道的关系;相反,这种表达恰恰是要通过‘反’或‘损’掉人的小言而达到道的大言。不然的话,老庄讲的那些‘常名’、‘其名不去’、‘大言’、‘与造物者游’之类的‘参差之辞’就都毫无着落了。”*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9页,第256页。可见:“道言”是一种“大言”,所谓“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2页,第1016页。,具有“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2页,第1016页。的特征。相比之下,“小言”拘泥于概念与表象,不足以显现“大言”玄妙的深远,老庄论述它的目的是通过“损”或“反”它的方式,去达道的“大言”。简言之,“道言”是“大言”,它具有“道出”性,同时超越具体概念性的“小言”。“按照老庄,只有‘道出’本身(‘道言’、‘大道’)而非它的退化形式(‘人言’、‘可道之道’)是最根本的通达和源泉。”*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59页,第256页。这正是笔墨必须“体阴阳”的根本原因。笔墨“体阴阳”之后才能由人之“小言”而提升为能够“道道”之“大言”。
所以,画家如果要呈现“天地之自然”,必须化笔墨之“小言”而为“体阴阳”之“大言”。正因为这样,中国画论常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6页,第226页。性质的语言来形容笔墨之用,如“需笔笔实,却笔笔虚”*周积寅:《中国画论大辞典》,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9页。,“无墨之墨,无笔之笔”*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83页。等等。因此,历代画论家用笔墨语言去呈现“道性”天地,即唐岱所言“体阴阳”之笔墨,这种笔墨才能称为“真笔墨”:“运笔古秀,着墨飞动,望之元气淋漓,恍对岚容川色,是为真笔墨。”*王昱:《东庄论画》,黄宾虹、邓实编著:《中华美术丛书·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真笔墨”才是替天“道言”的“言道者”,也只有这种“真笔墨”营构的山水绘画,才可称为“真画”:“活泼泼于其中,方为真画”*王原祁:《雨窗漫笔》,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71页。。可见,对笔墨的要求就是要呈现天地中那生命自然状态中的山水,显现出活泼的生机,这是“画道”,也是“天道”。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历代画论家在描绘山水过程中,相比具体的山水外在形质,更主张呈现山水的内在灵趣。其意就在于描绘外在形质的笔墨仅相当于道出的“小言”,虽然它是呈现生命特征的“大言”所具有可表述性的前提,但绝非能够彰显出道性天地的“大言”意义。笔墨真正的意义在于显“道”,在于显“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赵建伟,陈鼓应:《周易今注今译》,第621页。的“道言”之域,以成就“生生之谓神也”*程颢:《河南程式遗书》卷十一。这天道之大用。因此,画论家提出了诸多彰显“大言”意义的命题,比如“不求形似求气韵”、“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维:《山水诀》,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256页。、“超乎象外,得其圜中。”*范玑:《过云庐论画山水》,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399页。这些命题都是为了达到“拟气象万千而得道之大用”的目的,可以说,笔墨是绘画上“写天地万物”的“言道者”。
再次,笔墨山水使大道流行的“化机”得以显现。何为“化机”?它是指天地变化之几,是天地的能力,也是天地的功能。知“几”者得“机”,“几”即道化生万物时,变化最微妙、最氤氲化醇、有形动于无形而得生机之处——“机”即“几”微妙变化时的关枢,得机(几)者可以显现天地在氤氲醇化以生万物的趣时。所谓“趣时”,《系辞》下传第一章讲到:“刚柔(即阴阳)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意为“趋向适宜的时机”*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70页。。张祥龙将“时机”称之为原发时间,他认为原发时间绝非线性的,也不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第207页。因此,知晓“时机”可以得“天机”,进而知晓万物之最微妙的变化,最终感悟到天地的“化机”的能力与真实样貌。“化机”立足于整个天地化生万物,显现物象生意的能力层面;“时机”立足于人对天机“恰时”的感通,而“天机”可以理解为这种天地玄妙本身。并且,知“机”者也必知“几”,故有“通几”、“质测”*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一说。画家能以“神”会,画论中便有“机神”*⑨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论山水》,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393页,第390页。的连用,以及“与神为徒”、“心会神融”的思想。实际上,画家论山水,看重山水的“气象”、“气势”、“生意”、“灵趣”、“生动”、“灵动”等审美特性,背后隐含的正是对道的体悟,对“生生”与“通变”中道生万物的无穷尽能力的体悟,以及对传达时机中天地化机出万物生意的追求。“要知天地以灵气而生物,在人以灵气而成画,是以生物无穷尽而画之出于人亦无穷尽,唯皆出于灵气,故得神其变化也。”⑨“灵气”就是“化机”中流行的元气。笔墨要表现的,就是元气流动中,在化机时,万物生命的自然样貌。因此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山水画存在于画家对天地“化机”的审美关注与捕捉中,所以,笔者认为,画家画的不是山石,而是“石之机”:用物显道,以小见大,显现出惟恍惟惚至变的道境。“化机”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形而上概念,它是对道生万物,并使生意不息能力的概括。画家正是通过这“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的艺术实践达到“有道有艺”*苏轼:《东坡论山水画·书李伯时山庄图后》,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273页。的画境。具体来说,笔墨自然表现出“化机”感,就是直观地通过笔墨语言将自然的道性呈现在素纸上,呈现出“惟恍惟惚”的审美效果,所谓“以素纸为大地,以炭朽为鸿钧,以主宰为造物,用心目经营之,谛观良久,则纸上生情,山川恍惚……”*布颜图:《画学心法问答》,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精读》,第83页。,即形成笔墨山水生命的自然灵动,一切按照自为的方式在微妙变化着,仿佛天地氤氲的元气正在画面中流转,使画家体验到与造化同流的审美愉悦。
那么,相合之后所产生的画面艺术效果最终是什么样子的?笔者的回答是,笔墨之自然状态呈现出天地生命的自然状态:画面中,天地氤氲之气淋漓尽致地呼之欲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画的就是天地氤氲化生万物的状态。通过最微缩的山水物象把整个天地的生生之德、氤氲之气描绘出来:即使是一抹流云、一座淡淡的远山,一片落叶,一挂枝桠,都能很简洁地体现出天地氤氲之气。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画家品评画作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小中见大”,做到“咫尺应须论万里”*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同时,这种相合的自然境界的实现,画家自身精神境界与人格修养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笔者认为,画家自身修养的价值与意义,是笔法与墨法的人格基础,也正是“体阴阳”的人格基础。无此人生境界,则无以“体阴阳”也。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探讨的相合思想体现出了一系列环境美学思想,某种程度上可以贯通艺术美学与环境美学。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唐岱用简洁地语言表达出天地之自然状态具有显现自身的客观性,这与当代环境美学所关注的“如期本然的欣赏自然”这一核心问题存在着积极互动的可能。二是“画什么”与“怎么画”两个问题实则与环境美学所讨论的两个核心问题有关,即“在自然审美中我们到底欣赏自然的什么,以及如何才能适当地欣赏自然”*[加]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富兴译,孙小鸿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三是当代环境美学思想也重视对环境“生命价值”的欣赏,如著名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认为,环境之美是体现环境“生命价值”*[加]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杨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的,认为“生命价值”才是环境欣赏的恰当出发点,而不是客体性的形式美。虽然卡尔松此番论证的目的是导向生态美学,但是其内在阐发的核心思想仍然是对天地生命的关注,这便是对天地中自然山水内在生命价值的认可与强调。因此可以看出,环境美学与艺术美学还有很多共同内容值得我们探究。
[责任编辑:王源]
赵卿(1984-),女,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在读。
J29
A
1003-8353(2016)03-01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