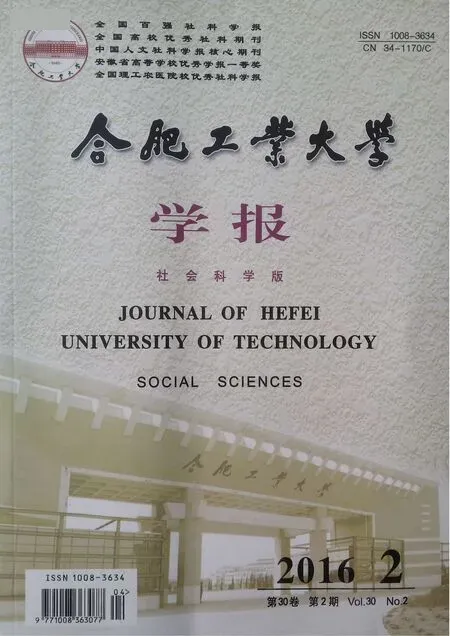论保险如实告知义务司法认定标准
——基于义务履行的规范解释
石光乾
(兰州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730000)
论保险如实告知义务司法认定标准
——基于义务履行的规范解释
石光乾
(兰州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兰州730000)
保险如实告知义务制度是构建保险体系平稳运行的法律设定,也是维系商业保险合理运营的前提和基础。在保险缔约过程中,有关义务履行主体界定、履行期限、告知事项“重要事实”判定标准、违反告知义务法律责任等相关立法规定及其适用问题产生的争议并未消除,因现行保险立法和司法解释并不完善,在立法层面缺乏可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明确规定。文章认为,通过义务履行的规范解释得出相关认定标准,可为保险理论和司法实践提供明晰的裁判思路,以提升保险司法权威并促进保险业均衡可持续发展。
保险法;告知义务;司法裁判;认定标准
我国现行《保险法》第十六条用6个条款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及其违反的法律后果作了规定,为保险纠纷法律责任的认定提供了可鉴标准。但因具体立法规定的局限及其适用问题而产生的保险争议并未消除,在实务中引发了诸多问题[1],尤其在义务履行主体界定、履行期限、告知事项“重要事实”判定标准、违反告知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诸多冲突和纠纷。保险消费者主张已如实履行义务,而保险人却以“履行义务瑕疵”为由推归投保人承担不利法律责任,且渐有将本为“危险估测”的法定制度演变为规避给付责任的“弹性”工具之势。如何从比较法和保险法理审视和规制上述法律问题,则是衡平双方利益关系、确立此类纠纷案件裁断准则的基础。
一、如实告知义务纠纷的法理审视
在保险法律关系中,投保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是实现双方契约关系的合同对价,也是构成商业保险合理运营的基础和前提。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如果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管其表现形式是故意陈述虚假事实,还是消极隐瞒真实情况,在性质上均可认定为民法上的欺诈[2]。保险公司一般认为: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对足以影响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如实告知保险人,如不实告知或未为告知,投保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投保人则认为:自己对保险人书面提出的询问事项已作如实填写,对未经询问的事项可推定为非重要事实不负告知义务,而对是否影响保险人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应知事实”出于个人对事实的理解和把握难以作出与保险人认定“重要事实”的同样判断,故不应承担履行告知义务不当之责。
从保险实务研究来看,投保人告知义务之“真实”与“充分”是法律对义务主体提出的当然要求[3],但因当事人无法从法律和法理争讼中寻求到确定规则,一旦发生纠纷,保险双方往往会因在如实告知界分、告知程度上存有分歧而导致主观上对“重要事实”的不确定认识。我国保险法和司法规范对告知义务履行缺乏具体操作规定,加之《保险法》和《海商法》对此类问题的范畴界定和解释规定相异,不仅造成司法实践中解决此类纠纷适用法律条文的不同,也因不能衡平保险利益关系而无法从实践中总结出解决此类纠纷的裁判标准,而厘清此核心要素和规则,则是消弭此间法权冲突,衡平保险双方利益的归结所在。
二、域外立法制度理论学说述评
相较而言,无论英美抑或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如实告知义务立法主张和学说各有不同,而我国兼采各国立法之长实现了理论学说的融通。设定保险告知义务制度,应是适应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危险状况进行合理预测与评估的法定要求[4]179-180,自被誉为“英国海上保险法之父”的曼斯菲尔德勋爵(Mansfild Lord)创设告知义务制度以来,“推定被保险人更为了解有关评价危险的特定事实”已为各国立法制度的思想基础与认识前提[5]。
1.告知主义理论学说及评析
传统保险法理论认为,如实告知范围包括无限告知主义和有限告知主义两大原则。前者原则要求告知义务主体应将与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有关的所有重要事实告知保险人,而不以保险人是否询问的重要事项为限,采此立法例的有英国、美国、日本、挪威、意大利等国家;后者原则要求告知义务主体对保险人所询问事项应如实回答,对未及询问事项不负告知义务,采此立法例的有德国、俄罗斯、瑞士、韩国等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在各国立法合理限定告知范围的程度上,英国大法官曼斯菲尔德通过Carter v. Boehm案的判决坚持了合理限制告知范围的有限告知义务观,并体现了两个理性规则:一是被保险人不必披露那些“并非属于他们专业知识的事实与情况”;二是“披露义务应当符合适当谨慎标准,只有出于疏忽的误述或遗漏才会构成义务的违反”[6]。而在19世纪 Lindenau v. Desborough一案中,法官Bayley则把告知范围扩展到被保险人知悉的一切事实,保险人由此不负任何调查义务,此判决注重强调了无限告知主义原则。
英国法的无限告知主义观最初也为美国法所采纳。在美国M'Lamahan一案中,该案法官Stoly在肯定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告知其知悉的那些“对危险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事实的同时,进一步认为被保险人的义务应当以“适当的、合理谨慎”为标准来判断。而最早在立法中确认有限告知义务原则的是瑞士《1908年保险契约法》,澳大利亚《1984年保险合同法》也明确采用有限告知主义,该合同法第4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书面询问的有关危险测定的重要事实,以订立合同时知悉或应知悉为限者须以书面告知。
综上可知,英美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对确定告知范围是采有限告知或无限告知存有对立。笔者认为:如采取有限告知主义,能对被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赋予理性界定,但无法反映“如实”告知的程度和深度,也存在被保险人会以不知悉为由抗辩保险人合理主张的制度缺陷;如采取无限告知主义,不仅应告知知道的重要事实,且还应对推定被保险人在正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重要事实负无限告知义务,而这种被推定应当知道的重要事实只是基于被保险人一方的理解,但英国法院却又采用理性保险人的标准来判断纠纷案件中某个事实的重要性,如此便导致了对事实重要性判断标准的偏差。
2.告知内容之“重要事实”理论学说及评析
“重要事实”(Material Circumstance)的范畴源自英国法,在被纳入成文法典前曾综合了众多有效判例,实质表现为立法对英国法院认为对保险主体双方须真实陈述“重要情况”的采纳。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把重要事实定义为“影响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保的每一情况”,英国法确立“重要事实”的范畴规则已被各国保险法所继承。如美国把重要事实定义为“对一个谨慎的保险人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法国《保险合同法》第15条规定把重要事实界定为“投保人就其所知悉影响危险承受性质的事实”。英国法上的“重要事实”标准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的主观意志是否认为它重要,而是排除某一“特定”保险人的看法,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此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通说认为,对谨慎保险人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与被保险人达成保险契约是否产生影响,二是对保险人以何种费率向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是否产生影响。作为法理判断。英国1957年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第4号报告并提出了引进“理性被保险人标准”作为重要性判断依据,但因并非所有被保险人均通晓告知义务,以此标准来确定事实重要性会导致判定结果更为不确定。
而在美国保险法律中,对以“谨慎保险人标准”能否最终确定是否承保和采取何种保险费率在立法中确定了两种证明事实重要性的方法:一是影响损失法,二是风险增加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各国保险立法对重要事实的判断基本上都采用与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相同的标准。有些国家立法因采询问回答主义,故告知义务人无须判断保险人所询问事项是否为“重要事实”,但“唯若保险人对此问题已于书面标明之,则得视为重要事项”[7]。由此推论,即使存有告知义务人主观上认为重要之事实,非经保险人询问亦不纳入告知范围内,此种限制应为告知主体义务之所属。而无论是采自动申告原则还是询问回答原则,从保险立法意旨而言,义务主体均应恪尽诚实信用之责,对影响保险人是否承保或确定保险费率的所有事实须据实告知。
三、我国保险相关立法学说及其评价
我国学术上多以《保险法》条文的规定来“解释、推定、界定”各自的理论观点,体现了移植法的传统。我国《保险法》第16条、17条和《海商法》第222条、223条规定了如实告知义务制度,但从以上法律规定和裁判实务来看,无论保险公司还是保险消费者对义务履行范围和内容深度的把握都无法找到确切依据。通过考察《保险法》第16条第1款、《海商法》第222条第1款等相关规定都表明:我国保险法律对如实告知的内容分别以“询问告知”和“知道或应当知道”为标准,但对如何判断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缺乏具体规定。我国《海商法》对重要事实界定为“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在规定如实告知范围时除纳入重要事实外,仅以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为标准。而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款立法规定来看,我国对如实告知范围以“询问告知”为标准,并未确立“知道或应当知道”规则,即并未对“重要事实”具体认定标准做出规定,继而在司法实践中,其事实重要性多是以法官的理性解释来确定,而抽象标准无法明判所有法律事实,导致实务中此类纠纷解决的障碍重重。
因此,从我国保险立法架构合理性来看,《保险法》因投保人可以不知或未为可知为由对保险人先行主张抗辩,此告知范围瑕疵凸显了立法制度的缺陷;从“知道或应当知道”规则立法标准来看,《海商法》缺乏对重要事实进行实体界定的操作规范。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保险法律体系下,实务中能否建立并适用统一的告知制度,应是保险立法规范对两大原则兼容并蓄的过程。在保险实务中,如依《海商法》规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是否如实告知没有询问义务,但却要求其对“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由此以来,被保险人告知时要自己判断何谓“重要情况”、哪些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重要事实”,并要承担对重要事实的认定过失和应知悉而未加谨慎注意过失的责任风险,这种判断义务和责任分配方式明显有失公允。如依《保险法》规定,告知义务人仅以“询问告知”为限,却必然产生能否合理界分如实和非如实告知的困惑,尤其对告知范围难以作出区分。因此,必须从学理上对告知义务的法律性质及其保险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予以明确界定,最终确立如实告知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
四、保险如实告知义务法律性质和内容
根据保险立法规定,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与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相关的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陈述或说明[8]。告知义务履行贯穿于保险合同订立、合同效力中止复效和合同续约等各个时段,明确其法律性质和内容是界定保险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从告知义务立法设定和规范程序上分析,各国立法和学说对告知义务性质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论证。
首先,从立法层面来看,保险合同是基于维护被保险人投保的预期利益,并为确定保险人因要保人支付保险费而在未来不特定时期赔付保险金的法律文件。而告知制度是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状况进行合理预测与评估提出的法定要求,进而作出以何种费率承保和确定保险费的法律承诺,履行告知义务能为保险人获取评测风险的信息提供保证,是为“评测危险”而定。如实履行该义务则为合同成立后依法主张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的生效要件,即是说,该义务并非是随附合同成立而产生的合同义务,而是依据保险法确定的法定义务,保险人可以其不履行为由先行主张抗辩。
其次,从权义层面来看,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既是明定也是对等的。此权义将义务人作为或不作为与权利人合法利益实现或请求赔偿对应起来,如契约成立则不问义务人意愿必须履行,并可因未为履行而授以相对人提请损害赔偿之权利。如瑞士《保险契约法》第7条规定,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者,保险人除可请求退还保险费外,并可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而对于未为告知之后果,保险人并非可依权义对等关系进行追偿,仅可以契约解除权对义务人预期保险利益课以正当性损害,因此在契约成立前,保险人并无强制要保人履行告知义务之请求权,要保人亦不受强制履行之约束,故告知义务应为“不真正义务”,这“与其他法律上之纯粹义务或债务不同”[4]176-178。大陆《保险法》对被保险人是否履行告知义务没有强制要求。但从义务人“故意隐瞒、不实告知”而产生的后果来看,法律还是课以告知人不利益损失。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2015年修正)》第16条对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课以不同的法律后果来看[9],告知义务在相应立法中均被明确规定为强制性规范,是依保险法之规定所生的义务,这些明定规范也实质突出了法定性义务的特征。
从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来看,告知义务主体双方因为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会产生不同的履行内容,而双方合同内容不以告知内容为确定,投保人所作的告知陈述并不构成合同内容的必然组成。在有限告知主义下,告知义务主体对保险人所询问事项应如实回答,对未及询问事项不负告知义务,其告知内容仅以“询问告知”为准;而在无限告知主义下对告知内容的界定,各国则以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影响谨慎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者决定是否承保的每一情况”为圭臬,立法是将“知道或应当知道”的重要事实作为告知内容,并不以保险人询问为限。而同为自动申告原则的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第3款却规定了投保人在未及询问时不负告知义务的例外情形:一是任何使危险减少的事实;二是任何保险人已经知道或推定知道的事实;三是保险人声明放弃了解的事实;四是任何因为明示或默示保证无需贅述之事实。因此,保险法无限告知主义并非体现“无限”扩张,只有突破以告知内容为限的危险评测手段,建立起衡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价值秩序和规则,才是保险立法应全面考量的内容。
五、均衡秩序下如实告知义务的司法认定标准
因国内外保险立法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不同。为实现保险双方权益的最大化,国外保险立法正从消极规则到积极保护的转进,我国也在制度设计上引入了不同法理规则。因告知义务履行问题涉及一系列抽象的法律解释和判定要素,实务中会因纠纷产生不同的法理认识,义务主体双方权义关系也因此多有不同。相应地,此义务仅在法条框架下是难以实现法理公正和价值诉求的,须结合相关理论学说并从主客观等多方面综合判断,进而得出告知义务履行的法律责任和司法认定标准。
第一,从告知义务本质属性来看,如实告知就是义务人为保险人提供承保危险的判定依据,相关义务人要出于最大善意提供有关危险事实资料,告知者据此危险评测所缴保险费应与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形成对价,而对价平衡原则下的权义内容则是衡平保险合同双方关系、体现保险价值的确定性标准。
第二,要以维护保险法律关系稳定性为原则,确定保险人更多地担负相关承保标的调查义务及危险估测判断责任,突破法理规则和司法条文的僵硬束缚,将对投保人的理性支持建立在强势保险人更多地承担法外责任的内容上来,这更是体现社会正义之法律价值要求在立法中强化对弱者利益的保护[10],以平衡现实司法纠纷裁决中法条适用的矛盾。
第三,要综合考察告知权利义务的法律内容,纠正因我国保险立法相异而形成的告知规则的差异,并确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的认定标准,在实际争讼中减除加重义务人负担的无限告知规则的适用。
第四,对重要事实的判定应体现客观衡量标准,排除被保险人主观臆断和具体保险人认识因素,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此情况下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来确定告知事项的重要程度,以此确立裁判标准可提升法律事实的客观公正性。
第五,法官在纠纷裁断时,对告知事实重要性的确定上应坚持“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主观标准,强调义务人应尽到通常保险业务中应有的谨慎,告知人对这种“应然性”事实标准存有异议时,应由保险人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以达到双方权义分配的均衡。
[1]马宁.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的制度重构[J].政治与法律,2014,(1):58-59.
[2]雷桂森.保险法上告知义务违反与民法上欺诈之关系[J].人民司法,2013,(19):88-99.
[3]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222-224.
[4]陈云中.保险学[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5:179-180.
[5](英)M·A·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中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84.
[6]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43-144.
[7]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21-230.
[8]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台北: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155-158.
[9]本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年修订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4-5.
[10]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控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89-290.
(责任编辑蒋涛涌)
On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Insurance Disclosure Obligation:Based on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of Obligation Performance
SHI Guang-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Lanzhou 730000, China)
The disclosure obligation of insurance is the legal sett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mooth running of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to maintain the reasonable operation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n the course of insurance contract, there are disputations in relevant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bout the obligation subject definition, time of performance, judgment standard of informing the “important facts”, the breach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disclosure obligation. Due to the current imperfect insuranc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re are no clear provisions as the judicial judgment foundation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levant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gotten by the standard explanation of obligation performance can provide clear referee ideas for insurance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so as to enhance the insurance judiciary authorit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industry.
insurance law; disclosure obligation; judicial adjudication;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2015-07-03
石光乾(1971-),男,甘肃平凉人,副教授,硕士。
F840.32
A
1008-3634(2016)02-0024-05
——与林刚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