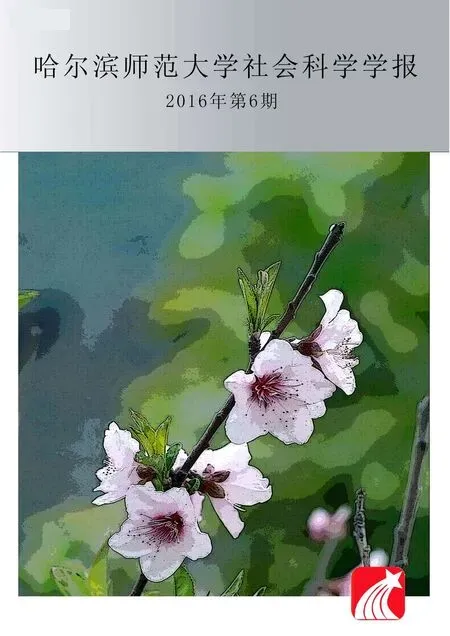人生何处不桃源
——从“桃园诗”看陶渊明的真我人生
杨 一
(黑龙江财经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人生何处不桃源
——从“桃园诗”看陶渊明的真我人生
杨 一
(黑龙江财经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很多人评价陶渊明是伟大的文学家、不朽的诗人。其实,陶渊明更是一位自然、智慧的哲人、真人!带着一份“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归田园,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自由和洒脱,并创造了精神世界的桃花源。面对原始的自然与现实的政治社会,陶渊明结合了儒道释三家的精髓,打造了一个和平安宁、平等公正、仁爱自由的中国式乌托邦。本文通过陶渊明所处时代的分析,阐释了其“桃源诗”的成因,描绘了陶渊明渴望的理想社会图景,及其诗词中映射出的诗人言自心生的真我人格、乐天安命的人生境界。如果我们现代人能够持有“抱朴归真”的自然状态,那么,人生何处不是“桃花源”呢?
陶渊明;桃花源;真我;自由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不聊生,同时儒学、玄学、佛学三教同传,人民的思想不断地整合与重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魏晋士人选择了用背离常理的放荡或傲然行为来释放内心的惊恐与彷徨。陶渊明家这位也曾有过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没落贵族,面对社会的黑暗现实,选择了投身山水之间,追求心灵与自然的融合,感受属于生命本真的自由与喜悦。
一、陶渊明与桃源诗成因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整个三百多年间,战乱不断。汉族政权内部争权夺利以至改朝换代,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整个中国大地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是在铁骑与血水中度过。战乱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这样的社会不是陶渊明所向往的。遥想陶渊明“少年有壮志,能文博学。”面对当时“朝廷无人莫做官”的社会风气,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到:“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从其曾祖陶侃始,三代为官,按照魏晋以来选官的制度,他不用考试就有了当官的资格。陶渊明第一次为官时才29岁,出任江州祭酒,管理的是五斗米教(道教)事务。由于不喜阿谀上级,不久他就辞去了江州祭酒的职务,回到他的故乡过着悠哉悠哉的田园生活。第二次在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当时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很欣赏陶渊明的文才,授他为军府参军,掌管军中的文书簿籍。但桓玄只得其才不得其人,正值陶母西去,陶渊明以居丧为名,离开桓玄军营。第三次为官是在晋安帝元兴三年,被当时的镇军将军刘裕召为参军,东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赴任。没想刘裕性情暴虐、唯亲任用,陶渊明再次归田。第四次为官是晋安帝义熙元年三月,当时的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给了陶渊明去京城递交辞书的差事,原因是陶渊明乃东晋名臣陶侃之后。得了一个参军的虚职,由于“耕植不足以自给”,陶渊明就出任了。在他完成了出使京城的使命之后,这“参军”一职也结束了。第五次为官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出任彭泽县令。他虽看不上这小官,可是当县令可以养家糊口。但当他又碰到被迫阿谀上司等违心事,终于忍不住内心的痛苦,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少日自解归”。“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离开了入世的世界,从此陶渊明发扬儒道之长,规避儒道之短,走进了玄学的世界,超越了一般归隐的境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隐居田园。
出仕,归田,再出仕,再归田。陶渊明对少年时的抱负和理想不抱希望。《五柳先生传》中描写了他的草庐生活:“闲情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短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到了晚年,陶渊明更是遭遇了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样的经历没有让他发出:“怀瑾抱瑜兮,穷不得所示”的慨叹,而是用其妙笔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社会图景——世外桃源。
二、“桃源诗”中的理想社会
陶渊明出生在仕人家庭,但他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随着其父母的去逝和家族田产的失去,其生活变得更加的困顿。所以很早就参与到了农耕之中,也就相较其它贵族仕人更近距离地接触劳动人民。由于他仕人出身,学问又很突出,因此能更好的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东晋末年,不断的战乱让陶渊明深切的体会到劳动人民内受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外受胡族入侵之苦,活的如此凄惨。但门阀政治,土地兼并,又让那些大地主阶级的仕人得有广阔的庄园,在那相对封闭的庄园里,农民可以相对自然的耕种,这就给“桃花源”原型的形成带来直观的表象和感受。陶渊明内心阔达,曾经有一腔“爱国之心”想为百姓做点事情,但现实政治的堕落,使他的想法很难达到。因此在他人格的另一个天地,他要为自己和百姓找寻一个“极乐世界”般的世外之境,这就是桃花源。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是一个人迹罕至、喜乐祥和、丰衣足食的离苦得乐世界,在这个乌托邦里有一幅令古今中外的读者羡慕不已的画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他们过着“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与世隔绝生活。萧遥洒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合为一体,似乎真正成为了自然的一个细胞,享受着天地馈赠的平静与惬意。同时,这里还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陶渊明与劳动人民产生了真挚纯洁的友谊,打造了他向往的平民文化世界。陶渊明为什么要打造这样一片乐土,这是一个理想社会,没有战乱,人人平等,喜乐大同。“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桃源的世界朴素自然、生机勃勃。这个景象的产生正是大时代一系列问题反方向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陶渊明追求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可以说是陶之后千百年间,中国人民追逐向往的社会。
三、陶渊明洒脱自然的真我人格
由于魏晋玄学的影响,时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和阔达,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土壤,儒释玄的发展,给予他无量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的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农耕,与农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体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与自然与人民接近的田园诗的风格,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质性天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陶渊明归隐了。正如苏东坡所言“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这种率性与坦然充分地展现了他的的天然与本真。“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归隐田园,在体力劳动中体会着劳动的艰辛,更有“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 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的无奈。但是他的身体是自由的,精神是愉悦的,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和谐自然之美才得以呈现在世人眼前。
在世俗人的眼中,人生需要的是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留名青史。陶渊明曾祖父曾任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和父亲都曾官至太守,陶渊明自小接受儒学教育,自然有一颗治国之心。可惜“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毅然选择了脱离尘世的“逍遥游”!古人归隐多选择山林硅谷,而陶渊明则选择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与百姓同乐,扎根土地,蓬勃生长,田园不仅滋长了庄稼,也滋润了陶渊明的心田。“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只有大自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让人真正感受到灵魂的流动与喜悦。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写的不是诗,而是生活。“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活在当下,活在一呼一吸间。陶渊明的快乐不是因为物欲的满足,而是天性的保全与发展。耕田、折蔬、酌酒和读书,物质上的贫瘠已然不足为道,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世俗人生的真正乐趣——“草木扶疏欣生意,微雨好风我自足。”
陶渊明从困苦入仕的小我世界走进了遗世逍遥的大我世界,回归到了他质性自然真我人生中。表面看上去,田园的生活辛苦、悲凉、艰难、无奈,但其内在的实质却是平静、安然、喜乐、自由。他失去了现实的衣食无忧,换来了自然的拥抱,乡邻的真情。不必再趋炎附势、委曲求全,而是白日耕田,日落心安。不随俗、不顺世,而是选择顺应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天性。如叶嘉莹先生的评价:“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园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
四、 陶渊明乐天安命的人生境界
王国维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陶渊明的桃源生活并不是完美的,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常常是残酷的:“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宁故穷以济志,不委曲而累己。”他在躬耕劳动中体会着自己的良知的安宁,在饥寒中感受着安贫乐道的自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来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徜徉于大自然的永恒中,他感受到了生命“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的短暂,体会着“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无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陶渊明毫不掩饰他内心的痛苦与悲凉,同时也更让他学会了喜乐当下。面对死亡他表现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潇洒;面对易逝的光阴,他发出了“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的慨叹;面对劳作的辛苦,他享受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美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生命源于自然,生命回归自然。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陶渊明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
实际上桃源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功名利禄只是浮云、泡影。人生像蜉蝣浮游一样短暂,《诗经·曹风·蜉蝣》有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的生命短暂,朝生暮死。我们人类对于整个宇宙而言又何尝不是?有人追求千秋万世不朽,有人追求声色犬马行乐,还有人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人生弹指一挥间,其实还有一种活法——向死而生,这是对生命的本质活法。顺从自己的内心的反省。“千秋万岁后 ,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返。”作为身处东晋末年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高僧、仙道交流,儒、道、释三者的思想在他的灵魂里冲击撞荡。诗人抱持“养真”与“守拙”的态度享受着“活在当下”的喜悦,“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陶渊明达到了乐天安命的精神境界,抛去了一切背离本心的装饰与负累,与天地合为一体,回归本真,享受自由,实现了精神世界的天地人和。
五、结语
当今社会高速的城市化、人工化,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更好的生活,身心疲惫地劳碌着。陶渊明的诗意人生对当代人做了很好的醒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抱朴归真,回归宁静,对功名利禄重新审视,从而获得淡泊的快乐,心灵的自由,生命的真我,那么人生何处不是“桃花源”呢?
[1]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M].台湾:台湾九思出版社,1977.
[2]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4]杨天芬.诗意人生——浅析陶渊明的隐逸[J].高校讲坛,2008(7).
[5]张杰.谈陶渊明后期隐逸生活的另一面[J].九江学院学报,2007(8).
[6]钟忧民.陶渊明论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8-31.
[7]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8]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孙 葳]
2016-09-07
黑龙江财经学院2013年度课题 “桃花源主题的溯源与流变”(2016YB14)
杨一,黑龙江财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论。
I206
A
2095-0292(2016)06-013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