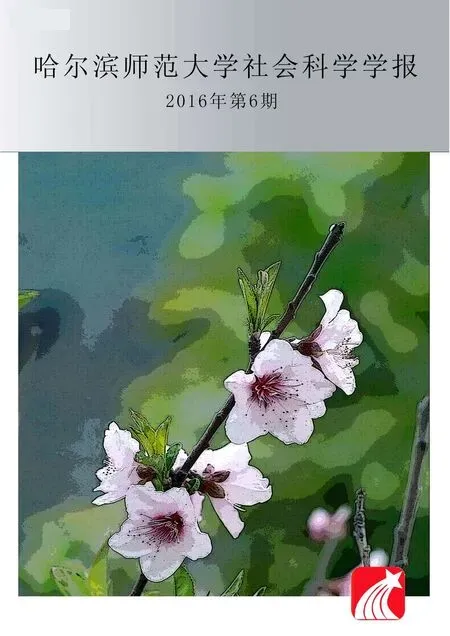中国女性媒介话语权在新媒体中的缺失与建设
覃晓玲
(中华女子学院 艺术学院,北京 100101)
中国女性媒介话语权在新媒体中的缺失与建设
覃晓玲
(中华女子学院 艺术学院,北京 100101)
中国女性话语权的缺失表现在政治领域和传媒领域,尤其是传媒领域内,女性不在场乃至缺失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主流文化影响下的女性自我期许、掌握话语权的新媒体女性从业人员占比较少、女性精英群体缺乏一定的新媒介素养等诸多因素造成中国新媒体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为了建设新媒体中的女性媒介话语权,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社会应该尽量构建一个平等的环境,而不是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鼓之吹之;普通女性网民和手机用户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做一个沉默的潜水者;在各个专业领域,女性意见领袖应该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这样才能参与到公共话语空间中。
女性;话语权;媒介话语权;新媒体
时至今日,很多女权主义者包括一些研究者呼吁中国女性话语权的建构,这样就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中国女性没有话语权。但在真实世界里,中国却存在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在现实生活的私人话语空间中,特别是家庭空间中的女性往往掌握着主动权和话语权;在政治和传媒生活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女性却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基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中国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更多地表现在政治领域和传媒领域,尤其是传媒领域内,女性不在场乃至缺失的现象比比皆是。
今天的媒介被无形中划分为以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和以互联网、手机为主的新媒体。传统媒体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传统媒体的节目如果没有在新媒体上成为热门话题,就会很快被人们遗忘。因此,本文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网络自制节目和自媒体上,因为对于青年人而言,在电脑、手机等新媒体上观看节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是在讨论这些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来了解一下话语权以及女性媒介话语权在中国的建构历史。
一、话语权与中国女性媒介话语权的发展
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福柯对话语权进行深入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P159)。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性主导权的确立就是通过创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完成的。无论是政治领域内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还是生活中的三从四德,女性都被排斥在男性话语之外,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近代以来,女性通过自己的斗争逐渐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丁玲、萧红、张爱玲、冰心等女作家建立起了中国女性的话语权以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感悟生活,感知世界,。但是由于她们基本集中在文学创作领域,而且创作的女性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缺乏代表性,不如娜拉、安娜、艾丝美拉达、包法利夫人、茶花女等具有世界影响力,因此对社会的影响也局限在小范围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慢慢地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但总体而言仍旧局限在生活层面,在政治、媒介领域内没有泛起什么波澜。
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传媒领域才开始发力。在这一时期,随着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女性电视节目和妇女杂志开始兴起。20世纪90年代末,在“频道专业化”背景下出现了专门的女性频道及以女性特色定位的卫视综合频道,如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广西卫视。从2006 年起,以旅游卫视《美丽俏佳人》为代表的时尚综艺女性节目逐渐兴起,纪实类女性节目逐渐萎缩,形成时尚类、真人秀类、谈话类女性节目“三分天下”的格局。2011 年,纪实类女性节目《半边天》的停播标志着纪实类女性节目的全面退守,在收视率末位淘汰制的驱使下,很多高端、严肃的女性节目纷纷败走麦城,被一些时尚类、生活类女性节目取代。
进入新世纪后,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它日益具有主流媒体的气质和影响力,网络节目开始大行其道,以超高点击率在网民、手机用户中流传开来,但是它依旧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态势,即女性节目少之又少。网络节目一般都是男性的天下,而腾讯视频出品的《爱呀,幸福女人》《完美lady》,爱奇艺旗下的《青春那些事儿》虽然都是女性气质比较突出的节目,但是这些节目往往无法持续,存在时间很短,也没有在市场上引起太多的关注,而更像是视频网站自我营销的一种手段。
二、中国新媒体中女性话语权缺失的原因
一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是很多因素合力造成的,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主流文化影响下的女性自我期许、掌握话语权的新媒体女性从业人员占比较少、女性精英群体缺乏一定的新媒介素养等诸多因素造成中国新媒体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1.社会对女性的压抑
美国特拉华大学传播学教授Nancy Signorielli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媒体对性别身份的影响,在于媒体提供了压倒性的信息表明,女性更关注约会和罗曼史,而男性更关注职业[2]。即便在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北欧社会,女性也仍是新闻报道中被轻视的对象, 妇女在传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记者通常被派去采访有关家庭健康、儿童艺术教育、消费等软新闻,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多为男性, 并且妇女在传媒的领导阶层的地位也相对较低。北欧传播研究者们将此称之“为媒介压抑妇女现象[3]”。从上述数据和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便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女性被轻视、被主流文化建构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而在今天,大众传媒中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仍然符合着男性对女性的固有要求,刘慧芳、杨桃、毛豆豆等贤惠、美丽、温柔、孝顺的女性成为新时代的银幕女性形象,罗鹂、叶珊等现代事业女性最后也无一例外以恨嫁之心走入家庭。这些电视剧中女性塑造形象的以及她们在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及其强大的力量。
2.主流文化影响下的女性自我期许
女性被社会压抑更多的是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而主流文化影响下的女性自我期许则是一种主动选择。波伏娃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4](P23)女人是由传媒所构筑的拟态环境、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等三重因素合力形成的。小女生从小就被芭比娃娃、白雪公主、灰姑娘等拟态环境包围,长大后被家庭、学校、单位等无形包围,容易成为物质的奴隶,而女博士、白骨精等则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这些都诱便女孩对自我的期许就是找一个有房有车的男人结婚,相夫教子,从而舍弃自我人格的进一步发展,陷入家庭之网中。
3.掌握话语权的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占比较少
根据首都记者协会副主席王冬梅在2015年3月20日举行的“性别平等与媒介责任”研讨会上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持有记者证的人数是25.8万人,其中,女性11.4万人,占44.23%,而驻外记者中,女性占40%左右*数据来源:2015年3月20日中华女子学院举办的“性别平等与媒介责任”研讨会发言。。女性新闻工作者承担着家庭、社会的双重压力,在工作中容易受到外力的影响,导致其很难在事业上付出100%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中国的名主持人、名记者中女性的数量也相对较少。另外一个事实是,占据媒介管理层的女性数量也很少,例如,在32家省级卫视中,女性台长只有4位。虽然这些数据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中国媒体的现状,即掌握话语权的女性媒介者和女性媒介从业人员比较少。
4.女性精英群体还缺乏一定的媒介素养,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新媒体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意见领袖
在女性精英群体中,有一类是以董明珠、张欣、张兰、杨惠妍等为代表的企业家,另一类是以胡舒立、张泉灵、杨澜、洪晃等为代表的媒体人。无论是哪一类女性,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些女性精英群体的媒介素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即便是媒体从业者也没有很好地利用新媒体来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而从传统媒体投身新媒体的王利芬、青音等媒体人的品牌意识非常强,她们通过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等方式聚集自己的粉丝群体,从而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与之相比,男性精英群体的媒介素养普遍较高,韩寒、张朝阳、李彦宏、潘石屹、任志强、王健林、马化腾等商界、文化界精英都比较擅长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工具,使之成为自己发声的最好方式,任志强、韩寒在微博上的每一次发声都能吸引无数网民的注意力,使得他们的话语很容易引发舆论,成为议程的设置者和真正的意见领袖。
三、如何建设新媒体中的女性媒介话语权
1.社会应该尽量构建一个平等的环境,而不是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鼓之吹之
在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力量应该是均衡而且各司其职的。目前,中国两性关系的角力在各种媒介中的表现总是倾向于男性。我们可以看到,在新闻报道中,以女性作为报道对象的数量较少,即便出现女性,也基本上是抱着猎奇的心态。而在影视文化、绘画设计、广告等媒介传播中,女性往往是被观赏、被把玩的对象,女性基本被定位在年轻貌美、温婉的贤妻身份上。只有在文学作品中,女性才呈现出多元化的独立面貌,在张爱玲、安妮宝贝、严歌苓、池莉、王安忆等作家的笔下,女性摆脱了男性的掌控,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鲜明个体,但为此总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虽然《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曾明确提出要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传媒政策的主流,但是电视栏目、女性频道、女性品牌的培养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意识的缺失。即便长沙女性频道、广西卫视等频道定位于女性,但是由于这些频道影响力不大,因此很难成为主流,依然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倾向。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上层的政治决策层,还是媒体决策层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从来没有呼吁改变现状,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女性媒介的无力乃至匮乏。
2.普通女性网民和手机用户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做一个沉默的潜水者
朱颖、廖振华在《当代女性媒介话语权缺失探析》一文中认为,“女性媒介的话语权,就是女性通过大众媒介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社会形态的意见和观点的权利,它既包括女性受众的话语权,也包括女性传播者的话语权”[5]。
过去,由于掌握工具能力的欠缺,中国女性往往被局限在私人领域和私人话语空间。在新媒体时代,技术的便利使得很多中国女性开始利用电脑、手机等工具发声,如在微博、微信这样的圈子里,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女性得以进入公共领域。即便是很多家庭主妇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新媒体工具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但现实却是很多女性仍然习惯沉默,习惯做一个围观者而不是话语体系的建设者。这些女性习惯于把自己看作受众,而且是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习惯被“皮下注射”,缺乏新媒体时代受众的主动性、互动性和参与性。而在目前中国的现实境况下,虽然很多女性传播者也在使用互联网和手机这样的新媒体工具进行传播,但是由于没有树立品牌效应,缺乏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因此,她们的话语很快被淹没在巨量的信息废墟中,也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体系[6]。。
3.在各个专业领域,女性意见领袖应该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这样才能参与到公共话语空间中
在传统媒体时代,虽然女性话语权没有占据绝对的主流,但是也先后涌现出一些意见领袖,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发出了女性的声音。例如,张越及其《半边天》,《半边天》栏目从开播之日起便被视为中国媒介中弘扬男女平等的一面旗帜,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亦曾盛赞其“极具影响力”。而陈鲁豫的《鲁豫有约》、杨澜的《天下女人》、李静的《超级访问》等节目也先后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充当这样的角色,也曾经在她们的时代里成为一面旗帜。但是随着《半边天》等节目的停播,曾经引以为傲的女性节目集体沦陷,纷纷让位于现在流行的真人秀节目、综艺节目。在《一年级》《花样姐姐》《花儿与少年》《奔跑吧,兄弟》《明星到我家》等节目中,宋佳、刘涛、林志玲、Angela baby、张柏芝等女性都被编导组塑造成大姐、贤妻、甜美姐姐、女汉子等辨识度高的标签形像,她们的这种行为方式对于女性公共话语空间的营造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相反,她们本人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借此拓展明星个人的知名度。
在后电视时代,借助手机、网络等公共平台,女性艺人开始进入到公众视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网络大V徐静蕾、姚晨,还是王菲、谢娜等拥有自己特定粉丝群的女性艺人,她们在微博上发布的消息更多涉及的是化妆、美容、旅游、家庭等轻话题,很少对社会重大事件和热点事件保持足够的关注度了反倒是胡紫薇、胡舒立这样的传统女性媒体人还在借助微博等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过相比较那些明星数量巨大的粉丝群和社会轰动效应来说,她们的影响力仍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离建立自己的公共话语空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小说《达威罗夫人》中反复强调“花与花联合起来”。如果每个女人都是一朵花的话,那么“花与花联合起来”就意味着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对男权文化的整体突围,但在现实生活中,要让花与花联合起来,还任重道远。
[1]王治河. 福柯[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宋红.电视女性节目与超性别视角[J].当代电视,2006(1).
[3]杨端明.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J].国际新闻界,1998(3).
[4][法]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5]朱颖,廖振华.当代女性媒介话语权缺失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8(8).
[6]左伟.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社会科学战线,2014(8).
[责任编辑 薄 刚]
2016-09-20
中华女子学院校级课题“中国电视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和建设”(KG11-03005)
覃晓玲,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产业。
G20
A
2095-0292(2016)06-01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