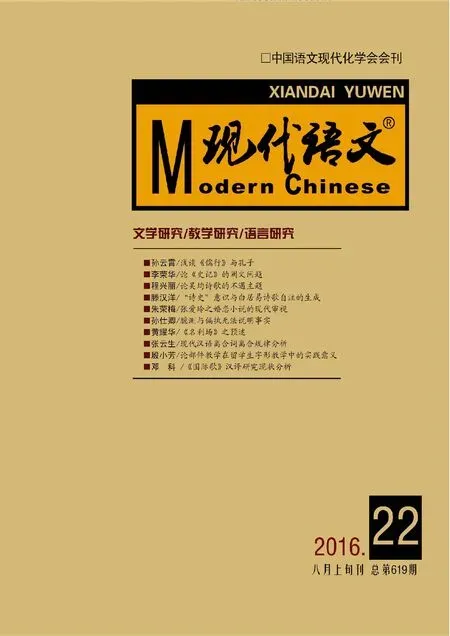臆测与偏执无法说明事实
——重读《心灵史》
○孙仕卿
臆测与偏执无法说明事实
——重读《心灵史》
○孙仕卿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张承志以哲合忍耶教派的秘史为题,创作了《心灵史》及其他篇章,目的之一是让穆斯林以外的人们了解这段历史,认识哲合忍耶。然而,他在行文中倾注了大量个人情绪,影响了文字表述的严密性和准确性,造成前后不一致、缺乏理性和人性的关照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没有引起论者足够的注意和评析。文章着重于发掘《心灵史》文本中有关历史事件的自相矛盾之处,以人性的视角评析作者渗入文本的倾向,在真伪、善恶两个方面作一些个人的思考。
《心灵史》 矛盾 偏执 人性
一
读过张承志的作品之后,我们或许赞同论者对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的描述:“张承志笔下的小说语言摒弃了作为简单的信息交流工具的日常语言,而是选择了承载其浓烈的内在情感与自觉的审美追求的诗化语言。……以其强烈的情感冲击打动人心,以意象化的语言与结构对人生与人性进行象征性的透视,并通过符号化的隐喻手法表达主体对于终极和神性的探问。”[1]固然,他的语言富有感染力,但其承载的内容该如何评价?以哲合忍耶教派为题材的《心灵史》《西省暗杀考》,写于同时期的《心灵模式》《宁肯湮灭》等文章,都可以当作考察的对象——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被文字和激情遮蔽的事物,它们或者经不住推敲,需谨慎对待,或者不可轻信,唯有理性才可以判明是非,而尤为关键的则是怎样看待作者的倾向,怎样理解他的言说。尤其是解读《心灵史》,应立足于文本自身,结合同时期的创作,发现问题。
《心灵史》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叙述了中国西北哲合忍耶教派二百余年间的历史,起于18世纪立教之时,终于民国时期,一共七代光阴,分为七“门”。与哲合忍耶相遇、相知,为它震撼、感动,因而举意,描摹一幅幅悲壮绚丽的场景,便是创作《心灵史》的缘起。作者说:“我被灵感和冲动窒息了。我如此渺小;而辽阔的世界却在争抢着我。谜底全数公开,本质如击来的大浪,数不清的人物故事融化着又凝固成一片岩石森林。我兴奋而恐惧,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只想拼命加入进去,变成那潮水中的一粒泡沫,变成那岩石中的一个棱角。然而我面临的使命却是描述它们。”[2]毫无疑问,这是他私人的心灵体验或启示,但不止于此,“它不应当仅仅是一种私人的体验”,作者“盼望人们能理解,至少了解我近年来消失其间的大西北”。
二
“历史全是秘密。偏执地追求历史而且企图追求心灵的历史,有时全靠心的直感、与古人的神交,以及超验的判断。”这句提纲挈领的话,可以看做整部《心灵史》的注释。它的体裁是独特的,正如作者告诉读者的:
我决定——
舍弃我科班毕业的历史系写史的方法,采用接近我的前辈——关里爷、曼苏尔、毡爷的写法,只描述今日在哲合忍耶教内被记忆、被坚信的那些史事。这将意味着我删砍了自己这部生命之著的数十万言;这将意味着我要放弃对同治战争许多事件的发言权;这也将使我面临崭新的困难——熔历史、宗教、文学为一炉,同时经受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
……
这是一场尔麦里,不是一笔流水账。繁琐哲学是最低级的,我要像哲合忍耶大众一样抓住根本。
给予张承志莫大影响和震撼的《热什哈尔》,多次以引文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提供了写作的范本。
不仅仅只是史学、哲学或者神学,也不仅仅只是某种西北底层生活状况的实录,《热什哈尔》一书提供了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
民众与国家,现世与理想,迫害与追求,慰藉与神秘,真实与淡漠,作品与信仰——尤其是人迎送的日子和人的心灵精神,在一部《热什哈尔》中,都若隐若现,于沉默中始终坚守,于倾诉中藏着节制。……这是被迫害时代的中国回族的一种形象,是他们的心灵模式。
它(指《热什哈尔》——笔者注)既是史事,又是神学,接近散文记录文体,又像在隐喻象征。它间于历史、文学、宗教三者之间,但作者坚持的——却是一种真诚的向往。他向往着一个超然的存在,他只求在那里被接受。他不费笔墨解释他早已坚信的,他也不追述他认为那伟大存在早已洞知的事实真相。他只管他与它的独自交流。
的确,和《热什哈尔》类似,《心灵史》是一部很难读透的书,作者力图要读者理解他、接近他,但是他的主观意志过于强烈,具有浓厚的自我意识,因而行文是拒绝阅读的,个人的心灵体验仍然令人望而生畏。
既已宣称“《心灵史》不是小说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文学力量的掩护,它也不是历史学但比一切考据更扎实”[3],那么,这一自信的论断是否经受住了检验?先来看一下书中对待历史的态度:“这里回民不主张儿童读方块字,但他们却精熟二百年历史”“《热什哈尔》关于平凉太爷下狱的记载很少,正反映关里爷的严谨”,又说:
关里爷、毡爷、曼苏尔、以及无名氏们对于历史的过程本身的淡漠,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他们这种作家来说,只要实现了牺牲殉教的念想,一切就已经结束。若是非要回忆过程,他们宁愿编个故事。
前后矛盾,自相抵牾,哪里有信度可言?难道人们熟识于心的历史,就是编撰的那些故事吗?作者一再地否定官修历史,斥其为“书耻”,然而在他的笔下,历史不过是换了一副面孔,真实程度如何,不能不叫人怀疑。
针对清朝乾隆年间石峰堡一役,只因发生的时间与回历开斋节大致重合,因为信不过官方说辞,作者断定,官方有意隐瞒事实真相,删去了官军对回民的屠杀这一重要的环节,从而欺骗世人。但是,他的立论又是怎样的?“可以断定:石峰堡内困守数月的哲合忍耶回民一定是在礼尔德节这尊贵的拜功。”又如,“张文庆阿訇一定决意此日不礼尔德,等官军攻上来时再礼——这是牺牲仪式的宣布。”读者或许无法明白,张承志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原始文献证实他的说法,甚至没有证实的念头,便带出了“一定”的论断,比起他加在官方身上的伪造文献、回避事实,难道就更有资本传于后世?对于谎言和欺骗,作者和读者都不会容忍,但为了揭穿它们就去制造另一种形式的瞒和骗,甚至用宗教的感情影响人们作出合乎理性的评价,这样的作法并不值得推崇。
历史、宗教与文学并非不可并存,三者合一,往往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但是,无论是题材的来源,还是具体的表述,乃至引证的资料,都应使人信服,至少怀着认真的、严谨的态度,笔下的文字才能经得起考验。如果没有事实的佐证,轻易作出论断,结果只能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的判断只忠于心灵获得的感受,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我直觉地信赖着他——所以关里爷著《热什哈尔》一书所载平凉故事最为可信”,如此说法,也许反映了作者内心认定的“历史”“真实”,但也只能作为他个人的体验,是他与先辈的某种神契,而不是可以拿出来跟读者交流、叫人指摘的观念。作者宣称要接受三方面的挑战,但至少在历史这一方面,他的成绩并不合格,也不能以文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实际成就加以弥补。
三
对于哲合忍耶教众的反抗斗争,作者无疑是热切地肯定的,他花费了大幅笔墨描述这些事件,激情昂扬,甚而失去节制。由此引出评判的问题:这种反抗斗争是不是正义的?面对强权压迫,人们为生存和信仰拿起了武器,这种行为应予以适度的肯定。但是,以暴易暴,换来的是什么?报杀戮以流血,用新的仇恨代替了旧的对立,难道不应当反思吗?
虽然也意识到“不惜杀伤人命也不惜牺牲的错误,比比见于中国回民漫长的历史中,各派都应引以为诫”,但是作者更加肯定了暴力、流血的正义性、正当性,为“圣战”而呼号:“圣战,只有在不堪宗教歧视和保卫心灵的信仰不被发动时,才能够成立。仅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以圣的名义流血。”此外,作者频繁地使用绝对化的评述,偏执地认定他所理解的就是对的,不给旁人反驳的可能。比如,“举义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受人赞美”“我坚信,如果谁能够看见当时的情形并把它描述出来,那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的一幕”“哪怕是一个无神论者或没有信仰的人,只要他善良而真诚,他一定会在人生长途上遭逢一些不可思议的体验”……。
不仅如此,张承志的偏执还体现在深度的自我沉醉,对读者、对学界反应的厌恶鄙薄之情,完全不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态度。他不无狂妄地说:
不信仰因而怀疑的人们其实是没有能力假装评论《心灵史》的;这册书里活着的不是我,而是无数与他们采取完全不同的生存原则的人。他们既没有必要因我叙述中的戏剧性而廉价地感动,也没有必要因为听说了信仰世界的世俗而得意。人遵循着艰难的处境生存,人的社会中存在着利益、矛盾和分歧。根本的区别在于那些人信仰。这是无可置疑的生存的高级形式。[4]
我至今在我自己的行为面前惊异,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感谢让我不能容忍的学术界和文学界,没有它们的逼迫和我对它们的厌恶,我不可能发现如下的真理——正确的方式存在于被描写的人们的方式之中。[5]
《心灵史》的最终阐释权也许握在作者一人手中,但是普通读者就不可以给出自己的解读吗?宗教不单属于信教者,平凡的人们同样可以照着世俗的道路接近真理,获得感悟。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鸿沟,还没有宽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即使信仰不同,也可以交流一番,不奉上帝、真主,就不能坐而论道吗?在对世界、社会、历史的认知方面,人们往往会形成某些相通之处。退一步说,观念的冲突也是可以弥合的,只要人们愿意交流,而非诉诸暴力。这是于宗教而言。何况,《心灵史》也可以纳入文学的范畴,为什么不能给人阐释的空间?作者不是说过要让穆斯林以外的人们认识哲合忍耶吗,怎么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断定凡夫俗子缺少评论的资格?
向读者展示过度的自信,往往会妨碍阅读,一味固执己见,只能归结为偏执、狂妄、臆断,拒绝阐释,显得造作。为了理解作者的偏执,我们不妨翻翻《清洁的精神》这一篇文章。他景仰古代的侠士,推崇英雄主义,为杀伐正名,乃至讴歌:
刺,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本来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制胜的决死拼斗。
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经常呈现着一种异样的美。……人的烈性、人在个人利害上的敢于舍己,压倒了是非的曲直。[6]
对于正义的态度,对于世界的看法,人会因品质和血性的不同,导致笔下的分歧。……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7]
他醉心于寻找血性,寻找可以同刺客媲美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张承志放浪于广袤的大西北,完成了《西省暗杀考》这部中篇小说,同样取材于哲合忍耶的故事,文笔较为单一,尤其重视情感烈度的收和放,可以看作《心灵史》的参照。
同治年间,清政府进军西北,平定回变,处决了义军首领马化龙。侥幸逃脱的哲合忍耶信徒伊斯儿和其他三人发誓复仇,躲到一个叫做一棵杨的村落,伺机行动,然而一次次地失败,最终意识到“复仇的口唤,并没有落在一棵杨——这个举意暗杀的教派身上”[8],才安心做阿訇,安心地逝去。作者的宗教热情充斥着行文,感慨之外,一些段落也显得过于突兀,甚至美化暴力。在《西省暗杀考》里面,这种倾向尤为激烈。如描写清廷官员遇刺的场面:
喊叫水的马夫突然一抖手,酒杯飞上空中,手中现出一柄斧头。马夫一跃而起……一斧子剁在刚钻出轿门的人头上……马夫闪电般抡动斧头,如雨的砍伐带着噗噗的溅血声,密如鼓点……顷刻时那头被剁进泥土,又被连同泥地剁烂,变成血泥不分的一滩……[9]
针对张承志作品中显现的美化暴力倾向,论者指出,“他手执一端,始终处于激烈对抗状态中……造成了一种内耗性很强的简化。荒芜视野中展现的是无数赴死者和受难者,所以《心灵史》将人民的暴力和圣徒的牺牲之美推上制高点,极尽赞颂。”[10]这种解释仍是从肯定文本的合理性出发,并未关注人性。
文学作品中不乏暴力场面,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我相信文学是宽容的,无法制定什么规则,标明哪些不能写,缘由则是道德、政治因素,等等。关键在于拿笔的人,他是以哪一种态度进行创作,是冷静,客观,还是心怀仇恨,甚至为了宣泄仇恨而不加节制,甚至自我陶醉。鲁迅写过祥林嫂、孔乙己等遭遇的冷暴力,写过许许多多看客的漠然,然而我们知道他是心怀苍生的,文笔固然冷峻,其内里却是热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体现了人性的温度。读过张承志文章的人不难看出,他与现世生活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崇尚游侠,行笔带着刚硬之气,相信这也是很多人欣赏的特质。然而,过度的推崇免不了造成单一的效果,对暴力不加节制的渲染,反映了作者内心的阴暗一面。上文引述的刺杀场面,呈现给读者的只可能是恐怖和战栗,以及厌恶之感。暂且抛开读者的身份、族群属性,从普遍的人性视角加以考察,这样推崇暴力、宣泄仇恨,沉醉于所谓悲壮的、绚丽的血色,为之歌颂,书之传诸后世,其后果如何?论及此处,作者高昂的理想主义、清洁的精神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现出杂质,不仅没有丝毫值得肯定的可能,而且应引以为诫。人性才是我们衡量作家、作品的尺度。假如只看到所谓“理想主义”“虔诚”,就不问它们的内容和背后的动机,从而赞扬它、肯定它,那么评论再精彩也毫无意义。
描述历史,需要去伪存真的严谨态度,摒除私人情感的干扰,而后才有可能呈现出历史本来的面貌。具有虔诚信仰的教徒,怀着热切的盼望,清洁的精神,更应该慎重一些,下笔之时,考虑题材来源可靠与否、行文是否站得住脚,这些都是检验作品的重要参考。《心灵史》以破除偏见为目的,却造成了新的偏见,力图让读者了解哲合忍耶,却没有做到客观公正,难以发现其中含有人性的因素,反而歌颂暴力、肯定暴力——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有权利批评这样一部书,行文固然是力透纸背,但其中蕴含的种种杂质,不能不引起深思。
四
阅读品味文学作品,除了字面的意义,结构布局的方法,作者秉持的态度同样重要。对待批评,作者也应该表示出理性的反思,不可局限于一家一派之言。在这个方面,改进的空间仍然不少。如《张承志研究》(杨怀中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这一本集子,所收论文多为溢美之辞,鲜有涉及批评的文字,是不是有狭隘之嫌呢?研究论文结集成册,理应做到客观公正,读者期待着更完善、更优质的资料,以便全面认识和理解文本,用于对比分析。
不过,在众多的称颂之中,我们也看到了些许不一致的观点。胡庆章已将《心灵史》的缺陷作了简要概括,如“是非不分”“以偏概全”“自相矛盾”等,给本文提供了参考。但是,该文分析产生这些缺陷的原因,归结为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就显得牵强附会了。[11]应该为作品负责的仍是作家,他的选择与考量决定了行文的品质。张承志没有刻意地约束自己,没有对材料和细节加以甄别,因而造成了偏颇,很难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上找出相关的因素。
亦有论者尖锐地指出张承志高扬理想主义和清洁精神的反讽性质,“他乃是以反流行的形象成为部分人的偶像的,是以拒绝大众的激进而慷慨的与呵斥与指责赢得一些人的欢呼的”“张承志的个人信仰值得人们尊重,但他的姿态和诉求恰恰最好地适应了这个时代的某些文化消费的走向,他的充满‘终极关怀’的‘神’的宣谕也并未脱离当下的世俗文化。……张承志恰恰以一种后现代的‘崇高’变成了变幻的媒体的舞台上有趣的献演。”[12]人们对他和他作品的称颂,具有喜剧色彩,因而是值得反思的。
也许正像作者自己说的那样,廉价的感动不值一提,一些文章只是在肯定《心灵史》所宣示的宗教热忱、悲壮情怀,显得单薄。这中间也不乏冷静的声音。“每一位知识者不一定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圣者,但都有向着道德完善的方向发展的趋向,至少在精神上有一种非达目的不甘罢休的寻求完善的冲动。这种具有戒律意义的道德理想,是规范张承志思想的‘道’,也是驱使他思想的原动力。……在《心灵史》及一系列随笔中,对道德的呼唤已变成了一种宗教的激情。”[13]张承志对道德完善的追寻,理应值得肯定。
张承志无疑非常看重他的《心灵史》,他在序言中写到:“对于我——对于你们从《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以来就一直默默地追随的我来说,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不敢说——我还会有超过此数的作品。甚至我还在考虑,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作为一部总结性的作品,《心灵史》并不完美,张承志画下的这个句号也不那么圆,叫人读了满意。他恣意挥洒强烈的主观情绪,将心灵体验不加节制地融入描述当中,因而远远没有达到历史的、宗教的、文学的统一,这一试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作者的偏执影响了他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也干扰了他客观公正地选取资料、采纳资料,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造成了文本自身的矛盾,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和甄别,评价自然是偏颇肤浅的。读者也需要持以冷静的观察角度,不可一味地赞扬宗教和理想的虔诚、纯洁、高贵,而忽略了最基本的人性因素。异端之美,美在何处?精神的清洁不只是态度,以及故作高深,更意味着宽容,超越自身的狭隘,提升认知的境界。
注释:
[1]黄发有:《诗化品格与多语混融——张承志小说的语言风格》,回族研究,2009年,第4期。
[2]张承志:《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长篇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下文所引《心灵史》皆为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3]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后记》,《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14页。
[4]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后记》,《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15页。
[5]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后记》,《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15页。
[6]张承志:《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01-402页。
[7]张承志:《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页。
[8]张承志:《西省暗杀考》,《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19页。
[9]张承志:《西省暗杀考》,见《北方的河·西省暗杀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98页。
[10]李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心灵史〉解读》,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1]胡庆章:《抒情压倒了理性——论〈心灵史〉批判力的丧失》,文教资料,2015年,第14期。
[12]张颐武:《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2期。
[13]杨扬:《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历史过程——论张承志的文化批判》,回族研究,2002年,第3期。
(孙仕卿 江苏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10046)
——从叙述者“我”的角度解读心灵之作《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