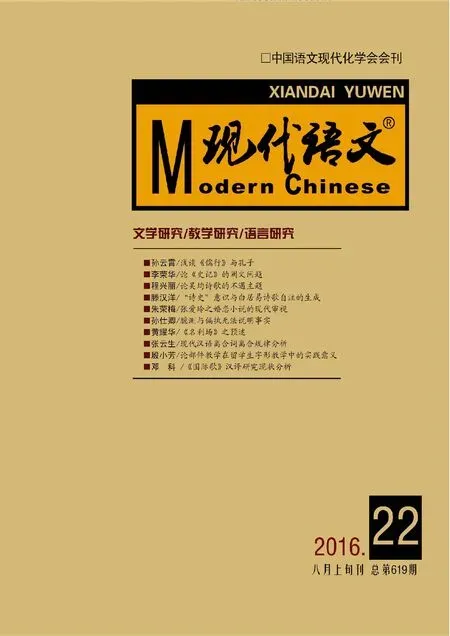《姑妄言》与《金瓶梅》评点中的“寓意说”比较谈
○董定一
《姑妄言》与《金瓶梅》评点中的“寓意说”比较谈
○董定一
在于评点《金瓶梅》之时力主“寓意说”的张竹坡的熏陶沾溉下,清代世情小说《姑妄言》的评点中同样出现了诸多凭借“寓意”为判断准则以解读小说情节建构与思想内蕴的文字。不同于前者之处在于,《姑妄言》与众不同的成书过程使得评点者可以对作品所具寓意作出与作者本意几无暌隔差池的解读,并在这种解读中更加专注于对文本自身的分析;这就使得其在评骘过程中所提出并申明的“寓意说”更具说服力。
《姑妄言》 《金瓶梅》 小说观 寓意
《姑妄言》为辽东人曹去晶创作于清朝雍正初年的长篇小说,其书内容放诞恣肆、奇突骇异,可谓独树一帜。《姑妄言》对当是时的社会生活给予了不遗巨细的展示,对构成社会生活的诸多或美好或丑恶、或可敬或可笑的元素予以了精准的剖析;小说于创作时强调对世态人情的细致描摹和追思考察,这一叙事偏好实承《金瓶梅》之遗风。与作者在实际创作内容上的遥相对应相仿,《姑妄言》之评点者林钝翁在品评作品时同样对为《金瓶梅》作评的张竹坡所主张的小说观有所继承;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二者在把握文本架构、阐释文本内涵之时对作品本身所包孕的“寓意”的相似的关注与讨论上。
在《姑妄言》第八卷中,评点者林钝翁即以回前批的形式,取《金瓶梅》而为正典,对适时通行的“以正史而为小说之佐证”的说法提出质疑,并借机申明自身所支持的小说观念:
《金瓶梅》一书可称小说之祖,有等一窍不通之辈,谓是西门庆家一本大账簿。又指摘内中有年月不合,事有相左者为谬,诚为可笑。真所谓目中无珠者,何足与言看书也。……但作小说者,不过因人言事,随笔成文,岂定要学太史公作《史记》用年月表耶?大凡书遇此等不通人持看,亦书之一厄。诚所谓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1](P388)
在这里,评点者既点明了《金瓶梅》一书作为小说所采用的表现方法的合理性,更指出了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在写作方法和叙述形式上的差异性,其概括可谓独具只眼——须知在《金瓶梅》诞生之初,其所采用的“以工笔而描摹世情”的描述方式即颇受非议;论者或因其琐碎绵长、事无巨细的记叙风格而比之于详备之实录,或因其间有矛盾、时出错讹的记叙内容而比之于精严之史著,其在文体判断上多有疏失。《姑妄言》的评点者对此类观点给予了坚决的反驳。他指出,在鉴赏时将小说与实录或史著完全混为一谈,实属“一窍不通”“殊为可笑”之举。评点者认为,这种创作与现实的不符实是小说塑造艺术形象之需,作小说者无须如著史者一般,在提笔撰文之时先将事件的真伪先后考辨一番;作者当“因人言事,随笔成文”——在素材的选取与寻觅阶段,创作者固然要依从生活真实而对所获材料略加约束,以避荒谬不经;然在对已有的故事胚型施与煅烧捶打之时,创作者则不妨将实录因素纳入文学视野,以酣畅淋漓、天马行空的叙事方式来尽情挥洒,使笔下的情节人物更加趋近于艺术真实。
从小说理论史的角度来看,《姑妄言》的评点者林钝翁之所以能够挺身而出为历来受评论者口舌诘难的《金瓶梅》辩护,并以一种开明的态度来认识后者所呈现的“于史乖谬”的面貌,其言行自有其理论渊源。很容易看出,评点者这一事涉文史关系的观点实源自《金瓶梅》的评点者张竹坡。后者在论述《金瓶梅》与实录关系时,虽然亦在书前开宗明义,指出“《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强调了作为小说的《金瓶梅》与作为史传的《史记》在以实录笔法记录世事这一层面所存在的共通点,然张氏随即腾挪笔锋,转而关注两书于叙事时序上的差异,并借此以言说小说与史传的具体区别:“此书(《金瓶梅》)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帐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迷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金瓶梅读法》之三十七)[2](P47)张竹坡认为,小说创作既不必像年谱一般严格遵循时序,亦无须像实录一般如实记录事件;就小说家而言,他们尽可以将这些束缚所引发的顾虑置之脑后,完全借助以虚构为本的神妙文笔而引得读者目眩神迷;在张竹坡们这些事涉作品叙事策略的、貌似简单明了的说法的背后,体现的是清初小说评论家在小说的文体特征认识上的进步。
事实上,张竹坡与林钝翁在文学阐释上所具有的一致性并不单单局限于其凭借对作品(小说与实录/史著)文体方面的大致准确的界定所作出的事涉不同写作话语与文体形态的解读。作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评论家,张林二人之于小说理论的共同贡献还体现在其于研析作者创作理念之时所采用的相仿的讨论路径上——在评述过程中,他们不断猜度、揣测作者的创作心态,并对后者在布局谋篇之时所展现的艺术偏好及所隐含的思想感情予以有针对性的追缉与联想。作为文本的接受者与解读者,评点者在进行上述赏析之时首先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选择性的整合了小说中其所认定的最能够“折射”出作者个人意愿的信息,并将之作为彰显其所具“不同于实录”之特质的文本内证;在此之后,评点者又结合自身的欣赏趣味与审美喜好来对这些内证所隐含的意蕴进行带有个人色彩的熔铸提炼;“寓意说”也便在这一阐释环境之下应运而生,成为清初小说评点家所曾提及的最具新意的观点。
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之时即曾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以“寓言”为中心的小说观,并写成《〈金瓶梅〉寓意说》一文付之于小说之前。竹坡在这一篇文字的起始处这样写道: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2](P27)
在张氏看来,小说(“稗官”)应当具有“寓言”的性质,作者叙述文学世界中幻设的“风影之谈”的目的是“依山点石,借海扬波”,为自己叙写刻画现实世界中与之存在逻辑关联的人与事设定出合于情理、意趣盎然的叙事模型;受制于这样一种判断前提,张氏在对小说施以评论之时亦是洞烛幽微、心细如发,更加看重对小说中那些可能另有深意的相关人物事件的内涵揭示;也正因由此,他才会提出为作者笔下人物形象名字所隐含之寓意“寻端竟委”的主张——在竹坡眼中,不但“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皆为作者借助类似于寓言的创作模式“托名摭事”而成,书中所采用的人物名称更是为其主观上建构小说主体、编织故事情节起到了直接而有力的推动作用。
就叙事作品而言,“除了叙述事件以激发人格特征之外,叙述中还有一个使人物生成的重要手段,这就是通过专名的暗示与粘结。”[3](P226)很容易发现,《金瓶梅》在人物塑造方面确实广泛地应用了这一叙述手段:在这部小说中,笑笑生往往令其笔下人物的名字先于其行为出现于读者面前,并以近乎“量体裁衣”的方式,借用富有寄寓之意的修辞方式而使之成为影射、暗示、粘连相关人物人格特征与行为表现的符号表记:“应伯爵”其号谐音“白嚼”,自然是善于白占人便宜的帮闲;“常峙节”之名类于“吃借”,则必属入不敷出借贷为生的布衣。小说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般般种种、不一而足。读者在未见《金瓶》其人之前,便可以通过浏览其名讳而在内心中建立直观的第一印象。应当说,张竹坡提出“寓言”小说观,进而通过解读作品人物的名字以揣测作者之创作意图:这一分析门径有其合乎情理之处。与张评《金瓶梅》之“寓意说”相承相应,纵观《姑妄言》之评点,其文虽未明确提及寓言,然评点者亦多效仿张竹坡之法,对作品中物类名称所具寓意加以释解,并指明这种有所寄寓的创作方式在展现小说文体特质方面所起到的效用——在《姑妄言》中,评点者提出“因人言事,随笔成文”之观点,此实与张氏“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之论调遥遥相应。
要而言之,两部小说的评点者在对小说中的内容从“表现小说独具的文体特质”这一作品层面上加以定性,解决了“何为作小说”这一问题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以自我为中心来推断“独具文体特质的小说”的创作观,从作者这一层面上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解决了“为何作小说”的问题,这种对小说文本深层次内涵的挖掘也就促成了“寓意”之说的形成和完善,其论断虽有深浅之别,究其本质而言是一致的。
从评点者对文本材料的诠释程度来看,钝翁对《姑妄言》之寓意的讨论并未向我们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其阐释深度和论述广度亦远较张评《金瓶梅》为逊;不过,倘若我们不仅仅拘泥于评点文字本身,而是将之与评点者联系起来而加以拟想猜度的话,似乎又会有不同的发现。
《姑妄言》的评点者与小说作者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根据前贤对其于文本之中所留下的诸多线索的考据钩索,此书之评作很可能是一人身兼二职;即非如是,评点者对作者其人亦有着超乎寻常的了解。[4]正因由此,在阅读《姑妄言》所附评语时,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中评点者自人物名称申而论出的“寓意”视为作者创作这一人物时的“本意”来理解,这与《金瓶梅》之张评殊为不同。
在其《金瓶梅读法》之三十六中,张竹坡有感于寓意索隐之法的得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作小说者,概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近见《七才子书》,满纸王四,虽批者各自有意,而予则谓何不留此闲工,多曲折于其文之起尽也哉?偶记于此,以白当世。[2](P47)
表面看来,张评在其谈及寓意之时强调“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指出倘若接受群体一本正经的摛词摘文,到现实与历史中“寻端竟委”并考据作者的真实面目,实有误作者本意而“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弊;但事实上,他并未在涉事人物寓意的评点过程中完全践行自己所提出的这一标准。一方面,竹坡曾指出小说评论者不应在进行文学鉴赏之时如《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评点者般进行无谓的蠡测,单凭“琵琶二字中包含四个王字”这一并无深意的文学事实便草率的将作者定为“王四”;然在另一方面,张氏在后续事关作品正文的评述过程中仍对人物所具寓意的考察颇感兴趣,甚至提出了牵强附会的“孟玉楼自喻说”,将《金瓶梅》中孟玉楼的形象特征与作者的思想意识合而论之。可以说,张竹坡只是转变了钩沉索隐之法的研究方向,更迭了在考辨文本内相关意义符号所蕴寓意时的关注点——评点者依然希望将讨论的触角延伸到文本之外,借助对小说寓意的联想来认识作者其人,只不过阐释目标由作者之身份而转为了作者之禀性。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评点者同作者的时空差异而造成的。作者与评点者所在的历史文化环境与所处的社会生活语境之间相去甚远,时空上的鸿沟使得有关作者的一切都笼罩于历史的迷雾之中;完成“补白”,令小说成为合格的史籍之附丽——这对于深受“史传”小说观影响、认定“小说当具补史之用”的中国古代文人而言实属难以抗拒的诱惑,对此张氏亦概莫能外。正因如此,其于评点中提出“寓意说”这一虽有创见亦有曲解的论点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在《姑妄言》中,这一问题不复存在。如前所述,《姑妄言》的评点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难分的关系,小说在评论与正文中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亦可谓难辨你我;在行文中,评点者完全不必花费时间以猜测、推理作者的身份和构思,而是在关键之处一笔切中肯綮,进而点明作者的用意。显然,评点者深晓作者写作的个中三昧,这一点也体现在前者对后者词句的寓意的探讨上:钝翁对自小说中采拾而出的诸多富有寓意的专属名词的解释大多可以在不加曲解的前提下直入主题,不会使读者产生误会,如其指出恶妇崔命儿其名寓指“催命”,孽子卜孝之名则实寓“不孝”等,显然就实无他解。即使个中寓意难以一参即明,评点者的解释也大多入情入理。《姑妄言》评点者在身份上与作者毫无暌隔,无需兵行弯路,结合自身的思想情趣与审美偏好去猜测想象后者于行文间所潜藏的真实意图,无形中也避免了如张竹坡般因“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之举而自行引入迂腐难解的推断曲解故事的可能。
综观整部《姑妄言》,评点者关涉小说人物寓意的评点虽每言必中,然其此类评语与其他评语相比却是数量寥寥、内容简单。显而易见,对于钝翁来说,对作者的深知实际既减弱了其猜测作者所留的那些文字所构成的“谜语”的好奇心,也使得其可以不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点破人物所具有的甚为浅露的寓意上;在评点者看来,与其漫无目的地游离于文本外、将其中富有寓意色彩的笔墨视作隐喻作者之生平经历的谜语,倒不如切实认真地进入文本中、以这些笔墨作为寄托自身评点思想的工具。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来看其在第十八卷回前评中评论书中人物“富新”的一段文字:
处处负心,才写他名字满足。富新负了司进朝,便接庞氏三妇负富新。富新因负心于司进朝而死。三妇亦因负心于富新而死,借这几个男女,骂尽负心人,尚不足为妙,又借富新之负心,骂尽明末降贼诸文武之负心者,妙极。倘有负心之人见此,当极为改悔,不身罹横祸而贻后人之笑骂也。[1](P888)
作者为书中多有负心之举的人物起名“富新”,明显是借谐音而有意暗喻;然而评点者并不借此进行漫无边际的推想,来窥探其具体影射现实中的何人或是否与作者的某些经历暗合,而是对名字中的寓意进行就文论文的解释,以此“负心”生发开去,以小见大,用类比的方式揭露出世道之中种种“负心”之人及“负心”之为,从而反映出自身的基本评点思想——对炎凉世态的切齿痛恨及对失德世人的谆谆告诫,其着重点实际上仍在文本。
反观张竹坡所评《金瓶梅》,其评点中虽然亦有如《姑妄言》般借对小说寓意的解构阐释来言说文本情节的情形,然在很多时候却总令人感觉事理扞格,时有强为之说之嫌。如其在《〈金瓶梅〉寓意说》的最后对故事结局的一番解读:
若夫玉楼弹阮,爱姐继其后,抱阮以往湖州何官人家,依二捣鬼以终,是作者穷途有泪无可洒处,乃于爱河中捣此一篇鬼话。明亦无可如何之中,作书以自遣也。至其以孝哥结入一百回,用普净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万恶,惟孝可以永锡尔类,今使我不能全孝,抑曾反思尔之于尔亲,却是如何!千秋万岁,此恨绵绵,悠悠苍天,曷有其极,悲哉,悲哉
张氏于整篇《寓意说》中都在不厌其烦的解读着小说中大小不一的人物形象的名字寓意,然而在最后却忽然接入这样一段借助情节分析而表露其对小说创作思想之理解的观点(“苦孝说”)的文字,甚是突兀。这需要我们回到评点者本身来理解这一问题。如上所述,张竹坡对《金瓶梅》作者几无了解,其对《金瓶梅》中寓意的把握不可能如《姑妄言》评点者那样准确;而张氏家世没落遭遇坎坷,自身的不幸很容易使得其在借评点以抒闷怀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经历和情绪感触糅合到对情节寓意的解读中去,“置换”掉属于作者自己可能想要在那些情节中表露的真实的想法。将语多臆断的“苦孝说”置于《〈金瓶梅〉寓意说》之尾,以愤激之论而结寓意之辩,实际上亦是这一倾向的一种表现。评点者在思想上以自我确立的“所指”,将篇幅宏富的小说中的“能指”单一化:在这里,评点并非是为了作品和作者而述,乃是为了评点者而作。要而言之,张评《金瓶梅》在言及寓意之时因其对作者的不了解(抑或不求甚解)而更多地套用自身情况来衡量小说,在文本内探究作者进而自由联想出含酸说及苦孝说等评点思想,而《姑妄言》评点则于对作品的寓意认同上实现了评作合一,并在这一基础上以更加合理的推论来结合文本演绎自身的创见。
总之,从各个层面而言,《姑妄言》评点中涉及寓言与寓意的观点全承《金瓶梅》张评而来,二者皆以评点者对小说这一文体的独到认识为基础而发端。其中,《姑妄言》评点中关于小说寓意的解释言说虽然从质量与数量上皆难望张评《金瓶梅》之项背,然其却由于评论者与作者“实为一体”的独特身份以及评论中毫无索隐联想之嫌的主旨揭示而独具特点;与在将“寓意”小说观落实到文本之时不时游离于作品之外、投目于作者性情与评论者处境的张竹坡,《姑妄言》中对物类寓意的解读少牵强附会之据、多基于文本之论。在笔者看来,《姑妄言》评点中关于寓意的诸多内容应当作为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个特例而加以重视与考察。
注释:
[1][清]林钝翁评,[清]曹去晶著:《姑妄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2][清]张道深评,[明]兰陵笑笑生著:《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3]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4]陈辽:《奇书〈姑妄言〉及其作者曹去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郭醒:《也谈〈姑妄言〉的作者“曹去晶”》,光明日报,2002年10月09日。
(董定一 吉林通化 通化师范学院文学院 13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