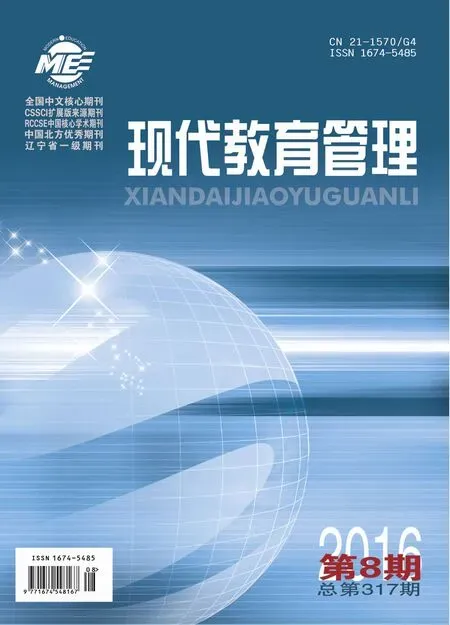“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须预防四大误区
杨兴林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100192)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须预防四大误区
杨兴林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100192)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基础。总结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扎实打好这样的基础特别需要预防四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要大力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要全面提升履行大学基本功能的水平;“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要大量增加各类学术头衔的人才;“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要全力达到有关一流建设指标的要求。
“世界一流学科”;科学研究;大学功能;学术人才;评估指标
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逐渐成为我国高教研究和实践探讨的重要主题,汲取“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就“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可能出现的四大误区及其预防略述看法。
误区之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要大力提高科学研究的水平
学术界关于学科的定义很多,但不管如何定义,作为一个知识分类和动态发展的体系,科学研究都是学科内涵中最具关键性的内容:它持续不断地为学科拓展新的发展方向,充实新的知识内容,提供新的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方法与视角,没有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科学研究,学科势将因无法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而走向没落或枯萎。作为大学的基本细胞,学科发展程度直接决定大学学术发展的程度。在这样的意义上,进行学科建设自当必须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意蕴也在于科学研究,当下我国开展“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尤其应当将科学研究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是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大国,但不是高等教育强国,特别是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相比,即使是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大学,其学科能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者也为数不多,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由此可见,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当然必须依照世界一流水准制定发展规划,创造高水平条件,营造适宜的环境和氛围,坚定不移地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1]的精神,大力激发人的创新激情和智慧,努力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但是,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的是,大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极为重要的方面,却绝非唯一方面。立足于学科的本质意蕴,学科既是一个知识分类体系,又是一个传承和创新知识的人才体系,还是一个相应的条件保障和支撑体系。在这样的意蕴基础上,我们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至少包括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术队伍、构筑学科平台、着力人才培养、开展科学研究、营造学术环境等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在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彼此相互联系和影响,共同促进或制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推进及成效。仅仅强调“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大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将学科建设内涵简单地压缩为科学研究,不仅在实践中极易导致对其他方面的忽视,而且必然严重消解科学研究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性作用。还应注意的是,立足于学科的本质意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其中居于基础地位的却是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研究,这是学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是学科实现社会功能的基本前提;一是人才培养,这也是学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更是学科实现社会功能的根本前提。二者相比,由于大学的本质功能在于人才培养,因而在学科建设中,人才培养事实上比科学研究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系一直长盛不衰,固然在于它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学术成果,更在于从这个实验室里走出了2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中有教师,也有学生,教学相长、教研相长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结合。[2]正因为人才培养在学科建设和大学建设中的突出作用,社会对大学或其学科的评价,往往也就不会刻意关注它有多少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而是特别关注它培养了多少卓越的科学家、政治家、社会管理者等。这样的大学和学科即使没有“世界一流”的标签,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
在我国高等教育环境中,学科建设意蕴往往被压缩至科学研究一项。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人们通常习惯于把学科建设等同于科学研究,将专业建设等同于人才培养,一提学科建设,第一思维指向就是加强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人才培养是“文火慢炖”的工作,周期长,成效难以即时显现,科学研究见效快,短期内即可出现明显成效,以至于现实中人们抓学科建设往往更多地倾向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则处于相对不受重视的地位。当前中国开展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从学术研究侧面看,对于如何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术人才,特别是如何开展科学研究的声音相对比较突出,而对于如何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声音却比较弱。从实践侧面看,从政府到高校对于如何加大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创造一流的科学研究条件,讨论多、行动多,对于如何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却鲜有声音。为有效避免把“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简单等同于科学研究,国家在实施“双一流”建设中,必须把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各学段的人才培养纳入建设和考评体系,不仅要强调高水平的博士、硕士学位人才培养,而且必须高度重视学士学位人才培养,将“双一流”建设与“一流专业”建设有机融合,具体实施途径上可以考虑将人才培养质量,包括“一流专业”建设质量,同时纳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申报以及获得批准单位的后续考评,只有“一流学科”建设、“一流人才”培养同时符合要求者才能够获得建设资格,或进一步建设的资格。
误区之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要全面提升履行大学基本功能的水平
大学是以学科为基本细胞构成的有机体。同样,“世界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细胞,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若干“世界一流学科”为基本支撑。2013-201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行结果显示:加州理工学院排名世界第1,它的物理学科排名世界第1,工程技术学科排名世界第4;牛津大学排名世界第2,它的5个学科领域均处于世界顶尖水平,临床预防医学排名世界第1,社会科学排名世界第2,生命科学、艺术与人文排名世界第3;麻省理工学院排名世界第5,它的4个学科领域排名均居于世界顶尖水平,工程技术排名世界第1,生命科学、物理科学、社会科学均排名世界第2。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也表明:凡进入学术水平世界前100名的大学,均有15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其中哈佛大学是22个,麻省理工学院是21个。[3]正因为学科特别是一流学科对大学的建设如此重要,所以大学建设必须从学科建设抓起,同时又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精力在优势领域建设起若干“世界一流学科”,进而整体推进大学实力的提升。对此,加州大学原校长田长霖教授受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表示:“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有后,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4]
学科在大学有机体中居于基础地位,因而大学基本功能的履行必须依靠学科的发展和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学科都必须履行大学的全部功能,或者说每一个学科都有履行大学全部基本功能的同样能力。大学是一个社会组织,需要直接对社会履行其基本功能;作为大学的基本细胞,学科是直接面向大学履行其基本功能。大学基本功能的履行,依靠自身有机体内不同学科的协同和整合;学科基本功能的履行依靠自身内部不同要素的协同和整合。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学实际运转中,每个学科的学科性质、学科体系、教学科研内容、知识生产方式、发挥社会作用的途径等差距甚大。“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学科、理工学科,基础学科不同于应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不同于传统学科。”[5]确实,大学所有学科都有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大功能,但是对于社会服务功能而言,却是不同学科间差距甚大,一些学科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所要开展的社会服务、履行的社会功能就是尽心竭力地培养人才,从事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则主要是通过努力履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来实现,一定要求这些学科直接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势必严重影响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功能的履行。理工学科,特别是工程应用学科、社会应用学科,在从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自然需要与社会和有关产业对接,既在回应社会和有关产业发展要求的过程中拓展学科发展视野,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也更好地将人才培养与工程实践、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实际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学科”对大学功能的履行一定要立足于相应学科的基本性质,对不同的学科提出不同的要求,建立不同的考评体系,绝不能不问学科特点,用同一个模式、同一种标准来处理。
我国大学由社会边缘迅速进入社会中心,从过去不太明确、不太注重研究自身基本功能,开始清楚地意识、明确、践行自身社会功能,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先导性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加之对国外大学发展经验缺乏深入了解和研究,我们在大学如何履行社会功能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识误区:一方面,在大学层面,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缺乏深入了解,将其原本先后相继、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并以实现前者为根本前提的递进关系简单地看成平行关系,甚至一些大学由于受利益驱动影响,把提供社会服务、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特别是获得较大经济利益回报置于首要地位,导致一切向钱看,严重影响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本功能的履行,其中人才培养受到的干扰尤其突出;另一方面,在学科建设层面,不仅片面地强调以科学研究为主,有些学科甚至热衷于有偿服务,获得利益回报,经济收入大小成为衡量学科发展成就的重要标尺,从而导致一些教师或研究人员把无法获得经济收入、特别是较大经济收入的学科研究弃置一边,集中精力“拉关系”、“跑路子”,争取能够获得经济利益回报,严重破坏了大学潜心治学的环境和气氛。我国推动“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旨在通过特殊的政策引导,从根本上增强我国大学的整体实力。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必须深入汲取我国大学履行社会功能的经验和教训,切实立足大学发展规律和学科发展规律发展大学、发展学科,对不同类型的大学不同性质的学科确定不同的建设与评价指标,既有效引导不同类型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在建设过程中更好地履行其本质功能,又推动两个“一流”建设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误区之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要大量增加各类学术头衔的人才
学科建设,学者为先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学科水平直接取决于学科队伍的水平。如上所述,在上海交通大学201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哈佛大学有22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而它的2259名教师中,拥有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头衔的教师达300余人。哈佛大学在其数百年的辉煌生涯中,教授团队中共有44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同样,在2013-201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行榜中名列世界第1的加州理工学院,在20世纪20年代初尚无名气,之后它从芝加哥大学引进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担任物理学科带头人,引进前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著名化学家阿瑟·诺伊斯开办化学系,引进现代航空航天工程学先驱西奥多·冯·卡门负责航空航天科学及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建设和研究,引进天文学家乔治·埃勒里·海耳负责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威尔逊山天文台建设。这些学术大师的加盟使加州理工学院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正因为学术精英和学术大师对学科建设的作用如此重要,世界一流大学校长都对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哈佛大学第21、23、25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科南特、博克曾分别指出:“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教师”;“大学者,大师云集之地也,如果学校的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要使我们学校经常居于前列,归根到底是要有好的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也曾言:“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聚焦于此的教师和学者的质量,而不应取决于数量,更不能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6]
学术精英和学术大师是学科建设之魂,但是学科建设的长足发展却绝非仅靠一两个学术大师能够实现,尤其需要有高水平的学术团队为其坚强后盾,这在当代科学发展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背景下尤其重要。这样的学术团队不仅要有学术功底深厚、视野开阔、具有学科发展战略思维的大师充当学科带头人,而且要有学术功底扎实、学术能力出众的专家、学者充当各个方向的带头人,更要有适宜数量的学术精英成为各个方向的重要支撑及开拓力量。团队“将星”云集,学术功底厚、素质好,容易造就学术发展的“高原”,高水平的学术大师则独具慧眼,把握学科发展的时代脉搏,立足团队实际,为学科开辟出可持续发展方向,推动学科由高原走向顶峰。这样的学术团队,成员的学术职称、年龄结构应有相应的梯级安排,能够保证不同职称层次和年龄层次成员的智慧多元化、多样化,发挥最佳整体效应,更能保证学术事业发展“江山代有才人出”,薪火相传。这样的学术团队,学缘结构应当且必须多元化,有来自于不同大学、不同学派的学术成员,这样思维方式、学术眼光、研究专长、行事风格便各有特点,极其有利于推动团队多视角、多方位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形成活泼、多向的思维风格和学术风格,易于在学习、借鉴、汲取其他大学、学派研究成果及其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打通与有关学科的内在联系,推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毕竟“今天,科学中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是在学术院系和传统学科之缝隙发生的。一个一流的物理系可能受益于一个较低级别的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考古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系”。[7]这样的学术团队是在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引导下,经过多年反复磨合的结果,没有较长时间的彼此磨合,成员与成员之间、方向带头人与成员之间、学科带头人与方向带头人以及所有成员之间就不可能达到相互默契,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国自20世纪末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来,高等教育界逐渐普遍认识到“世界一流学科”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工程,进而围绕学术队伍建设、研究经费及重大课题、研究平台建设等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985工程”、“211工程”大学建设,包括部分地方重点大学建设,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整体上提高了我国大学的整体实力,但是在诸如学科发展方向凝聚、学科方向提炼、汇聚学术队伍、学科发展平台建设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和误区。其中,汇聚学术队伍方面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求名重于求实。一些没有院士的大学普遍采取所谓的“双聘”形式,名义上受聘院士每年到受聘大学全职工作若干个月不等,事实上聘书、仪式、丰厚的待遇是一回事,到受聘大学全职工作相应时间的要求却始终不能落实。一些大学从国外聘请教授作为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同样是有聘书、有仪式、有丰厚的待遇,全职工作的时间同样大打折扣,有的甚至根本不来校工作。二是重人才引进轻工作条件配备和完善。一些大学积极引进各种称号的学术带头人,人才引进来后,却不能提供相应的科研平台,人才作用无从发挥,有的人才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开。三是重人才吸引轻团队建设。有的大学往往集中引进人才,大打人才争夺战,一时间人才引进不少,却不注重引进人才与原有人才之间的融合,特别是过于重引进人才,轻原有人才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导致“引来女婿气死儿”,不仅没有增强团队凝聚力,反而加大了离心力。面对这些问题,我国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首先必须注重汇聚学术队伍,但是必须尊重学术队伍的汇聚和建设规律,高度重视不同级别、不同学缘、不同年龄人才的按需引进,建立合适的学术队伍结构;其次是要高度注重学术队伍的磨合与调适,营造适宜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使学术队伍发挥出整体最佳效益;第三是特别要注意引得适用,人才与岗位要求相适,绝不能为数量而数量,为引进而引进,浪费学科建设的宝贵资源。学科建设是系统工程,必须按照系统工程的要求系统推进,在高度重视学术队伍建设的同时,科学确定学科定位及其发展目标,立足具体学科的本质及其规律开展科学研究,特别是要善于通过适当的大课题锻炼队伍。平台建设则既要保持先进性,又要坚持节约原则,当下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政府支持经费比较充足,一些学校于是出现了为购设备而购设备的极不正常现象,导致大量设备从购进之日起就闲置,严重浪费国家钱财,这样的所谓“建设”在当下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应当得到有效避免。
误区之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就是要全力达到有关一流评估指标的要求
在时间维度上,“世界一流学科”是继“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出现的概念。对现实的中国而言,无论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都是基于学习、追赶“先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就国际范围看,20世纪中后期,欧美一些国家曾先后提出和建设“一流大学”。自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发布第一个大学排行榜以来,现在国际范围内已有包括“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四大最具影响力的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全球性排名。其中,关于“世界一流学科”的评估主要是对学术声誉、雇主声誉、论文引用率的把握。国内有学者提出,应考虑一流学者、一流学生、一流科学研究、一流学术声誉、一流社会服务5个方面。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下简称《方案》)中有关我国“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改革的任务共计10项:建设一流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环节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概括10项任务,其中反映“世界一流大学”及“世界一流学科”特性的一般内容大体有一流师资队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水平、优秀文化传承、科技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与合作6项。“大学是花钱的,好大学是很花钱的”,[8]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当然需要花很多的钱,这样的钱在我国大学现行经费筹集体制中主要依靠财政投入,正因为如此,国家对“双一流”建设明确任务或标准,并且据此严格考核,自然有其充足的理由和根据。所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重点是要完善学科评价与动态调整机制”,“提高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和公信度”。[9]
但是,客观而言,“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既有可明确考核、评估的一面,又有不可明确考核、评估的一面,因而在建设和评估中一定要两方面同时兼顾,绝不可“单打一”。言其有可明确考核、评估的一面,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科学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门别类地解剖,通过严格的考察得出比较清晰的结论。对于“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人们同样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不管那些被称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学科有何不同,或有多少不同,研究者总可以在一定的理论视角下将它们的内部结构、要素等一一区隔开来,逐个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解剖、观察和研究,进而将体现“世界一流”的所有元素集中起来,进行仔细比较、对比和筛选,最终获取“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共性元素,这些元素由于抽去了各个“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特殊性而具有一般的、普遍的意义,因而可以为“后发”国家的大学学习、借鉴、建设和评估提供一个比较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另一方面,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一些大学、学科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世界一流”,往往可能是由于某些比较特殊的原因,如一些是由于教授水平高,一些是由于学习和研究的人特别多,一些是由于毕业生出路好、薪酬高等,这样的标准尽管特殊、充满个性,却可以从某个层面进行相对精确的比较和评估。言其有不可明确考核、评估的一面,一方面是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概念的由来,最初并非依据什么精确的指标评估而得出,而是因为这些大学、学科在长期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科技精英,在自然科学领域或社会科学领域,抑或在两个领域,同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世人心目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印象,进而成为世界各地莘莘学子崇尚和向往的学术圣地。显而易见,这类源于人们心底意会的标准实在难以用精确的指标来衡量。另一方面,任何大学、学科的育人都不仅仅在于教会学生谋生的技能,还必须高度注重社会伦理价值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感,而这类教育的水平和程度,事实上也无法用精确的指标来度量。
立足于“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上述特点,《方案》确定的相应建设要求,不妨可以称之为明确的建设、评估标准或硬性的建设、评估标准,而隐含于这类明确标准或硬性标准之内的伦理价值取向、各种特质则是相应的模糊标准或柔性标准。前者建立在归纳、概括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基础之上,具有重要的一般意义和定量意义,后者旨在注重挖掘硬性标准背后的深层价值意蕴以及不同大学、不同学科的特殊意蕴,具有特殊意义与定性意义。从根本上说,我国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当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先发”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展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多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在学习“先发”国家经验时,往往容易照搬外显指标,对于蕴藏其中的价值伦理、文化追求等往往不闻不问,以至于仅仅搬来现代化的“躯壳”,却没有学到现代化的真谛。汲取这样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务须高度重视认识和把握两类指标之间的关系,既抓明确指标,又抓模糊指标,绝不能仅仅聚焦明确指标,轻视模糊指标,甚至于只抓明确指标无视模糊指标,最终导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有硬件无软件、有学术追求无伦理追求。至于明确指标的次级指标体系则必须易评估、易操作,能够为实际的建设提供清晰导向,但对模糊指标而言,由于其模糊性,需要人们通过对其相关侧面细致的观察来体会,不宜设置过细的次级指标体系,但应当将其作为明确的价值导向贯穿其中。还应强调的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高度学术性、专业性的工作,应当更多地尊重学术权威、学科权威,行政权力、行政权威需要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和评估提供必要的、适时的服务,却不能够任性地施加不当的影响和干预。
[1]江泽民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0.
[2][5]胡娟.如何认识和评价世界一流学科[N].光明日报,2016-03-29(13).
[3][6]徐翠华.英美一流高校的学科建设启示[J].江苏高教,2013,(6):155-157.
[4]杨玉良.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有关问题的认识[J].中国高等教育,2009,(19):4-7,19.
[7][美]达里尔·E·楚宾·爱德华.J哈克特.难有同行的科学:同行评议与美国科学政策[M].谭文华,曾国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1.
[8][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9.
[9]张伟,徐广宇,缪楠.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潜力与对策[J].现代教育管理,2016,(6):36.
(责任编辑:徐治中;责任校对:于翔)
Four Aspects of Misunderstandings for Prer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First Class Discipline
YANG Xinglin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Beijing 100192)
As a whole,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first class disciplin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first class university.By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to play a good basis of this work must prevent four aspects of misunderstandings especially,there are: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first class discipline i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i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arrying out university basic functions,is to have a large increase of talents with all sorts of academic titles,i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relevant index of th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world first class discipline;scientific research;university function;academic talents;the index of evaluation
G640
A
1674-5485(2016)08-0014-06
杨兴林(1958-),男,湖北房县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