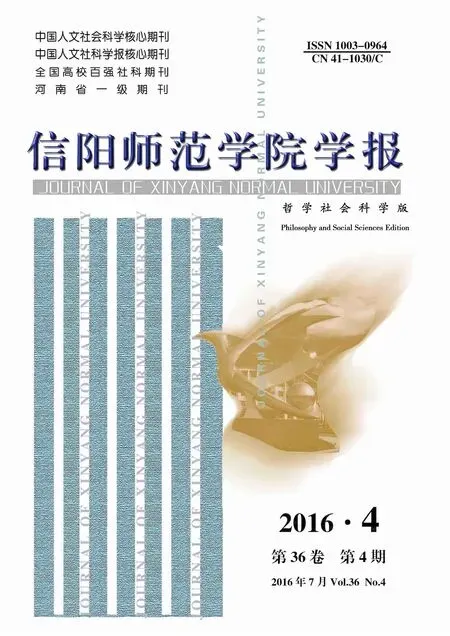《论语》之“学”探析
刘 寒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
《论语》之“学”探析
刘寒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论语》之“学”在内容上包括文、行、忠、信;在方法上要求学与习相结合,学思并重;在目的上强调“学以致其道”。《论语》之“学”本质上是“为己之学”,它具有文化传承意蕴,同时,其内涵和“为己之学”传统都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论语》;学;为己
“学”是《论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在《论语》中共出现64次(笔者与杨伯峻先生统计数字相同)。钱穆先生曾讲道:“孔子一生为人,即在悦于学而乐于教。孔子之自居,在学在教,不在求为一圣人。”[1]1“好学”是孔子极为看重的品质,在他的所有弟子中,只有颜回被他赞为“好学”,而他自身也以“好学”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①(《公冶长》)此外,在孔子看来,“学”是一切德行的基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学”在《论语》和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论语》之“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学”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内容上看,它是对文、行、忠、信的学习;从方法上看,它强调学与习相结合,学思并重;从目的上看,它强调“学以致其道”。
(一)“学”的内容:文、行、忠、信
《述而》篇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同时也是对“学”的内容的集中概括。
第二,“行”。此处所谓“行”,主要指德行,也指社会生活实践,而当时的社会实践主要指包括了狭义的礼乐活动和射御之法在内的礼乐操演。
第三,“忠”。这里的“忠”似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忠恕”之“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为仁之方”。另一层含义则指“与人忠”之“忠”,即曾子所说的“与人谋而不忠乎”的一种品德,指忠诚[2]154。
第四,“信”。“信”是针对“言”而说的,强调在与人交往中,要言而有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民无信不立。”(《颜渊》)
不难看出,在内容上,《论语》之“学”是德行与学问的统一。而在二者中,德行为本,文艺为末。例如,孔子强调“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孔子赞颜回好学乃因其“不迁怒,不贰过”(《雍也》)等,这都表明“德行”在孔门之学中相对于“学文”更具根本性。当然,在立德、成德的最终意义上,二者是一致、不可分离的。正如朱熹引用洪氏所言:“未有余力而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不学文,则质盛而野。”朱熹也说:“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3]51近人钱穆也认为:“弟子为学,当重德行,若一意于书籍文字,则有文灭其质之蔽。但专重德行,不学于文求多闻博识,则心胸不开,志趣不高,仅一乡里自好之士,无以达深大之境。”[1]10欲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成圣成贤,德行与学文缺一不可,但如若二者不可兼修,则以行为本,文为末。
(二)“学”的方法:学与习相结合,学与思相并重
一是学与习相结合,即读书与实践相结合。习,有实践、演习之义,而不仅指复习。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程子解释道:“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悦。”[3]49另外,孔子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所谓“博学于文”即对诗书礼乐、典章制度、著作义理等的学习,博学始能会通,然后知其真义。“约之以礼”一方面有“由博返约”之义,一方面也有“以礼约文”之义,“以礼”指代躬行践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博文与约礼要齐头并进,相辅相成,意指读书与实践相结合,正如颜渊所叹:“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
二是学与思并重。《论语》中强调学与思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学,是吸收积累的工夫,思,是消化贯通的工夫。学而不思,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所以孔子虽教人“博学于文”,但亦告诫人“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这阙疑、求证验,其实就是思的作用。当然,思的工夫不止于此,它还须由已知以求未知。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为政》),“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以及子贡“闻一知二”,颜子“闻一知十”(《公冶长》),都是经由思考而获得的结果。一个人如果不思,便不可能有推理的能力。所以孔子对于“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人,不愿再予教诲[4]44-45。一方面,思考必须在知识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可以凭空冥想。思而不学,不习其事,则事无征验,疑不能定,危殆不安。因此《论语》中强调学思交修并进。仅学不思,将失去自己;仅思不学,则把自己封闭孤立了。学思并重,交互为用,才是切实而完整的求知之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孔子之学基本上是做人之学,因此孔子所谓“思”,基本上也是有关宇宙和人生的智慧之思,强调体悟,而不是单纯的对象思维。
(三)“学”的目的:“学以致其道”
竹叶青酒是以中国清香型名酒——汾酒为基酒,以竹叶、当归、陈皮、栀子、砂仁、檀香、丁香等十余味名贵中药材的浸泡液为基础配制而成的一种露酒。常年适量饮用,可以达到调和脏腑、疏气养血、消火消痰、解毒利尿、健脾滋肝等功效,曾被国家卫生部连续3次颁发“中国名酒”称号。竹叶青酒酒体稳定,金黄微翠,清澈透明,具有药材芳香并兼有汾酒清香,诸香和谐,入口甜、落口绵、醇厚爽口、余味悠长。前期相关研究主要是对竹叶青酒功能研究和化学成分含量的分析,而未涉及竹叶青酒的气味特征的分析。
作为“一套兼含内圣外王的生命的学问”[4]14,儒家之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经验知识的获得,而是德行的提升和自我修养的完善。孔子并不排除知识和技艺的学习和掌握,如他也主张“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但他更强调“君子不器”(《为政》)。他认为,士人的本分更应是学道,如子夏所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学以致其道”是《论语》中对“学”的目的的最高概括。
孔子之学最重在道,主张“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学而》)。这里的道,即做人之道。孔子常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礼等行为规范及做事的规则当作道,但孔子之道,更是指礼乐之“本”——“仁”。他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另外,孔子所讲的人道与天道相通。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强调君子应知天命并自觉完成天命。所谓天道、天命,是指创生万物的天地的“生生”价值,在人身上体现为向善的目的性,赋予人成己成物的使命,这即是天命。天道、天命都是通过人的德行来实现的,这就凸显了“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孔子将人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季氏》),绝大多数人都非“生而知之”,因此就需要通过“学”实现“下学上达”,由学人事进到知天命。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皇侃《义疏》云:“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5]177如钱穆所言:“一部《论语》,皆言下学。能下学,自能上达。……故圣人于人事能竭其忠,于天命能尽其信。”[1]383即“学”架通了人道与天道之间的桥梁。联系“学”的方法,我们可以说,“学”是“知道”的过程,“思”是“化道”的过程,“行”则是“成道”的过程。
二、《论语》之“学”的本质:“为己之学”
在《论语·宪问》篇,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构成了《论语》中关于“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尽管历代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6],但儒家“为己之学”的传统却得到确认,孔子也被指认为“为己之学”的开创者。
所谓“学者为己”,通俗来讲,就是学问是为了自己。但这并非是自我中心主义或个人利己主义。这里的“己”是自我,但“不是一般的自我,而是作为此时此地体验着和反映着人的自我”[7]54,是承载着天道和人道的“人”的具体体现。这个“己”是一个道德自我,“为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也不是为了个人客观知识的丰富和增加,而是为了作为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的提升和完善。因此所谓“为己之学”,笼统看来,就是修身之学,德行之学,与儒家重德行伦理的一贯价值取向相契合。
此外,要对“为己之学”做深刻透彻的理解,还须明了“为己”与“为人”的关系。对此,自先秦以来,学界就有不同理解,大致可归为以下两类。
一是以“为己”彻底否定“为人”。持此种解释的学者,多把“为己”理解为自我的完善,以内在性情为旨归;把“为人”解释为沽名钓誉,取悦于人,显己于世。因此,“为己之学”呈于内心,显于行动;“为人之学”则留于口头。如《荀子·劝学》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汉代的孔安国则简洁地注解:“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朱熹引程子言:“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杨伯峻解释为“古代学者的目的在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等等。这种肇始于荀子、集大成于朱熹的解释思路,随着朱学的兴盛与传播而被众多学者认同、接受。这一解释的实质在于强调为学应追求内在的精神价值,内在德行的完善和人格的完满,反对驰骛于外,追求外在的名利。
二是以“为己”为本,以“为人”为末,但对“为人”并无贬斥之义。这多是在儒家成己成物、内圣外王框架下给予的解释,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中载二程之言:“‘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8]325另有学者将“为己”“为人”分别对应于内圣、外王,甚至还有人将“为人”直接等同为“治国平天下”[6]。钱穆则认为:“孔子所谓为己,殆指德行之科言。为人,指言语、政事、文学之科言。孔子非不主张学以为人,惟必有为己之本,乃可以达于为人之效。……己立己达是为己,立人达人是为人。孔门不薄为人之学,惟必以为己之学树其本,未有不能为己而能为人者。”[1]374这种解释并不反对“为人”,但强调“为人”要建立在“为己”基础上,不能脱离为己而追求为人,否则就会失去根本。立己才能立人,达己才能达人。
本文认为,以上两种基本解释框架都有其合理性,在不同层面上契合了孔子真意。第一种解释是在为学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上道出“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别,强调“学”的内在指向性;第二种解释是从为学的效果和落脚点上道出二者关系,更为注重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并将为学的外在指向统一于其内在指向。据此,本文认为,对孔子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可作如下理解。
首先,为学的目的(“学以致其道”)具有内在和外在的双重指向性。其内在指向追求内圣、成己、立己达己,其外在指向追求外王、成物和立人达人。儒家向来以强烈的心系天下之道德情怀而著称,由内圣而达外王,由修身而至家齐、国治、天下平是历来儒者的追求。《论语》中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都表明了其内圣之学的外王之义。
其次,从为学的动机和评价标准看,学应该旨在提升和完善自身的德行,而不是追求外在功名利禄。因此,对“己”的评价也应以自身修养是否提升为标准,而不是以外在评价为导向。“君子求诸己”“不病人之不己知”“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不患莫己知”等表述都体现了这一点。
再次,从为学的过程来看,自我总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求学,不可能脱离社会,因此无论是经验知识的获得,还是道德修养的提升,都不可能完全局限于“己”的范围之内,“为己之学”并非与他人无关。
最后,从为学的效果来看,学虽然不能以外在利禄为追求,但“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即“禄”是“学”的自然结果,同样,所谓名利也会是“学”的自然结果。
三、对《论语》之“学”的评价
如上所述,《论语》之“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本质是“为己之学”。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做出评价。
第一,《论语》之“学”的文化传承意蕴。朱熹将“学”解释为“效”,即后觉对先觉的效仿,而《论语》中尤为强调对古人尤其是古之圣人、贤人的效仿,强调对古代文献的学习,这种“学”对于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论语》之“学”本身,尤其是其所开创的儒家“为己之学”的传统,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大民族特色。从这一意义上讲,即便我们不能直接将其应用于现代社会,《论语》之“学”也有其内在的文化价值。
第二,《论语》之“学”的现代意义。首先,从“学”的内容上来看,《论语》之“学”或可相当于现代社会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内容丰富的人文教育。其很多教育内容在今日看来仍有意义。《论语》之“学”重在学为人之道,有助于促进个体的社会化,使人成为真正的社会人。虽然《论语》之“学”从本质上讲是“为己之学”,但在其内圣外王的致思趋向下,它由德行推出德治,因此并未丧失其社会意义。而这一点与当今的通识教育、公民教育旨在将人培养成合格的公民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可引发深思。其次,从“学”的方法上看,《论语》之“学”强调学与习、读书与实践的结合,实已具备知行合一之义,对当今从实践中学习,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的培养不乏启示意义。而强调学思并重,也启示我们应注重知识的内化,而这恰是知识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于知识创新也具有启迪作用。再次,从“学”的目的上看,《论语》之“学”强调“学以致其道”“下学上达”,将人道与天道相结合,其实内含“天人合一”的观念,这对于提升今之学者的学习层次和境界不无裨益。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所谓“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观念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生态的观念、人和自然应该有一种持久和谐的关系的观念完全相配。这种深具强烈的历史感和超越感的主体性,代表着一种非常全面的人文思想。这种人文思想一直是中国哲学界、也是中国文化界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传统[9]89。
第三,“为己之学”的当代启示。首先,孔子“为己之学”彰显了人(自我)的道德主体性。在孔子之前,人一直处于天、神之下。在周公那里,人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在孔子这里,人的地位则真正完成了转变,人被提升至载道、弘道、成道的极端重要的地位。孔子把道德问题的重心放在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上,强调一己之德的至关重要性,高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不啻一种“道德革命”。狄百瑞就曾指出儒家的为己学说包含着“自我的觉醒”“独立的判断”等观念[10]20。不过,作为成德之学,“为己之学”偏重于道德理性和道德主体,对认知理性和认知主体则缺乏必要的关照,这不失为一种缺陷。其次,“为己之学”对于个人在社会中修身具有启发作用。如前所述,孔子所谓“为己之学”并非与他人无关的修养之学,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进行。当代人的社会性得到空前彰显,这一方面并未取消个人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赋予个人修养以更大的社会空间。个体道德修养离不开其社会化过程,愈发凸显了《论语》中“忠恕”等交往原则的现实意义。同时,“为己之学”对个体社会责任的强调,是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统的思想源头,对于当今学者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再次,《论语》中的“为己之学”有将外王内含于内圣的倾向(这一倾向后来得以强化,尤其是在宋儒那里)。也就是说,孔子倾向于认为,外王可以由内圣直接推出来,是内圣的必然结果,然而,事实上,内圣只是外王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国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没有开出客观法制化的‘政道’,中国文化也没有充分透显知性主体,所以外王之道一直未能获得充分的完成”。因此,“当前儒家第三期的文化使命,除了内圣成德之教的承继与光大之外,主要就是集中于开出新外王(含政治、事功、知识三层),以期‘内圣外王之道’中的‘外王’一面,亦能如同‘内圣’一面之充其极”[4]48。
不过,虽然内圣未必能开出外王之道,但内圣始终是前提,是基础,不可或缺。其现实启示就是,自我道德修养虽然不足以支撑个体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德治也不足以支撑一个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但德行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德行本身也已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论语》中的“为己之学”所强调的德行或可成为政治伦理的重要基础,为法治中的平等原则增添新的内容。其德行学说中的人文因素,也能够全面提高人的道德素质,特别是执法者的道德素质,从而保证法律能够公正而有效地得到实施。而文质彬彬、德行与才能兼修的儒家君子的特质对当前人才培养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之,《论语》之“学”虽然与现代社会不完全匹配,但仍不乏启示意义。孔子对君子、圣人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为己之学”和修身之道的强调,能够对缺乏价值信仰和追求的现代人类寻找精神家园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也能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培育贡献道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治的“道德空白”。
注释:
①文中所引《论语》具体篇章均出自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
参考文献:
[1]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蒙培元.蒙培元讲孔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蔡仁厚.孔孟荀哲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6]肖永明.对《论语》“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与宋代儒学的内倾[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4-38.
[7] [美]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M].曹幼华,单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8][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杜维明,范增.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 杜维明 范曾对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蔡宇宏)
收稿日期:2016-03-23;收修日期:2016-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ZS027)
作者简介:刘寒(1988—),女,山东菏泽人,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6)04-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