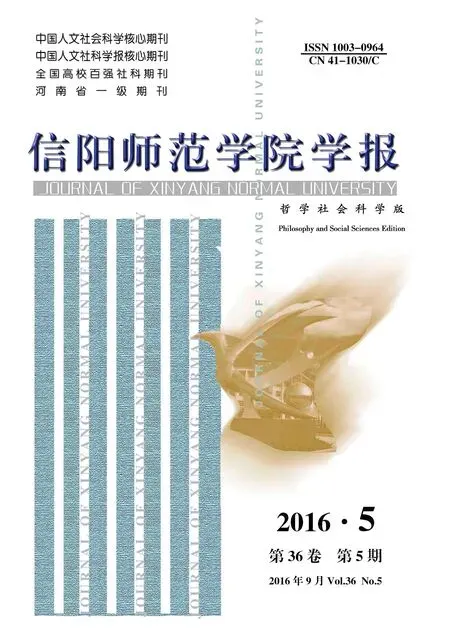性别视域下的“文革”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作家笔下的“文革小说”①研究
董 琼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文学研究·
性别视域下的“文革”叙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作家笔下的“文革小说”①研究
董琼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从一贯的男性话语遮蔽下呈现女性的生存经验并由此延伸对历史的不同把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鲜明姿态。这一时期的女性更注重挖掘革命历史话语背后女性在历史及现实中的真实处境、欲望及心理。在她们笔下,不仅“文革”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而且也是女性寻找自身合理位置,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完成女性作为女性的历史存在的主动与自觉。
“文革”叙事; 女性 ;话语权威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写作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起,女性与男性作家一道,将被“文革”禁锢了的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人对自我的发现重新点燃和接续上了的话,那么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到来,女性更注重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及革命历史话语背后女性的自我发现。和80年代女性“文革”书写的相对沉寂不同,90年代以来女作家表现出“文革”书写的热情,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洁的《无字》、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池莉的《所以》、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魏微的《流年》、徐坤的《野草根》、黄蓓佳的《所有的》《家人们》等等。这些小说基本从“文革”延伸到当下,显示出女性特有的细腻体验与女性驾驭历史叙事的能力,也体现出女性言说自我、反叛政治话语权及男性话语权威和建构自身历史的从容与自觉。
一、探寻“文革”背景下女性生存的合理位置
新时期以来,在反思历史苦难、呼唤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感召下,女性写作基本被纳入到男性话语规范,作为女性的特殊部分即她对男性的另一种性别体验却无法凸显。虽然不乏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张洁的《方舟》等作品,作家在历史的反思背后意识到女性存在的尴尬与无奈,并由此探讨被政治生活和主流话语所压抑的女性的合理位置和正常欲求,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反思基本停留在男性所认可的价值规范内,女性作为特殊历史存在并没有彰显。如在《人到中年》中作家对陆文婷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命运的强调,在《方舟》中三位女性基本放弃了家庭生活,包括女性欲望及日常体验在内的女性独有的气韵也没有展示。值得一提的是王安忆,在早期发表的《流逝》中,“文革”的日常遭遇让一个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变成了操持家务的主妇,小说从细小处发掘宏大政治背景下平凡人物的酸甜苦辣,充溢着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创作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透过特殊年代女性更为隐秘的性欲情爱的描写,展露“文革”禁欲背景下饮食男女世俗欲望的潜在影响力。不过,作为女性生命体验中需要正视的部分,王安忆却有意识地将它们设置在“荒山”“小城”上演,表现出女性对自身体验缺乏坦然的直视。及至铁凝的《玫瑰门》,小说从文化的、权力的、人性的角度反思“文革”政治对人性阴暗面的催生和放大,开辟了一个女性自审与审视历史的领域,可以说是对“文革”题材的重要开拓。
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历史反思的深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以更自觉的性别意识重新思考“文革”背景下(女)人的合理位置以及如何生存的问题。如这一时期王安忆的《长恨歌》,王琦瑶历经半个世纪的历史变革,作家刻意回避历次革命运动和政治暴力对现实人生的冲击,但这不等于作家就此抛开了历史,而是以一种日常化的叙述,将记忆中上海人的真实生活及文化娓娓道来。王琦瑶们“围炉夜话”,讲故事,猜谜语,漫无主题地聊天、吃饭、搓麻将,比起宏大高远的政治理想与革命激情,这些日常琐事凡俗不值一提,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则更贴近他们的心声,代表着真正日常化的市民形态及生活状况,也由此揭开另一种文化层面的真实,或者说一种底层市民生活的真实。这一日常化历史的写作态势是对新时期以来过度历史化所带来的过分注重群体思想情感和历史决定论的“原则”和“理性”倾向的批判与反思。透过日常生活的一以贯之,小说流露出的不再是单一刻板的政治文化,而是将个体融入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将生活演变的过程融入对历史演变过程的叙述,以此实现个体生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存状态及精神境界的深度开掘。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女性往往是沉默的、被书写的,很少作为主体存在。严歌苓的历史叙事不刻意于历史本身,而是凸显历史进程中女性特有的生活状态及体验。重大历史事件不再作为特别表现的对象,而是作为背景,小说在洋溢个体生命体验的同时,也成功构筑起女性在历史文化中的真实感受与处境。如《第九个寡妇》中,作家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末到80年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一个普通乡村女子的命运变迁。尽管历史给王葡萄贴上了众多时代的标签,她却以女性的生命本能及从容豁达姿态甘愿生活在主流历史之外,然而也正是王葡萄的“落后”与“一意孤行”才使得历史更富有色彩与人情味。在《小姨多鹤》中,作家摹写了一个身份暧昧的日本遗孤在当代中国曲折跌宕的日常生活传奇。她的身份非妻也非母,在政治主导一切的特殊年代里,她隐忍执着地闯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怀疑的眼神,将自己融入日常琐碎中努力地活着。她真实而鲜活,展现出女性主体强韧的生命力及女性建构日常生活传奇的可能与可行。而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作家直视“过日子”的生存哲学,在母女俩琐碎而踏实的日常生活潜流中,轰轰烈烈的革命政治已然变成了生活的背景,由此彰显历史变迁下女性独特的生存姿态与生命体验。
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自觉,女性参与历史的决心,要求女性摆脱主流意识及男性话语的束缚与“他者”地位,呈现出女性在历史及现实中的真实处境、欲望及心理,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自觉完成女性作为女性的特殊存在。如果说新时期以来,启蒙及精英话语构筑的宏大叙事更多表现的是男性的话语立场和规范的话,那么由日常生活构筑的小叙事所带来的宏大眼光让我们看到近年来女性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不仅如此,这类小说基本将女性置于社会文化环境的整体考察,直视女性自我的生存处境与生命体验,从文化、文本语境中探寻女性历史话语叙述的权威,在女性作为“个人—女人—人类”的生命体验的升华中重构女性历史。这也是90年代以来女性主体意识张扬的必然结果。
二、凸显“文革”背景下女性个体的隐秘成长体验
只有历经岁月的洗涤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个体的生命也只有到了“讲述话语的年代”才得以显露。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开放性的时间场域对“文革小说”的生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同于80年代集体化的悲情控诉,以私密的女性话语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成为90年代以来女性特有的叙事基调。
尽管林白将小说命名为“致一九七五”,其中也不乏关于革命、青春的写作母题,然而她有意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整部小说充溢着李飘扬的内心独白,侧重的仍是女知青个体的真实体验。林白曾说:“我选1975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标志性……1975年只是‘文革’后期的一个平凡年份。所以‘一九七五’揭示的是革命年代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1]林白既不愿将小说简单地看作一部“文革小说”,也不愿割舍这段岁月中的隐秘生命体验,于是,“一九七五”成为她刻意凸显“文革”政治背景下女性隐秘历史的有意为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林白尽管摆脱了以往过于狭小的私人话语,将视野投向了更为宽广深远的历史及生活场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彻底放弃了个人的“私人空间”。小说所塑造的那个时代的红卫兵及知青,同以往及同时期其他小说中所塑造的形象相比,虽同属于一个谱系,却呈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林白对总结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没有太大的兴趣,她更愿意将个人化写作与女性自我的历史观结合,完成新世纪以来女性隐秘历史的重新建构。
剥开革命的宏大外壳,立足于历史纵深处女性的“隐秘的深处”和“重要的瞬间”,不啻为女性打破男性话语秩序还原女性历史的一种手段,而在徐坤的笔下,同样书写个人化的“文革”历史,我们则看到女性有意识地反思与批判男性话语、建构女性自我声音的努力。作为徐坤唯一一部以第一人称书写的自传体女性成长小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通过一个叫徐小红的女性视角,展示了男性视域下女性作为文化的“他者”所受到的歧视,以及隐含在作者操纵下的叙事者建构女性意识及自我声音的历程。小说共分8节, 作者从10岁的“我”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游行开始追溯,回忆童年时期当苗子的辉煌时刻,然后笔锋一转,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为线索,讲述了大学课堂里“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故事和在乡下遭到嘲笑的故事。文中的故事平平常常,然而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正是作者构筑女性自我声音的一种尝试,它随意而感性,犹如拉家常,却在不经意间解构了传统的男性话语逻辑方式,呈现出女性特有的话语表达方式。2006年徐坤又创作了《野草根》,小说同样跳出了传统叙事对知青人生的宏大历史反思,以速写的方式讲述了三个女人纤弱而挣扎的人生。小说也不乏历史与主人公经历的描写,然而社会、男性及家庭对女性的规避,就像让野草生长的风雨,并没有刻进她们的心里。只有当女性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作为女性的生命时,女性才真正复活。是生命都有自己的境界,小说让我们体验到“自然人”升华为“生命人”时那种纤弱又猛烈的震动,而这无疑是属于女性自己的生命颤动。和这一体验合拍,小说在形式上就像一部三幕剧:《引子》和《尾声》犹如历史与现实的双括号,内里则上演女性短暂而激烈的生命历程。这一话剧式的选择将“史诗”中常见的细密的历史叙述,转换成剧中的“话外”,它们犹如影子伴随着女性的一生,而真正影响女性的却是女性自己。这一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显示出作者建构女性个体成长体验的某种努力,也使得徐坤在对“文革”的书写中独具特色。
三、彰显历史苦难的诗意关怀
对“文革”历史形态的提取与选择,缘于作家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深刻把握。对于书写苦难,迟子建认为:“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我相信这种力量是更强大的。”[2]所以,无论是《北极村童话》《花瓣饭》,还是《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既听不到揭露控诉的声音,也看不见感伤愤怒的情绪宣泄,即使对待《越过云层的晴朗》中遭到世人唾弃的梅红,作家依旧给予了相当的关切与悲悯,尽管其命运悲惨孤寂,却同样彰显出生命的亮色。而在更年轻一代作家魏微的《流年》中,作者也善于用婉约优美的笔触将童年记忆中的“文革”逐一还原,描绘出一幅泛着晕黄的温暖底色的印象画。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阳光”温暖着“我”的童年记忆,政治让位于生活的逻辑,“我”也幸运地在历史的夹缝中完成“个人记忆”的美好成长。不仅如此,小说以童年人的视角触摸“文革”,寻找着生活的本色:喧嚣的政治抵不过“过日子”的深沉厚重。小说叙写了“微湖闸”的世外桃源,但也没有掩盖生活带给人们的五味杂陈,在温暖的亲情背后,同样充满着令人尴尬的皱褶与破败。然而作者朴实无华的细节描写、清朗呢喃的低语陈述,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庸俗而是诗意,不是彻痛而是感伤。同样,在《美哉少年》中,叶弥也向我们展示了“文革”背景下找寻精神家园的成长命题。小说中的主人公李不安,“文革”浩劫带给他的是身心的疲惫与美好家园的缺失。没有人知道孩子内心的隐秘感受,也没有人能明白,在面对父母的沦丧时他被击垮到何种程度。然而在成长的苦痛中李不安并没有放弃寻找的意义。小说尽可能地借人物自己的行为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人物心态及找寻精神家园、寻求精神救赎的成长蜕变。叶弥没有将成长的悲剧留给读者,也没有放弃追寻的意义,而是以女性特有的温存和无私的关爱理解着人生,诠释着成长。在她看来,灵魂的找寻与诗意的栖居显得更为重要。
在女性看来,以诗意的方式承载苦难,并不是忘却苦难,而是试图以积极向上的情感指向完成对现实的整合与超越。既然苦难是人生无法逃脱的生命悲剧,我们又何妨用一双善良的、宽容的眼睛来看待它?有意思的是,这类小说基本都选用了动物的、儿童的纯然、感性、未经世俗濡染的视角来呈现成人的“文革”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成人式的理性的、功利的、全知式的“文革”叙事,在现实与记忆的叠合、成人与儿童世界的并存中,建构起叙述者意味深长的思想内容与情感言说。当然,以童年视角来反思“文革”并非女作家所独有,然而和男性相比,长期以来女性与儿童间天然的亲密情感,由母爱生发的对爱与美的执着追求以及女性意识的萌动,女性在创作中更着力于对情感的捕捉与再现,再加上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的性格特点,就使得她们笔下的文本呈现出更为女性化的情感特质:细腻、敏感和悲悯情怀。不仅如此,和男性作家相比,同样是构筑“成人—儿童”世界,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叶兆言的《没有玻璃的花房》、苏童的《河岸》等,男性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基本采用了“父与子”的对立关系——作为父亲的成人占据着强势地位与权威话语,作为儿童的“我”则基本被疏离冷落。很多时候,父亲是一种象征。对父性力量的寻找和颠覆,让人物通过对自身血缘身份的求证与确立,成为男性寻求精神家园、完成历史追溯与个人主体建构的重要手段。与之不同的是,在女性所建构的“成人—儿童”世界里,父辈处于缺席或隐匿状态,女性更着力于透过对历史的日常生活追忆,完成对现实苦难的超越,表达出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与诗意的栖息。
四、显露消费主导下“文革”历史的世俗化写作
和西方相比,中国的世俗化不是相对于宗教来说的,而是相对于政治化、神圣化而言。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政治意识的疏离与市场经济的兴盛,世俗化所强调的去政治化、对日常生活的还原,修正了以往在政治革命话语下“文革小说”对绝大多数人生存及生命体验的遮蔽与漠视,作家不再倾向于正面构建“文革”的宏大叙事和苦难叙事,而是将“文革”淡化为一个或隐或现的背景,力求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筑起一个个的“文革”故事。应当承认,世俗化写作所带来的“文革小说”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还原,弥补了80年代宏大叙事特征下对绝大多数人话语权的遮蔽,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日常生活本身的特点,特别是消费社会的到来,日常生活在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后又重新踏入消费主义的陷阱,这使得文学在摆脱了以往过度历史化制约的同时,又潜藏着商业市场对其书写的要求和制约。如果说在8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文革”更多作为一个充满血泪、未曾远去的政治灾难被控诉与反思,那么近20年来,“文革”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一种商业资源,并显示出它在商业语境中奇妙“变质”的遭遇。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来说,消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带动并影响着以市场和商品消费为主导的文学生产,促使作家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去设计自己的文字产出,因而不可避免地被大众的阅读趣味左右。作为当下颇受市场欢迎的影视剧作家,张欣的《那些迷人的往事》里,精美的剧照与纯文学文字混搭,小说尽管借助抗美自“文革”上山下乡到改革开放下海经商近30年的人生经历来折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然而不断变换的人物背景、紧凑的人物关系,高干子女不为人知的命运历程都更接近电视剧式的情节模式。正像“迷人的往事”所昭示的,小说倾向于缅怀知青一代艰苦卓绝的一生,借以唤起中年人的怀旧情绪,迎合当下占据主流的中年群体的消费趣味与审美需求。同时还有池莉,在她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中,作者将历史背景、苦难忏悔抛到一边,一改往昔知青小说的深沉严肃,在叙事姿态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轻松。不仅如此,小说以一女两男的情爱模式,流露出的是当下的世俗情感认同:豆芽菜误入歧途,爱上坏男人,后来悔悟,回到好男人怀抱。池莉在2007年出版的《所以》,小说从60年代写起,以主人公叶紫成长过程中三段失败的婚姻为主线,探讨和反思当下女性自身及其出路的问题,然而小说在叙事上的通俗直白,依旧是“一种适合市民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唠叨文体”的创作模式,小说流露出的过于市民化的婚恋立场表现出对商业化大众情感与审美诉求的迎合,缺乏一种历史的批判立场和审视姿态。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夸大商业浪潮的影响,然而90年代以来作家“文革”书写姿态确实要复杂得多。《没有名字的身体》具有黄蓓佳小说惯有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基调之一就是“好看”,有相当的可读性。小说讲述了“文革”时期“我”13岁与“他”相识,随后20年相爱不渝又无法与“他”偕老的浪漫爱情悲剧。如果说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所表现出的对婚外恋的困惑与忌讳还包含着作家对美好人生期许的话,那么在《所有的》中,我们则感受到其更为世俗化的审美追求。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姐姐艾早杀了丈夫张根本——也是妹妹艾晚的养父、她们的表姨父,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猎奇心理。不仅如此,小说交织着早恋、未婚生子、神童的陨落、三角恋(孪生姐妹俩爱上同一个男人)、谋杀等刺激的故事元素。很难将这部小说和“文革”的严肃性结合起来,小说在人物性格及情感脉络上缺乏更深入的剖析,几十年的时代巨变在主人公身上流于表面。也许这一“说不清楚的痛楚和迷失”[3],正是作者对现实人生的体味与品读,然而思想情感上的迷离与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作家应有的历史反思与批判。
事实上,在欲望化消费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文革”叙事中频频出现的媚俗化倾向并非女性所独有。我们在摒弃革命宏大化的历史叙述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必然放弃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放弃从深层次阐释创造这些日常生活的文化缘由和思想表征。因为相对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历史叙事,女性书写日常世俗、理性看待自身历史的过程正是女性审视男性话语规范,反思女性自身历史,建构女性话语方式的一种努力。正如福柯所强调:“话语是权力关系的关键……各个社会群体对话语的掌握是不平等的,有些社会群体通过手中的权力防止其他社会群体控制话语,从而控制社会主要的文化机制。”[4]213女性在日常叙事中的才华带来女性文学的崭新局面,催生出女性建构自身历史的从容与自觉,然而如果女性在逃离了革命的宏大叙事之后,又掉进消费主义的陷阱同样是不足取的。这是当代女性写作所应该警惕的。
从一贯的男性话语遮蔽下呈现女性的生存经验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呈现出的鲜明写作态势。事实上在对女性笔下“文革小说”的归纳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由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所延伸出的对历史的不同把握。“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5]198。90年代女性渴望建立属于女性自己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女性建构自身话语权威的某种努力,与此同时,女性对“文革”历史的独特把握也由此彰显。在她们笔下,不仅“文革”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而且写作“文革”的意义也变得复杂得多。她们重拾这段过往岁月,展示真实历史情境下的女性生活,实际上也是女性抛开男性主流话语规范,寻找自身合理位置,建构自我历史的主动与自觉。
注释:
①本文所强调的“文革小说”是指“文革”后发表的、与“文革”或“文革”历史相关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文革”成为其叙述对象或主要背景,影响到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极大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作者对这段历史生活的体验和感悟。
[1]林白.“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我不会写小说”[N].南方都市报,2007-10-23(04).
[2]迟子建,郭力.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1):58-64.
[3]黄蓓佳.所有的[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4]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韩大强)
On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A Study on Cultural Revolution Novels by Female Writers Since the 1990s
DONG Qi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3, China)
Writing survival experience of female an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history from male discourse were distinctive performance of female writing since the 1990s. In this period, wome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 situation, desires and psychological of female which are hidden behind the discours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In their writing, Cultural Revolution presented some different historical features and it shows that women seek for their rational place, really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and initiatively complete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women's existence as women.
Cultural Revolution narrative; Female; Authoritative discourse
2016-07-20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5Q08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W011)
董琼(1981—),女,湖北襄阳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42
A
1003-0964(2016)05-01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