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讹变问题研究回顾与再探
冯玉涛 彭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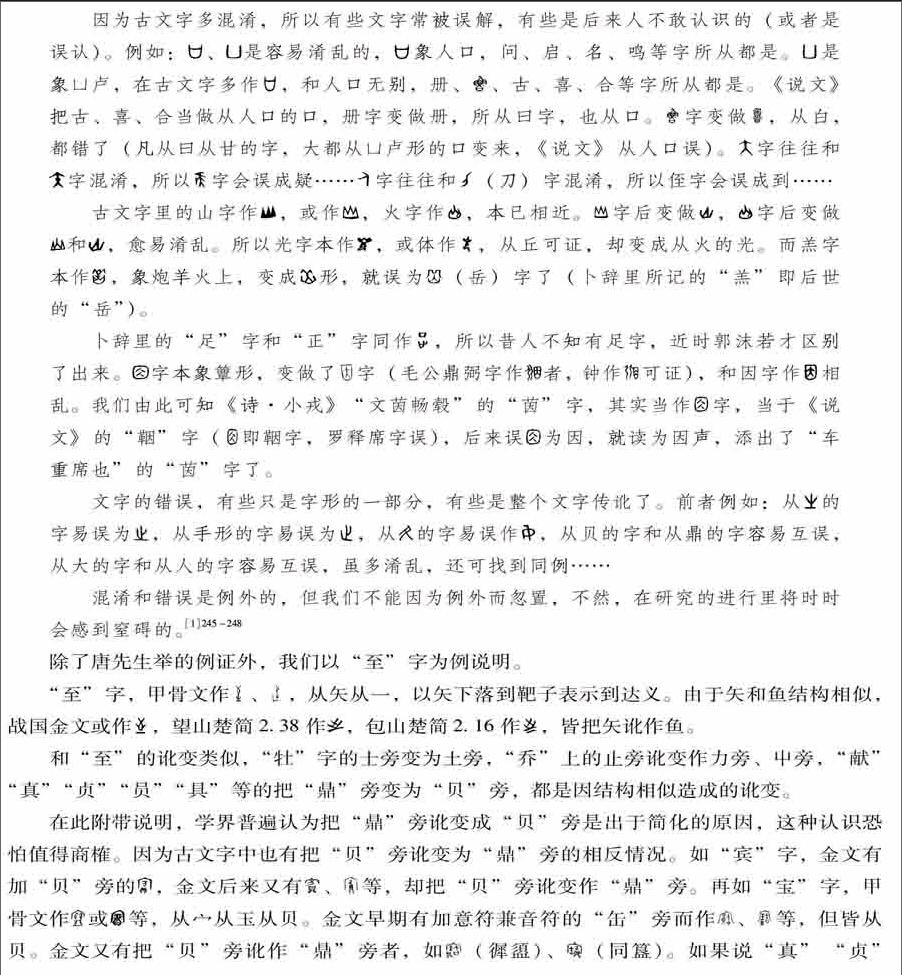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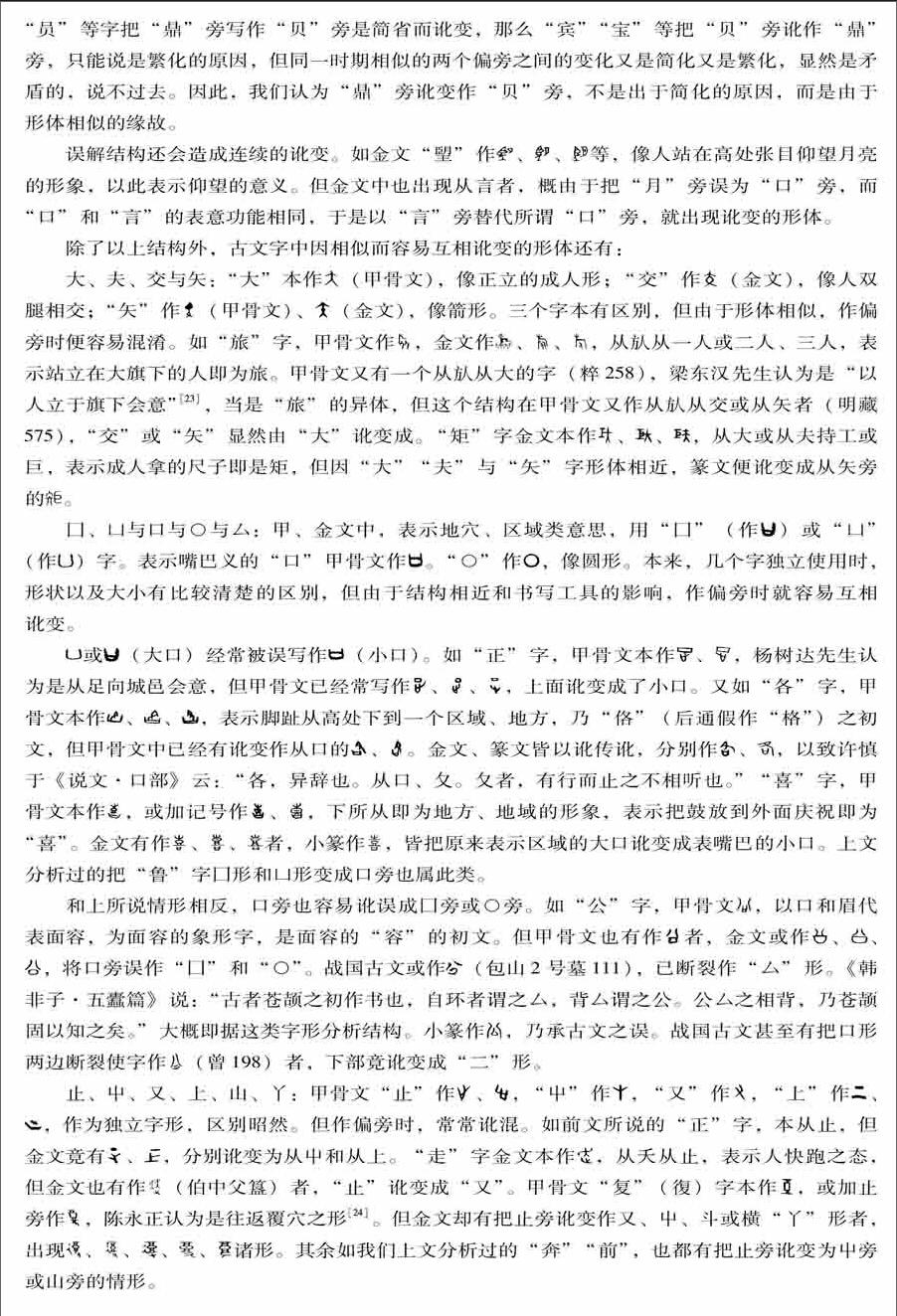
摘 要:汉字形体讹变现象在甲骨文即已出现,在整个古文字阶段普遍存在并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唐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古文字的讹变现象,但此后一段时期内几乎无人在汉字结构演变过程的视野下讨论讹变,直至近40年这一问题才受到重视,李孝定、张桂光等十多位学者对其概念、类型、原因、结果等有比较热烈的讨论。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古文字讹变现象,发现几乎所有的古文字都出现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讹变字形,讹变和简化、繁化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其类型有意符讹变、声符讹变和整字讹变三种。形成讹变的原因有六:因结构相近、因误解记号、因误解字形、因以字形附会字义、因字形断裂、因字形粘连。讹变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影响,而以消极影响为主。
关键词:古文字;讹变;讹变之类型;讹变之原因
中图分类号:H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4-0123-18
一 讹变现象研究的回顾
所谓讹变,又叫讹化、异化,指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书写者把一些本来有理据的构件或整字写成了相似而意义或读音无关的形体,使字形脱离了原来的形音义理据的错误现象。简言之,讹变就是字形结构发生了错误的变化。
讹变现象在甲骨文阶段就已经存在,并且很多古文字都经历过数量或多或少、时间或长或短的讹变,有些讹变形体甚至持续至今,因而可以说讹变伴随着汉字发展之始终,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准确掌握、区分汉字的形音义关系,了解汉字发展的全貌。但是,除了唐兰、张桂光等少数先生在其专著中讨论汉字的讹变问题外,大多数学者在讨论汉字结构演变过程时,只分析简化和繁化,却没有涉及讹变。
汉字讹变的研究颇有历史,宋以来的说文学即涉及此,19世纪末以来的甲金文研究者或有提及。罗振玉在《同簋跋》中说:“金文中别字极多,与后世碑版同,不可尽据为典要。”罗氏同时示例性地分析了金文中的几个别字。在罗氏的基础上,唐兰先生将讹变放在汉字的演变过程中予以讨论,并用了专门的术语“讹别”称呼这种现象,这是首次对古文字讹变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
唐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说:“因为文字趋于简单,简单的形体有限,所以常有淆混。而文字的演变,又常会造成错误。有些淆混是由错误而来的,而淆混的结果,也会变为错误。这两者狠难区别。古文字里的错误,前人很少注意到,罗振玉在《同簋跋》里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狠有价值的。不过罗氏研究文字的方法本不精密,所以他所提出的几个字,有些是不能算做讹别的……照我们看来,文字的型式,虽是流动,但不是‘随意两字所能包括,只要精细地研究,每个字的变化增省,都在历史的范围里,总可以找出牠的原由,即使是错误,也一定是有原由的。文字的淆混和错误,是一部分文字在演变里的或然的结果,在文字的本身上,本只有演变。只有我们去认识、解释或应用牠的时候,才觉得混淆和错误,而这混淆、错误的由来,仍逃不出演变和通转的规律。”[1]242-245几乎同时,马叙伦先生《说文解字研究法》中设立“伪篆”一节,专门讨论《说文》的讹变小篆。
近四十余年来,汉字讹变问题成为比较热门的话题,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李孝定、高景成、林澐、张桂光、董琨、金国泰、季素彩、古敬恒、刘钊、林志强、王海平等,皆或专章节或专文讨论过讹变现象。
台湾李孝定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讨论了讹变的概念及产生原因。他在《从中国文字的结构和演变过程泛论汉字的整理》一文中说:“以上所述的演变,大体上还有规律可寻,另有一种个别字体的讹变,则是每一个字的情形不同,但也有一个规律,那便是由于形近而讹,如古文中的‘交讹为‘矢,‘矢‘寅互讹,‘凡讹为‘舟,‘人讹为‘刀之类。讹变现象以由大小篆演变隶楷时为尤甚。所以隶楷的演变,有不少是逾越了文字演变的常轨,破坏了文字原有的结构,即使说是讹变,也已非‘形近而讹所能解释,而是苟趋约易的结果。”[2]78-79李先生另在《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一文谈及讹变时说:“这也应该属于文字演变的一种方式。以上数节所述文字演变的情形,大体上还有规律可寻,而文字的讹变,则是个别的现象,每一个讹变的情形都可能不同。但其所以致讹之故,却也有个共同之点,那便是由于形近而讹。凡甲骨文、金文、篆文之间的形体讹变,大都不出这个范围。降及隶楷,因为苟趋约易,或者力求整齐方正,以之与大小篆相比较,其讹变情形,往往匪夷所思。”[2]181概而言之,他认为讹变是“逾越了文字演变的常轨,破坏了文字原有的结构”,并主张讹变的原因随古今文字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差异:古文字是因形近而讹,今文字则是苟趋约易和力求整齐方正而讹变。
高景成在《略谈汉字字形发展中的合并与讹变》一文中说:“‘汉字字形演变的总的趋势是简化是一条大的规律,而它们的合并和讹变则是其中的两条小的规律。合并和讹变也常常是减少笔画和简化结构的一种手段。”[3]高氏在文中还分析了讹变和合并、讹变与简化的联系与区别,启发了后来有关讹变的研究工作。
林澐更简明地界定了讹变的概念。他说:“在字形变异中有一类特殊的现象——在对文字的原有结构和组成偏旁缺乏正确理解的情况下,错误地破坏了原构造或改变了原偏旁。这类现象,习惯上称之为‘讹变。”[4]103这个定义简要而概括性强,直至目前,仍是最好的定义。
张桂光指出:“所谓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指的是古文字演变过程中,由于使用文字的人误解了字形与原义的关系,而将它的某些部件误写成与它意义不同的其它部件,以致造成字形结构上的错误的现象。”[5]张先生是大陆较早专门研究古文字形体讹变现象的学者,对古文字的讹变情况分析得不可谓不细致,但其讹变的定义似有所不足,因为把声符的讹变排除在讹变之外。
金国泰指出:“讹变与简化表面上相似,但讹变本无目的,或源于无心,或源于误解或者误改。字形演变过程中,突破六书原则,失去结构原义,并不就是讹变,其中大部分为改造。简化是改造的一部分,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人们追求书写简易而采取的改造手段的结果。”[6]金国泰明确区别了简化与讹变的不同,并且认为人们有目的地追求简化而造成的字形变化并不属于讹变,强调讹变的非目的性。此观点虽然有理可循,但是有明显不足。因为诚如李孝定先生所言,“每一个讹变的情形都可能不同”,因而不能一概而论,对具体的字、不同的字形还需具体分析。
董琨认为:“字体即书写风格的变化带有整体性,因而是一目了然的。而字形即组织构造的变化则往往因字而异,但是大致划分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到了小篆阶段仍然可以从字形分析字义的,这是正常的循例的变化,叫做‘循化(或‘循变);一是到了小篆或在更早的阶段,字形在演变过程中发生讹误,从而脱离了与字义的联系,这样的变化叫做‘讹化(或‘讹变)。”[7]虽然这一定义是对小篆而言,但同样符合所有书体,属于高度概括的定义。
王梦华说:“字的讹变指的是由于误解了字形中的部分笔画和部件的来源造成的现象。”[8]
季素彩在《汉字形体讹变说》一文说:“汉字形体在几千年的漫长演变过程中,由甲骨文而金文而小篆而隶书,不少字不是按照常规演变的,于是就产生了讹变。”[9]季先生的讹变现象研究不只限定在古文字阶段,还进入了今文字阶段,她将讹变现象归于非常规演变,强调形体讹变破坏了汉字的表义性,使本义不能通过形体表现出来,并认为讹变适应了表音和简化规律,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林志强《关于汉字的讹变现象》一文认为:“所谓讹变,指的是某些汉字在演变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使用者把本来有理据的结构或构件偏旁误写成了与之相似而意义不相干的结构或构件偏旁,从而使得文字的形体结构丧失或脱离了原来的形义关系的错误现象。”[10]这个定义的明显不足是没有把声符讹变涵盖进来。
王海平认为:“所谓讹变,是指在理据、简化、字体转换等动力的驱使下而发生的违背原有形义联系的形体变化。”[11]这个定义更不准确。因为既然有理据,就不算讹变。况且字体转化即书体的演变是笔意、笔势发生改变而导致的结构差异,自不应算讹变,否则,从甲骨文至今的所有汉字都是讹变了。
古敬恒、李晓华认为:“文字的使用者在对文字的原有结构和组成偏旁缺乏正确理解的情况下,错误地破坏了原构造或改变了原偏旁,从而使得文字的形体结构丧失或脱离了原来的形义关系,这种情况我们称为汉字形体的讹变。”[12]这一定义显然源自林澐的认识,文字增多了,表面看似乎周延了,但却存在明显不足。因为它同样只涉及形符或意符的讹变,没有涉及声符的讹变。
学者们也探讨了讹变的原因。
季素彩说:“汉字形体讹变的原因很复杂,有汉字自身发展的内部原因,也有汉字发展的外部原因。”她认为从内部看,讹变适应了汉字表音、简化的发展规律,适应了汉字结构的内部平衡律,适应了汉字的孳乳和分化,为“亦声”说提供了立论依据。从外部看,形体讹变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典章制度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促进了讹变的产生。但是,若真如季先生所说,讹变就不是一种错误,而是科学的、有理据的、正常的变化,如此,真正的“讹”变似乎就不存在了。
林志强认为:“只要有演变,只要有变异与规范的矛盾运动存在,都可能有讹变现象产生。”这种认识过于宽泛,且把规范当做讹变的原因,显然不合事实。因为小篆之前的古文字并不存在规范,而其中的讹变却大量存在。
张桂光认为假借字、形声字的不断增多和容易产生形似部件的书写工具的出现、使用,是古文字讹变产生的两大动因。
王海平将讹变的原因归纳为:客观上的形体相近、主观上的误解、汉字理据变化的影响、字体演变的影响和其他原因等五个方面。
古敬恒、李晓华将讹变的原因归纳为:形近相混、字形的离析与粘连、误形为音三个方面。
二 古文字讹变之类型
讹变在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甲骨文中已出现,而且意符(包括形符)讹变、声符讹变和整字讹变三种类型在当时也都存在。
进入金文阶段,文字的讹变现象依旧连绵不绝。这个时期除了甲骨文中由于形体相似造成的讹变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即由于远离了造字时的文化环境,不能理解原字的取义依据而产生讹变。
春秋战国阶段,汉字的讹变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各诸侯国之间地域的间隔和军事、政治等方面的纷争而呈现更加剧烈的变化,又因为年代久远,无法推知造字时文化环境的文字更多,讹变也就更加普遍。
1.意符讹变
这里所说的意符包括形声字的形符和会意字的意符。所谓意符讹变就是把会意字的意符或者形声字的形符写成错误且意义无关的形体,以致被误以为其他意符、形符甚至声符。
“牡”原为会意字,甲骨文中或从牛作,或从羊作,或从豕作,或从鹿作,所从的丄旁是雄性动物生殖器的样子,就是后来的“士”字,和“牛”等动物类的字组合表示相应的雄性动物。到金文中出于习惯,在竖线的中部加一起填空作用的记号点而字作等,或把点延长成横线而字作,本来还是士旁,但后人书写出现错误,把士旁最后一笔拉长,使其变得像土旁,如小篆作,就把士旁讹变成土旁,以致许慎不察,在《说文解字·牛部》解释说:“牡,畜父也。从牛,土声。”虽然许慎准确说明了该字的本义,但他把土旁当做声符,就是由于讹变造成的误解。许慎之后,人们发现“土”和“牡”的读音相去较远,已怀疑其作为声符的资格,因而采用替换或补充新声符的办法改造该字,在篆字中就出现、、这三个声符和字音一致的形声字。
“祭”字甲骨文本作、、,从又或从左从肉,几个点代替血滴或者象征肉的新鲜气息,整个字形表示手持鲜肉祭祀之义。但甲骨文中有时把“祭”字的肉旁方向朝上写作(掇一·四六三)形,甚至省形作,使肉旁讹变成口旁。林澐说:“商代甲骨文中已识的祭字中肉旁有、两种形体,作的肉旁在形体上跟‘口是难以区别的。”[4]67准确指出了肉旁、口旁之间讹变的事实。又有在讹变字形之上加示旁而字作(前三·三八·二)者,已经很难看出持肉祭祀的意义。金文大多以循变方式加示旁繁化而作(邾公华钟)、(史喜鼎)、(蔡侯午錞)等,但也出现讹变的形体,如蔡侯盘中作,变成从日旁的结构。
“歲”字原形为(甲二九六一)、(粹一七),为象形字,象戈类武器。在甲骨文中,也有作、、等者,字形基本未变,但加上了装饰性的填空记号点或者横线。大概由于古人认为岁星在空中运行,后来就在戈旁的右边多了两个左右方向相反的止旁,使字形或作。到金文阶段,添加止旁的字形进一步演变为、(毛公鼎)。这些字形都是向正确的方向演变。但甲骨文中已经有在戈旁的旁边添加肉旁的结构,如果不联系甲骨文的,会对肉旁的来历感到莫名其妙。这个肉旁乃是由于肉旁和止旁相似而导致的讹变。添加了肉旁的字一度在西周消失,但春秋战国时再次出现,如(楚王酓肯鼎)、(噩君启舟节)、(包山2号墓楚简2)、(望山2号墓楚简1)等,都是讹形。从止旁的“歲”后来也发生讹变,如《六书通》中的小篆有、、等,竟然把止旁讹变成山旁或才旁。最后,“歲”字就定型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也是讹变的字体。
“□”字,《说文·丮部》:“设饪也。从丮从食,才声。”在甲骨文原为(合32663),为表意字,表示跪坐的人在进献食物。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云:“□,从丮从艮才声。从艮与从食同,皆会手持熟食祭神之意,乃□之初文。”[13]271但甲骨文也有作(合41768)者,人旁已讹变为“戈”。这一讹变字形在金文中或有出现,不过春秋以后不再出现。
“亘”(音恒,后音转读艮)、“恒”和“GAFB6”,这三个字原为一字,甲骨文初形作(合集一四七六二)、(合集一四七六六),从二从月。或外加弓形作。“二”象征天地,以月在天地之间表示恒久义。金文开始在“亘”上加心旁作(恒簋盖)或(舀鼎),月形仍清晰可见。小篆却把月形讹作舟旁,出现讹变的字形和,以致许慎按照错误的形体分析造字理据,在《说文·二部》说:“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显然误解了字形结构。王国维先生曾经详细阐发了“亘”“恒”等的形体沿革过程,纠正了许氏的误解。他说:“案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古文恒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恒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又《说文·木部》:‘GAFB6,竟也。从木,恒声。,古文GAFB6。案古文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以此例之,本当作。舀鼎有字,从心从,与篆文之恒从者同,即恒之初字。可知、一字。卜辞字从二从,其为、亘二字或恒字之省无疑。其作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二字确为恒字。”[14]又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说:“金文恒字从心亘声,为后出形声字,小篆讹月为舟,许氏据小篆说解,失之。楚帛书恒字作,与《说文》古文同。商锡永师曰:‘木部GAFB6古文作,乃借为GAFB6,从舟为月之误。”[15]1084-1085可见公认小篆中的舟形为月旁的错讹。
“者”在甲骨文本来是象形字,初形为(铁八六·三),其取形依据和古人的生活习惯、认识相关。当古人懂得使用书写工具和夹取食物的用具时,这两种用具形状、材料、来源一样,都是长条形,都是就地取材,随手折取树枝、草枝而来,实际就是一种工具,本无区别,既可以用来书写,也可以用来夹取食物,因此,“者”也是“书”“箸”“著”的初形。把筷子当笔使用,后代亦偶然出现。如《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劝阻刘邦通过分封诸侯以阻挠项羽的想法时,“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张良即“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于是,一边说一边用“箸”在案几上划了八点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就是把箸当笔使用,反映了古代的遗俗。
甲骨文中,“者”中间一竖既可以象征书写工具,又可以象征筷子;“者”字上的交叉形既可以表示写出的线条,又可以表示架构的柴火;其中的点既可以象征文字的线条、墨点、刻写时落下的碎片,又可以象征火焰。古文字有在字的下部或者空虚之处加填空记号的习惯,“者”字也不例外,因而甲骨文有在下面加填空记号口旁的“者”字,如《甲骨文粹编》之二七。由于本来作为填空记号的口旁和表示书板、餐具或火炉形的偏旁相似,甲骨文便以形附会字义,把“者”字下部写作“口”字底,使字形发生讹变。金文主要继承讹变的形体,出现、、、等形。(比较“书”:最早见金文,初作,加形作、、、、、、、,小篆。《说文》云:“书,箸也。从聿,者声。”)金文中也有把字下部的口旁稍作改变,使更像火炉形而字作,如此,“煮”和“著”就区别开。但金文中甚至出现更大的讹变,把火炉形或口旁讹变成鼻子形,出现、、等。又由于口旁或火炉形中间空虚,人们就按照习惯在其中加一点或横线作为填空记号,使字形变为、、、等,如此,口旁又极易混淆成甘旁。到小篆,字形讹变作,以致许慎不察,误以为“者”字下面从白(音自,“自”的异体)。许氏在《说文·白部》解释:“者,别事词也。从白从。”甚至在金文中还有在口旁中加填空记号“乂”的“者”字,作形,如此一来,“者”字的下部就和表示簸箕的“其”字完全一样了。
“利”在甲骨文本作、、诸形,从禾从刀,会用镰刀收割禾谷而锋利之意,但甲骨文中同样出现在禾旁右上加点的,或在禾旁右上和中间各加一点的、,甚至把点延长成线条,加在禾旁和刀旁中间而字作。点或线条,本表示刀割取禾谷时掉落的碎屑或者颗粒,无论数量多少,都属于代替或象征记号。浸淫至金文,“利”字以加记号的形体为常见,如、、、诸形皆是。无论甲骨文还是金文,“利”字所加的作为记号的点或线条的数量、位置并不固定,从以上诸形即可知晓。但春秋战国时期,以把记号加在表示刀刃部分的线条的上下为常见,出现(侯马盟书)和(《说文》古文),如此,使刀旁变得像勿旁,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利”字从勿,至今,学者谈及“利”字的结构发展,还往往说从勿。
“鲁”字甲骨文本作或,下部为地方、区域的形象,以出产鱼的地域表示鲁地之意。但因为表示地方的囗旁、凵旁和表示嘴巴意义的口旁形状类似,甲骨文就出现、等,把下部讹变成口旁。金文或承接甲骨文的本形作,或承接讹变的形体作,或又加记号作。后因与上半部分笔画交叉而讹变为(颂鼎)、,并一直持续到春秋以后。
“献”字甲骨文原作(合31812),是从鬲从犬的会意字,会以犬牲献祭之意。金文中或给加声符“虍”而出现、等,或把“鬲”类化为鼎旁而字作等,这是合理的变化。但金文中也有、、等形,把鼎旁讹变成相似的贝旁,甚至讹变作、、等,已完全看不出鬲、鼎的影子。也有把声符讹变作结构近似的戈旁而字作者。到春秋甚至讹变出(郑大师甗),与原字差别甚大。
“祈”甲骨文本作、、等,为会意字,从单从斤从GAFB7,“单”“斤”表示战斗武器,“GAFB7”表示旗游。“从单从斤或从GAFB7……金文中借为旂、祈,但卜辞中无祈丐涵义之用例。”[13]25陈初生说:“金文祈字多数从GAFB7从单,与甲骨文作同。单乃兵器之象形。罗振玉谓:‘从旂从单,盖战时祷于军旗之下。会意。其它诸形皆之省变或借字。”[15]28其分析及引用罗振玉讨论皆是。“祈”字在金文颂鼎上作,旗游表现得更清楚,但或稍变而作(陈公孫GAFB9父瓶),“GAFB7”已和“止”无别。再进而讹变为(伯GAFB8簋)、(大师虘豆)等,竟然把“单”讹变成“言”。或省形作(归父盘)、(□鎛),已难以看出旗游。春秋战国时期,或讹变作难以分析其结构的(番君召簠),或省形保声作(邾公GAFBA钟),或再记号化而作(栾书缶),都看不出取义的依据。
“周”字,甲骨文作、、、,金文有、、者,皆表示田地之周围、周严。金文也常见作者,上面的横线被缺省一半。金文又有在下面加口旁或凵旁的、、等形,点、口旁、凵旁都是为了和“田”字区别的别形记号。《说文》所收古文作,上部从金文讹省的形体,而下部把口旁或凵旁讹变成曲线。小篆作,承接金文上部讹变的形体而来,以致许慎不明,按照讹变的古文、小篆分析结构,出现误解。《说文·用部》说:“周,密也。从用、口。,古文周字从古文及。”释义甚是,但说“古文周字从古文及”,是一误;又以为小篆“周”字“从用”,为再误。
甲骨文“凡”作、,金文承之作、,或少变而作、,仍能够看出是盘类器具(包括抬盘、饭盘、洗漱用盘等)的象形字。甲骨文“舟”作、、,金文作、、、。两个字在甲、金文中都有几乎相同的结体,因而古文字中的“凡”“舟”独立使用及作偏旁时,最易讹变。
“凡”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常用字,这一点在实物和文字方面都能够证明。“凡”作为古代抬重物的器具,已经有实物出土。1934年,在河南安阳1001号殷王大墓中,曾经出土过三件像担架的器具,总长2.3米,前后柄各长0.3米,身长1.7米,宽0.6米,与甲骨文“凡”字的轮廓相同,学者认为这就是古人使用的抬盘。另外,“凡”在一些常用字如甲骨文(凤)、(兴)等中作偏旁,也说明“凡”是当时的常用字。
由于“凡”和“舟”等结构相近,古文字中经常讹变成“舟”等。如以下诸例:
“盘”“般”“搬”三个字原来是一个形体,甲骨文初以“凡”为之,表示作为名词的盘形物如方盘、抬盘,也用以表示动词的盘旋、搬动义。甲骨文后来在“凡”字上加手旁或殳旁,出现、、、、等形,金文承接而作、,这就是“般”字,表示盘旋、搬动义,从而把名词性和动词性的意义通过字形区别开。后来,“凡”假借作总括范围的副词,“般”才既表示名词性意义,又表示动词性意义。由于甲骨文、金文皆有把凡旁的竖线向同方向弯曲的结构,加之古文字习惯在空缺结构中加填空记号,因而出现(甲骨文,般、盘、搬)、、(金文,般、盘、搬),于是凡旁就变成舟旁。金文也出现加形符皿旁的分化字(盘),首先把表示名词性的意义通过字形表现出来,古文继承而作,《说文》小篆替换形符作,而金文直至小篆仍用“般”表示一般和搬动义。
“受”字,甲骨文作、,金文正体作,加填空记号作。和“盘”等变化的原因一样,甲骨文、金文的“受”字也可写作、、(甲骨文)、、、、(金文),已把凡旁讹变成舟旁。小篆作,乃是由讹变而简省来的结构。赵诚先生说:“受字甲骨文作、等形,从两手执一舟(即盘),表示受授之意,乃会意字。金文、石鼓乃至郭忠恕《汗简》所收古《尚书》的受字均从舟作。汉代的印章文字作、等形,中间所从的冂、冃,很明显地能使人感到是从、演化而来,但失其本形。《说文》所用的篆文应该是行于先汉,比汉印文字要稍微早一些,不知何以竟然写成了,中间所从的居然比汉印文字还要趋于简化,很难使人感到是或之讹变。”[16]
“前”字甲骨文初作,从止从凡,为会意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说:“甲骨文从止在凡上,凡或作,象高圈足盘形,篆文从舟乃凡之讹。李孝定谓止在盘中乃洗足之意,为湔之原字,前进字乃其借义(《甲骨文字集释》卷三)。”[13]126按李孝定的说法可备一说。此字所从的凡旁也为古代抬盘即今担架的象形字,字也可能以止在抬盘前方来表示前面或前进之义。后来甲骨文中加行旁而字作,专表示前进义。或于凡旁中加一填空记号而字作、,虽然还表示前进义,凡旁虽然还像盘形,但已扭曲,为金文的讹变埋下伏笔。到金文,“前”字即作、,下部已讹变作舟旁。甚至同时把止旁讹变作屮旁而字作、、等,若非甲骨文“前”字作参照,已难以看出其原始构造。小篆作,承接讹变的金文而来,以致许慎确信字形从舟,于《说文·止部》云:“歬,不行而进谓之歬。从止在舟上。”
“服”字,甲骨文作(林1.24),金文常作或、,从凡从人从又,表示手按人头给其洗头,有服侍义,也表示服从义。与前面两个字的凡旁误作舟旁缘由相同,金文中也有作、、等,《说文·舟部》收录的古文延续讹变的形体而又简省了又旁作,小篆遵从讹变的金文作,隶书、楷书延续讹变的小篆而又把舟旁和月旁混同而作“服”。
古文字中不惟作偏旁的“凡”会误作舟旁,甚或“凡”字亦会直接误作“舟”字。典型的例证见《周礼·春官·司尊彝》。原文说:
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秋尝,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隹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罍。
郑玄《周礼注》云:“‘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17]这段话主要说明司尊彝所掌管的各种祭祀用器即彝、舟、尊、斝、壶、罍。但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其他器具都属于酒器,唯独“舟”非酒器,和前者明显不同类。这究竟怎么回事呢?郑玄的注解提供了线索。他引用了郑众《周礼解诂》的解释说:“郑司农云:舟,尊下台,若今之承盘。”从文意看,郑众的说解甚迪。至此,我们明白,这个“舟”就相当汉朝的承盘。不过,单从“舟”本身看,说它有承盘义,还扞格难通。原因就在这里的字形出了问题,其原字本当为“凡”,而非“舟”字,“舟”是个形误字。郑玄注解《周礼》,主要是对郑众《周礼解诂》的纠正和补充。郑众本人是古文经学家,其所注解的《周礼》,源自西汉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的古文经。据文意和字形可知,后来所见“皆有舟”一语,在古文《周礼》中必作“皆有凡”,由于战国古文“凡”字和“舟”字相似,汉代经学家误读、误改,“皆有凡”便改头换面成“皆有舟”了。
“孝”字最早见西周金文,原作、等,为从老从子的会意字,以孩子搀扶老人来表示孝敬之意,但鄤仲孝簋中竟作,散氏盘中又作,皆因省形而导致讹变,已看不出老人的形象。春秋时又把子旁讹变,如番君簠中作,曾伯簠作,完全失去子旁的形状。
“朢”字甲骨文本作、等,人或站在高处,或站在平地,皆表示抬头仰望之状。金文加月旁作、、等,仰望的意义更明显。但金文有(师望鼎)、(师虎簋)、(無GAFBB鼎),逐渐把目旁讹变成亡旁。金文也出现从言的“望”,概因把月旁误为口旁,又以为言旁和口旁的表意功能相同而导致的讹变。金文中甚至有把“望”写作(GAFBC鼎)者,则是整字发生了讹变。
“晋”字甲骨文作,从曰从二矢,以双箭射靶子表示向前、向上义。许慎《说文·日部》:“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臸。”对本义的分析概接近事实。到金文中,“晋”大多作或,但也有作、、者,把矢旁讹变成结构相似的鱼旁。
“奔”字最早见于金文,作(盂鼎),从夭从三止,表示大步奔跑之状,为会意字。后来把止旁讹变为屮旁,故出现了(井侯簋)、(克鼎),使字下变成卉旁。春秋战国文字中,除在秦石鼓文中偶然保留三止作形外,其余多把止旁讹变为屮旁,如(石鼓)、(三体石经·僖公)等,甚或把下面讹变得像山旁,如(中山王GAFBD鼎),显然皆承接金文讹变形体而来。小篆作,完全延续讹变的形体,以致许慎认为其结构是“从夭,贲省声”,误为省声字。隶书、楷书皆以讹传讹,可谓积重难返。
“坯”字最早见金文,原字形作(競卣),从享(即“郭”字)不声,本义为未烧的砖瓦。后讹变为(咢侯鼎),已看不出形符,进而讹变为(秦公簋),更不知形符为何。
“春”字甲骨文或作、,为象形字,像春天草木生长的样子。甲骨文经常作、、、,从日从屯或从艸或从林或从森或从木,屯亦声,说明天气暖和草木开始艰难萌芽的日子就是春天。甲骨文省形作、、、等,仍为会意兼形声字。金文作、,承接甲骨文的结构,会意兼形声的意味依旧浓烈,“日”旁仍旧赫然,但春秋时栾书缶中作,左下角变成肉旁,显然是日旁的讹变。
“旁”字甲骨文作、,金文作、、,会意兼形声字,从凡从方,方也兼表读音。其本义为何,学者存疑。许慎《说文》所说恐非本义,当是引申义甚至假借义。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认为“旁”在甲骨文中表示三个意义:“一、方国或族邦名;二、人名;三、地名。”[13]8概从春秋开始,“旁”的形符发生变化,《说文》籀文作,楚帛书中作,《说文》古文作、,小篆作,皆为讹变形体。
“半”字最早见于春秋金文,作从斗从八,表示将斗的容量中分为五升即是半。侯马盟书承金文“半”的结构,亦从斗从八。另在盟书中,“半”作偏旁时亦皆从八从斗,若从门半声的“閗”字,里面的“半”显然从斗,皆证明从斗的“半”为正确的结构,亦为初形。眉胅鼎中“半”的下部乃是“斗”的省作,还可看出斗形。战国早期的“半”仍继承了春秋“半”字的精蕴。秦公簋的盖上刻作,所从的牛旁,是从“斗”讹变而来。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66作,又将牛旁讹变。这里还需说明的是,秦公簋虽然是春秋器物,但盖子上的文字却是战国晚期补刻的,故其中“半”的写法并非早期的形体。由于小篆继承了战国晚期的秦系文字构造,因而秦篆中将错就错作,以致许慎不明,于《说文·半部》云:“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解说得头头是道,颇能迷惑读者。
“昔”甲骨文作、,为会意字,以从日从洪水形表示洪水泛滥的古代即往昔之义。西周金文多从甲骨文之形,但春秋时该字出现讹变。有时把日旁写得像曰旁,如GAFBF□壶之;或加一竖线而使下部像田旁,如中山王GAFBD鼎的、江陵天星观1号墓楚策简;甚或出现(GAFBE王□鼎)、(《说文》籀文),皆为讹变的形体。
“乔”字最早见于金文,原作(郘GAFC5钟),是“高”的分化字,以在“高”上加一作为记号的长线来突出更高的意义。又在斜线上加记号而作(郘GAFC5钟)。又加记号而讹变作(乔君钲鋮),成为从止从高高亦声的形声字。战国时期的金文中还出现把上面的止旁又讹变为力旁的形体,如(楚王酓GAFC0鼎)、(中山王GAFBD鼎),甚至把止旁讹变为屮旁作(臣卫父辛尊)。战国古文又有把止旁讹变作又旁的(郭店楚简·唐虞之道18)、讹变作九旁的(包山2号墓楚简49)。凌迟至小篆,又把上面的屮旁和“高”最上端的部件加工组合成夭旁,字形又讹变成。许慎不明白小篆的“乔”字是从讹变的形体发展来,认为其结构为“从夭从高省”,甚至清人段玉裁曲为许慎辩护,于《说文解字注》中附会云:“以其曲,故从夭。”[18]494是不明形体讹变导致的误解。
“员”字甲骨文作、等,金文作、等,小篆作。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云:“员,从○从鼎。○象鼎正视圆口之形,故甲骨文员应为圆之初文。金文员作员父尊、员壶,《说文》员之籀文作,并与甲骨文同。《说文》:‘员,物数也。从贝,○声。《说文》从贝乃鼎之讹。”[13]700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说:“甲骨文员作、,与金文皆从○从鼎,与《说文》所录籀文同。高鸿缙谓○为意象字,本即方圆之圆之初文,后加鼎为意符,言鼎之口正为圆形也。后人又于员外加囗为意符作圆。古文字鼎与贝形近,故小篆讹为从贝。”[15]653他们于“员”(圆)的取义和讹变过程说得非常清楚,此不赘。
“具”字在甲骨文作、,从鼎从廾,以双手共举一鼎会意。金文初承甲骨文形体而作(宗周钟)、(函皇父簋)等,仍从鼎。但在馭八卣等中形体发生讹变,“鼎”旁变为“贝”旁,字形作、、等,石鼓文、曾伯簋和秦公簋中都继承了馭八卣中的形体,字都由贝旁和左右手组成。金文中同时又出现把贝旁讹变成像目旁的、、等字形。小篆继承金文讹变的形体作,以致许慎不察,认作贝旁的省形,说:“具,共置也。从廾从贝省。古以贝为货。”
“賓”字的甲骨文初作、,从宀从人或从元(兀),或加止旁作,金文初作(□鼎),与甲骨文字形无异。后加贝形作(保卣)。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说:“宾,上从宀……皆象屋形;下从人或卩、女,皆为人形;下又从止,与各字所从夂同义,示有人自外而至,故甲骨文宾字象人在室中迎宾之形。虽字形歧出,各有增省,而其所会意则同。金文及小篆易从止为从贝者,乃后起之字。”[13]703-704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宾”在甲骨文中的取义依据以及甲、金文中主要形体的沿革过程。因为鼎旁字和贝旁相似,金文“宾”字有时也作、 等,却把贝旁讹变作鼎旁。战国古文又有讹变作(郭店楚简《老子》甲本19)者,已不知房子下是何物,不能按照六书结构分析。
“饮”字甲骨文作(合10405)或(合755),从酉和低头张口之人,表示人从器皿中喝酒水。金文作(善夫山鼎)或(沇兒鎛),小篆继承作,皆把字形割裂且将张开的口形讹变成声符“今”,由会意字变成形声字。
“敄”字金文作(毛公鼎),用手持鞭棒之类工具击打戴羊角帽的人以表示强力驱使之义,承培元《广答问疏证》认为即“务强也”之务。篆文作,将形符误作声符,以致许慎不察,训释云:“敄,强也。从攴,矛声。”释义虽正确,但结构分析却错误。
“妒”字甲骨文从石从女,金文驭方鼎等承之,六国古文如《老子》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和秦系文字作(睡虎地秦简《日书》96),皆从石从女。至小篆将石旁误为结构相似的“户”而字形作,以致许慎当形声字解释,于《说文·女部》云:“妒,妇妒夫也。从女,户声。”至于“妒”从石旁的缘由,和古人的认识有关。明张自烈《正字通·女部》云:“方俗谓妇不孕为石妇,犹言石无土,不生物也。”又云:“女无子为妒。”揭示了“妒”从石的真谛。
“射”字,甲骨文初作、,以在弓上搭矢会射箭之义。偶加手(又)形作,突出射箭义。金文或保留初形作,或保留加形者作,这些都是规范、合理的循变。春秋战国时期作(《说文》所列字头,当是春秋籀文或战国古文),竟将弓旁和矢旁混合成身旁却又加了矢旁。小篆继承之而作,仍误作身旁。许慎于《说文·矢部》云:“,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从矢从身。,篆文射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析形、释义皆欠准确。
“折”字甲骨文本作,金文作(兮甲盘)、(齐侯壶)、(中山王GAFBD鼎),籀文作,《说文》古文作(《说文》该字的字头应是古文),小篆作。《说文·艸部》说:“折,断也。从斤断艸。谭长说。,籀文折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篆文折从手。”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说:“折字金文亦从金断艸,与古文同。齐侯壶在上下两之间加入二,以指其断折之处,二乃指示性符号,与籀文同,许慎附会为仌(冰),非是。中山王GAFBD鼎则变艸为木,且将二移置木之上,指示意义遂失……篆文变作从,乃由两相连与形近致讹。”[15]66
2.声符讹变
“凤”字甲骨文本作、等,为象形字,像孔雀之形[19],或加声符“凡”而作、等。由于“凡”和“兄”相像,竟有把声符讹变为兄旁而字作等,成为从孔雀形兄声的形声字,此即凤凰之“凰”(唐以前作“皇”)的来源。甚至可以讹变声符作,或简省作、者,已完全看不出声符。
“神”字甲骨文作、,金文作,但战国古文作(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甲篇3.36),已经看不出右边的部件是形符还是声符。
《说文·贝部》解释“质”字说:“以物相赘也。从贝从斦。阙。”各家于此“阙”颇有争议。段注云:“阙者,阙所从斦之说也。《韵会》‘从斦作‘斦声,无阙字。”[18]283王筠说:“小徐作斦声,无‘阙字,《韵会》引同。”[20]朱骏声说:“此字当从斦声。斦疑即椹质之质,后人又制櫍字,即斦字也。”[21]究竟如何,只有考察其形体演变才明白。“质”字最早见春秋末之侯马盟书,作,诅楚文作,上部皆不从斦。根据“质”字的形和音,联系“折”字的结构,可知盟书的“质”乃是把声符“折”的两个屮省略而来,诅楚文又写成曲线,以至小篆中讹成斤旁作,使字上部变成从斦。许慎对其本义的训释正确,也明白为什么要从贝,但不知道意符“斦”是声符“折”的讹变,又发现“质”的意义和“斦”无关,所以说“阙”。
“考”字甲骨文中为象形字,初形为(合21054),以长发老人扶杖形表示年老。稍变而为(合36416),又变为(合21482)。到金文演化出、等,形体已经发生讹变,都难看出老人的形象。还可以省形保声作。到春秋战国,讹变更为明显,除保留省形的外,甚或出现(GAFC1叔之仲子平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6),都已看不出“考”字的原形。
“勒”字在金文中基本字形为,或加作为填空记号的横线或点而作、、等,为从革从力力亦声的会意兼形声字,会用力刮制皮革之意。后为(盠彝),意符发生讹变。春秋战国时则定型为(石鼓)。
“真”字甲骨文从人从鼎、鼎亦声,是形声兼会意字。甲骨文中,“真”字的鼎旁虽有繁简不同,但鼎形一直比较醒目,不失本真。到金文中除多数情况保持甲骨文的结构外,也出现讹变的形体。如周中期的伯真甗中作,已经把鼎旁讹变成贝旁。春秋战国时期除保留从贝的写法外,又出现另一种讹变的结构,如真敖簋作,石鼓作,都把上面的人旁讹变成匕旁,这就是小篆字以及隶书、楷书“真”字的来源。战国时如天星观楚策等甚至把“真”讹省作,下从目而上不知何形。由于形体讹变,以致许慎按照讹形分析字义。《说文·匕部》云:“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
“贞”字甲骨文作 等,本借“鼎”字表示贞卜义,甲骨文偶或加卜旁作(合10072),专表贞卜义。金文皆加卜旁,如、等,成为从卜鼎声的形声字。但金文有作(冲子鼎)者,下面却讹变作“贝”。金文甚至有把卜旁讹变者,如番昶伯者君鼎的、,皆是。战国包山2号墓楚简20又把贝旁讹变作目旁而字作,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乙4·122又作。战国古文也有继承金文从贝者,如新乙4·35作,睡虎地《秦律》125作,小篆从之作。《说文·卜部》:“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一曰:鼎省声,京房所说。”从“贞”字的演变看,京房所说显然符合事实。又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云:“鼎贝形近,故乃讹变为貞也。”[22]此说是也。
“责”字甲骨文作(合22214),金文、篆文仍之,皆从贝朿声。《说文·贝部》云:“责,求也。从贝,朿声。”战国晚期睡虎地秦简作,始将声符讹变,已看不出是形声字,“责”即变成半记号半表意字。
3. 整字讹变
“舄”字金文字形为(大盂鼎)、(吴方彝)、(师晨鼎),象喜鹊扇动翅膀张口鸣叫之形,象形意味浓烈,但后讹变为(伯晨鼎),已毫无象形可言。
“龙(龍)”字甲骨文作、,金文前期作、,都是象形字。但金文后期作或。如果说前一个形体还保留象形意味的话,后一形体则彻底失去象形意味,发生讹变,无法用六书分析。战国印玺文字作(《玺印文字合徵》11·4),于右边之形体加了填空记号,小篆延续并加工成似“飞”旁而字作。许慎不察,误为形声字,于《说文·龙部》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宋徐铉概见过金文“龙”之初形,因而在《说文》“龙”字下加按语说:“象夗转飞动之皃。”已揭橥“龙”字结构之本真。
“章”字最早见金文,初作、,或在上加记号一作,或在竖中加记号点作,或把点延长成“一”使下部呈十字形而字作。战国时或把“田”字形中的横线省去而字作,或把竖线中间断裂而字作。最后一个形体明显讹变,使人们很容易将其分析成从音从十或从辛从早的结构。小篆以讹传讹,作。许慎不察,按照讹形分析,于《说文·音部》云:“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于义于形皆欠妥。
“乍”字甲骨文作、、,像物品开裂之形,故引申有起来、竖立、爆炸、劳作等意义。金文多作、、等,仍得甲骨文“乍”字的底蕴。但金文少变作,已有讹变趋向,很难从字形看出开裂之义。小篆作,整个字形彻底讹变。《说文·亡部》:“乍,止也。一曰:亡也。从亡从一。”因为许慎据讹变的小篆分析,其解释“乍”字的形和义皆错。
“克”字甲骨文作、、、,像人仰头张口弓腰咳嗽形,当为“咳”的初形,点或块状代替气息或者痰。金文和战国古文作(利簋)、(小克鼎)、(秦公镈)、(德克簋)、(GAFC2侯因GAFC3敦)、(中山王GAFBD鼎)、(曾侯乙墓竹简45)、(郭店楚简老子乙2)等,《说文》古文作、,小篆作,受填空记号、粘连、断裂等影响,逐渐变化而至整字讹变的过程一目了然。许慎于《说文》中云:“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因据讹形分析,于形于义皆未得。另按:甲骨文有一字,各家未识,《甲骨文编》附于“存疑”中。我们比较甲骨文“克”字,明此形即“克”的异体,用曲线表示气息而已,也形象地表现了咳嗽之状。
“丮”字甲骨文作、、,为象形字,像人张开双手跪拜之形,当是稽首之“稽”的本字。金文延续甲骨文之形体,初作,少变而作,但未失精蕴,仍能够看出稽拜之态。《说文》所收古文作,发生讹变,已毫无稽拜之形。《说文》小篆作,虽比古文保留了较多的甲、金文的轮廓,但也讹变不少。许慎据讹变的形体立说,云:“丮,持也。像手有所丮据也。”于义于形皆失。
“易”字甲骨文本作、、等,金文大多继承甲骨文的形体,或加填空记号作,或复古作、,皆像把容器中的酒水倒出的样子。原本像器柄,加记号后将手柄上移,出现、等形,这就使字的右边像蜥蜴的头和身子,与原字的形、义都大不相同了。春秋战国文字延续了讹变字形,出现(蔡侯钟)、(三体石经·尚书·君奭)等字形。
“申”字甲骨文作、等形,为象形字,像闪电的样子,是电、申、神、伸等的初形。西周金文多从甲骨文的形象,但寬儿鼎却作,已发生讹变,看不出电光的形象。春秋战国时,既继承了正确的写法,也延续了金文中讹变的形体,如楚子簠作,战国古文作(包山2号墓楚简42)、(信阳1号墓楚简053)。甚至如《说文》籀文作、《说文》古文作,讹变更严重,毫无闪电的影子,和原形大相径庭。
“长”字甲骨文作、、、、等,象老人头发或手臂细长形,为象形字。金文基本与原形相似,但是战国时出现多种变化,有、(皆见《说文》古文)、、、、等,都是讹变的字体,已经看不出以形表意的特点。小篆讹变作。许慎分析其结构说:“从兀从匕。兀者,高远意也,久则变化。亡声。匕者,倒亡也。”徐铉加按语说:“臣铉等曰:倒亡,不亡也,长久之义也。”皆依据讹形分析,不确。
“闻”字甲骨文作、等,用特写的耳朵表示听闻义。金文作(大盂鼎),将记号讹变而字作(利簋)、(徐王子GAFC4钟),再将人形讹变而字作(GAFC2侯因GAFC3敦),竟变成下从斗而上不知何象的字形,毫无理据。
“友”字甲骨文本作从二又的,或变向作,金文初继承甲骨文作、(王孙钟)、(嘉宝钟)等,皆为会意字,用方向相同的两只右手并列或重叠以会志同道合、协作相助之意。西周金文或加记号口形作,或于口旁中又加填空记号作,毋庸说这种加记号的变化是一种合乎理据的变化。《说文》“友”下收录了两个古文形体,第一个作,在两个“又”的竖线中部加作为填空记号的横线,也属于循变。但第二个古文作,竟然变成上从羽而下从百的结构,双手和口旁都讹变了。
“死”字甲骨文、金文皆作形,从人从歺,“歺”表示残骨,以人跪在枯骨旁表示死亡之义。但望山1号墓楚简作,《说文》古文作,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构造,显然发生讹变。好在小篆作,仍保留最初的结体,一直流传至今。
“良”字甲骨文作、等,为辅助象形字,皆像古代两端有进出廊道的房屋样子。西周金文除继承甲骨文的初形外,或美化作,但仍能看出廊道的样子。不过春秋战国出现诸多变化,或如中山王壶作,《说文》古文作、、,小篆作,都与原形差异显著,无疑是讹变的字体。
“师”字甲骨文作,以弓形象征军队。西周金文除偶然作外,其余皆加意符“帀”作(令鼎),表示用弓箭环绕之处即为师。后演化为(齐叔夷鈽)、(三体石经·僖公),进而讹变为(《说文》古文)。
甲胄之“胄”(冑)字,最早见金文,初形作(豦簋)、(小盂鼎),上像头盔,而用目旁代表头部,两形组合表示戴在头上的兜鍪即为胄,为辅助象形字。小篆作,因“目”和“冃”(“帽”的初形)的形体相近且据义赋形,目旁讹变成冃旁,原头盔形变成了声符“由”,整个字形发生讹变,以致许慎出现误解,在《说文·冃部》说:“胄,兜鍪也。从冃,由声。”意义训释正确,但因依据讹变的形体,字形分析出现错误。至隶书,因为把冃旁和肉旁都讹混成月旁,使甲胄之“胄”和胄胤之“胄”混为同形字。(比较《说文·肉部》:“胄,胤也。从肉,由声。”)
三 古文字讹变之原因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发现汉字讹变的原因有六:因结构相近、因误解记号、因误解字形、因以字形附会字义、因字形断裂、因字形粘连。
第一,因结构(包括整字和偏旁)相近而混淆。许多讹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汉字构形系统中存在相近的结构,当用形近部件的构意或读音也可以与该字的某一义项或读音建立联系时,就很容易出现形近相讹的现象。唐兰先生《古文字学导论》已经分析了这种现象:
因为古文字多混淆,所以有些文字常被误解,有些是后来人不敢认识的(或者是误认)。例如:、是容易淆乱的,象人口,问、启、名、鸣等字所从都是。是象凵卢,在古文字多作,和人口无别,册、、古、喜、合等字所从都是。《说文》把古、喜、合当做从人口的口,册字变做册,所从曰字,也从口。字变做,从白,都错了(凡从曰从甘的字,大都从凵卢形的口变来,《说文》从人口误)。字往往和字混淆,所以字会误成疑……字往往和(刀)字混淆,所以侄字会误成到……
古文字里的山字作,或作,火字作,本已相近。字后变做,字后变做和,愈易淆乱。所以光字本作,或体作,从丘可证,却变成从火的光。而羔字本作,象炮羊火上,变成形,就误为(岳)字了(卜辞里所记的“羔”即后世的“岳”)。
卜辞里的“足”字和“正”字同作,所以昔人不知有足字,近时郭沫若才区别了出来。字本象簟形,变做了字(毛公鼎弼字作者, 钟作可证),和因字作相乱。我们由此可知《诗·小戎》“文茵畅毂”的“茵”字,其实当作字,当于《说文》的“鞇”字(即鞇字,罗释席字误),后来误为因,就读为因声,添出了“车重席也”的“茵”字了。
文字的错误,有些只是字形的一部分,有些是整个文字传讹了。前者例如:从的字易误为,从手形的字易误为,从的字易误作,从贝的字和从鼎的字容易互误,从大的字和从人的字容易互误,虽多淆乱,还可找到同例……
混淆和错误是例外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例外而忽置,不然,在研究的进行里将时时会感到窒碍的。[1]245-248
除了唐先生举的例证外,我们以“至”字为例说明。
“至”字,甲骨文作、,从矢从一,以矢下落到靶子表示到达义。由于矢和鱼结构相似,战国金文或作,望山楚简2.38作,包山楚简2.16作,皆把矢讹作鱼。
和“至”的讹变类似,“牡”字的士旁变为土旁,“乔”上的止旁讹变作力旁、屮旁,“献”“真”“贞”“员”“具”等的把“鼎”旁变为“贝”旁,都是因结构相似造成的讹变。
在此附带说明,学界普遍认为把“鼎”旁讹变成“贝”旁是出于简化的原因,这种认识恐怕值得商榷。因为古文字中也有把“贝”旁讹变为“鼎”旁的相反情况。如“宾”字,金文有加“贝”旁的,金文后来又有、等,却把“贝”旁讹变作“鼎”旁。再如“宝”字,甲骨文作或等,从宀从玉从贝。金文早期有加意符兼音符的“缶”旁而作、等,但皆从贝。金文又有把“贝”旁讹作“鼎”旁者,如(徲盨)、(同簋)。如果说“真”“贞”“员”等字把“鼎”旁写作“贝”旁是简省而讹变,那么“宾”“宝”等把“贝”旁讹作“鼎”旁,只能说是繁化的原因,但同一时期相似的两个偏旁之间的变化又是简化又是繁化,显然是矛盾的,说不过去。因此,我们认为“鼎”旁讹变作“贝”旁,不是出于简化的原因,而是由于形体相似的缘故。
误解结构还会造成连续的讹变。如金文“朢”作、、等,像人站在高处张目仰望月亮的形象,以此表示仰望的意义。但金文中也出现从言者,概由于把“月”旁误为“口”旁,而“口”和“言”的表意功能相同,于是以“言”旁替代所谓“口”旁,就出现讹变的形体。
除了以上结构外,古文字中因相似而容易互相讹变的形体还有:
大、夫、交与矢:“大”本作(甲骨文),像正立的成人形;“交”作(金文),像人双腿相交;“矢”作(甲骨文)、(金文),像箭形。三个字本有区别,但由于形体相似,作偏旁时便容易混淆。如“旅”字,甲骨文作,金文作、、,从GAFB7从一人或二人、三人,表示站立在大旗下的人即为旅。甲骨文又有一个从GAFB7从大的字(粹258),梁东汉先生认为是“以人立于旗下会意”[23],当是“旅”的异体,但这个结构在甲骨文又作从GAFB7从交或从矢者(明藏575),“交”或“矢”显然由“大”讹变成。“矩”字金文本作、、,从大或从夫持工或巨,表示成人拿的尺子即是矩,但因“大”“夫”与“矢”字形体相近,篆文便讹变成从矢旁的。
囗、凵与口与○与厶:甲、金文中,表示地穴、区域类意思,用“囗”(作)或“凵”(作)字。表示嘴巴义的“口”甲骨文作。“○”作,像圆形。本来,几个字独立使用时,形状以及大小有比较清楚的区别,但由于结构相近和书写工具的影响,作偏旁时就容易互相讹变。
或(大口)经常被误写作(小口)。如“正”字,甲骨文本作、,杨树达先生认为是从足向城邑会意,但甲骨文已经常写作、、,上面讹变成了小口。又如“各”字,甲骨文本作、、,表示脚趾从高处下到一个区域、地方,乃“佫”(后通假作“格”)之初文,但甲骨文中已经有讹变作从口的、。金文、篆文皆以讹传讹,分别作、,以致许慎于《说文·口部》云:“各,异辞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听也。”“喜”字,甲骨文本作,或加记号作、,下所从即为地方、地域的形象,表示把鼓放到外面庆祝即为“喜”。金文有作、、者,小篆作,皆把原来表示区域的大口讹变成表嘴巴的小口。上文分析过的把“鲁”字囗形和凵形变成口旁也属此类。
和上所说情形相反,口旁也容易讹误成囗旁或○旁。如“公”字,甲骨文,以口和眉代表面容,为面容的象形字,是面容的“容”的初文。但甲骨文也有作者,金文或作、、,将口旁误作“囗”和“○”。战国古文或作(包山2号墓111),已断裂作“厶”形。《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苍颉之初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公厶之相背,乃苍颉固以知之矣。”大概即据这类字形分析结构。小篆作,乃承古文之误。战国古文甚至有把口形两边断裂使字作(曾198)者,下部竟讹变成“二”形。
止、屮、又、上、山、丫:甲骨文“止”作、,“屮”作,“又”作,“上”作、,作为独立字形,区别昭然。但作偏旁时,常常讹混。如前文所说的“正”字,本从止,但金文竟有、,分别讹变为从屮和从上。“走”字金文本作,从夭从止,表示人快跑之态,但金文也有作(伯中父簋)者,“止”讹变成“又”。甲骨文“复”(復)字本作,或加止旁作,陈永正认为是往返覆穴之形[24]。但金文却有把止旁讹变作又、屮、斗或横“丫”形者,出现、、、、诸形。其余如我们上文分析过的“奔”“前”,也都有把止旁讹变为屮旁或山旁的情形。
这种因结构相近而讹变的偏旁还有:凡与舟、口,肉与月、夕、口,口与曰、甘、其、自、白、百,目与凡、舟、肉、冃,等等,已揭橥上文,此不赘。
第二,添加、误解记号而讹变。按照我们把古文字的记号分成填空记号、别形记号、指示记号和代替记号的分类,我们发现记号在古文字中普遍存在,特别是填空记号,几乎每个古文字都有过它的影子,但由于前人对古文字记号缺乏系统、全面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其普遍性,往往会误解记号而导致字形的讹变。
“保”字甲骨文作、,表示将孩子背在背上保护。金文大多作、、诸形,习惯在“子”旁的竖线旁加一条或两条斜线作为填空记号,使字的结构平衡,小篆选取金文的一种字形写作,使右边的子旁变成“呆”字,失去因形见义的作用。
“曾”甲骨文作,金文或作、,上像升腾之热气,中像锅类本身,下像火炉(或为填空记号),用上面的热气和下面的火炉限定中间的器皿,表示该物为蒸烙食物的器具,当是“甑”的本字。金文或在下面表示火炉的偏旁中加填空记号,出现、等,导致“口”与“甘”“曰”讹混。
“肥”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如包山楚简作,从肉而像肥壮的肉条。战国文字或在右边肉条形的空缺处加填空记号而使字作,小篆承之作,右边就误为(卪),以致许慎于《说文·肉部》云:“肥,多肉也。从肉从卪。”
“寡”字最早见于金文,作、等,以一人在屋子巴眼相望表示孤单义。战国文字或省宀加四点作,小篆作,下所从“分”旁乃“页”下“儿”与两点合成而讹。
“畜”字甲骨文作,本从田(或以为从胃)幺声,表示蓄积于田义。金文承甲骨文字作,战国文字或加记号作,小篆承之作,或体作,以致许慎于《说文·田部》以为是从玄或从兹的会意字。
“昜”字甲骨文作或,以日在上方表示阳义。金文或加填空记号作、、等。小篆承之作,以致许慎于《说文·勿部》分析其结构为从日、一、勿。
“衆”字甲骨文作,表示众多人。甲骨文或加记号作、,金文承之作,小篆作,将上部的记号写成相似的(目),以致许慎于《说文·乑部》以为从目。
这类因加记号而讹变的字还有上文分析过的“者”“利”“鲁”“易”等。
第三,误解字形导致讹变。这主要是把形符误解为声符。
在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些表意字的意符受字音的影响,写成与该字读音相近且与自身形体相似的表音部件,致使字形讹变,造字理据也相应地丧失。
“到”字,最早见于金文,作(曶鼎)或(伯到簋)或(伯到壶),是在“至”字上加人旁的孳乳字,明确到达义。小篆作,把人旁讹变为相似的刀旁,以致许慎在《说文·至部》分析其结构是“从至,刀声”。
“福”字,甲骨文作,以酒坛充满酒来表示福禄的意思。后加形作,从示从酉;或再加双手作,从示从酉从廾,表示双手捧着酉(酒坛子)向神灵祈求福禄的意思。金文作或,简省了甲骨文中的双手,酒坛也类化成罐子之类的东西,后来又索性把罐子当做音符,“福”字也就成为从示畐声的形声字了。同样,“富”字金文本作、,以屋子中放着盛满酒的容器表示富足义,但春秋时作,已很难看出酒坛的样子,形符变成声符,字即成为从宀畐声的形声字。
这类误形符为声符的典型字还有上文分析过的“饮”字等,此不赘。
第四,用字形附会字义而造成讹变。有些古文字的讹变,是由于扭曲字形去适应甚至附会字义而导致的结果。
“甸”字最早见于金文,作,从田从人,本义为农夫在田地耕作。小篆作,“人”讹变成“勹”,以附会京郊义。
“封”字本以“丰”为之,甲骨文作,其中表示枝叶茂盛的树木,表示土堆,表示植树为界义。甲骨文或加又旁作,金文承之作,小篆作,误将金文的写成(之),故《说文·土部》说其结构是从之从土从寸。“之”意为长出,像植物过了发芽的阶段而日益茁壮。既有植物之形,又有扩张之意,还和结构相似,就讹变为。
“雍”字金文作,从隹从水从吕。小篆作,把“吕”讹变为“邑”。雍的本义为邕。《说文·巜部》:“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虽然“吕”讹变为“邑”,但雍字的本义变得更为明晰。
“丧”字,甲骨文本借“桑”字为之,先作,后或加口旁作(合19492),或重复口旁作(合58)、(合29115),等等,字就成为或从口或从吅或从品桑声的形声字。“丧”字的声符“桑”在甲骨文中已有较多变化,如(合28929)的声符就很诡异。金文中其声符变化更多,如(毛公鼎)、(冉钲鋮)等,甚至小臣鼎中作,都是将形写成,同时根部加(亡),强调消失义,甚至将口旁换成止旁,均已失去“桑”旁的踪迹。这样变化的原因在于“丧”引申表示死亡、消失的意义而强迫字形以就字义,给声符强加线条所致。辗转至小篆,字形作,更是谬以千里,以致许慎不察,在《说文·哭部》完全按照讹形分析,云:“丧,亾也。从哭从亾会意。亾亦声。”
第五,因离析导致讹变。书写者把一个部件拆分成至少两个部件,使部件分裂,字形发生讹变。
“黑”字甲骨文作,上部是脸,下部为人形,表示脸上有污点。金文加两点指事符号作,强调了脸上有污点的特征。有的金文则在脸部、身上都加表示“污点”的指事符号而使字作,表示全身沾有污点,有的金文还作(铸子叔黑臣簋),脸上加了更多的污点。篆文将金文沾满污点的花脸写成,又误将下部的拆分写成,字形作,导致表人形的“大”消失,字形讹变。
上文分析过的“周”字从甲骨文、金文的、,到金文的,战国古文的和小篆的,“章”字等的变化,也皆是因断裂导致的讹变。
第六,由于粘连而导致讹变。由于书写者将本应相互独立分开的线条、笔画、偏旁,粘连合并在一起而造成字形讹变。
“丞”字,甲骨文作,金文作,表示用两手拯救落入深坑之人。小篆作,将人形与凵形粘连成山旁,以致《说文·廾部》云:“丞,翊也。从廾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义。”
“实”字,最早见于金文,作,从宀从田从贝。小篆作,把田部的横延长粘连,导致形体错误,致使许慎《说文·宀部》云:“实,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
“帅”字甲骨文作(合7074),以代表两个人的两只手持一棍表示带领义。金文或加形符作(五祠卫鼎),或省一手作(师虎簋),小篆作,将甲、金文的粘连合并而讹误成。
“野”字甲骨文作(合22027),以有林木之地表示郊野意。战国古文或作(陶汇5.156),成为从土从田予声的形声字。小篆作,把“田”和“土”粘连成“里”旁,导致字形讹变,无法分析其理据。
另如上文谈及的“折”字,由甲骨文的、金文的形,变为小篆的,公认是将断木粘连而讹为手形。
四 讹变之影响
汉字的书体经历了数次演变,一些字在简化,一些字在繁化,而一些字又讹化。简化、繁化对汉字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样,讹化对汉字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诚如上文所引唐先生所言:“混淆和错误是例外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例外而忽置,不然,在研究的进行里将时时会感到窒碍的。”
我们认为,讹变的影响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而以消极影响为主。
其消极影响是:
第一,破坏了汉字有理有据的结构。讹变切断了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天然联系,导致后人无法通过字形推断字的本义。
第二,造成字的混同。由于讹变,许多原本不一样的部件或字形变成同形,影响了人们对字义、字音的理解、识读。
讹变的积极影响是:讹变往往把不同的部件、偏旁混同为同一个偏旁,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选用的是比较简单的部件,使一些古文字的线条减少,书写快捷,符合汉字发展过程中简化的总趋势,适应了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本质。如“帥”“折”“员”“貞”“富”等,字体简单了,同时新的形体与新的理据、读音在新的层面达到统一,既适应了汉字演变的需要,又从另一角度突出了理据、声音。
参考文献:
[1] 唐 兰.古文字学导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1.
[2]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3]高景成.略谈汉字字形发展中的合并与讹变[J].河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4]林 澐.古文字研究简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
[5]张桂光.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M]∥古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153.
[6]金国泰.汉字讹变三题[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
[7]刘 翔,陈 抗,陈初生,董 琨.商周古文字读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253.
[8]王梦华.汉字字形的混误与讹变[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
[9]季素彩.汉字形体讹变说[J].汉字文化,1994(2).
[10]林志强.关于汉字的讹变现象[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11]王海平.汉字形体讹变浅说[J].新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12]古敬恒,李晓华.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J].江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13]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14]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418-419.
[15]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16]赵 诚.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29.
[17]阮 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1:773.
[1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冯玉涛.凤凰崇拜之谜[J].人文杂志,1995(5).
[20]王 筠.说文句读·卷十二[M].北京:中国书店,1983:16.
[2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5.
[2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卜辞通纂[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225.
[23]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06.
[24]陈永正.释[M]∥古文字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25]彭 霞,冯玉涛.《说文解字》形声字之“多形多声”问题分析——兼论形声字形成的层次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01).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emerged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prevailed in the entire stage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at all stages. Mr. Donelan in the 1930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phenomenon of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but almost nobody put forward a further discussioni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Until the recent 40 years, this issue has been attached importance to.More than ten scholars like li Xiaoding, Zhang Guiguang have a heated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s, types, reasons and result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the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finds that almost all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involved in the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more or less, lightly or heavily, false changes and simplific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a split State. The three types of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are about meaning, phoneme and character. There are six reasons for the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its similar structur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mark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glyph, , glyph attached meaning, the glyphs and glyph adhesion. The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itself indeed has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 however, the negative effects matter more.
Key words:ancient characters;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types of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causes of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 程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