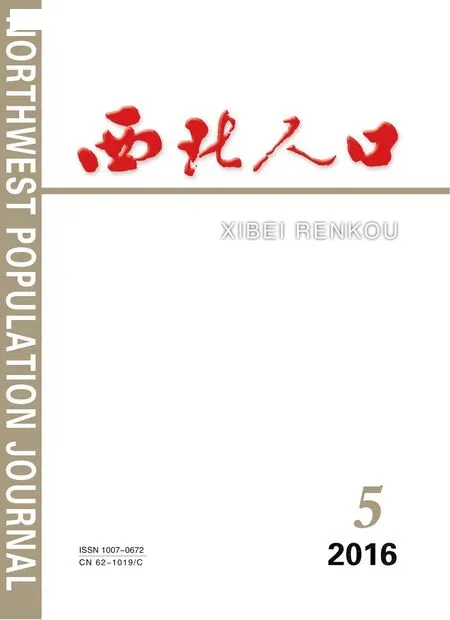发展性关怀抑或反思性关怀?
——对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社会关怀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陈晶环,叶敬忠
(1.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成都611130;2.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
发展性关怀抑或反思性关怀?
——对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社会关怀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陈晶环1,叶敬忠2
(1.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成都611130;2.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100193)
国外学者对社会关怀提出了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侧重强调关怀者和被关怀者是一种发展关系,第二层含义重点阐释社会和个体关于谁需要关怀,以及如何关怀的认知对关怀资源生产和分配的影响。本文以这两层含义为维度,界定出当前我国学者针对农村留守人口存在着两种关怀:发展性关怀和反思性关怀。发展性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村人口所面临的困境,但这种关怀依旧处于发展主义框架中。反思性关怀超越发展主义对关怀的限制,追求人本性关怀,从中深刻理解留守人口的境遇,对社会关怀研究的推进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分析发现,留守人口在关怀需求和关怀资源、关怀付出和关怀收获上存在着不对称;一种单一的、齐化的,以经济增长为衡量指标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判断标准,使得对留守人口的社会关怀不断的理性化、商品化。
社会关怀;农村留守人口;发展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和自身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很多农民只能自己进城务工,将子女、配偶和老人留在了农村,形成了“留守人口”。流动对留守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凸显。作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如何缓解留守人口“被留守”的现状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
(一)概念界定
社会关怀的概念来源西方国家的Social Care。20世纪70年代后,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复苏,引发了劳动者对个人不断付出劳动,却难以从社会再分配中收回福利的控诉。由此形成了一种社会再分配危机,或是称之为社会关怀危机(Shahra Razavi,2011)。虽然社会关怀危机是全球性的,但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的关怀危机是同质的。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社会关怀分配情况与发达国家紧密相关,这种相关性在上个世纪末有了更明显的表现。全球发展的不平等造成了不同个体获得物质资源机会的不平等,进而强化了关怀资源的不平等(inequalities of redistributing care resources),尤其是从事情感关怀工作的劳动力,他们来自于贫穷国家,所提供的情感关怀为富裕国家的成员所消费。例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劳动力为了满足生活需求,流动到西方国家务工,照料西方国家的儿童,而自己的子女则留守于家乡为别人照顾。关怀链(care chains)的改变,引发了学者对流动人群和留守群体关怀(Hoch-schild,A.R,2000)。总体来说,社会关怀涉及到三个维度:经济学维度(强调经济增长,关注无酬工作人员的待遇)、政治学维度(强调公民权利,关怀是公民的义务,也是权利)、社会学维度(强调关怀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Shahra Razavi,2007)。社会学维度是本文所关注的内容。国外学者将此维度的社会关怀阐释为一种发展关系,即提供方和接收方之间的互动发展,在深层上呈现出关怀需求和资源的不对等(Susan Himmelweit:2005)。在发展关系上,Shahra Razavi认为发达国家的妇女往往通过雇佣发展中国家的务工妇女,来弥补自身外出工作所造成的关怀缺失。然而较低的待遇导致双方的利益都受损,影响双方互动(Shahra Razavi,2011)。在关怀需求和资源的不对等关系上,Lourdes Benería提出了,人口的流动造成落后地区的儿童、老人无法享有家人的照料,而发达地区可以通过雇佣来弥补国家层面上社会关怀的缺失,在现实中,人们往往认为缺少家庭收入是造成关怀不足的主要原因,忽略了流动对关怀造成的影响(Lourdes Benería,2008)。
(二)研究内容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农民地位一直受到特别地强调,在士、农、工、商的职业序列中,农仅次于官。那时的农民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农村绝不需要改造以满足城市精英的特殊审美意识。农村如同世外桃源般,与城市相对应存在,维持乡村自然的“野”和“朴”的状态是许多人怀旧时最乐于抒发的情绪主题之一(赵旭东,2008)。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后,农村的原始状态成为诟病所在,城市成为农村发展的范本。通过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强制商品化,同时,一系列政策措施也鼓励农民融入商品经济之中(叶敬忠,2012)。农村不再独立存在于城市,而成为城市的附属物品和原料市场。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从事城市人口所不愿意做的苦力工作,支持城市的发展。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和艰辛的付出,并没有使他们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留在农村的农民,承担着繁重的劳作,忍受着亲人分离的痛苦。因流动而带来的留守,造成了留守老人的养老、留守妇女的情感、留守儿童的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针对这三类群体,政府和学界对此都有了一定的关注和探讨,然而为何留守群体生活现状的改观依旧非常有限?本文以改革开放后我国管理体制的变迁为背景,分析农村发展路径的变化,对留守人口形成当前生活现状的历史背景进行回顾。此内容作为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论述。借助国外学者对社会学维度社会关怀的定义,即关怀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行为、政治政策,在深层含义上体现了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微观个体在谁需要关怀,谁有责任提供关怀,以及如何分配关怀的认知上产生影响,界定出国内学者研究的两种类型:发展性关怀和反思性关怀。前者关注于关怀的提供方和接收方之间的互动形式、渠道,后者侧重于从城乡互动、社会分配来阐释留守群体关怀的变异,这两种关怀类型分别作为文中的三、四部分来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综述分析,以期解释为何留守人口在社会关怀中依旧面临窘境的问题。
二、研究背景:社会管理体制变迁下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到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总体的支配方式由总体控制和群众的总体动员实践经济积累和社会发展,向调动基层个体的积极性、灵活性、总体把握局部放开的方式转变。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市场成为调控的主要因素,效率变为关键的要素。可以说,农村留守群体的生活现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发展政策紧密相关。在本部分划分了三个阶段对农民个体生活境遇的变化进行了描述。若缺少这部分的考量,则会欠缺历史维度,造成社会关怀研究的表面化。
1978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实行土地承包,成为农村改革的起点。1982年1月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了包产到户、承包联产等责任制,正式拉开了序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还改变了单一僵化的生产关系,农民个体和家庭重新回到土地经营的结构中。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之外的收入,也就是说农民种地与务工两不误,并不需要在两地奔波。在改革的前十年中,城乡之间并无直接互动,以国家为中介进行间接互动。
到改革的中期,城乡之间的互动逐渐增多,并更加直接。在城市中,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也掀开了这个阶段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增长、数字提升、效率改善成为这十年的关键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成为衡量发展与否、进步与否的指标,一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心态。对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一方面导致物资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加重个人负担,尤其是对当时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而言。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兴起造成乡镇企业被迫关闭。农民不得不在土地、家乡之外寻找收入来源,进城务工的情况在这一阶段不再是特例,而成为常见的景观。在城市中出现了称为“农民工”的流动群体,他们年轻体壮的时候在强度大、条件差、缺乏福利保障的行业中工作,在他们无法产生城市所需要价值后返回农村。在农村中,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身影难以寻觅,更多地是很难产生经济价值的儿童、老人和照顾家庭的妇女。所以说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并不是剩余劳动力,而留守在家里的才是剩余劳动力(严海荣,2011)。在这一阶段,“经济热”带来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的流动带来了留守群体的出现,也带来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进入到新千年之后,改革的重点由工业化向城市化、商品化转变。在这一阶段中,经济的增长以土地为依托的特征明显,而城市化也体现出一种对土地的占用、经营。按照现行法律,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征收、开发和出让农业用地,其征收费用远低于城市建设用地出让的价格,并将低价收购的农业用地,进行平整、开发后,以招、拍、挂等形式在土地二级市场上出让(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这对地方政府来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也是政绩的体现。然而,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看,“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发展模式使得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展,社会保障滞后。对于农民来说,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了城市发展和政绩提高的砝码。农民丧失了经济来源,也打破了自然的、本土的生活方式。同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食价格,处于一种持续低迷的状态,即便是有土地的农民,也并未因种地免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如果说在改革中期,农民还有更多地空间回到农村,而在这一阶段基本生存资源的丧失——土地的流失和种粮难以解决温饱的现状,使得漂流在外的农民更难回到农村,进而加剧了留守情况。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三十年中,农村与城市的互动由无到有、由点到面,农民从中受益,但也从中受苦。留守群体便是这种苦的一种具体呈现。如果缺乏对留守群体产生历史背景和社会变迁的考察,很难从根本上来思考对留守群体来说何谓符合需求的社会关怀。
三、发展性关怀:发展主义的后果
如上部分所论述的内容,农村的从属地位和农民的艰辛境遇变得愈加明显,而相对应关怀的缺失,造成了留守老人在家死亡七天之后才被发现,留守儿童缺乏照顾出现的意外死亡,留守妇女受到侵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由此引起了对留守群体关怀的讨论。依据Susan社会关怀的第一层含义,即社会关怀呈现出一种发展关系,提供方与接收方之间的互动,本文将之简称为发展性关怀。此类关怀以发展为目标,或是实现关怀接收者自我发展能力。发展性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留守群体的生活困境,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一)留守老人的养老关怀
长期以来,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主,子女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承担者。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留在老人身边的子女越来越少。虽然外流子女往往会通过对老人的经济补偿来弥补照料等方面的缺位(孙娟鹃,2006)。但经济收入的增长,并未超越留守老人生活负担的增长,并且留守老人从外出子女经济支持中获益程度具有不稳定性和差异性(王全胜,2007)。这也就意味着,家庭因流动而获得的收入不足以使得留守老人可以安享清福。反而家中劳动力的缺失,造成留守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和家务劳动负担都加重了(杜鹏等,2004)。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大减少了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家庭成员流动与减少,使得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研究者多从经济保障、照料援助和生命关怀(蒋艳、钱娟,2007)三个方面入手。在经济保障方面,以土地保障为依托,探索多元养老保障形式(姚引妹,2006)。在照料援助方面,利用家庭支持网、社会网等网络缓解养老的困境和压力(东波、颜宪源,2009)。在生命关怀方面,加大农村老年人体育活动设施的投资力度(曹伟伟,200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高翔,2010)。
留守老人在生活中很容易产生生活“没意思”的感觉,而这种“没意思”正是源于没人照料、没人说话的孤独感(杨华、范芳旭,2009)。邻居、亲戚很难代替子女,村委会的人员也不可能每天陪伴所有的留守老人。当前围绕留守老人所进行的政策性研究和学术关怀并未聚焦于农村老人之所以成为留守老人的原因,这将造成对留守老人的关怀研究成为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持续性研究。
(二)留守妇女的劳作与情感关怀
农村妇女的身份之所以转化为留守妇女,一方面在于农村壮劳力流动到城市来获取家庭收入,而城市并没有提供“举家搬迁”的制度支持,教育、医疗、社保阻碍着农民进城长住的步伐。另一方面,农村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与男强女弱的性别观念导致两性之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农村妇女往往留在农村照顾老人和儿童。留守妇女肩负着本应该夫妻照顾家庭的共同责任,其所面临的生活和精神压力不容小觑。
当前学者对留守妇女的关怀主要表现在劳作关怀和情感关怀上。在劳作关怀上,农业女性化的背后是留守妇女劳动负担沉重、劳动强度大和家庭地位的问题(吴旭,2008)。若家中土地数量较大,无形中增加劳动负担;若拥有土地较少,则妇女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较少,妇女对家庭的有酬贡献则大大降低,家中的地位也受到影响。流动到城市的男性,仍是家庭农业生产的决策者,女性主要扮演的是劳作者,而非权力者。在情感关怀上,学者关注于流动对留守妇女婚姻所造成的影响。丈夫和妻子之间出现了城市化不同步的现象,丈夫处于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变化的生活环境中,而妻子则处于相对静态的、封闭的、少有变化的生活状态之中(吴惠芳、饶静,2009),留守妇女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留守妇女的生存现状和情感需求促使学者从多个维度探讨应对方法。在个人层面上,学者建议留守妇女应该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形成自强自立自主的意识(许传新,2007)。在农村层面上,增加对留守妇女的技能培训,提高收入(楚向红,2008)。在国家层面上,加快农业机械化,减轻留守妇女劳作负担(黄安丽,2007)。在提供主体上,除了相关政府部门之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建立农村个案工作室,通过采用积极聆听、复述,从而使留守妇女达到助人自助的效果(孙可敬、傅琼,2010)。
留守妇女作为关怀的提供者,进行着无酬劳动;作为关怀的接受者,她们对关怀的需求也在增加,同时还面临着挣钱养家的压力。通过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对留守妇女因流动而留守,并由此造成社会地位下降和心理负担增加等后果形成了共识。然而相关对策的提出却以一种经济难度作为解决问题的捷径。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留守妇女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但留守妇女的身份依旧没有改变,流动所造成的家庭风险依旧存在。
(三)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生命关怀
劳动力流动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坚实力量,但也因此产生了与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共同存在的另一群体——留守儿童。农村儿童之所以留守,一方面与造成农村老人、妇女成为留守人口的原因相似。另一方面,2001年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的调整,将农村中小学都集中到县市中。为了上学,这些学生远离父母,成为县市中的留守儿童。
当前国内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教育关怀和生命关怀。在教育关怀上,当一种标准化、齐一化的衡量指标横空出现在农村教育头上时,农村教育的发展被科学技术、实行赶超型战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所压倒(刘娟、刘晓林等,2012)。各种名义的市场化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加大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作为社会分层的工具,教育反而呈现出凝固和制造社会差距的功能(吕利丹,2014)。城市偏向的课程内容和评价标准,脱离了农村生产生活实践和农村社会发展(傅宝英,2007)。以城市为取向的课程内容,也并未帮助农村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相关院校,反而是农村学生在城市院校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生命关怀是建立在教育关怀的基础之上,即意识到农村教育出现了问题,围绕留守儿童的一系列关怀由外围逐渐向内围转变。伴随着父母外出工作,家庭教育缺失于儿童的成长过程。家长对儿童的心理需求关注也不够,致使有些孩子用“寂寞”、“烦躁”、“焦虑”等词语来描述心理感受(叶敬忠、王伊欢,2006)。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心灵关怀缺失的表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极端表现,包括自杀和犯罪;二是日常表现,包括逃学、沉溺网络,以及生活无聊、无助、无意义感等心理体验(马多秀,2011)。
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关注和生命关怀,促使学者从不同的主体入手来思考如何改善留守儿童所处环境。就学校而言,开设“亲情热线;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室”(赵玲,2007);建立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皮武,2008);建立“校中校”或“一校两制”的管理方式(殷世东、朱明山,2006)。就社区而言,可以建立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建立代理家长;扶贫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群体开展留守儿童的支持行动(叶敬忠、莫瑞,2005)。就国家制度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当前主要有两种途径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一是改革户籍制度;二是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潘璐、叶敬忠,2009)。
从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对留守儿童的关怀表现在两个方面:从人的角度来说,提倡任课老师和生活老师的作用;从物的角度来说,通过课外读物、图书馆、学校的建设来增加他们内心的正能量,减少孤独感。这些支持性举措为维系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之间的沟通、缓解留守儿童的心理负担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留守儿童所面临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留守于农村或县市,若忽视了这一点则很难从源头上实现对留守儿童生活境遇和心理活动的关怀。同时,留守儿童也是儿童,同所有儿童一样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我们不能将留守儿童问题化、过激化。
农民之所以自身的处境越艰难,对外界的需求越大,在于前提设定为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是贫穷的,而这种落后与贫穷是与城市和市民相比较的。由此,农村的问题变成如何去接近城市的问题(赵旭东,2009),农村也逐渐走进了一种发展主义的恶性循环之中。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同一性”思维和“齐一化”概念,试图建立一种普世的发展模型。这种意识形态造成农村建设日益城市化,造成土地成为建筑地,而非田地;农民生活也日渐商品化了,传统的红白喜事这些内容也都纳入了市场领域中。土地的流失和生活的商品化使得农民外出务工更多体现为一种被迫行为,而非自我选择的结果。流动与留守、离土与留乡,在发展主义的作用下拉扯着农村人口的福祉。发展性关怀阐释了关怀的提供方和接收方之间的发展关系,而在这背后两者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并没有揭示出来,也没有摆脱发展主义对农村、农民的偏见。对留守人口来说,发展性关怀虽能减轻现状,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关怀的需求。
四、反思性关怀:超越发展主义
Susan所定义的社会关怀的第二层含义为社会、个体的共识对社会关怀的认知产生影响,本文将之定义为反思性关怀,即关注于针对留守人口社会关怀的认知途径、分配机理。通过对三类农村留守人口社会关怀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这些关怀内容是一些良心学者和社会公益群体对留守人口所提出的人道性和弥补性措施,并未超越发展主义对农村人口所产生的辐射。公众对农村的认知、农村的流动化与发展主义不无关系,而这些形塑了留守人口所面临的关怀困境。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话语分析的方法,对这类“现实殖民”进行分析。话语分析工具对一个事实作出解释,即某些表征如何占据了支配地位,如何永无休止地形塑着现实被构想和被作用的方式(叶敬忠,2011)。如果我们把话语分析运用到社会关怀研究领域中,可以发现话语对农村、关怀认知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晏阳初将农民描述为“愚、穷、弱、私”。这四种病症在某些农民身上有所显露,但绝不是在每个农民身上都会生发这类实质性的“疾患”。可是,这种界定却成为一种“话语”在影响着没有去过农村、对农民的生活并不了解的城市人的思维(赵旭东,2008)。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强调发展就是硬道理。话语将之建构为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才是真正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化是发展主义的笼统体现,成为时代的口号。现代化的典型态度是霸道,这种霸道的一个核心表现就是唯我独尊,表现在城乡关系上,就是农村应该向城市看齐(叶敬忠,2011),也因此一系列以发展农村为缘由的项目、政策逐渐开展,而这种发展又单一的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指标。因此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成为总任务,而无法产生任何经济价值的照料、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关怀内容排除在发展之外。
反思性社会关怀采用福柯的话语分析法,解构发展主义束缚在农村留守人口社会关怀上的枷锁。这种关怀不直接提出对策,而是站在农民立场上,带有一种批判意识、反思态度来看待处于农村发展中留守人口的境遇以及社会公众、学者、政府的反应。通过上文对关怀群体的分析,发现留守老人由于年龄而留守;留守妇女因为照顾家庭而留守;留守儿童受户籍制限制而留守。虽然三个群体留守的直接原因不同,但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这种流动并非个体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生存空间挤压造成的非自我选择。一方面当政府相信唯有向城市看齐才是农村发展的出路时,新农村建设被地方政府的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冲动所挟持,拆村并居、拆房建楼也就顺理成章了(刘奇,2011)。这些大大损害了农民用以维持生计、扩大生存空间且减少能够抵抗风险的力量,失地农民在农村没有了生计之路。另一方面商品资本进入到农村,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用金钱来购买,而这些资料的价格也在不断地上升。虽说市场经济的趋势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中所有要素都必然而全面地被商品化,但是它却意味着人们无法在商品关系与其强加的原则之外进行生产(亨利·伯恩斯坦,2011)。农民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乡土社会都纳入到市场的价格体系中,无一不需要用来购买,关怀的商品化、理性化也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留守人口的选择是唯一的,依赖于流动来获得养老、生活、教育的支持。而其他社会群体,例如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与留守人口相比他们的关怀需求相对较弱,然而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障内容远多于留守人口。关怀需求与关怀资源之间不公平分配使得边缘的、修补的关怀很难从根本上改善留守人口的境遇。在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不平衡,即关怀的付出和收获之间的不平衡。农民为城市提供了服务,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但作为劳动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收入难以承担购买社会关怀的成本。
五、启示与讨论
对留守人口的关怀,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复杂,但也不像我们看到的简单。我们需要“后退几步,绕过那熟悉的事实,分析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背景”(米歇尔·福柯,2005),从单一的怎么办回归到是什么(农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为什么(究竟是何种原因让农民走上了“关怀”的不归路。)在“是什么”上,我们所关怀的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经济水平飞速提高,争取国家扶贫基金的经济逻辑?还是“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干部”的政绩逻辑?抑或是体现地区福利建设、精神道德建设的社会逻辑?对农民真正的关怀应建立在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同时关注于农民所思所想和所面临的的根本性问题。在“为什么”上,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当前农村人口需要关怀的现状,并且为什么关怀的持续却难以改善农村人口生活状态。农村留守人口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一半是冰山,一半是火焰”的状态。一方面是社会关注度不断上升,不同层级的政府、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将之纳入到视野中。另一方面,关怀的缺失、失衡、变味,造成亲人分离、儿童的另类童年、老人的静寞老年等困境。农村留守人口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就农村而言农村,就农民而论农民,那么城乡之间的不均衡依旧存在,农村和农民的困境依旧难以解决。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整体上反思农村留守人口需要怎样的乡村生活和关怀路径。
本文以国外学者对社会关怀两个层面的概念为分析框架,剥离开覆盖在留守人口关怀上为人所熟悉的面纱。分析发现关怀出现和关怀内容与当前社会的不均分配不无关系,一些关键性因素的掩埋或忽略,使关怀研究和关怀政策只能对留守人口的困境进行边缘性改善。我们应克服善意的关怀出现非善意的结果,从而使得关怀落在满足留守人口基本需求上。对农村社会关怀研究不仅仅需要人文关怀,更需要学理关怀的体现。也许在认识到本质后,才能形成“对症下药”的真正关怀。对于学者来说能否站在更高的角度、更深的层次和更理性的立场,对社会关怀研究的推进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1]曹伟伟.浅析老龄化与农村老年人体育开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社会科学,2009(13):250.
[2]楚向红.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中留守妇女问题研究[J].学习论坛,2008(11):69-72.
[3]东波,颜宪源.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老年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基于黑龙江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15-123.
[4]杜鹏.农村子女外出对留守老人的影响[J].人口研究,2004(6):44-55.
[5]傅宝英.城乡和谐发展中的教育公平问题与对策[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2-11.
[6]高翔.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0 (8).
[7]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M].汪淳玉,译.叶敬忠,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
[8]黄安丽.农村留守妇女生存现状的调查及思考[J].安徽农学通报,2007(3):14-15
[9]蒋艳,钱娟.农村留守老人需要社会关怀[J].社会工作,2007(12):47-49.
[10]刘奇.“灭村运动”是精英层的一厢情愿[J].中国发展观察,2011(1):37-40.
[11]刘娟,刘晓林等.发展主义逻辑下的农村教育:述评与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4):67-83.
[12]吕利丹.从“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终止及影响研究.人口研究,2014 (1):37-51.
[13]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7.
[14]马多秀.农村留守儿童的教师关怀[J].管理纵横,2011 (12):46-49.
[15]潘璐,叶敬忠.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5-18.
[16]皮武.学校关怀:打造“留守儿童”成长的生命绿洲[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4):68-69.
[17]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35-45.
[18]孙可敬,傅琼.农村社会工作与我国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建构[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30-35.
[19]孙娟鹃.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6(4):14-19.
[20]王全胜.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初探[J].学习论坛,2007(1):71-74.
[21]吴惠芳,饶静.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8-24.
[22]吴旭.关于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现状问题的综述[J].法制与社会,2008(1上):234.
[23]许传新.构建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J].中国国情国力,2007(3):47-50.
[24]严海荣.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J].读书,2001(3).
[25]姚引妹.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以浙江农村为例[J].人口研究,2006(6):42-44.
[26]杨华,范芳旭.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J].开放时代,2009(5):104-126.
[27]叶敬忠.留守人群——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痛[N].搜狐评论,2012-5-9.
[28]叶敬忠.留守人口与发展遭遇[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12.
[29]叶敬忠.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发展//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发展[M].汪淳玉,吴惠芳,潘露译,叶敬忠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6.
[30]叶敬忠,莫瑞.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1]叶敬忠,王伊欢.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情感生活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6(1):19-28.
[32]叶敬忠.一分耕耘未必有一分收获——当农民双脚站在市场经济之中[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1):5-13.
[33]殷世东,朱明山.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皖北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6(2):14-16.
[34]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和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J].社会科学,2008(3):110-118.
[35]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J].社会科学,2009 (2):53-65.
[36]赵玲.关怀留守儿童促进社会和谐——浙江省留守儿童工作的实践和思考[J].中国妇运,2007(10):14-17.
[37]Hochschild,A.R..Global Care Chains and Emotional Surplus Value’,in W.Hutton and A.Giddens(eds)On the Lourdes Benería.The crisis of care,international migration,and public policy,Feminist Economics,2008(7):1-21.
[38]Shahra Razavi.Rethinking Care in a Development Context:An Introduction,2005:873-904
[39]Shahra Razavi.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 of Care in a Development Context.Gender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2007(3):1-39.
[40]Susan Himmelweit.Can we afford(not)to care:prospects and policy.GeNet Working Paper,2005(11):1-32.
Developmental or Reflective: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f Social Care on Chinese Rural Left-behind Population
CHEN Jing-huan1,YE Jing-zhong2
(1.Southea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du 611130;2.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
Foreign scholars put forward for two meanings of the social care,the first meanings present a relationship of development,the second mean to interprete the cognitiv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that impact on who need to care and how to care.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social care,we define two kinds social care,which concern the study of Chinese scholars:developmental care and reflective care.Developmental care has slowed the certain extent the plight,which rural population facing up,but it is still in developmentalism framework.Reflective care surpass the limitation on social care from developmentalism,means to pursuit of human nature concern,which try to deep-understand of left-behind population situation and has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promote and perfect the social care research.It is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asymmetrict proposition on the population of left-behind care needs and care resource,care giving and care acquistion.A single,standarliazed and economic growth as the measure of the developmentalism became the judgment standard,which makes the social care for left-behind population ration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continuously.
social care;rural left-behind people;developmentalism
C912.82
A
1007-0672(2016)05-0071-08
2016-01-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研究”(编号:13ASH007)
陈晶环,女,河北石家庄人,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西部城乡统筹与社会建设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叶敬忠,男,江苏沭阳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发展历史与发展批判、发展干预与社会转型、农村社会与农政变迁、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