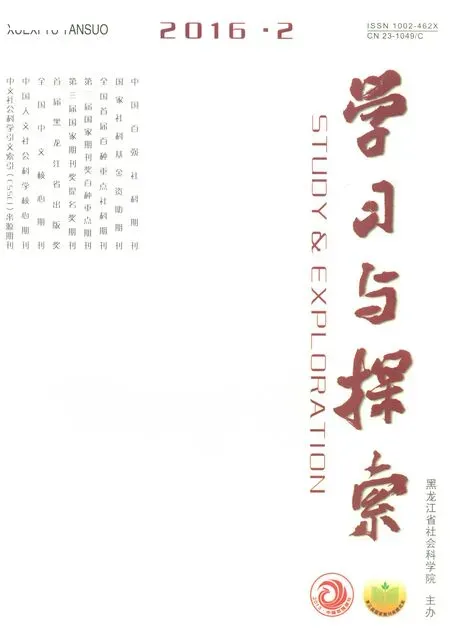中国治理现代化始终以增进人民福利为依归
洪大用,邵占鹏(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中国治理现代化始终以增进人民福利为依归
洪大用,邵占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摘要:治理实践与治理观念、治理借鉴与治理传承是两对辩证关系的概念,从这两对概念出发能够发现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发展道路与特殊品质。中国治理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善治”理论的关键是立足本土治理实践,侧重指向结果的程序改进,始终以增进人民福利为依归。推进这一取向的治理现代化需要着重处理好促进发展与科学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不断完善这一制度、改革国家与建设国家、扩大参与与规范参与、深化改革与加强法治这五对关系。
关键词:治理;国家治理;治理现代化;“善治”;人民福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此之前及之后,国内学界围绕“治理”和“治理现代化”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提出了各种观点和主张。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也同样适用于东方国家……把学习借鉴西方文明的合理因素,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简单地视为‘西化’甚至‘全盘西化’,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态度。”[1]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国国家治理西方化就会退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一穷二白’、‘一大二弱’。”[2]事实上,“治理”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弗朗西斯·福山,这位提出“历史终结论”并坚信民主至上的学者,在《国家建构》一书中却转变了观念:“在过去几年中,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抨击‘大政府’,力图把国家部门的事务交给自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却是严重问题的祸根。”[3]
不过,笼统地将以上学者关于治理发展趋势、治理现代化路径以及治理风险放到一个平台上加以比较是欠合理的,因为他们立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关注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人类历史大趋势,有的关注中国治理现代化如何处理中西治理思想的关系,有的关注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以及不同历史条件对治理模式的不同需求。尽管如此,从有关“治理”的不同观点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第一,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而不单单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各国都需要创新和改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第二,最佳治理模式尚未成定数,甚至并不存在,西方的治理不是灵丹妙药,一国的治理现代化需要考虑到历史条件、本土特质、潜在风险等多种因素。因此,中国治理现代化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是这种探索的取向必须是非常明确并始终坚持的,这就是在本土治理实践基础上侧重指向结果的程序改进,始终以增进全体人民福利为依归。
一、“治理”实践决定“治理”观念
“治理”概念包含了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应该说,作为实践的治理从人类社会诞生时就存在了。荀子认为“能群”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就展现了群体性的本质特征,人在群体中必然伴随着分工与规范,尽管这些最初的分工和规范并不是荀子所讲的“礼”、“义”等封建等级秩序,但原始社会中的群体性也必然包含着沟通、协调、规范等治理的原初成分。因此说,自人类社会诞生时起,人们保持群体性的方式方法就包含着治理的实践。同样地,国家治理也从国家诞生时就存在了,它指的是根据实际治理问题不断调整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内容,治理的对象包括国家自身、发展中的社会以及市场等。在国家生成演化过程中,各个国家都积累了自己的治理实践与治理经验。
在治理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治理”的观念。“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古人在治国、治世、治人方面都形成了很丰富的理论思想,如东方的如民本、德治、教化、王道等,西方的如政体、民主、契约、合法性等。“历史地看,治理的观念,无论中西,早已有之。但是现代治理概念,是西方总结其长期统治、管理的经验教训,适应三大部门成型、成熟,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矛盾的时代变化和现实情况,加以提炼、提升而形成的。”[4]现代“治理”概念是在已有“治理”观念基础上演绎发展而来的,是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 civil society)日益壮大[5]11为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6]而提出的应对办法,其核心是多主体(主要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商共治。这是西方现代治理概念生成的大体线索。
理解西方治理概念产生的背景和前提,并不是否定西方治理思想对东方的借鉴意义,而是在于指出治理实践与治理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治理实践决定治理观念,治理观念反作用于治理实践,治理实践中的挑战是推动治理观念变化的基础性力量。这既符合唯物辩证法,也符合中西方治理实践与治理观念演化的史实。在此基础上认识中国的治理实践与治理观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有着丰富的治理实践,在背景、前提、历史、需求等差异面前,不可能是与西方完全一致的治理概念;中国治理现代化应当是立足于本土治理实践基础上、针对本土治理实践的问题与挑战而进行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绝不是用西方的或是某种主观建构的治理思想来剪裁治理实践。
理解了治理实践与治理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论——一切从治理实践出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7]87,“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7]69-70。
二、在借鉴与传承中创新治理
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从治理实践出发探索治理现代化,并不是说不要借鉴一些先进的治理理念,关键是要处理好借鉴与照搬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7]84“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7]83
中国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推进中国治理现代化,当然需要借鉴国外可取经验。事实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议题就体现了对于治理思想的一种借鉴。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方面,例如“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民主执政”、“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等,都体现了治理现代化的取向。但是,这些是我们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主动借鉴、分析性借鉴,不是照搬和西方化。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治理危机不但在层级治理模式中容易发生,在交互式或网络式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中也容易出现,只不过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作用机制与互动关系[8],西方的治理模式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简单照搬西方治理经验和模式,没有体现主体性与批判性、没有处理好衔接和融入问题,往往加剧了治理危机,拉美的治理改革、泰国和中东地区的民主化等等,都是一些实际的例证。
在如何借鉴学习先进治理理念推进中国治理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曾经做出精辟阐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9]“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7]84“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7]69-70这些阐述清晰地指明了我们在借鉴中创新治理的方向,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此方面,我们仍然要对一些主张全盘西化、照搬西方治理理念和模式的观点和做法保持高度警惕。
与此同时,我们推进治理现代化也不是厚今薄古、虚无历史,而是要求正确处理传承与因袭的关系。客观地讲,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治理智慧、思想和经验,对于我们改进当下的治理实践依然有着重要启示。近代以来,我们逐步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我们也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治理经验,如群众路线、集体领导、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从严治党等等。进一步说,中国治理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现代民族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全国统一市场的构建、快速推进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加强的民主与法制、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都是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的突出亮点。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会对改革做出总体部署,提出了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涉及十五个领域、三百三十多项较大的改革举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在传承中改革、在改革中传承,这才是不断创新治理、推动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治理现代化以增进人民福利为依归
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推进治理现代化,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7]68
很明显,这样一种取向的治理现代化与简单地谋求“善治”的西方治理理论是有区别的。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等[5]8-11。该理论通过赋予公民权利(包括参与权、社会事务管理权等),以求实现政府组织、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各有分工且相互协调共治,从而避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出现。该模式的好处在于分担政府的执政风险,让公民对自身和自己的行动负责。不过,“善治”理论有自身缺陷:第一,社会组织之间,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诉求不一,协商共治背后实质上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以及三大主体内部之间的对抗过程,“善治”结果最终将取决于对抗主体的实力大小[10],所以“善治”更多的是一种程序上的合法性与公正性;第二,“善治”寻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更多的是为了避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分担政府执政风险的目的要大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善治”的重点在“治”而非在“善”,协商共治的程序正义并不一定最终指向结果正义。
相对而言,中国治理现代化需要更加强调结果正义,是从现实的角度(对阶级阶层不平等的承认)出发展开的立论,区别于西方从理想的层面(对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期望)展开立论[11]。我们党始终强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的治理举措也旨在达成人民满意的目标,这就为治理设定了更高的目标指向。当然,基于结果问责与实质正义的优势也带来了一些治理麻烦,如国家责任缺少底线(如一些缠访、上访专业户的出现等)、程序正义无法支撑决策的合法性(如合法合规的决策带来不了好的结果,民众依然不买账)等等。在结果与程序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中国的治理现代化赋予了更多程序正义的作用空间,但始终坚持着对人民负责的结果正义取向。
概括地说,中国治理现代化的要义可以说是“指向结果的程序改进”,具体的治理举措最终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服务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从而让最广大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共同实现“有感增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再次彰显了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明确取向。任何形式的治理,都不应以简单的制度移植和建设为目标,而是要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实质性地增进全体人民福利。
需要指出的是,“指向结果的程序改进”实践特别需要处理好五对关系:一是促进发展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必须明确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增进全体人民福利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要对发展的方式和内容进行更好的规范,努力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两个方面不能偏废。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不断改革完善这一制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实现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仍在探索和发展过程中,总是存在着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地方。我们既不能僵化坚持拒绝改革,也不能借改革之名自毁长城。三是改革国家与建设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不足,需要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从现代化的长波进程看,中国仍然处在现代化的较低阶段,国家不是要弱化,而是要强化,要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护人民福利的作用。很明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不是为了弱化国家,而是谋求国家更好地发挥作用。四是扩大参与与规范参与的关系。一方面,改进治理的过程需要扩大社会与市场力量的参与,促进多主体的协商共治;另一方面,也必须意识到当下中国的市场和社会还不够完善,需要着力培育、引导和规范,促进依法参与、理性参与。五是深化改革和加强法治的关系。一方面,着眼于更好地保障和发展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以推进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需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有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特别是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如此,“指向结果的程序改进”才能落到实处。
可以说,“指向结果的程序改进”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特殊品质,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立足中国治理实践基础上传承中国本土治理优势、并借鉴西方治理的可取经验而进行的理论综合。“指向结果”(即不断增进人民福利)是目标和根本,“程序改进”(即治理现代化的体制和机制)是载体和保障。只强调“指向结果”容易陷入“抽象集体主义”的问题,即现实生活中很多治理举措虽然强调让人民满意、让集体共享利益,但因为这里的“人民”和“集体”还只是抽象的概念,无法在实践中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以致增进人民福利的目的无法真正实现。与此同时,只是片面地强调“程序改进”则抛弃了中国本土治理的固有优势,甚至会背离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实质上弱化国家的治理。中国治理现代化是将“指向结果”和“程序正义”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努力在“指向结果”的引领下构建“程序正义”,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基础上“指向结果”。当然,这样一种进程也对中国治理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社会各方进一步凝聚共识、持续推进。在中国治理现代化探索中,“指向结果的程序改进”也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如何调节“指向结果”与“程序改进”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和冲突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2.
[2]胡鞍钢,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1.
[3]福山弗.国家建构: 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
[4]郑杭生.“理想类型”与本土特质——对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评论,2014,( 3).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梅里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C]/ /肖孝毛,编译.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08-109.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8]DIXON J,DOGAN R.Hierarchies,Networks and Markets: Responses to Societal Governance Failure[J].Administrative Theory&Praxis,2002,24( 1).
[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14-02-17),http: / / 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02/17/c _ 119374303.htm.
[10]郑杭生,邵占鹏.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14,( 2).
[11]冯仕政.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J].学海,2014,( 3).
[责任编辑:高云涌,张斐男]
作者简介:洪大用( 196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应用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邵占鹏( 1987—),男,博士研究生,从事理论社会学、社会治理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0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6)02-00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