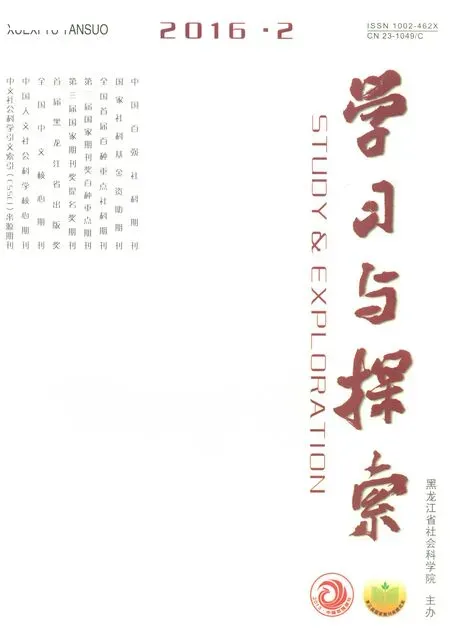论法治的转型
[美]弗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王金良编译(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上海201620)
论法治的转型
[美]弗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
王金良编译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上海201620)
摘要:法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法治的起源、发展与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世纪时期,西欧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文化,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地区由于教会控制政治权力,导致其难以形成真正的法治社会。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法治文化的侵入,传统宗教法律制度的权威逐渐衰落,这些地区面临着两难选择。实践证明,地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以当地传统宗教法为根本,才能更好地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完全移植西方的法治理念,只会引起“无法兼容”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法治;民主;法治转型;宗教;现代性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由自由和民主两个制度集合组成的。所谓民主指的是确保政府对公众选择负责;而自由则为法治提供保障。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进行理论研究之后,理论界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民主杂志》上)。然而,福山观察到很少有人去研究法治的转型问题,其具体问题包括:法治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的法治更强?法治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给予相应的回答。
一、关于“法治”的定义
福山指出,法治的定义是最重要的问题。正如民主的定义一样,法治也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概念。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在民主和治理实践领域出现了许多问题,人们给法治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以修正理论的偏差。这些学者大多数是经济学家,关于法治是什么以及从何而来等问题,他们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显然他们的观点是比较狭隘的[1]。
福山认为,在经济学家的谈论中,法治通常指的是现代产权制度以及合同的履行。个人是现代产权的持有人,他的资产可以不受亲属、宗教权威或国家的限制,能够自由地出售或转让。产权和合同的履行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逻辑关系是简单明了的。只有产权受到有效的保障,人们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同样,在交易过程中,合同和法律可以裁定各方之间的争端。合同规则的透明、合同执行的公平,将会推动交易的达成。经济学家一直强调可信承诺( credible commitments)的重要性,并把它视为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标志。强产权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一论点理论界已经有大量的经验研究[2]。关于普通法是否比大陆法更有利于促进发展的论点,还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福山指出,经济学家难以厘清法治和产权之间的关系,原因是经济学家对于“法律”这一术语的定义过于狭隘,不同于法学家的传统理解。根据老一辈法学家的定义,法律就是正义的规则主体,据此可以把共同体成员联合在一起。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相信法律是高于任何人类立法者的权威的,无论这种权威是神圣的还是自然的。国王、贵族、总统、议会和军阀可以采取积极的立法行为,然而根据法治的要求,他们的行为应该受制于现有法律的制度规则,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任意行事。
福山认为,在人们早期的理解和认识中,任何人类组织都不能改变法律的权威性。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是可以重新解释的。在现代社会中,宗教权威以及自然法信仰不断衰落,法律被视为人类的创造物,从本质上说是实证法( positive law)。即法律不过是提供了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则,以保证与建立在基本价值观基础上的社会共识相一致。例如,在当代美国,通过绝对多数制可以修改宪法,最高法院可以对宪法进行解释,而国会通过任何新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
关于法律的定义,经济学家认为其是与物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与法治的传统理解一致。福山认为,如果政府认为已有的法治体系不具备约束作用,那么就无法阻止其强夺公民的财产,甚至在其领土管辖的范围内,外国人的财产也得不到保障。强大的精英集团以及强有力的政府,都会阻碍一般法律规则的执行,这导致个人财产或交易的安全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3]。
福山强调,有一个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在没有“好”的产权和合同履行制度的条件下,国家也能够实现经济发展。设想当今中国政府如果把国外投资或个人资产进行国有化,那么现有法律制度是无法阻止这一行为的。然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国政府不会这么做,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能够兑现其承诺。中国不会为了抽象的“法治”概念,付出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这里,福山以中国为例论述了法治与产权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分析是有问题的。近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实效性的产权保护理论和制度,遗憾的是,福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福山认为,如果“法治”并不意味着可靠的产权和履行合同行为,已有的法律主权代表了正义规则的社会共识,而政府只是承认并继承了这一主权,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法治到底从何而来?法治的未来是什么?
二、宗教和法治
福山表示,如果人们想要一种稳定的社会规则,并且能够反映所有成员共享的道德价值观,显然这是宗教的功能。在前现代社会中,如古代以色列、中世纪的欧洲、早期的伊斯兰世界都有宗教的存在,然而这种宗教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宗教信徒们认为,宗教规则并不是源于人类的组织,而是神的权威,因而可以制约所有人类组织的主权。事实上,在这些社会中大多数统治者并没有主权的要求。神就是主权,统治者只是神在世俗社会的代理人。
不足为奇的是,法治最早起源于由先验的宗教所支配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统治者最早遵守的规则就是宗教。希伯来圣经、犹太法典、罗马十二铜表法、早期基督教教令和经典、伊斯兰教教规和圣训、吠陀经和印度教圣典,在当时的犹太人、罗马人、基督徒、穆斯林以及印度人社会中,都被当成是正义的规则,而统治者都明确承认并遵守这种宗教法律的规范。
福山认为,在法治建设方面中国是一个特例。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儒家文明是唯一没有派生出宗教法治的地方,原因是中国从未发展出一个被权威精英阶层所广泛接受的、超越祖先崇拜的先验宗教。祖先崇拜并不是法律的适当来源,没有人有义务去崇拜他人的祖先,因此对于大的社会组织来说,祖先崇拜并没有普遍的约束力。在中国秦、汉、唐、明时期,曾修订了大量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都是实在法( positive law)。也就是说,这些法律都是由皇帝颁布的,皇帝并不承认任何高于自己的权威。从商代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关于“天”的概念,“天”可以授权皇帝进行统治。虽然这很难说是一种法律,但却可用于王朝更迭的合法性解释。中国其他宗教如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并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共识。
与之相反,在东亚之外的许多国家,统治者认为国家的法律来自神的权威,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然而,法律对于这些统治者的限制程度是不同的,这既取决于统治者的认知,也受到法律形成和执行过程中制度条件的影响。具体来说,法律在四种情形下将会对统治者产生更强的约束力: ( 1)当某一法律成为权威性的版本时; ( 2)当某一法律主要由法学家而不是政府当局制定时; ( 3)当制度秩序与政治等级结构分开,并能够通过特定的资源和权力为某一法律提供保护时; ( 4)当某一法律与当地社会的规范和价值相一致,并符合支配政治体系的统治精英的需要时。
在进一步的解释中,福山认为与其他法治社会相比,西欧社会的法律制度化实现得更早,程度也更高。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其说是宗教观念,还不如说是欧洲发展的历史偶然性所导致,比如东正教从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在西方社会中,从民主、责任政府到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前,法治早已融入欧洲社会之中。在法律制度化的所有维度之中,这一点是最明显的[4]。
从法律的编纂入手,福山分析了法治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印度吠陀经的传承都是口头相传的形式,它的书写形式出现得比较晚。与之不同的是,早期三大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权威的经书。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会,在对圣经进行补充解释时,教会教规、教令和解释都是非常混乱的,直到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大帝主持将罗马法整理编纂为《国法大全》( Corpus iuris civilis),这一问题才得以改善。公元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 Gratian)编撰了《教令集》( Decretum),自此教令法得以进一步系统化。直到19世纪,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下,具有印度教或穆斯林教传统的东方教会才有了系统化的教令法。
关于法律专业问题,福山也有专门的论述。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新法律体系,传播到了整个欧洲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伟大的博洛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ologna)法学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17世纪格里高利改革之前,欧洲的国王、皇帝和其他世俗统治者都承认教会法的权威,法律成为教会的重要研究领域,紧接着也出现了教规和大陆法( civil law)的法律职业培训。从这一点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宗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它们都把法律置于等级化结构的法律专家乌里玛( the ulama)的控制之下。在印度教中,婆罗门祭司阶级则垄断了法律专家的身份。
关于制度上的自治性( institutional autonomy)问题,福山描述了它的历史。马克斯·韦伯杜撰了“政教合一”( Caesaropapism)一词,指的是世俗政权具有任免宗教职位的权力。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基督教教会都是“政教合一”的类型。直到11世纪,罗马教会爆发了“叙任权之争”( Investiture Contest)事件,强硬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干涉任命教皇和主教的权利提出了挑战,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在1122年教皇和皇帝达成了沃尔姆斯协定( the Concordat of worms),教会获得了任命自己神职人员的权利。这项权利以及牧师独身主义实践(有效地阻止了牧师亲属掌权的后果),使得教会摆脱了世俗政权的控制,并形成了被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 Harold Berman)称为最早的现代官僚制,这就是国家官僚制的雏形[5]。显然,在其他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并没有出现过这种制度化过程。
关于法律和社会规范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福山也有独到的解释。法律的规范性维度指的是人们相信法律是正义的,并愿意遵守这种法律规则,这是法治的关键。最好的法律依靠的不是严酷的惩罚,而是大多数公民的自愿遵从。无论在印度、中东还是欧洲的文明中,都代表了各自的宗教和社会规范,但在这一点上欧洲文明更具有优势。在现代西方法律体系植入社会规范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那就是这一法律体系与先前已有的社会规范之间的一致性问题。这一过程通常会引起社会变革,比如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强制性地贯彻男女平等的权利就会导致某种社会变动。如果法律和社会价值观之间存在巨大分歧,那么法治很可能无法维持下去。
同时,福山也表示,在现代国家之前,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文化。事实上,这是一种由天主教教会法支撑的跨国法律文化,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这种法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制约作用,使君主无法获取无限制的权力。即使欧洲的绝对君主,在没有某种正当程序的前提下,也不敢侵犯国家中精英分子的财产以及个人的权利。在早期英国的习惯法中,已经对于产权合法化进行了有效保护。
福山强调,法治的精神就是保护公民免受国家专制行为的干涉。这一权利最早仅仅适用于少数特权集团,这一点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并没有不同。举例来说,亚历山大·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引用了17世纪法国德·塞维涅夫人( de Sévigné)的书信。在信中,塞维涅夫人描述了布列塔尼省的士兵强制征新税,把老人和孩子赶出家门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由于无力缴税,大约有60多名市民被处以绞刑。塞维涅夫人写道:“一个开舞厅的小提琴师,因偷印花税而被车裂。他被五马分尸……并将他的四肢放在城市的四个角上示众。”[6]
显然,法国政府不会对塞维涅夫人及她的朋友处以这样严厉的刑法。17世纪的法国并不存在真正的法治,原因是法律并没有赋予平民与贵族同样的权利。同样地,在美国成立之初,黑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并不具备公民资格,而是被当作一种财产,而且白人女性也没有被赋予投票的权利。所谓民主化的进程,指的是适用于精英集团的法治逐渐扩展到所有成年人的过程。这一趋势持续至今,1992年南非的民主化转型成功地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把法治的权利适用于包括非白人在内的所有人。把法治的权利从精英阶层扩展到所有人并不容易,但更难的是建构一个新的法治社会。
此外,福山还认为,在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中,也出现过与欧洲相似的法治体系。法律是由教会编纂的,由神职人员组成的宗教机构充当了重要角色,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统治者意志之上的主权。与基督教不同的是,在印度教和穆斯林的传统中,宗教法的主体部分从未被系统化或形成法典,婆罗门阶级和穆斯林教士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单一的强大的统治集团。有一个例外是波斯什叶派的等级结构,它与天主教会的等级结构非常相似。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中,宗教法学家们只是根据先例进行解释。
西方人大都相信,政教分离是基督教社会的内在特征,而伊斯兰社会是反常的。事实上两个宗教社会在这一点上差别并不大,两者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政教分离的程度取决于两个社会的历史环境。在基督教社会的领主中,通常会高举“精神”和“世俗”两把剑。随着穆斯林社会制度的发展,哈里发和苏丹的统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伊斯兰教教法或穆斯林法中的学者或神职人员,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规则,统治者们需要向他们寻求合法性和宗教认可。福山表示,与欧洲教会相比,印度教和穆斯林教教会对于政治权力的控制力较强,这很可能是政教合一国家在穆斯林地区生根发芽的原因。
三、现代性的转型
福山认为,自18世纪以来,在欧洲、印度和中东地区,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法治逐渐削弱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转型过程。在欧洲,宗教改革破坏了天主教的权威,启蒙运动中的世俗观念也侵蚀了宗教信仰,这一转型就成为一个内在的结果。在早期的主权理论中,法律合法性的基础是上帝,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主权理论,其合法性基础变成了国王、国家或人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西方法治比现代民主制的出现要早几个世纪。在人民主权论的原则得到普遍承认之前,18世纪的普鲁士已经对行政权进行了制约,这时它可能已经是一个法治国家( Rechtsstaat)了。但直到19世纪晚期,民主思想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法律制定也成为民主社会的一个标志。长期以来,法治的文化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西方社会之中,即使合法性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但“文明生活离不开法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同时,规模庞大的和独立的法律机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等,都强化了法治的重要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印度和中东地区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法治社会。福山认为,在这些地区,与西方社会的交流和接触破坏了当地传统宗教法律制度的权威。19世纪60年代,英国废除了印度的班智达( panditas)体系,并试图恢复所谓真正的印度法律,这为20世纪引入欧洲法律铺平了道路[7]。19世纪晚期,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也废除了它的乌里玛系统,并重新编撰伊斯兰教教法,使之获得众多法律中唯一正统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之后,欧洲大陆法系取代了它的穆斯林法律体系。
1947年,印度共和国独立并采用了自由民主制度,它保留了英国统治带来的法律传统。在个人生活方面,印度试图重建早已破坏的印度教法律传统,相比而言,这一过程在阿拉伯世界非常糟糕。诸如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由英国和法国殖民当局带来的传统君主制很快就被世俗民族主义领导人所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行政体系,它既不受立法机关监督,也不受司法机关的制约。神职人员的传统角色消失了,代替它的是由行政当局控制的“现代化”法律。但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被殖民统治的经历,因此能够在行政当局与瓦哈比宗教( Wahhabi religious)之间维持某种平衡。
法学家诺亚·费德曼( Noah Feldman)认为,21世纪初伊斯兰教开始复兴,对于伊斯兰教法,整个阿拉伯世界有着广泛的需求,这既反映了人们对于蔑视法律的独裁主义政权的不满,同时也代表了人们的一种怀旧情感,即对于行政权力受法律约束时代的怀念。费德曼认为,对于伊斯兰教法的需求,不应该简单地看作是试图恢复中世纪伊斯兰的秩序,或希望实施严酷的塔利班式的统治,而是反映了人们渴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政治社会之中,即政治权力与法律规则之间能够达成某种平衡[8]。在许多伊斯兰政党的名称中,都反复强调了“正义”,这与其说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不如说反映了对于法律公平的诉求。在那些现代的强力国家中,如果无法形成法治或责任性政府,那么它只能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和完善,这有悖于民主的制度设计。
然而,现代伊斯兰主义国家能否建立一种受到法治约束的民主政体呢?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1979年,伊朗共和国革命的成功并不那么鼓舞人心,伊朗1979年宪法本可成为建设一个温和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基础。这一宪法规定,由非选举产生的最高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 Guardian Council)组成的高级牧师,是神在人世间的代表,同时它也具有立法和总统选举的权利。就其本身而言,这种安排并不一定就是“中世纪”或前现代的模式。在最高法院监督下,如果最高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只是充当传统牧师集团的角色,他们的权利仅限于定期宣布法律的通过,而只有民主选举的伊朗议会(非伊斯兰教的)才有权决定法律是否通过的话,那么就可以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伊斯兰教的法治形式。
不幸的是,伊朗的1979年宪法不仅把司法权赋予了最高领袖,还赋予他实质性的行政权(宪法第8节第107-12条)。伊朗的1979年宪法以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ck)的德国帝国宪法以及日本明治宪法为模板,虽然没有保留皇帝但却产生了一个最高领袖,他具有强大的行政权力。最高领袖控制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准军事民兵组织——“巴斯杰”( Basij),他能够取消候选人的竞选资格,并操纵选举结果[9]。在日本和德国,由于行政权力日益腐败,军队逐渐控制了知识分子,显然这违背了宪法的精神。相对于逊尼派伊斯兰教,伊朗牧师的等级结构有着更好的组织性,虽然它失去了一些司法功能,但却使得伊朗成为一个神权的独裁政权,这一政权可以无视法律,把政治对手关进监狱,甚至处死。
四、一些启示
对于法治起源的历史梳理,可能对于它的未来发展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福山认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第一个启示是,法治建设的时间顺序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从历史上看,法治最早出现在社会的精英集团之中,它可以调解富人与权贵阶层之间的关系。今天,人们相信任何制度安排都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如果某种制度仅仅适用于主要城市或特权阶层,那么它就是失败的。然而,资源是具有稀缺性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在政府体系中,法律制度建设是成本最高的也是最难的,它需要包括人和物质资本等基础条件。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制度安排能够为后人提供更多的先例,如果人们有能力将这些制度安排传播开来,那么它最终会生根发芽。同时,在社会中也可能存在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它建立在社会习惯或混合规则的基础之上,这种制度的发展过程通常是比较顺利的。
第二个启示是,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些身处于西方社会之中的人们,通常把法律看作是一个积极的和程序性的术语,他们总是认为应当改善发展中国家程序性的基础条件,例如,正式的法律条文、电子化诉讼、律师协会以及高效的法庭等等[10]。他们很少思考这些外来移植的法律到底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的需求。例如,国外法律能否与当代社会的商法所兼容,能否很好地处理自然人身份、家庭法和继承法等问题。福山谈到,许多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如以色列和印度,都偏离了现代自由主义的法律实践,其原因在于它们从传统宗教法中汲取了营养,从而获得了人们的支持。
如果要推动阿拉伯中东地区以及伊朗的民主化进程,那么人们将不得不面临这一问题。福山等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法治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专制的行政权力应该受到法律的监督;第二,法律应该尊重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比如女性应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关于第一点,人们当然应该坚持法律对于行政权的监督,但是对于第二点则存在较大的争议,它是否会削弱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如果人们不赞成法律的某些方面,那么在构建法律制度时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呢?
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人们无法真正知道潜在的社会共识是什么,但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例如,2009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候选人侯赛因·穆萨维及其支持者,对于大选的结果进行了抗议。示威者们声称,他们并不想破坏伊斯兰共和国,只是迫使其履行民主的承诺。假如伊朗的宗教军政权( clerical-military)崩溃,伊朗人是选择伊斯兰教法,还是选择一个现代的、世俗的法律体系呢?是否会选择伊朗1906年自由宪法?显然这种分歧在未来的法治建设中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法治必须最大限度地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具有稳定性。如果伊朗人是保守的,他们只是希望重建伊斯兰教法,那么,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即是否只有法治与民主的价值观相一致时,才能够积极推动法治的建设。
福山认为,人们必须建立关于法治转型的比较框架,这是关于未来研究的重要议程。在前现代的非西方社会中,都有一些习惯法和成文法,这必然与后来移植的现代西方法律规范和制度相冲突。关于殖民地法律是如何运行的,以及殖民地法律框架如何运用于后殖民地的法律体系之中等问题,仍然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人们的研究兴趣还应该包括那些引进西方法律并成功与当地社会文化传统相兼容的国家。例如,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日本政府倾向于用低成本的法律仲裁制度来解决诉讼问题,所以其人均律师数要远少于美国,案件诉讼数量也比较低,然而,这并不能说日本的法治水平就一定比美国弱。
如果要更好地认识法治的转型过程,那么对于它的结果人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它不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在经济性需求的刺激下,会自发地形成强大的法律体系[11]。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法律建设出现了“外生性”的问题,即除经济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如宗教信仰等。此外,在西欧国家形成强大的现代国家之前,它的法治建设进程早已启动了,因此从一开始,法律就能够避免这些国家发展成为专横的强国家。然而,福山的假设是,如果在法治建设进程开始之前,西欧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国家,那么在建构法治社会时就会困难重重。在过去20年之中,人们已经掌握了推进民主化的能力,也有了组织和监督选举的能力,这是一个好的兆头。然而,关于法治建设问题,是否还有其他更具有可比性的研究,这还有待观察。
参考文献:
[1]HAGGARD S,MACINTYRE A,TIEDE L.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8,11( 1) : 205-234.
[2]KAUFMANN D,KRAAY A.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R].Washington: World Bank Institute,2005.
[3]NORTH D,WEINGAST B.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J].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89,( 4) : 803-832.
[4]JOSEPH R.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5]BERMAN H.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6]TOCQUEVILLE A.Democracy in America[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537.
[7]DUNCAN M.History of Indian Law[M].The Netherlands: E.J.Brill,1973.
[8]FELDMAN N.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1-17.
[9]BAKHASH S.The Reign of the Ayatollahs: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M].New York: Basic Books,1984.
[10]CAROTHERS T.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M].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2006.
[11]NORTH 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51-52.
[责任编辑:巩村磊]
作者简介:弗兰西斯·福山( 1952—),男,教授,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研究。 王金良( 1980—),男,讲师,政治学博士,从事全球治理、比较政治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治理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研究”( 13CGJ02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14AZD133)
收稿日期:2015-11-08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6) 02-003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