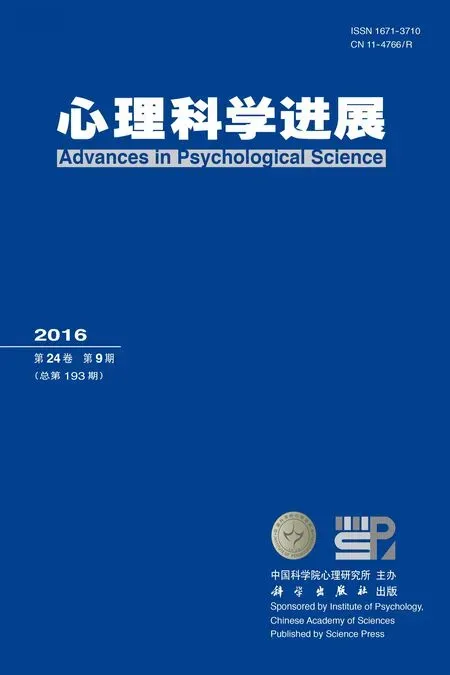影响群体道歉有效性的因素*
艾 娟
(天津商业大学心理学系, 天津 300134)
与人际道歉研究的热闹相比, 立足群际视角探讨群体道歉的研究就稍显清冷。群体道歉是群体对群体, 即侵犯群体对受害群体发出的一种社会解释行为(Hareli & Eisikovits, 2006)。近年来,学界对群体道歉的研究肯定了它所具有的积极功能, 认为它可以引发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性后果,不但可以减少受害群体的愤怒情绪, 恢复双方的自尊, 提升彼此的共情水平, 还可以改变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的人性归因和认知评价, 减少彼此对伤害的认知分歧, 是修补群际关系的重要策略之一(Páez, 2010; Philpot & Hornsey, 2008; Leonard,2012)。在社会现实环境中也不难发现, 群际冲突或者伤害事件发生之后, 侵犯群体如若忽视自身实施的伤害行为, 则会阻碍与受害群体关系和解的进程, 而做出道歉则是修复群际关系的润滑剂,比如在社会政治领域内,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千年一跪”至今令人难以忘记, 并对推进德国与波兰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 群体道歉的积极价值必须是在群体道歉有效的前提下来进行探讨的, 因此, 群体道歉的有效性才是一个更为核心与关键的问题。
1 侵犯群体:怎样道歉有效?
对于侵犯群体来讲, 道歉是一种有勇气的行为, 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开启了群际关系修复的第一步,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问题是, 侵犯群体应该怎样道歉, 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道歉的有效性呢?
1.1 群体道歉的言语表达
群体道歉突出的是言语的力量, 因此, 群体道歉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侵犯群体怎样说(Andrieu, 2009)。群体道歉的言语表达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值得关注的问题,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其一, 群体道歉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其二,群体道歉中哪些内容更有效?
首先, 有效的群体道歉应该包含哪些要素呢?关于这个问题至今并无定论, 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研究者指出, 道歉的内容包含三个要素, 即表达共情/懊悔, 承认破坏了制度和规范以及提供赔偿, 包含的内容成分越多,道歉越有效(Hill, 2013)。Nadler和 Saguy (2004)则认为道歉必须包括两个方面, 即对受害群体遭受到的伤害表达共情, 其次要承担责任。Blatz,Schumann和 Ross (2009)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 他们指出, 群体道歉(主要指官方道歉)往往面对的是一些伤害程度很严重的事件, 相比人际道歉来讲, 群体道歉应该包含更多、更全面的内容, 即在表达歉意; 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 承认给对方造成伤害, 表达共情; 许诺未来不会重蹈覆辙; 提供赔偿六个要素的基础上, 还需要强调受害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贡献和价值,提高他们的认同感; 强调伤害事件的过去时态,降低对受害群体的威胁感。
鉴于事件性质的不同, 群体类型的不同, 关于全面的群体道歉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但总体来看, 群体道歉的内容也存在着一些一致性的地方, 即道歉需要包含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表达懊悔、做出承诺四种基本的要素(Blatz, Day, & Schryer, 2014)。首先, 道歉需要侵犯群体明确承认伤害和错误行为的事实已经发生。其次, 道歉时侵犯群体要勇于承担责任, 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来讲, 更希望从道歉中看到侵犯群体能否承担伤害的责任。再次, 道歉需要侵犯群体通过言语或者非言语的形式表达出对实施伤害行为的懊悔与内疚。最后, 道歉需要侵犯群体做出承诺, 即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伤害行为。
其次, 群体道歉中的哪些内容更具有效性呢?群体道歉包含的内容是越多越好吗?有研究者认为, 侵犯群体在道歉的时候应该更多的体现出对受害群体的积极关注与共情, 更多的关注和表达受害群体的真实感受和需要, 如此才能使得受害群体更容易接受道歉(Berndsen, Hornsey, &Wohl, 2015)。有的研究者则发现, 道歉中的悔意表达并无积极效果(Philpot & Hornsey, 2008), 相比没有任何情感表达的道歉来讲, 效果也并非更好(Wohl, Hornsey, & Bennett, 2012)。Blatz等(2009)认为, 在官方道歉中对自身实施的损害行为表达出懊悔感要比提供经济赔偿有效的多。应该说,关于群体道歉中哪些内容更有效这个问题目前尚缺乏一致性的观点, 以往的研究过于粗略, 大多没有充分考虑到情境的具体性。道歉的哪些成分更有效还要取决于不同的冲突情境和冲突严重程度, 比如在性别歧视的群体情境中, 道歉需要包括承认错误、表示歉意、承担责任、做出承诺以及表达羞愧之情五个要素, 这种道歉要比包含更少或更多成分的道歉更加有效, 也更容易被受害群体接受; 可是在群体战争冲突的情境中, 承认错误、表示歉意、承认破坏规则以及表达苦难之情则更加有效, 而且在固定前三个成分的前提下,有无表达苦难之情对道歉的有效性影响最明显(Kirchhoff & Čehajić-Clancy, 2014)。由此可见, 道歉的有效性并非取决于道歉的全面性, 或者包含的成分越多越有效, 群体道歉应该根据不同的伤害情境和程度, 符合受害群体的具体要求和心理需要。当群体道歉忽略了受害群体的具体需要时,道歉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 因为有些道歉并非是为了获得赔偿, 更可能是因为其他心理原因, 比如博得同情、挽回自尊、寻求公正等。
1.2 群体道歉的行为策略
群体道歉研究更多的是聚焦于道歉的言语内容, 却忽略了道歉作为一种行为表演艺术所具有的作用, 群体道歉也是一种象征形式的群际关系修补行为(Andrieu, 2009), 群体道歉的有效性取决于谁来道歉, 怎样道歉等形式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道歉来讲, 特别重视在哪儿道歉以及如何道歉的问题, 以此彰显群体道歉的仪式性和象征性特点。群体道歉需要群体中的特定人物在特定的场合做出, 选择合适的言语、行为和时机, 尤其是官方层面上的道歉, 更加强调道歉的公开性, 即道歉的仪式感。比如, Páez(2010)指出, 对于群体道歉中的官方道歉而言,其形式和实施过程极其复杂, 它是一种正式的、象征性的仪式, 需要大众媒体的加入, 需要道歉群体中位居主要地位的领导人参与, 并需要得到道歉群体内成员的一致性支持。而对于群体道歉中的政治性道歉来讲, 它的有效性不但取决于说了什么, 还需要重视在哪儿说、谁来说以及如何说的问题(Sanderijn, 2015)。因此, 群体道歉需要发生在公共性的仪式活动中, 这些仪式对受害群体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 日本政府与韩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并在其中提及了“责任”和“道歉”的字眼, 但这一协议并未明确犯罪的主体是日本政府, 所谓的首相道歉也并非由安倍晋三直接道歉, 而仅为他人代读道歉声明, 这些做法着实令韩国民众无法接受并进行抗议。当然, 鉴于群体道歉是群体对群体做出的一种行为, 受害群体如何感知道歉是代表着侵犯群体的整体意愿还是道歉者个人意愿的表达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解释的问题。
另外, 群体道歉的有效性还需要后续行为的辅助。道歉不仅仅是言语的表达, 还应该有相应的行为产生。研究发现, 加拿大政府对中国移民的道歉效果受到后续行为的影响, 刚刚进行过道歉之后, 受害群体表现出对政府一定的宽恕心理,但时隔 1年之后, 这种宽恕水平随之降低, 究其原因是言语道歉并未伴随后续的行为产生(Wohl,Hornsey, & Philpot, 2011)。也就是说, 如果道歉后,道歉者再做出一定的赔偿行为或者相应的行为改变, 这种行为与其言语道歉相一致, 那么受害群体的宽恕水平就会有一定的提高(Blatz et al.,2009; Philpot, Balvin, Mellor, & Bretherton, 2013)。因此, 除却道歉的言语力量之外, 还需要侵犯群体有后续的与言语承诺相一致的真实行为表现,做出侵犯群体道歉中所应诺的行为改变, 才可能推动道歉的积极效果更进一层, 进一步激发受害群体的宽恕心理, 促进群际关系的和解。
1.3 群体道歉的动机影响
道歉的积极效果还会受到道歉者基于何种动机的影响(Iyer & Blatz, 2012), 道歉动机会影响道歉者对言语内容的选择和表述(Ohbuchi, Atsumi, &Takaku, 2008), 影响他们如何说, 说什么, 怎么做等, 道歉的内容或者情感表述又会影响到受害者对于道歉真诚性的感知, 从而进一步影响群体道歉的有效性。
首先, 侵犯群体对曾经发生过的伤害行为而产生的内疚、羞愧以及愤怒体验更容易引发群体的道歉行为(Schoemann, 2011; 石伟, 闫现洋, 刘杰,2011)。内疚是一种源于内在的、自我聚焦的情感,它不但使侵犯群体产生了消极的情感负担, 也可以激发侵犯群体关注对受害群体的伤害以及因伤害而遭受的痛苦, 进而产生共情体验。共情是一种源于外部的、他者聚焦性的情感, 即“看到你难过我也感到很悲伤” (Schoemann, 2011; Hill, 2013)。因此, 源于群体内疚的道歉会更多地表达共情、懊悔以及羞愧等情感成分(Hill, 2013), 而这些情感表达有助于改善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的认知评价,从而提高道歉的有效性。同时, 在群体层面上表达内疚和羞愧感也会对侵犯群体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比如表现出更强烈的和解姿态, 或者更愿意提供赔偿(Giner-Sorolla, Castano, Espinosa, & Brown,2008)。
其次, 侵犯群体的道歉也可能是源于一种“责任转移(obligation shifting motive)”的动机。基于责任转移动机的侵犯群体认为, 自身做出道歉行为之后, 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否得到缓和或者修复则成为受害群体一方的责任, 因为是否接受道歉, 是否停止各种请求的追讨主要是受害群体一方的事情(Zaiser & Giner-Sorolla, 2013)。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道歉行为的发生是侵犯群体有意施加给受害群体的一种“必须性”的要求, 而侵犯群体则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摆脱了因冲突带来的各种情感和形象认同危机。但是, 以转移责任为目的的道歉虽然满足了侵犯群体的意愿, 却带有一定的消极性, 对未来群际关系的和解并没有提供太多有益的帮助(Zaiser & Giner-Sorolla, 2013)。
最后, 群体是否做出道歉行为有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性的决定, 是迫于内群体以及第三方群体的压力而做出的。比如, 当内群体成员一致要求修复受损的群际关系时, 或者由于外在压力而使自身处于政治危机中时(Blatz et al., 2009), 或者侵犯群体在面临着外群体对其道德形象的认同危机时, 最有可能做出道歉行为。在此情况下, 群体道歉就成为一种政治性需要, 并被置于公众视野中, 群体道歉的表述和效果也会受到更多围观者评价的影响(Philpot & Hornsey, 2008)。此种道歉更可能成为一种策略性的做法, 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缺乏诚意的道歉(Thompson, 2008)。虽然基于自我形象维持的道歉会主动承认自身的错误,承担责任, 做出承诺(Hill, 2013), 尤其会特别强调自身承担的责任(Ohbuchi et al., 2008), 但迫于群体压力而做出的道歉也会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被动性, 受害群体知觉到的道歉主动性和道歉意愿也是不一样的, 道歉的有效性也随之降低(Jehle,Miller, Kemmelmeier, & Maskaly, 2012)。
2 受害群体:道歉为什么有效?
侵犯群体发出道歉是修复群际关系的第一步,但是受害群体能否接受这种道歉, 则成为修复关系的关键一步。对受害群体而言, 道歉的有效性要关注:道歉是否迎合了自身的情感需要, 以及是否感知到道歉者的诚意等。
2.1 群体道歉的情感功能
群体情感是引发行为表现的基础, 受害群体是否采取报复行为亦或是宽恕对方都取决于道歉能否减少与之相关的情感水平(Leonard, Mackie,& Smith, 2011)。Nadler和 Saguy (2004)认为, 道歉可以使群体之间达到社会-情感性的和解, 即通过道歉获得对方的宽恕。那么, 群体道歉是如何实现社会情感和解的呢?这主要是缘于道歉本身可以引发受害群体的积极情感效应, 可以减少受害群体的愤怒, 增加对侵犯群体的满意感(Philpot& Hornsey, 2008), 可以还给受害群体一个公正,重建其尊严与势力(Thompson, 2008), 甚至还可能激发比如合作等建设性的行为(Branscombe &Cronin, 2010)。在道歉对群际关系的作用过程中,道歉所引发的不同群体情感起到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道歉降低了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的直接性的愤怒水平, 减少了对侵犯群体的报复动机, 同时, 道歉也提升了受害群体的自尊感, 促进了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的宽恕(Leonard et al., 2011)。
另外, 从受害群体的角度来讲, 道歉迎合了他们的某些心理需要或者期望。如果道歉满足了受害群体的尊重需要会引发积极的效果。受害群体希望得到对方的道歉从而修复受损的自尊和颜面(诸彦含, 范黎娟, 2014), 尤其是对于一些内群体认同水平较高的受害群体来讲, 更加重视群体道歉所表达出来的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尊重程度,并进一步影响他们对道歉的接受程度和对侵犯群体的宽恕水平(Arthur, 2010)。如果道歉符合了受害群体对未来双方关系和解的强烈期望也会增加道歉的有效性。在受害群体希望与侵犯群体和解的情况下, 受害群体在接收到对方的道歉之后,更愿意相信侵犯群体对内群体的伤害是独立事件,相信侵犯群体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伤害行为, 从而更愿意宽恕对方(Bombay, Matheson, & Anisman, 2013)。
2.2 群体道歉真诚性的感知
成功的道歉需要受害群体感知到道歉方的真诚, 而不是侵犯群体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迎合社会期望、挽回颜面, 或者是得到某种奖赏而做出的(Philpot & Hornsey, 2008; Blatz et al., 2009)。群体道歉要比个体道歉更为复杂, 群体道歉的诚意也不容易被感知到(Valencia, Momoitio, & Idoyaga,2010)。那么, 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道歉诚意的感知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首先, 对道歉真诚性的感知会受到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认知信念的影响。如果受害群体认为侵犯群体的性格或品性是难以改变的, 侵犯群体成员的可塑性很差, 顽冥不化, 那么道歉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如果受害群体知觉到道歉中表达出较强烈的懊悔,则可以对受害群体存在的这种认知信念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改善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成员的品性认知, 进而提升道歉的积极效果(Wohl et al.,2015)。其次, 对道歉真诚性的感知还会受到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低人化偏见的影响。如果受害群体认为, 侵犯群体不具备或不能真切地体验复杂、独特的人类情感(比如内疚、共情), 即便侵犯群体在道歉时表达出这类情感, 受害群体也可能认为侵犯群体的道歉缺乏真实感与真诚性, 对其道歉的信任程度随之降低(Wohl et al., 2012)。最后,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道德水平与道歉情感一致性的感知也影响道歉的有效性。当受害群体知觉到的道歉情感与侵犯群体的道德特征不一致时, 道歉引发的宽恕效果最差。比如, 侵犯群体的道德水平较高, 并且在道歉中表现出深深的内疚感,那么受害群体就认为侵犯群体道歉中表达出的情感体验是真实的, 与其道德水平是一致的, 由此更容易引发受害群体的宽恕(Schoemann, 2011)。
当然, 还有一些外在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到受害群体对道歉真诚性的感知。比如, 群体地位会影响受害群体对道歉诚意的感知。弱势群体认为,强势群体的道歉并非是为了改善目前弱势群体的状况, 而是为了保持自身现有的地位, 因此, 弱势群体更倾向于认为强势群体的道歉是伪善的、无诚意的, 也更不愿意宽恕对方(Shnabel, Halabi, &SimanTov-Nachlieli, 2015)。再比如, 受害群体知觉到的伤害有意性对道歉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受害群体能够对侵犯群体的伤害意图进行归因, 在无意伤害、无消极后果的情况下, 侵犯群体的道歉对宽恕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Azar, Mullet,& Vinsonneau, 1999)。
但总体而言, 基于受害群体视角的道歉有效性研究也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诸如受害群体接受道歉时的状态、接受道歉的动机等对道歉效果的影响。而且, 道歉有效性的研究应该是基于侵犯群体与受害群体双方整合的视角,提高道歉与受害群体需要的匹配性, 使得道歉的言语和行为能够更容易被受害群体所接受, 发挥道歉的积极功能。
3 主体之外:其他影响因素
目前, 群体道歉有效性的研究多基于群体双方各自的视角, 即从侵犯群体的角度或者从受害群体的角度分别开展。但是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看, 群体道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有效性还会受到主体之外诸多因素的影响。
群际关系质量会影响道歉效果。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的信任程度作为群际关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影响到道歉的有效性, 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的信任水平越高, 道歉的有效性越强(Nadler &Liviatan, 2006)。也就是说, 先前群际关系的质量影响着后期群体道歉的感知和接受, 群际关系质量较高, 平时交好的两个群体发生冲突后, 群体道歉会更容易被对方接受。
另外, 基于不同的伤害程度, 道歉的时机和内容可能会影响道歉的积极效应。有研究指出,对于一些造成严重伤害后果的政治事件而言, 道歉的时机可以适当拖后一些, 这样做可以有效避免受害群体对道歉真诚性的怀疑, 避免激发更多的愤怒和复仇情绪, 而且侵犯群体在道歉的内容上也可以有一定的变化性和选择性, 随着创伤事件的时间远去, 道歉时的内容可以倾向于选择一些去责任化的表述, 言语表达中可以减少关于“不公平”、“错误”或者“犯错”之类的表述, 同时,道歉也可以更倾向于情感化表述, 更多的表达歉意以及懊悔之情(Blatz et al., 2009; Blatz & Philpot,2010)。但是, 这方面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跨群体、跨事件的一致性, 还缺乏更加有效且深入的探讨。
最后, 不同的文化信念对群体道歉的效果有一定的影响。文化类型和价值观会影响道歉的频率、形式、倾向性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讲, 文化信念的不同还可能会影响群体道歉的意愿和自发性。研究者指出, 大多数的道歉研究都是在宗教与西方文化背景中展开, 但是在亚洲或者伊斯兰等文化背景中的道歉行为以及后果则较少被探讨。比如,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等级制的集体主义文化, 强调面子、权威和声望, 因此, 道歉就难以产生, 也同样不会被人轻易接受, 否则会有损颜面和地位, 道歉意味着软弱、缺乏集体自尊感(Páez, 2010)。但也有不同的意见, 认为集体主义文化信念的影响下, 群体为了保护自尊可能会更多的选择承担责任, 所以道歉时言语表述更强调接受自身在伤害中的过错(Ohbuchi et al., 2008)。由此可见, 不同的文化群体产生冲突后, 需要针对不同的文化特征来实施道歉, 才能保证道歉的积极有效。只是文化信念对群体道歉的影响还不甚明确, 在二者的关系中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比如群体事件的性质、道歉的风险与收益等等, 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4 展望:有效群体道歉的应用
简言之, 群体道歉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也成为当下社会诸多群体修复受损群际关系所采用的较为简单、有效的策略之一。但目前来看, 关于群体道歉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还不是十分丰富, 各家观点与看法不尽相同, 道歉的心理机制也并未得到有机的整合,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道歉不能够充分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生活。
首先, 需要更加充分地整合群体道歉的过程机制, 为现实干预提供基础。目前, 基于侵犯群体、受害群体的道歉研究比较多, 但是主体之外的其他情境因素研究较少, 且所有这些因素并未得到更加充分的整合, 并没有更加完整的体现出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即在什么样的情境中, 针对不同文化特点的群体, 采用怎样的道歉方式(比如书面表达、面对面表达, 还是媒体网络致歉等), 表达怎样的道歉内容才能更符合对方群体的心理需求和期望, 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道歉的积极作用?今后需要对这个过程进行更加全面的整合和探讨, 并进一步以此为基础提出不同的现实干预策略。
其次, 从道歉的后果来看, 还需要更加丰富多元的指标来考察道歉的有效性, 以体现其在社会实践中的不同作用。目前来看, 大多数研究探讨了群体道歉与群际宽恕的关系, 并将宽恕看作是衡量道歉效果的主要指标, 然而这一做法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 道歉最理想的结果便是侵犯者得到了受害者的宽恕, 道歉引发了宽恕(Azar et al.,1999)。但质疑者则指出, 群体道歉能够促进受害群体对侵犯群体产生正向认知和满意感, 但不一定引发宽恕,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道歉带来的积极后果也将日趋减弱(Philpot & Hornsey,2008)。因此, 我们认为, 将宽恕甚至是群际关系的和解作为道歉的后果是不妥的, 也是单一的、狭隘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受伤害程度较严重的群体来讲, 侵犯群体期望着通过道歉引发对方的宽恕也是不现实的。所以, 对于道歉有效性的考察指标还需要进一步多元化, 加强受害群体对道歉的接受性、满意度、积极情感以及和解期望等方面的研究。
最后, 从社会应用的价值来看, 群体道歉更多运用在商业领域中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政治领域中的政府与民众之间, 或者不同类型群体(性别、宗教、职业等)的摩擦之间。比如, 商业领域的道歉是时常发生的事情, 很多企业都曾经因为犯错而向消费者道歉。但道歉的内容和技巧所导致的效果却不尽相同, 有人总结了这类道歉的四大要点, 即包括坦承错误、负起全责、提供解决方案、倾听客户感受并迅速采取行动*参考 http://it.sohu.com/20130830/n385420111.shtml。而在政治领域, 有效的道歉却可能是另一番要求, 比如在历史不公正事件中, 不管是侵犯群体还是受害群体都认为赔偿并不是首要的(Blatz et al., 2014),如果侵犯群体道歉时并未表现出对自身行为强烈的羞耻感, 而是更多提及到钱款的赔偿时, 受害群体会更加反感(Giner-Sorolla et al., 2008)。前不久, 日韩签订的慰安妇协议遭到了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 日本政府并未还原当年的历史真相, 也并未对当年的伤害行为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谢罪, 而协议所提及的赔偿则是一种用金钱践踏人类尊严的行为。因此, 今后还应该重视和发挥群体道歉在更多社会公共伤害或者政治冲突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进一步增进不同组织机构、种族、民族、宗教以及其他各类型群体的关系。比如医患、民族、国家等发生导致关系紧张的危机事件时, 应该考虑到道歉对安抚受害者情绪,坦诚接受责任以及促进关系和谐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可惜的是, 我们还缺乏对不同类型的群体道歉展开广泛且深入的研究, 更缺少在实践领域内的道歉干预。
石伟, 闫现洋, 刘杰. (2011). 对不公正历史事件的情绪反应——群体内疚.心理科学进展, 19(2), 224–232.
诸彦含, 范黎娟. (2014). 关系补救: 类型、潜在机制与作用模型.心理科学进展, 22(3), 512–521.
Andrieu, K. (2009). 'sorry for the genocide': How public apologies can help promot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8, 3–23.
Arthur, S. A. (2010).Using apology to promote intergroup forgiveness: Appealing to group identity(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Purdue University.
Azar, F., Mullet, E., & Vinsonneau, G. (1999). The propensity to forgive: Findings from Lebanon.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36(2), 169–181.
Berndsen, M., Hornsey, M. J., & Wohl, M. J. A. (2015). The impact of a victim-focused apology on forgivenes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18(5), 726–739.
Blatz, C. W., Day, M. V., & Schryer, E. (2014). Official public apology effects on victim group members’ evaluations of the perpetrator group.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46(3), 337–345.
Blatz, C. W., & Philpot, C. (2010). On the outcomes of intergroup apologies: A review.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4, 995–1007.
Blatz, C. W., Schumann, K., & Ross, M. (2009). Government apologies for historical injustices.Political Psychology,30(2), 219–241.
Bombay, A., Matheson, K., & Anisman, H. (2013). Expectations among aboriginal peoples in Canada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a government apology.Political Psychology,34(3), 443–460.
Branscombe, N. R., & Cronin, T. (2010). Confronting the past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The antecedents and benefits of intergroup forgiveness. In A. E. Azzi, X. Chryssochoou, B.Klandermans, & B. Simon (Eds.),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ly diverse societies(pp. 338–358).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Giner-Sorolla, R., Castano, E., Espinosa, P., & Brown, R.(2008). Shame expressions reduce the recipient’s insult from out-group reparation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3), 519–526.
Hareli, S., & Eisikovits, Z. (2006). The role of communicating social emotions accompanying apologies in forgiveness.Motivation & Emotion, 30, 189–197.
Hill, K. M. (2013).When are apologies effectiv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mponents that increase an apology's efficacy(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Iyer, A., & Blatz, C. (2012). Apology and reparation. In L. R.Tropp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group conflict(pp. 309–327). New York, NY,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ehle, A., Miller, M. K., Kemmelmeier, M., & Maskaly, J.(2012). How voluntariness of apologies affects actual and hypothetical victims' perceptions of the offender.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2(6), 727–745.
Kirchhoff, J., & Čehajić-Clancy, S. (2014). Intergroup apologies: Does it matter what they say? Experimental analyses.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20(4), 430–451.
Leonard, D. J., Mackie, D. M., & Smith, E. R. (2011). Emotional responses to intergroup apology mediate intergroup forgiveness and retribu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6), 1198–1206.
Leonard, D. J. (2012).Crafting intergroup apology: A matched emotion strategy(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Nadler, A., & Liviatan, I. (2006). Intergroup reconciliation:Effects of adversary’s expressions of empathy, responsibility,and recipients’ trus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459–470.
Nadler, A., & Saguy, T. (2004). Reconciliation between nations: Overcoming emotional deterrents to ending conflicts between groups. In H. J. Langholtz & C. E. Stout(Eds.),The psychology of diplomacy(pp. 29–46). Westport,CT: Praeger Publishers.
Ohbuchi, K. I., Atsumi, E., & Takaku, S. (2008). Do people reject apology for group harms? A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Tohoku Psychologica Folia, 66, 46–53.
Páez, D. (2010). Official or political apologies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 neo-durkheimian approach to official apologies as rituals.Revista De Psicología Social, 25(1), 101–115.
Philpot, C. R., Balvin, N., Mellor, D., & Bretherton, D. (2013).Making meaning from collective apologies: Australia’s apology to its indigenous peoples.Peace and Conflict, 19,34–50.
Philpot, C. R., & Hornsey, M. J. (2008). What happens when groups say sorry: The effect of intergroup apologies on their recipient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4, 474–487.
Sanderijn, C. (2015). Interpreting political apologies: The neglected role of performance.Political Psychology, 36,351–360.
Schoemann, A. M. (2011).Expressions of Emotion in Intergroup Apologies and Forgiveness: The moderatingrole of percieved perpetrator morality(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Shnabel, N., Halabi, S., & SimanTov-Nachlieli, I. (2015).Group apology under unstable status relations: Perceptions of insincerity hinder reconciliation and forgiveness.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8(5), 716–725.
Thompson, J. (2008). Apology, justice, and respect: A critical defense of political apology. In M. Gibney, R. E.Howard-Hasmann, J.-M. Coicaud, & N. Steiner (Eds.),The age of apology: Facing up to the past(pp. 31–44).Philadelphia, PA, US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Valencia, J. F., Momoitio, J., & Idoyaga, N. (2010).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nd memory: The psychosocial impact of the Spanish "Law of Memory", related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Revista De Psicología Social, 25(1), 73–86.
Wohl, M. J. A., Cohen-Chen, S., Halperin, E., Caouette, J.,Hayes, N., & Hornsey, M. J. (2015). Belief in the malleability of groups strengthens the tenuous link between a collective apology and intergroup forgivenes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1(5), 714–725.
Wohl, M. J. A., Hornsey, M. J., & Bennett, S. H. (2012). Why group apologies succeed and fail: Intergroup forgiveness and the rol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mo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02(2), 306–322.
Wohl, M. J. A., Hornsey, M. J., & Philpot, C. R. (2011). A critical review of official public apologies: Aims, pitfalls,and a staircase model of effectiveness.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5(1), 70–100.
Zaiser, E., & Giner-Sorolla, R. (2013). Saying sorry: Shifting obligation after conciliatory acts satisfies perpetrator group members.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05(4), 585–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