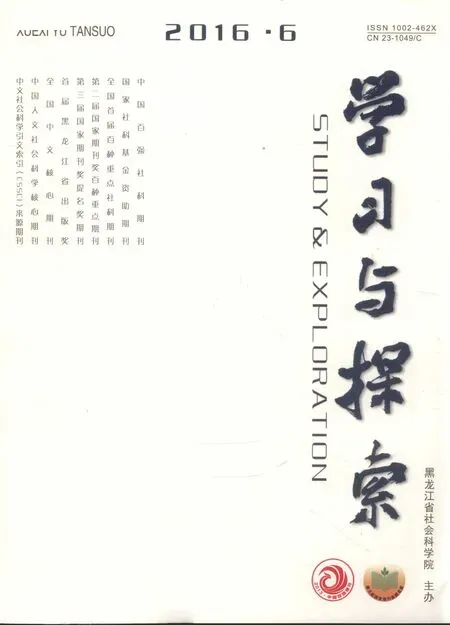《中庸》之作为儒学“心法”新释
王 乐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北京 100091)
《中庸》之作为儒学“心法”新释
王乐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北京 100091)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政治、道德因“心”而融通,“心”既是它们的基础,又是它们相互转换的枢纽。《中庸》历来有儒学“心法”之称,前人多从思想、方法和文本等角度来理解《中庸》作为儒学“心法”的原因。但这一原因,更应该从《中庸》的内容,尤其是《中庸》的某些特定范畴上去理解。通过发掘内求、时中、通达等范畴,通过“心”而融通儒学的主要思想,能够为《中庸》之作为儒学“心法”探寻出新的解释。
关键词:《中庸》;“心法”;儒学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中,曾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1]17然而,朱熹并未对这一提法,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一方面,朱熹用“心法”来指称《中庸》的儒学特征,可谓言尽其意;然而,另一方面,如何理解《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则聚讼纷纭。
关于《中庸》之作为儒学“心法”,后世学者具代表性的理解有三种:其一,认为《中庸》之作为儒学“心法”,是因为它秉承并发扬了儒学的“祖训”。蔡元培就曾说:“文武虽没有中庸的标榜,但孔子曾说:‘张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是文、武不肯为张而弗弛的太过,也不肯为弛而弗张的不及,一张一弛,就是中庸……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篇,是传祖训的。”[2]其二,认为《中庸》之作为儒学“心法”,是因为它在继承和发展以道德为中心的儒家传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徐复观认为,就“承上”的一面,“《论语》中虽屡提到圣人,但对圣人未做明显的叙述;《中庸》则对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叙述得相当的详尽。同时,《论语》对‘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一类的问题,谈得不少;《中庸》承继了这一方面的思想而进一步加以系统化……”就“启下”的一面,“《中庸》所提出的工夫,可以说是内外兼顾而内外合一。即‘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兼顾与合一。向内的工夫是由‘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的‘慎独’,朱子以‘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释‘独’,与《中庸》后面所说的‘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正合。程朱之‘敬以直内’,即由此而来。以后王阳明之所谓‘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时乾坤万有基’,也是由此而出。”[3]其三,认为《中庸》之作为儒学“心法”,是因为它在“四书”中具有特殊地位。陈荣捷曾说,“《中庸》一书,可以看出它是本哲学的著作,而且很可能是古代儒家文献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本”[4]。
这三种解释分别是从思想、方法和文本等三个角度来理解《中庸》作为“孔门传授心法”的原因。其实,在《中庸》中,存在这样一些范畴,这些范畴本身既可以用来表达某种思想,亦可以用来暗指某种方法。这样的范畴本身,就是对《中庸》作为“孔门传授心法”的鲜活体现。这些范畴主要包括内求、时中和通达,等等。
一、内求
在实质上,儒家强调的“内求”即是“自得”。正如《吕氏春秋》所言:“何谓反诸己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途。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凡彼万形,得一后成。”“内求”是一种自得之道。道家也强调“内求”,不同的是,在道家眼里,“内求”即是“自求”。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提倡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等方法,“复归于”人类的最初状态。“内求”是追求自然状态的自己。
《中庸》中蕴含着丰富而辨证的“内求”思想。首先,《中庸》强调“正己”:“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对“正己”的解释,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将“正己”解释为“正身”,如朱熹认为:“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画布曰正,棲皮曰鹄,皆侯之中,射之的也。”[1]24箭能否射中靶心,是由自己身体的正斜而不是靶子决定的;一是将“正己”解释为“正心”,王夫之认为“所谓‘正己’者,亦别于上文随位尽道之实,但以心之无邪而即谓之正矣。”[5]111“正己”就是指心无旁骛。尽管《中庸》多言“修身”,对“心”字只字未提,然而,比较而言,王夫之的解释较为贴切,原因有三。
其一,“正心”比“正身”更彻底。在《中庸》中,“内”“己”“身”表现的都是“位”,《中庸》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位”是“身”的内容,是区分“此身”与“彼身”的标准。在这一意义上,修身便可解释为“修”处于某“位”之身。然而,一方面,“位”的变动性较强,同一个“身”,表达的可能是多个不同的“位”,这就决定了“正身”始终具有某种不彻底性。而“正心”则不同,较“身”而言,“心”更为自由,它既可以不因“位”变换而改变,只是《中庸》所言“择善而固执之”;亦可以根据“位”的变换而做出新的选择,正如《中庸》所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也就是说,“心”是以不变应万变者,是唯一的,因而“正心”便是彻底的。另一方面,“身”的个体性较强,人的外在体态形形色色,而“心”却不同,“心”的普遍性较强:“一人之心,可以感觉异地数百千里外,异时数百千年他人之心以为。数百千里外他心之忧喜郁乐,数百千年他心之忧喜郁乐。吾心之于他心亦然。”[6]“心”是共通的,成语心有灵犀、心心相印说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心”的普遍性、相互影响性,说明的就是“正心”具有彻底性。
其二,“正心”比“正身”更牢固。在《中庸》中,“心”永远是“身”的基础。一方面,如前所述,在知行问题上,《中庸》倡导的是具有重知倾向的“知行相顾”。《中庸》有言:“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此处的“善”,朱熹的解释是“人心天命之本然”[1]31。“心”是具有“善”之先天本性的事物,这与《释文》的解释“心,或作道”不谋而合。心是道之本源、人之本性。《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亦是对这种解释的发展。将“心”与“道”“性”打通,不仅在理论上为“正心”提供坚实的依据,在实践中,也确定了“正心”的牢固性。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为何《中庸》在知行问题上具有明显的重知倾向。另一方面,《中庸》强调“心”诚:“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就某事物内部而言,“诚”存在于事物的始终;就一事物与另一事物而言,“诚”涤除事物的外内之分。“正心”其实就是“诚心”,使“心”在时间和空间上永保“诚”的状态,这也正是《中庸》所言的“至诚”:“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在一意义上的“心”是拥有绝对牢固性的。
其三,“正心”比“正身”更超越。一方面,“正心”超越于“正身”表现在“心”的能力上。关于“心”的能力,《礼记·大学疏》:“总包万虑谓之心”,认为“心”的能力就是“虑”明确了“心”之“思”的能力。《中庸》则认为“心”的能力就是“中庸”,“心”不仅能够“中节”“已发之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从而使“情之发”合于“中庸之道”,实现“尽己之性”,而且能够“……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之性、物之性、甚至天地之性,因“心”的能力而贯通。无限之“心”超越了有形之“身”,故,“正心”比“正身”更超越。另一方面,“正心”超越于“正身”还表现在“心”的意义上。关于“心”的意义,《大学》说的透彻:“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前者是道德问题,后者是理性问题。理性是做出正确的判断、选择的基础,而正确的判断、选择又是修身的基础。在《中庸》中,“知”(理性)永远是“修”(道德)的基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以理性为基础,道德亦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即:道德理性。“心”的意义就在于赋“道德”以理性的内涵。
其次,《中庸》强调“自卑”。“自卑”所强调的就是为道由己的“内求”。孔颖达认为:“不云近者远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于身,然后能被于物,而可谓之高原耳”[7],马其昶也解释此句为“尽道于己”[8]。“自卑”在知、情、意中的表现不同。其一,就知而言,“自卑”倡导“学以为己”为知的目的。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观点,《荀子·劝学》亦见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之说,倡导的学习目的应该是为己。在知的态度上,“自卑”强调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中庸》有言:“好学近乎知”,朱熹引吕氏言解释道:“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儒者甘为人下而不辞。故好学非知,然足以破愚……”[1]29“自卑”本身就是一种“自觉”“自得”和“自足”。其二,就情而言,“自卑”倡导“絮情之性”。在《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解决的不是性、道、教的问题,而是三者之间的通达和支撑,即:如何通达命-性-道-教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中庸之为中庸的地基。一方面,《中庸》认为正是性、道、教的相通相成才生发出中庸之道:“性也,道也,教也,内外相成之道,是三者得之,然后为中庸之道”[9];另一方面,《中庸》认为性、道、教在中庸之道中的担当是不同的:“不知性则不知中庸所自来,不知道则不知中庸之所由在,不知教则不知中庸所咸由成”[10]。不管怎样,“性”始终与中庸之道相联系,是“未发”的,“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7]1424。“性”是“心”的虚静、自卑状态,也是“心”离“中庸之道”最近的状态,是一种较具普遍性的状态。而“情”则不同,“情”是“已发”的,是“心”的躁动、自傲状态,也是“心”离“中庸之道”最远的状态,是较具个性的状态。在此,“自卑”就是以普遍之“性”,“卑”一己特殊之“情”。其三,就意而言,“自卑”倡导“诚意之志”。《中庸》认为“诚身有道”,具体而言,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在讲明“诚身”的阶段性的同时,也说明“诚身”对意志的要求。一方面,要“诚”,一心一意;另一方面,要意志坚定,持之以恒。
综上所述,“内求”就是发现自我、放大自我。“内求”的方法有很多,“正己”的、“自卑”的,等等。在中国思想史上,“内求”常常与人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人性善则“率性修道”;人性恶则“存理去欲”,一句话,“内求”重在“修身”,在此“‘身’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它是一个主动因作用的结果”,而“那个主动因是‘心’(灵)”[11]。于是,“修身”就成了“修心”。这有些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个人拥有不依赖于外界环境和命运安排而获得幸福的能力。这种理论的预设是:人具有协调自身的身心、灵肉之间关系的能力。所以,人的幸福不取决于他在世界上的具体地位,而是取决于他如何看待、在内心中如何评价自己对世界的参与[12]。可以说,“内求”就是一种“心”与世界的博弈:世界在心中,心在世界中。
二、时中
“时”,《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四时也。”[13]137可见,“时中”的观念源于一定的客观、自然条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因时制宜”。《中庸》借孔子之言道出“时中”,却并未对此做出直接的解释。朱熹的解释是:“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1]19。朱熹用“在我之德”解释“中”,认为“中”是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品质,而“时中”是这种道德品质在不同场合中的表现,强调“我”之于“时中”的主动性。康有为认为:“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焉。其统异,其世异,则其道亦异。故君子当因其所处之时,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上下无常,惟变所适。别寒暑而易裘褐,因水陆而资舟车。道极相反,行亦相反。然适当其时则为此时之中庸,故谓之时中”[14]。康有为以“时宜”为标准,强调“时变”之于“时中”的决定性。前者强调的是“我”(道德主体),而后者强调的是道德环境(客体)。其实,“时中”既强调“中”因“时”而变(道德原则的相对性),也强调要因“时”而用“中”(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一方面,“中”的灵活性和多变性不是肆无忌惮、随心所欲,而是以客观环境的复杂性、运动性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人在客观环境面前是具有能动性的,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做出相应的不同选择。其实,关于道德原则的绝对性及其相对性的讨论,并非《中庸》一言。早在《尚书·舜典》就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针对不同的事物,“中”的表现是不同的,正是这些不同的表现,促成了世界之“和”。可见,在当时,“时中”的思想与“和”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是由多个“时中”共同组成的。
《中庸》直接从“道”的角度解读“时中”。《中庸》认为“道”主要是道德主体“内求”的结果。《中庸》在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后,紧接着就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道其不行矣夫!”可以看出,君子、中庸、时中、至德、道这一连串的概念,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时中”不再是某种“和”、某种“成”,而是包含“和”“成”在内的“道”。然而,这种思想并未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例如,朱熹就重新将“道”与“时中”拆分开来,认为“中一名而有二义……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谓在中之义,未发之前,无所偏倚之名也;无过不及者,程子所谓中之道也,见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盖不偏不倚,犹立而不见四旁,心之体,地之中也。无过不及,犹行而不先不后,理之当,事之中也。故于未发之大本则取不偏不倚之名,于已发而时中,则取无过不及之义。”[15]545“未发之中”不偏不倚是“道”,是体;“已发之中”无过无不及,是“时中”,是用。“不偏不倚,未发之中,以心说者也,中之体也。无过不及,时中之中,以事论者也,中之用也。”[15]325王夫之试图挽回“时中”作为“道”的地位,认为朱熹“专以中和之中为体则可,而专以时中之中为用则所未安。”[5]60王夫之提出:“中无往而不为体。未发而不偏不倚,全体之体,犹人四体而共名为一体也。发而无过不及,犹人四体而各名一体也。固不得以分而效之为用者之为非体也。”[5]60-61然而,他的挽回具有不彻底性:“已发者固然其有体。则‘中和’之和,统乎一中以有体,不但中为体而和非体也。‘时中’之中,兼和为言。和固为体,‘时中’之中不但为用也明矣。”[5]60这不过是将“时中”与“和”相提并论罢了。的确,作为一种较为概括和抽象的原则,“中”本身不是目的,“中”的目的是“和”。然而,“中”之于“和”的重要性表明,“中”绝不仅限于“和”。“中”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大道,而“和”是大道运行的结果。“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没有“中”,“和”便是不可能的。正所谓“盖所谓中庸者,天下事物之理而措诸日用者也”[5]65。也就是说,“时中”是“理”“用”统一之“道”。
在《中庸》中,“时中”的作用集中表现在“择道”“守道”上。“择道”主要涉及的是“中”,而“守道”则主要涉及“时”。就“择道”而言,天下之“道”有很多种,故对“道”的选择便成为必要。如前所述,中庸之道是一种“道中之道”,是“道”的原则和标准。例如,学习中的中道,可以是《论语·为政》所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与“思”的中和状态;处世时的中道,可以是《论语·子路》中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是“狂”与“狷”的中和状态;为政时的中道,可以是《中庸》的“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是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等等。正因为如此,中庸之道才为人心所向,所选。然而,不同于其他的“道”,譬如“仁道”,《论语·述而》的“吾欲仁斯仁至矣”,选择仁道,即是拥有了仁道。选择中庸之道,还不能算做真正的持有中庸之道,“守道”才是持有中庸之道的开端。对“守道”之难,《中庸》中有较为鲜活的比证:“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难也,然不必其合于中庸,则质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若中庸,则虽不必皆如三者之难,然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此民之所以鲜能也。”[1]21笔者认为,朱熹的解释有失全面。理由如下:其一,这一解释在《中庸》文本中,没有对应之处。相反,《中庸》认为,“知”道、择“道”容易,而“守道”实难:“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相对应的是颜回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的“守道”,是他持有中庸之道的真正原因:“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因此,可以说,“时中”的关键在“时”不在“中”,中庸之道的心法在“守”而不在“择”。其二,这一解释自身存在矛盾。原文所列举的“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的实现,都离不开朱熹所言的“无一毫人欲之私”,如此一来,此三种行为及其“道”,与中庸之道便无差别可言,为何单“中庸不可能”呢?其实,前三种行为及其“道”,与中庸之道的本质区别,一方面在于前三种行为及其“道”是单一的具体的,依次表现为平等、清正和刚强,而中庸之道是多向的抽象的;另一方面在于前三种行为及其“道”的实现可以是一时一瞬的,而中庸之道的实现却是长久长时的。这就是戴震所谓“中庸必具众德,又非勉于一时,故难”[16]。也正是因为“守道”难,“时中”才成为“中庸之道”的心得所在。一方面,“时中”的要求是立体的,强调的是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中庸之道,这体现了中庸之道之于不同道德主体的灵活性,也证明了“内求”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时中”的要求是动态的,强调的是中庸之道就存在于执守中庸之道的过程之中,所谓执即得,不执便不得,揭示的是“内求”的必要性。
《中庸》之后,孟子继承和发展了《中庸》的“时中”思想。《孟子·尽心上》以杨墨为反例,揭示“执中无权”的危害:“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朱熹的解释是:“执中而无权,则膠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难识,须是默识心通。且试言一廳,则中央为中;一家,则廳非中而堂为中;一国,则堂非中而国之中为中,推此类可见矣。’又曰:‘中不可执也,识得则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则不中矣。’”[1]357“中”的原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像“权”一样灵活多变的。“执中无权”就好比将秤砣固定下来去给所有物品称重一样,是行不通的。此外,《孟子·万章下》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公孙丑上》认为“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孔子的行为没有不成功的,因为他的行为都是“时中”的。可见,到了孟子那里,“时中”的思想又与“成(功)”的观念关系密切。
三、通达
“通”,《说文解字》的解释是:“达也。”[13]40“达”,《广雅》释云:“通也。”可见,通、达原是可以互释的两个字。《中庸》中言“通”1处,言“达”6处。 “通达”是除“内求”心法、“时中”心法外,《中庸》的又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心法。“内求”的心法,强调道德是内在于人心人性的,尽管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变化发展是维持事物不穷的必要条件。然而,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中庸》中,道德之普遍性、道德之规律性以及道德之包容性的问题,都是由“通达”心法来表达的。
首先,“通达”是相对于“蔽”而言的,强调心把握事物时的“全”。“蔽”是相对于“全”而言的。《庄子·天下》曾这样描写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道德状况:“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认为,当时社会的道德均不具普遍性。《荀子·解蔽》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认为诸子如同盲人摸象,硬把道德之树,说成是道德的森林。借此,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解蔽”说,他认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人心不能“通达”,是由于“道”(“大理”)不得彰显。而解心之“蔽”就要彰显“道”之“全”。放眼全部事物,对其做出全面地分析,从而才能中正如实地把握事物及其关系,才能不被一种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所蒙蔽。“通达”作为《中庸》“解蔽”的心法,集中表现在其对人(“内”)与物(“外”)的全盘考虑上。《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由“人”达“物”,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合二而一。尽管《中庸》并不是这种思想的首创者,《论语·述而》中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将道德的普遍性从人延展至“物”。但是,这种思想在《中庸》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中庸》提及“物”达12处之多。
《中庸》重视道德,却不止于道德。《中庸》强调人、物(心、物)通达的思想,不是为了说明“物”的世界中也存在有某种类似于人类社会的道德,而是一方面强调一种更为通透全面地看待世界的方法,正如邵雍所言“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另一方面,强调一种即内在又超越的精神境界:“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7]《中庸》这种强调人、物(心、物)通达的思想更不是要将物纳入人、纳入心,形成唯人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为了让人、让人的心灵不断进入和参与物的世界之生成。脱离“物”,人则难成为人;脱离“他者”(相对于“物”来说,“人”即“他者”),“物”亦难成为“物”。唯有他者进入物的世界,物才得以“完成”,才得以成为“事物自身”,才得以成物之性,人性与物性才得以通达。《中庸》倡导的正是这种心灵开放下的万物生发,而不是被物的表象所蒙蔽的退隐心灵。就前者而言,世界其实就是心灵的展现,是人之意义的展现;而就后者而言,万物皆空。
其次,“通达”是相对于“半途而废”而言的,强调心把握事物时的“固执”。《中庸》有言:“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不难看出,孔子“一以贯之”的品质,是《中庸》“通达”心法的雏形。这似乎于前文所言“全”之“通达”心法有相悖之处。其实不然,一方面,“全”发生在“择”道之前,而“固执”则发生在“择”道之后;另一方面,“固执”之“执”是执中有权之“执”,不是执一之“执”。就“一以贯之”而言,“一”是原则,“贯”是原则的“通达”。就孔子的思想而言,“仁”是孔子之学的原则,“义”“礼”则是“通达”“仁”的主要手段。“义”“礼”将“仁”贯通到知命、伦常、为学、为政等人生活动中,将人的整个生命以及几乎其所有活动都与“仁”“通达”起来,即:将人的整个生存状态与“仁”的“通达”结合起来。在《中庸》看来,这种“通达”是孔子之所以为圣者的重要心法。《传习录·上卷》:“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中庸》称赞颜回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承继:“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不同于孔子的是,《中庸》拓宽了孔子“一以贯之”的范围。一方面,孔子的“一以贯之”与人的情感、欲望是针锋相对的。“仁道”的持守,是建立在不断地合理化人与其情感欲望的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庸》则不同,《中庸》认为“情感、欲望和心灵是密不可分的,心灵不断解蔽实现通达的过程也是情感欲望不断获得合理满足的过程。”[18]另一方面,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仁道”,其范围是仅限于人的活动,即人类的社会活动的。而《中庸》所“固执”的“中庸之道”是涉及物的,“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最后,“通达”是相对于“分”而言的,强调心把握事物时的“合”。真正的“道”不是一而是多,“能肯定‘事物有理’,人就可建立最基本的人生态度,去了解事理,循理来做一切决定。能肯定‘人生有分’,人就明白人人各有‘应该做’的事,而不会只顺着情绪欲望或个人利害计算来行动。人人能做到这两点,就发挥了道德观念的力量,而使社会有品质上的发展。至于人知道多少‘理’,人在某一环境中有那些事应看作‘分’,自然是随时代和社会结构等等而改变的。”[19]“道”是包容的;真正的“道”不是“自成”的,“道”是相成的。“道”是独立而自足的,物各有分,各司其能。然而,“道”的基本精神却是通达的。这种通达是因为生命体超越其自身、不断发展的基本依据。同样地,“道”是没有范围的,不论家、国、天下,《论语·颜渊》篇上说“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在“道”中,人、物、世界是相生相合的。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J].东方杂志,1931,(1).
[3]徐复观.《中庸》的地位问题——谨就正于钱宾四先生[C]//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
[4]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M].杨儒宾,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06.
[5][明]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钱穆.灵魂与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9.
[7]李学勤.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34.
[8]陈柱.中庸注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
[9][宋]黎立武.中庸指归,中庸古本及其他三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1:7.
[10][清]潘家邦.中庸笺注讲义别体[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173.
[11]廖申白.德性伦理学:内在的观点与外在的观点——一份临时提纲[J].道德与文明,2010,(6).
[12]古谢伊诺夫,伊尔利特茨.西方哲学简史[M].刘献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78.
[13][汉]许慎.说文解字[M].[宋]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康有为.中庸注[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3-4.
[15]胡广,等.四书大全[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
[16][清]戴震.中庸補注[C]//戴震全书:第二册.杨应芹,诸伟奇,主编.合肥:黄山书社,2010:57.
[17]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8]吴树勤.即日用常行而成就道德[J].甘肃社会科学,2005,(6).
[19]劳思光.从“普遍性”与“具体性”探究儒家道德哲学之要旨[C]//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东南亚哲学研究所,1987.
[责任编辑:高云涌]
收稿日期:2015-1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化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14CZX04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研究”(12&ZD093)
作者简介:王乐(1983—),女,讲师,哲学博士,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6-0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