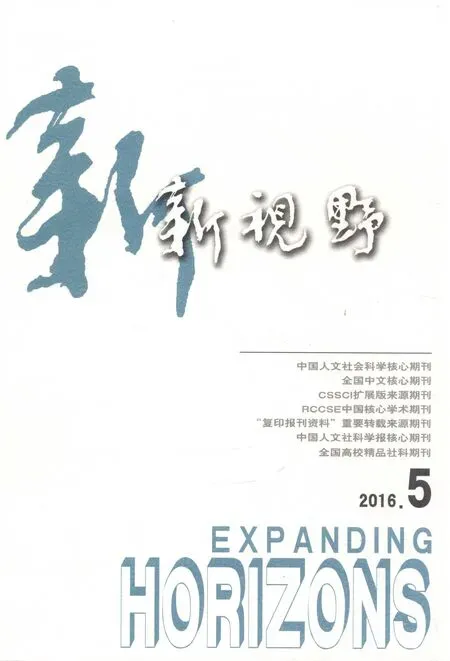从行政主导到福利治理:社区服务的范式演变及其未来走向
文/刘杰
从行政主导到福利治理:社区服务的范式演变及其未来走向
文/刘杰
作为社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服务”研究方兴未艾。立足于社区服务的“福利”本质,运用福利治理视角,聚焦于中国社区服务的政策文本演化与服务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社区服务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萌动期、推进期和发展期,在这个进程中存在着从行政主导到福利治理,由政府范式向市场范式,最终形成治理范式的演变过程。治理范式下的社区服务应致力于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网络格局构建,重新审视治理范式下社区内涵及其社区服务的性质界定,打造主体多元意义下的社区共同体。
社区服务;福利治理;范式演变;未来走向
自1930年代吴文藻、费孝通引进“社区”概念以来,“社区研究”便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议题。已有研究揭示了中国社区服务的基本问题和发展理念,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研究的碎片化,过分强调社区服务具体案例的微观特征,没有对这些案例的一般性理论概括,从而缺乏对中国社区服务的整体反思;二是过分强调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的西方经验,而对中国社区服务的研究“泛泛而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并逐步取代了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揭开了公共政策领域治理范式的序幕。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社会治理”更是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所在。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部分,福利治理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诸多学者将研究聚焦于“多元福利主体的互动、供给与传递过程”。[1]本文立足于社区服务的“福利”本质,运用福利治理视角,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福利实践,聚焦于中国社区服务的政策文本演化与服务实践,探讨福利治理视角下中国社区服务的未来走向,建构社区共同体。
一 中国社区服务实践的范式演变
(一)社区服务萌动期的政府范式(建国初至1980年代初)
从词源意义上理解,“社区服务”一词由民政部时任部长崔乃夫在1987年的大连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但就其“福利”本质而言,其内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显现。学理上的“福利”,指的是国家和社会为了使个人或社会达到某种良好的状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其内容包括由不同的福利主体或制度所形成的收入和价值生产、相关服务、转移支付与津贴、政府补贴或基础投资等,广义上的社会福利由国家福利和社会福利构成。从此内涵出发,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建立的单位制度和街居制可视为“社区服务”的萌动期。根据具体历史特点的不同,可以将“社区服务”的萌动期区分成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的过渡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这种体制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通过单位制度和街居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整个城市社会形成一个“类蜂窝状”的社会结构。对于单位内部的居民需求,政府通过其单位供给的方式进行。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各不相同,为其单位成员提供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及其就业等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管理,政府在城市辖区以及不设区的市,划分一定的管理区域,一般以2~3万人为地域单位,设立了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其目的是把那些不属于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减轻政府和公安派出所的负担。[2]1954年12月31日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设立的目的即为加强城市中街道居民的组织和工作,增进居民的公共福利。街居制的建立,其目的是为了给体制外的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福利”,这些公共福利的资金和资源都由政府承担。虽然当时并无“社区”概念,但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街道办事处从事的工作带有浓厚的社区服务工作性质。特别是在1957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城市街道办事处除了承担市辖区人民政府交办的日常改造以外,还积极组织以家庭妇女为主的闲散劳动力,发展里弄生产加工和修配服务站,开展社会福利事业,兴办托儿所、幼儿园等公益性的服务机构”。[3]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的社区服务属于典型的政府包办式供给服务。
历经十年“文革”期间城市街道管理工作的全面瘫痪,1979年2月,全国人大重新公布了1954年颁发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城市街居体制开始全面恢复。这一时点至1987年“社区服务”概念正式提出,我们视为社区服务“萌动期”的过渡阶段。从1979年始,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城市各街道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也逐渐增多。在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单位制开始趋向消解和变异,在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步发展出“双轨制”形态,建立了一种“分割制”的社会结构,“在保持单位制相对完整的前提下,对市场空间进行开拓与培育”。[4]“双轨制”的结果导致社会福利的分配在满足单位福利的同时,为改变单位福利膨胀带来的巨大社会不平等,“社区服务”的发展成为必需。民政系统对“社区服务”的探索起源于福利事业的社会化,1983年4月,在全国第八次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首次提出要改革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形式,集合国家和社会力量办社会福利事业。1984年,全国城市福利事业单位改革整顿工作经验交流会在福建漳州市召开,民政部在会议上提出要实现社会福利事业的“三个转变”,认为社会福利事业要改变单一的、封闭的国家包办局面,转向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的体制,指出要面向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确定社会福利事业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发展战略。1985年,民政部总结推广了“四个层次一条龙”的社会福利网络化的“上海经验”,以街道为重点、以居委会为依托的基层福利格局初步形成,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开始基层化道路。
从表面上看,这一阶段的“社区服务”开始了“社会化”路径,但从以下两点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判断该阶段“社区服务”的政府范式,一是从经费来源分析,此阶段社会福利事业的经费以政府财政拨款为绝对主体,二是从目的论分析,此阶段开展社会福利事业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初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开始显露,单位制的改革使社会福利服务需求和供给短缺之间的弊端日益突出,其目的在于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
1987年初,民政部首次明确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5]1987年9月,“全国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全国性的社区服务工作进入起步阶段。时任民政部副部长张德江在座谈会上指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城镇的社区服务,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在街道有组织地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提倡居民间的互助精神,以灵活多样的社会化服务形式,为社会居民特别是有困难的人提供各类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同时认为“社区服务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是民政部门承担社会保障任务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城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延伸和扩展”。[6]就政策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的社区服务体现出鲜明的政府范式。
(二)社区服务推进期的市场范式(1980年代末至1999年)
随着我国改革事业的进一步深化,“市场”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学术界亦称这场改革为“市场改革”或“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7]同时,这场发起于经济领域的市场改革给社会、政治和福利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化,在福利领域的最直接表现即为“社区服务”的市场取向。
市场范式的直接表征即为社区服务的产业化。1989年12月颁布的《居委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这为社区服务的产业化提供了法律依据。民政部1993年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指出社区服务业具有福利性、群众性、服务性、区域性四大特点,要根据社区服务业的不同服务对象和项目,依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采取无偿、低偿、有偿相结合,以有偿服务为主的方式,建立起标准有别的服务价格体系,改变社区服务业价格偏低、价值补偿不足的状况。对老弱病残,服务价格必须优惠;对社区居民,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价格和收费标准完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在市场范式的规制下,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居委会掀起了一股创业热潮。
不可否认的是,市场范式下的社区服务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但这一范式下的社区范式同样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表现在政府责任层面。1980年代末以来,单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制的进一步推进,将大量原属单位制庇护的社会成员推向社会,扎根于社区,沦为社会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社区服务体系的福利介入。但是,更多的地方政府领导或由于财政资金的紧张,或出于认识上的混乱与不足,不愿在社区服务领域投入更多的财政资金,而是以“社区服务产业化”为由,把更多的本应由政府解决、属于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问题推给街道、居委会,推给社会,经过“这样一嫁接,社会福利服务变成了‘社区服务’,国家(政府)主办主体变成了‘倡导’,主办主体模糊化,政府职责变成了‘社会互助’,结果是该由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服务没有得到发展,有的地方甚至推得一干二净”。[8]二是对社区服务“福利”本质的伤害。虽然诸多的政策文件都规定在推进社区服务产业的过程中,要注重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格局下,经济效益成为社区服务实践中压倒一切的追求目标,很多地方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甚至给每个社区居委会下达创收指标。在这个导向下,社区居委会围绕社区服务产业化挖空心思,但由于区域的限制及其经营能力的缺乏,社区服务业往往经营不善,导致经济效益无法实现,其福利本质亦被忽略。
(三)社区服务发展期的治理范式(2000年以来)
1990年代末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对各类需求精细化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事实使当时的社区服务面临三大困境:一是服务主体层面,单纯由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当时主要以救助、救济服务为主,社区居委会提供的微薄的便民服务无法满足当时社区居民要求;二是服务质量层面,由社区居委会兴办的社区服务业所提供的各类服务质量已经不适应社区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三是发展方向层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育完善,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财税制度、工商行政管理制度逐渐规范,社区居委会兴办的各类社区服务业逐渐走进死胡同。
鉴于此,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社区服务范式实现了重大调整,突出表现在政策文件不再提“社区服务业”,不再强调社区服务的经济效益,转而更加注重强调社区服务的公共性,强调要发展社区公共服务,尤其要突出发展针对弱势群体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强调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所有这些表明,社区服务的福利宗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归,治理范式开始显现。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指出“社区服务主要是开展面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社会贫困户、优抚对象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面向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其中明确规定“资源共享、共驻共建”是开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原则。从社区服务的内涵界定及其社区建设的目的原则分析,此文件强调社区服务内容的社会化和主体的多元化,社区服务范式的转向趋势明显。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将福利主体分解为非正式部门、自愿部门、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并认为福利主体的多元化实质是政府在福利领域的权力分散和其他部门包括社会民众的社会参与不断提升的过程。[9]这一点在2007年颁布的《“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得到了明确的规定,指出“社区服务体系是指以各类社区服务设施为基础,以社区居民、驻区单位为服务对象,以满足社区居民公共服务和多样性生活服务需求为主要内容,政府引导支持,多方共同参与的服务网络及运行机制”,强调社区服务参与方的多元性。2009年,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制、互助机制、志愿机制、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社区居民的社区服务体系,满足居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服务需求”。2013年颁布的《民政部关于加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形成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主导,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社区社会组织、业主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格局”。至此,中国社区服务的治理范式得以初步确立,并作为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的目标持续推进。
二 治理范式下社区服务的未来走向
(一)致力于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社区服务网络格局构建
当前我国社区服务的治理范式初步形成,但从社区服务实践来看,依然是“病弱者为导向”和以“个体消费者为导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完成了社区服务的纵向整合功能,[10]而治理范式下的社区服务亟待构建出一种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网络格局。
不同于政府范式、市场范式下的社区服务,治理范式下的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网络社区服务格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政府角色上,治理范式下的社区服务要求政府转变角色,由原来的资源掌控、权力集聚型的角色转换为信息发布、需求调研、资源对接以及协调平台等;二是在主体关系上,治理范式下的社区服务需要重新调整各个主体间的权力格局,需要彻底摆脱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格局,制定各类有效规则,形成各主体之间合作“共治”的良好局面;三是在服务内容上,治理范式下的社区服务需要摆脱长期以来的弱势群体取向,面向全体社区居民,调研社区居民实际需求,分类别、有层次地提供社区服务,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系统中各种组织的优势,形成整体合力,打造优势互补的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网络格局社区服务格局。
(二)重新审视治理范式下社区内涵及其社区服务的性质界定
近十余年来,“社区服务”在城市居民当中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名词,但需要指出的是,“社区服务”这个词汇“自它在我国诞生之日或使用之日起,就因其理论表征上的缺失和实践归属上的模糊而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11]而之所以出现“理论表征上的缺失和实践归属上的模糊”现象,其根源在于对“社区”界定的偏颇。我国使用的“社区”一词,更多地注重地理方位,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管理而进行的行政区划,更多地倾向于地域和行政意义上的内涵。而滕尼斯的“社区”是先于“社会”的结合类型,它与“社会”是一种对应关系,注重精神、感情,追求心理信仰的归属,是在传统的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紧密联系起来的小群体。[12]在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过程中,政府、学界和社会对于社区的基本定位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即为基层治理和共同体。前者强调政府的权力再造和权力下沉,后者强调公共服务建设和团结感的营造。[13]长期以来,基于地域和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中国社区,在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制度规范。以此为基础,在当前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营造和构建社区的“共同体”定位至关重要。美国学者桑德斯(I.T.Sanders)认为“社区”的界定方法归纳起来有四种:一是定性的方法,把“社区”理解为一个居住地;二是生态学的方法,把“社区”看成一个空间单位;三是人类学的方法,把“社区”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四是社会学的方法,把“社区”看作一种社会互助。[14]我们认为,“共同体”定位下的社区内涵,宜采用综合性的视角进行界定,即包括生态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在内的综合。
长期以来对“社区服务”性质界定的犹疑,亦是出现“理论表征上的缺失和实践归属上的模糊”现象的根源之一。有学者将社区服务视为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笔者认为社区服务的出现和发展与单位制的消解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密切相关,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考量,设定社区服务的初始目的在于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在于将改制背景下游离于单位体制之外的“闲杂人员”和进城务工的“盲流”纳入可控的地域范围内。正是基于这种出发点,自“社区服务”的萌动期和推进期,对其性质的界定一直在“福利”和“产业”两者之间徘徊,在更长的时期内,社区服务的“福利”性质被漠视和忽略。从本来意义上探究,社区服务的内核是面向社区居民的福利性、公益性的社会服务。[15]因此,在治理范式下,“福利性”应是“社区服务”的主旨所在,确切地说,“社区服务”应该是我国福利体系在地域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我们认为,学术界关于“社区服务”的两种提法值得关注:一是社区服务的公民导向,认为社区服务应是一种基于公民身份和资格享有并参与的活动,这种取向表达“社区服务”不是施舍而是权利这样一种理念。[16]二是将社区服务视为一种“区域性集体物品”,在这种观点下,我们在保证社区服务“福利性”的同时,并不排斥其“市场性”,而是在“签订了一致同意的社区协议框架之下,企业家就可以参与进来提供最优化的集体物品水平”。[17]这就意味着社区服务不应是单纯的福利性服务,应该根据社区类型的不同和社区居民需求的不同分别提供不同层级的、不同性质的服务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与社区服务的多元主体构建密切关联。
(三)打造主体多元意义下的社区共同体
在当前治理范式下,构建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社区服务网络格局,需要明确各个主体之间的权责分工,明确“国家—市场—社会”格局下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
一是要明确政府在该范式下的职责和功能。社区服务主体多元化的趋势,需要摆脱将政府视为社会福利运行的唯一主体,认为政府应该承担一切福利责任的偏颇观念和实践行为。治理范式下的政府不应该是社区服务的唯一供给者,政府为社区居民提供的服务也不应局限于救济性、兜底性社会救助服务,政府应在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努力建构社区居民服务信息的收集平台、需求与主体供给之间的沟通和对接平台、社区服务质量的监督平台等,努力构建出一种社区的“服务传递协力合作网络”。[18]
二是要充分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在社区服务中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要充分意识到第三部门在中国情境下发展的特殊性。当前学术界对第三部门的研究存在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实践者在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简单按照西方经验生搬硬套的误区,要想在中国情境下促进第三部门的快速发展,更好地发挥第三部门在治理范式下社区服务的重要主体作用,就必须由原来的“西化”道路转向“化西”的途径,实现第三部门在理念、组织运营以及与政府关系等层面的“创造性转化”。[19]
三是要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自身积极性,打造社区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社区意识的培育至关重要。王处辉提出社区意识“五维一体”的“结构”分析法,涵盖社区情感认同、社区参与程度、社区满意度、信任与奉献精神以及是否关注社区发展五个方面的内容,并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情感认同、高质量的社区参与以及对社区发展的持续关注是形成社区治理合力的关键。[20]我们认为这些亦是治理范式下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社区服务网络格局构建的基础所在,而要夯实这一基础,打造社区共同体是其关键。但需要注意的是,治理范式下多元主体水平化的社区服务网络格局构建过程中,温情脉脉式的共同体或许在短时间内能起到一定效果,但打造一个将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更为妥当。以此为平台,我们可以在整合社区居民自身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共同努力,满足社区居民的整体服务诉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治”,开创治理范式下社区服务的新局面。
注释:
[1]韩央迪:《从福利多元主义到福利治理:福利改革的路径演化》,《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2]王振耀、白益华:《街道工作与居民委员会建设》,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4页。
[3]徐永祥:《社会发展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4]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5]崔乃夫:《在大连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民政工作文件选编(1987)》,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48-250页。
[6]张德江:《在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政部政策研究室编:《民政工作文件选编(1987)》,第259-260页。
[7]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页。
[8]王先胜:《城市社区服务综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9]N.John,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Amherst: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7,p.94
[10]陈建胜、毛丹:《论社区服务的公民导向》,《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1]徐永祥:《社区发展论》,第172页。
[12]赵寿星:《论“社区”的多样性与中国的“社区建设”》,《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9期。
[13]陈建胜、毛丹:《论社区服务的公民导向》,《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4]转引自方明、王颖:《观察社会的视角:社区新论》,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
[15]徐永祥:《社区发展论》,第173页。
[16]陈建胜、毛丹:《论社区服务的公民导向》,《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7]弗雷德·E.弗尔德瓦里:《公共物品与私人社区》,郑秉文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8]蔺丰奇:《社会福利服务输送与治理研究》,《社会福利》2012年第11期。
[19]刘杰、田毅鹏:《本土情境下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困境及道路选择》,《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5期。
[20]王处辉、朱焱龙:《社区意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刘秀秀
C913
A
1006-0138(2016)05-0092-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样态及其治理研究”(14CSH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市社区新公共性构建及其路径研究”(13YJC840025)
刘杰,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武汉市,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