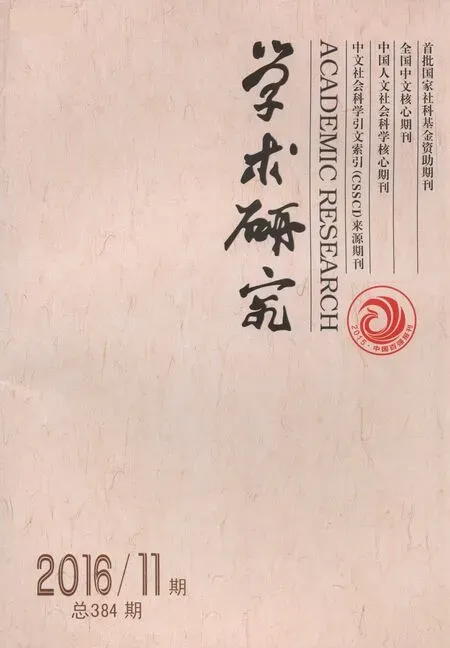风宪与立宪:清季都察院裁改的冲突*
林 剑
风宪与立宪:清季都察院裁改的冲突*
林 剑
清末预备立宪,京内官制改革首当其冲,各部院或更名或裁撤合并。风宪衙门都察院何去何从,朝臣和舆论建言献策,裁改意见分歧明显,一方面,内有因势而变的改革动力,外有分化组合的改革压力;另一方面,科道鼓噪而鸣,高层矛盾重重,上下难以和衷共济,争执乃至冲突始终存在。激烈交锋之后,主政者权衡利弊,保存名目、变通整顿成为都察院维系皇权体制与进入宪政政体的折衷选择,既影响了1906年丙午改制成效,也为日后再议裁改埋下伏笔。
都察院 预备立宪 风宪 丙午改制
被称为风宪衙门的都察院,①都察院创设于明,改自御史台,其职掌大抵传承自历代御史,可谓源远流长。《明会典》记载,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是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申时行等重修:《都察院·风宪总例》,《明会典》卷209,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6年,第4153页)《皇朝文献通考》称都察院专掌风宪,以整纲饬纪为职。凡政事得失、官方邪正,有关于国计民生之大利害者皆得言之,大狱重囚偕刑部、大理寺谳平之。(清高宗敕撰:《职官六·都察院》,《清朝文献通考》卷82,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6年,考5603)清承明制,雍正年间六科始隶都察院,自始“台省合一”,制度较前朝慎密,皇权体制登峰造极。由于明清设官分职注重“大小相制、内外相维”,耳目之官让帝王明目达聪,纪纲攸系,是为维系皇权体制重要机构。与清末预备立宪关系甚大。近年来学术界已有相当关注,且在丙午改制讨论方面成果丰硕。②侯宜杰爬梳中央体制改革过程,指出保留吏部、都察院是编纂官制大臣妥协的结果。(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细珠注意到科道等京官弹章蜂起现象,试图揭秘幕后操纵者。(李细珠:《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8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迟云飞重点研究宪政改革的起因,官方各派人士对立宪的体认,清政府改革措施的讨论与决策,预备立宪产生的影响。(迟云飞:《清末预备立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关晓红考述改制前的外官制和外官改制的酝酿和定案,揭示清末官制变革,将原来“内外相维”格局改为上下贯注,是近代中国政体转型的重要内容。(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上述专著所涉及的丙午改制相关史实成为本文重要参考,其研究思路提示笔者从制度移植与本土回应的角度解读都察院裁改问题。此外,以言路、言官和法制史视野考察都察院存废之著述的还有杨雄威:《日暮途穷——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言路》,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郑云波:《言官与光绪朝政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李启成:《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刘涛:《从都察院到检察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然而,既有研究成果侧重官制讨论过程中风宪官科道各奏折内容,较少深究风宪衙门改革与预备立宪展开的内在联系,易于忽略朝野舆论屡屡强调汉唐以来风宪一职[1]对于皇权体制的重要性,进而影响对体制转型的整体理解。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历时梳理丙午改制期间都察院议改情形的基本脉络,以图深化对清末官制改革艰难曲折的认识。
一、重新定位:沟通中西的努力
丙午厘定官制以前,着眼于师法立宪国而变更本国官制,且旁及都察院变革的意见有:甲午前后,较早将都察院与下议院联系起来的是汤震,从广开言路出发,仿照西法设置上下议院。设想下议院由都察院主导,上议院由军机处主导,共同讨论“大利之当兴,大害之当替,大制度之当沿革”。[2]百日维新时期,蔡镇藩建议仿西国议员做法,都察院增加议事之官。[3]新政之后,康有为《官制议》主张“法古经、行西法”,指出都察院六科既是中国议院,又是中国行政裁判所。强调未有议院之前,都察院是最重要的机关。[4]日俄战争胜负未分之际,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上书政务处王大臣,倡言效法英国、德国、日本开设上下议院,都察院定为下议院,政务处定为上议院。[5]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间,皇室载振奏请变通各部旧制,考虑到因系建言论事之地,都察院未可轻议裁撤。[6]
上述构想,相似之处均肯定都察院在皇权体制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抽取其奏议、弹劾、审官犯、判百事等职掌,对应宪政国议院或行政裁判机构的职能,指出改设方向;即使保留衙门,亦据西方司法独立原则调整权限。上述建议与意见,有如下值得关注点:其一,视角问题,中为体,西为用。都察院作为天子之耳目,设官之意重在下情上达,内部监督及纠偏防弊,服从服务于皇权。各种方案初衷不是使之走向皇权体制的对立面,而是新陈代谢后功能回归。其二,若采用三权分立推进改制,议会终将监督皇权。上述诸议中以通上下之情比附代议职能,实未突破皇权体制封闭监督模式。此求形似而非神似的思路,究竟是时人认识局限抑或是已有自觉的刻意含糊,有待进一步研究。①时论认为都察院与议院不可相提并论,但可比附,“第天下事有精神不同,而形式尚可比附者。存其形式,即可预为改易精神之地”。见《本馆论说·论裁减科道之不宜》,《时报》1906年3月23日第1版。其三,底层官员言论多以经世文编系列或报刊杂志为传播媒介,未必能够上达天听。驻外使节以及大臣采用正式渠道表达观点,虽纳入政府视野,亦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仿行立宪渐成朝野共识,官制改革进入倒计时。由于清朝皇权体制和外国宪政体制的主旨和架构大为不同,内官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各部院依照三权分立原则进行调整,②“三权”之说是舶来之物,新概念与旧制度差异甚大,以“行政”为例,其范围内容不断扩展,参见关晓红:《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学术研究》2009 年第11期。势必关联推动都察院重新定位。
1906年8月25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礼部尚书戴鸿慈与闽浙总督端方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建议共8条,3条与都察院密切相关:一是仿行设置责任内阁,统一中央行政。二是内外各重要衙门堂官明确主辅,避免推诿牵制。三是“中央各官宜酌量增置、裁撤、归并也”。此最后一条至为关键。在其中央官制总体设计中,新内阁总领中央九部,新内阁之外,增置集议院等独立机关。该折认为,各国于司法行政之外设立行政裁判院,上图国家公益,下保人民权利,制度虽各有不同,而“公开裁判许众庶旁听,扶助私益许吏民对质”,立意与都察院大略相等。[7]
若按中西官制对应思路,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都裁判厅、都察院改行政裁判院似乎顺理成章。然而,该折主张单独设立行政裁判院,专门受理官民不公之诉讼及官员惩戒处分。而以国会不能骤然开办,权宜之计仿照日本做法将都察院改集议院,作为国会“练习之区”。[8]其主要职能和选举办法也有考量,负责审议财政预算、建议条陈、疏通舆情等,“选额既已平均,意见自无畛域,而本省利病亦可因此研究,以补中央耳目所不逮矣。”并表示将来成立国会,自可赋予立法权。[9]
需要指出的是,深谙本国实情又熟稔立宪国体制的戴鸿慈与端方,制度设计煞费苦心。一是总体框架效仿日本二元君主制,与虚君共和的英国相比,皇权尤重;选择“练习之区”过渡,不采取一步到位方式,且将弹劾权划给行政裁判院,立法权留待将来之国会,可弱化对皇权的冲击。二是集议院通上下之情,有言事之权、耳目功能,似与都察院职掌相同,改设师出有名。三是全国按省划定选区,除王公、勋爵、京员额公推,绅商、士子参选议员。有别于以往都察院与议院、御史与议员直接或间接划等号的主张,议员公推公选而非钦定,意味着官民开放式监督有望取代封闭监督机制,皇权受到影响。由此可见,设计者如此安排,在由旧的君主专制国家体制向新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有意让新、旧势力分享政权,并形成暂时的平衡。①参见迟云飞:《清末预备立宪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戴折明确以中央与地方官制对应清朝原有的内外官制,如此套用外来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置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改制造成很大困扰。②参见关晓红:《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就都察院而言,外官的督抚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名衔,乃原先“内外相维”的格局所致。倘若将都察院抽离皇权体制,改为中央机关,实际上难以安置,亦是后来论者争辩不休的关节。
同样拥有直接观察外国政体经验、出使德国的大臣杨晟意识到立宪前后应分阶段处理,暂存整肃风宪之官极其重要。他建言疏通监察,都察院职官视情形决定去留。具体言之,国会未开之前,裁撤长官、改革行取之法、废除科道名目,比照立宪国“三大委员”重新条理职能,分设三职:一司谏诤,一司监察,一司代达。限制条款为不得议论法律、敕令,防止阻碍行政运作。国会成立之后,裁撤与宪法规定权限相抵触之职,分别并入应管之官。[10]
杨折虽未明言裁撤都察院,然所议科道更名转型的出路,实仍仰赖宪法规定确认进退,近乎渐进式裁撤取向。在其官制大纲中,讨论顺序以官员为先,机构为后。例如,法制撰定之官协赞立法,各级裁判之官郑重司法,整肃风宪之官疏通监察等。与戴鸿慈、端方注重将中西机构对应改革构想不同,杨晟注意到中国地域广阔、人民众多,设官数量将十倍于外国,百倍于前代,应顾及本土实情,侧重为既有体制旧官员找到新官制新位置,并不拘泥于衙门裁撤并转,似乎借此建立一条平缓坡道,让皇权体制逐渐淡出,宪政体制逐渐兴起,实现对接中西之目的。
二、改设之议:分歧与冲突
在接受戴鸿慈、端方所奏之后,1906年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政体,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决定“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11]随后,媒体披露编制官制大臣拟定的官制大纲,其中,集议院以都察院改设为议院基础,其制度大要8条,与戴鸿慈、端方等原奏大致相同,③《代论·拟定官制大纲(续)》,《时报》1906年9月12日第1版。另,官报披露都察院改为集议院消息,御史闻之颇为疑虑。见《御史王步瀛奏新定官制多有未妥应饬认真厘定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8页。说明改设意见进入官方编纂程序。
9月18日,御史王步瀛奏陈妥定官制宜“兼采众议”,奉旨考察政治馆王大臣知照各衙门各抒所见。[12]其后,被誉为风宪官的御史们则合力协同大小官员将讨论引向全面深入,将言责作用发挥淋漓尽致,彰显自身价值。
关于改设议院,一些御史基于维护风宪官既有职能,提出不同意见。给事中陈田认为改设之后,只得议论政事,不得单衔具奏,使得朝廷耳目闭塞,进而警告朝廷,“万一不幸有如康有为之谋为不轨者,言官不得直达,朝廷欲闻文悌之忠言,杨崇伊之告变,何可再得也?”[13]陈田意在弹劾疆臣跋扈、庸臣误国,反响热烈。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慈禧太后把陈疏“持示枢臣,旋即收回。闻疏辞甚切,直可谓朝阳鸣凤矣”。[14]报载,太后询问枢臣陈田人品。[15]军机大臣荣庆力保,“系奴才同年,人极忠诚,名誉极好”。另一位军机大臣铁良附和,“现在他们拟裁御史,若使裁去,老佛爷安能知此事?”[16]传闻暗合陈田保存言路之意。
御史叶芾堂申明通达之义,指陈都察院改为集议院将阻塞言路,要求“纠弹不法,下通民隐,剔弊锄奸,宜仍归都察院”,又以民众尚无议员资格,缓设集议院。[17]御史赵炳麟瞩目新设机构责任内阁与集议院关系,认为内阁官制草案授权总理大臣自行交议、自行议决、自作议长,明里仅有行政名义,暗地里掌握立法、司法之权,“集议院徒作赘疣,甚或资为政府之傀儡”,[18]言下之意,对集议院并不赞同。
值得一提的是,赵炳麟还发现新内阁制侵损上奏权,动摇都察院地位,危及皇权。雍正以来,清朝有上奏权官员人数相当固定,对于上奏权的使用极为慎重,各衙门堂官上奏一般都联衔,以机构的名义出奏。①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5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5页。相形之下,都察院别具一格,除了满汉6堂官以外,80名科道官员均可单独直递封奏,并许风闻奏事,权力很大。而按新内阁制条目规定,一是原有上奏权内外官员数百名锐减为内阁及各部大臣共14人,“言路隘之又隘”。二是例行事件方许该部尚书单衔具奏,有名无实。三是阁议破坏祖制召见独对之法。赵氏直言,“臣不知此次该大臣等所拟官制,将置朝廷于何地也。”一言以蔽之,新编官制权归内阁,“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19]切中慈禧心事。②慈禧首要关注“君权不可侵损”,见《余肇康致瞿鸿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五日),《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一些官员延续前述都察院比附议院思路,试图阐明风宪与立宪相通相助。员外郎闵荷生认为,国朝爱惜言官,讨论庶政部议再三,实兼专制、立宪之美意。“方今指陈政事得失,不可无人,遵守朝章推行尽利,尤不可无人,人多则言杂”,主张以都察院为会议之地,精选进言之官,不必裁员。[20]赵炳麟进一步申论,议院尚未设置,立法权无所归属,建议遵从祖制,以有直接上奏权的御史、讲官及四品以上京堂,分任立法职务,畅通民意表达渠道。[21]所谓立法之职务,应指议员。对于御史等官充当议员,大臣看法不同,“殊恐程度不及,难胜其任”。[22]
与朝臣反复申辩意见悬殊,有媒体从根本上质疑改设之举。《宪政杂志》发表题为《庶政公诸舆论释义》社论,解读9月1日上谕,指出国家机关分为执行机关及监督机关,监督机关即舆论之所寄也,在中央则为国会,在地方则为地方议会;强调舆论机关由人民选举组织,代表民意,注重于监督政府。一针见血指出,“集议院之性质与都察院截然不同。都察院拾遗补阙,为君主之私属。集议院代表舆论,为国家一独立机关。”所言之意,风宪衙门之于皇权体制,集议院之于立宪体制,泾渭分明。如果以旧改新,将导致名实相混、精神湮灭。社论还分析朝臣未曾提及而现实存在的困难,譬如,旧衙门习气问题,都察院人员如何安置问题,全部更新还是妥协仍旧问题,可能因为该杂志的宪政研究会背景,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此院必宜新置也”。[23]
坊间消息,自裁撤都察院之议起,台谏人人自危。[24]王宝田、周克宽、胡思敬等官员纷纷上折提醒当道:六部以外,都察院最为重要,“诚以风宪之臣,固国家耳目所寄也”,历代忠清骨鲠之臣弹劾权奸,使远近震悚,豪贵敛迹,言官突然全部裁撤,会引发下情壅塞、深宫孤立、臣民惊惧的后果,故“闲散或有可裁,而都察院断无可裁之理”。[25]
在官制讨论期间,都察院总宪陆宝忠授意御史交章攻击官制改革,陆的背后又有军机大臣铁良、荣庆,而其幕后指挥则是军机大臣中位高权重的瞿鸿禨。③参见李细珠:《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侧重清廷高层政治权力运作的探讨》,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8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7页。因反对声音众多,阻力太大,厘定官制有“五不议”之说,都察院名列其中。[26]报纸进一步探悉,内官制草案大致敲定,“惟都察院议论不一”。起初,袁世凯、端方倡议将都察院并入集议院,消灭其名目。载泽则主张存留,且设法改良。嗣后,“两宫圣意亦欲保存此衙门,故决议不提议,袁宫保召见时亦奏明不改都察院。”[27]袁世凯何以改变主意,有两种说法,一是当事人杨寿枏回忆,源于自己力争,“台谏之职,总司风宪,纠察官邪,实为汉唐以来之善制,似宜保存”,以及载泽相劝,“台官弹劾不避权贵,我辈不宜轻”。[28]另一是孙家鼐反对。第一次会议袁主裁都察院,孙与争甚烈,不欢而散。第二次会议孙缺席,但提交书面意见,中有“都察院之制,最不利于雄奸臣慝,亦惟雄奸臣慝,最不乐有都察院”数语,举座为之失色,都察院遂得保存。[29]
显而易见,主张立宪的官员和保守的官员异口同声风宪官利于皇权,不利于权臣。而在戴鸿慈看来,风宪官自身抗争至关重要,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其后组织内阁,以各部为行政大臣,拟以察院改为立法部,以刑部改为司法省,嗣因察院御史不肯听裁,遂罢议立法一部。”[30]
三、风宪所关:进不去的立宪体制
保留主张既定,如何符合厘定要旨安置都察院,考验厘定官制大臣们的政治智慧。坊间传闻,针对都察院与新定各部官制有所抵触的质疑,大臣以圣意所在,又恐开罪言官,均不愿意更张。[31]载泽等迎难而上,主张官制草案将其纳入直隶朝廷监督内阁之五院序列,“有集贤院以备咨询,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弹劾,有审计院以查滥费,有行政裁判院以待控诉。”[32]不言而喻,作为中央独立机关,四院皆仿宪政体制之新设,惟独都察院为皇权体制之旧有,于此,立宪与风宪似可兼容并蓄。
《都察院官制草案》解释“存古”之义,“汉唐以来悉重此职,实中国制度之特色,亦为各国所交称。风宪所关,无可裁并。”惟需变通厘定三事:各部院新官制一长官、二次官,均不分满汉,都察院沿用旧制,与之相歧。六部变更,六科仍存旧目,名实不符。旧制都察院兼掌伸理冤抑、稽核报销,职务太繁,遂难尽举;既仿司法独立之制,应专掌监察非违、条陈利弊。[33]该草案经奕劻、孙家鼐、瞿鸿禨等总司厘定后奏报。
11月6日,清廷公布新官制上谕,宣称都察院本纠察行政之官,职在指陈阙失、伸理冤滞,着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着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均暂如旧。[34]可见,慈禧太后最大限度保留旧制,同时,否决责任内阁制。观此一去一留,除了瞿鸿禨默运挽回,[35]还有科道的因素。《申报》称,太后览阅关于新内阁之总理大臣权势太重等奏折,大为动容,故内阁、军机处均未更动。[36]《盛京时报》传闻,赵炳麟、王步瀛、刘汝骥等科道前后所上改定官制条陈语多中肯,颇蒙两宫采择嘉许,特许都察院衙门维持现状,并将科道各官优加倚任。[37]而据当事人记述,慈禧太后曾对刘汝骥说,“所谓预备立宪者,无非通下情就是了,那不是空空立宪两个字,祖宗法度就全不用了。就是各国宪法,亦自不同。我自然有主意,不至失了大权,你只管放心。”①刘汝骥:《陶甓公牍》,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64页。一定程度折射主政者激扬风宪的用心和对立宪的认识偏差。
细绎新官制关于都察院17个字的定位,与前引《皇朝文献通考》之表述大同小异。“纠察行政之官”似为趋新说法,实质仍为风宪官;“指陈阙失”与《都察院官制草案》“条陈利弊”说法相符。至于“伸理冤滞”通达下情,原系都察院专有职责,故京控案件向归办理。奕劻等核定方案时曾据司法独立原则删除,清廷则在裁定方案中予以恢复。可见,涉及皇权体制的关键职掌不容有失。但是,三法司之制渐废,[38]此一与审判紧密相关的权限尚未切割,留下日后部院争议空间。若以行政裁判者视之,②织田万认为都察院具有伸张冤枉、检查会计等9项职权,是“实质上之行政裁判者”、“兼我会计检查院者”,见氏撰:《清国行政法》,李秀清、王沛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0-211页。鉴于行政裁判院已被剔除出新官制,则为重议都察院改设行政裁判机构留有伏笔。时论已关注行政裁判缺位现象,并对都察院寄以厚望,“可补行政裁判所之穷”。[39]此外,上谕决定渐次增设审计院、资政院,两院职掌与都察院的会计检查、疏通舆情、通达民意等职掌互有交叉,亦隐含冲突的可能。综合而言,丙午官制改革方案中,都察院大体如旧,显示其不似其他部院,通过裁改并转逐渐成为宪政体制的中央机构一员,仍属于皇权体制的风宪衙门。其新表述边界模糊,或因为军机大臣未明新学,“故颁谕之始,即已含混不分疆界”,③新官制关于法部和大理院权属并未清晰界定,后来引发争执,史称“部院之争”,法部尚书戴鸿慈跨洋去信求教梁启超解决之道,见戴鸿慈:《致任公先生书》(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卅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0页。给都察院未来走向增添不确定因素。
有意思的是,新官制尘埃落定之际,革命党人孙中山从共和政治的角度,给都察院指出独一无二的道路。他认为:纠察制是中国固有优良制度,长期埋没而不为所用,期望在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中复活。除了监督议会外,还要专门监督国家政治,以纠正其所犯错误,并解决共和政治的不足处。[40]只是孙中山理念真正付诸实践,已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四、结语
要而言之,都察院维系皇权,作用独特,无法割舍。仿行宪政,都察院难以转型为“中央”机构。究其原因,既凸显时人对都察院重新定位的认识纠葛以及高层派系纷争,更深层次则反映风宪衙门与立宪体制不相凿枘。面对两难选择,清廷在保守者和改革者之间左右摇摆,取法中庸。正如外论所言,“弥缝主义”四字而已。[41]如此结局,各方均不满意。随着仿行宪政步伐越迈越大,改革迫切性与日俱增。此后数年,都察院屡议裁改,屡次延宕,两广总督岑春煊、都御史陆宝忠先后奏请以都察院代下院(改国议会),遭到科道极力反对,当轴亦不以为然。①会议政务处重申“都察院职司风宪,关系至重”,强调“谏官之与议员体制不同,万难合混”,说明主政者心目中,风宪衙门依附皇权体制,止步于立宪体制。见《会议政务处议奏都察院不可轻议更张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5754-5755页。职能部分重叠的新机构资政院与旧衙门都察院并存,计划之内的行政裁判院迟迟未能开办,新内阁办事暂行章程仍许言官自行专折入奏,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主政者既无勇气除旧布新,又对日益强大改革呼声反应迟钝。直至辛亥鼎革,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伊始,即暂停奏事,绵延百年的封奏戛然而止。丙午年间,御史赵炳麟所奏陈新内阁破坏祖制的担心,众多言官所警示大权旁落权臣当国的预言,似皆不幸言中。只是星转斗移,都察院与清廷的覆灭,均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1][33]《宪政初纲·官制草案·都察院官制草案》,《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第77、77-78页。
[2]汤震:《议院》,《危言(选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77页。
[3]蔡镇藩:《奏请审官定职以成新政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87页。
[4]康有为:《官制议》,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7、252页。
[5]《内务·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第83页。
[6]《奏为官制窳败事权不一亟宜仿专任之法一律改定以维政体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0页。
[7][8][9]《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71-374、374页。
[10]《出使德国大臣杨晟条陈官制大纲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93-394页。
[11]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12]《清德宗实录》卷563,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乙丑,《清实录》第5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7页。
[13]《掌户科给事中陈田奏疆臣跋扈庸臣误国将酿成藩镇之祸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22 辑,第779页。
[14]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324页。
[15]《本馆专电·太后注察言官人品》,《新闻报》1906年10月13日第1张。
[16]《要闻·京师近信》,《时报》1906年10月29日第2版。
[17]《御史叶芾堂奏官制不宜多所更张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47页。
[18][19][21]《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流弊太多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3辑,第46、41-43、47页。
[20]《户部员外郎闵荷生建言官制不必多所更张呈》(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06-407页。
[22]《条陈议员不宜以御史改充(京师)》,《申报》1906年10月4日第3版。
[23]罗普:《庶政公诸舆论释义》,《宪政杂志》第1卷第1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朔日,张玉法主编:《清末民初期刊汇编》,台北:经世书局,1985年,第54-63页。
[24]《要闻·京师近信》,《时报》1906年11月8日第2版。
[25]《内阁中书王宝田等条陈立宪更改官制之弊呈》(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克宽奏更改官制只各易新名实不如旧制折》(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59、420、433页。
[26]《中国要事·改定官制有五不议》,《新闻报》1906年10月12日第1张。
[27][31]《要闻·京师近信》,《时报》1906年10月22日第2版。
[28]苓泉居士辑:《觉花寮杂记》卷1,《云在山房类稿》第4册,民国19年刻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第4页。
[29]徐一士著、徐禾选编:《言官小议》,《亦佳庐小品》,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页。
[30]戴鸿慈:《致任公先生书》(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卅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0页。
[32]《宪政初纲·官制草案·厘定阁部院官制总说帖》,《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第2页。
[34]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96-197页。
[35]《张之洞致鹿传霖两电》(光绪三十二年),《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8号,第33页。
[36]《新官制事宜三志》(京师),《申报》1906年11月18日第2版。
[37]《京师要闻·两宫嘉许科道员之条陈》,《盛京时报》1906年11月16日第2版。
[38]“国史馆”校注:《清史稿校注》第5册,卷15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93页。
[39]《社论·论时局危险之象》(天池),《时报》1907年2月6日第1版。
[40]孙逸仙:《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9-320、331页。
[41]《宪政初纲·外论选译》,《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第12页。
责任编辑:杨向艳
K257.5
А
1000-7326(2016)11-0127-07
*本文系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林剑,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