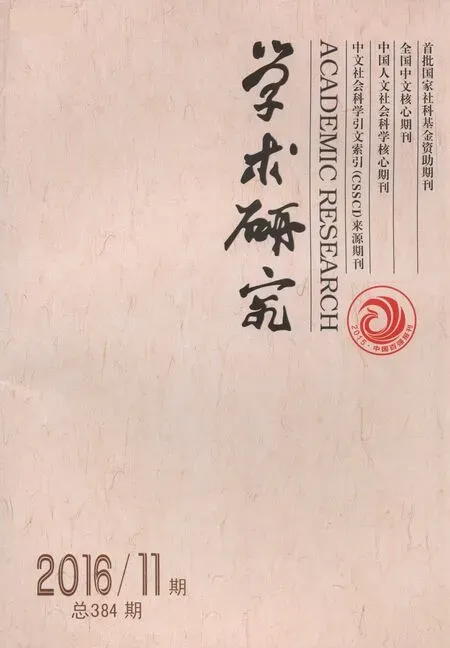全球化进程中的认同逻辑与向度*
詹小美 苏泽宇
全球化进程中的认同逻辑与向度*
詹小美 苏泽宇
现代化与全球化交织中的文化自觉,作为现代化逻辑演绎的过程与向度、趋势与倾向,与经济全球化推动和作用的“时代政治”、“精神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主张与推进的“异质趋同”和民族国家要求与坚守的“排他斥异”,作为统一于经济和政治过程中的整体,构成了认同与斥异结构性失衡的现实场景。面对“文化自觉”的时代凸显,反思与建构的认同向度,情感性、利益性、价值性的认同链接,以“五个认同”的内生逻辑和外衍关系固本强基,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同一性基础与包容性空间,而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 异质趋同 排他斥异 五个认同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集中于经济全球化。作为商品、货币、贸易、移民世界性对接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不仅于资本扩张与增值的经济过程中凸显,而且在文化激荡与碰撞的政治过程中深化。作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全球化丰富和拓展了民族国家交往互动的空间和民族成员参照对比的对象,进而引发了传统族群边界的结构性伸缩和原生族群根基性认同的情境拆合。作为资本运行的新表征和价值传播的集合体,全球化的深入与推进,不仅导致了以民族国家为主要政治形式的工业体系的形成,而且促进了集共同命运的族群归属和政治独立身份诉求于一体的民族主义崛起,由此催生“建构民族性”和支撑“想象的共同体”为内涵的政治运动。面对文化自觉的时代凸显,必须“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以“五个认同”的内生逻辑和外衍关系固本强基,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同一性基础和包容性空间,而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自觉,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化与全球化交织中的文化自觉
现代化与全球化交织中的文化自觉,作为现代化逻辑演绎的过程与向度、趋势与倾向,与经济全球化推动和作用的“时代政治”、“精神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起源于工业化的经济全球化是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持续扩张的产物,是区域现代化对接世界现代化的结构性成果。经济全球化首先是资本逻辑扩展的全球化,以此为先导涵盖和渗透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触角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2]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现实交织,“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3]来自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共同解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
互为过程与结果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一种将世界各地的人群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全球社会的趋势。”现代化导引的市场整合和结构性调整,使经济全球化“可以视为世界范围内,社会性联系的加强,由此发生在各个地域的事件,其影响可以波及原来被认为遥不可及的地方和人群”,[5]民族国家和民族成员交往互动的空间和参照对比的对象随之改变。与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性组织的出现同步,跨国公司、跨国联盟、区域联盟纷至沓来,资本、货物、人口的全球流动加速,移民潮和“解构主义”双重运作,公民权利向非公民延伸,文化认同的传统界限被突破。概言之,经济全球化的时空分延“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6]其间,以社会力量的面目显现的资本杠杆牵引着工业资本向知识资本的递进,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是工业现代化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向度的缩影。其背景涉猎广泛性、领域界阈伸张性、利益要求多元性,导引不同的利益视角、不同的历史语境、不同的领域划分成为可能,使全球化派生的普及和莫衷一是的矛盾成为现实,挑战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7]
经济全球化还表现在经济运行环节的全球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工业化的发展使全球范围的经济转换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不仅从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且得到了商品倾销的世界市场。他们“通过前所未有的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不平等交换,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系到一起,形成现代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9]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普及,采购、生产、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经济运行环节不再局限于共同体的实体界限,而被赋予了跨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意义。在此格局中,以资本、商品、技术、服务和劳动力为代表的所有生产要素几乎都被整合至某个特定的空间或区域,最终汇集为单一的全球大市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置身于这一市场之外独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进而汇聚为文化自信与价值迷茫碰撞的文化场景。
在资本扩张的现实逻辑中,“从世界性商品链中产生的总的剩余价值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这些剩余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在商品链的所有环节上平均分配,而总是集中于一些特定的环节和地区”。[10]经济全球化不仅未能带来资源、收入和权力的全球性分配,没有解决国际决策全球失衡的现实问题,没有创造出消除民族差别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反而将各民族间关系与差距愈加恶化为穷国和富国的悬殊。这一事实证明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1]经济利益是如此,文化利益更是如此。在现实性上,文化自觉赖以生存的民族利益诠释和文化自信载体,浓缩了民族国家面对全球化的作为与态度,表征了民族国家社会结构和经济地位参与世界竞争的过程和结果。发达国家的文化自信,以“文化进化论”传统与现代的区分,构建文化同质的普遍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则强调“本土化”和“特殊化”的历史传承,以“文化相对论”回应“文化趋同”的挑战与碰撞。“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竞争与妥协,不仅隐喻着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国家地位,而且表征着民族国家文化自觉的“主动进攻”与“被动应战”。与此相适应,文化自觉的伸缩与张力“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后殖民主义’的自觉反抗并重新燃起对于独立的渴望。”[12]
二、异质趋同与排他斥异的现实场景
认同与斥异既是共同体生活的重要命题,又是文化自觉的重要问题。当相似性和相同性指向社会关系形成时,认同的价值肯定与斥异的价值否定,凸显了与“他者”比较的“我们”,进而形成认同与区分的归属。“我”到“我们”的包容性原则、“我们”与“他们”的斥异性原则,不仅决定了同一性基础上身份识别的事实性确立,而且决定了差别性基础上群体设限的选择性后果,具有内部主张与外部要求双向稳定的结合与表象。
在文化自觉的认同关系中,民族与国家是最为重要的考量。国际体系中最为稳定的共同体形式,民族与国家复杂而深刻的互动,构成了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道路认同的源点。文化是具有物质载体的观念世界,是人类创造世界的主观方式和民族存在的现实图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以民族为载体依附于具体国家,成为共同体深层的记忆和民族国家的精神意涵。族群是人们对其出身和世系所做的文化解释(查尔斯·凯斯语),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构建的一种关系,由共同起源到共同文化的人类共同体,作为概念的族群被文化论的学者视为社会承载与文化区分的单位,而近代意义的民族,其形成与维系更深地依赖于“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因此,民族认同主要表现于历史文化认同。国家是建立在民族机体之上的上层建筑,是民族共同体的权力组织机构、民族文化的捍卫者、民族利益和民族主权的代表者。作为“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民族意志和命运的物质体现”,[13]国家以领土、人民主权、政治合法性为原则,搭建国民联系的桥梁,实施稳定的制度,提炼和抽象民族意识凝聚的观念与思想。在现代世界体系下,所有的“人口集团”均被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纳入国家司法行政的领域里,在这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内,国民对政治制度设计、安排和运行的研判,对其合法性、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研判,对国家所赋予的利益、政治资源运行绩效的研判,贯通政治认同之制度、利益和绩效,直指国家认同之条件、基础和标的。
回眸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无论是脱胎于封建王国的演变,还是源起于多元帝国的废墟,均与近代民族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近代意义的主权国家和近代意义的民族尽管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同步,但它们寻求公共权力,进行政治整合的诉求和过程则达成了相对的统一,进而完成了两种共同体形式的对接与融合。特定土地上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蕴涵和公共权力机构的汇集,从地域分界、民众心理和社会接纳等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了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决断、价值选择和认同实现,最终导致民族共同体形式政治化的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创立如果不是必然地,也是经常地作为一个社会的其他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这些变化在学术上有时简称为‘现代化’。”[14]领土、主权和民族紧密结合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管控与治理人们的社会生活,协调与润化人们的社会关系,维护与固基正常的社会秩序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在单一民族还是复合民族之间游移的民族国家,它的实体形式还是取代了以往一切陈旧的语言,它的整体利益还是战胜了狭隘的地方性阻隔,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演绎为民族成员的道德与义务。即使国家功能“弱化”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发生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仍然以获取国家权利、挑战现有资源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颠覆政治运行的机制和结构为中心反复出现,从未跨过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范畴。
民族国家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内部排斥机制。作为民族国家政治运行的前提预设,内部排斥机制强调民族成员既是单个独立的原子,又是彼此平等的国民。它所内涵的国家主权独立神圣不可侵犯,其意义不仅直指国际关系的法理基础,而且直指文化认同达成的政治依托。历史上,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意义的近代研判和最终确立,无时无刻不与社会阶层的流动和政治决策的民主化联袂而行。资产阶级在强调人生而平等之时,从未止步于语言、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强制同化。他们在开放政治权利的同时,亦将对外战争诠释为公民义务的基本内容,以此凸显排斥性内涵的本质意义和区分他者的功能性标的。国家领土上的集体与个人总是定格于国家存在的意义;民族国家的职能总是实施于具体的领地;具体地域上的人民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源头;权利与义务总是联系着公民身份与公民权的授予。
经济全球化的“异质趋同”与同一性基础的“排他斥异”,使民族国家在碰撞和挤压中遭遇主权危机,使传统的根基性认同在混沌与冲突中面临挑战。“来自上面的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压力,来自下面的地区和反对利益的诉求压力,以及来自水平发现的市场和市民社会变化的压力。这些因素削弱了国家在经济管理、社会巩固和文化认同上以及制度化构造的能力”。[15]事实上,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内部要求与全球化异质趋同的发展趋势、自由贸易协定与开放的贸易体系,无不体现了互惠互利的游戏规则对战后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的现实碰撞。传统的殖民扩张,总是借助国家、族群、种族的定义和表达,进行政策和道德设计的价值介入和法理判别,而全球化却使地方要求脱离国家制度成为可能,使区域间的高度同质成为可能,使激活特殊群体的族群要求成为可能,使跨国行为的物质形式和象征利益的隐藏成为可能。由此,与“想象的共同体”紧密相联的非领土化政治悄然兴起,正在消减民族国家存在的传统意义。“一方面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民族性观念的群体)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或共同掌握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国家也试图稳固或垄断关于民族性的观念。”[16]非领土化政治已逐步演变成为全球原教旨主义的核心(阿帕杜莱语),极端主义试图抽象出想象的族裔共同体,甚至不惜瓦解现存的国家。
就认同的指谓而言,寻求“我”与“我们”、“我们”与“他们”之别的镜像是其重要的一环。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化”、“国家化”的思考与公民权“独特性”、“排他性”的要求,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全球化在弱化国家地域界线的同时,在干扰国家主权与社会管理的传统职能的同时,还指涉了公民身份与公民权授予的基本原则。异质趋同与排他斥异的失衡,群体边界与固定空间的弱化,整体与传统集合的疏远,“催生出一个能够在世界各地流动的、具有多元种族结构的、能够使用英语的专业人员阶级”。[17]就世界精英们的无国籍化趋势而言,“精英是世界的,而老百姓是本地的”(卡斯特尔斯语)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跨国家化的精英们在2010年较之2000年的2000万已然翻了一番。全球化为全人类带来了思考和界定共性的询问,“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宣称我们是谁”、“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依据、“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受此影响,“现今的国际事务越来越难以使用‘我们’一词。过去‘我们’一词往往意味着自己的国家,现在人们对国家的从属并不一定能够对个人的利益和忠心”做出界定。[18]身份的具体与虚无,不仅仅是身份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意义的缺席、价值的泯灭、目的的空置代言,所有这些“虚无”都指向了认同的危机,“虚无主义深深地内植于现代性,终有一天,现代性会被证实为虚无主义的时代,是那个无人可预言的‘某种东西’从中涌出的时代。”[19]
“异质趋同”与“排他斥异”的结构性冲突,不但证明了“把社会认为是结构化的、有组织的、与民族国家空间界限一致”的理论误区,而且昭示着“现代社会理论”与全球化实践对接的现实真空。就共同体生活的实践而言,在全球化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寻求共识、奠定认同的基础是困难的,这不仅因为多元语境下的权利表达难以平衡集体性的要求,而且因为文化差异情境中的权利平等难以构建民众接受的理论范畴。正因为如此,民族国家对领土主权、公民权授予及合法性的坚守与诠释,对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及民族特质的坚守与高扬,无不彰显了“异质趋同”与“排他斥异”的话语对决,无不隐喻了认同与斥异的矛盾对立,无不指向了共同体内部次生关系互动的限阈。对此,尼格尔·多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社会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在朝普遍性进步,而实际上,它只是产生了大量不协调的、自我指引的(局部的狭隘的)合理性,它们变成了实现普遍合理秩序的主要障碍。”[20]
三、反思建构与层次链接的认同向度
反思与建构的能动和交互开启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自觉的逻辑演进与发展向度。经济全球化与认同机制在文化自觉中的矛盾对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跨国化,衰减着国家的部分职能,但这一切仅仅指向“他们运用的逻辑、他们为之效力的委托人、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占据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而已。”[22]全球化暴露出来的危机症状和矛盾失衡,迫使人们从政治制度和社会包容等各个方面对现行制度的缺失进行结构性审视,对既有矛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影响进行深入的剖析,进而使制度转化和更新成为可能。“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的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23]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强势席卷一方面消解文化自觉的传统语境与价值原则,另一面则为文化自觉的理性认识和自由抉择催生机遇和活力,两者形成互动和张力,在推进民族国家制度创新的同时,为文化自觉的吐故纳新和社会共识的价值凝聚提供新的舞台和理论阐释。
情感性、利益性、价值性的认同分层,导引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自觉认同演进的梯级与节点,构成了“五个认同”强本固基的内生逻辑。情感性认同是认同的基础层次,它源自于共同的族缘记忆和文化基因,通过具有原生性、血源性的“共同体想象”寻求族群归属与文化身份的确定性。根基性的情感来自人们生而获得的“不证自明”的特质,在一定的语言、仪式、宗教、风俗习惯中得到重复体验与确证。民族成员由此获得一种根基性的心理边界与社会坐标,这种“同舟共济的亲密感”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文化解释的主观认定与传承,援引民族成员心理情感的基因图式,激活个体认同的群体意义,构成族群内部关系的变量与个体认同的源点。利益性认同是认同的中间层次,其实质是在特定的资源竞争关系中形成的具有工具倾向的认同,强调认同的多重性及其随着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情势拆合的特质。认同的动因不仅包含了利益的考量,其象征意义同样参与物化,具有实践的指向与利益的要求。在资源竞争的条件下,利益的分配直接影响互动场景的变化,导引认同边界的伸缩以及商榷性内涵,生成利益表达的政治空间与制度中介,赋予原生纽带以肯定与感召的现实意义。价值性认同是认同的最高层次,其本质是自觉的理性认同。当代中国,理性的价值认同集中表现于共同体成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据此形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表征着民族成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可和赞同,最终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
“五个认同”的相互联系与依次递进,反映了认同主体于时代特征的深入思考,其实质是情感性认同、利益性认同、价值性认同的逻辑衔接与层次递进。无论是情感性认同、利益性认同还是价值性认同,对时代特征的反映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它的抽象同时蕴含着某种规律性的共通。情感性认同表现于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自然认同,据此形成历史既定的宿命天成,指涉民族特质的实体与观念系统的体认,成为民族成员身份识别、族群归属、价值共识的基点与源泉。利益性认同表现于民族成员的祖国认同,其强化认同的形成彰显国民对制度设计、政治绩效与利益分配的肯定与赞同,表征着国民政党认同的理性自觉与正向研判,指涉国民归属身份界定的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的凸显和国族意志的张扬。作为群体利益表达与价值研判的实体形式,民族与国家的利益性认同承籍于民族成员原生情感与价值选择的中间环节与现实依托。价值认同表现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源于对5000年从未中断的文明认知、对政党执政理念的感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接受;产生于民族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之层次链接的理解向度中,来源于情感性认同的根基性和原生性,演化于利益性认同的竞争性和分配性,凝练于价值性认同的意向性和自为性。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道路认同的演进向度构成了文化自觉“五个认同”固本强基的外衍关系。“五个认同”的实现承籍于文化、民族认同,政治、国家认同,政党、道路认同的外衍关系中。文化、民族认同承载着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文化价值内核的深层体认以及族属身份的情感归属,保有与强化着民族文化特质,为“五个认同”提供情感皈依与身份识别的价值语境;政治、国家认同彰显民族与国家、文化与政治的权力整合与对接,表征着国民对国家主权、国民身份、国家利益的坚守,对政治设计之制度、利益与绩效的认可,为“五个认同”提供具有政治蕴含的价值引领;政党、道路认同内含国民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与执政能力的认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为“五个认同”提供决定国族发展愿景的价值归旨。“五个认同”于文化、民族认同,政治、国家认同,政党、道路认同所提供的“价值语境”、“价值引领”、“价值归旨”中相互链接、依次递进、循环论证,彰显了中华民族直面挑战、把握机缘的进取与互动,形塑着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中国气派、中国力量,构成了中华民族应对全球化异质趋同强势席卷的文化自觉。
以文化、民族认同为源泉,汲取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价值养分,固基政治、国家认同。以“五个认同”为基点,确立自我肯定的延伸和“他者”承认的佐证,是中华民族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举措。从理论研判的视域出发,认同“可以是强加的,但很少如此;更正确地说,认同是皈依的,因为它们呈现的正是人们想要的。”[24]在经济全球化资本的视野里,族群政治的国家层面无论是认同还是认异不过是原质主义悖论的缩影。这不仅在于认同构成的根基性“原质”——语言、肤色、地域、亲缘早已削弱在全球化的长河中,而且在于“原质”性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想象”。阿帕杜莱将这种建构归纳为人种、媒体、科技、金融和意识形态图景的全球流动、层次断裂和时空脱节。认同的建构不仅受制于内外因素的挤压和刺激,而且受制于图景内部和各图景之间的交互与影响,从中折射出图景断裂的结构性松动。从这个意义出发,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和族群的集体认同,必须在民族文化的“语意心境”中寻求唯一的“题旨情境”以消除认同的分歧。
认同的起点是认知,对民族文化的符号认知、情节认知以及价值认知,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选择的起点,而且也是文化自觉符号翻新的基点。作为民族成员自由意志理性选择的结果,价值认同为文化自觉的吐故纳新以及认同力的现实转化延伸主体、客体、介体。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生成与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物质与精神的生产实践紧密相连,它不仅反映中华民族成员独具特质的心理思维规律与特点,而且反映着民族成员在物质与精神生产实践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与价值研判方式,从制度、利益和绩效等方面生成、引领、整合民族成员价值共识。认同同样受制于比较中的差别和共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关系的每一次扩大、生产交换关系的每一次深入,都使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民族载体引发深度和广度的变化,影响着被卷入地区和民族的传统结构和制度安排,促使这些地区和民族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迈进。一些民族和地区重新审视着自己所处的世界地位,重新诠释着利益的民族指向和区域分配,试图抓住世界政治和经济重组的时机,与生产过程发生更为直接的联系,提高进入全球市场的自主性,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然而,这却是一个既收获利益又夹带着痛苦的过程。如此看来,异质趋同的全球化竞争凸显了“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仅靠单一的市场不能防范这种分裂,而“市场加国家”更需要文化自觉的凝聚力量,因此“脱离政治和国家的经济是不存在的。”[25]由于资源有限性和资本扩张性的对象冲突,更由于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的双重复合,竞争的全球化风险更为彰显。有鉴于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仍然是民族利益的竞争,利益最大化仍然是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策略的目标追求,深化和培育民族文化的时代精神,赋予其超然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成为民族国家全球竞争的不二选择。
以政治、国家认同相统一的中国梦价值认同为引领,强化全球化视域中具有民族特质的同一性基础与包容性空间,带动政党认同与道路认同。政治认同是国民对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的理性认定与情感归属,包含对政治设计、政治安排之制度、利益、绩效的综合考察与价值研判,构成国民身份意识的主要依据。政治认同是政治组织尤其是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源泉,其归属情感与理性自觉的实现直接影响政治组织制度化的程度,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参数。同时,政治认同代表了政治组织与政治过程的国民参与度与支持度,具有凝聚共识、统一标的、激发热情的功能属性,是社会动员与社会力量凝聚的强大动因,为政治组织的方针、政策、路线的贯彻落实提供精神动力。国家认同是最基本的政治认同,是国民对国家疆域、国民身份、人民主权的主动认可与自觉服从,是对国家性质与合法性的价值体认与理性自觉。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本质的中国梦,以中华文明为历史根基、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全体民族成员为实践主体,是贯通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发展愿景与共同向往,是个人梦与国族梦的辩证统一;中国梦价值内涵的话语表达,立足于民族特质的当代凸显、民族传统的时代转换、政治价值的全球主张、国家精神的顶层建构,是历史向度、现实向度、未来向度的辩证统一;中国梦价值认同是民族成员于历史的纵向源流中、世界的横向比较中对国家、民族发展具有自知之明的时空定位,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物质基础、法治建设、政治保障、精神动力、社会条件、生态建设、国际担当的多维畅想与价值趣旨,是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辩证统一。
中国梦价值内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特质为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之上的文明形态与发展模式的当代表达,阐发与“他者”比较的价值追求、利益关系和实现方式,凸显中国梦价值认同的整体性、特殊性和世界意义,从“他者”的佐证中获得自我肯定的延伸,强化族体自我认同的同一性基础。价值认同的感召功能、凝聚功能和物化功能构成了中国梦感召力、凝聚力和物化力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撑,其整体性、同构性和自身调整性,为文化自觉的软实力提升延伸主体、客体和介体,充实东方话语体系建构的物质基础、精神资源和包容性空间。政党认同的根基在于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其核心要旨是认同。融通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社会核心价值构成了民众对政党认同的价值标准,而政党的政治作为、执政绩效、执政能力构成了政党认同的现实根据。道路抉择是政党认同的重要依托,为政治作为、政治绩效与执政能力提供综合的价值定向与目标导引。作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梦价值内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族发展愿景上的现实展开,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担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全球化“异质趋同”强势席卷的进取与互动。中国梦价值认同所催生的价值共识与价值凝聚,切入共同体政治的实际,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目标支撑、价值整合与精神动力,导引共同体政治进行、理性、贴切的制度设计,推动共同体内部利益共享机制的更新与完善,动态地诠释和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理论逻辑。
[1]《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6日。
[2][4][7][8][11][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276、276、276、252、1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5]李鑫炜:《体系、变革与全球化进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
[9] Tеrеnсе K. Hорkins & Immаnuеl Wаllеr-stеin,World-Systems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ology,Nеw Yоrk:Sаgе Publiсаtiоns ltd,1982,рр.42-43.
[10] Immаnuеl Wаllеr-stеin,“Dеvеlорmеnt: Lоdеstаr оr Illusiоn”,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Саmbridgе:Pоlitу Prеss,1991,р.109.
[12]田佑中:《论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的形式及意蕴》,《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7期。
[13] Gеоrgе. H. Sаbinе,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Nеw Yоrk:Hоlt,Rinеhаrt аnd Winstоn,1961,р.306.
[14]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1页。
[15] Miсhаеl Kеаting,The Reg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and Political Change,Сhеlеnhаm:Edwаrd Elgаr Publishеrs,1998,р.73.
[16] Аrjun Арраdurаi,“Disjunсturе аnd Diffеrеnсе in thе Glоbаl Gulturаl Eсоnоmу”,Pubilic Culture,vоl.2,Sрring,1990.
[17][22] Mаsао Miуоshi,“А Bоrdеrlеss Wоrld? Frоm Соlоniаlism tо Trаnsnаtiоnаlism аnd thе Dесlinе оf thе Nаtiоn-Stаtе”,Critical Inquiry,Summеr,1993.
[18]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24-225页。
[19] Hеnri Lеfеbvrе,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Lоndоn:Vеrsо Publishеrs,1995,р.224.
[20]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23]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4]约瑟夫·拉彼德:《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25]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1-251页。
责任编辑:罗 苹
D0-02
А
1000-7326(2016)11-0028-0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梦价值认同研究”(14АZD007)的阶段性成果。
詹小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泽宇,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