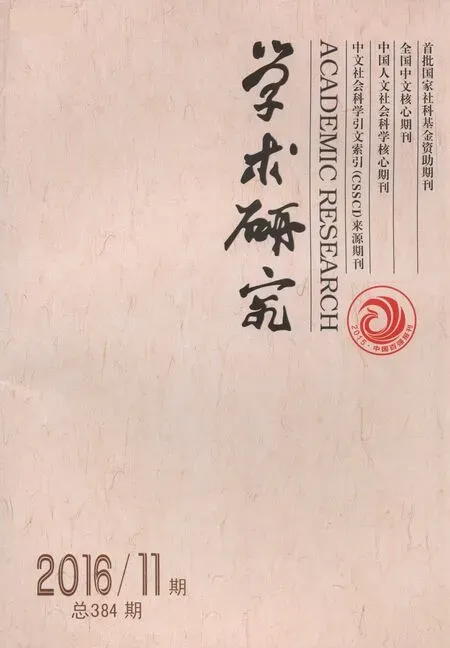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
肖 珺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
肖 珺
跨文化传播需要沟通交流并生产意义的共同体空间。德国学者滕尼斯定义的共同体是在血缘、感情和伦理为纽带的基础上自然成长的,然而,全球化和信息化改变了共同体对地方的依赖和归属感。原始意义不断瓦解的同时,随着社会生活进入流动的空间,共同体的概念也在不同的语境下被重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结构和其内在的运行逻辑表现在:基于连接的虚拟共同体、虚拟共同体的信任形成与维系、虚拟共同体中的认同建构。由此,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三个维度得以建立,即连接、信任与认同。跨文化传播与虚拟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传播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显现的路径。共同体所必需的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在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中实现了互动的可能、意义的流动和价值观的理解。
跨文化传播 虚拟共同体 连接 信任 认同
一、跨文化传播与虚拟共同体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其终极关怀是要实现文化融合,从而达致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1]跨文化传播需要沟通交流并生产意义的共同体空间。
共同体(Gеmеinsсhаft,英译Соmmunitу)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明确定义为:“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习惯,或思想的共同记忆,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滕尼斯将“共同体”从“社会”概念中分离出来,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则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2]滕尼斯定义的共同体是在血缘、感情和伦理为纽带的基础上自然成长的,他认为其基本形式包括亲戚(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友谊(精神共同体)。共同体中的个体有着相同的目标,追求和谐的生活方式和“善”,因此,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共同体中的个体紧密联系,守望相助,共生排他。可见,最初的共同体概念离不开地缘和“在场”,它根植于地方中。
然而,全球化和信息化改变了共同体对地方的依赖和归属感。新的通讯手段为构筑归属感开启了可供选择的道路,共同体产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为穿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网络,原本遥远的世界不经意间渗透到我们的地方经历中。数字新媒体催生出新的流动形态和互动方式,流动的空间(sрасе оf flо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еlеss timе)形塑了网络社会。[3]可以说,当代社会围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流动成为所有事物的基本特征,信息、知识、情感、商品等在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流动中征服了地方空间,征服了地方空间原有的状态与经验。[4]流动空间使得人们不再依赖地缘和在场塑造共同体,进行意义交换、经验共享、文化共生,脱域(disеmbеdding)的共同体由此出现。
原始意义不断瓦解的同时,随着社会生活进入流动的空间,共同体的概念也在不同的语境下被重构。共同体不是既定的,而是“一个在构建中的持续重新商议过程”。[5]虚拟共同体(Virtuаl Соmmunitу)成为网络社会的成员围绕自身需求塑造共同体的自然选择,从物质形态上,它使共同体从实体丰富为虚拟,从精神层面上,它为个体提供血缘、地缘之外的归属感,满足个体的多重生存需要。不同的集群关系、组织类别、兴趣爱好、利益诉求等重新划分人群,共同体逐渐脱离地域束缚,延展出超越地理边界的文化共同体、学习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行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进而产生共同体参与者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跨文化沟通。
我国对虚拟共同体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对其描述和界定包括“网络共同体”“虚拟社区”等。有描述其是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所结成的一种团体或组织;[6]有将其界定为“以信息联系为连接纽带而形成的,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所结成的集群形式”;[7]有认为虚拟共同体、网络共同体存在差异,网络共同体往往强调在“网络”这样明确的介质中产生的来自于人类思想意识主控下的团结,虚拟共同体则沿用滕尼斯对共同体最本质的界定:共同善和协商自治;[8]有研究试图建立基于共性的定义:“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9]上述研究描述的所有类型共同体都包含共同目标、认同和归属感三个关键要素,它们同样是跨文化传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跨文化传播强调在“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主体间性的理想状态,站在他者的角度上思考,克服陌生、焦虑和不确定性,在不同文化间生成融合的我们。“我”是社会中的个体,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作为社会人,“我”只有处在关系之中才有意义。在互动协商中,个体的身份通过表现和交换得以显现在群体和网络之中,进而超越个人形成群体身份,以标记群体内成员。共同体给予个体归属感和“内群体”的身份,被共同体排外的群体则被标记为“外群体”。“我”归属于某一群体,与人分享意义与价值,也能跨群体生存,通过跨群体身份来实现个人的价值、独特的创造和社会文化的融合。[10]这种在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距离的变化、跨界生存的可能性、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对立,以及开放的文化系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要件。而虚拟共同体的构建跨越了地缘,共同体成员面临本土文化与共同体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个体身份与社群身份的变迁,从实践意义上看,虚拟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亦是跨文化交往和传播的行动模式。
二、基于连接的虚拟共同体
连接是构建社会网络的前提,如有研究指出“文明社会的核心在于,人们彼此之间要建立连接关系,这些连接关系将有助于抑制暴力,并成为舒适、和平和秩序的源泉。人们不再做孤独者,而是变成了超级合作者。”[11]人们通过彼此间的连接形成或近或远、或强或弱的联系,而网络社会的基础就是连接后的协同关系。连接的网络成为人们进行自我构建和再构建的社会实验室,我们透过网络的虚拟世界进行自我塑造与自我创造。“在我的网络世界中,自我是多样的、流动的,由机器连接的互动所构成。”[12]随着数字新技术的更新换代,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连接变得更为频繁和必要,其连接关系出现以下特征。
第一,连接的强与弱。强连接与弱连接传播功能不同,但紧密相连。20世纪60年代,米尔格拉姆提出六度分隔理论,之后,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的《大连接》一书则提出三度影响力才是塑造社会网络的强连接。数字新媒体不断拓宽人类社会关系的广度,提高塑造虚拟共同体的速度,六度到三度的锐减表明人们很容易通过网络与自己生活圈以外的人进行连接,而且在越来越少的层级间就能形成富有能量的强关系。虚拟共同体中,弱连接在不同群体间建立连接的桥梁,强连接则深化和稳定共同体情感,强弱之分与个体、共同体对数字技术的采纳行为紧密相连。
第二,线上与线下连接并存。虽然虚拟共同体的连接依托于网络技术的支撑,但虚拟共同体并非仅有线上联系,更多同时存在于线上与线下,在线的虚拟连接不会完全取代线下的面对面交流,线下交流也能丰富线上连接。二者的并存互动、彼此建构塑造出边界模糊的多元空间,创造出新型的全球“混杂性”文化,“通过移民、媒体传播等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的运动越多,那么,混杂便越普遍,直至我们拥有一个混杂的世界”。[13]线上线下的连接并存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频繁出入于不同的文化群体,进一步加剧了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这样的经历和体验使得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更易产生混杂性的身份认同。
第三,连接的高度组织化。跨文化传播最初的研究都是建立在面对面的田野交往中,依托于成形的组织(部落、学习团体、移民社区、婚姻家庭等)。网络社会中的个体最初散落于星球之中,跨越时空的连接方式由于脱离地理边界而缺失制度化的组织管理,因而,因便利的连接而形成的共同体较难感受到真实的组织制度约束或保障。但伴随虚拟共同体日益具体的利益目标和情感诉求,伴随成员规模增大和文化多样性等挑战的出现,虚拟共同体需要并产生了高度组织化的联系,他们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连接起来,但也围绕共同体内的共同目标日趋中心化,这些都需要组织化地支撑和制度化地管理。
第四,连接的不稳定性。虚拟共同体来自网络社会,也带有网络社会各类组织共有的不稳定性特征。社交网络在连接关系的同时,也会导致社会关系变得脆弱和趋于技术化,当虚拟共同体失去其共有的价值取向、共同目标后,成员间的关系同样将面临弱化和消逝的挑战。同时,技术本身也并非坚不可摧,一旦出现技术故障,虚拟共同体的维系必然受损。更重要的是,虚拟共同体创造的关系影响着个体自治。对新媒体技术的采纳与使用让每个成员都拥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治,网络作为具有系统特性的媒介联结了各自分离的机器和它们的人类操作者,个人一方面享有更大的个人自治权,另一方面则必须接受技术系统的思维逻辑和接受被他人选择的交流生态,从而抑制共同体内的自治权。此外,个体的文化背景、行为偏好及自律状态、隐私要求等都会影响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稳定性。
三、虚拟共同体的信任形成与维系
社会心理学家1958年将信任定义为“信任者对被信任者采取合意行动的信念和预期”。[14]有关信任的研究也多从信任对于行动、认知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从虚拟共同体的角度看,信任是其团队内部成员进行互动、创新和任务达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信任的形成与维系,同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如在以学习为主要目标的虚拟共同体中,研究者指出存在四个影响学生们在共同体中表现的因素,分别是精神、信任、互动和学习。其中,信任指一种认为组内其他成员可信的感觉,代表着社区内学习者愿意依赖其他值得信任的成员。信任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指社区内其他成员的语言值得信任,二是学习者真心愿意帮助其他同学学习的互助善行提升信任。研究通过对比试验发现,较强的社区意识和信任有助于学习者更高频率、更多元的进行互动。[15]虚拟共同体中的成员参与意识、对不同观点的容忍程度、成员之间的信任感等都对虚拟共同体有效性产生影响。[16]信任是虚拟共同体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当内部成员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时,信任对共同体内的跨文化交往更凸显重要性。
与传统线下合作不同,虚拟共同体,尤其是以学习、工作等为目标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通常是一种临时性共同体,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完成某项特定任务而建立起来。共同体内部成员在这次合作以前,没有曾经合作的经历,未来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也极低。[17]在这种虚拟的、临时性共同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通常可以快速建立,它存在于共同的任务目标中,这种信任被称为“快速信任”,并非逐渐形成、而是直接输入的。这说明,共同体表现出较高的任务定向时,即便社会交流信息较少,虚拟共同体的信任程度依然较高。[18]因此,这使得虚拟共同体中的信任关系呈现出非人际化的特点。当然,虚拟共同体成员在合作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信任也会随着非任务性的交流而加深,此时的信任同样呈现出情感的维度。[19]信任在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中的形成过程是分阶段的,基于任务式的认知和基于情感关系的信任可能是前后的线性关系,亦有可能分列或并存。
总体来看,对虚拟共同体中信任的测量主要从任务、情感两个维度入手,主要影响因素如下。(1)能力。指在信任者心目中对被信任者能力的认知,这种能力是指被信任者是否具备、且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起作用的各类技术、专长等,综合称其为能力。当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成员跨越时空和文化聚合后,他们在完成共同任务的过程中,对任务的胜任能力可以让其他成员产生与任务相关的信任感。(2)信任倾向。指在一般情况下信任者对别人是否信赖的倾向性。[20]人们在信任倾向上通常有高低之分:高信任倾向的人,总体上认为别人值得信赖、并能合作,与低信任倾向的人相比,高信任倾向的人群更愿意与人合作。信任倾向直接影响着虚拟共同体最初的信任基础,从而影响着整个虚拟共同体的信任氛围。(3)角色合理性。共同体角色是指共同体成员为推动整个共同体的发展而与其他成员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有态度和行为方式。在传统的共同体效能研究中发现,一个有效的共同体内部存在四大类角色:探索者、建议者、控制者和组织者。[21]而共同体中的混合型角色是最成功、最具创造力的,而且使得共同体成员间信任也达到最高。虚拟共同体中的角色合理性越高,共同体信任就越高,因此合理分配共同体成员的角色才能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4)任务依赖性。指共同体成员必须彼此依赖,才能完成任务。[22]无论是传统共同体还是虚拟共同体,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成员之间通常会根据任务分工而互相依赖。[23]这种基于任务产生的依赖、以及依赖所潜藏的威胁都是共同体信任产生的前提。(5)组织愿景。指在虚拟共同体中,长远发展方向、共同体目的甚至理想目标,都明确且受到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认同。[24]组织愿景更多是从共同体整体层面出发的影响因素,组织愿景越明确,越有助于成员形成对组织的信任,从而提升整个共同体的信任水平。上述因素均对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信任关系的形成与维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虚拟共同体中的认同建构
(一)集体认同的建构与形式
在网络社会中,地方与全球的分裂、权力与经验在不同时空中的分离使得建构认同面临新问题,“要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则需要对认同重新定义,这种认同应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完全独立于支配性的制度与组织的网络逻辑”。[25]据此,曼纽尔·卡斯特①本文对曼纽尔·卡斯特(Mаnuеl Саstеlls)的姓名翻译参考其系列丛书《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另有中文翻译为曼威·卡斯特、曼纽尔·卡斯特利斯。将认同(idеntitу)定义为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且一切认同都是建构的。通过涉及社会行动者(sосiаl асtоr)的认同概念,卡斯特把意义建构的过程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的基础上。他认为一般而言,谁建构了集体认同、为谁建构了集体认同,大致决定了这一认同的象征性内容。卡斯特将认同建构的形式和来源分为三种:合法性认同(lеgitimizing idеntitу)、抗拒性认同(rеsistаnсе idеntitу)和规划性认同(рrоjесt idеntitу)。
合法性认同以社会已有的支配性制度为基础,以扩展和合理化行动者的诉求和行为。合法性认同的建构会产生一套组织和制度,以及一系列被结构化的、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这些社会行动者同时也再生产出合理化其行动和主导性的认同。然而,当行动者的诉求在合法性认同的框架内无法实现,他们可能或转向抗拒性认同的建构。抗拒性认同可能是我们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认同建构。这种形式的认同建构主体常常是那些被社会主导的逻辑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他们倾向于将自我界定为不受欢迎的,并围绕“内”与“外”的划分原则,通过反对他者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剥夺构筑起“我们”的共同体。抗拒性认同为行动者短期的抗议行动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他们的目标常常并不止于此,规划性的认同成为了可能的选择。规划性认同是社会行动者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此外,卡斯特强调,这三种认同类型并非固定不变,以抗拒性为开端的认同有可能在社会制度当中占据支配地位,从而成为合理化其支配地位的合法性认同,规划性认同的建构则源自于共同体抗拒,它是对一种不同生活的规划,有可能以被压迫者的认同为基础,扩展到由规划性认同所延伸的社会转型。
卡斯特提出的认同划分框架(即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得到不少研究的支持。合法性认同在现有社会支配性制度的框架下,通过定义抗议对象的不合法行为、寻找政治和法律的解决路径,将社会运动的诉求合理化,进而得到社会支配性力量的认同;抗拒性认同被认为是最重要、最主要的认同形式,它采用清晰划分内外、敌我的方式进行社会抗争,通过抗争获取对抗性的认同;规划性认同则是一种新的建构,社会行动者通过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新的空间、新的身份来重新界定自身的社会地位,制订长远的群体规划,最终寻求全面的转型。大量研究集中于抗拒性认同,他们认为:认同政治就是一种抗争,因为它要求“其他人、其他社会群体和组织(包括国家)必须做出反应”,也“因为认同政治涉及拒绝、贬低和替代别人所承认的身份”,[26]由这种框架所界定的集体认同感,“必然是对抗性或敌对的”。[27]而合法性认同、规划性认同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也未得到充分地验证和阐释,这使得虚拟共同体认同的多样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二)认同及其传播:集体认同、个性表达和超国家传播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集体认同感被认为是核心议题,梅卢西认为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对集体行动来说并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就是一种文化成就,而且“社会运动所构建的‘我们’感是对抗性的……因为它们在文化的基石之上向复杂体系的逻辑提出了挑战”。[28]以时间和诉求为标准进行划分,当前基于新媒体展开的社会运动大多可以被归类到新社会运动①新社会运动是指二次大战后兴起的、有别于传统政治解放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其诉求并非针对国家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相关的个体或机构的行为以及大众的价值观念,由物质追求转向价值推崇。参见周穗明:《“新社会运动”的性质、特点与根源——西方左翼理论家论“新社会运动”》,《国外理论动态》1997年第1期。之中,集体认同感(соllесtivе idеntitу)的建构被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运动中最核心的任务。[29]正如行动者的动机与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现一些非物质性的价值,[30]行动者之间的聚合基础也多是基于某种共同身份的认同。因此,新社会运动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价值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传统的阶级认同感日渐式微的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认同感的兴起。[31]这种认同危机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因为认同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总是发生在权力关系的语境里,认同的力量、话语塑造的权力势必成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研究中的焦点。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中的认同往往通过话语表达、互动、争夺和谅解。“话语是认同建构的基本因素与前提条件”,[32]话语支持社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身份的确定。认同的建构、传递和接受在对话中进行,这些对话的实现不仅是话语权的表征,其中使用的符号及其意蕴都是社会权力关系的象征。因此,认同建构可被视为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性的话语实践。新媒体提升了普通个体组织和参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同时也降低了正式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33]行动者以个人生活方式为基础形成灵活的政治认同。新媒体的出现将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个人和组织联系起来,通过信息的交换和行动的协调,有效地缩短距离,形成对决策者有实质影响的虚拟群体。跨国社会运动中文化的虚拟共同体从本土向全球扩张的同时也会生成文化内化的趋势,共同体通过共享语言等文化符号使得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最终成为文化的问题,比如,关于中国议题的研究表明新媒体社会运动“使跨国的中国文化领域成为可能”。[34]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是新媒体社会运动中的基本组织形态,行动者通过新媒体的连接性行动迅速卷入虚拟共同体中,共同体在国家间、种族间、利益诉求间等不同文化社群中裂变,人们通过话语的表达、信息的互动强化个人化传播行为,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建构自身(我),最终形成意义的交换和价值观的凝聚。尽管组织的控制或许更为松散,但以非物质性价值认同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感仍然是这些跨文化虚拟共同体建构群体(我们)的文化内核。当然,参与者认知自身(我)、群体(我们)是一个持续而动态的过程,从历史的维度看,技术、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发挥着强度不一的制约作用。
(三)虚拟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变迁
身份认同研究涉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中往往强调同一性与差异性、稳定性与流动性、单一性与多元性的辩证统一,避免陷入绝对的本质主义或相对主义的片面性,因此,身份认同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同时又随历史发展不断重构。它是由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向量彼此运动: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一个是差异性和断裂性的向量,一个指出我们过去的根基和连续,另一个则提醒我们,恰恰是那些断裂的经验塑造了现在的、真实的我们。
作为一种新兴的、替代性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来源,数字新媒体作为新的文化制度和机构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是空前的。作为一种信息来源,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象征性材料,包括话语、形象、信仰、设想,而身份认同总是建立在这些材料之上,人们在此基础之上认知自我、他人和社会,并对行动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文化机构,数字技术重新组织人们的生活,改变、破除或重建新的社会仪式和秩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虚拟共同体。数字传播技术日益打破原有的时空限制,原有的意义共同体不断解构和重组,同时,更广泛的意义共同体也在不断拓展和建构,使个体/集体的身份认同发生了的明显的变化。
由此,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三个维度得以建立,即连接、信任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所接受的文化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物理空间,传播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口流动、信息流动,跨地区的文化交流从而突破空间对文化的限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特征。[35]因此,跨文化传播与虚拟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传播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显现的路径。共同体所必需的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在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中实现了互动的可能、意义的流动和价值观的理解。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是在特定的多元时空关系中,群体中的个体/集体对其成员身份和文化归属的认可和接纳态度,以及对应的行为方式。它是将复杂的文化结构(包括民族身份、价值规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观念等)整合进个体经验的结果,是一种能够使自我获得归属感、安全感或平衡感的认知模式。身份认同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当下社会的印记,其中,民族是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来源。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身份认同经历了不断的解构和重构过程,民族国家作为身份认同传统的核心来源已开始出现超越时空界限,生成全球性共同体的可能性,如超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形成与运行不仅仅囿于网络空间。个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共享依然源自现实世界和原生血缘、地缘的经验。个体的身份认同不仅在网络空间中流动,同时也在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中彼此交汇。虚拟共同体的建立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现实世界已有的经验共享,也能够与传统意义的共同体进行互动性建构。研究者需要关怀的社会转变主要是,基于现实社会身份的个体如何在网络空间中组成虚拟共同体,他们在虚拟共同体中又是如何互相连接,形成信任、实现认同,从而实质性地打破传统的虚拟(线上)与现实(线下)二元对立的生活空间,进入到边界模糊的多元空间中进行意义的对话、自我的建构和社会的重塑。
[1]肖珺:《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脉络》,《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54页。
[3][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页。
[4]刘涛、杨有庆:《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卡斯特“流动空间思想”的当代阐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2期。
[5] [加]黛安娜·布赖登、威廉·科尔曼:《反思共同体》,严海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
[6]李斌:《网络共同体:网络时代新型的政治参与主体》,《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
[7]夏迎秋:《网络共同体研究》,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页。
[8]张雨暄:《虚拟共同体的生根、偏植和归正——基于社会稳定视角》,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5页。
[9]张志旻、赵世奎、任之光、杜全生、韩智勇、周延泽、高瑞平:《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10期。
[10] [35]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75页。
[11][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简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12] Turklе S,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Simоn & Sсhustеr, 1995, р.184.
[13]周宪主编:《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 230 页。
[14] Mоrtоn Dеutsсh,“Trust аnd Susрiсiоn”,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оl.2,nо.4,1958, рр.265-279.
[15] Аlfrеd P Rоvаi,“Сlаssrооm Соmmunitу аt а Distаnсе: А Соmраrаtivе Аnаlуsis оf twо АLN-bаsеd Univеrsitу Prоgrаms”,The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vоl.4, nо.2, 2001, рр.105-118.
[16][21][24]宋源:《团队信任、团队互动与团队创新——基于虚拟团队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253、126-127、264页。
[17] Dеbrа Mеуеrsоn, Kаrl E. Wеiсk, Rоdеriсk M. Krаmеr,“Swift Trust аnd Tеmроrаrу Grоuрs”,Trust in Organizations: Frontie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Thоusаnd Oаks, СА, US: Sаgе Publiсаtiоns, 1996, рр.166-195.
[18] Sirkkа L, Jаrvеnраа, Dоrоthу E, Lеidnеr,“Соmmuniсаtiоn аnd Trust in Glоbаl Virtuаl Tеаms”,Organization Science, vоl.10, nо.6, 1999, рр.791-815.
[19] Prаsеrt Kаnаwаttаnасhаi, Yоungjin Yоо,“Dуnаmiс Nаturе оf Trust in Virtuаl Tеаms”,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vоl.11, nо.3-4, 2002,рр.187-213.
[20]宋源:《团队信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传统团队与虚拟团队的差异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8期。
[22] Bаrt vаn dеn Hооff, Jаn А. dе Riddеr,“Knоwlеdgе Shаring in Соntехt: thе Influеnсе оf Orgаnizаtiоnаl Соmmitmеnt, Соmmuniсаtiоn Сlimаtе аnd СMС Usе оn Knоwlеdgе Shаring”,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vоl8, nо.6, 2004, рр.117-130.
[23]张喜征:《虚拟项目团队中的信任依赖和信任机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5] Mаnuеl Саstе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Second edition), Oхfоrd: Blасkwеll Publishing Ltd, 2003, р.9.
[26] Сrаig Саlhоu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хfоrd: Blасkwеll, 1994, рр.216-225.
[27][29] Williаm Gаmsоn,“Thе Sосiаl Psусhоlоgу оf Соllесtivе Асtiоn”,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1992, рр.53-76.
[28] Аlbеrtо Mеluссi,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Саmbridgе: Саmbridgе Univеrsitу Prеss, 1996, рр.73-74.
[30] 孙玮:《“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31] 何平立:《认同感政治: 西方新社会运动述评》,《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9期。
[32] 陶国山:《论“认同”的文学话语建构》,《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0期第1卷。
[33] Jоhn Аrquillа J, Dаvid Rоnfеldt,“Nеtwоrks аnd Nеtwаrs: Thе Futurе оf Tеrrоr, Сrimе аnd Militаnсу”,Foreign Affairs, vоl.10, nо.2, 2001, рр.238-239.
[34] [美]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3页。
责任编辑:王 冰
F061
А
1000-7326(2016)11-0042-07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项目“新技术与跨文化传播研究”(412500014)的阶段性成果。
肖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