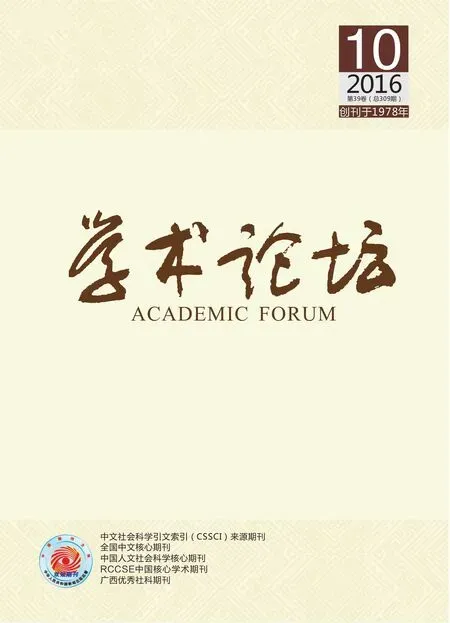《白鹿原》研究二十二年(1993-2015)述评
宋海婷,陈思广
《白鹿原》研究二十二年(1993-2015)述评
宋海婷,陈思广
《白鹿原》研究22年来,在文本主题研究方面,由前期的文化历史反思到后来的人性救赎,主题解读趋于多义;在创作手法方面,由现实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吸纳,到神奇、神秘、魔幻质素的汇入,使人们更深刻地感悟到现实主义永久的生命力;在人物形象解读方面,主要人物文化的、历史的、悲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解读;比较视阈一方面将其置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链条中,由此探寻1990年代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东西文学的坐标系内,发掘《白鹿原》所蕴含的世界意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白鹿原》研究的实绩与进展,为后来者提供了继续前行的支点。当然,研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白鹿原》;陈忠实;述评
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恐怕没有哪部作品像陈忠实的《白鹿原》那样自出版之日起就备受读者的关注,也没有哪部作品像《白鹿原》那样既不断阐释又聚讼纷纭。据笔者依中国知网统计,1993年至2015年6月间,学界共发表专论《白鹿原》的论文640余篇(不包括连环画、秦腔、话剧、舞剧及电影类),而关涉《白鹿原》的评论文章则在1460篇以上,论著近15部,硕博士论文150余篇。这无疑表明,这部一问世就被誉为“19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水平”[1]的优秀作品,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行列。也因此,几乎所有的当代文学学者都就《白鹿原》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可以说,“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1]。故而,探讨学者们在持续22年的《白鹿原》研究中提出了哪些富有启迪性的视点?它们对深化推进《白鹿原》的研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相应的,这些视点又折射出哪些问题?在未来的《白鹿原》研究中,我们应当如何寻求新的突破?等等,对于推动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主题:文化反思与人性救赎
《白鹿原》是一部横空出世之作,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小说所反映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深刻性。小说通过对白鹿两家半个世纪相互争斗的历史命运的书写,重新思考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悲剧动因,以及蕴含其中的复杂的人性因素与文化内涵。与以往创作不同的是,陈忠实没有单纯地从政治路线与阶级关系的视野去表现主题,而是将其置于悠久的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下考量我们民族的命运,这就使得小说的主题具有了对民族传统文化反思与审视现实历史的双层意蕴。雷达就认为,文本中“无论是大革命的
‘风搅雪’,大饥荒大瘟疫的灾祸,国共两党的分与合,还是家族间的明争暗斗,维护礼教的决心,天理与人欲的对抗,以至每一次的新生与死亡,包括许许多多人的死,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都与中华文化的深刻渊源有关,都会勾起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长思考”[2]。唐云也认为,“正是从文化内核之裂变来观察社会政治的变革,展示人类心智在时代诱因下的更张。陈忠实以这种眼光检阅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了有益因素,阐明这样的观点,人唯一永恒面对的是自己的心灵,一个民族也必须面对自己的传统,觅我所失”[3]。也有论者试图从历史观的角度阐释主题:“鏊子暗示着烙饼式的翻来覆去的运动,溶注了作者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评判和思考。”[4]而“(白鹿原》在深层意义上重构了民族精神”[5]。还有论者试图揭示《白鹿原》在现实的文化建设中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即“试图对传统文化的精神生命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本源性的阐释和理解,从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对于我们精神人格所具有的守护意义和家园意义”[6](P1)。
当然,也有学者对文本中对于儒家文化的肯定态度并不认同,南帆就指出:“《白鹿原》力图表明,儒家文化不仅是历史上一个遥远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传统还活在今天,而且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7]在他看来,这终究是作家的信念而已,事实是“现代社会的崛起也就是儒家文化渐行渐远的历史”[7]。但传统与现代的确是如此对峙不相容的吗?有论者对此进行了辩驳:“在《白鹿原》中,陈忠实并不是动用传统/现代、保守/开放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凸显传统文化的道德力量,来贬义历史权力冲突中的暴力意味,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民族信念,牢牢地确立在创作主体的精神意志之中。”[8]《白鹿原》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坚守成为一个鲜明的标记。
不过,也有论者指出,“《白鹿原》里的人性救赎意味和济世意味,要远远大于历史反思意味”[8]。而且“它穿越了一次次历史的狂波巨澜,不动声色地实现了对一个个乖张生命的救赎。它看似拥裹在深厚的传统痼疾之中,却又融合了儒与道的精髓,以强悍的伦理姿态,直击人性的脆弱部位,理性、祥和而又毫不含糊地左右着我们的生存,并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展示出它那卓越非凡的整合能力”[8]。这一观点对于长期已基本定位的文化历史反思主题无疑作了必要的补充。由此,文化反思与人性救赎共同成为解读《白鹿原》主题的两大重要视点。
二、手法: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
《白鹿原》毫无疑问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诚如李星所言,它并未标举或者创造什么新的艺术方法,现实主义仍然是陈忠实进行艺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所以使读者有了全新的阅读感受,源于“对于现实主义这个曾被一些激进者判为死刑的创作方法的新的体验”,这种新的体验即是对生命的体验与理解,具体体现在“将东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观同西方文化、文学中象征主义、生命意识、拉美魔幻主义相结合的特色鲜明的现代艺术”[9]。这也表明,《白鹿原》中的现实主义已不同于以往作品的现实主义,它“传递着现实主义在当今中国文学中推进的最新信息”[13]。所谓“推进”就是“他(陈忠实)在充分意识到文化制约的不可抗拒的前提下,把文化眼光与阶级斗争眼光交融互渗,从而把真实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2]。
1980年代,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全世界点燃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热潮,也激活了中国作家的历史想象,尤其在实写、虚写两种人物,魔幻气氛与神话,象征手法,夸张的运用等具体方面,其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弥补了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单一的弊端,也使作品呈现出不同寻常的风格。陈忠实受其影响自不待言,论者也一眼看出《白鹿原》是“一部神奇现实主义的大作”[10]。《白鹿原》中的现实主义也因之被注入新鲜血液,显示出生机与活力。
也有学者提出:“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历史‘现实主义文学’的猜测之外,我有点点相信它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地方志范畴里的 ‘现实主义文学’。在这方面,《白鹿原》大概应该被称作一部贯通着司马迁和柳青某种文化血脉和传承性的长篇小说”[11],也是一得。
正是《白鹿原》中的现实主义的丰富性,使人们更深刻地感悟到现实主义永久的生命力。
三、人物形象:文化的、历史的与悲剧的
《白鹿原》人物众多,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复杂关系的人物谱系,这其中,白嘉轩、朱先生、田小娥、黑娃等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对于白嘉轩,人们给他贴上了各异的身份标签。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强者:“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个族
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9]“作者把他当作较为理想的农人典型,也把他当作一面可以澄影鉴形的‘镜子’”[12]。“这种封建精英人物长久地活在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陈忠实终于捕捉到了他”[2]。他“是一个来自历史文化深处的族长形象”,“这个人物凝聚了陈忠实的历史思考与文化选择”[13],道出了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的奥秘所在。也有不少论者看到了他同样是弱者,“他也有其孤独和无奈脆弱的一面,有他因人格面具过度膨胀而带来与集体相疏离的孤独感和离异感,以及人格面具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丑恶社会势力面前其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悲叹”[14],因而这个人物充满悲情,被定格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乡村遗老”。其实,强与弱原本并非绝然分明,所谓“柔弱胜刚强”也不足为奇。只是白嘉轩的这种强弱之间“竟然杂糅着那么丰富的道教文化因素,这恐怕是作者本人始料未及的罢”[15]。上述观点虽然有异,但也恰恰说明了白嘉轩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朱先生是一个难以被图像化的人物形象。有学者认为他“多智而近于妖”,具有“无处安放的智慧”,是“作者所塑造的关中学派的大儒”,但是“缺乏人间气和血肉之躯,他更像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的‘人化’,更接近于抽象的精神化身”[2]。也有学者认为,朱先生既是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位守望者、独行人,也是儒家礼教的终结者[16]。不过,南帆并不认为朱先生是一个人格神。他说:“朱先生形象的表明了一种文化的尴尬。”“朱先生半人半神的身份是文化尴尬的恰当隐喻:某些时候,儒家文化可能演示出现实主义情节,儒家文化烙印在许许多多日常细节之中;另一些时候,儒家文化已经退化为遥远的传说,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想象性虚构。”[7]对此,洪治纲并不赞同。他指出:“朱先生(包括白嘉轩)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化的存在。在他身上,折射了陈忠实对革命化境域中的中国历史的极为独特的思考——这种思考,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而是超越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僵化思维,自觉而又深刻地意识到了本土文明的演进,绝对离不开对民族精魂的重新激活,离不开对传统文化中某些重要品质的重铸于丰富。”“但他毕竟是一个旧儒风范,其骨子里又不免带着保守这固执的文化风貌,甚至是道家的自然主义质色。表现为既崇尚自然质朴又彪炳传统守旧的衣着装扮以及不为物役的思想,暗含了某种道家的人生境界。”[8]因此,“朱先生也并非‘醇儒’,他兼收并蓄了道教、佛家、原始巫鬼崇拜以及其他种种民间俗神的信仰,思想言行异常驳杂”[17]。也许,朱先生如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贯穿在作品当中,带着无可挽回的悲剧性。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最为重要的女性角色,也“是一个备受争议、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无疑值得谅解和同情的文学中罕见的复杂而浑然的女性人物形象”[17]。当然,“田小娥不是潘金莲式的人物,也不是常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的文化内涵相当错杂”。“这个‘尤物’‘淫妇’以仅有的性武器在白鹿原上报复着,反抗着,亵渎着,她是传统文化的弃儿,反过来又给这文化以极大的破坏”[2]。这种反抗主要体现在她的情爱观上,“她有力地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婚恋藩篱,带有一种还原性爱的娱情悦性的本色的意味”[12]。“本色”使这个形象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让她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从而区别于其他以传宗接代为生存价值的女性。而“田小娥的魅力来自女性内心深处自我的苏醒,来自她对真与善的执着”[18]。田小娥死后魂魄附于鹿三身上伸冤的情节,“使这个牺牲在封建礼教屠刀下的中国妇女的悲剧有了更加峻烈的性质”[19]。也许是受到被戏称作“田小娥传”的电影《白鹿原》的影响,有论者作出了这样的判断:“田小娥和《白鹿原》中任何一个人物都迥然不同。她恰似一面镜子,先后照见黑娃的善良与倔强,照见白嘉轩和鹿三基于儒家文化伦理‘女人祸水论’的偏激、愚昧与残忍,照见白孝文混合着真情的虚伪,照见鹿子霖灵魂和身体的邪恶与肮脏,照见早先利用小娥‘吃泡枣’和采阴补阳的‘武举’以及首肯此事的正房太太的丑陋与自私,照见她的穷秀才父亲的面子文化,某种程度上甚至也照见了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者面对这个不幸的女人时经常陷入的情感与价值判断的游移暧昧”[15]。因此,其重要性自然凸显出来。事实上,作家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暧昧态度显在其中,只不过理智与情感有时难以抉择,但这也正好反映了田小娥“复杂与浑然”的性格特征。
黑娃的形象有些另类,对于他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形象的意义,即他的悲剧性。无疑,黑娃身上有更浓重的悲剧色彩,“黑娃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种草莽英雄,也不是由农民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是宗法文化的牺牲品”。“黑娃的经历可谓极尽曲折,其文化意味更是引人深思。虽然他金刚怒目,敢做敢为,不愧顶天立地的好汉,虽然他国、共、匪、儒家信徒一身而四任,但他仍在长夜里摸索,他的困境实为我们民族的困境”[2]。也有论者看到了人性深处的东西,“他(黑娃)对传统
礼教的‘神性’又惧怕又向往,对“神圣”革命一片赤忱,对“反人性”的阴谋毫无预测,都归根于他本性的‘弱’”。“他的‘弱’代表着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和凝聚力,也代表其致命的脆弱”[20]。在“告别革命”的另一语境中,李扬指出:“黑娃的悲剧性故事,实际上也是后革命时代‘新儒家’所遭遇的精神困境:精神还在,却没有了可依附的物质——现代革命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让儒学精神成为一个幽灵——在全球资本主义重组了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无根漂浮的幽灵。”[21]于是,“黑娃向儒家传统的回归象征着传统文化心理的残余,而他的冤死象征着历史的未完成”[22]。二是黑娃身份不断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寓意。对于转换,有论者指出其前后转变似乎缺乏内在逻辑,“我不知道作者究竟是以赞赏的还是遗憾的心情在看黑娃的忏悔、修身,拜朱先生为师?在我看来,这除了证明传统文化的黑洞具有强大吸力之外,声泪俱下的黑娃呢喃‘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求祖宗宽容’,是颇有些滑稽的”[22]。之所以如此,或许与黑娃负载了过多的文化与历史之重,因而人性本身的复杂与丰富被遮蔽起来,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关。对于寓意,有学者认为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叙述人之所以不惜牺牲黑娃的性格发展逻辑,只是为了表达他的拯救民族命运的抱负:回归传统儒家文化似乎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2]。但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作家要展示的究竟是人的文化还是文化中的人?是人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人?这是耐人寻味的。
无论如何,《白鹿原》“成功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具有一种时代的、历史的概括力和艺术地阐释人生的深刻性,它是(足)以改变人们的一些旧观念、旧思想乃至旧的思维方式,让人们获得感受和理解历史与现实人生的新视野”[23](P1)。
四、比较视阈与视阈比较
《白鹿原》另具影响力的研究视角就是比较视野,大体而言,可分为两类:
第一,文学比较视阈,即《白鹿原》与其他中国当代小说相比有哪些贡献。在当代文学发展的链条上,王晓明认为从《白鹿原》看到了《古船》所开辟的“不再是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的道路在《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中得以延伸[24]。许子东则指出《白鹿原》“后设的历史叙述结构”,“是从《灵旗》《大年》对《红旗谱》革命历史故事叙述模式的破坏和颠覆发展过来的。如果没有‘寻根派’对乡俗土风的现代观照和‘后寻根派’对叙述方式的种种实验《白鹿原》出现是不可想像的”[25]。在与《红旗谱》的比较中,朱水涌认为“可以看到两个时代中国文学不同的创作风貌,进而去探讨当代历史叙事的变化及其精神结构的变动”[26]。在这一视阈的研究中,明显拓展了地域文学视阈中的比较。有论者将《白鹿原》与《秦腔》放在整个的乡土文学的历史中观照,发现“从《白》到《秦》体现出文化视角的转换,那就是由文化反思走向了文化凭吊。从这个意义上说,《秦》的问世,打开了乡土文学的新的视域,更具有史的意义”[27]。有论者认为“从《白鹿原》到《高兴》,从陈忠实到贾平凹,世纪的更替,生命的演绎,秦地农民的民生权叙事便有了历时性的递进观照,这就是说在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态中,这一新的描写触角不仅是秦地小说的,更是中国当下文学的本来走向”[28]。而以性别政之的视角透视陕西的地域文学,也会有所发现:“贾平凹为那些深陷在消费文化‘废都’里,而且被消费文化‘废掉’了政治话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说男性文化英雄量身打造了一个性神话;陈忠实在‘白鹿原’上为践行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人君子建造了一座性道德丰碑”,共同的是“其笔下的性叙述也透露着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29]。在比较中,凸显出作家们文化心理的同源性。
第二,比较文学视阈,即与西方文学作品的比较。在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比较中,论者更多地发现了两部作品在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方面的共同特征[30]。在与《静静的顿河》的比较中,李建军认为,在大量的世界文学巨著中,《白鹿原》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如“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对民族苦难的深切体察和难以释怀的忧患”[31]等诸多有更多的契合点,他还以其中的非情节因素之一的景物描写为切入点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作品的精神风貌反映着作家的人格状况和心理结构”,陈忠实大体属于理智—情感型(所谓“理胜于情”)的作家,肖洛霍夫则属于情感—理智型(所谓“情胜于理”)的作家。在与帕斯捷尔帕克的《日瓦戈医生》等文本的比较中,从主题到象征都可以见出其中的异同。在主题方面,“这两部作品的主题都在彰显一种富有理性色彩的战争观,都注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反思暴力及种种类似的坏的冲动;所不同的是,《白鹿原》的价
值基准是儒家的伦理观念,而《日瓦戈医生》所依本的则是具有基督教色彩和个性主义倾向的伦理观念”[32]。在象征手法方面,“《白鹿原》与《日瓦戈医生》在对某些象征形象的选择,对人物象征意味的注重以及对严整的两极对照的象喻体系的营构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或共同倾向;而在景物象征、表达象征的构语模式和文体形式上,则显示出迥异的风貌”[33]。此外,研究者在与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霍桑的《红字》等不同方面的比较中,同样感受到了《白鹿原》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当代长篇小说与西方文学的内在联结,印证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朴素的道理。
五、问题与思考
《白鹿原》研究22年来,在文本主题研究方面,由前期的文化历史反思到后来的人性救赎,主题解读趋于多义;在创作手法方面,由现实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吸纳到神奇、神秘、魔幻质素的汇入,使人们更深刻地感悟到现实主义永久的生命力;在人物形象解读方面,主要人物文化的、历史的、悲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得到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解读;比较视阈一方面将其置于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链条中,由此探寻1990年代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东西文学的坐标系内发掘《白鹿原》所蕴含的世界意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白鹿原》研究的实绩与进展,为后来者提供了继续前行的支点。当然,这绝不是说《白鹿原》研究已达到了顶峰,相反,在研究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问题一:文本主题的当下意义。《白鹿原》的主题研究已经摆脱了文化历史反思的单一向度,而趋于多义,但目前的许多研究者却将文本研究引向了社会问题研究,即《白鹿原》中所表达的传统儒家文化是否可以解决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儒家文化如何存在于现代社会?儒家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新的现实进行有效的对话?这无疑将文学研究引向了另途。《白鹿原》是小说,不是历史文化读本,更不是教科书,它不具备给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提供方向性的指导功能。一味地扭转《白鹿原》的研究路径,只能将《白鹿原》的研究引向死胡同。
问题二:现实主义、历史真实、新历史主义。《白鹿原》中所使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内涵,拓新了研究者对现实主义的定义与认识。当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大潮”消退之后,新历史主义文学时潮应运而生。“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思潮悄悄地改变了运行方向,人们由热衷于由揭示历史规律的功利性书写转向对某些偶然性、寓言性历史认知的叙述;由善于历时性历史进程的完整把握,转向用人性、文化等元素来完成对历史的共时性写作。”[34]《白鹿原》正是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共时性写作。但有的论者以历史考证的方式“试图从《白鹿原》中涉及的部分地名、人物、事件、传说、方言民俗的探讨中,用历史的真实突现《白鹿原》的思想艺术价值”[35],这不能不说又落入到索隐派的窠臼之中。当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被置换成为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之后,如何以现实主义的丰富性打开历史,通过文学细节发掘文本的复杂性、丰富性与深刻性,而非简单地对应于历史真实,是一些研究者亟待思考的研究问题。何况历史本身无法被定于一尊。
问题三:作家立场与人物逻辑。众所周知,陈忠实是抱着“画出民族的灵魂”的雄心写作《白鹿原》的,小说也确有一种“白鹿精魂”象征中华传统文化,以之为立场创造出笔下的人物,也使人物负载了厚重的文化意义。但有论者抓住小说中朱先生让鹿兆海在战斗中收集鬼子头发后焚烧的细节,指责陈忠实为“狭隘民族主义”[36](P2),这显然混同了作家立场与人物逻辑间的复杂关系。同样,将“女性一边永远地被排挤在历史的边缘地带,一边却被献祭在祠堂里,作为‘他者’被任意损害着”[37],归因于作家对女性人物的冷漠,也走入了相同的误区。
《白鹿原》是20世纪90年代涌现的一部杰作,必将汇入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对于这样一部经典性作品,目前的阐释无论是视角还是观点都远远没有达到人们对它的期望,更没有达到视界的顶点。我们总结22年来《白鹿原》研究的成果与问题,就在于我们对它充满期待,充满着继往开来,不断拓新的期待。
[1]何西来.关于《白鹿原》及其评论——评〈白鹿原〉评论集[J].小说评论,2000(5).
[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J].文学评论,1993(6).
[3]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阐释和留连[J].小说评论,1995(1).
[4]文斌,佘向军.鏊子·白鹿·砖塔[J].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1).
[5]郑万鹏.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1).
[6]赵录旺.《白鹿原》写作中的文化叙事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7]南帆.文化的尴尬——重读《白鹿原》[J].文艺理论研究,2005(2).
[8]洪治纲.民族精魂的现代思考[J].南方文坛,2007(2).
[9]李星.世纪末的回眸[N].文学报,1993-05-20.
[10]段建军.一部神奇现实主义大作——再谈《白鹿原》的审美魅力[J].小说评论,2000(3).
[11]程光炜.陕西人的地方志和白鹿原[J].文艺研究,2014(8).
[12]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J].当代作家评论,1993(4).
[13]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J].小说评论,1993(4).
[14]王渭清.《白鹿原》人物形象的人格治疗学意义探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
[15]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J].文学评论,2015(2).
[16]陈思广.论白鹿原的思想之本与立意内涵[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1).
[17]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J].文学评论,2015(2).
[18]申霞艳.乡土中国与现代性[J].南方文坛,2013(2).
[19]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J].文学评论,1998(3).
[20]盐旗伸一郎.站在“鸡卵”一侧的文学——今读《白鹿原》[J].小说评论,2011(2).
[21]李扬.《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J].文学评论,2013(2).
[22]王小平.论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白鹿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4).
[23]袁盛勇.回归传统的平庸[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1).
[24]畅广元.《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J].小说评论,1998(1).
[25]王晓明,等.《古船》的道路——漫谈《古船》《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J].当代作家评论,1994(2).
[26]许子东.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论《红旗谱》《灵旗》《大年》和《白鹿原》[J].上海文学,1994(10).
[27]朱水涌.《红旗谱》《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J].小说评论,1998(4).
[28]王世杰.乡土小说人文性向现实性的转变——《白鹿原》与《秦腔》之比较[J].西北师大学报,2008(6).
[29]冯肖华.秦地小说民生权的深度叙事——《白鹿原》《高兴》之史线透视[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5).
[30]刘传霞.论《废都》《白鹿原》性叙述中的性别政治[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2).
[31]乔美丽.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和《白鹿原》[J].殷都学刊,1995(4).
[32]李建军.景物描写:《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之比较[J].小说评论,1996(4).
[33]李建军.主题:《白鹿原》与《日瓦戈医生》之比较[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4).
[34]李建军.论《白鹿原》与《日瓦戈医生》中的象征[J].唐都学刊,1998(1).
[35]刘东方.也说新历史主义[N].中国文化报,2006-01-18.
[36]卞寿堂.《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7]惠西平.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它[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戴庆瑄]
宋海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讲师;陈思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610065
I206.7
A
1004-4434(2016)10-0113-06
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专项“《白鹿原》与关中文化研究”(14Jk1441);西安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项目“接受视域中的《白鹿原》研究”(2014SY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