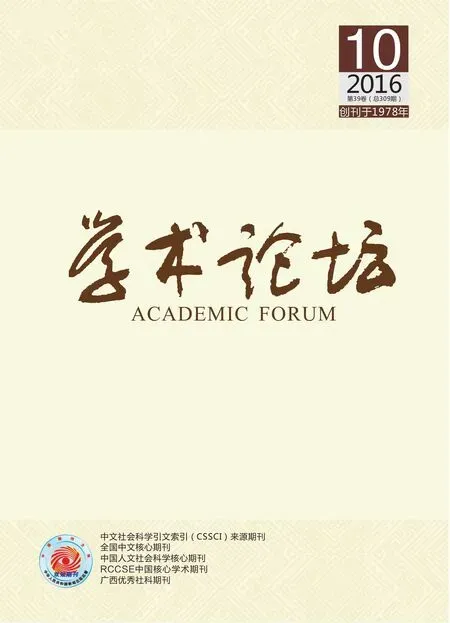时间、空间与文学北京
——论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
吴雪丽
时间、空间与文学北京
——论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
吴雪丽
在作为一种文学书写与文学想象的“北京叙事”中,时间和空间的位置影响着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中,那些都市北京的“外来者”“边缘者”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流转中努力重构自我的身份认知,在“边缘”与“中心”的空间位移中不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重新定义了“城”与“人”之间的关系,丰富和拓展了以往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徐则臣小说;时间;空间;文学北京
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版图上,“北京”是少数几个建构了自己的文学形象的城市,提及作为一种文学书写与文学想象的“北京叙事”,老舍、陈建功、刘心武、王朔、邱华栋、铁凝等都在其列。时间和空间的位置影响着作家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借助于“北京”这个参照体系,不同的作家构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景观,同时也在定义着人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中,那些都市的“外来者”与“边缘者”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交错中试图重构自我的身份认知,在“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区隔中倔强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重构了文学北京中“城”与“人”的关系,丰富和拓展了以往的北京书写与北京想象。
一、时间流转:过去和现在交错
以赛亚·伯林在论及“现实感”时曾说:“对过去岁月的浪漫渴望,实质上是一种取消事件‘无情的’逻辑性的欲望。一旦可能重现过去的情形,历史的因果关系就会被打破;而我们又不可能不用因果律来思考,所以这不仅在心理上令人难以接受,而且是非理性的可笑的。”[1](P5)那么,我们如何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流转中重建我们的“现实感”,如何在不打破历史的因果关系的意义上定义“现在”?徐则臣的北京系列小说在过去与现在、乡村与都市、历史与未来等问题上提供了关于这一向度的可能思考。在他的小说中,“京漂”“异乡人”“边缘者”的生命经验与个人际遇,往往指称着那些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镇到大都市、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流转与空间位移,并在时空转换中重新定义“现在”与自我。
这些漂在北京的人几乎都有一个“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的时间焦虑与身份犹疑。《啊,北京》中的边红旗曾经是江南小镇上的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从江南小镇到都市北京的空间位移背后,始终伴随着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的缠绕。边红旗虽然在表面上很轻易地跨越了这种身份漂移可能带来的焦虑,刚来北京时,他想找一个和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相关的工作,“找个记者、编辑之类的活儿干干总还是可以的”,可是却处处碰壁,最后不得已蹬起了三轮车,即使这样,边红旗依然是快乐的、豪情万丈的,甚至这段时间“在他秘不示人的诗歌生涯中,这是一个创作的高峰”。尽管在三轮车被警察扣了后转行卖假证,边红旗也没有气馁,在他看来,要生存,要在北京活下去,首先意味着放弃那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而“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的真正交锋出现在对边红旗至关重要的情感选择上,和沈丹在一起,意味着可以
在北京扎根,可以拥有“北京人”的身份。但是面对温柔贤惠的边嫂、以及和他的江南小镇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的生活,边红旗不仅难以割舍而且经历着良心与道德的拷问。虽然他那么得热爱北京,那么想成为一个可以融入这座城市的“北京人”,可他怎么都说不出“离婚”这两个字。江南小镇和边嫂不仅是过去温情的、安宁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那是边红旗灵魂与心灵的“过去”,是在时间的链条上指向过往的自我的情感选择,他无法与过去的自己决裂,也无法和过去的生活决裂,虽然未来指向他自己的梦想和自我期许。斯图亚特·霍尔在论及人们的身份认同时,认为“文化身份既是‘存在’,也是一种‘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中”[2](P211)。身份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是有源头和历史的,而边红旗如何重新在这个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必然地携带了他的“过去”,当然,这也是徐则臣小说带给我们的安慰:欲望都市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但未曾完全吞噬人们的灵魂与良知。
《我们在北京相遇》中的沙袖,在香野地是一个优秀的幼儿园老师,是一个自信、热情的姑娘,可是跟随未婚夫一明来到北京后却陷入了深深的空虚和失落中,因为在北京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语言”这个根深蒂固的、和我们每个人的“来处”密切相关的关于“过去”的标签几乎摧毁了沙袖所有的尊严与自信。去菜场买菜,卖菜的大妈听她不是北京人就提价,好不容易找了个书店店员的活,可因为一口东北普通话被人嘲弄。属于过去的一切是真实的、温暖的,但当“过去”与“现在”相遇却是猝不及防地令人心碎。在属于过去的岁月里,沙袖不仅有踏实的存在感,而且可以把握自己的情感,她对自己有信心。可是在北京,在她义无反顾地远离“过去”选择和一明来北京,她变得如此的虚弱,唯有以身体这一自己可以感知的“现在”的存在感的物质性存在反抗“虚无”,只是“身体”不仅不能拯救灵魂,而且会陷入更为黑暗的深渊。在小说的最后,可以挽救“身体”出轨伤痛的依然是属于一明和沙袖共同的“过去”,是他们共同成长的故土与少年岁月。一明不辞而别回到了香野地,在香野地一明选择了宽容、承担与爱,这是“过去”对“现在”的拯救,是“历史”对“现实”的胜利,是“乡村”对“都市”的宽宥。或许可以说,这些小人物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身份漂移与情感重建,也是我们人类的“过去”与“现在”的相遇,“过去”属于乡村,这个“乡村”不是启蒙现代性视野下的蒙昧、麻木、亟待被启蒙的乡村,而是那个遥远的、温暖的、淳朴的、可以安放人的灵魂的田园牧歌,是我们人类的“童年”,是我们任何时候可资回望、伤怀并提供抚慰的“过去”。实际上,这种有关“过去”的“黄金时代”的讲述不啻是一种神话,它铭记、怀念、重建那个遥远的、联系着我们来处的“过去”,也隐喻了对“现在”的改变的恐慌与抗拒。
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的“外来者”“异乡人”中,大多是边红旗、沙袖这样的从乡村或者小镇来到北京的小人物,《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敦煌和保定,《伪证制造者》中的姑父和路玉离,《三人行》中的佳丽和小号,《天上人间》中的周子平和子午,《把脸拉下》中的微千万等,都有一个关于“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的纠葛,“过去”联系着时间逻辑上“前现代”的那些纯真、善良、古朴的品质,他们的“来处”很多时候也规定了他们的“去处”,这是徐则臣都市小说的温暖与朴素。子午越过了这条底线,为了在都市立足以恶抗恶,在幸福来临的最后时刻丢掉了生命。徐则臣说:“我倒觉得边红旗们并非一味要寻找一个新的身份,而是努力在搞清楚过去的身份,以及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城市里如何自处。在陌生却又熟悉的城市,他们身份意识才开始凸显,他们更想知道自己是谁,而不是自己可能是谁。尽管都要求一个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但他们可能更多的心思在‘来路’上,而非‘去路’。”[3]正是这样一个“来路”,他们在“现在”作出了不同于都市欲望与贪念的选择。《跑步穿过中关村》中敦煌卖盗版碟都选“质量”好的,先在自己的破影碟机里试一下。《把脸拉下》中的魏千万,在警察来抓时承认自己是假古董的主人,而《天上人间》中的周子平始终强调卖假证的“职业道德”。徐则臣小说中的这些“边缘人”不是英雄,他们灰暗甚至卑微,但也古朴、仗义,在冷硬的现实中互相温暖,这使徐则臣的小说虽然书写“底层”但却没有“底层书写”的悲伤与绝望。
在徐则臣的“京漂”人物谱系中,那些办假证的、倒卖光盘的几乎都来自遥远的不知名的乡村、小城镇,而唯有《浮世绘》中的王琦瑶是个来自上海的姑娘,为了自我发展也为了“寻根”而来。她是前清的贵族后裔,在“北京”的寻梦之旅(成为一个名演员)伴随着对过往的“格格”历史的确认与寻找,“寻根”之梦联系着前朝繁华也联系着她对爷爷“成功者”的想象。这个从上海来的王琦瑶也许是对王
安忆的致敬,也许是戏仿与解构,因为那个在《长恨歌》中和上海这座城市水乳交融的王琦瑶来到北京后,发现她的美貌和“格格”的身份指认是唯一的通行证,而这个“格格”也被欲望时代所收编,她在不同的男人身边漂移,以身体换取物质的丰裕和演艺事业发展的可能,而王琦瑶最后对男人世界的失望不过是期望离开男人来到天上人间“自食其力”,这一看似决绝的反抗不过是一次更深的陷落。在小说的最后,那个想象中的作为富豪的爷爷被找到了,却是一个落魄的、贫穷的、行动不便的老人,王琦瑶的“寻根”、在都市北京寻找自我价值的追梦之旅相继破灭,在这个已充分资本化、权力化的都市空间中,“过去”既不能安放漂泊的灵魂,也不能建构出新的“身份”认知,指认繁华旧梦的“过去”在欲望都市的“现在时”只能风吹云散。
雷蒙·威廉斯曾经说:“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我们或许最好按照这种分裂和冲突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它。”[4](P402)应该说,徐则臣并不缺乏现实态度,他小说中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身份漂移与时间流转的书写呈现的正是这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说到底,边红旗、沙袖、王琦瑶们都有他们的“过去”,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他们的“现在”,时间流转中的“过去”与“现在”相遇的伤痛,是沙袖、边红旗,王琦瑶们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正是徐则臣北京书写的厚度。
二、空间区隔:在中心与边缘之间
徐则臣的“京漂”小说不仅讲述了那些京城的“边缘者”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时间焦虑和身份犹疑,更重要的是,之所以把徐则臣称之为写“北京”作家,因为他小说所构建的“北京”想象,以及与此相关的“北京”作为都市空间生产出的边缘者、底层等社会空间与权力政治。徐则臣的北京不是老舍笔下那些古朴、封闭的四合院,不是铁凝笔下仁义的胡同文化,也不是王朔笔下有某种身份象征的部队大院。徐则臣的“北京”集中于海淀、中关村、知春里一带,这里是中国的精英院校北大、清华、人大等所在地,是IT人才聚集的地方,但徐则臣小说中贩卖假证的、卖盗版光碟的都不属于这些“中心”,他们是边缘者,那些高大气派的写字楼、繁华热闹的商场和他们无关,双安商场、时代大厦等这些现代都市空间只是作为流动的工作地点出现的,属于他们的是破旧的小平房、简陋的地下室或者逼仄的单元楼,甚至于无家可归时在大街上的流浪与漫游。他们在这样的一些被分割的、边缘性的空间中寄居,在丛林般的都市中挣扎着谋生,扭曲而坚韧地寻找可能属于自己的阳光与空气。
福柯曾经说过:“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时代,这是远近的时代、比肩的时代、星罗散布的时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或者我们可以说:特定意识形态的冲突,推动了当前时间之虔诚继承者与被空间决定之居民的两极化对峙。”[5]因此,“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于时间的关系更甚”[5]。在徐则臣那里,这种对北京的“空间”焦虑是那些都市外来者猝不及防的生命经验,“北京”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故乡的都市空间,在《啊,北京》中,初到北京的边红旗“就是觉得北京好,他经常站在北京的立交桥上看下面永远也停不下来的马路,好,真好,每次都有作诗的欲望,但总是作不完整,第一句无一例外都是腻歪得让人汗毛倒竖地喊叫:啊,北京!”[5]可是,在丢了赖以谋生的三轮车后,边红旗突然觉得:“它是他和北京的大地发生联系的唯一中介,现在没有了,他觉得脚底下空了,整个人悬浮在了北京的半空里,上不能顶天,下不能立地。唯一能和北京发生关系的凭证丢了,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我们在北京相遇》中沙袖在北京经常迷路:“这里不同于香野地,那里是平面的,站在哪里都明白自己的位置;北京是立体的,陷在高楼之间,连影子都找不到。”这让沙袖恐惧,在北京,她完全失去了在香野地的坚强和自信。他们都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个体精神空间对个人的认知和在社会空间中被建构、被规划的、被生产的身份归属产生了巨大的分裂,那不仅是“过去”的自我与“现在”的自我的冲突,更是那个属于江南小镇、香野地的想象中温暖、安宁的乡土空间与喧嚣的、欲望的都市空间的冲突,这种在新的生存空间中“位置”的缺失,让他们惶恐而茫然。
在这个被资本、知识、权力逻辑所建构的都市空间中,边红旗们是“外来者”“边缘者”,这种被定义本身就隐喻了这样一种身份和空间逻辑:他们不属于这座城市,不管是身处繁华还是落寞,他们都
被定义为“他者”,这一空间的身份区隔不仅是简陋的小平房、地下室与高楼大厦的空间对峙,更是“外来者”与“北京人”的属于不同的地理空间的身份指认。“对特性的定义,是根据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根据我们是谁。这正是地理学的切入点,因为这里的‘我们’和‘他们’常常是以地域来划分界限的……空间对于定义‘其他’群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被称作‘他者化’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特性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了起来。”[6](P78)虽然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出现的“北京人”都不是精英与显贵者,沈丹、闻敬是超市收银员、疗养院的服务员,但因为是“北京人”,她们可以以户口、住房等这些抽象或具体的“物”指认自我的身份,可这些外来者除了作为物质的身体几乎一无所有,《跑步穿过中关村》中,敦煌在丢掉自行车后以奔跑这样的方式丈量着他在都市北京的空间位置,从北大西门、太平洋电脑城、中关村大街到北四环、知春里,通过奔跑这一属于自己的可支配的身体,暂时超越了现代都市碎片化的空间分割,从身体时间对物质空间的支配中得到了短暂的愉悦。
“进入都市的权力,意味着建立或者重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一种取代了分割的联合体。”[7](P14)边红旗从江南小镇来到北京,正是试图跨越这种空间的区隔所产生的未曾实现自我价值的“自我”而来到北京,正如列斐伏尔所说,进入都市,“并没有消除对抗和斗争,而是相反”[7](P14),因为这个主体在空间的位移中并未获得“主体性”,未能确立自己的内在性,不能找到“安全与幸福”。边红旗因为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希望在北京能够重建自己的自我认知,但从来到北京的那一刻,从踏上北京冰凉的水泥地,心中高涨的热情因为求职的屡屡失败而最后走向了办假证这一非法的谋生方式,“北京”以如此冰冷、高傲的姿态轻易地打败了“寻梦”的边红旗。他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却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条件,这种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的断裂,一方面是知识和政治权力对边红旗这样的小人物的拒绝,另一方面也来自于时空的区隔,即一个江南小镇和首都北京的遥远的、无法跨越的时空距离。“在社会历史中,重建那些已经被分割、解体和离散的一切,还是很遥远的事情。”[7](P14)在《啊,北京》中边红旗在北京经历了事业的失败、爱情的失败,最后当边嫂把身陷囹圄的边红旗领出来时,那个虚弱的、恍惚的、茫然的牵着妻子衣角的边红旗不过再次确认了这种空间跨越与自我重构的艰难:“边红旗其实还是属于苏北的那个小镇的,那里有他的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他的家,有永远也不会放弃他的生活,那些东西,应该才是最终能让他心安的东西。”
在《天上人间》中,办假证的周子平感慨:“和别人一样,此刻我和子午也生活在繁华的生活里。在其他时间里,我们刻意地接近或躲着大家,那是有预谋的,和你一样,我们也想从这个世界里得到一点东西。我们一直在某个小小的角落潜伏着,即使淹没在人群里,内心里也知道自己十分醒目,就像一枚枚企图楔入正常生活的生锈的钉子。”可见,这种“繁华的生活”,“这个世界”不是“外来者”周子平和子午的,他们努力像“一枚枚生锈的钉子”要嵌入都市北京、嵌入“别人”的生活里,但是“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就像其它事物一般,空间是种历史的产物”[8](P62)。这种历史和现实所产生的“空间区隔”与身份政治却不是这些北京的“外来者”所能够跨越的,边红旗、敦煌、沙袖、周子平、小号、佳丽都失败了,子午几乎就要通过婚姻这条路成功了却死于非命,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些“边缘者”试图跨越历史裂隙、空间权力、身份政治的悲剧性处境。
北京作为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都市空间,始终生产着关于精英者、权贵者、外来者的诸多权力空间与社会关系,但属于边红旗、敦煌们的只是身处“边缘”的生命经验,在这个空间分裂的时代里,他们只能互相温暖而不能互相拯救。属于这些“边缘者”的空间是异质的,或者说,他们生活在一个不能安置个体的身体与精神的空间中,“城市的组织原则是自然权利而非生有权,所以个人会被其感召,去追求更高的自我感,去寻求个人的命运”[9](P285)。他们被梦想召唤,期待在都市北京追求“更高的自我感”,但属于他们的命运依然是难以跨越的空间区隔与身份政治。
三、“城”与“人”:别一种北京想象
“把城市当作文本来考察”,“将城市文本化,既创造出自己的现实,也成为看待城市的一种方式”[9](P383)。那么,文学书写创造出怎样一个文本“北京”?而“北京”作为城市文本是被什么样的“他者”建构?这其中隐喻了怎样的“城”与“人”的关系?徐则臣的小说为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北京想象的路径,在他的文本北京,“人”与“城”的关系亲密又疏离,其中既有时间上的“过去”与“现在”的纠葛,也有空间视野下的“边
缘”与“中心”的区隔,在这样的时空流转与错置中,“人”与“城”演绎着“边缘者”与“新北京”的新故事、新传说。
赵园曾在《北京:城与人》用“乡土”概括北京的“传统性”:“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属于共同文化经验、共同文化感情的世界。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它对于标志‘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和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的丰富性。”[10](P5)“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感性化、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它是属于昨天、今天、明天的城,永远的城。”[10](P6)因此,在作为“乡土中国”意义上的北京书写中,“城”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即使老舍笔下的“外来者”祥子那样的挣扎着生存,北京仍然是他最为亲近的故园。这样的书写从现代文学中的老舍、郁达夫、林语堂到当代的刘心武、陈建功、铁凝等一脉相承。而同样是书写作为现代都市意义上的“外来者”,在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中,那些“外来者”如杨哭大多是知识分子与高级白领,他们带着雄心与梦想妄想征服这座城市,北京在邱华栋那里是欲望之都、声色犬马之都,是全球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一“城”与“人”的书写脉络上,徐则臣提供了不同的北京书写与北京想象。正是徐则臣小说中的边红旗、敦煌、小号、佳丽、夏晓蓉等这些在空间和身份上都处于边缘的都市“他者”发现了北京的另一张面孔,使这座城市获得了再度被辨识的机缘。北京作为一个亲切又异质的城市空间,联系着他们的首都想象与现实生存的背离与矛盾,边红旗、敦煌们要努力表达的自我认同并不是“我们”的北京,而是“我们”试图镶嵌进“他们”的北京,以首都北京来“提升”自己的个人认同,故乡、家园已是遥远的过去,而当下的都市经验又充满了风险、挣扎甚至内心的孤寂、茫然。
徐则臣的小说“北京”首先是那些“外来者”基于北京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物,是一代人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教育中构建的心灵图景。在《啊,北京》中,边红旗觉得“到了北京我真觉得闯进了世界的大生活里头了。……我感觉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占据的那个点了,别人可能看不见我的那个点,可我自己看见了”。在《三人行》中,对于漂在北京的小号和佳丽来说:“在很多时候盘旋在内心和理想里的,并不是什么美好的生活,而是‘北京’这个地名。首都,中国的中心、心脏,成就事业的最好去处,好像呆在这里就是待在了所有地方的最高处,待在了这里一切都有了可能。”北京在这些边缘者心目中是梦想之都,也是希望之都。但是,北京却不是他们的北京,作为地标意义的天安门、中南海离他们是如此遥远,甚至于安稳的日常生活都不能得到。当想象的图景与现实的北京相遇,边嫂(《啊,北京》)站在天安门广场前,突然就哭了:“这就是天安门?”“怎么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大?”从想象到现实,这些“外来者”的北京想象经历了震惊与重建。
作为都市空间的北京,在刘心武、陈建功、邓友梅等的北京书写中,所构建的是关于“老北京”的文化乡愁,这个文化地形图的标识是胡同、四合院、大宅门,重在对北京的知识考古与文化想象。在邱华栋那里是关于“新北京”的资本、欲望书写,这个文化地形图的标识是国际饭店、凯莱大酒店、国际大厦、赛特购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等冒险家的“乐园”,是一个要征服都市的野心家的异化空间。但在徐则臣那里,北京是双安商场的门口、人大东门的天桥、北大南门、中关村大厦等,这些都市空间既不负载文化意义也不指认现实欲望,这些显赫的地标并不能安放徐则臣小说中的“人”,他们随时面临着被抓捕的命运,属于他们的北京,是光鲜、繁华的白天退去后夜晚的北京,是海淀简陋的出租屋里的孤单与寂寞。福柯在讨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时曾经指出:“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从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间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5](P21)在徐则臣的小说中,这种关系是乡村与都市的距离,是外来者与在地者的距离,是底层与精英的距离。在这座想象之城与希望之城中,边红旗、敦煌们是精英、白领、权力等构建的社会关系中的底层人与边缘者,这座城市接受了他们但拒绝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北京似乎提供了改变生活的可能性,但规则、边界往往也限制了改变生活的可能性。换言之,徐则臣小说中的“城”与“人”既亲和又背离,是火热的生活与渺小的自我的分裂,是白天与黑夜的交错,是希望与失望的轮回。
在徐则臣的都市北京讨生活的是敦煌、边红旗、姑父、小号这样一些怀揣着梦想的都市“边缘者”,“生存”而不是“发财”是他们生活中的关键词,办假证、卖盗版碟的生存方式与在出租屋、监狱之
间空间流转的生命际遇,使他们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觊觎,他们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因此他们不负载太多的文化记忆,也没有试图征服这座城市的雄心壮志,他们踏实、本分、朴素、坚定,为了更好的活着而努力,有挣扎而无异化,他们身上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保留着古朴、温暖的乡土伦理与道德,即使遭遇生活的变故,依然坚韧、乐观,并享受着普通人可能有的短暂的快乐。徐则臣说:“在某种意义可以说,他们是这个社会旁逸斜出的那一部分,歪歪扭扭地一边独自成长。”“我写他们,也包括我自己,与简单的是非、善恶判断无关。我感兴趣的是他们身上的那种没有被规训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那种逐渐被我们忽略乃至遗忘的‘野’的东西。”[11]而这种未被规训和秩序化的蓬勃的生命力,使徐则臣的小说写底层却没有底层文学的悲愤与绝望。而且,这些小人物的精神追求、心灵际遇与他们的现实生存状态构成的张力,也为广为诟病的“底层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敦煌(《跑步穿过中关村》)从看守所出来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可他既没绝望也没自暴自弃,依然努力寻找新生活的可能。周子平和端午在夜晚的北京吃顿水煮鱼,也觉得生活很温暖、很美好。边红旗兼具两种身份:作为民间诗人的边塞和作为假证制作者的边红旗,厨师小号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诗人班禅,在他们哪里,现实的沉重与精神的飞翔同在,挣扎着活得更好的世俗愿望与超越肉身的心灵追求同在,职业的晦暗仓皇与精神的正大光明同在。
周蕾在《从乡愁里的“故园”到冒险家的“乐园”》一文中说:“当写作者带着不同的历史记忆、文化诉求与个人体验,去书写和想象各自的‘北京’,最终呈现的并不是一个达成共识的形象体,而是一组分化各异的形象群。”在这一“形象群”中,徐则臣的“新北京”白天的繁华背后那些隐匿的角落得以呈现,夜晚的霓虹闪烁背后那些流浪漂泊者的面容闪过,但这些北京的“边缘者”人群挣扎着去爱、去追寻、坚韧顽强地生活着,他们被空间区隔,他们身处随时可能被抛入的困境,但又向着未知的未来与可能再次出发。当然,这一北京想象还携带着重要的问题:作家徐则臣的位置在哪里?他何以如此呈现这座“城”里的“人”?布尔迪厄认为:“建构了社会空间之后,我们知道这些观点(其字面意义是站在特定地点的观看),是源自社会空间中的某个确定位置。我们也知道,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敌对的观点出现,因为视点乃视其所采取的观看地点而定,行为者对这个空间的看法,乃是根植于他在空间中的位置。”[12](P300)正是居于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北京想象”,不管那个作家穆鱼、那个大学毕业后的记者背后有没有徐则臣的个人经验,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选择了和“他们”在一起,他是以平视的目光注视着他的朋友、兄弟、亲人、邻居,虽然满怀忧虑,但目光温暖、平和。
迈克·克朗在论及20世纪时间的加速引出的文本危机时说:“文学作品对空间和时间的处理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城市的地理空间开始碎片化,随着城市生活的节奏加快,时间似乎也在加速,人们感到了20世纪的来临。在19世纪,主要的小说文体是叙述性的描写,但在20世纪出现了新的形式。(如《追忆似水年华》、意识流小说等)……这样的文学作品在揭示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给人们带来了理解世界和进行写作的困难。”[6](P71)而对于当代文坛中的城市书写来说,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碎片化也带来了城市写作的困难,以至于长期以来,城市书写中经验的匮乏使城市文学大多陷于对既有的文学传统的借用与复制,如欲望书写对“海派”传统的继承,“故园”想象对“京派”传统的回应,底层文学对左翼传统的延续等,徐则臣的北京系列小说的意义在于,他尝试在时间流转、空间位移中重构“城”与“人”的复杂性,提供别一种想象与可能。
[1]以赛亚·伯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钢,刘向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徐则臣,姜广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和叙事资源[J].西湖,2012(12).
[4]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A].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A].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徐则臣.自序[A].跑步穿过中关村[C].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2]皮埃尔·布尔迪厄.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A].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戴庆瑄]
吴雪丽,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四川 成都 610041
I206.7
A
1004-4434(2016)10-0107-06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城市文学审美的历史演变”(13YJA751030);西南民族大学学位点建设项目中国语言文学硕士一级学科(2016XWD-S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