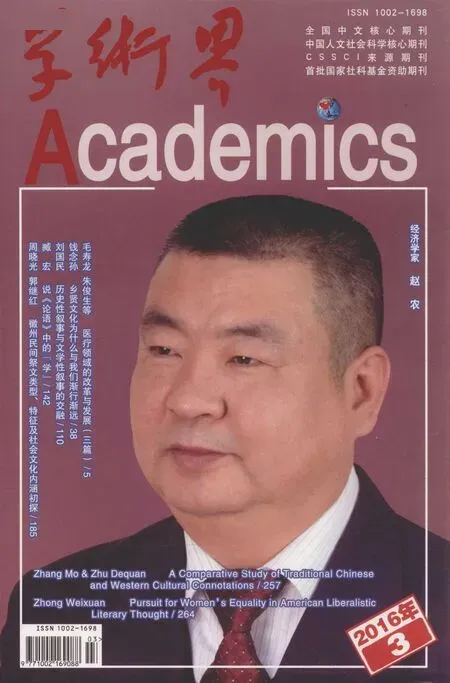说《论语》中的“学”
○ 臧 宏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学者专论·
说《论语》中的“学”
○臧宏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安徽芜湖241000)
本文对《论语》的主要篇章中的“学”字,作了独特的诠释,主要是讲这个“学”字,在孔子那里,虽然包含有学知识、 学文化、学道德的意思在内,但根本之点不在于此。学“明明德”、学“知天命”,即学“觉悟”、学“智慧”才是它的主旨。文章分六个部分:(一)“学”与“君子”;(二)“学”与“知”;(三)“学”与“乐”;(四)“学”与“思”;(五)“学”与“为己”“为人”;(六)结语。这六个部分,都是为了说明学“智慧”、学“觉悟”这个主旨的。其中“结语”对“学”与“觉悟”以及“价值观”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论语》;学;智慧;觉悟;价值
《论语》中有近40处讲到“学”字,其中大多数出自孔子之口,只有少数是孔子弟子说的,而且说的与孔子有异。所以,本文只讲孔子说的“学”。孔子说的“学”,虽然包括今日的“学文化”“学知识”“学道德”,但都不是根本的,根本之“学”,还是人之“学”于“天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智慧”、学“觉悟”。所以,本文的重点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孔子说的“学”字,多与“君子”“知”“乐”“思”“忠”“礼”“义”“信”“道”“为己”“为人”等词字相连。讲清了“学”与这些字词的关系,也就基本弄清了《论语》中“学”字的本义。
一、“学”与“君子”
《论语》中有不少章将“学”与“君子”联系在一起。这里仅讲两章。先看《学而》篇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其原文是: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一章共分三段。第一段是:“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杨伯峻注这里的“君子”说:“君子——这一词一直贯串到末尾,因此译文将这两字作一停顿。”〔1〕此注有理。但他把这一段译为“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读书,所学的也不会巩固。”则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不庄重”“没有威严”和“读书所学的也不会巩固”,是没有内在联系的。杨的译文和多数注家相雷同。唯有明代僧人藕益的注,别开生面,令人读后茅塞顿开。他在《藕益大师全集·四书藕益解·论语点睛补注上》中说:“期心于大圣大贤,名为自重。戒慎恐惧,名为威。始觉之功,有进无退,名为学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自重的人,就是一个立志作圣贤的人,用心之时,要特别戒慎恐惧,不然其明明德的修炼就不会牢靠。”我认为,藕益的解释比较接近孔子的本意。首先,他释“重”字为“自重”,并以“立志作圣贤”解释之,这就与《学而》篇的第7章的“贤贤易色”句接续上了,并且进了一层,不仅看到贤人便肃然起敬,而且立志要作“大圣大贤”。其次,他将“威”字解释为“戒慎恐惧”,不仅有文字学上的根据——“威”通“畏”,《诗经》毛传:“威,畏。”而且是儒家乃至儒、道、佛三家的共识,因为要“明明德”,要成圣成佛,就要用戒慎的方法去排除各种“私欲”“妄念”的干扰。再次,他将“学”释为“明明德”之学,其主要根据,在《大学》是《大学》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本章的第二段是:“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有了前一段的解释,这一段也就容易理解了。既然立下了作“圣贤”之“志”,那“主忠信”就不是外在地忠于什么人,对什么人讲信用的问题了,而是忠信于自己的“心”,说得准确点,就是忠于本心之“仁”,信于本心之“义”。还是藕益说得好:“忠,则直心正念真如。信,则的确知得自己可为圣贤。正是自重之处。”即是说,“忠”要忠于作圣贤之“志”(“本心”),“信”要信于作圣贤之“志”(“本心”)。所谓“本心”,就是无分别的“心”,心外无人,无物,无一切,当然无是非、无对错、无美丑、无善恶。有这样“本心”的人,就不会去挑剔任何人的过错,因为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天地间的合理的存在,你只需从人与人的行为中去体悟天地的自然运动流向,认真地把握友人的行为所传来的信息,最后决定自己的行为。即便是发现朋友的行为有过错,这过错是你发现的,也应看作是他对你“明明德”的一种提示。所以,不要看轻任何一个朋友及与你接触的任何一个人。要知道,在生命本体面前,所有的个体生命(包括生命的最佳载体——人),都是平平等等的,也各有其长处和短处。因此那种把“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解释为“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是荒唐的。应该解释为:“我的朋友没有不如自己的”。
本章的第三段是:“过,则勿惮改。”什么是“过”?这不是指一般的道德上的错误,而是指在“明明德”的过程中所犯的孔子所说的“意、必、固、我”之类的错误。在“明明德”的过程中,犯这类的错误,是经常的、难免的,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发现了,当下改了就完了。当然,这里不是改外在的错误,而是改“用心”的错误。对于孔门弟子来说,就是要时时处处观照自己的“心”,看它是否跟妄念跑了,跑了,收回,再跑了,再收回,这便是“过,则勿惮改”。
通观对本章的解释,我们看到,孔子所说的“学”,是君子之“学”,其基本内容是“明明德”“知天命”,说得明确一点,君子之“学”,就是学“智慧”、学“觉悟”。 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上达”。
次看《学而》篇的“君子食无求饱”章。其原文是:子曰:“君子食无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本章主要是讲什么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认为,能够称之为“好学”的人才是“君子”。“好学”的“学”,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大学”,其根本目的是“明明德”,这也即是说,爱好“明明德”的人,才是“君子”。爱好“明明德”的人,亦即是“有道”之人。“就有道而正焉”这一句是一个关节点。有了接近已经“明明德”或已经把握了生命本体的人来匡正自己,那自然就能做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讲的也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颜回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三月不违仁”的人,是一个能合天德、达天道的“好学”之人。“敏于事”,也要用“道”,用“明明德”去匡正,合于“道”的事,要勤勉地去做,不合于“道”的事,则不能做。“慎于言”,不是不说,不合于“道”的话,不说,合于“道”的话,则要大说特说。总之,生活、工作、与人交谈,都要为了“道”,都不能离开“明明德”,离开了,就会迷失方向,就会犯错误。
但是,只是“就有道而正焉”,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君子”,称为真正的“好学”之人。如何“就有道”,即如何向已经“明明德”、已经把握了生命本来面目的人请教呢?到书本中去找他们?还是到深山老林中去找他们?孟子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到书中是找不到他们的。儒家主张“有为法”,决不会到深山老林中去做隐士,恰恰相反,积极治世,倒是他们的一个特点。所以,“敏于事”是本章的又一个关节点。只有在生命实践中事事“明明德”,才可能是“就有道而正焉”。必须记住:任何“明明德”永远是在具体“事”中,任何对生命本体的觉悟,永远不能空说,只能就事来说,所以“君子”永远最重视“事”中之“敏”。
于此,我们看到了孔子说的“吾叩其两端”的又一个例子。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好学”的“君子”吗?那你就要一方面“就有道而正焉”,同时,另一方面,又要“敏于事”,即在生命实践中事事“明明德”。这两端,是密切结合,缺一不可的。明人李卓吾就识透了这一点,他说:“此是训君子如此,不是赞君子如此。若作赞君子看,末句血脉便碍。”〔2〕意思是,这一章是解释“君子”的,是说只有具备这样“两端”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君子”,这样的“君子”才可说是“好学”的人。如把这一章当作是赞君子的,那么,紧接在“就有道而正焉”的最后一句的“可谓好学也已”,就容易被误解成喜爱空洞之学之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看成是社会分工的不同,是不够的。应当从思维方式上看二者的区别。孔子说:“君子不器。”又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都是从思维方式上来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在孔子眼里,能从“下学而上达”,从而有大思维、大智慧、大觉悟的人,才是“君子”,而“小人”则是为“器”即为形而下的东西所拘限的人,是甘心做形而下奴隶的人。但是,决不可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绝对化,因为“下学”与“上达”之间的界限是不断变化的。
二、“学”与“知”
《论语》中有三处将“学”与“知”连在一起。先看《季氏》篇的“生而知之者”章,其原文是: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里的关键是“学”与“知”两个字。弄清楚这两个字的本义,整章的内涵也就把握住了。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决不只是多数注家所说的“学知识”的“学”,而应是《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的“大学”。这是二程和朱熹告诉我们的。他们都强调《礼记》中的《大学》是研究儒学的纲领性文献。大家知道,《大学》开篇第一句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既是如此,那么,这里的“学”,就只能是对“明明德”而言,这也即是道家所谓的“见道”,佛家所谓的“明心见性”。
孔子还在《为政》篇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此“学”当然也是“明明德”之学。十五岁虽还小,但一说到是“志”于“学”,就不是童蒙学习文化知识了。这个“学”还是“知天命”之“学”,因为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之后,到五十岁便“知天命”了(“五十而知天命”)。
“学”字弄清楚了,“知”字也就自然明白了。既然“学”是“明明德”“知天命”,那么,这个“知”也就是“真智慧”和“大觉悟”了。因为“明明德”的“明德”就是“知”,就是一种认知力(包括感知力、觉知力和悟知力),它是“道”“天”“佛”的根本的表现形式,把握了它,就是把握了“道”“天”“佛”。何谓“真智慧”“大觉悟”?对生命本体、整体的把握,就是“真智慧”“大觉悟”。
在历代的注家中,能对本章作出合乎孔子本意解释者,真是极少,极少。他们都认为这是孔子对人类的层次的分类,都认为“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虚悬一格”,等于没有。在这方面,李泽厚的解释可谓是典型的代表。一看其“译文”:“孔子说:‘生来就有知识是上等,学习而后有知识是次等,遇到困难再去学,再次一等,遇到困难仍然不学,这样的人就真是下等了。’”〔3〕在这里,李泽厚将孔子说的“学”解释为“学习”,将孔子说的“知”解释为“知识”,而且从“知识”的角度将人分为四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看其“注”:“《朱注》杨氏曰:生知、学知以至困学,虽其质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学之为贵。”〔4〕这里的“其质不同”的“质”,是指“气质”。“其知之一也”的“知”,是指的“知识”。“惟学之为贵”的“学”,是“学习”之“学”,它可以变化人的气质。在朱熹看来,从“气质”上说,可以将人分为四等,人可用学习的方法来变化人的气质,所以,有道之人是很重视学习的。应当说,李泽厚所依据的《朱注》,同样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的观点与孔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看其“记”:“朱注强调学习。当然并没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孔子就否认自己属于这一等:‘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否认全知全能,‘天纵之圣’,指出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有缺失,这是儒学基本精神。”〔5〕这是用孔子的话来否定孔子自己说的“生而知之者,上也”的观点。是这样吗?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只是说他自己不属于这一等,并不是说这一等就不存在。应该知道,从“我非生而知之者”这句话,是绝对得不出“并没有什么‘生而知之’”这个结论的。实际上,“生而知之者”和“非生而知之者”,二者并不矛盾。人们之所以将其对立起来,是由于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看问题所致。
直至今日,我认为对本章解释得最好的,还是董子竹。他的解释非同一般,且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释“学”为“明明德”,释“知”为不死的生命本体,这不仅与孔子的本意相符合,而且为我们破解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将“生而知之”和“非生而知之”对立起来的观点。如他所说,就“明德”即“知”是“宇宙——生命”系统本有来说,一切人皆是“生而知之”;就“明明德”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来说,则一切人又是“学而知之”〔6〕。 第二,他用不同层次的“觉悟”来解释本章中的“上也”“次也”“又其次也”“民斯为下矣”,这不仅角度奇特,而且意义非常深刻。因为这样做,既是对以“气质”或“知识”来划分人的等次的这些做法的破除,又是对儒家之魂的一种继承和高扬。因为“觉悟”,只有“觉悟”,才是儒家的终极的价值和归宿。〔7〕第三,上述解释的最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为我们揭示了人们不能理解“生而知之”的真实原因。他告诉我们,西方人之所以否定“生而知之”的存在,这是与他们把生命的本体和生命的载体混为一谈密切相关的,也是和他们认为生命是有开端的这个观点分不开的,一句话,这是由于东西方的生命观的根本不同造成的。
为了加深对“生而知之”这句话的理解,还有一段孔子的语录值得注意,这就是《述而》篇第20章说的: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第1章说的“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好古”二字,是这两段语录的关键。弄清楚孔子“好”的是什么“古”,“敏以求之者”又是指何而言的,以及他为何“述而不作”?他所说的“我非生而知之者”的真实意义,就会十分明白地显露在我们的面前。从孔子读《周易》而“韦编三绝”,可以看出他“好”的、“敏以求之”的、“述而不作”的,是《周易》传达下来的“明明德”“知天命”的“道”。孔子如此地看重《周易》,相信它传达下来的“道”——“明明德”、《知天命》,并在自己的心中暗暗地追慕着老彭。这都是为了说明“学”的重要性,为了说明“学而知之”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只有强调“学而知之”,才不会使“生而知之”流于空谈,才会使那些“困而不学”、甘心做动物的人有所醒悟。
三、“学”与“乐”
请看《学而》篇的首章。其原文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本章的特点,是通过“习”字、“乐”字来讲“学”字。
本章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核心,可以说是《论语》的纲领性的一句话。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第一句的展开。这如同一只鸟,第一句是它的身子,二、三句则是它的两翼,三者是连贯在一起的,切不可分为三块或打成三截。
“学而时习之”的“习”字,朱熹《论语集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不亦说乎”的“说”,通“悦”,内心的喜悦。“学而时习之”,就是一刻也不会中断对生命本体的追导、体验和审美。一个真正悟得了生命本体的人,不仅内心有着无比的喜悦,而且在与别人交往中,也是无时不是快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朋”,“同门曰朋”,即指同学,泛指朋友。有朋友从远方而来,在一起交流一下各自对生命本体体验的感受,虽各不相同,也同样是快乐的;因为悟得了生命本体的内心的喜悦,表现于外的快乐,是很自然的。这是讲的有人来。反之,“人不知,而不愠”,没有人来,甚至没有人知道我这“心”中的无穷的喜悦,我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更不会产生怨恨之感。有了这种坦荡胸怀的人,不也是识了“道”的“君子”吗?这里说的“不亦君子乎”的“君子”,与前面多次讲的“君子”一样,也是“下学而上达”的人,是“知天命”“明明德”,即“觉悟”了生命本来面目的人。
“乐”字乃孔学的要旨。在《论语》中,除了本章说的“乐”外,还有不少篇章讲到“乐”字的。如《雍也》篇就有:“回也不改其乐”“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知者乐,仁者寿”等。《述而》篇就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等。
其实,不只是孔子多言“乐”,孔子之后的大儒也多是言“乐”的。宋代名臣范仲淹就为我们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不朽的名句。二程的老师周敦颐提出的“寻孔颜乐处”这一重大思想课题,对二程及整个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对曾点之“乐”所作的解释,至今还为人们所吟诵。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十分重视“乐”的本体和“乐”的工夫。他在给弟子的信中说:“乐是心之本体。……圣人只是至诚无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时习。时习之要,只是谨独。谨独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乐之本体。”〔8〕最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的学生、“泰州学派”的掌门人王艮,他在《王之斋全集·乐学歌》中对“学”与“乐”的关系作了很好的描绘:“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吁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其实,说孔学乃至整个儒学是一门快乐的学说,这并不难。真正的难处是在:到底什么是快乐?快乐在哪里?如何去得到这种快乐?要知道,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有人把快乐简单地理解为人的感官的一种愉悦,这显然是不对的。他们不知道,若被感官所迷惑,误把堕落当享乐,其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老子所说的“目盲”“耳聋”“口爽”“心狂”“行妨”。而这些,是只能叫做“痛苦”,决不可称作“快乐”的。
有人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翻译为“学习并且经常温习,难道不是很快乐吗?”从字面上说,这样翻译,没有什么不可。但学习《论语》的人却常常表示质疑。他们并不认为读书复习功课是件快乐的事,特别是那些简单易懂的问题,已经了解了,再让他去复习,他不但不觉得快乐,反而感到很痛苦。
出现上述情况,是由于他们没有抓住形成“不亦说(悦)乎”这个“悦”字的真实原因造成的。“说”(悦)是“己心”在刹那间与“天道”“至善”合和了的产物。没有合和于“天道”“至善”的“学而时习之”(简称“学”“习”),是不可能引起真正内心的“说”(“悦”)的。今天的学生之所以对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不断地提出质疑,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自己的“学”“习”中,找到这个发自内心底层的“说”(“悦”)。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段话是《论语》全书的总纲或书眼,那么,其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则是“总纲”中的“总纲”或“书眼”中的“书眼”。因为这句话,集中地体现了孔学的四个合一:工夫与本体的合一、出世与入世的合一、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无为法和有为法的合一。只有明白了这四个合一,才能真正地理解下面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从何而来?孔颜为何能在任何情况下“不改其乐”?
大凡对“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句话作过深入研究的人,都会觉得其中的“学”“习”“悦”三个字的排序,值得仔细玩味。 这里的 “学”,是《大学》说的“大学之道”的“大学”,其根本任务和终极目的是“明明德”“知天命”,即对生命本体的“觉悟”。要使这个“觉悟”,由“立志”变为现实,就要时刻把握自己当下一念,不断地反省,警惕自己时时不犯错误。如果你能够时时善念相继,那就是“习”的功夫了,一旦善念相继,你也就没有恶念了,也就“止于至善”了,即与“天道”合一了。与“天道”合一,才会有“悦”,即发自内心的喜悦,这个“悦”,才是永恒的快乐,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的快乐。
从上面对“学”“习”“悦”三字排序的描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习”字的重要地位。首先,正是这个“习”字,体现了工夫与本体的合一。“习”是达到与“本体”(“天道”“至善”)合一的“工夫”,而“本体”(“天道”“至善”)则是“习”(“工夫”)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二者是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多数注家之所以将“时习之”翻译为“时常温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将“工夫”与“本体”割裂了,尤其是忽略了孔子所说的“本体”,因而也就寻找不到真正快乐的根源。因为没有“己心”与“天道”的合一,“不亦悦乎”的“悦”,也就无从出现。 其次,正是这个“习”字,体现了“人道”与“天道”的合一、“入世”与“出世”的合一。一般认为,儒家思想是“入世的”。细想起来,这个看法,并不正确。正确的看法应当是:出世与入世的统一。这可以用“天人合一”的命题来说明。何谓“天人合一”?“天”就是出世之道,“人”就是入世之道,“天人合一”就是说出世之道和入世之道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但是,多数注家都从入世的层面去理解,而忽视了孔子之道的出世意义。他们把“时习之”翻译成“时常复习”,就是没有看到孔子的出世精神的表现。他们不知,孔子一生弘大道,他虽然立足于入世,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出世的。正是这种出世精神,才使孔子获得了真正的、永恒的快乐! 再次,正是这个“习”字体现了“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合一。凡人所知,凡人所见,永远是“窥豹一斑”的“学而时习之”,正是这一斑的“学而时习之”,组成了个体生命的“有为法”运动。“天道”“至善”永远有自己的运动,自己的轨迹,它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任何个体人可以全然把握的,这便是生命的“无为法”运动。这两条运动线永远是矛盾且又统一的,但“无为法”是运动的主要方面,对“有为法”有绝对的强制性。所谓“先知先觉”,只是通过在“有为法”中的“时习之”,从而达到对“无为法”即那个“看不见的手”的体认,也就是相合和。有了这种“相合和”,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没有道理又有道理、既无目的又合目的的审美愉悦。这样的“悦”,才是世间人一切快乐的本源,才是世间审美现象产生的根源。这样的“悦”,才是终极“觉悟”的体现,即“学”的根本内容。
四、“学”与“思”
《论语》讲“学”与“思”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为政》篇第15章,其原文是: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里,有“学”“思”“罔”“殆”四个词,需要解释。注家们对这四个词的解释,有明显的分歧,现将有代表性的观点抄录于此,以供比较。
杨伯峻将此章译为:“孔子说:‘只是读书,却不思考,就会受骗;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缺乏信心。’”他将“学”解释为“读书”,将“思”解释为“思考”,将“罔”解释为“诬罔”,并说:“‘学而不思’则受欺,似乎是《孟子·尽心下》‘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意思。”他对“殆”的解释是:“《论语》的‘殆’(dài)有两个意义,下文第十八章‘多见阙殆’的‘殆’当‘疑惑’解(说本王引之《经义述闻》),《微子篇》‘今之从政者殆而’的‘殆’当危险解。这里两个意义都讲得过去,译文取前一义。”〔9〕
李泽厚将本章译为:“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迷惘;思考而不学习,危险。’”他引朱熹的《注》说:“不求诸心,故昬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他在《记》中说:“就认识论说,与康德所说‘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几乎同一思路。这一道理至今不过时。东海西海,此心相同,此理相同。叶适《习学记言》说,‘其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者,不思之类也。其穿穴性命,空虚自喜者,不学之类也。士不越此二涂也’。汉学宋学,国粹西髦,古今同慨。”〔10〕
董子竹将此章解释为:“如果光懂上述道理(指人是可以达到对‘宇宙——生命’系统整体或‘至善’的认识、体悟、感知),而对具体的映象不思索,你就会越来越糊涂。但是,如果仅仅是被这些光怪陆离的折光映象牵着鼻子走,即被自己一时的意识牵着鼻子走,而不知他们仅仅是‘至善’的折光,是‘至善’在某个阶段某个层次的特殊映象,那就更加危险了。若只是这样,你会失去对‘至善’的把握,对‘明德’的把握,最后失去生存的定盘星。人类的大量灾难痛苦正是来源于此啊!所以,孔子在这里要用一个‘殆’字,以警世人。”〔11〕
将杨、李、董三位的解释放在一起,稍作比较,便可看出,董的观点更接近于孔子。
首先,他把“学”解释为对“至善”的认识、体悟、感知,就和《大学》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观点完全一致,就和说“今有颜回者好学”,因其“三月不违仁”之赞完全吻合。这是杨、李二氏所不及的。他们把“学”解释为“读书”“学习”,不但过于肤浅,而且与孔子本意相去甚远。
其次,董虽然和杨、李二氏一样,也将“思”解释为“思考”,但他强调“思”要以“学”为前提、为主导。他说:“‘学’是致良知达天心的过程。‘思’是对这个过程的品味、总结、清理。正如一个棋手,一盘棋后必然复盘。中国文化的‘思’,就是这种‘复盘’。逻辑分析会在其中,但不是主旨。逻辑理性只是整理思绪之用。”〔12〕杨、李二氏恰恰相反,在他们那里,“思”为主,“学”为从,“学”是感性的东西,“思”是理性的东西,这显然是和孔子的思维方式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悖的。
再次,董强调“学”与“思”的不可分割性,指出“学”的整体思维若离开了“思”的逻辑分析,就不能得到清晰的表现;但他更为强调“思”对“学”的依赖性,认为“思”的逻辑分析若离开了“学”的整体思维,就会迷失方向,陷入由概念所造成的种种灾难。这和孔子的“吾叩其两端”的思维方法是完全符合的。而杨、李二氏虽然看到了“学”与“思”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强调的却是“学”对“思”的依赖,这就与西方的思维方式相合而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相悖了。
孔子还在另一处讲到“学”与“思”的关系,这就是《卫灵公》篇第31章说的:“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寢,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请看以下的“注”与“解”:
朱熹《集注》:“此为思而不学者言之。”〔13〕
李卓吾《四书评》:“‘致知’必在‘格物’,‘尽性’必在‘穷理’。孔子已身验之矣。彼讲心学者何如?”〔14〕
康有为《论语注》:“贾子《新书》:‘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此为思而不学者言之。”〔15〕
董子竹《论语正裁》:“‘致知’必在‘格物’之中,而‘尽性’便是‘穷理’,孔子终身致力于此‘学’,而不作空洞的‘道’‘性’‘理’的思考推理,这是儒家文化的生命线。”〔16〕又在《论语真智慧》中注:“孔子《学而》开篇‘学而时习之’之学即‘大学之道’之学,绝不止读书问学,而是‘致良知’学于‘天道’。孔子之‘学’字,说到底是对每时每刻的‘天道’的‘觉悟’,不是自食之学,也不是如何‘做人’之学。”〔17〕
以上的“注”与“解”,告诉我们,这一章是孔子对“思”而不“学”者的批评,也是对前章的第二句“思而不学则殆”的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李卓吾在《四书评》中的“评”和董子竹在《论语正裁》中的“解”,他们强调“学”自始至终不作空洞的思考推理,而“思”若不以“学”为前提,则有这种危险性。
第二,是康有为和钱穆的解释,他们强调生命整体之“学”“如日”,个体生命之“思”“如火”,前者为“大知”,后者为“小知”,孰重孰轻,孰主孰从,一目了然。
第三,是董子竹在《论语真智慧》中的“注”,他强调这里的“学”,是“致良知”学于“天道”,是对每时每刻的“天道”的“觉悟”。这样的“学”和“思”怎么能分开呢?离开“当下”“思”本体,离开“当下”“致良知”,离开“当下”“悟”“天道”,是很危险的。
“思”与“学”不可分,即使对《论语》中单独使用的“思”字,也不可与“学”字割裂开来。如《季氏》篇第10章:“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里取董子竹的解释。他说:“我以为这段语录,并不是要事事如孔子所提示的去做,关键是首先搞清‘见得思义’四个字。只要事事‘见得思义’,自是视明、听聪、色温、貌恭、言忠、事敬、疑问、忿难。‘见’之一字即上文视、听、色、貌……的总括;‘得’之一字便是视已明,听已聪,色已温……谓之‘得’。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在视、听、言、动之中一直‘思义’了。‘见得思义’,不是说‘得’了之后才思其‘义’。所以这段话应是‘欲得者必以思义为先,因思义为先,视必明、听必聪、色必温、貌必恭……’何谓‘义’?‘义’,‘宜’也。何谓‘宜’?即‘仁’欲令一切众生一切人类‘明明德’所显之相,纵使繁华似锦,冷寒若冰,料峭如刃,艰苦如死……无非一个‘义’字。识得么?识得了,视便是明,听便是聪,色也必然温……此乃天道,色何不温;此乃天意,貌何以不恭;此乃天命,言何不忠……”〔18〕
董子竹的解释,好就好在他抓住了这段语录中的关键——“见得思义”四字,并对其作了使人茅塞顿开的解释。他把“思义”说成是“见得”的原因,强调不是“得”了之后才思其“义”,而是“欲得者必以思义为先”。这就突出了“义”的重要地位。什么是“义”?多数注家都将“义”解释为人世间的道德规范,而董子竹则与众不同,他把“义”解释为“宜”,解释为包藏于最具体事物中的“仁”“天道”“天意”“天命”。这样,“思义”,就与“求仁”“知天命” 没有什么差别了;“思义”也就成了“思学”了,因为孔子“志于学”,就是志于“知天命”。于此,我们便看到,“思”与“学”是密不可分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思”是“学”的工夫,是实现“学”的方法,它虽然包含着逻辑分析,但从总体上说,则不可以此为主旨,因为逻辑分析,对生命本体的把握即“知天命”“明明德”“致良知”,是无能为力的。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就在本段语录中。不要忘记,这里讲的是“君子有九思”,而不是一般人有“九思”。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下学而上达”的人,就是“明明德”“知天命”与“道”合一的人,一句话,就是学“智慧”、学“觉悟”的人。这样的人,是决不会将“思”与“学”分割开来的。
五、“学”与“为己”“为人”
这也是《论语》讲“学”字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它主要包涵在《宪问》篇第24章中。其原文是: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多数注家都分别对这里的“为己”和“为人”作解释,意思大同小异,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皇侃《论语义疏》中的话:“明今古有异也。古人所学,己未善,故学先王之道,欲以自己行之,成己而已也。今之世学,非复为补己之行阙,正是图能胜人,欲为人言己之美,非为己行不足也。”〔19〕这和朱《集注》引程子的话:“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20〕意思大致相同。
安德义则另有其解。他说:“旧之诠解,大多孤立,一古一今,两不相涉,其实不然。为学有两事,一曰‘为己’,一曰‘为人’,为己乃修己,为人乃安人,两者不可割裂,‘为己’则独善其身,‘为人’则兼善天下。先善身而后济天下。只为善身而不为人而济天下,只是‘独善’,‘独善’于己有利,于社会无益;只思为人济天下而不修己,济天下只是空想,只有修己才能安人,才能为人。当然孔子在‘为己’‘为人’这两端时,他可能更强调于‘为己’,因为‘为己’是‘为人’的根本。”〔21〕
安德义强调不要将“为人”和“为己”割裂开来,强调在孔子那里,“为己”比“为人”更根本;如果按他对“为人”“为己”的界定(“为己”即“修己”,“为人”即“安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真正理解孔子讲这段话的真实用心。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有两种“为学”,一是古人的“为学”——“为己”,一是今人的“为学”——“为人”。在孔子看来,“为己”之学,是“明明德”的“觉悟”之学,是真正的“学”,而“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相比,则是名同而实异,有害而无利的。这是孔子的本意。安德义不理解它,《四书辨疑》却识透了它。该书说:“盖为己,务欲治己也。为人,务欲治人也。但学治己,则治人之用斯在。专学治人,则治己之本斯亡。若于正心修己以善自治之道不用力焉,而乃专学为师教人之艺,专学为官治人之能,不明己德,而务新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凡如此者,皆为人之学也。”〔22〕
必须明确,孔子并不反对谈“为人”,但他主张以“为己”为前提来谈“为人”,而不能离开“为己”谈“为人”。在孔子看来,只要将“为己”说透,“为人”也就自然包涵在其中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孔子本人就是个典型。他的伟大正在于他永远审问自我、拷问自我,这个过程也就是他发现自我、寻找自我乃至实现自我的过程,也即是“克己复礼”,不用管别人是否这样,只要我能这样,这天下肯定“归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句话,就是讲“为己”即是“为人”这个深刻的道理的。
六、结 语
从以上对《论语》里的“学”字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看法之一,要以“体用一如”的态度对待这个“学”字。这是由《论语》中“学”字的本义决定的。前面说过,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论语》中的“学”主要是对“明明德”“知天命”来说的。这个问题,在曾子、子思、孟子、荀子那里,在老、庄那里,在后来的禅宗(南禅)那里,都是无需详加论证的。但是,“明明德”“知天命”,并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仍然是“用”。佛、道两家讲“无用之用”,自有其深刻性。儒家则讲现实之用,提出了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具体领域的运用。这在中国的古代应是合理的,因为一个小康温饱的农业封建帝国,真正的大用,主要只是在这四个领域。学别的全是技巧性的东西,很难直捣生命本体。“明德”“天命”遍于一切处,无处不在,处处在,干什么都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真实存在,当然最好还是在处理大事件中更易明“明德”、知“天命”。这是孔子的本意。但是,很遗憾,他的用心并未为其所有的后来者所理解,他们中不少人,把“学稼”“学圃”真的当成了小道,不知从“稼”“圃”中去明“明德”、知“天命”,实际上是把“学”的体用一如的关系割裂了。
孔子的后人误解了他,但是,历史却没有误解他。这就是西方人的物质生产和自然科学上的大发展,给麻木的中国人身后猛击一掌,使其补上物质生产和自然科学这一课。这个课补了一二百年,中国人不但从中尝到了甜头,而且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本是大好事。谁知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又陷入到另一个极端,只顾眼前的实利、实用,“学”又被局限在“数理化”等等的知识牢笼中,中国儒学的“明明德”“知天命”的“大学”,又被人们遗忘了,甚至被说成为“唯心主义”“神秘主义”。
“体”与“用”缺一不可,特别是“体”更是不可或缺的;没有生命的本体,没有“明德”的运动、“天”的运动,也就不可能有“审美的人生”。对于明“明德”、知“天命”的人来说,做事的对错与否,成功与否,自己为人的是是非非,都不是第一位的事,第一位的事则是:通过个人行为的善恶美丑真假对错,体验蕴藏在这些行为背后的那种“美”“妙”的生命的运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通晓“自己”是谁,“自己”是如何“在”的。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孔子厄于陈蔡的全过程。当时的孔子被人撵得如丧家之犬,但他却豪气满怀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不是在自己的困苦的生活中欣赏着“天”即生命本体的存在吗?
看法之二,要以“体用一如”的态度对待“觉悟”二字。这也是和“学”字相关的。既然“学”,有“体”有“用”,“体用一如”,那么,作为“学”的基本内容“明明德”,即“觉悟”,当然也是有“体”有“用”,“体用一如”的,也必须以“体用一如”的态度去对待之。
“觉悟”,不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果仅仅从“认识”来理解“觉悟”,那是错误的。“觉悟”是时代的产物,是因缘的产物,它只能来自于“当下”的实践,决不是架空的“意识”。这就是说,实践到了这个时代,你都得觉悟,我觉悟就是与我有缘的一切生命的觉悟,只是因缘成熟有早晚不同而已。
人类生命的“觉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终极觉悟”,一种是“命运轨迹中的具体觉悟”。对天、地、人总体进步的认知,对生命本体、全体、整体的认知,就是“终极觉悟”。还可以作这样的表述:透过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来看生命的本质,或观生命运动的“矢量”,就是“终极觉悟”。生命运动的“矢量”,是无形无相、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表现为“标量”才能为我们所把握。这“标量”就是我们每个人觉悟的轨迹,亦即“命运轨迹中的具体觉悟”。
“终极觉悟”与“命运轨迹中的具体觉悟”之间的关系,就是生命的“矢量”与“标量”的关系,这是典型的“体用一如”的关系。有人用北京的“鸟巢”来比喻,我觉得是很贴切的。“终极觉悟”,就如同整个鸟巢,而“命运轨迹中的具体觉悟”,则如同鸟巢中的钢构。没有诸多钢构,整个鸟巢撑不起来,没有“命运轨迹中的具体觉悟”,“终极觉悟”则不能得到体现。反过来说,没有鸟巢这个整体,诸个钢构也就失去其意义。要知道,历史本身始终是被生命的“终极觉悟”左右的。“终极觉悟”就是全体觉悟,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懂得了释迦牟尼的如下一段话:“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金刚经第三品·大乘正宗分》)这个“无余涅槃”就是“终极觉悟”,它是属于一切生命的,是一种终极的力量,是一种谁也无法抗拒的力量,是一切众生都要依赖于它的力量。于此,我们对两种“觉悟”的关系,当有进一步的理解,即二者的“体用一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与“用”的不可分离,而是说,这个“体用一如”,是以“体”为“主”的。
看法之三,要深入地探讨中国和西方的“价值观”。这是和前面讲的“觉悟”问题紧密相连的。讲“觉悟”,必然要讲“需求”或“价值”。因为“觉悟”就是一种“需求”或“价值”,特别是“终极觉悟”,就是人类的根本“需求”或根本“价值”。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就是讲人的需求的道理的,讲生命需求是什么,就是一种“价值观”。
“需求论”或“价值观”是和“觉悟观”分不开的。前面讲了,有两个层次的“觉悟”,就是“终极觉悟”和“命运轨迹的具体觉悟”,实际上,还有一个层次的“觉悟”,就是“肉体的觉悟”。比如,人类有性的要求,就变成了爱情,人类要吃饭,就变成了美食,人类要游乐,就变成了艺术……这些超越,就都是觉悟的表现。这是“终极觉悟”和“命运轨迹的具体觉悟”一定要包涵的,可谓是“觉悟”的第三层。
与“觉悟”相适应,人的“需求”也应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就必然追求“终极觉悟”,这个觉悟是决定人类需求的根本动力。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它来源于生命的本体。何谓生命?生命的根本表现就是“知”,而任何“知”又绝对是全宇宙的。个体人的“知”,看来是个人的,实际上是全宇宙的“良知”。如果整个的宇宙场的运动出现一点偏差,还能有爱因施坦的相对论吗?“需求”是“知”的一个内容,生命的需求只能永远指向“终极觉悟”,即“明明德”。这个终极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它也同时左右着每个生命的运动,每个生命的运动都离不开这个根本的需求。所以,生命的需求说到底就是希望“终极觉悟”。就拿肉体的需求来说,人的肉体需求就不同于动物的肉体需求。这区别点就在“觉悟”上。人的动物性的需求,总是包涵着超越,人吃饭,要求美食,这就是超越,就是“觉悟”,它包涵着向上一步的追求。这种向上一步的追求,最终它是要走向它的“矢量”——“终极觉悟”。任何向上一步的追求,都是“终极觉悟”里的东西在左右着,所以才有向上一步的追求。这一切,是动物的需求不可比拟的,都不是“生存”二字可以概括的。
但是,美国人马斯洛却不懂得这一点。他提出的宝塔式的五种需求,说穿了,就是一种动物的需求。充其量只不过是把人这个动物变成了高级动物而已。他的五层需求理论当中,只有最后的“自我实现”是高级动物的需求。所以这个理论是绝对错误的。最多不过是对动物需求作的一种表面的概括,其主旨是把肉体的需求,当成了人类价值观的基础,这在本质上是从属于古希腊文化的,是古希腊文化的价值观。
生命的需求,说到底,就是希望“终极觉悟”。这才是根本的需求,才是一切价值观的根本。某件事,有没有价值?该做不该做?具体说时可能五花八门,但就整体而言,只看这件事本身是否有利于生命的“终极觉悟”。同样的,某种文化的价值观,它的存在是否合理?在它束缚下的需求是否是终极的?这也只能看这种文化价值观是否与人类走向“终极觉悟”的大方向相一致。如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以基督教文化为制衡的、以美国文化为经典的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由兴盛到强大,到成为世界的霸主,这是因为生命“终极觉悟”的需要,生命必须经过西方文化这个阶段,特别需要经过美国文化这个阶段,不经过美国这个阶段不行。为什么?正是美国的这个阶段促使了全球的一体化。美国人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从自由贸易就可以直达全球一体化,这本身就有利于全人类的“终极觉悟”。
但是,千万不可以为美国文化的需求就是终极的。要知道,美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样板,而西方文化则是以欧洲的海盗文化为基础的,它的价值观必然表现为掠夺、挥霍和堕落。它和生命本体的价值观肯定是有矛盾的,肯定是对立的。同时,它又不懂得“觉悟”为何物,更不懂得一切依赖于“终极觉悟”这个道理,所以它不可能是终极的需求,只能是一个过程,一个必然的过程。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迟早要被符合于生命整体的前进方向的文化价值观所代替。
生命“终极觉悟”的火种在中国。《论语》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五十而知天命。”“天之历数在尔躬。”《大学》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都是讲“终极觉悟”的。这种“终极觉悟”,才是中国人的终极需求,根本需求。但是,要实现这个根本的需求,是要有合适的物质基础的。这个基础,古代的中国人没找到,西方人找到了,这就是前面说的,美国人利用自由贸易,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美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促使了中国的崛起,这就为中国的“心学”文化在全世界的弘扬做好了准备。21世纪,是人类直接要求把“终极觉悟”作为人类的价值观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国人会不会像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那样,以肉体的享受作为终极追求,把掠夺、挥霍和堕落作为自己文化的主轴呢?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国人没有这个基因。你不妨去看看中国的古代圣贤和古代人的文学作品,他们并不满足于食色,他们永远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永远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最后达到“天之历数在尔躬”。中国人终极价值的追求是:“我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这种价值观是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大不相同的。中国人的需求是明白“心”的运动的需求,西方人是不明白“心”的运动的需求。西方人的需求实是动物的需求,所以更多地表现为两个极端,要么是强盗式的需求,要么是兔子般的需求。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永远不做强盗,也永远不是小白兔。他是驶向人类“终极觉悟”这只航船上的领航者!
注释:
〔1〕〔9〕杨柏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18页。
〔2〕〔14〕李贽:《四书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136页。
〔3〕〔4〕〔5〕〔10〕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93、393、393、63-64页。
〔6〕〔11〕〔16〕董子竹:《论语正裁——与南怀瑾商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5、57、241页。
〔7〕〔12〕〔17〕〔18〕董子竹:《论语真智慧——兼就教于钱穆、李泽厚先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82、54、365、384页。
〔8〕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1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页。
〔15〕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1页。
〔19〕〔20〕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04、1005页。
〔21〕安德义:《论语解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62页。
〔22〕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05页。
〔责任编辑:嘉耀〕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天下、王、霸:先秦儒法的‘世界秩序’理念及其当代启示”(项目编号:15YJC810016)的阶段性成果。
徐恺(1979—),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