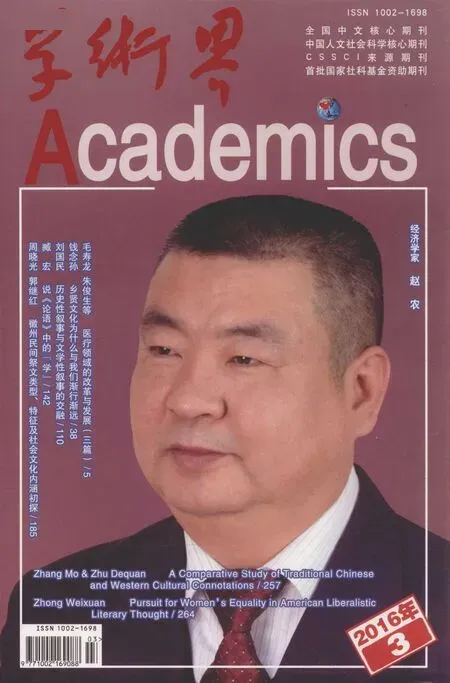边缘抑或中心:美国印第安女性主义
○ 许晓莉
(安徽大学 大学英语教学部, 安徽 合肥 230601)
边缘抑或中心:美国印第安女性主义
○许晓莉
(安徽大学大学英语教学部, 安徽合肥230601)
当代美国女性主义强调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性,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本文聚焦多元美国女性主义中的一角——美国印第安女性,从文化传承和历史发展的维度,挖掘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文化,揭示当代印第安女性的边缘现实,以此考量美国当代印第安民族的女性身份,并探究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
美国印第安;女性主义;中心传统;边缘;延续和发展
美国女性主义,旨在批判男性中心主义,追求男女两性在社会中平等、和谐的发展愿景。早期美国女性主义运动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主导力量,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美国少数族裔女性受到的歧视、压迫和边缘境遇。于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女性主义者阵营内部才出现了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群体挑战的声音,当代女性主义继而开始呈现出多元的发展趋势。不能以白人女性主义语境中的“妇女”概念来理解所有妇女,因为它无法反映所有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1〕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是不完全的。美国印第安女性主义正是多元美国女性主义中的一角,具有鲜明的族裔文化和地域特异性。
一、记忆中的中心传统
印第安土著人认为,神话就是真实的历史,讲述并牢记这样的历史是族人神圣的职责,对于现世的生存必不可少。〔2〕追溯北美印第安的传统神话故事,可找寻不胜枚举的女性神祇形象,诸如老蜘蛛女(Old Woman Spider)、第一女(First Woman)、蛇女(Serpent Woman)、谷物女(Corn Woman)、大地女(Earth Woman)、思想女(Thought Woman)、沙祭女(Sand Altar Woman)、生育水流女(Childbirth Water Woman)、天空女(Sky Woman)、变化女(Changing Woman)等等。土著人对于女性神祇的信仰是源于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是对她“具体发出的神圣力量”的崇拜,〔3〕是态度、信念和行动的总和。〔4〕印第安传统文化里,把诸多神灵崇拜与女性而非男性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将女性特征神圣化、美好化的族裔心理现实,揭示了印第安人真实、神圣、独特的女性中心主义传统。美国印第安女性学者波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指出“传统的部落生活方式大多是女性制的,从来不是父权制的,这样的特征对于所有负责任的活动家理解部落文化非常重要……不管如何的千差万别,美洲印第安人都将他们的社会体系建立在仪式的、神灵居中的、女性为核心的世界基础之上”。〔5〕由此可见,女性意象和神祇意象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的联系是必然的,女性和神祇通过神圣的传统的仪式合体,固定下来,共同构成印第安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核心,并在历史和文化中传承、延续。
追溯和研究女性神祇原型,探究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有助于理解北美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女性特征和女性意识。其一,印第安女性神祇是女性的生命孕育力和创造力的神圣化。正如波拉·甘·艾伦所说“我们就是大地。据我的理解,这是渗透在美国印第安生活中最基本的理念。大地(母亲)和人类(母亲们)是相同的。”女性是人类生命的孕育者,大地是万物生存的创造者,把两者类比、融合于“大地之母”的意象,折射出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女性作为母亲的意象,不仅是显性的万物生命的创造者,还是隐性的印第安族裔文化的延续者和创造者。其二,印第安女性神祇体现了印第安女性思想激发的能力。“位于西南的凯瑞斯布普洛,很久以前女人就是社会的中心……人们称思想女为蜘蛛祖母,认为她是创造者、是梦幻的存在,她把所有的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事物编织成为一种存在”。〔6〕印第安神话独具匠心地创造出“思想女”这一神祇,将神圣的思维能力赋予女性。女性是思想和语言的传承者,这种思维能力是印第安人的精神灵魂所在,更奠定了女性中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其三,印第安女性神祇打破了男女两性关系对立的意识。印第安文化中女性中心主义传统,不是与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相反的另一种性别压迫,而是一种两性平等的平衡状态。例如,“变化女”——印第安纳瓦霍人敬仰的女神,面对太阳提出让她作为自己的伴侣的要求,她机智而又富有哲理地回答:“你是天空,必须一直保持不变,而我是大地,我随季节而变化。你一直在移动而我保持原地不动,这样,我们相互完善,让世界保持完整。你和我都有相同的精神特征,我们的价值是平等的,尽管我们不相同,但是我们是相似的。”〔7〕“变化女”这段诗意的回答,不是女性对男性不平等地、被动地接受或拒绝,而是在男女处于平等身份地位的基础上,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存在于他们本身的性别特征和社会分工的不同。由此可见,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对于男女两性平等、互补、平衡关系的认可和推崇。
印第安女神文化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精神信仰,而是源于生活,又紧密联系和关照现实生活的。女性神祇不仅是女性特征的神圣化,还是印第安女性在真实生活中平等身份和中心地位的真实写照。传统的印第安社会并没男女性别的对立、分级,只有社会分工、角色能力的差异。女性因其特有的生命孕育力、思维创造和语言能力,一直享有平等的身份乃至受尊重的社会地位。历史研究发现,传统印第安部落大多属于母系社会,女性在氏族事务中行使决策权。米歇琳·佩桑图比(Michelene Pesantubbee)研究发现,美国东南部的乔克托族的部落经济状态长期保持为男猎女耕,且以母系传统为核心。妇女在族群中因为在提供食物、生育后代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成为受尊重的敬爱之人(Beloved People);在庆典仪式和葬礼等群体活动中担任主导角色;在部族决议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8〕斯科特·莫马迪(Scott Momaday)谈到基奥瓦部落群体中,植物性药物有着神奇的魔力,男人充当祭司、药师等角色,而“药物的知识和灵性却同样由女性拥有”〔9〕,对植物理解和药材使用、掌握的分工,揭示了男性和女性在氏族社会中拥有平等的身份和地位。特瓦族学者爱德华·齐尔(Edward Dozier)则指出,西部布普洛部落(霍皮、哈诺、祖尼、阿科马和拉古纳)主要“建立在与外族通婚的母系氏族之上,女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房屋和田地的所有权,并流行男方入赘女家的风俗”。〔10〕此外,印第安女性还是家族故事的主要讲述者。传统印第安人生活里,时常有家族所有男女老幼在忙碌了一天的劳作之后,围坐在家庭的核心女性人物——往往是受到族人尊重的老祖母身边,听她讲述部落和家族的故事。族人通过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活动聚集在一起,故事成为印第安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讲故事是继承和延续印第安部族传统的有效策略。印第安人的智慧、思想、文化和历史在年年岁岁、代代相传的故事里记忆、传承。故事的讲述者主要为女性,也因此成为印第安语言发展的推动者和部族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二、被边缘化的现实
自1492年哥伦布踏上北美大陆,在美国白人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下,印第安土著的传统的部族生活开始被打破,传统文化被白人主流文化逐渐蚕食,而其特有的女性中心主义传统也在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冲击下逐渐被取代乃至失落。传统印第安社会里女性和男性平等地社会分工、受到男性和社会的尊重、男性和女性和谐发展的社会现象不复存在。究其缘由,印第安部族社会的诸多变化如土地、宗教和白人父权思想的入侵影响并改变了印第安女性的身份、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齐佩瓦学者拉杜克(Winona La Duke)等人认为,对“土地”占有观念的改变,是瓦解印第安母系文化的核心原因。〔11〕美国白人殖民者的入侵,带来美国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域环境的变化:人与自然的疏离、边界的划分、土地的失去和家园的消失。“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失去了土地,印第安女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女性核心价值观,在白人主流社会里如浮萍般受到冲击,飘荡至社会的边缘。波拉·甘·艾伦这样谈及印第安妇女的处境:“土著妇女依然必须应对一个事实,一个更难于注意或讲述的事实:如果公众和个人视美国印第安人这一群体是隐形的话,那么印第安妇女则根本不存在。”〔12〕宗教方面,美国白人崇拜的是男性的基督文化,男性角色作为创造者取代了印第安人崇拜的女性神祇。艾伦曾经指出部落女性地位的改变,是印第安部落文化转变的核心。印第安传统社会的女性意识最直接、最根本的改变则来自于美国白人的父权思想。父权思想下,把印第安人视为野蛮人,把印第安女性视为劣等性别,印第安妇女在政治和社会及经济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受到质疑,她们的地位不再稳固,她们的声音被湮没。由此,印第安女性主义者提出相对于性别压迫,殖民压迫才是当代印第安社会妇女问题的根源:“我们是美国的印第安妇女,在这个秩序里,我们是被压迫者,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印第安人,作为被美利坚合众国所殖民统治的人,而不是作为女人。”〔13〕
印第安女性在社会、文化中身份、地位的改变也因此体现在印第安文学中。印第安女性文学则在文学领域中表达了印第安女性的经历、感受和诉求。正如不能用美国白人女权主义来看待、理解美国所有阶层和族裔的女性,也不能将其用来解释印第安女性文学的特异性和探究印第安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于1991年发表了《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女性写作的传统与变化》,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她注意到因种族、阶级和性选择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女性创作的多样性,并指出女性文本的历史性和多元文化性研究的必要性。肖沃尔特还特别强调,美国女性创作的历史“必须……学会理解和尊重每个姐妹的选择”。〔14〕
纵观美国印第安文学,并没有一开始就出现类似美国白人文学、美国华裔文学和美国黑人文学中男性经典作家作品对于女性形象的扭曲、厌女现象描写和男女作家对峙的局面。在印第安人部族的女性中心传统影响下,印第安人男作家通常对自己的女性同胞厚爱有加,而印第安人女作家也很少大肆抨击某位印第安人男作家的父权思想。〔15〕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部族尚无自己族裔的书写文字,印第安人主要是用口述的方式来延续部族古老的传说和自己的故事。印第安女性文学书写最早可以追溯到1891年克里克人索非亚·爱丽丝·卡拉汉(S.Alice Callahan)的小说《森林之子瓦妮玛》。它的问世标志着印第安妇女开始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也意味着白人殖民者无法再继续漠视印第安妇女的存在。〔16〕自此开启了印第安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890-1970年),即女性意识萌发阶段。印第安妇女写作的目的,在女性意识方面,主要是记忆和保存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印第安女性文学兴起、成长和发展则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末声势浩大的“印第安文学复兴”时期,构成第二阶段(1970年至今)的女性身份书写。其间,涌现了大量的印第安女性作家,主要有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波拉·甘·艾伦、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琳达·霍根(Linda Hogan)、伊丽莎白·库克琳恩(Elizabeth Cook-Lynn)、乔伊·哈久(Joy Hario)、玛丽·托芒顿(Mary Tall Mountain)和雷娜·格林(Rayna Green)等。这一时期的印第安女性作家无论从作品数量上,还是作品的内涵和其对印第安文学影响意义上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印第安男性作家作品。然而,遍寻当代的美国文学史及其研究,鲜有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别说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对于印第安族裔女性作家而言,“边缘”是印第安族裔女性在白人父权制主流社会里的生活状态,也是印第安女性作家作为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所处的由中心滑落后所面临的困境;是她们的真正的本性,体现了她们真实的创作姿态和话语空间位置。〔17〕印第安族裔女性文学的边缘写作是在白人文化殖民冲击下,对印第安女性境遇现状的考查、女性社会存在缺失的描写、印第安女性命运的关注及印第安女性身份建构的探索和思考。
三、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比较印第安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波拉·甘·艾伦发现印第安男性文学强调殖民过程带来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异化和对印第安人消亡的焦虑感,而印第安女性文学的主题则是延续、适应和存活。〔18〕可见,当代印第安女性文学较之于印第安男性文学主题,除了族裔意识觉醒和族裔身份建构,更多了对印第安女性意识和女性身份的关注和思考。印第安女性作家重新审视自己被殖民化的女性传统文化,并从传统记忆中获得力量,抵抗印第安族裔和印第安女性遭受的边缘境遇,对印第安族裔和女性的延续和发展,思考得更加深刻,表现得更加乐观、积极和努力。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是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和路易斯·厄德里克。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诺顿女性文学史》中最年轻的一位作家,出生于1948年美国新墨西哥州,有着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白人的混血。西尔科从小就喜欢听部落里的人讲故事,并将这些故事最后都融进了她的文学创作。《典仪》是她获得艺术上巨大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印第安退伍老兵塔尤怎样通过印第安神话和传统仪典,寻求精神救赎,治愈在白人主流文化社会里受到的心理创伤,并重新找回生活信心的心路历程。在白人的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塔尤感觉自己是一股在白人世界里进进出出的‘白烟’”〔19〕,白人医生诊断他得了“战争创伤应激障碍”,然而比这种战争心理创伤更痛楚的是他在白人社会里生活的边缘感和印第安族裔身份的缺失感,这一切让塔尤找不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若不是遇见了夜天鹅(Night Swan)和提茨(Ts’eh)这对既是母亲又是情人的女神,得到她们的救助和治愈,塔尤几度濒临死亡。在印第安的女神文化中,夜天鹅是神坛上的女子,她是“没有年龄”的老祖母,是母系氏族的象征,她的后代都是女子。〔20〕夜天鹅是塔尤的情人,通过灵与肉,在性方面引领着他,唤醒他灵魂深处爱的能力;夜天鹅又是塔尤的母亲,使得塔尤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实现了精神的启蒙,完成了成年礼,实现了精神上的新生。和夜天鹅一样,提茨也扮演着情人和母亲的双重角色。提茨居住地有漫山遍野的黄色的玉米,还有塔尤遇见提茨那天她穿的黄裙子,西尔科对黄色独具匠心的运用,无不暗示提茨是印第安部族传说中拥有神奇力量的黄女人的化身。塔尤寻找走失的斑点牛标志着他寻求精神救赎旅程的开始,提茨亲自帮助塔尤拯救了牛群;她还用所掌握的药理知识救了塔尤的性命;此外,提茨用身体和爱消除了塔尤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唤醒了他在白人社会中失落的族裔灵魂,“他热爱那个创造了万事万物的女人,他终于意识到她一直爱着他和她的人民”。〔21〕最后,塔尤在提茨的爱中也变成了一个“黄色”的人,暴雪的茧白已经从他的皮肤上褪去,祖先赋予他的黄色开始渐渐显露,在命名仪式上,塔尤接受了他的“印第安的名字”,这意味着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在身份回归中获得了新生。如果说《典仪》中的塔尤是印第安族裔命运的代表和象征,塔尤在夜天鹅和提茨两位女神的救助下治愈伤痛,最终蜕变成“黄色”的印第安人,揭示了印第安族裔身份是印第安人生存的灵魂,而这种印第安人身份的寻求和重建,是借助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记忆和印第安女性的神圣力量完成和实现的。
路易斯·厄德里克是20世纪60年代印第安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她的《爱药》一举夺得全国图书评论界奖。厄德里克从女性作家的视角,描述了美国白人殖民统治和父权制文化冲击下,印第安女性的边缘境遇和命运以及她们对自身女性身份的探索。《爱药》将族裔“归家”的任务聚焦于琼——一个离开了印第安部族居留地,生活在白人社会里的边缘印第安女性人物,颠覆了印第安文学中男性主人公“归家”的常规。琼的归家暗示着印第安人的归家是族裔身份和女性身份建构的双重任务,且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小说的开篇,琼死于返回居留地的风雪途中,学者认为是琼肉体的回归;小说发人深思的结尾则是琼精神的回归。在小说的最后,琼的儿子——利普夏凝望河水的描写中,厄德里克使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利普夏的记忆如同河水般流淌,回到曾经的印第安人精神家园,家已是一种集体记忆中的历史和传统。他想起了自己一直不认可的母亲琼,对琼的理解象征着他对自己印第安根源文化的理解。印第安人精神家园的回归、印第安族裔文化的找寻和族裔身份的重建之路,一如“桥下的河水蜿蜒曲折”〔22〕,充满艰辛、挫败,却又不乏希望和力量。“变幻莫测的水下”是厄德里克对印第安人生存现状和命运前途的意象描绘,关于印第安人的归家、印第安族裔的思考,在《爱药》中她没有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却书写出自己印第安族裔的信心和乐观:“所以我只要渡河把她带回家就行了”。〔23〕琼的灵魂已踏上归家之路,成功与否已不再重要,在厄德里克看来,印第安人重新找回了传统文化的记忆,并一路前行,如河水般流淌不息。
从女性神祇崇拜,到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女性中心地位和身份,美国印第安传统文化无不强化了女性的力量,突出了印第安人宇宙观中母系的核心价值。然而当代印第安部族受到美国白人的殖民压迫、文化蚕食和边缘排挤,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也随之被破坏、边缘乃至失落。当代印第安女性在边缘化的现实境遇中,是选择被同化的边缘,抑或是回归中心的传统?路漫漫其修远兮!印第安女性在探究族裔和女性身份建构的道路上,也许尚无明确、统一的答案,然而可以确信的是无法忘却也不能失落的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将会照亮印第安女性和族裔在白人殖民文化里的抗争之路,并给之以无穷的启示。
注释:
〔1〕〔18〕金莉:《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多维视野》,《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第98、100页。
〔2〕〔8〕秦苏珏:《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当代美国土著小说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61、71页。
〔3〕〔意〕拉裴尔·贝塔佐尼:《神话的真实性》,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4〕Vine Deloria Jr.,God Is Red:A Native View of Religion.Golden:Fulcrum Publishing,2003,p.121.
〔5〕Paula Gunn Allen,“Introduction” in The Sacred Hoop: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Boston:Beacon Press,1992,p.2.
〔6〕〔12〕Paula Gunn Allen,The Sacred Hoop: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Boston:Beacon Press,1986,pp.264,9.
〔7〕Paula Gunn Allen,Grandmothers of the Light:A Medicine Woman’s Sourcebook.Boston:Beacon Press,1991,p.80.
〔9〕Charles L.Woodard,Ancestral Voice:Conversations with N.Scott Momada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p.67.
〔10〕Dozier,E.The Puelo Indians of North America.New York:Holt,Rhinehart & Winston,1970,p.133.
〔11〕蔡俊:《超越生态印第安:论露易丝·厄德里克小说中的自然主题》,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13〕Karen J.Warren.Ed.Ecofeminism:Women,Culture,Nature.Indiana U P,1997,p.22.
〔14〕Elaine Showalter.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75.
〔15〕〔16〕刘玉:《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述评》,《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3期。
〔17〕王军、李艳红:《异质文化背景下的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研究》,《名作欣赏》2009年第18期。
〔19〕〔20〕Silko,L.M.Ceremony.New York:Signet Books of New American Library,1977,pp.14,90-91.
〔21〕Allen,P.U.The psychological landscape of Ceremony,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1979.5(1),pp.7-12.
〔22〕〔23〕〔美〕路易斯·厄德里克:《爱药》,张廷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307页。
〔责任编辑:弘亭〕
臧宏,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和儒、道、佛三家原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