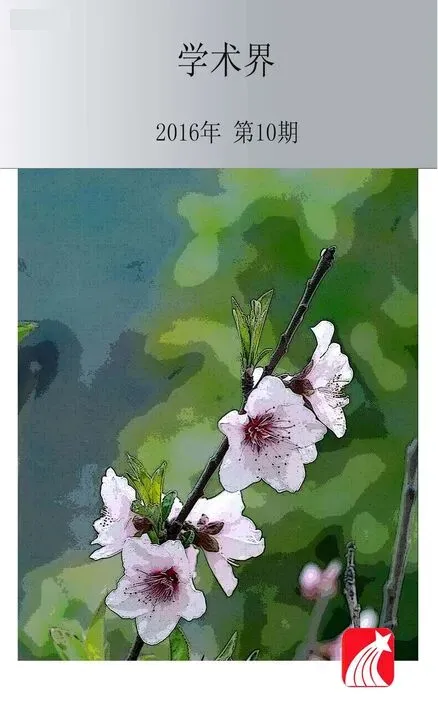酷刑的仪式性和民间革命心理——《檀香刑》的精神解析
○缪丽芳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 安徽 合肥 230051)
酷刑的仪式性和民间革命心理
——《檀香刑》的精神解析
○缪丽芳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安徽合肥230051)
莫言的《檀香刑》,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的肉体在接受法律判决时,演化为最极端的刑罚场景。它真实地再现了人类命运中某种内在的悲剧,通过描绘、安排场景和对话,让我们这些观众(或听众)体验到最大的恐惧。对酷刑的反省,是这样一种可能的模拟试验,它的目的,是检查蕴含在旧制度文化中的残酷性,也检省一种面向个体的制度暴力,以及一个社会个体的肉体生命和司法制度的关系,唤起民间革命心理的集体回忆。本文尝试从这样的制度与暴力的阴暗特性中,找到对已经发生之事的反思性分析和批判维度。
肉体与政治;酷刑;刑罚机制的仪式;集体回忆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内掀起了新的研究热。在这股热潮之中,本文试图重新阅读莫言的《檀香刑》,揭示其中“酷刑”所遮盖的东西:血腥的现实和戏剧化场景中获得的脆弱的记忆。
在莫言的《檀香刑》里,“檀香(祭祀仪式的氛围)”不是戏曲的中心,“刑”才是中心,而且是酷刑。这一系列的酷刑变成示众性的痛苦,它就肯定是要建立起关于政治权力的“恐惧秩序”,并由此使人们感觉到生存的疑惧和可怕,变成注定走向毁灭的政治事件的神秘性,在临刑者的苦难中产生了狂喜的幻觉,经由刽子手——专业的、职业化的,以执行酷刑为死亡取向的人——的戏剧表演,达到制度和政治的快乐秩序,同时又由此变成一个悠久的神话。与此相应的,民间〔1〕智慧充当了临刑的受难者,作为民间艺人的受刑者,把死亡的酷刑化,这种真正的悲痛和生存事实分离开,甚至以艺术的方式面对这一制度的恐惧,这是一曲民间精神可悲的颂歌。“莫言艺术最根本也最有生命力的特征,正是他得天独厚地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深深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才得以天马行空般地充沛着淋漓的大精神大气象。”〔2〕
一、刽子手和受刑者的对手戏
如何理解刽子手和受刑者?这个是关键。阿Q也受刑,但《檀香刑》的受刑者孙丙自身是唱戏的,这个身份,别有味道。在《檀香刑》里,莫言把酷刑艺术化了,有时甚至如同童话一样美丽。但这种喜剧性的产生,它是莫言经典的小说笔法,从“红高粱系列”一直存在。借助喜剧性的受刑和刽子手,我们看到的首先不是制度,似乎酷刑并不仅仅是制度的疾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始于刽子手的虚荣心。这一巧妙、狂欢化的转换,把刽子手变成旧制度的一种“活的精神”。而且当它把受刑者的鲜血、刽子手的艺术智慧和权力者的嗜血本能紧密结合在一起时,它才真正成为美丽的神话。
酷刑中的肉体是血腥残酷的,它意味着世俗政治双重的虚无。孙丙在被处死前是有机会逃走的,但他声称自己必须处在自己的位置,否则刽子手赵甲和他,都会成为生活的例外。事实上,在完成酷刑这一意义上,孙丙来自民间,这种伤害是随时发生的,他也就不具有殉道者的意味,在刑场上,他还对观众唱他的猫戏:
“……若不是俺打定主意要上刑场,此时刻,神不知,鬼不觉,只有那小山站在这囚车上。朱八哥哥呀,俺孙丙辜负了你和众兄弟的一片心意,使得你们命丧黄泉,首级挂在了衙墙上,但愿得姓名早上封神榜,猫腔戏中把名扬。”——第十六章:猫腔《檀香刑·孙丙游街》〔3〕
如果说死刑作为惩罚是制度的潜在逻辑的话,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酷刑的虚荣,则来源于刽子手的疯狂和快感,来自权力的专横和人性的残酷。在通向死亡的途中,受刑者不再单个成为示众性的物,在每一次行刑中,观众产生复杂的感受,有快感、也有恐惧,快感是肉性的,恐惧是公共伦理允许的。鲁迅自己对这种围观做过精妙的精神分析,在受刑者和围观的众人的神经纤维的颤抖中,从一块块被肢解的肉的被悬挂,或被抛掉这一模糊而真实的事实上,刽子手也变成示众性的要素。也正是如此,刽子手本身变成狂欢仪式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在莫言《檀香刑》里,莫言借大清王朝最后的统治者感叹地说:“你为了我们大清杀了这么多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4〕刽子手终于成了大清皇权的保护神。
《檀香刑》里的刽子手一直是显性的要素,因为酷刑的目的不只是针对受刑者本人,也不是为了制造出一个匆匆忙忙的“革命”的替罪羊。和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阿Q的受刑是漫画式的寓言,而《檀香刑》中孙丙的受刑则成为一种民间生命境遇的隐喻。
“俺深情地看着这个优秀的东北乡子弟,说:好孩子,咱爷们两个正在演出猫腔的第二台看家大戏,这出戏的名宇也许就叫《檀香刑》。”——第十六章:猫腔《檀香刑·孙丙游街》〔5〕
《檀香刑》不为孙丙立传,而是为“刑”立传,这样刽子手赵甲不可能不出现,他必须参与孙丙受刑的状态。“受刑者”和“刽子手”是“刑”的两面,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恐惧和不安;也只有这样,孙丙才能把受刑变成戏剧场面,他是死于“刑”的残酷,人们不会对“刑”本身产生怜悯,只能在动态的“刑”中作出判断,这由孙丙所处的民间生活之本性决定着。
《檀香刑》里,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词语中的决定论。如果我们认为接受酷刑是孙丙在大清王朝没落前必须承受的事实,这样一来,他就可能成为一个符号化的隐喻,隐喻作为民间身份的肉体在政治危机或社会危机中,总是处于被转嫁灾难的地位,总要接受一种“兴亡百姓皆苦”式的结局。从历史的角度,这的确是几千年的事实,政治统治上的制度与权力,总是把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演化成为致命的灾难,并转嫁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之上。也可以说,民间的处境是变成酷刑与灾难之间的二重悖论。对于我们的现实世界,《檀香刑》是一个反讽,它来自民间生活底层的潜意识,是一个制度中政治和特殊个人恶性的最为歇斯底里的欲望。
受刑是目的,演出是桥梁,唱戏是为酷刑立传的小说手法。需要受刑者和刽子手双方通力合作。在鲁迅的《药》中,是围观的人群挡住了施刑者,在《阿Q正传》中,阿Q受刑前后都只是一个猥琐的意识符号,他是在一个遥远的记忆中死于谋杀和痛苦的沉默,他身上不可能有一丁点的背叛。由于阿Q在受刑时,一直挡住了施刑者的出场,施刑者处于被搁置的状态,它更主要地成为背景,不再是受刑本身,甚至阿Q之死也不会带来恐惧和威慑。
孙丙的身份,和阿Q不同,喜剧性也不同。阿Q在临刑前唱戏,也试图恢复一丁点悲壮的气度,现实对戏文的致命的模仿,但那是“他人”的声音,是弱者阿Q内心的呓语,所以连模仿者阿Q也会感到不安和沮丧,感到力不从心。孙丙自己就是一个唱戏的人,舞台和戏曲就是他的生活,他自己也充当戏曲中的角色(造反者):
“前呼后拥威风浩……俺穿一件蟒龙袍,戴一顶金花帽……俺也可摆摆摇摇,玉带围腰……且看那猪狗群小,有谁取来揣俺孙爷的根脚……”——第十六章:猫腔《檀香刑·孙丙游街》〔6〕
把受刑变成舞台上的演戏,并不是虚无,孙丙对自己的认知是一种事实状态,他也许对这种事实状态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这些清醒的意识来自何处呢?来自民间的卑微?来自江湖义气?来自一种荒诞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把他受的“檀香刑”看作是事实,把他演的“檀香刑”看作是游戏,是他力图摆脱生命的有限性的一种戏剧化叙事。这种主题并不少见,但这种方式,它是无可奈何的,是面对政治暴力只能听天由命的民间姿态,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完整记忆。他已经造过反,只不过造反失败,但孙丙的受刑经由莫言的手,避免了成为古典主义的老生常谈的命运。最终的结局是酷刑成为神话,只有一个法则,那就是个人对界限的关系所产生的精神生活的恐惧模式。
“他(孙丙)的眼中突然迸发了灿烂的火花,把他的脸膛光映得格外明亮——比月光还要明亮。……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来,与鲜血同时涌出来的还有一句短促的话:‘戏……演完了……’”——第十八章:《知县绝唱》〔7〕
根据米兰·昆德拉的说法,这不是笑和嘲讽,而是一类特殊类型的可笑,巴赫金把它称之为“狂欢”。——我们叹服莫言把一个老套的抗日的故事,变成鲜活的《红高粱》,也叹服他把一个旧时代的刽子手杀人,变成一种艺术性的不幸叙事。——这一不幸只有从民间的角度看才是真实的。一些遥远的回忆片段带着幽默的成分,把猫戏和封神榜联系了起来,孙丙一边走向刑场(这是戏曲片段),一边把这一场景当作上演猫戏的场面,不懂得来自民间自己幽默逻辑的人,是不会理解这种小说的艺术的。
二、旧制度的活精神
在把民间从里往外翻的游戏中,运用地方方言、戏曲语言、官方白话、书面语等话语形式使民间造反的行为成了心理学——戏曲化——形象化的三位一体,记忆经由孙丙的形象,一再深化,通过以戏曲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记忆,反复还原某种具有鉴赏价值的场景,又一再经过心理学的展示,把刽子手推向前台,使民间处境的精神性,被恢复得十分准确。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刽子手的“不朽的荣耀”?首先是别人的“漂亮的死”。赵甲把杀人把戏——他认为,这是他这样的艺术家所能做到的最伟大的艺术表演——变成“不朽的荣耀”,有他的荣誉感。
这是皇朝之下“漂亮的死”,这漂亮,是因为死刑执行的场面被表演得像一台戏,并成了公共性的东西了。酷刑的戏剧表演相伴随着成为公共性的示众场面而产生,示众性又成为戏剧表演性的再次戏曲化效果,两者在“刑”中会合后,然后又相互分离,由示众走向的是政治权力的刑罚实践机制。在这类实践机制给社会和政治的运作情境带来的某种经验领域中,如果我们从个人自己在死亡中可能构成的问题出发,就可以发现在中国酷刑史上,死亡的对象是制度存在风格的见证,个体只在皇权秩序的法约束关系中,成为制度暴力的“艺术对象”,成为制度本身自我验证的技巧。个体在《檀香刑》中,其目的是制造自我实践的更优美的形式,无论是权力者(皇帝、太后、官僚),还是刽子手(赵甲、余姥姥)或者受刑者(太监、钱雄飞、孙丙)都只是这“漂亮的死”的一种形式。
“余姥姥把那阎王闩一寸一寸地摸了一遍,点点头,用三尺大红绸子,珍重地包起来,然后恭恭敬敬地供在祖师爷的神像前。”——《凤头部:赵甲狂言》〔8〕
从示众性的刑罚机制的仪式崇拜到刽子手本身侵占专制王权的精神舞台,这便是酷刑的戏剧表演性走向。刽子手成为王朝的平衡力量,连权力者也只好把他的椅子赏赐给这个出身卑微的尸体崇拜者,刽子手借助酷刑的艺术表演性与专制君权缔结了象征性的契约:恐惧胜于杀戮,残酷胜于惩罚,示众性胜于禁止。
这便是刽子手能将最高的荣耀建立在别人的“漂亮的死”的原因。刽子手(赵甲)通过自己的艺术表演和权力者(袁世凯)通过酷刑的实施达成同盟,恐惧和残酷同属于建立起这一秩序的适用逻辑。
王大人道:“京里太监犯了事,历朝历代都是由慎刑司执行,皇上把任务交给刑部,这事破了天荒,这说明皇上记挂着咱刑部,器重着咱刑部,天恩浩荡啊!你们一定要加小心,活儿干得俊……。”〔9〕
皇上也说:“还是刑部的刽子手活儿做得地道,有条有理、有板有眼、有松有紧,让我看了一台好戏”。〔10〕
酷刑以精神病态的经验方式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当这一经验成为一个单独有效的,并且是经常性的领域时,它在陌生化的道路上被道德化(这种陌生化,是指它原来的功用销蚀了,变成与法律和禁止相反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专制制度由此向前迈进一步,酷刑不仅把没有自由的个体轻易推上道德本质化的刑场,也很轻易地变成专制制度寻求和获取快乐的途径,欲望(涉及权力等级的构建和权力形态的行为)由此再次从酷刑中产生,我们可以从酷刑史中找到全部专制政权的变态欲望与经验。在这种变态欲望与经验作为独立领域以后,等级权力经由特殊性的文化秩序潜入民间,变成民间记忆的一部分。酷刑在任意地制造刑罚对象和残酷地摧毁肉体的两重禁忌中,使人们对权力产生极大的恐惧,这一恐惧本身与独断的政治行为、君权的恣意妄为、官僚的骄横贪婪、宗教迷信、知识者的萎葸以及民间的愚昧的幻觉搅和于一处,如果说刑罚是制度的必然逻辑,则酷刑是王权专制的当然结果。
刽子手的“艺术”表现在他们执行酷刑的行为方式中,而且在执行酷刑时,他们的称谓是女性化(被称为姥姥、姨等)的,这表明他的个体人格隶属于巫术化的原始奴役人格,这种人格在被权力等级遮蔽的同时作为专制王权的“阴”性器具物品对比突出了权力者的阳性一极。除了显性的国家巫术外,还有另一种民间巫术的变形化也对君权起着精神支持基础作用。换句话说,国家精神不仅体现在国家巫术之上,还体现在对民间巫术的挪用之上。
这一挪用经过了技术的处理,首先就是仪式化:
“姥姥磕头,前额碰到青砖地面上,咚咚地响。我们跟着姥姥磕头,前额碰到青砖地面上,咚咚地响。蜡烛光影里,祖师爷的脸油汪汪地红,我们各磕了九个头,跟着姥姥站起来,退后三步。二姨跑到外边去,端进来一个青瓷的钵子。小姨跑到外面去,倒提进来一只黑冠子的公鸡,血脉最旺,我们每次执大刑,都要买一只这样的公鸡来杀,一会儿,血流尽,将血献在供桌上,两个师弟磕了头,弓着腰退到后边去。我随着姥姥,趋前,下跪,磕头三个,学着姥姥的样子,伸出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从青瓷钵子里蘸了鸡血,一道道地,戏子化妆一样的往脸上抹……。”——《凤头部:赵甲狂言》〔11〕
通常,仪式性驱邪是行业中的共同信仰,它所具有的巫术力量往往蕴含于一定的仪式中。这种仪式在《檀香刑》中成了刽子手“牺牲”礼的表演,也正如赵甲所说:“执刑杀人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是国家的法(第二章:《赵甲狂言》)”。〔12〕以人(肉体)为刑的对象的牺牲行为,持续为刽子手的巫术宗教化行为,这种“执刑”的关系保证了刽子手作为酷刑的施与者与国家之间的暗喻关系——通过对神灵世界的模拟,通过对远古的行为者(皋陶)的祭祀而达成了“天意”行为:这一行为将刽子手的禁忌变成天意的补偿,他们成了制度的鲜活的精神。
三、民间的革命心理
在受刑过程里,孙丙不具有清醒的个体意识,莫言用他特有的叙事方式,使得这一昏睡的个体意识得以复苏,使一个民间艺人遭受酷刑的行为本身成为戏曲片段中的一种井井有条、郑重其事的悲哀叙事,它使莫言回到了古典情怀,戏曲由此成了莫言回忆高密乡的民间秘史的“情绪几何学”。
也是出于民间的处境:孙丙他是真实的、活生生的,同时又是种种事件的汇合点。他在自己的生存和周围的关系中引出了生存的欲望,他是无奈而绝望的欲望,他对自己亲人的情感,对友人、对戏曲本身的兴趣,又引出了深切的绝望中更强烈的生存感,这种关怀不仅表现在他的戏曲语言中,也表现在他复杂的欲望形式里(他甚至因此而虚荣、可悲,显得因软弱和精神胜利而来的反抗的空洞)。
受刑者孙丙的存在是两重性的显证。他带着民间疾病的蔓延性,同时也带有荒诞的激情。他试图在反抗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但他的反抗无法找到一个足够有效的方式和价值,这就使得他求助于历代造反者的神秘化仪式。孙丙的造反,在第二部分《猪肚部》写得十分成功,它浓缩并象征着长期以来中国民间这一心理的演绎历程。莫言以夸张的方式揭示了真正的反抗主题的面目,在那些“梁山好汉们的年月”,在我们熟悉的造反者身上有许多复杂的精神气质。
“二十天后的一个下午,孙丙穿着白袍,披着银甲,背插着六面银色令旗,头戴着银盔,盔上簇着一朵拳大的红缨,脸抹成朱砂红,眉描成倒剑锋,足蹬厚底靴,手提枣木棍,一步三摇,回到了马桑镇。他的身后,紧跟着两足虎将,一个身材玲珑、腿轻脚快、腰扎着虎头裙、头戴金箍圈、手提如意棒、尖声嘶叫着,活蹦乱跳着,恰似那齐天大圣孙悟空;另一位袒着大肚皮,披着黑直裰,头顶卢帽,倒拖着倒粪耙,不用说就是天蓬元帅猪悟能。”〔13〕
造反者以戏子的扮相出现,在戏曲舞台上我们常能看见这样的扮相,孙丙把反抗本身形式化后,一种有趣的场面效果产生了,我们宁愿称孙丙为戏曲家,因为在他身上的这些事是如此真实而又难以想象。这一类细节,是莫言的匠心,通过这一种扮相与行径,莫言写活了民间反抗的精神内涵。来自生活的困厄和政治权力的挤压以及中国民间宗教的杂乱的仪式和迷信心理,使民间的反抗从神秘的心理定势出发,把天灾人祸和社会危机引向了“请神上法”的造反行为。由于制度性民间正义的缺乏,宗法和专制横行的社会现实加重了民间固有的“历世造劫”意识,这种仪式成为一种笼罩着人们生活的浓密阴影,在极度的恐慌之下,把民间纳入了神秘力量操纵的怪圈。孙丙的反抗形式是如此真实,它正是中国民间迷信的宗教心理,迷狂的信仰方式的产物。孙丙把这种神秘荒诞的形式带入了戏曲性场面。头顶着一张黑色的小猫皮,绘画了一个小猫的四喜唱的正是民间对待这种秘密仪式的态度。它使孙丙的戏曲化“表演中”成为悲怆的、严肃的悲剧:个体生命丧失了话语权,被剥夺了想象力,也被取消了摆脱被愚弄的权利,在这样的国度里,整个民间在虚设的仪式化的抗争中奄奄一息。
“有孙丙,不平凡,曹州学来了义和拳,搬来了孙猪两大仙,扒铁路,杀汉奸,驱逐洋鬼保平安。晚上演习义和拳,地点就是桥头边,男女老幼都去看,人人都学义和拳,学了义和拳,枪刀不入体,益寿又延年。学了义和拳,四海皆兄弟,吃饭不要钱。学了义和拳,皇上要招安,一旦招了安,个个做大官,封妻又荫子,分粮又分田……”——第八章:《神坛》〔14〕
残酷只有面对懦怯才能有所作为,酷刑的对象只能是懦怯,以神秘的仪式出现在街头巷尾、城镇乡村。造反者面对酷刑毫无武器,只能拿起各种神秘荒诞的形式化工具,在精神上压倒对手,弥补物质上的劣势。毫无话语权力的民间反抗者面对强大的国家神话,也借用或自创了繁复的自我神话,成百上千的平民百姓齐集于义和团的神坛前,“念符念咒”“烧香叩头,求神附体”,以获得超自然的神力。荒诞的形式和语言,属于隐秘的民间社会的心理,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众多神仙鬼怪、传说人物、小说人物符咒法术的蜂拥而至,请各路神仙来下凡显灵,神灵附体,这是民间蒙昧在生存危机时的大爆发,企图“仗此神威以寒敌胆”。
民间虚构的想象力在范围和精神层次上明显地比成体系的国家神话零乱、卑琐得多,但言词诡秘,怪诞奇特的“坛谕”还是轻易撩拔起千家万户固有的民间想象。贫困的民间只剩下这些反抗用的工具,肉体上无谓的牺牲无节制地蔓延,王权毁坏了他们的精神生存条件以后,民间只有操起代价昂贵的,在危险的想象中获得的武器,面对神话了的庙堂秩序和刽子手,面对民间自身的卑微和怯懦,只有自我神话这样一种盛行于原始巫术中的手段可用。自我神话的诸多领域,如延年益寿、兄弟义气、造反、招安、封妻荫子等,与庙堂理念混杂,和阿Q革命所想的“财产和女人”一样,是民间的革命心理学。它见证了莫言对民间礼俗的关怀,也表现了莫言对待民间社会种种仪式化的精神生活的复杂的心态。在可能的情况下,它成为王朝更替的最重要的手段,在通常情况下,是民间在信仰世界典型的自慰行为,对这种历史,写实和虚构都难以达到显示民间自我神话的效果,《檀香刑》则是把这一秘密心理以可见的、神话式的、外似滑稽可笑、内含悲悯的方式揭示出来。
在漫长的岁月中,民间记忆与民间心理的形成仍然是个谜,人的死亡在中国人的心中引起的恐惧因为轮回观而有所减弱。彼岸世界的鬼神氛围也消除了人离开世界的紧张,但“轮回”并不能兼容并超越一切。在某些政治酷烈的时代(例如魏晋),由于随意的杀戮,精神的压力变成可怕的事实,肉体的存在变得越来越不可忍受,现实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在这样的窒息之中轮回被从生命意志上取消了。因为人活着时,所承受的恐惧和分裂已经远远大于世界造物的隐秘意图。
不过对于莫言笔下的孙丙而言,这些都不重要了,他已经借助奇怪的途径,感受到命运的目的。当那长长的木楔子钉入他的躯体时,他也会痛苦凄厉地尖叫。痛苦没有从感觉中消失,但在疼痛难忍的同时,他也自得地想到他肉体的一部分躺在民间说唱的场面中,这是一种大的恩惠,只有接受这样的恩惠,采取这样的姿态,他才可能把大悲大喜的体验用戏曲的方式去展示,他才能在临死前,吐出带血的字句“戏……演完了……”。这是把身躯当作命运游戏的骰子,在如此的赌局中,他置身于包罗万象永恒轮转的内部。莫言从始至终也不打算把孙丙的造反,变成成功的帝王哲学,那已经不属于民间记忆,而是属于庙堂秩序的虚构了,一个无力的民间当然也只能在孙丙这一民间艺人身上才能再现他们反抗的久违的欢宴与仪式。
莫言作为高密乡记忆的收集者,颇费了苦心。因为他的标准不是农民起义领袖的体面,这种体面一旦越过细屑的事物都将变成空谈的历史观,他的标准立足于民间的鉴赏力。如果作家截取的是事先稳定的,已经经过价值观的处理的场景,就不可能再现一个复杂的事实,作为艺术的开端,它通常不可能以虚构的客观性的句子碎片、单个词、单个语调来完整地再现记忆世界,因为见解可以和个人分离而融入营造的事实中。记忆的重点是民间的秘密,从孙丙身上,对他的自身事件的思考必须纳入莫言设计的戏曲外衣。他履行小说家的职责,在小说中隐姓埋名,利用“倒箱式”的记忆,用狂欢的语句(叠句、戏曲句、异构同义句、非生活化的言语等)把我们安排在受幻想支配的舞台之下。使得我们能够轻松地面对酷刑,我们可以暂时地避开人性的黑暗巷道,部分地远离那些深深浸染着我们的恐惧和黑暗。
注释:
〔1〕这里的“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的边缘区域。陈思和先生指出:“与权力中心相对的一端为民间,如果以金字塔形来描绘这两者关系,那底层的一面就是民间,它与塔尖之间不仅包容了多层次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且塔底部分也涵盖了塔尖部分,故而民间也包容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民间自身含有的藏污纳垢、有容乃大的特点。”(参见陈思和:《民间形态与现代都市文化》,《思和文存(第二卷)·文学史理论新探》,合肥: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3年,第37页)。
〔2〕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事》,陈思和:《思和文存(第二卷)·文学史理论新探》,合肥: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3年。
〔3〕〔4〕〔5〕〔6〕〔7〕〔8〕〔9〕〔10〕〔11〕〔12〕〔13〕〔14〕莫言:《檀香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61、235、271、271、321、31、29、38、31、32、130、131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
缪丽芳,文学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