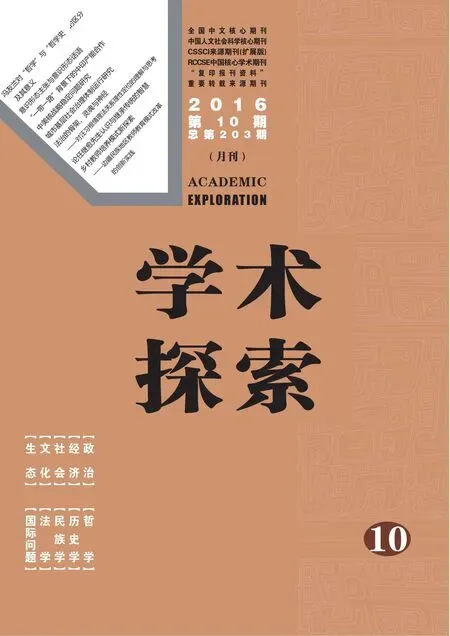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研究
崔运武,柯尊清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研究
崔运武,柯尊清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有序推进的体制保障和重要依托,也是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是治理体制服务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功能输出过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需要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阶段性地配置政府职能,实现治理体制的纵向层次整合,并建构起适合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规则。
城市基层社会;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运行
基层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小基层”“大舞台”的战略位置。“社会凝聚力不能在民族(或国家)层面运作的国家来保证,但可以通过能生产忠诚感、社区认同与归属感的地方政府来维持”。[1](P92)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来展开并以有序和谐的基层社会为依托。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景下,“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是一个全面的转型,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协奏与融合,而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无疑是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不适应社会需求是社会治理问题频发的症结所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是社会体制外在的实践形式,是社会治理体制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功能输出过程。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创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而制度空间则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发挥作用的场域和依托。“制度空间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作用中发生联系,共同构建起来的网络空间”。[2](P61)制度空间是一个社会建构物,社会建构性是其固有属性,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在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各个制度间、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制度空间形成的重要变量。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预设
党和政府从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以及社会治理的需求共同形塑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预设。制度空间为制度的产生和功能发挥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约束。“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提出和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与居委会之间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与“协助”关系,街居制向社区制的演进和转变,这些从规则程序、组织环境和制度生态三个方面建构起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预设。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制度规引、规则程序和制度环境,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需要在制度空间的预设中形成阶段性的具体目标,并基于制度条件、制度环境而开展治理活动。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行社区制,社区制的产生和运行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空间中实现。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空间中的街居制与社区制
现阶段,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离制度空间的预设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治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仍然不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功能仍然弱化,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离公众的需求还有较大距离。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就要在街居制的制度条件下完善社区制,将社区制建设嵌入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体制中,实现政府与城市基层社会的同构与互动。
街居制是指在城市基层社会形成的由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共同实施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单位制逐步解体,单位制作用的制度空间急剧压缩,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职能落到了街居制上。传统的街居制只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辅助性制度,负责对城市基层社会单位之外的闲散人员、退休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等进行管理,街居制中的人员都是无法进入单位的年龄较高的边缘群体,街居制在组织建设、权威资源、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政社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中,城市基层政府通过组织结构条块中的“条”将职能下放到街道层面。街道办事处只是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则作为群众自治性组织,街居制在承接单位制转移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职能转移方面,职能超载的问题突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街居制在更大的制度空间中发挥作用,而传统的街居制显然无力予以承担,推进传统街居制改革势在必行,社区制建设呼之欲出。
社区制是建立在城市社区基础上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平台搭建、体制建构、运行规则的社会性建构。传统的街居制无法承担单位制逐步解体以及政府职能转变所转移和剥离出来的职能,按照现代公共管理理念,政府不可能通过扩大政府自身职能和机构来予以承担,社区制建设应运而生。从区域上看,在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下,制度空间是单位内部和居于辅助地位的街居辖区;而在社区制下,制度空间在单位体制中收缩,在城市社区内则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和建构。社区制是对传统街居制的创新和超越,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任务,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社区制是在街居制的体制框架内展开的体制创新实践,街居制的运行对社区制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是,在社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建构由单一主体建构向多元主体建构转型;三是,社区制对街居制的超越体现在理念上的公共治理取向,治理主体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运行机制上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职能阶段性配置
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质是政府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其改革和创新的取向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公共治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建设就是要通过培育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扩大公民参与,建构和完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体制,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自治。政府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主导,居于“元治理”地位,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输出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中的重要构件。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发挥不平衡,在区域间、同一地区的不同社区间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单一主体建构阶段、单一主体建构向多元主体建构过渡阶段和多元主体建构阶段,在各地区均有现实标本,各个阶段共时态并将持续较长时间。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职能配置应该坚持阶段性的思想。
(一)单一主体建构阶段
我国城市社区的建立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非原生性”“非诱致性”演进的过程。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兼具政治、经济与社会功能的单位基本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的分配,呈现单位办社会和单位社区化的特点,与此同时,街居制则处于辅助地位,负责对无法纳入单位制的人员进行管理,发挥弥补单位制不足的辅助性功能。随着单位制逐渐走向解体,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势在必行。“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过程中,数量日增的“社会人”以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提高,而高度依附于政府的初创期的社区无法承担起相应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基层社会存在的大量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又在政府职能的范畴内,所以,政府需要为城市社区建设提供必需的软硬件条件。
在单一主体建构阶段,政府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和市场发育不足,在城市基层公共事务管理中无力参与。从政府的角度看,主要解决的是政府在城市社区建立及初创时期的制度供给以及其他软硬件提供的问题;从社区的角度看,社区的建立以及初期的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需要政府发挥引导、推动作用。具体而言,政府职能应该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要发挥政府政治权威作用,参与城市社区范围的规划、社区治理组织机构的建设,组织社区居委会的民主选举等;二是,要制定和执行适合于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三是,政府为社区建立及其治理运行提供必要的经费、办公场所等硬件条件;四是,提供社区基础性、保障性、民生性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二)过渡阶段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由单一主体建构向多元主体建构的过渡阶段,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建设的任务在于充分、有效地发挥社区管理中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功能,解决社区管理平台、组织、机制的完善问题,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提高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性。具体而言,城市社区治理的单一主体建构向多元主体建构的过渡阶段,政府职能配置的主要领域:一是,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权责划分,即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为社区居委会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提供制度支持,政府“主导”而不“包办”、“监督”而不“控制”;建立和完善社区工作准入制,社区居委会承担政府分派工作、协助政府开展相关活动的同时有权要求相应的财权,坚持“费随事转、权随责走”原则。二是,街道党工委领导社区党组织建设,保证社区治理坚持和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三是,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支持互益性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群体维权组织等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工作。四是,通过社区民主建设,培育社区公民精神,鼓励、引导和支持公众参与,着力提高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从社区居民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出发,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以及其扶持性政策,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实现社区的社会管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五是,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培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将社区治理法治化贯穿于全过程和各环节。
(三)多元主体建构阶段
多元主体建构阶段指的是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治理阶段,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共治阶段。社区自治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归宿,公共治理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和基本路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建构阶段的目标是:政府行政干预逐步退出社区而专司必需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社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流畅衔接,社区社会资本丰厚,邻里关系和谐,社区由“冷冰冰的钢筋混凝土睡城”转变成“其乐融融的共有家园”。政府的职能配置是通过社区法治化等途径,实现政府治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与协同,政府培育社区自治力量,达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目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建构阶段的政府职能配置:一是,政府职能范围和履行方式法治化,社区居委会切实履行发挥自治功能,业主委员会发挥集体维权作用;二是,进一步培育公民社会和社会资本,社区互益性组织和志愿服务组织崛起;三是,夯实社区治理的物质基础,社区经济实体发展良好;四是,完善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合作参与格局,建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畅通的沟通渠道,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和密切的伙伴关系,政府“协调”而不“干扰”、“淡出”而不“撒手”,各个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社区和谐稳定。
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层次及其整合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系统,而纵向的层次结构则是多维立体的重要一维。从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的逻辑来看,政府社会治理中权力是依循制度供给——机制设计——操作实务的基本路径来行使的。自上而下的层级节制体制“非常适合于命令下达,却对资讯上传这种良性流动的必要性缺乏敏感”。[3](P198)实现制度供给层、机制设计层和操作实务层之间的整合是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的重要任务。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层次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供给层居于城市基层社会体制的内核,塑造着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也形塑和导引着社会治理的机制设计层。机制的形成源于体制和制度的规定性和执行性,社会治理机制设计层是社会治理制度供给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反映。作为社会治理制度供给的延伸,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机制设计是社会治理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走向实践的桥梁和纽带。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操作实务层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治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操作化问题,即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转化为现实的问题,属于社会治理体制的微观范畴,以社会治理任务为客体指向。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操作实务层次,通过路径、手段、方法、方式的选择来实现治理目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治理工具的评估和选择是核心问题。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层次整合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公共需求、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在基层社会,但是,治理体制的建设及运行则需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共同发力,这就需要实现各层次的整合与联动。制度供给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了灵魂、精神和价值,机制设计层搭建起骨骼和框架,操作实务层提供了肌肉和血液,三个层次整合起来实现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共建与互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制度供给层、机制设计层和操作实务层的整合,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各个层次之间存在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之间的导引和塑造,下一层级对上一层级的践行和反馈。制度供给层形成了机制设计层的制度环境保障,机制设计层则对供给层的践行;机制设计层对操作实务层的机制承载,操作实务层对机制设计层的运行支撑。也正是由于上下层级之间的导引和践行、塑造和反馈,具有层次结构的社会治理体制才能成为一个圆融的、运行流畅的体系。在治理体制中,制度供给层、机制设计层和操作实务层的基本属性、目标取向、主要任务和对象选择等都是不同的,所以在社会治理中它们所发挥的功能也就各异。要让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能够有效运行,就要明确各个层次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任务和功能,并建立和完善三个层次之间的导引和反馈机制,实现不同层次之间的任务合理划分、功能互补整合、运行协作联动。
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的规则建构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规则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在城市基层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共同建构起来并普遍遵循的调节多元主体行为、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和准则。运行规则建构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发挥其功能并作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机制,是实现政府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同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黏合剂,有利于弥合行政性与社会性之间、管理与自治之间的张力,消除多元主体间的歧见,在多元中谋共识、在多样中求包容,化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一)理念层面的互认
要实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多元主体间在理念和意识场面的相互认可是前提。多元主体间的互认,一方面表现为成员对其所属组织在情感和意识层面的归属感,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其他的社会治理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认同。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议题设置、体制建构、规则形成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规则建构的理念层面的互认主要还是政府及其公务员对于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以及社区市场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的认可。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居委会充当政府的“腿”和“脚”,职能超载、负担过重,行政化问题突出,自治功能被弱化,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低,社区公民参与意识和水平不高等问题,都与政府社会治理理念有密切的关系。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影响,政府及其公务员在意识层面将自身视作基层社会的管理者、造福者,一方面受全能型政府模式影响,夸大了政府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对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及其相应的功能认识不到位。要实现建构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治理体制,需要首先从理念层面实现政府与社会二者间的互认:一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并不是对政府能力的消解,而是政府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更加丰富了;二是,政府要能够调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作关系,需要以承认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行为选择为前提。
(二)利益层面的互利
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必须扎根于市场经济体制当中,才能获得与社会治理体系内外环境的平衡,以达到其预期的目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经济环境。正如包国宪、霍春龙所言:“市场经济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市场制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即自主的、在讨价还价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4](P81)从利益关系方面看,良好的社会信任应该建立在互益互惠原则上,互益互惠原则的形成需要社会规范。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看来,社会规范减小了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而社会规范又由基于相同价值交换的均衡的互惠以及非均衡的、持续进行的、产生共同期望的普遍化的互惠构成。从多元治理主体间关系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在利益层面的互利规则就是要能够让社会治理中各履其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凡有效履行其职责的社会治理主体,其合理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就必然会得到应有的保障,出现利益矛盾时能够有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予以协调。
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的经济基础看,当前的任务是建构和完善互益型社会。互益型社会,以利益为基础,以公民权利保障为主要途径,是对传统社会治理中被动式、运动式管理模式以及“维稳”思维模式的超越,意在通过公民权利的保障来实现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建设互益型社会,以支持基层社会治理体制运行,是由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呈现的新特点、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以及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互益型社会以基于利益的合作机制为基础,其基本特点体现在:其一,公民权利的保障是公民切身利益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互益型社会首先要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明确,并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中予以保障,如此才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加强和改进社会建设,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其二,就公民之间的关系看,互益性要求,某一主体利益的实现不以另一主体利益的减少或损害为条件,即互益型社会追求帕累托改进(Pareto Optimality),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帕累托改进,既是效率的体现,也是公平原则的要求;其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规则也是因为自身具有的工具理性而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互益互惠规则能够赢得更多的公民认同、参与和支持,进而强化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三)社会层面的互信
“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博弈”,[5](P33)信任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行为,包含了可预期性、采取的行动及相应的责任。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社会成员间的互相信任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互信规则建构的基础。信任存在于公民个体之间、公民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基于社区居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信任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信任的形成和巩固并非盲目性的,是个体基于对特定的个体、组织的既有的特质而做出的判断,信任建立的过程是通过一点一滴缓慢形成,而信任的丢失则在转瞬间。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的社会信任是“弱社会、强私人”,组织体制运行则更加依赖于非私人化的或间接的信任,并非私人间的直接信任。社会信任以及互惠规范,需要通过倡导、教育、持续的社会合作等社会化手段,也需要通过惩罚性的强制手段。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需要将公民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公证体系,培育和强化公民精神。只有信任触发和维持各合作主体的合作动机和意愿,社会信任也才能够成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基础。从社会环境对于社会行为范式、社会行为主体的影响看,社会规范、互益互惠原则、社会信任等都必须在社会资本丰厚、公民社会发达、公民社会组织化水平高的背景下才能得以培育和发展。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是城市基层社会中的互信规则的重要源泉。当社会自我调节机制无法通过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形成社会成员间的互信时,政府的介入就成为必需。政府可以通过个人诚信档案、宣传教育、行政执法等方式予以介入。政府通过自身的法制化、民主化、透明化建设、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而建构起来的合法性则是获得公信力的关键。
(四)责任层面的共担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行动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活动,多元主体也因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共担规则实际上是对多元主体履职的约束性要求,是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重要保障。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关系的建构,意味着政府一元化管理模式下政府责任的转移和变迁。责任转移是因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社会服务职能而相应地承担责任;责任的变迁则体现在要让社会组织、公民承担其所负责事权的相应责任,政府也因此而负有监督、协商的责任。责任共担有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基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明确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的职能配置,进而合理划分政府事权与社区事权,以明确多元主体的职责;二是,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关系建构中,合理转移和调整责任归属,政府转移社会职能的同时要转移相应的责任,社区工作准入的同时需要配置相应的权责,政府退出社会服务领域需要承担起新的监督、协调之责;三是,各多元主体的自律和主体间的互律,各主体需要强化自律性以及对其他主体的监督;四是,建构和完善责任共担机制中的激励机制和冲突解决机制,协调责任共担中的矛盾冲突。
[1]布赖恩·特纳.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刘迟.基层社区组织权威生成的制度空间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09.
[3]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胡国成,赵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何增科,陈雪莲.政府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5]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左安嵩〕
On the Operation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
CUI Yun-wu, KE Zun-q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650091, Yunnan, China)
Urba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 i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the important support of the urba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 is also the focal point fo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urba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e operation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 is the function output process of the governance institution serving the urba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objectiv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we should take the institution space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to account, conduct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periodically, make sure the longitudinal integr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levels and construct rules for cooperation and co- -governance of diverse subjects.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soci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 soci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 operation
云南省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资助
崔运武(1959— ),男,广西容县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C912.81
A
1006-723X(2016)10-0064-06
柯尊清(1989— ),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