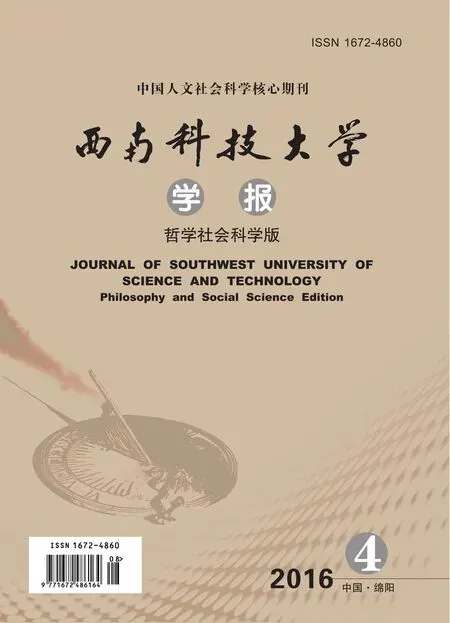《欲望号街车》中的角色与作者人格辨析
唐亦珊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长沙 410205)
《欲望号街车》中的角色与作者人格辨析
唐亦珊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田纳西·威廉姆斯在《欲望号街车》中将自己的三重人格投射成3个主要角色。作者的生活体验和人格之间的矛盾浓缩成了作品中的情节和冲突。作品结尾的角色人物命运安排,又与作者在作品发布之后的人生境遇产生了重合。剧本情节与现实之间的多重映照体现了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弗洛伊德;人格投射;潘乔·罗德里格斯;弗兰克·梅洛
田纳西·威廉姆斯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戏剧家之一,与尤金·奥尼尔和阿瑟·米勒并称为20世纪美国戏剧界的三大巨匠[1]5。这一时期,剧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使美国戏剧逐步摆脱了欧洲戏剧的影响,更加民族化和现代化。田纳西·威廉姆斯的著名戏剧包括《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后两者更是分别在1948年和1955年为田纳西·威廉姆斯赢得了普利策戏剧奖的殊荣。
《欲望号街车》作为田纳西·威廉姆斯最广为人知的短篇戏剧,为其一举囊括了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奖、普利策奖和道诺森奖。虽然全剧仅有11幕,但自1947年在百老汇舞台上演以来,一直吸引着各方评论家孜孜不倦地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角度进行诠释与分析。田纳西·威廉姆斯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欲望号街车》的意义在于表现现代社会里各式的野蛮势力强奸了那些温柔、敏感而优雅的人”[2]390。因此,大多数评论家将《欲望号街车》解读为美国内战南方失利之后,以女主角布兰琪为代表的南方淑女们因为无法适应新世界的规律而面临着悲剧的命运,并以此反映旧南方文明的陷落和新兴工业文明的兴起。研究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戏剧历史的专家费利西亚·伦得瑞,曾逐幕对比布兰琪和斯坦利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两方势力的消长与升沉。[3]45剧中布兰琪的悲剧命运,也引发了评论家们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的热潮,其被认为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和悲剧人物。与此同时,由于作者田纳西·威廉姆斯本人同性恋的特殊身份,亦引起一些评论家从这一视觉对《欲望号街车》给予解读。赞同田纳西·威廉姆斯的评论家认为其创造的新式、激进的戏剧形式,是对霸权主义下冷战时期憎恶同性恋行为的挑战,具有先进的政治意识;[4]112反对田纳西的评论家则认为,田纳西·威廉姆斯是一名装腔作势的同性恋者,根本没有资格来写作异性恋的戏剧,并批判了他本人奢华放荡的生活作风。
田纳西本人曾说:“我从我的真实生活中塑造剧本中的人物,我无法塑造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5]153费利西亚·伦得瑞更指出:“给大家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首先是创作这部伟大作品的作家的神秘感,然后才是作品本身的神秘感。”[3]48笔者则认为,只有更进一步挖掘田纳西·威廉姆斯本人的现实生活,对他的人格进行心理学层面的剖析,才能真正理解《欲望号街车》这部作品。基于对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成长历程和生活经历的分析,笔者认为,《欲望号街车》实则是作者本身真实生活的反映,剧中的许多角色场景均能在作者生活中找到原型;《欲望号街车》中的主角布兰琪、斯黛拉和斯坦利与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映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技法。
一、作者生活与剧中角色特征的对应
(一)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成长环境与布兰琪的出身
田纳西·威廉姆斯1911年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的哥伦布市,其母亲出身于南方贵族家庭,奉行南方传统道德下的清教主义,优雅的同时也有着敏感的个性。田纳西遵循南方传统称他的母亲为“爱德维娜小姐” (Miss Edwina),她在儿子心中的形象是“一名失落的南方公主”[6]151。田纳西的父亲,常年在外、四处兜售鞋子。他为人现实,且奉行享乐主义,酗酒成性,脾气暴躁。田纳西在身为牧师的外祖父家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之后随父亲工作调动搬迁至北方工业城市圣路易斯。从宁静的南方田园生活到喧嚣的北方现代化城市,环境的巨大反差使年幼的田纳西无法适应新生活:“在南方我们从未意识到我们比他人贫穷,但是在圣路易斯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富人和穷人,而我们大多数属于穷人……如果我不贫穷的话,也许我不会产生这种僧恨,而这种憎恨已演化成一种反抗,这种反抗成了我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22
在《欲望号街车》中,女主角布兰琪同样出生于美国南方贵族家庭,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密西西比州的贝拉里夫庄园。她符合南方淑女的标准形象,一出场便是“穿着一身讲究的白色裙装,外罩一件轻软的白色马甲,戴着珍珠项链和耳环,还有白色手套和帽子,看起来像是到新奥尔良的花园区来参加一次夏日茶会或是鸡尾酒会”[8]8。同田纳西被迫搬家不同,布兰琪是直接遭遇了摧毁美国旧南方的美国内战,走投无路不得不前往新兴工业城市新奥尔良,以寻求妹妹斯黛拉的帮助。到达新奥尔良后,布兰琪同样无法接受眼前的景象。她“看看手里的纸条,然后看看这幢楼房,再看看手里的纸条,再看看楼房,一脸难以置信的震惊。”[8]9在妹妹斯黛拉的房间里,她“姿态非常僵硬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微微耸动肩膀,两条腿紧贴在一起,双手紧紧抓住皮包”, 并自言自语道:“我一定得把持住自己”。[8]13从这样的描写不难看出,布兰琪在面对截然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生活环境时内心的惶恐和不安。这也正是作者田纳西·威廉姆斯初到圣路易斯时心境的重现。
生活环境的巨变使田纳西无从适应,在学校他更因为南方口音而备受排挤,这使他更加怀念幼年时期美好平静的南方生活。他曾在之后的采访中表示:“我还记得儿时在南方的生活经历,南方文化充满优美、典雅……这是根植于文化中的东西……南方社会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北方不同,我为目前的状况感到十分遗憾。”[9]96在田纳西之后的创作生涯中,对南方生活的追忆也一直是他作品的一大主题,这足以证明他对曾经有过的南方生活深深的眷恋和不舍。而布兰琪,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辉煌的过去。她时不时提起年轻时候的几位仰慕者,提醒斯黛拉“不可能把咱们的出身教养全部忘记”[8]98。她甚至逃避现实,只愿意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和幻梦中——“我可不想脚踏实地。我要魔法巫术!”[8]172
(二)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性取向与布兰琪的被排斥
同性恋身份,一直让田纳西·威廉姆斯饱受争议。他在1970年一次电视访谈中,首次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之后更表示:“我现在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完全是我自己的,并没有受到国内外任何剧作家或者其他戏剧学派的影响,我的作品一直是用任何一种恰当的形式表达我的生存体验。”[10]77田纳西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正是美国社会同性恋恐惧症日益加剧的时期,随后的“麦卡锡主义”更是将反对同性恋推向了极端——“冷战和反共浪潮兴起也把同性恋卷了进去。男女同性恋从言辞攻击的靶子迅速上升为政策和行动的目标,同性恋变成了正在污染全国的流行病,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11]149,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同性恋者自身也深受同性恋是“不道德、无权和病态的”思想的影响。[12]40因此,田纳西的性取向使他愈发焦虑和迷失、无法认同自己的身份,故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于是他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局外人”(outsider)[6]151。
在《欲望号街车》中,作者笔下的布兰琪与斯黛拉位于新奥尔良市的家是格格不入的。这里的“房屋构造大都是白色,日晒雨淋成了一色的灰,大都带有摇摇晃晃的外部楼梯……有道褪色的白漆楼梯通两户人家的门口”[8]5,而布兰琪过去的住处“好大一片地方,都是白柱子”[8]12。她认为斯黛拉的住所是“在最可怕的恶梦里我也从来,从来都想象不到”[8]15。她随身带着一个大衣物箱,里面有“纯金的衣裙……狐狸皮毛,足有半英里长!毛茸茸、雪雪白的毛皮”[8]41,衣箱的小抽屉里还有“成串的珍珠……好多串赤金的镯子!”[8]41在如此粗陋、混乱的市井住处,布兰琪却对米奇说“我受不了一句粗话或是一个粗俗的举动”[8]71;她还会在斯黛拉的房间里伴随着收音机的歌声,带着米奇“和着华尔兹的舞曲翩翩起舞”[8]74。布兰琪的这一切行为举止,完全违背了当时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她同斯坦利以及他的朋友和邻居们,甚至斯黛拉都是大相径庭的。他们粗俗、市井,甚至说不了标准的英语;他们的娱乐方式是打扑克、喝得烂醉。而布兰琪却试图在这样的环境下,保留以往的生活习惯——打扮优雅、看戏跳舞,这无疑更加深了她的焦虑和迷茫。
(三)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爱情倾向与斯坦利的形象特征
剧中的男主角斯坦利,是典型的未受教育、崇尚暴力的粗俗现实主义者。他在剧中的首次出场是“大大咧咧地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8]6,表明着他工人阶级的身份。随后,作者对他的形象描写是“身体强壮结实,他生命中那种动物的快乐在他所有的动作和态度中都表现出来。”[8]29斯坦利的“动物性”表现在他的简单粗暴。他生活的全部便是“对待哥们儿的热心,对粗俗笑话的欣赏,对美酒佳肴和体育比赛的热爱,他的汽车,他的收音机……”[8]30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用语言暴力和拳头,在斯黛拉以布兰琪需要换衣服为由要求他出去时,斯坦利的回应是“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发号施令了?”[8]43跟斯黛拉发生冲突时,他可以不顾斯黛拉已有身孕,“朝斯黛拉冲过去……传出殴打的声音……有样什么东西摔到地上打碎了”[8]75。 斯坦利的动物性更表现在他的享乐主义和现实主义上,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布兰琪说:“舒服是我的不二箴言。”[8]32对此,作者给予的定义是,斯坦利带有一种“有种男人”的俗艳色彩。[8]29
现实生活中,田纳西·威廉姆斯于1945年邂逅了身为酒店员工的潘乔·罗德里格斯,并被他深深地吸引,开始了一段为期两年的恋情。田纳西的好友、电影《欲望号街车》的导演伊利亚·卡赞说:“如果田纳西是布兰琪的话,潘乔就是斯坦利。”[6]151潘乔是“一个粗暴的年轻墨西哥男人”[6]146,他跟斯坦利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如果厌恶什么的话,就要破坏、毁灭他。”[5]154卡赞记录了一次田纳西和潘乔发生冲突的全过程:潘乔“用西班牙语咒骂,威胁他说要杀人,打碎了房间里的花瓶,毁掉了装饰灯。”[6]151而田纳西面对潘乔的发怒却并不生气,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异议。事实上,当他同卡赞谈起这次事件时,他甚至表现出了对潘乔的崇拜。[6]151
在《欲望号街车》中,布兰琪看到斯坦利的第一眼,“就对自己说,这个人就是我的刽子手,这个人会毁了我。”[9]132斯坦利最终的确充当了布兰琪的毁灭者角色,但布兰琪也不可抑制地被他身上“彻头彻尾的兽性”[9]53吸引着。布兰琪会一边在布帘后换衣服,一边邀请斯坦利到布帘后面来请他帮忙扣背后的纽扣。她跟斯坦利调情,“拿自己的香水往自己身上喷了喷,然后开玩笑地往他身上喷。”[9]49她还毫不避讳地当面对斯坦利说:“你简单、直率又诚实,我想还多少有点儿粗野”,“我妹妹嫁了个男人”[9]44。她也会对斯黛拉说:“没准儿他正是我们需要用来传宗接代的男人。”[9]53
现实生活中的田纳西在与潘乔交往的过程中,当潘乔大闹一番负气出走又返回时,田纳西非但不生气,还会欣喜地迎接他,毫不在意他之前的暴行,看起来也没有丝毫的“恐惧、沮丧和不赞同他的行为”[6]151,甚至表现得十分渴望见到潘乔。潘乔的暴行让田纳西有着莫名的“兴奋感”[6]151。同时,田纳西已经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也认为持续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现有的生活将被毁灭,但又无法抗拒潘乔身上的、他自身所不具备的特性带来的刺激。卡赞这样说到:“我一直试图将布兰琪和田纳西联系起来,布兰琪被那个最终将她摧毁的男人吸引着,田纳西似乎在试图告诉我们他的真实生活。”[6]152潘乔是“更粗野的斯坦利”[6]152,这个男人身上的暴力因子,总是游离于危险边缘的特质,在让田纳西感到害怕的同时也深深吸引着他。卡赞回忆到,在电影《欲望号街车》彩排时,其中的一幕是斯黛拉试图纠正斯坦利的餐桌礼仪,斯坦利却将桌上的盘子全部扫到地上,教育斯黛拉应该好好地同男人说话。田纳西当时十分激动,“我怀疑他根本不认为斯坦利行为粗野,而是深深被这种行为吸引”。[6]152
(四)田纳西·威廉姆斯的内心需求与斯黛拉的形象特征
剧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斯黛拉和布兰琪一样,出身于南方贵族家庭。但她在南方没落之后选择嫁给了出身工人阶级的斯坦利,定居在了北方工业城市新奥尔良。在剧中的首次出场,斯黛拉是“一个温柔的年轻女人”[8]6,也可以看出“出身背景显然跟她丈夫大不相同”。[8]6斯黛拉对姐姐布兰琪既同情又充满爱护之心的,她愿意时不时夸赞布兰琪最在乎的外貌,总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布兰琪,甚至说“我喜欢服侍你,布兰琪”[8]109。在斯坦利揭发了布兰琪不堪的过往时,她能坚定地维护布兰琪,并说:“所有的这些故事我一概不信。”[8]147现实生活中,田纳西·威廉姆斯和年轻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弗兰克·梅洛,维持了一段长达14年的恋情,这也是田纳西个人感情生活中最长久的一段恋情。弗兰克·梅洛在田纳西·威廉姆斯丰富的、甚至近似放纵的感情生活中,充当了他最终的爱人。据称,这是田纳西生命中“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他再未有过如梅洛般可爱、诚实、忠诚的爱人。”[6]152在这期间,梅洛充当了田纳西的私人秘书,不仅照顾田纳西的生活起居,还陪伴他共同抗击困扰其多年的抑郁症的侵袭,他给了田纳西之前从未有过的稳定、幸福的生活。他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也是田纳西最多产的时候。之后梅洛身患肺癌,田纳西悉心照顾他直至其去世。
二、作者人格与主要角色的对应关系
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从内部控制人类行为的一种心理机制,人类在一切情境中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特征都由此决定。本我、自我、超我,是人格的3个组成部分。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是人类生而有之的无意识部分,这其中蕴含了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欲望。性欲 (libido)是本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我奉行快乐原则,表现为非理性的想法和冲动,不受任何理性和道德的约束。然而,本我中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被完全满足,必然受到社会道德观的影响和制约,这时就需要另一个人格——自我为其寻求达到目的的最佳方式,使本我在现实世界中能以一种更容易被人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自我是个体在与外界环境的接触过程中从本我中衍生出来的,是现实社会的产物,调节着本我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说:“自我寻求用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及其倾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本能所起的作用。”[13]126超我可以被理解成人类追求完美的目标。超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部分构成。自我理想表现为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良心则表现为对违反相应道德标准和规范行为的惩罚。相较于自我的现实原则和本我的快乐原则,超我以追求完善、完美为目标。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试图协调和处理好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满足两者的需要。在弗洛伊德[14]24看来,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比作骑士和马匹的关系。自我是骑士,而本我是马匹,马匹提供必要的能量和信息,骑士控制其最终的方向。如果将自我拟人化,他就好似是3个严苛主人(本我、超我和现实)的奴隶,自我必须全力以赴应对这三者,结果就是经常面临只能满足其一而使另外二者不满的局面。人格结构理论不仅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解读文学作品、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之一。
(一)布兰琪-作者人格中的本我
田纳西·威廉姆斯曾说过,“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必须就是那个所塑造的人物,否则的话,那个人物就不真实。”[15]8正如笔者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女主角布兰琪正是作者田纳西·威廉姆斯本我的投射,也正如他本人所说:“我的性格有着两面,一面强烈地对性欲感兴趣,另一面却非常的温柔, 沉思而且富有同情心”[16]81,这跟布兰琪的性格和经历惊人地相似。
布兰琪本是劳雷尔镇的一名英语教师,却因为跟一个17岁大的男孩子鬼混被抓了个正着,最终因被告发被赶出学校。之后,她一直居住在镇里的“火烈鸟旅馆”,不断地勾搭男人,用“老一套伎俩,老一套花言巧语”[8]144跟陌生人有过多次亲密关系。她认为,“跟陌生人缠绵悱恻对我而言是唯一能将我空洞的心填满的途径……”[8]174在斯黛拉家中,布兰琪甚至勾引收报纸费的年轻男孩:“过来,我想吻吻你,就一下,在你的嘴唇上轻柔甜蜜地吻一下!”[8]117但是,布兰琪的另一面却是一种纤弱得需要避开强光照射的美。[8]8正如布兰琪自己述说的那样,她拥有“心灵之美、精神的丰富和内心的温柔,非但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减,反而会日益滋长!与日俱增!”[8]185斯黛拉更是认为她“太娇弱了”,“她现在、过去都很娇弱,你不知道布兰琪小姑娘时候的样子。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比她更加温柔,更加轻信人的了。”[8]162而田纳西本人,在高贵优雅却又敏感的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成年后跟姐姐的关系十分要好,这让他个性害羞又柔弱。然而,田纳西的个人感情生活却十分丰富,早年的他曾尝试跟女性交往,在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后交往过两名年轻男性,然后遇到了潘乔,虽然他们仅维持了两年的恋情,但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在遇到梅洛之前,他还同一名意大利少年共度了半年时光。伊利亚·卡赞认为,可以在田纳西身上看到“父母双方的影子”[6]151,来自母亲的优雅与克制与来自父亲的粗俗和放纵,在田纳西·威廉姆斯身上都得到了体现;清教徒的保守作风和简单粗暴的现实主义产生了强烈撞击,其矛盾和纠结也成为他戏剧中冲突主题的主要来源。布兰琪也正是这样一个矛盾和纠结的存在,她夹在旧南方曾经的辉煌和北方工业残酷的现实中生存,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她试图维持原本的南方淑女形象,遵循南方传统道德,却又控制不住自己跟不同的男人发生亲密关系,最后还用法语向不懂法语的米奇试探,“今晚您愿意跟我同床共枕吗?”[8]124布兰琪时而优雅、时而放纵,在淑女和荡妇之间游走。田纳西的影子清晰地在布兰琪身上得到了映射。
(二)斯坦利-作者人格中的超我
粗暴的斯坦利表面看来毫无教养、一无是处,但他却是强壮体魄和富有决断力的代表。正如斯黛拉所说,他身上有一股干劲。斯坦利在每次对斯黛拉发脾气后都会感到内疚,他在喝醉后打了已有身孕的斯黛拉,事后却喊“我的宝贝娃娃离开了我!”[8]77“我要我的小姑娘下来跟我在一起!”[8]78,最终他找到了斯黛拉,展现了他无限的柔情,在“台阶上屈膝跪下,把脸贴在她因怀孕微微隆起的肚子上。”[8]79这表现了他具有的良知的一面。同时,斯坦利有稳定的社交生活,他能呼朋唤友,随时跟一大帮人打扑克、喝酒;每周有固定的社交活动“扑克之夜”,这时“桌子上会摆着刚切好的西瓜、威士忌酒瓶和杯子”[8]55,在自己生活里占主导位置。斯坦利不仅是朋友圈里的核心人物,也是家庭中的领导者,他认为:“每个男人都是一个国王,而我就是这里的国王”[8]156。
反观田纳西本人的生活,他在学校被排挤,跟自己的姐姐关系最要好。他不善交际,在大学时曾加入兄弟会却无法融入其中,被认为是一个“只知道躲起来打字的孤僻的人”[17]15。根据田纳西母亲的回忆,当时的田纳西为自己设定了一周写一个故事的目标,他会“带着咖啡和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敲字。”[18]201伊利亚·卡赞更认为田纳西之所以与他一见如故,是因为他们都是“怪胎”,都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disappearer)[6]146。
斯坦利的性格恰好是田纳西的反面,他不仅仅是潘乔的投影,更代表了作者内心深处最想要成为的人,也就是他的超我。田纳西在谈到《欲望号街车》时曾说:“布兰琪不是毫无缺点的天使,斯坦利也并不是坏人,我知道习惯让剧中的好人和坏人一目了然,但是这部剧不一样,不要试着将事情简单化。”[6]151在给卡赞的一封信中,田纳西进一步提醒他小心处理对斯坦利的刻画,不要将其塑造成一个恶棍形象。[6]151这里不难看出,田纳西本人对斯坦利这个角色怀有深厚的情感,因为斯坦利就是他的超我,是他渴望达到的目标。
(三)斯黛拉-作者人格中的自我
斯黛拉原本的计划是和代表超我的斯坦利平静地生活下去,但本我布兰琪的不请自来,让她不得安宁。斯黛拉夹在满足本我和满足超我之间左右为难,这是作者“自我”的投射。斯黛拉与布兰琪的成长环境相同,原本也受到了南方传统道德观和清教教义的深刻影响,但在南方经济落后、文明逐步没落之后,她勇敢地挣脱了约束、适应了现实,果敢地投向了代表北方新兴工业文明的斯坦利的怀抱。而且,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并未打倒斯黛拉,反而能在面对布兰琪对她家环境的品头论足时回答:“你是不是有点反应过激了?这里根本就没那么糟!”[8]16在布兰琪问斯黛拉自己看起来怎么样时,她愿意说“你看起来好极了。”[8]18在布兰琪看来,斯黛拉的形象却是“你这个邋遢孩子,那么漂亮的白色衣领上竟然溅上了脏东西!还有你的头发……”[8]18斯黛拉清楚斯坦利“属于另一个物种”[8]22,也明白自己“当然也有需要调整我自己去迁就他的方面。”[8]22斯黛拉也曾在斯坦利打她的时候大喊,“我要走,我要离开这个地方。”[8]75,最终却仍选择原谅他,跟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的斯黛拉恰恰是全剧中最具理性、最能适应现实的人物形象:在粗俗的丈夫和优雅的姐姐之间,斯黛拉能容忍斯坦利的坏脾气甚至被这种脾气所迷住;能容忍布兰琪的过度敏感给予她容身之所。她能平衡关系,在丈夫和姐姐发生矛盾时斡旋其中,起到调节作用,这也正是人格中自我的作用。她要求斯坦利尽力体谅布兰琪,对她好一点, “还要称赞一下她的衣裙,跟她说她漂亮极了。这对布兰琪来说很重要。”[8]37在布兰琪评价斯坦利“不那么趣味高雅”时[8]20,斯黛拉提醒她“尽量别——老拿他跟我们在老家时交往的那些男人比。”[8]21在斯坦利不断挑刺时她会指责他:“别再总是跟布兰琪过不去了。”[8]140因此,田纳西虽然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暴力、粗野,非常阳刚、有一大群朋友和社交圈子的斯坦利,本性上却是纤细敏感、纠结矛盾的布兰琪。唯一能同时和两者共存的,就是斯黛拉,也就是作者的自我。
三、剧本的结局与作者的人生选择
布兰琪最终被斯坦利强奸,送入了精神病院,预示了本我被超我驱逐的结局。在布兰琪被带走的前夜作者这样写到:“夜幕中充满各种非人的声音,就像丛林中野兽的嚎叫”[8]188,“憧憧黑影和可怕的投影,交错蜿蜒地在墙上游动,恍若火焰”[8]188。虽然田纳西明白本我为社会现实所不容,但对驱赶本我又极度不舍且犹疑,正如身为自我的斯黛拉的质问:“也没必要对她这个孤苦伶仃的人这么残忍吧”![8]161在剧中的最后一幕,斯黛拉一边给布兰琪收拾行李一边哭,当她目睹布兰琪被精神病院带走时亦深感不安:“我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8]196,仿佛是作者在悲凄地控诉现实世界的残忍,自我为了生存下去要驱逐本我,可内心对放弃本我又是万般不舍。布兰琪最终被“说话声温柔又镇定”[8]210的医生带走。医生没有对她使用紧身衣,而是温和地拉起她,“用胳膊扶着她,领她穿过布帘”。[8]210这个画面好似布兰琪一直渴求的那样,被一位有教养的绅士带走,脱离现实的苦海。与此同时,布兰琪也有所感应地给予这位绅士绝对的信任,“任由他领着她向前”[8]210,“头也不回地继续朝前走”。[8]211而斯黛拉最终选择回到丈夫斯坦利的怀抱,是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就“没办法跟斯坦利过下去”[8]196。作者安排由旁观者说出:“生活总得继续过下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总得继续过下去”。[8]196这似乎是田纳西·威廉姆斯内心深处的独白,为了在现实社会中生存下去,只能狠心驱赶本我,更是田纳西在通过代表自我的斯黛拉告诉观众,这就是生活。或许,这也是“威廉姆斯的生活目标”[6]153,他仿佛在述说:“我们还是得继续正常的生活,这是最好的办法”[6]153。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传世之作似乎往往有一种作者本身不能操控的,贯穿命运的力量。田纳西·威廉姆斯为本我布兰琪安排的出路是被送往精神病院,从无法容纳她的新奥尔良逃离。带走她的医生对她是温和而宽容的。现实生活中,在《欲望号街车》发表的同年,田纳西遇到了能吸引他、宽容他,与他和谐相处的同性伴侣弗兰克·梅洛,并开始了长达14年的稳定感情生涯。这种现实境遇,就像是威廉姆斯也为自己找到了“医生”和庇护所。当《欲望号街车》在百老汇成为大热门时,冥冥中仿佛有命运主宰听到了威廉姆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剖析,带给了他一个能懂得他人格三重奏的弗兰克·梅洛。正如布兰琪在离开斯坦利和斯黛拉时所说:“不管你是谁—我总是指望陌生人的慈悲。”[8]210这样一句触动人心的台词,述说着被最后的亲人所抛弃的孤独与无助,却又隐隐暗示着依靠陌生人的可能。这样一部把作者人格最深处进行残酷解剖,并呈现给观众的精彩戏剧却又映照回作者的现实人生,实现了现实和艺术交融的浪漫转换。
结语
如果仅仅观看《欲望号街车》这部剧作,读者欣赏到的是跌宕起伏极具张力的剧情。但当我们把剧情人物和作者田纳西·威廉姆斯本人的人格进行解析,以及创作此剧时作者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对照就会发现,这是一部问心之作。《欲望号街车》的创作过程就是田纳西·威廉姆斯反复拷问自己的内心,探寻他的三重人格和平相处可能性的过程。而当剧本走向尾声,代表作者本我的布兰琪得到宽恕的放逐时,也就表明了作者的人生选择。田纳西·威廉姆斯通过人格投射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不仅留下了《欲望号街车》这部传世之作,也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
[1]Harold Bloom. Tennessee Williams [M]. Chelsea House Publishing. 1999:5.
[2]Tennessee Williams.Letter to Joseph I. Breen,Quoted by Gerald Wealse, in Leonard ed1, Tennessee Williams: American Writers: 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Biographies [M]. New York :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2 :390.
[3]Felica Hardison Londre. A Streetcar running fifty years [A].//In Matthew C.Roudane ed.,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nnessee Williams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45-48.
[4]David Savran. Communists, Cowboys, and Queers: 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in the Work of Arthur Miller and Tennessee Williams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112.
[5]Donald Spoto.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The Life of Tenessee Williams [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5:153-154.
[6]Elia Kazan. A Life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8:151-153.
[7]C.W.Bigsby. An Introduction to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Drama v2 [M]. Britain: Cambridge Uinvertisy Press. 1985:22.
[8]田纳西·威廉姆斯.欲望号街车[M]. 冯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211.
[9]张生珍. 论田纳西·威廉斯创作中的地域意识[J]. 外国文学研究,2011(5):96.
[10] Ruas,Charles. Conversation with American Writer [M].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5:77.
[11] Ellen Schreker. Many are The Crimes: Mc,Carthyism in American [M]. Priceton: 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149.
[12] 赵庆寺. 20世纪60年代美国同性恋运动兴起的历史考察[J].安徽史学. 2003(2):40.
[1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M]. 车文博,主编.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126.
[14] Gay, Peter. ed. The Freud Reader [M]. New York, W.W.Norton&Co., 1989:24.
[15] Froster Hirsch.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The Plays of Tennessee Williams, Port Washington [M]. New York: Associated Faculty Press, Inc., 1979:8.
[16] 徐静.新的起点与觉悟:试用荣格理论分析《欲望号街车》 里白兰奇的神经官能症[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25(5):81.
[17] Roudané, Matthew Charl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nnessee Williams [M].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15.
[18] Tennessee Williams and Margaret Bradham Thornton. Notebooks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201.
Analysis of Characters’ Personality and Reality Projections in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TANG Yi-shan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410205, Hunan, China)
Abstract:Tennessee Williams projected his id, ego, and superego into three main characters in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The author’s life experience and contradictions among his personalities are condensed into the plot and conflicts in the play. The arrangement for characters’ destinies in the end of the play is coincident with the author’s life circumstance after the play being staged. The multi-fold scenario-reality projections demonstrate the uniqueness of the play.
Key words:Sigmund Freud; Personality projection; Pancho Rodríguez; Frank Melor
收稿日期:2015-12-20
作者简介:唐亦珊(1989-),女,汉,湖南永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6)04-00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