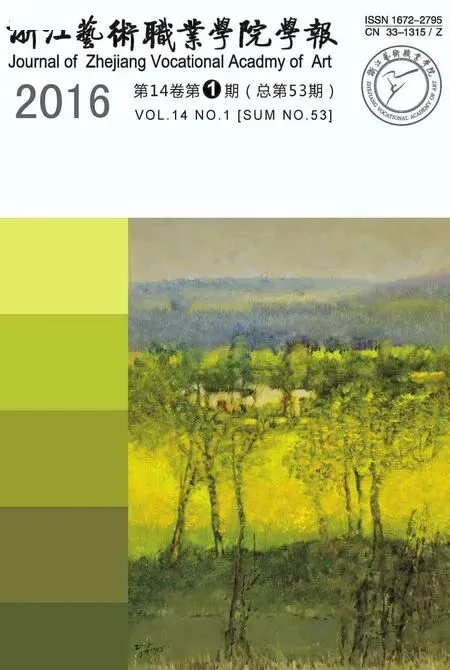“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
杜亚雄
“传统音乐”与“音乐传统”
杜亚雄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包括“音乐传统”和“传统音乐”两个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方面。前者是指有关音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后者系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的成果。目前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应把有关“音乐传统”的研究作为重点。
关键词:传统音乐;音乐传统;研究重点
“中国传统音乐”是我国音乐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但从那时起到目前,对其内涵和外延一直没有进行过深入探讨。“中国传统音乐”是指中国传统的、有关音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还是指由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的成果,并不十分明确。笔者抛砖引玉,撰文讨论此概念,发表一孔之见,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界定,关键是搞清楚“传统音乐”和“音乐传统”的关系。在这方面,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很大启发。1916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这本书主张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何为“语言”?什么是“言语”?语言学家指出:“语言是工具,人人都可以使用它,造出千差万别的句子,那就是言语了。”[1]也就是说“语言”是形式和规则,“言语”是个人对“语言”形式和规则的具体运用。“语言”是排除了一切个体差异,对所有人所说的话的所做的抽象;“言语”是运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就是每个人每天说出来的话。
索氏的这本书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他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具有分层次的形式结构;主张研究一种语言时,应从大量的“言语”素材进行抽象概括,从中发现“语言”的各种单位和规则。他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期成为语言学的主流,其观点也给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以极大影响。
在汉语中,“传统”是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2]194。从音乐方面来看,“传统”不仅包括“世代相传”的优秀作品,也包括“具有特点”的创作音乐的方法。如“传统音乐曲目”中的“传统”指的是前者,而“发扬音乐传统,提高创作水平”中的“传统”则主要是指后者。既然如此,“中国传统音乐”这个词组就应当包括“传统音乐”和“音乐传统”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索氏对“言语”和“语言”的界定,对这一对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不同的概念进行辨析。在我看来,“传统音乐”应与“言语”相对应,而“音乐传统”则应和“语言”相对应。具体地讲,“传统音乐”应当是指人们“运用本民族固有方法、采取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音乐”[3]作品,其中不仅包括在历史上产生、世代相传至今的古代作品,也包括当代人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作的、具有民族固有形态的音乐作品。而“音乐传统”则指本民族固有的创作音乐的方法和本民族固有的乐曲形式。简言之,“传统音乐”是指音乐作品,而“音乐传统”则是创作传统音乐的方法。“音乐传统”是创造“传统音乐”的根据,前者和后者有四点不同。“音乐传统”具有民族性、概括性、有限性和静态性,而“传统音乐”则具有个体性、具体性、无限性和动态性。
“音乐传统”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为全民族每个成员所共有,大家都可以创造和使用。根据“音乐传统”创作出来的“传统音乐”则具个体性。不仅每个人创作出的作品不同,同一作品的每次表演也会因表演者的地域、性别、年龄、文化素养、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如“以词生腔”是汉民族“音乐传统”中的一种创作曲调的办法,任何人都可以用,士大夫可用来吟诗,老百姓可用来唱民歌。然而每个人根据这种办法吟出的诗或唱出的歌都会不同。又如“添眼加花”是汉族器乐曲常用的变奏手法,各地的艺人都可以用它来发展曲牌[老八板],但加花而成的乐曲,不同乐种、不同艺人便不一样。
“音乐传统”是从“传统音乐”中抽象出来的,它排除了一切个体性的差异,而“传统音乐”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作品。人们听到的都是“传统音乐”,听不到“音乐传统”。人们对于“音乐传统”的认识通常是从通过了解具体作品开始的。音乐学家通过对大量的“传统音乐”作品进行研究,才能从中发现创作出它们的规律,也就是“音乐传统”。
根据一种“音乐传统”创作出来”的“传统音乐”作品可能是无限的,而这些从具体的、无限的“传统音乐”作品概括出来的抽象出来“音乐传统”规则却是有限的。因为每个人、每天都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作品,所以一个“传统音乐”中的作品便可能是无限的。但在这个“音乐传统”中,所能采用的乐音、音阶、曲调发展手法等都是有限的,曲式的样式、和声的规则、配器的法则、复调的手法也是有限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就像语言学家不可能将某种语言的句子搜集全一样,音乐学家们也不可将某一种“传统音乐”中的作品搜集全。语言学家通过分析一定数量的“言语”,得出某种“语言”结构规律,音乐学家也应能够通过一定数量的“传统音乐”作品,研究出构成“音乐传统”法则。
在人们的音乐活动中,其“音乐传统”中规则都是现存的、约定的,在一定时期内处于静止状态,不允许处于经常的变动中,这是“传统音乐”作品的创作和表演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如京剧的基本唱腔是“西皮”和“二簧”,如果突然把这两种腔调变成没有管弦乐器伴奏的高腔和用板胡伴奏的梆子腔,观众就不会认为它还是“京剧”。西洋音乐中的交响乐、协奏曲也有相对静止的写作程式。当然,随着社会的变化和音乐的发展,“音乐传统”也会出现适应性变化,但也是静中有动。如果完全不顾“音乐传统”中的约定,任意破坏其静止性,听众在聆听时便会不知所云。“传统音乐”就不同了,一部作品、一首歌曲言从创作、表演到聆听都是具有动态性的、信息传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音响充当信息传递的代码,表演者通过表演来发送音乐,听众通过音乐接收信息,其间所经历的发送、传递、接收几个连续衔接的过程无一不是动态的。
搞清了“传统音乐”和“音乐传统”的区别和联系,我们审视一下20世纪初以来我国专业音乐院校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
1922年8月,蔡元培先生接受萧友梅先生的建议,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组。该所简章提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4]。由此看来,在成立我国现代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时,先贤们为高等音乐院校规定了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学习包括西洋音乐的理论和技术,二是保存本民族传统音乐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的音乐传统。
北大音乐传习所成立至今已将近一个世纪,回顾近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应当说,第一项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我们不但全面地“传习”了西洋音乐的历史和包括作曲技术理论、各种表演技术在内的各种知识,而且在许多领域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水平,为传承和发扬光大欧美各民族的“音乐传统”做出了巨大和杰出的贡献。在国际比赛中,每当我国选手击败欧美众多对手夺冠,大家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媒体报捷,学校报喜,政府部门给予奖励,庆祝“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实际上,这不是“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而是“西洋音乐走向中国”。
文化是民族存亡的关键,我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如匈奴、柔然、鲜卑等都是因为民族文化的逐渐消亡导致民族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的。一般认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2]884,然而犹太、吉普赛等一些民族在没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情况下,存在千年并获得发展的事实,说明一个民族只要保存民族文化,在没有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同样能够传承、发展、壮大。历史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对一个民族来说,共同文化比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来说都更重要。因此,先贤们提出的保持并发扬光大本民族音乐文化传统的任务,比第一项任务更为重要。
然而,第二项任务完成的情况和第一项任务相比,却是十分不理想,大家也都不很满意,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刻检讨。然而问题就出在我们只注意了“保存”“传统音乐”,而在“发扬光大”“音乐传统”方面并没有下大的功夫。
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些高等音乐院校开设过“国乐课”。当时的“国乐课”有两种,一种是学习演奏古琴、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个别课,另一种是介绍有关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集体课。这些课程和后来的被称为“民族民间音乐”、“民族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课的教学目的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通过教学达到传授“传统音乐”的目的,而不怎么涉及“音乐传统”方面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创造社会主义音乐文化逐渐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教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增设了“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比起民国时期,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些课程便是今天高等音乐院校有关“中国传统音乐”各门功课的雏形。
1949年,沈阳音乐学院的前身东北鲁艺最早开设“民族民间音乐”课程,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则分别在1952年和1954年开课,随后其他音乐院校也竞相效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开设了“民族民间音乐”课。那时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各专业必修的共同课,侧重于民间音乐的声乐部分,主要开设民歌、说唱和戏曲课,授课方式以唱为主,主要的目的是使学生“从感性上了解接触民间音乐”。上课时除了教唱以外,老师“还辅之以风格特点、历史发展、流传概况、演唱方法以及曲种、剧情等简要介绍,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教唱的内容”[5]24。
当时开设“民族民间音乐课”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我国传统音乐“是什么”,改变他们对传统音乐“不熟、不懂、不爱的不正常状况”[6]。这些课程的教学无不带有感性化、常识化、浅层化和具体化的特征,通过教学可使学生对我国传统音乐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众所周知,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包括感觉、知觉、表象三种形式,其特点是直接性和具体性。简言之,这些课程是介绍“传统音乐”的课程,不是教授“音乐传统”的课程。
虽然民歌、戏曲、说唱、民族器乐等课程曾被人称为“民族四大件”[5]287,实际上它们并不能和“西洋四大件”,即“和声”、“配器”、“复调”、“曲式”相提并论。在“民族四大件”中只教唱民歌、戏曲和说唱的唱段,也教授一些有关民族乐器和民族器乐的知识,但不教学生如何写出一条具有“信天游”风格或“广东音乐”风格的旋律,如何设计某种说唱的唱段或某种戏曲的唱腔。因此,“民族四大件”所教是“传统音乐”,并没有把“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规律性的原则,即“音乐传统”总结出来教给学生。“西洋四大件”则不然,它们是欧洲音乐创作实践的总结,教学目的是通过“传统音乐”教“音乐传统”。学过这些课程,便能学会如何写作具有欧洲风格的音乐作品,学得好的人还能从事保持和发扬欧洲“音乐传统”的工作。目前活动在欧美乐坛的华裔作曲家,很多都毕业于国内音乐院校,他们在发扬欧美“音乐传统”方面所做的工作,得到欧美音乐界和群众的认可。这一“中为洋用”的现象,便证明了我们在各个音乐学院里所教授的“西洋四大件”就是欧美的“音乐传统”。
如果把“音乐传统”和“传统音乐”分清楚,就不难看出,在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明显地存在两条不同的音乐发展道路:第一条可称为“学府道路”,第二条则可称为“民间道路”。虽然这两种道路目前都被肯定,但走在这两种道路上的人们,社会地位、知识结构有所不同,这两种道路的影响层面及传承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
从社会地位来看,进入“学府道路”的音乐家,多是“海归”、“教授”、“学者”、“艺术家”,如萧友梅、黄自、杨荫浏、钱仁康等,社会地位较高,为大家所尊重。走在“民间道路”上的音乐家们,多是“民间艺人”,也有一些“票友”。“民间艺人”如阿炳、孙文明,“票友”如广东音乐的专家司徒梦岩、钱大叔、尹自重等。“票友”一般社会地位较高,“民间艺人”则是“吹鼓手”、“乐户”、“戏子”、“堕民”甚至是“乞丐”,社会地位低下。
走在“学府道路”上的音乐家,学贯中西,知书达理,知识结构全面。他们办学校,推广西洋音乐的知识,培养学生,并使学生成为能够创作和表演西洋音乐和西式新音乐的专家。在音乐创作方面,走这条道路的人一般都通过学习欧洲的“音乐传统”来“提高”和改编、改造我们的“传统音乐”。新中国成立以前,学府中的音乐家们只注意了我们的“传统音乐”,没有集中精力注意我们的“音乐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各音乐学府,特别是上海音乐学院,曾经一度非常重视对“音乐传统”的探索,黎英海先生出版了《汉族调式及其和声》,胡登跳先生出版了《民族乐队配器法》,于会泳先生写了《腔词关系研究》,高厚永先生写了《民族曲式中的变奏原则》和《论曲牌》等著作。樊祖荫、刘国杰、连波等先生也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建立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体系是一个极为繁难的系统化工程,尽管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然而时至今日,体系尚未建立,连一本能够概括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乐理书都没有写出来。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在各音乐学府中,研究“音乐传统”不再时髦,“音声”产生的环境和背景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似乎更吸引人们的眼球,没有多少人有兴趣探索传统音乐的形态和本民族的作曲技术理论。
走在“民间道路”上的艺人有不少是文盲。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本民族固有的作曲手法,写新作品,发展本民族的“音乐传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们也通过学习西洋的“传统音乐”,吸收其中的一些成分。如阿炳在《听松》一曲中采用了号角声,是他在无锡听军乐队演奏时学到的[7]。而广东音乐中学习西洋音乐的成分就更多,不仅有西洋音乐的音调,如《步步高》的头几个小节的曲调,而且在乐队中吸收了小提琴和萨克斯管。然而,无论是“民间艺人”还是“票友”,都不是专业的音乐理论家,就像会讲某种语言的人们,不一定了解它的结构规律和构词、组词和造句的规则一样,他们虽然创作出了不少“传统音乐”,但不一定了解指导音乐创作的理论,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对我们民族的“音乐传统”进行总结。
因为在这两条道路上前进的音乐家,都没有刻意地去做总结“音乐传统”的工作,所以目前我国的音乐院校虽然开设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课程,但课程中教授的主要是“传统音乐”,而不是“音乐传统”。
如果将1980年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作为将民族音乐学引入我国的开端,这一学科在我国已有36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36年中,对各地、各民族传统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和描写一直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界研究的最主要内容。简言之,我们一直在努力地研究“传统音乐”,一直在结合文化背景通过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作品,试图搞清某种传统音乐的分类状态、形态特征和社会功能,在这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然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任务不仅仅是了解世界各地、各民族音乐的“传统音乐”,也不仅仅要了解某种传统音乐的分类状态、形态特征和社会功能,还要知道它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即不同的“音乐传统”。海伦·迈尔斯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尽管课题多种多样,但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统一了。人类学和音乐学各自关注的问题融合了,研究兴趣从具体音乐作品转向了音乐创造和表演的过程——即作曲和即兴表演,焦点也从曲目的收集转向了对上述过程的调研。”[8]16内特尔也指出:“如果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不同以往,主要区别在于对过程的研究,对作为过程而非仅仅作为产品的音乐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也可以说,现在更多的兴趣是在事情发生的方式,而不是事情所处的状态。”[8]489
音乐是表演艺术,因此创造它的方法便有两种:一是作曲,即作曲家将他的乐思用书写符号记录下来,以便自己或他人可以按图索骥地去进行二度创造,通过表演把他的乐思变成真实的音乐;另一种是即兴表演,即演奏家或演唱家直接将其乐思表演出来,不经过二度创造的过程。无论是作曲还是即兴表演,都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这些知识的总和就是“音乐传统”。
音乐不是国际性的语言,就像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语法体系一样。要创造出某种音乐文化中的音乐,一定要学习这种音乐文化中的音乐创造方法。任何一个音乐家都不是凭空,而是在一定“音乐传统”的指导下进行音乐创造的。
根据创造“传统音乐”的过程总结出某种文化的“音乐传统”,则是民族音乐学家的重要任务。既然民族音乐学认为世界上各民族的音乐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内在逻辑性和具有连贯性的体系,民族音乐学家就应当研究这种逻辑性及其所具有的连贯性,即创造各民族音乐的方法。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很有必要学习国外同行的做法,将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作品转入研究创造音乐的方法,即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来。我们要传承“传统音乐”,更要总结“音乐传统”。
随着全社会对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程度的提高,有音乐院校开设了有关课程,还有人呼吁音乐院校应当主动负担起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也就是说音乐院校应当加强“传统音乐”的教学,甚至成为保存“传统音乐”的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应当得到很好的传承,然而音乐学院不是博物馆,音乐院校是教育单位,当然可以教授“传统音乐”,但更应当通过对“传统音乐”的教学和研究,总结出“音乐传统”的内容,将其传承下去。如果音乐学院只能用博物馆或半博物馆的方式保存一部分传统音乐,而不能使中国人的音乐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那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不符合一个世纪以前的先贤创办高等音乐教育的初衷。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任何一个“音乐传统”来说,没有“怎样制造”“怎样写作”就没有发展,而没有发展也就谈不上继承。
我们应当把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感性认识迅速提高到理性认识阶段,即不仅仅认识“传统音乐”,也要明了“音乐传统”。目前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应当通过“传统音乐”研究“音乐传统”,并把这一课题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诚能如此,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笔者愿和大家一起,为完成这一研究课题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胡裕树.现代汉语(重订本)[M]. 6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3.
[2]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杜亚雄.什么是中国传统音乐[J].中国音乐,1996(3).
[4]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EB/ OL].百度百科,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465765. htm?fr=aladdin.
[5]高厚永.万古文明的见证[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6]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6.
[7]杜亚雄.阿炳的三首二胡曲[J].乐府新声,1985(4).
[8]海伦·迈尔斯.民族音乐学导论[M].秦闻展,汤亚汀,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黄向苗)
“Traditional Music”and“Musical tradition”
DU Yaxiong
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includes“musical tradition”and“traditional music”. There are both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about music;the latter is the result of the thinking and behavior. At present,the folk music circle in China should take“musical tradition”as the priority of research.
Key words:traditional music;musical traditions;research priority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1-23
作者简介:杜亚雄(1945— ),男,河北鹿泉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音乐教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杭州31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