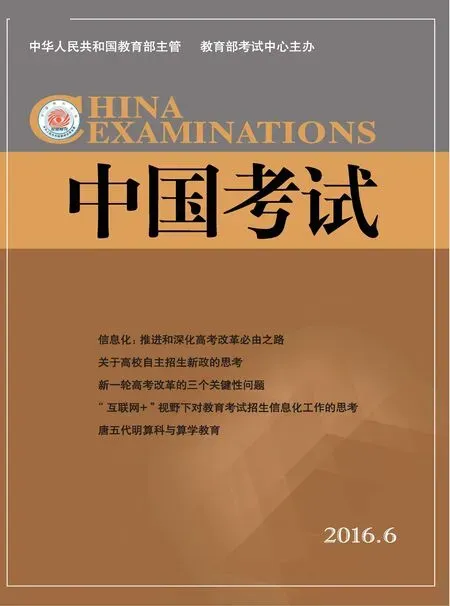论元代统治对云南科举的推进
杨冉
论元代统治对云南科举的推进
杨冉
元代对于中原文化的进展并未有太多深远且积极的影响,但对云南而言,其统治对加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南诏、大理时期封建割据的终结使云南地区能够和中原保持相对同步发展。科举制度的推行和儒学的推广使得云南文教获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科举;云南科举;儒学
1 南诏、大理时期的云南教育与考试
南诏、大理政权对云南的统治长达7个世纪。在此期间,中原政权一直用“羁縻”[1]来管理和控制云南;即便南诏后期相对独立,也与中原保持紧密的联系。但从北宋开始,中央政府对云南地区放松了治理,内政外交重心偏向北方民族,云南与中原王朝的联系稍有疏远。但事实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两地之间文化、经济交往从未断绝。虽然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地区受到中原文化极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云南大部分人口组成依旧是少数民族,其文教与中原地区也有很大的不同。
公元7世纪,“南诏”在唐朝政府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以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为中心建立南诏国。其时南诏国内语言文字并未统一。樊绰《云南志》卷八中指出:“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大事多不与面言,必使人往来达其词意,以此取定,谓之行诺。”[2]此中指出白蛮语与汉语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依旧有不同之处。且若遇紧要之事,为保证沟通的准确性,往往不当面言说。方国瑜先生在《洱海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中提到:“南诏统一洱海区到樊绰著书时,已一百三十年,原来不同种属的各部族已逐渐融合,但还没有结合成为只有一种语言。”所以其他部族的语言要“三译四译乃与华通”。[3]更何况自唐代始,佛教流入云南,其时南诏地区乃有“佛国”之称。宗教对云南影响深远,上到百官,下至黎民,无不诵经。因此,若在云南境内推行中原的考试制度,必须要结合当地的语言文字以及文化、宗教特点。
关于南诏时期的儒学教育形式有三种,见于《云南考试史》。其一为私学,其二为境内兴办儒学,其三为求学成都。
自春秋起,私学一直是士人们常见的学习方式,在云南地区则多见于王公贵族之家,而南诏境内仿照中原兴办儒学也确有其事。《僰古通记浅述教校注》中记载:“是年,唐武宗改元会昌。建二文学,一在峨崀,一在玉局山,为儒教典籍驯化士庶,以明三纲五常。”[4]虽有文献记载确实有儒学出现,但并未提及如何进行教学。
相对以上两条而言,去成都学习是南诏时期士人主要的求学方式。南诏与唐关系密切,统治者也多提倡中原文化,常遣本国贵族子弟进学于唐。《南诏德化碑》记载,在细奴罗到阁罗凤统治的百年期间:“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即便天宝战争之后,南诏与唐关系破裂,也并不排斥中原文化。诸多战争期间被俘的中原文人在南诏任教讲学,再加上儒家典籍的流入,使得南诏的儒学教育并未中断。
贞元十年后,南诏与唐重建外交,又恢复以往求学惯例。在成都设立剑南西川节度使来辖制西南地区后,按照以往的惯例,南诏应当使质于成都。时韦皋任西川节度使,南诏王异牟寻请以大臣子质于成都,被韦皋拒绝。《新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七记载:“十五年,异牟寻谋击吐蕃,以邆川、宁北等城当寇路,乃峭山深堑修战备,帝许出兵助力。又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5]由此观之,韦皋接受南诏学子来成都学习,并非以其为质。相对于前两种学习方式而言,第三种求学成都,能够让南诏学子受到更系统的儒家教育。蜀中人杰地灵,有极好的儒学氛围,更有良师益友相互切磋学习。据方国瑜先生推测,南诏遣人去成都学习大概持续了四十余年。即便中途有所变故,但的确为云南儒学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风气和影响。
虽然南诏时期便有留学生的出现,且当时大唐也有针对各地进学学子的推优参加科举的政策,推优政策并不限制民族与国籍,但是史料里一直未曾见过有南诏学生入唐为官的记载。关于南诏国的选官制度,在《云南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南诏下设清平官六名,官职同宰相。清平官后设大将军十二名,与清平官一道组成南诏政权的中枢系统。又设立兵曹、户曹、刑曹、工曹、客曹、仓曹等部门。各部门分工严密且有详细的考核制度,多按照官员在任政绩为主。关于南诏文官选拔的制度并未有详细记载,但南诏地处偏远,民风剽悍,军事力量强大。关于军事的考核有详细文献记载。
总体而言,南诏属于奴隶制社会,多采取兵农合一的政策,辅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和考核政策,使南诏武力长久保持在活跃状态。《云南志》记载了南诏对于军队的考核标准,较之唐朝武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剽悍之处可一观唐代天宝战争,唐军于西洱河两次惨败:“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贵衄,元帅沉江。”[6]主帅李宓也在此次战役中身殒。
南诏灭亡之后,剑川节度使段思平于公元938年建立大理国。北宋王朝对大理态度略显冷淡,但两国一直保持民间和半官方的来往。儒家思想在唐之时早已传入云南,进入云南的中原人士也大量增加,或任教于宫中与贵族之家,或游历山川,传学于民。但大理时期未曾有派学生前往中原求学和建立专门的儒学部门的记载。其时对成都的士人多以“师僧”“释儒”称呼。由此观之,大理国应是儒佛并举的教育方式。
《云南志略》记载:“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7]“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子,然往往读儒书,段氏而上有国家者设科选士,皆出此辈。今则不尔。”[8]而大理国选仕,以僧道读儒者,选官吏多由此。《南诏野史·大理总管段实传》记载:“段氏有国,亦开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读儒者。”[9]由此说明,大理一定有选举官吏的制度,但是如何选择并无完全记载。但毫无疑问的是,南诏、大理时期已经有了儒学教育,且已逐渐开始深入发展。但是由于南诏、大理时期依旧属于地方割据政权,其主流文化中有鲜明的本土色彩,并不能与中原地区合辙同一。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南诏还是大理的科举体系都与中原不尽相同,且暂无文献发现有入中原为官者。这样的局面在公元1254年蒙古平定大理之后发生了转变。
2 元代云南的教育与考试
南宋朱熹曾言:“谋恢复,当废科举三十年。”元代从建国来,三十四年未兴科举。蒙古强大的铁骑纵横欧亚,其地“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少数民族政权,完全入主了中原。[10]最初,元蒙贵族并未在意科举。他们所倚靠的是本民族的贵族和军功书吏。当蒙古征服辽金,将剑锋指向遥远的中原后,在攻伐与管理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了士人的重要性——士人乃舆论喉舌;掌控了士人,管理中原的阻力必定会减轻许多。
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清楚地认识到儒学在士人中的地位,主张以“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11]他建议开科取士,希望窝阔台能选用汉儒入朝为官。元代政权中始终存在吏儒之争,想要恢复科举阻力很大,设科极其困难。窝阔台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于至元九年八月,“下诏始命断事官术忽斛与山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12]
次年,选中者可参加朝廷的正式考试。这是元代开国以来进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虽然它对于安抚汉民有积极作用,使汉族官吏能够进入地方任职,但是更多的只是将部分考中的举子免为奴隶,并未任用。所以,这次科举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科举考试。科举的施行使得一些蒙古贵族极其不满,如浙江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因不愿皇帝提高汉人地位,上书要求罢除科举。因蒙古权贵极力反对,朝廷被迫停止科举。经王恽等人的不懈努力,六年后才得到恢复。
自从1253年蒙古大军征服大理国,云南基本划入元版图。1276年元朝建立云南行省。此时,整个云南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由大理转移到了拓东城(即昆明)。随着蒙段割据统治结束,云南逐渐开始和中原地区合辙同一,云南文教政策和风气与官吏选拔任用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其一,儒学的普遍传播。庙学是在孔庙中对孔子等先哲祭祀礼拜后进行的以宣讲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形式。前文已提过,南诏、大理时期基本上是儒佛并举的教育方式。官吏多在通晓儒佛的“师僧”中选拔任命。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其时云南还受少数民族习惯影响较深,政治局势动荡,且没有系统的儒学体制。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盛”。塞典赤将自己的俸金捐献,“市地于城中之北偏,已基庙学”。[13]两年之后,中庆路文庙建成。现虽旧址犹存,却已不复当年威严。进门烟火缭绕,早已成为喝茶下棋、打牌聊天之地。
由于赛典赤的大力推广,云南各地开始兴建文庙。《元史·张立道传》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张立道除中庆路总管。先是云南虽知孔子,而祀逸少为先师。立道广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14]除了拓东城以外,其他府卫州县也相继建立孔庙与地方官学。地方官学和孔庙的发展、政府对儒学的尊重以及重才养士等措施,既巩固了元蒙王朝的统治,也使各地读书人有了学习的场所和为官的机会。即便元代对“是否进行科举”进行了无数次讨论和立废,但其国子学、地方儒学和乡村社学(包括地方书院和私学)都得到了行省长官的重视和支持。
其二,中央到行省皆设立机构,专管文教与考试。元代官学继承了金朝的体制,也吸收了唐宋的经验。元代还结合本朝情况建立起一个适宜于元朝中央政府管控的官学体制。集贤院是元代为管辖全国学校教育所设立的机构,下设国子监、蒙古国子监和回回国子监。据《元史·百官志三》载:“集贤院,轶从二品。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15]地方官学统一归集贤院管理。中央和地方的教学之人主要由汉族儒士担任,也吸收了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有才华的人任教。地方官学的教师必须是通晓儒经且“志成”的儒家学者。
少中大夫王恽不主张草率实行科举:“科场停罢日久,欲收实效,行之不可草率。必先整学校、选教官、择生徒,限以岁日方可考试,如是则能得实材,以备国家之用。”[16]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滞。因此,由学校选拔人才参加科举是能够改善当下“无材可取”形势的唯一办法。不过元代统治者并未完全被“汉化”。其本民族传统的蒙古字学、蒙古国子学也并未被遗忘。除儒学外,蒙古字学、医学和阴阳学与中央的蒙古国子学、医学和天文学相对应。地方和中央的教学机构同一,这在之前的朝代从未做到过。
行省机构中设立“儒学提举”。各级学校设教授、学正、学录等,且官民汉夷之子弟皆可入学读书。这一条自然也针对云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除去儒学之外,元代也注重医学的教育与医学人才的选用。各行省下设医学提举,与儒学提举一般,专管医学教育与考试。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冬十月甲辰开科举,下诏全国在皇庆三年八月,全国郡县推举贤能者充贡有司,于次年二月在京师进行会试。根据选举制记载,此时全国可选择三百人进行会试,取一百人。一百人中施行分卷测试。云南最初的定额为:蒙古人一名,色目人、汉人各两名。淡生堂抄本《南诏野史》记载:有元一代,云南六人中进士。[17]虽人数不多,但也能看出云南文教已经和中原地区逐渐同步,成为统一的整体。元代之后,明清科举中出现的蒙、回、白、彝、纳西等族的举人和进士不在少数。元代科举政策为以后明清两朝云南地区的文教发展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3 元代统治对云南文教的影响
元代云南科举虽然只取中六人,皆为第三甲同进士出身,且官职不高,并未进入国家的政治中心;但元代在云南设立行省,推广儒学,对元代之后的云南的文教事业甚至政治、经济、民族融合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隋唐兴科举以来,云南并未直接归中央管理,而是由南诏、大理国先后统治。地方政权的相对独立性使云南基本无法参与到全国性的科举体系中。自大理政权覆灭后,云南逐渐受到元的统治。除了境内本就有的少数民族以外,又迁入色目人、蒙古族和从北地移居云南的汉人等。民族的融合和政权的统一使云南极具民族特色的考试与选官制度被淘汰。经过几任行省长官和各路儒学提举的大力推行和人文关怀,云南文教在向中原地区靠拢的同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云南开始正式取士,其影响有以下三点:
首先,科举的推行,一改南诏、大理时期杂乱的考试方法,形成有序的考察制度。科举将儒学教育与官员选拔考核相结合,给予了边疆学子进入庙堂的机会,稳固了中央政府对于边疆的统治和民族融合。元代科举考试虽然充满民族歧视,对各族分而治之,这对于元帝国本身而言固然弊端重重,但对于刚加入大一统帝国的云南来说,能与中原地区在各种制度上的同一,从附属国变为元代的一部分,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其次,儒学教育蓬勃发展。兴文庙,建官学,置学田。元代统治者虽在科举选制上实行了民族歧视政策,但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却是纯粹的儒家思想。元代采用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内容,原因词赋与经义之争持久不下,以致程朱理学从中得利。“今欲兴天下之贤能,如以科举取之,犹胜于多门而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真材也。”[18]“朱子《贡举私议》可损益行之,又言取士当以经学为本,经义为用,程朱传注,唐宋词章之弊不可袭。”[19]程朱理学,淡化词赋,以经学为本,省却一分诗赋才气,多几分钻研精神,奠定了儒教统治的局面。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对云南学子相对有利。文气不足,可以勤奋与之;才华未够,可以学问补之。
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对儒学的大力推广前文已说明,不再赘述。他与历任儒学提举的贡献使云南学子拥有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术环境。元代对云南儒学发展的支持加上几次科举积累的经验使云南学子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亦有杰出文人。据史料记载,元代云南考中的六位进士多在本省任职,亦有任诸路儒学提举者,也为云南推行儒学尽心竭力,并未受到回避制度的影响。
最后,元代科举为云南积蓄力量,人才培养、学文风气得以延续发展。有元一代,即便云南进士只有零星几位。但到明清之时,在元代科举的基础上,科举在云南进一步推行。云南厚积而薄发,举人进士人数激增,少数民族并不少见。云南教育文化进一步发展提高。据统计,元代云南文进士共六名;至明代则文进士二百六十七名,武进士四十七名,共三百一十四名;至清代文进士七百零四名,武进士一百三十九名,共八百四十三人。[20]人数重点分布为云南府昆明。与江浙中第人数相比,云南科举的成就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元代才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和文教的云南来说,已是可叹的成绩了。
元代科举考试有诸多弊端,或如民族歧视——南北两榜,分而治之,或如程朱理学——禁锢思想,压抑自由。但对于云南来说,元代的统治促进了云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实行科举加快了云南学习中原文化、融入大一统帝国的步伐。对于云南来说,元代统治更像一个转折点——从边缘处的独立政权成为元朝版图的一份子,从史书上的西南诸夷成为云南行省。不同于中原地区仿若雾霾笼罩的黑暗年代,元代对于云南来说更像是于孤独前行时迎面而来的耀眼火光,让彳亍而行之人有了前进的方向。
[1]刘昫.旧唐书:卷102[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017.
[2]樊绰.云南志补注:卷8[M].方国瑜,等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19.
[3]樊绰.云南志补注:附录四[M].方国瑜,等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66.
[4]僰古通记浅述校注[M].尤中,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29.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81.
[6]阮福.南诏德化碑:滇南古金石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7]郭松年,李京.民族调查研究丛刊: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86.
[8]郭松年,李京.民族调查研究丛刊: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23.
[9]倪辂.南诏野史会证[M].王崧,校理.胡蔚,增订.木芹,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347.
[10]宋濂.元史·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45.
[11][12][18][19]宋濂.元史·列传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455,3456,4084,4015.
[13]宋濂.元史·列传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3063.
[14]宋濂.元史·列传五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3915.
[15]宋濂.元史·百官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2187.
[16]王恽.秋涧集:卷79[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7]倪辂.南诏野史会正[M].王崧,校理.胡蔚,增订.木芹,会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375.
[20]党乐群.云南古代举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59.
On Yuan’s Promo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Yunnan
YANG Ran
The Yuan dynasty did not have much profound and ac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However,in Yunnan,Yuan’s ruling wa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advancement of politics,economy and culture.The termination of the feudal system of the Nanzhao-Dali period enabled Yunnan to keep pace with the Central Plain.The promo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nfucianism brought considerabl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o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Yunnan.
Yuan Dynasty;Imperial Examination in Yunnan;Confucianism
G405
A
1005-8427(2016)06-0060-5
(责任编辑:陈宁)
杨冉,女,云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昆明 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