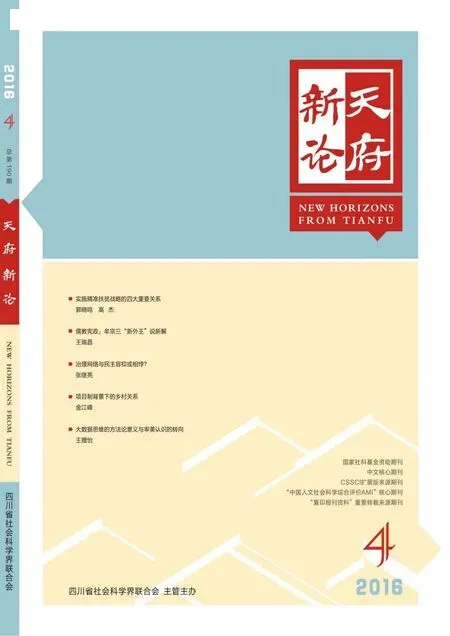治理网络与民主相容抑或相悖?
张继亮
治理网络与民主相容抑或相悖?
张继亮
摘要:面对日益复杂化、碎片化以及动态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效解决由之带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从这一方面来说,治理网络是一个能够带来良好治理效能的工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治理网络却与自由民主相抵牾。尽管治理网络与自由民主不相匹配,但它却能与各种后自由民主相辅相成,换言之,从后自由民主的视角来看,治理网络能有效促进民主。当然,治理网络也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发挥作为“元治理”主体的国家的作用。
关键词:治理网络 自由民主 后自由民主 元治理
继传统公共管理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治理网络 (governance network)这一模式被认为是能应对复杂化的(complex)、碎片化的(fragmented)以及动态化的 (dynamic)现代社会的有效手段。然而,人们往往仅从它带来的后果来对它进行思考,却很少考虑它对民主带来的问题或者没有考虑它是否蕴含特定的民主潜能这一问题。即使人们对上述问题有所思考,人们的意见也不太一致。有些政治理论家倾向于认为,治理网络会对自由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带来挑战〔1〕,例如,艾娃·索伦森 (Eva Sørensen)指出,治理网络会对代议制民主关于人民、代表、政治与行政相区分以及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区分的看法或假定带来挑战;而另外一些政治理论家则倾向于认为,治理网络的兴起有益于代议制民主,例如,罗德·罗德斯 (Rod Rhodes)认为,治理网络从功能上来说是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2〕。笔者认为,治理网络与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不匹配,但它却与各种后自由民主的理念相符合。然而,在具体分析这些观点之前,本文首先会简要说明一下治理网络兴起的背景及其基本概念,而且,本文最后一部分会指出,治理网络虽然与各种后自由民主模式相匹配,但它并非尽善尽美,它还隐藏着一些对民主不利的隐患,要消除这些隐患,国家这一“元治理”主体就要充分发挥其功能。
一、治理网络的兴起及其含义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人类社会不断面临着各种新的“变局”。从管理的视角来看,人们需要应对的这些新“变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从国际层面来看,许多跨国性问题,诸如跨国犯罪、跨国移民、国际资本的流动、全球气候的治理,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一个或两个主权国家自身难以应对或解决好以上各种跨国性问题。而人们所要应对的新“变局”则在国内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简单地说,人们需要面对一个日益碎片化的、复杂化的以及动态化的社会。碎片化不仅指的是社会日益分化为各种亚系统、子系统,或者说社会日益分化为各种独立的公共、半公共以及私人的机构,它还意味着人们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政治认同与归属日益多元化。复杂化指的是社会中的“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日益增多。“棘手问题”指的是一个与其它多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或者说,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会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造成相互冲突或截然相反的影响。动态化则是与复杂化联系在一起的,它指的是一些问题,特别是“棘手问题”,涉及到各种层级的各种制度、组织或机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对未来造成不可预期或不可估量的影响。〔3〕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甚至是新公共管理模式,都无法有效应对这样一个日益碎片化、复杂化以及动态化的社会。总之,面对人类社会的新“变局”,人们如试图对它们做出有效的应对,就需要探索新的应对模式,人们探索出的这一新的应对模式就是治理网络模式。
所谓治理网络,就是指在一系列规范性框架以及一些外部机构的约束之下,一些独立的以及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公共的、半公共的以及私人的行为者为达成公共或半公共的目的,通过协商与沟通等手段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水平的、自治性的行为模式。〔4〕这里所描述的治理网络只是观察现实的“理想类型”之一,现实中的治理网络可能并不会像定义里所描述的那样包含上述所有要素,但是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包含或体现一些治理网络的特征,换言之,它们具有“家族相似性”。
按照上述定义,治理网络包含多个行为者,这些行为者包括公共机构、半公共机构以及私人机构,也就是说,治理网络横跨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个领域。不仅如此,治理网络中的行为者还包括各种层面的超国家机构、国家机构以及地方性机构。〔5〕所以,治理网络从横向与纵向角度来讲囊括了各类行为者。这些行为者拥有独立性以及自主性,并且具有各自独特的资源,例如政府部门拥有权力,非营利组织等半公共机构拥有正当性,企业拥有资金。正因为治理网络中各个行为者具有这些特点,所以,这些行为者如要实现公共或半公共目标就不能依靠强制来达成,正如萨拉蒙所说,在治理网络内部,“任何实体 (包括国家在内)都不能将其意志长期施加于他者”〔6〕,换言之,治理网络中的行为者需要依靠“协商和说服”才有可能达成目标。所以,基于以上特点,治理网络是“一种独特的协调行动与分配资源的治理框架”〔7〕。治理网络这一独特的治理框架也正因为具有以上特点才能够有效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新“变局”,即,它能有效应对各种跨国问题,应对各种“棘手问题”,甚至可以应对日益复杂化、碎片化以及动态化的社会。
毫无疑问,从治理效能的角度来讲,治理网络是一个有效的治理工具,它能够有效应对目前的各种新“变局”。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将视野仅仅局限在关注治理网络的治理效能上,他们忽略了关于治理网络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治理网络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的议题:它是对民主的挑战还是对民主的完善?如上文所述,学者们即使关注这一议题,他们在这一议题上的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其实,探究治理网络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的关键点在于厘清民主的含义,因为,“民主”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数概念而是一个复数概念,或者说,“民主”这一标签之下囊括了各种类型的民主,“从字面上看,民主是指‘人民的权力’,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民主一词还代表着某种东西,问题不止是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同时还有民主是种什么事物。”〔8〕
二、治理网络与自由民主
“民主”一词虽然可以贴到很多民主模式之上,例如古典民主、共和主义民主、自由民主、直接民主、竞争性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合法型民主、参与型民主以及协商民主等〔9〕,但是,目前占主要地位的民主模式还是自由民主或代议制民主。自由民主的基本预设包括:一国范围内的全体公民构成的人民;由人民定期选举产生代表,代表们替选民们做出各项决定并向其负责;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分离,公民在公民社会之中拥有宪法所保护的生命、财产、言论自由、结社等方面的公民权利;政治与行政相分离,即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表与行政机构相分离。〔10〕治理网络对自由民主上述特征均构成了挑战。
自由民主预设了它所指的“人民”就是本国范围内的成年公民。然而,治理网络对其行为者并没有做出这样的预设,它的行为者既可以是来自于国内层面的非盈利组织或私人公司,也可以是来自于国际层面的相关行为者,特别地,当一国政府无法单独解决某些跨国性的国际问题而与其它国家或国际政治、社会团体结成治理网络而共同应对这一问题时,这一情况尤为明显。当一个治理网络之中的行为者主要是由其它国家或国际行为者构成时,它实际上就打破了自由民主关于“人民”的预设。
自由民主的另外一个重要预设是人民行使主权,“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11〕当然,人民并不是直接决定具体的国家事务,而是由平等的成年公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然后由这些代表替他们做出决定,选民们可以对这些决定进行讨论、批评或者质询,但是他们自身并不能够做出决定。尽管如此,对于这些决定,代表们也需要向选民们负责。相比之下,治理网络之下的行为者并不是像代议制民主之中的代表那样通过全民选举产生的,它们大多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半公共目标而结成非正式网络,通过做出有约束力的决策来约束与这些决策有关联的利益相关者。治理网络中的行为者通过履行类似于代议制民主之中的代表们需要履行的相关职能的方式来与代表们争夺代表资源或正当性资源,虽然这些行为者并不像代表们那样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如此,如果说,在代议制民主之下,代表们责任非常明确的话,那么,治理网络的兴起就会带来一个重大的问责 (accountability)问题,即,由于治理网络中的决策是由多元行为者制定的,那么具体由哪一个行为者对其负责呢?
古典自由理论家诸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对政府权力非常警觉,他们纷纷阐明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以及限制权力的方法。自由民主通过各种方式来落实这些古典自由理论家们关于限制政府权力的论点,其中,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为公民留下自由的活动空间就是重要方式之一。这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划清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密尔在 《论自由》中明确表达了划分这一界限的标准:“人们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干涉出自个人还是出自集体,其惟一正当的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12〕如果说自由民主划定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的话,那么治理网络的出现则模糊了这一界限。既然治理网络包含了公共、半公共以及私人行为者,那么,作为公共行为者的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到个人生活和非盈利组织的活动当中去,即使个体或非盈利组织的行为并没有“伤害”到他人。简言之,治理网络对自由民主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划分提出了挑战。
自由民主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设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即威尔逊所倡导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自由民主的视野下,政治领域是代表们或政务官制定法律法规、确定政策内容、目标或方向的领域,而行政领域是行政官僚们执行法律、法规以及确定实现政策的方式或手段的领域,简言之,在自由民主理论家看来,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治理网络使自由民主这一关于政治与行政划分的预设归于无效,其原因在于,行政机构是治理网络中的重要一员,它们不再局限于执行治理网络内部的各项政策,它们还会参与制定这些政策,具体而言,它们会参与确定这些政策的内容、方向及其所欲实现的目标。
总而言之,治理网络对自由民主四个基本特征都提出了挑战,即治理网络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成员;它会与代议制民主之下的代表争夺正当性资源,并且会带来问责问题;它会对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划分提出挑战;它会模糊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界限。如果说,治理网络会对自由民主带来如此重大的挑战,那么,即使它拥有非常高的治理效能,人们也不得不对它存在的正当性产生疑问。然而,这里的问题在于,治理网络虽然会给自由民主带来挑战,但它并不见得会对民主自身带来挑战。
三、治理网络与后自由民主
目前,自由民主虽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模式,但是它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民主模式。许多理论家纷纷提出了其它各种非自由民主模式,诸如竞争性民主 (competitive democracy)、结果性民主(outcome democracy)、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以及争胜性民主 (agonistic democracy)等等,我们可将这些非自由民主模式称为“后自由民主模式”。治理网络虽然与自由民主相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与这些后自由民主模式相匹配。
(一)治理网络与竞争性民主
埃奇奥尼-阿累维 (Etzioni-Halevy)在 《精英的联合:西方民主的问题及潜能》(The Elite Connection:Problems and Potential of Western Democracy)一书中具体论述了竞争性民主的基本要点。在阿累维看来,代议制民主的核心特征并不在于选民通过选举来任命或控制政治精英,而在于它能够制度化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或者说,它为政治精英之间相互制衡提供了一个平台。〔13〕其次,阿累维认为,传统代议制民主理论忽略了一些诸如社会运动领袖以及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之类的半公共性的亚精英(semi-public sub-elites)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这些亚精英能够有效提升民主的质量,因为他们能够从纵向的角度来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施加压力或进行制衡。此外,阿累维也认为这些亚精英还可以充当联系普通公民与统治精英的纽带,他们可以将普通公民的诉求传达给统治精英,从而通过间接的方式促进公众的政治参与。
从竞争性民主的视角来看,治理网络能够有效促进民主。首先,治理网络提供了培养与组织各种半公共性的亚精英的平台。其次,治理网络加强了普通公民与各类半公共性的亚精英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些亚精英,公民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去。最后,治理网络提供了各类半公共性的亚精英与统治精英之间的交流、沟通的平台。总而言之,治理网络与竞争性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它能有效促进竞争性民主。〔14〕
(二)治理网络与结果性民主
阿奇恩·冯与艾瑞克·赖特 (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提出一种他们称之为“赋权参与治理”(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简称EPG)式民主。他们认为,EPG式民主的一个根本性准则是,判定一个民主制度好坏的标准是它能否有效解决人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15〕以此为标准,他们认为,要建立一个优良或有效的民主制度需要遵循三个方针。第一,民主制度要以具体问题为导向,要面向实际情况,所以,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永恒的民主制度,所有民主制度都是为了具体问题而设立的。第二,民主制度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在于它能否促进与某项政策有关的利益相关者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第三,必须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具体问题,因为,许多具体的冲突只能通过谈判与协商的方式才能解决。
治理网络是促进结果性民主的有效方式,或者说,它完全符合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的三个方针。首先,治理网络出现的目的就是要去解决各种实际的、具体的问题。其次,治理网络倾向于促进各个行为者自下而上参与到政策制定当中去。最后,由于各个行为者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且拥有各具特色的资源,所以,各个行为者需要通过讨论、协商的方式才能达成共识,才能实现目标。〔16〕
(三)治理网络与协商民主
建立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协商民主强调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理性说明等交流方式进行沟通,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互惠性、公共性的理由来表明自己的观点的合理性,从而最终试图达成共识。用埃米·古特曼(Amy Gutmann)和丹尼斯·汤普森 (Dennis Thompson)的话来说,协商民主即“自由而平等的公民 (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17〕协商民主强调的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共同参与到某个决策活动之中去,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理性说服等各种方式向其他人说明自己带有互惠性、公共性的观点,以此试图说服别人,同时期望别人也提出具有类似特点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从而最终就某项政策达成共识。
(四)治理网络与争胜性民主
尚塔尔·墨菲 (Chantal Mouffe)在区分了“政治”(politics)与“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基础上提出了“争胜性民主”这一概念。“政治性”指的是人类社会之中以不同形态呈现出来的各种敌对面相,而“政治”则指的是“因受到‘政治性’面相的影响,而在永远潜在地充满冲突的情况下,试图建立某种秩序与组织人类共同生存的一套实践、论述以及制度。”〔18〕或者说,政治意味着在多样性冲突中创建统一性,“它关注的永远都是藉由决定‘他们’来创造‘我们’”〔19〕。基于此,墨菲认为,民主政治并不能克服他们/我们的区分,这一区分并不能通过理性协商的方式加以祛除,所以,民主政治关注的是如何构建这一区分。墨菲认为,民主政治的目标是“不复将‘他们’认为是应被歼灭的敌人,而是将之视为某些虽然观念与我们的立场相互扞格,然而其捍卫自己观念的权利却不受到我们质疑的人。”〔20〕简言之,墨菲认为,民主政治承认人们之间在观念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差异是一种不可消除的存在,但这一差异并不是敌人的象征,与我们观点相异的他人只是我们的对手,他们不是我们要消灭的敌人,我们需要尊重对手表达其意见的权利,民主政治鼓励各种不同的观点相互砥砺。
治理网络从两个方面能促进墨菲提出的这种“争胜性民主”。首先,治理网络包含了观念、价值观各异的行为者,这些观念与价值观之间会在治理网络中相互碰撞,相互竞争。其次,由于治理网络中的各个行为者是相互依赖的,所以,即使几个行为者之间在观念上相冲突,他们也会通过对话与协商而不会运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执和分歧,除非他们放弃通过治理网络来达成他们试图实现的目标。
通过分析四种后自由民主模式的要点,我们发现,虽然它们之间有分歧,但治理网络能够有效地促进这四种后自由民主,即,治理网络中的行为者多元化,行为者之间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争执以及治理网络促进政治精英、亚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交流等面相,能够从不同的方面有效促进竞争性民主、结果性民主、协商民主、争胜性民主这四种民主。所以,这就证明了治理网络虽不能与自由民主有效地匹配起来,但它完全能够与其它一些非自由民主或后自由民主模式相匹配。既然治理网络一方面具有非常高的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当高的民主效能,那么,这是否说明治理网络已经是尽善尽美了呢?
四、治理网络与国家
治理网络虽然兼具治理效能与民主效能,但这并不能说明它是完美无缺的。治理网络存在三方面的问题:包容性问题、平等问题以及问责问题。
治理网络之所以兼具治理与民主效能的重要原因,是它能够将与特定政策议题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容纳到治理网络之中。与这一点相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当一项政策将特定行为者影响至何种程度才能将他们算作是“利益相关者”,并将他们纳入到相应的治理网络中?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些治理网络中的某些行为者可能会通过故意忽略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或故意封闭与特定政策相关的信息的方式来将他们排除在制定政策活动之外。
与上述包容性问题相关的是,治理网络无法保证参与网络的平等以及行为者在参与网络过程中具有平等的谈判或协商能力。如果说治理网络中的某些行为者会故意排除某些利益相关者的话,那么,即使他们不那么做,某些利益相关者也仍然会因为其自身缺乏相关的能力、资源来接近治理网络。其次,即使治理网络能够保证所有利益相关者自身有能力、资源来接近治理网络,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能力、资源差别非常大,所以,他们在治理网络中的话语权差别也非常大。然而,人们要确保利益相关者在能力、资源方面实现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能确保他们在能力和资源方面的差别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一范围的界限又是什么?
与治理网络相关的最后一个问题牵涉到问责的问题,即人们如何确定治理网络中的责任主体?治理网络中行为者的多元化使得问责问题成为令人挠头的难题,“政策是在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者网络中被制定出来的……因为很多参与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所以,从原则上来说,人们很难确认谁应该对政治结果负责,因而很难确立相关参与者的政治责任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21〕
治理网络存在的这些问题可能会抵消它所具有的优势。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作用,或者需要“找回国家”,需要发挥国家作为“元治理”主体的功能。从规范意义上和能力上来讲,国家应该并且能够有效应对治理网络中的这些问题。从规范意义上来讲,国家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它有责任确保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它有责任根据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去解决治理网络中存在的包容性问题、平等问题以及问责问题。如果说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去解决治理网络中的这些问题,那么,它是否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因为,很多政治理论家都纷纷指出国家已经“空洞化”、“被边缘化”,国家失去了承担起其“元治理”主体责任的能力。实际上,情况并不是如此,国家拥有足够的能力与资源来承担起其作为“元治理”主体的责任,因为,国家仍然拥有“领导权和权威,财政或行政资源,丰富的专业知识,充足的信息和制定法律、规则或规范的能力”〔22〕。国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话语塑造、过程管理以及直接参与的方式来应对治理网络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实现“对治理的治理”。〔23〕
(2)基尔莫市挡水坝。澳大利亚基尔莫市,于1996年修建一座均质土挡水坝,坝高为13 m。蓄水使用后发生了管涌破坏,渗流冲蚀成孔洞,发展成贯穿性通道,直径达到11 m。经过技术修复后,在下游处再次出现直径为0.15 m空洞,引发管涌破坏。
参考文献:
〔1〕Eva Sørensen,“Democratic Theory and Network Governance”,Administrative Theory&Praxis,24:4,pp.693-720.
〔2〕Rod Rhodes,Understanding Governance:Policy Networks,Governance,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Buckingham/ 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p.9.
〔3〕Eva Sørensen and Jacob Torfing(eds.),Theories of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5.
〔4〕Martin Marcussen and Jacob Torfing(eds.),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 in Europe(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5.
〔5〕Jon Pierre and B.Guy Peters.治理、政治与国家 [M].孙本初译.台北: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99-104.
〔6〕〔美〕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工具 [M].肖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
〔7〕Mark Bevir,Democratic Governanc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32.
〔8〕〔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 [M].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8.
〔9〕〔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 [M].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4-5.
〔10〕〔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 [M].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94、109.
〔11〕〔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 [M].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3.68.
〔12〕〔英〕约翰·穆勒.论自由 [M].孟凡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13〕E.Etzioni-Halevy,The Elite Connection:Problems and Potential of Western Democrac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pp. 53-54.
〔14〕Eva Sørensen and Jacob Torfing,“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in Eva Sørensen and Jacob Torfing(eds.),Theories of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238.
〔15〕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Deepening Democracy: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in 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eds.),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Real Utopias Project Series,IV(London:Verso,2003),p.25.
〔16〕Eva Sørensen and Jacob Torfing,“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in Eva Sørensen and Jacob Torfing(eds.),Theories of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240.
〔17〕谈火生.审议民主 [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7.
〔18〕〔比利时〕珊妲·慕孚.民主的吊诡 [M].林淑芬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5.87.
〔19〕〔比利时〕珊妲·慕孚.民主的吊诡 [M].林淑芬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5.88.
〔20〕〔比利时〕珊妲·慕孚.民主的吊诡 [M].林淑芬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5.88.
〔21〕J.G.March and J.P.Olsen,Democratic Governanc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158.
〔22〕Stephen Bell and Andrew Hindmoor,Rethinking Governance:The Centrality of 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49.
〔23〕Jacob Torfing,“Network Governance”,in David Levi-Faur(ed.),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08.
(责任编辑:赵荣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别思想史”(编号:13&ZD149);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代西方自由帝国主义理论评析”(编号:TJZZ15-009)。
[收稿日期]2016-04-13
[作者简介]张继亮,政治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讲师。天津 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