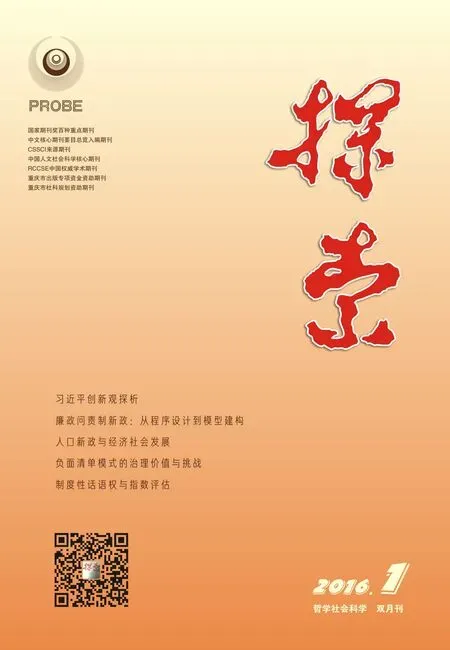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法治化: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突破口
陈 仲
(四川文理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达州635000)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政治生态”问题。生态原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自然界的天然状态,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运行。良好的自然生态是各生态系统各元素之间处于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状态。政治生态遵循的是政治运行法则,即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权力为公。从“社会契约论”视阈来看,国家或权力产生的根源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只有为公的权力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具有执政的合法性、运行的可持续性。但理论上的自洽性、圆满性难以遮蔽和解决现实政治中的矛盾性、残缺性。古今中外,权力为私的滥用情形并不鲜见,较为极端的方式是国家权力归属君主个人或者家族所有的世袭政治,其实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即使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政治体制中,哪些人上与下以及如何上与下等问题都会直接影响政治生态的好与坏。一般而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上”者,在交接权力的过程中,也会按照相应的方式来进行。以公开、竞争选拔而“上”与“下”的法治方式凸显任人唯贤,这就为良好政治生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以秘密、个别人说了算而“上”与“下”的人治方式就难免任人唯亲,为政治生态的恶化埋下了祸根。因此,要建设良好政治生态,必须做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法治化。生态更多地体现为动态特质,环境更多地表现为静态特征,环境再不好也有适合其生长的动植物,而生态失衡则会遭遇毁灭性的灾难。2015年7月起施行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态文明建设。
1 权力滥用:不良政治生态的基本表征
不良政治生态主要是指在权力场域的较大范围内普遍存在着权力滥用现象,既可能表现为明显的违法乱纪,又可能表现为在“政治场域”中普遍存在的“潜规则”行为。
第一,官僚主义蔓延。官僚主义不同于官僚制,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是高效率的管理模式。斯廷奇康姆提出,如果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在现有岗位上所展现的熟练技巧将会获得晋升,那么这一动力就是最强劲的,晋升制度将会使组织走向成功[1]198。然而,任何官僚组织都必然会出现“彼得原理”①即在等级制中,每个雇员都会升到其能力不够的级别,不称职的人待在他们不能胜任的岗位上,而称职的人也会因升职而变得不称职。,也即是“天花板”效应,当一个人升到一定职位之后再无可能上升,因而工作怠惰再无工作热情和激情,出现贝卡利亚所说的“政治惰性”[2]187。罗伯特·默顿认为所有官僚组织似乎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莫里斯所称的“帅才倾向”,即管理者的能力往往言过其实;另一个是“追求次要目标的战略倾向”,即在管理中普遍地采用人治做法[3]208,与之伴随的现象必然是官本位思想的盛行,低效运转、庸才当道、压制个性的“官僚综合症”。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进行了生动的刻画②官僚主义具体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讲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同时,还会出现“帕金森定律”问题,即行政管理人员比一般雇员的增长要快得多[1]325。高一级的管理者希望有更多低一级的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随意指挥下级,实现动口不动手的“老板化”;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更大的、稳定的官僚“利益共同体”。无过就是功的“太平官”必然出现,很难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更遑论有什么创新的奋发有为。
第二,权力中心主义。从理论来看,无论是社会契约理论还是委托代理人理论都认为权力源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从现实来看,民主法治国家的权力同样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即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赋。在专制条件下,统治阶级一般都将权力作为实现小团体利益和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工具,权力要么来源于神授,要么来自于先王,而很少出自于人民大众,这就必然出现权力者与民争利的“寡头统治铁律”③指组织会呈现被选举人统治选举人、被授权人统治授权人、被委派代表统治委派人的情况,其产生原因主要是由于人性、政治阶级的实质、组织自身的特性。。通向权力的政治组织手段异化为终极目标,“主仆颠倒、反仆为主、倒主为仆”,整个政治关系发生错位,自然形成权力中心(本位)主义。权力中心主义产生的原因除了领导干部自身的权力欲望导致以外,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所处的权力场域,即便是“哲人王”,一旦深陷其中也会难以自拔。领导干部为了了解民情社情进行实地调查,但却往往变成前呼后拥的“跑马观花”,下级汇报更多的是优异成绩而极少甚至无问题。领导干部在不完全了解权力边缘,即社会底层真实信息的状况下就进行决策,这样的决策当然难免具有盲目性。盲目的决策不但破坏良好的政治生态,而且还会祸国殃民。阿伦特在其《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专门描述了在领袖周围筑起由精英组织组成的一种不透明的“神秘气氛”,形成一种“不可触及的优势”,使其“神秘化”[4]477。在极权政治垮塌之前,这种人造的神秘“权力场”可以胡作非为、为所欲为,不但可以吞噬人的生命,而且可以改变人性。
第三,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权力滥用的极端形态,是不良政治生态最突出的表现。无论是权钱交易和权学(色)交易,还是“塌方式”“前腐后继式”腐败,其本质都是以权谋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许多“老虎”“苍蝇”落马就说明了我国的政治生态建设还有很大的空间。如果出现了以上权力滥用情形,不采取相应的纠偏措施加以矫正,而是听之任之,必然导致政治生态恶化。不良政治生态,比如世袭政权容易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并最终演变为“全国性灾难”[5]65-66,这种灾难最终演化为政治危机,执政者失去政权是迟早之事。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强调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现实贪腐案件中所揭秘的“边腐边升”现象就是该下的领导干部不下,结果反而上,而正直清廉有为者该上,结果反而下,这些现象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污染了整个政治环境,破坏良好政治生态。因此,领导干部的上与下不但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生态文明的发展程度,而且成为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突破口。
2 领导干部上与下:政治生态发展的关键节点
领导干部的“上”是指由“民”而“官”或由低一级官员升为高一级官员,“下”则与之相对。在领导岗位既定的情形下,有上者也就必然有下者,反之亦然。如何“上”,“上”需要满足哪些基本条件,上任后有无任职期限,如何“下”,“下”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发展。
从正面来看,在民主法治国家,领导干部“上”与“下”的条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领导干部通过竞选而“上”,任职有相应期限,比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重要职位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美国宪法也有对总统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上任之前的竞选、组织的考察,可以将最适合的人任用到相应的领导岗位上去,这在最大限度上排除了品德不过关、能力不过硬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同时,对于不再继续适合当领导干部的人,可以中途换下,即使没有及时换下,也只是在短期内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不会对国家与社会再产生持续性危害。
从反面来看,在专制集权国家,领导干部的升迁浮沉完全决定于上级,掌握在君主及其亲信等少数人手中,这种人治状态下的干部升迁,必然产生“长官意志”现象,即“上级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下,必然出现“官大一级压死人”“假民主真专权”的一言堂现象,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必然培育出一些唯上级马首是瞻的奴性官吏,这些官吏对下级颐指气使,高高在上,完全是其上级的“翻版”。自上而下,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官员不论大小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势必造成官民关系紧张。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民不聊生,生不如死,风平浪静的外表不能掩盖其“波涛汹涌”的潜在危机。当人民群众的忍耐达到极限就会直接导致革命,社会进入吴思先生所说的“崇祯死弯”,即达到了政治生态的极端恶化程度。“一个专制君主,不论性情多么善良,也不能不在暗中摸索,从别人的报告中了解情况,依靠别人的帮助做出决定……什么地方有专制政体,什么地方就会永远有专制带来的罪恶、反复无常和专横迫害。”[6]333-334“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必然反复重演。
从现实来看,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转型国家还存在着“能上不能下”“上下都未完全依法”的典型不良政治生态之病根。能上不能下或者都由个别人或者极少数人说了算就是一种相对没有限制的权力运行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上与下不决定于人之德才,而决定于与上级领导关系的亲疏度。“能上不能下”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一个人一旦进入领导干部队伍,除非出现死亡或者重大犯罪等情形,一般都不会退出该队伍;二是指“能升不能降”,即一旦权力者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官位后,在以后的任职中就不会低于该官级。这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旦一个领导干部还没有“到点”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即使是没有犯错误的主动辞职,在人们心目中也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种惯性想法,即该领导干部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众口铄金,有口难辩,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担“被问题化”的风险,这就造成即使一些领导干部厌倦了领导工作,也要“拖”到“退点”。同时,在干部任用上一般都遵循年龄、资历的原则,“很多部门往往把资历深浅和辈分大小作为提升和使用人的主要依据”[7]。无论组织和个人,都得考虑“情面”,最差也得换一个“闲职”,实际是退而不下。领导干部任职期限与人事制度中的退休年龄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实质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实际上,大多数权力者总是不想主动退出“权力舞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管理指挥别人总是比被别人管理指挥更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权力的“附加利益”太多。再则上领导干部“上”与“下”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久而久之会造成以权力而非以权利为中心,以资历而非以能力为中心,以领导人而非以事业为中心,完全背离了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的行为标准,形成一种不良的政治生态。
3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法治化:良好政治生态的源头活水
3.1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化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领导干部的上与下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如果没有法治作为后盾,就跳不出任人唯亲之窠臼,也就难以建立良好政治生态。佛罗伦萨1434年到1494年的统治者经常说,必须每隔五年彻底“整顿”一次国家,对违反生活方式的行为恶劣者严惩不贷[8]315。每隔一段时间的“整顿”和“清除”,对不合格者进行更换,对严重违法者要进行惩罚是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一种实践。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明确指出,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度,同时需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等要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是无限期的”[9]332,他还主张打破“论资排辈”的落后习惯,要破格选拔人才。从理论上讲,对于没有办法也不能分割的权力,只能借助法治,以法定方式规定权力范围、权力运行、权力任期、权力更换等,宪法正义也强调正当地取得国家公职,对权力分配、议会和宪法法院的权力进行控制,对规整权进行约束等原则[10]233。如此既可以调动更多优秀的人热心于公益事业,参与公共管理,又可以有效避免权力作恶者继续作恶。
一方面,法律应规定“上”的条件。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上”主要考虑人之“德”与“才”两个大的方面,更加注重人之德。德指美德,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和礼义廉耻“四维”都是对人之美德的一种阐发,美德作为选官标准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根据《尚书·皋陶谟》记载,如何选拔官员,皋陶跟大禹讨论,总结出“为政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德”可以说是官员道德水平的理想境界,推举“德才兼备”之士是孔子治国思想的重要观点[11]。同时,在国家管理过程中也主要强调德治,施行仁政。孔子在《为政》的开篇中就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核心是要求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儒家思想为主线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官德,注重道德修养,治国首先就得修身、齐家。修身放在第一位,只有当个人品德达到了一定的要求和标准,才有资格被纳入选官范围,用人先观德,后察才。《贞观政要》确立以“公平”“仁义”为准绳的择官准则,在提拔、任用官员时往往比较注重对官员道德水平的考察[12]。墨子也主张不分亲疏贵贱,要任人唯贤。在古希腊,个人品格体现为“行为庄重、考虑周全、公平正直、宽容大度、忠实可靠”,这些品质连同“非凡军事才能”构成了极富魅力的性格组合[13]88。统治者不是富有“物质上的黄金”,而是富有通往幸福所必需的那种“精神上的黄金”,即“善的和智慧的生活”[14]281。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中指出,当罗马共和国把执政官一职授予公民时不讲年龄与身世,但它总是追求德行;如果没有世所罕见、登峰造极的德行,罗马人是根本不可能征服其他人的;国家的真正强大,依靠的不是金钱,而是德行[8]202-300。中世纪的阿奎那也认为,人们相互之间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个人的“知识和美德”,最优秀的人应该担任统治者,统治的职责应根据美德水平来进行分配[13]240。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干部选拔任用标准,邓小平1979年借用叶剑英提出的选拔接班人的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此外,还需要有充沛的精力[9]222。
另一方面,法律应明确“下”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党政干部任用工作条例》规定了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所应该具备的工作经历、文化程度、身体条件等“上”的基本资格以及免职、辞职、降职等“下”的基本情形。《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规定了“下”的理由,即到龄免职、任期届满离任、问责处理、调整不适宜任职干部、健康原因、违纪违法免职等。更多地指向本人以外的客观原因,可以借鉴诸如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如果属于违法犯罪而“下”的领导干部,就将永远取消其“上”的资格。从现实来看,还应该增加由于领导干部自身主观原因的主动辞职,这需要完善领导干部辞职的相关法律规定。
3.2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程序化
相对于“下”而言,“上”是领导干部进入权力场的关口,如何“上”是维持良好政治生态的“第一道防线”,要通过严密的程序筛选出优秀人才,将德才不合格者阻止在关口之外。民主法治社会采用竞争性选举的方法来任命领导干部,在此过程中当然也包含着候选人的提名、自荐、推荐等程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强调要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中国共产党党政干部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方式之一。有竞争才有比较,有比较才能够区分出优劣,比如一些地方曾经试行过的“公推直选”“政治竞选”使优秀人才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走上领导岗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竞争性选举就犹如“赛场选马”,虽然不能选择出最好的“千里马”“上等马”,但至少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病马”“劣马”“钝马”。一般而言,选举产生的官员认为工作是否有效取决于公众的满意度而非那些最有权势的“特别利益集团”。因此,取信于民而不是讨好于民成为选举官员的工作原则,取信于民就得为大众服务,为民服务本身就是美德,在服务过程中又塑造美德、提升美德。选举被认为是代议制民主的最重要内容,有没有竞争性选举不仅成为评判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最重要的“标尺”[15]45,而且也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生态是否良好的基本标志。只有在竞争条件下产生并在法治约束下的权力才不会异化为私人谋利的工具,才可以有效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避免懒政、庸政、散政,确保勤政、廉政、能政。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指岗位上领导干部的变化,而岗位本身未变。在良好政治生态中,领导干部的上下通道都应该是畅通的,无论是自荐、推荐而“上”,还是主动请求辞职或者其他原因而“下”,都要按照严格程序来进行,因为程序化本身就是法治的基本要义。
3.3 领导干部权力运行公开化
“上”与“下”犹如比赛中接力棒的“交”与“接”,不但权力的交接需要公开,而且权力的整个运行过程都需要公开。权力运行公开是法治的题中之义,不仅可以有效预防和及时处理权力滥用,而且是领导干部“上”与“下”的最重要依据。“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要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6]184这个界限不仅表现为权力制衡的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且更重要地体现为以民众主权的权利监督权力。从现实来看,无论哪一个国家,腐败案件的曝光多数都归功于群众,因为“再狡猾的狐狸也难以逃脱群众的火眼金睛”。“一旦‘治权'披上‘公共意志'的道德外衣,并以‘主权者'的口气声称不可分割和不受约束,便极有可能演化为自命不凡的现代‘僭政'。雅各宾派专政说明了这一点。”[17]在法治保障良好的政治生态里,领导干部即使“下”了也不能完全免除责任,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的那样,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即责任倒查机制。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人民群众是决定领导干部上与下的最佳评判者。为此,必须要保障人民群众对于权力的有效监督,这自然需要赋予人民群众广泛的言论表达自由权,言论表达自由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标志。
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视角、所处环境的不同,对同一个人是否可以“上”的问题,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可能绝对统一。这不同的声音就好比生物多样性,任何一个自然生态系统的良好发展都需要以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如果一个自然系统中只有一种生物,就必然造成生态失衡,最终的结果是这种单一的生物也难以生存。因此,对于执政者而言,应该听得到不同的声音和表达,历史上所有盛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位开明的君主,不但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这就自然形成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如果将不同的声音视为“异己”加以打压、封杀,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不敢说的不良局面。未公开表达并不代表不会以其他方式表达,万马齐喑并不代表没有声音,潜藏着的可能还是“一边倒”的反对之声。压制不同意见是愚蠢之做法,不仅没有阻止思想运动,有时反而加速这个运动[18]192。畅通渠道,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开言路,学会倾听来自各方对在职领导干部的不同评价,兼听则明,在调查核实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决定领导干部的“上”与“下”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权力行使者有批评、建议、控告、申诉等权利,这不仅是主权者的权利,而且是维持良好政治生态的必备条件。如果说监督权力是政治生态良性运行的防御系统,具有“杀菌”和防止肌体发生“癌变”的功能,那么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不贷则是政治生态良性运行的救济系统,具有矫正的功能。与此同时,在权力场域,人格独立是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前提。从横向看,要有效避免官官相护、互相包庇的不良现象,应该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良好状态;从纵向看,上下级之间要形成和谐关系,以为人民服务为统领和归宿,各自在职权范围内履职,尤其要避免下级在上级面前完全失去人格尊严,要在真理面前保持判断的独立性。总体来看,如果权力的纵向、横向、侧向等多个面向都暴露在阳光下,权力也就真正被关进了笼子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权力滥用。从“四十位教授同台竞技一个处长岗位”到有些厅级干部主动辞职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只有从制度设计层面上减少权力的“附加利益”,并有效防止权力可能带来的任何“隐形利益”,领导干部的“上”与“下”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件再寻常不过之事。
总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法治化是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能上能下”或者“可上可下”是指一种权力的运行状态,一个人既应有从士兵升为将军的竞争勇气、拼搏精神,也应有从将军到士兵的坦然接受、从容面对的态度。同时“上”“下”是相对的,从权力的来源看,人民群众或者说被管理方有权决定谁上谁下,但从权力的现实运行来看,权力以国家机器作为坚强的后盾,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所有人都要敬畏权力。大家都应有一个共识:如果没有处于“上位”的有权威的公共权力,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必然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良好的政治生态蕴含着权力不是什么荣誉,而是一种责任、使命和担当,领导干部的上与下,由民而官、由官而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上得去、下得来”还指领导干部的一种健康政治心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是一部重要党内法规,牵住了权力运行的“牛鼻子”,使权力在正常的轨道运行。能上能下是干部任职的一种方式、一种样态、一种自然状态,更是常态。从本质来看,领导干部是一种职权,更是一种责任,是一个为民行使权力的过程,任何一个领导干部担任领导职位之前是普通群众,卸任领导职务后又变成普通群众,领导干部的“上”与“下”真正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参考文献:
[1] 斯坦因·U.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M].任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 吴思.潜规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 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M].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 文丰安.化解党员干部论资排辈困局的变革思路[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5):83-86.
[8] 马基雅维里.论李维[M].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莱因荷德·齐佩利乌斯.法哲学[M].金振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徐大同.孔子仁政、德治、礼范的治国之道[J].政治思想史,2013(1):1-12.
[12]韩伟.借鉴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N].人民日报,2013-05-30.
[1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4]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明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5]王绍光.民主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7]张凤阳.共和传统的历史叙事[J].中国社会科学,2008(4):79-95.
[1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