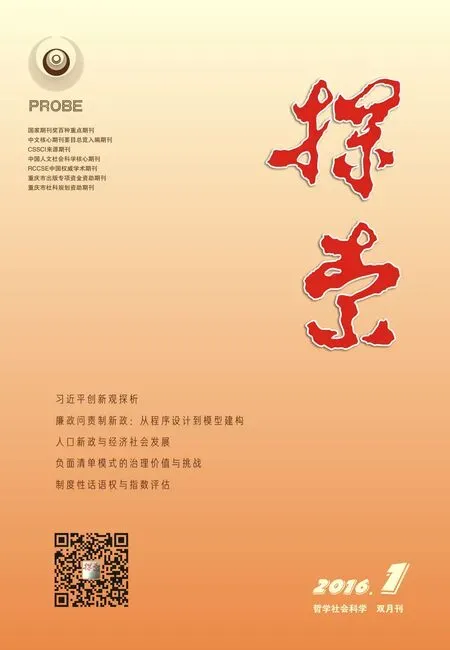超越绿色资本主义
——社会生态转型和全球绿色左翼的视点
[奥]乌尔里希·布兰德著,王聪聪译
(1.维也纳大学政治学系,奥地利维也纳1010;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北京100191)
“一切照旧”是当前欧洲政治流行的箴言。主流的公共政策和讨论都倾向于认为,紧缩政策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挽救措施,而没有其他出路和替代性方案。我们也经常被灌输这样的观念,即日益增长的贫困率,自下而上的财富再分配,以及社会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削减,都只是暂时性的,我们终将重回增长之路。未来是当前的延续,相应地,只要资本利益和富人地位受到威胁,政府就会有重大决策出台。
事实上,社会运动、替代性企业家、进步的政府官员、左翼政党、批判性学者,都在提出并实施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替代性方案,而它们也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希腊激进左翼政党“激进左翼联盟”领导的新政府,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015年即将举行的西班牙大选中,新成立的左翼政党“我们可以”(We Can),也很可能会获得选举胜利①该党在2015年议会大选中获得69席,成为西班牙议会中第三大党——译者注。。同样,中国也正在发生着环境保护运动。
将环境问题与正义问题相结合,是当前社会争论的核心性议题之一,也即绿色左翼的政治分析,或者说“社会生态转型”的战略争论。在西欧和拉丁美洲的政治讨论中,资本主义的增长机制本身已经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持续的增长,已经造成潜在的社会不稳定与诸多方面的社会冲突。依此,本文将着重阐发“去增长”(degrowth)这一概念。因为它很容易被理解为来自北方国家的帝国主义概念,以及对于穷人的紧缩方案。但笔者认为,从绿色左翼的视角去理解增长概念,会大有裨益。同样重要的是,对增长的更加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分析,是实现人们福祉的前提条件。很显然,不顾任何代价的数量型增长和关心生产与消费过程、社会关系、正义与福祉的质量型增长,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后者是对资本主义增长机制的批判。最后,笔者将从绿色左翼视角出发,重点阐述全球社会生态转型的理论观点,以及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
几年前,围绕着“社会的和大转型”(Societal and Great Transformation),发生了一场关于生产和消费系统层面的可能改变的激烈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则是能源和自然资源问题。这场争论的基本共识是:生态问题将在未来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急剧地减少资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改变当前主导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问题[1]687-711。进步的自由主义精英,以及大部分社会民众,都对我们当前应对生态危机的方式心存不满:他们希望改变政治现状、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呼吁技术创新。但他们并不希望改变权力和财产关系,不希望放弃他们的地位,不希望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和竞争力。因此,他们更喜欢所谓的“绿色经济”战略以及生态现代化战略,比如,“智慧农业”就较好地掩饰了工农业副食品供应背后的复杂性、逻辑和权力关系,并将转基因食品贴上积极的标签。
社会生态转型主张是对绿色经济/生态现代化战略的超越。它代表着以解放之维解决多重危机的路径选择。其突出特征是:有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超越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对福祉的新理解、摆脱化石能源和核能依赖、社会劳动分工的解放等。此外,一个更理想的社会,不仅需要社会-经济生产层面上的“物质内核”(葛兰西术语),更需要具有吸引力的多样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这其中的基本规范性要求是,重大的社会生态转型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或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比如,我们正在讨论的工业转型(如德国汽车工业转型),就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转型必须是一个社会-生态的学习过程——不是为了避免冲突,而是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因此,任何替代性方案都必须首先回答:谁来决定当前的主导性的、存在各种问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比如对科研、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交通与交流的形式、住房与城市发展、农业和食品;以及整体的发展路径等。其次,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的增长机制与世界市场发展的背后驱动力,以及如何民主地控制社会和社会自然关系。
“社会生态转型”概念,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等左翼智库和批判性学者中间,以及在进步的政党、工会、非政府组织内部等,已被广泛讨论。此外,这一概念还已出现在国际报道中,有时也被联邦与州政府官员所使用。面对创造利润和资本积累、扩大经济活动和资本主义增长机制、强化利益和权力关系的主导性的社会发展逻辑,以及由其产生并日趋强大和不可控的社会危机的爆发,“社会生态转型”概念的提出,便具有特殊的意义。
从一种批判性视角来看,“社会生态转型”的关键性假设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改变是持续发生着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进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2]240-268因而,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转型逻辑应该占主导地位。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2 社会生态转型的切入点
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因为已经存在着许多替代性方案的讨论、建议和可行性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捍卫自己的利益,反对当前不合理的政治秩序,并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来工作和学习——一种社会化的、合生态的方式。社会生态转型有很多切入点——它们是否以及如何代表整体利益,以及在哪种程度上能够被称为一种葛兰西所指称的、超越特定利益集团的新的“集体意志”,都依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创造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种能让生活变得繁荣与和平、个性得到彰显、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和文化。
汉斯·蒂对此指出,我们已经能够辨别出那些深刻重构社会进程的原则:合作代替竞争、平等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更多的经济规划、生产使用价值占主导地位[3]。其他的原则还包括,承认人们的不同身份——正如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所说的,自由社会的基础是“不因不同而畏惧”。
当然,发生在西欧的激烈争论,也使得人们变得日益明晰: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的倡议,并不是旨在制定一个总体规划或蓝图,生态社会转型这一术语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变化已经在发生着,而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创造着替代性方案,比如社区花园、互换小组、汽车共享、回收与再利用倡议等。此外,还有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抵制,关于食物主权、能源民主与城市权利的社会运动,以及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相结合的概念如“生产消费者”等。他们也经常被称作“改变的先驱者”。这些先驱者是非常多元化的,不尽然都是绿色左翼。对我们来说,一个重要挑战是发现这些替代性倡议,并建立、强化它们彼此间的密切联系,使之系统化,从而寻找其后资本主义和解放的潜力。
在笔者看来,关注这些小型改革、替代性主体及其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大大小小的倡议,就拓宽了人们对于繁荣的新理解。在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很多“改变的先驱者”将会日益认识到,他们所引领的变化应该被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下。为了摆脱其边缘化的地位,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相关性,他们可能要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因而获得民众的政治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
社会生态转型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也是经常在绿色左翼讨论中被低估的方面:尽管许多国家如中国,仍致力于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逻辑,但不同形式的社会经济(再)生产和日益增多的“变革实践”正在世界各地发生。他们不是行动主体,如“改变的先驱者”,而是改变进程中的实践。比如,在西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素食主义者,而在维也纳,一多半的家庭不再购买小汽车。同时,日常的劳动分工,以及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其他的生产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笔者确信,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人更希望每周工作四天,并能够接受较少的收入,而追求除工资之外的其他社会活动。
为实现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建立一个广泛的“红绿”左翼联盟是必要的,即联合社会运动、工会、政党、企业家、进步的工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地方官员、教师、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科学家、媒体工作者等社会力量,甚至可以团结相对保守的主体,如教会,加入到社会生态转型的学习过程。对于有组织的绿色左翼而言,这将是一个以我为主的舞台:多元左翼承认相互间差异,以及特定领域中的冲突(如食品和农业、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环境抗议和移民问题等)。全球绿色左翼是社会生态转型进程中不同倡议的推动者和稳定剂。它将推动资本权力、既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以及相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剥削自然资源意识的弱化。政治和社会制度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固化至关重要。因此,绿色左翼应致力于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推动文化制度朝着解放性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国家与相关主体如政党,是改变现存世界的关键性力量。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监管机构,或者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而是社会权力关系的聚合[4]。
这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而是涉及如何让不同转型过程都能成为社会生态转型总进程的一部分的问题。联合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真正改变生产和生活模式是至关重要的。集体的绿色左翼行动者,承认当前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转型过程,讨论并挖掘它们的解放潜力。用葛兰西的话来说,绿色左翼应该促使社会和政治行动者,为解放事业而克服自己和他人狭隘的“经济-社团主义”,并将它们转化为“政治-伦理”行动,即克服短期的团体利益,并准备好妥协[5]。这很可能是走向一种“霸权国家”进程中的发展阶段,国家终将运用战略性金融、法律、物质以及认知资源的支持,来保障替代性方案的实施。
3 社会生态转型的未来构想
社会生态转型的未来愿景,是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我们有很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来描述这些替代性方案、行动者和政治,比如能源民主、食物主权、城市权利等。这些概念并非来源于书本,而是源于社会斗争实践,“去增长”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我们不仅仅需要这些中间层次概念,更需要一个克服了资本主义增长机制和权力关系、具有吸引力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故事和视野。这一广义上的故事,可以被称作“好的生活”。笔者认为,绿色左翼、特别是全球绿色左翼的视角,应该更强调社会生态转型的未来故事和具有吸引力的愿景。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成员雷恩·利玲指出,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的未来、愿景和路径,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争论领域。比如,在今天如何设想可能的未来,如何将它们融入日常的战略和抗争活动之中,如何窥见厄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真实乌托邦”,如何为转型提供可能的方向和指引,以及如何为实现未来目标而动员可能的力量[6]12-48?在雷恩·利玲看来,关注社会生态转型的未来,不应将侧重点放在可能的未来上面,而应试图回答如何将那些想象中的未来和当前的社会相契合。就此而言,社会生态转型的未来,意味着捕捉、诠释和设想未来,即将它们作为当前决策和行动的目标。关于转型、转型管理、预占或活力等的争论,意味着“试图占领空缺的未来大陆,挪用和篡夺未来,以及将未来事件现实化”[6]48。
这一争辩过程,是为了使环境和社会价值更加明确化。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富有远见的、战略性的维度,应该与往往是抽象的启蒙运动相联系,如自主权和自决权、平等和正义、各种工作与生产消费方式的不同实现形式等。民主地塑造社会和社会自然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民主地控制自然资源,同时民主地控制生产和消费过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现存的对自然资源的民主控制形式有哪些?实现民主控制的背后有哪些抗争形式?它们如何被加以制度化?从广义上讲,民主地重塑社会与自然关系还需要哪些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的争论以及对于一个构建政治计划的声称,都提供了一种对当前主导性未来化的对立性观点。
4 去增长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目前,在西欧的精英和工会中间,关于克服危机的主导性声音是“增长、增长、增长”。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和繁荣也正在被热烈地讨论和质疑着。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经济危机和经合组织国家中日益放缓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生态危机的再政治化。就后者而言,十分明显的是,国际环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环境破坏在很多领域都在加剧。
除了各种战略性分歧以外,“稳态经济”的概念——源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稳态国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在这个概念中,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单独核算,物质和能源的产量与产出都被纳入考量之中。市场应对生态和社会危机的(不)可能性,是一个核心性议题。一些人呼吁生态和社会成本的国际化,而有些人走得更远:他们呼吁更多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再殖民化,以及从经济主义的理念走向集体主义的设想。
关于“去增长”争论的一个观点是,呼吁给予基层或草根社会运动更多的支持,如一些人希望为“去增长”创造更多的政治条件、实现个人行为的多元化、减少工作时间等,或者更广意义上的“为方向性改变寻求支持的一个多层面的政治工程,在宏观层面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微观层面则是个人价值观和愿望。收入和物质舒适将会减少,当然,最终目标并不是减少社会福利”[7]873-880。合作和社会正义等规范性的原则,被重新引入“去增长”的讨论之中,而社会运动被看作是变化的主体。很多人指出,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去增长”不应该侧重于危机或增长率放缓的长期趋势。相反,他们提出“自愿、平稳和公平地过渡到较低生产和消费的制度”[8]511-518,也就是说,“去增长”被看作是一个基于价值观改变的有意识的社会过程。
笔者在此试图展现关于“去增长”争论的全貌,并呼吁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质的变化。与围绕有质量的增长的争论相反,尽管资本权力和竞争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去增长”和增长的讨论中,人们未能更加彻底地考虑到社会统治的多方面结构和进程。权力和统治通常是指国家或政治主体如政党、协会或公司的权力。当然,在笔者看来,关于统治的更加复杂的界定,有助于我们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现实。明确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超越对于增长的“是与否”的回答,从而更加准确地探求资本主义的增长动力。当然,教育和健康制度、健康食物的生产以及可再生能源,必须实现增长。
那么问题就来了: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应该实现怎样的增长,以及它相关的利益是什么。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增长的批判很容易低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一些关键节点,即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关系和统治。经济增长不仅仅只是物质福利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它同时也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但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无论是个人机遇、行动空间还是财产与收入,都未能得到平均分配的社会关系支持的特性。它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保障了社会包容和排斥、阶级和财产关系、男性和女性的不对称关系、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秩序的不平等。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不平等的制度,更是一个权力和统治制度,特别是对自然的统治。
从“红-绿”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批判增长,并认为,社会关系首先由生产的交换价值所决定,而不是生产的使用价值。商品,由其交换价值所体现,“与它们的物体属性,以及其中的物质关系没有任何关联”[9]86。马克思对这一点特别敏感,指出通过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机制,自然的“所有财富资源”都会被破坏。此外,从经济角度去量化资源,如无偿的劳动力、公共服务或自然资源,它们也会被转化为商品和交换价值。资本主义竞争及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机制,导致更多的廉价商品被生产出来,与之相伴随的是免费资源的利用和再利用。资本“狂热地投入到自身的增殖过程中……无情地驱使人们生产更多的商品……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9]618。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这一趋势尤其明显,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更加激烈的竞争和资源的大规模消耗。
不仅如此,统治型的社会劳动分工是关键性的。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作为生产资料和其他财产所有者的阶级,致力于扩大自己的财产规模。人们大都拥有或多或少的财产,但仍需以工资劳动为生,并创造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而人们越是凭借工资劳动为生,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增长就越是得到鼓励。的确,阶级结构在许多国家已经变得日益多样化。但尽管如此,如果人们依靠工资劳动为生,那么他们的组织比如工会就会希望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和永久化,因为它们的工资收入依赖于这种生产,并相应地强化着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作为挣取工资者,大多数人不仅接受资本主义增长机器,而且要接受作为其基础的控制与所有权关系,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情愿和无能为力的。
增长的动力机制,比如技术革新、生产力增长、消费主义及其社会心理维度、债务危机和偿还周期、全球化和城市化等,也被人们广泛讨论。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从葛兰西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明晰的是,在那些被统治的人们看来,社会统治关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而更像是静悄悄的隐形关系[10],一种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全球化与生产主义不受控制的进程。换句话说,大部分人都是作为相对无权力的个体,来经历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尽管存在着新的管理手段,以及转移责任和政治参与的新途径。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此外,作为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动态关系,还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维度转化为市场上的货物,如资本主义商品。这不仅涉及自然,还涉及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市场或资本主义经济,不仅限制了社会创新和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范围,同时也限制了权力关系的构成方式,再现了决定性的阶级、性别以及种族界限。
5 全球社会生态转型
格雷戈·阿尔伯曾批评说,社会生态转型的替代性方案,都集中于地区性甚至地方性的变化。这些地方层面的小规模替代方案,的确很重要,但需要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对建立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公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左翼思考和政治行动的全球影响与全球贡献是什么?
从一般意义上我们需要回答:一种能为每个人的美好生活、财富、自由、生态可持续性创造条件的,具有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如何才能出现?在一个真正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与公正、摆脱了资本权力的增长和积累机制的经济制度中,一个不再致力于推动资本权力的国家中,如何来维持和创造就业?如何实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劳动分工?或者用葛兰西的话说,人们自己如何能提出超越特定利益的新的“集体意愿”,但同时又能根植于制度、经济和文化的实践之中?在笔者对这些问题给出试探性回答之前,需要先阐明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绿色左翼的观点注定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话语。
政治平等、工人权利或妇女权利,以及很多环境法律等解放性运动,在对抗权力以及强大的经济利益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国家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成就的获得往往基于希望获得更好生活的人们的斗争,包括工人、妇女、移民、环保人士以及那些希望获得更好教育的人们。对此,我们可称之为“纵向的”政治视角,特别是一种阶级的视角[11]。
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在民族国家之间。除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纵向斗争,还存在着很多妥协,特别是以反对“民粹主义”为导向的阶级之间的妥协。一旦这些妥协达成,并且条件适宜时,就会出现多样化的增长模式。可以看到,二战以后,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就包含着大量的阶级妥协。这一战后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不仅造成了阶级内部与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以牺牲性别平等、特别是移民福利与尊严为代价。但与此同时,很多民众感到满意,并享受着这一增长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社会保障。目前,中国也正在经历着这一进程。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横向的”政治视角。其间,经济发展是可能的,因为经济相对具有竞争力,且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或多或少地在起作用,同时又有一定的分配机制和对中下层民众的权利保障机制。但经济的发展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并且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因此,国际劳动分工将一些地区与国家比如拉丁美洲、非洲、俄罗斯等,置于资源供应者的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如中国、孟加拉国、德国等,扮演着“全球工厂”的角色,还有一些国家如印度,则为全球提供廉价劳动力。
绿色左翼政治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横向的”政治发展,比如将人们置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背景之下。正如笔者之前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并且以牺牲他人、牺牲自然、牺牲未来人的利益为代价。整个帝国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将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效应外部化,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特别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国家发展是可能发生的,并且有效地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任何对这一兼具生产力和破坏力、融合和霸权、排外和破坏特性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都必须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生活。这是全球社会生态转型的底线,也是真正全球绿色左翼的底线。接下来,笔者将重点阐述全球绿色左翼的四个方面意蕴。
第一,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绿色左翼政治必须思考如何改变当前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相关的权力关系,广泛地接受整体性的社会导向和社会实践。同时,绿色左翼政治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强化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当前的国际政治合作,主要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形成新自由主义的“锁定”效应,比如WTO。只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竞争在社会中和国际层面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很难提出甚至思考激进的替代性方案。因此,在笔者看来,首要的原则就是减少竞争和竞争力。绿色左翼的国际政治,必须具有与之不同的政治视野。资本主义方式推动的竞争和竞争力,注定将服务于资本的利益,阻碍建立在合作和团结基础上的全球生产方式的出现。虽然任重道远,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竞争必须一步步被削弱和克服。
第二,当我们讨论一个为所有人提供优质生活的更好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提到就业、雇佣劳动、非雇佣劳动、社会分工等。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但劳动力却面临着巨大压力,很多人并不能靠一份工作的工资来养家糊口。我们称他们为“工作的穷人”,因为他们并不能获得一份可以过上体面生活的工资。在许多国家中,最低工资并不能保障正常生活,甚至很多人的收入都达不到最低工资。即便在很多发达国家,许多人的工资收入依然在2008年危机时的水平之下。对全球绿色左翼而言,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所有人过上好的生活而创造条件。这就意味着,要支持工薪阶层和非工薪阶层的斗争,比如支持工人组建政治上独立的工会、组织各种抵抗活动,以及罢工等。
蒂莫西·米切尔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权利,都与化石燃料密切相关。他指出,自19世纪以来,工人通过提取、分配和使用煤炭,来获得政治和社会包容。对此,他称之为“碳民主”(carbon democracy)。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为工人通过罢工等形式中断生产过程或至少阻碍煤炭的使用创造了条件。比如:“一个世纪以前,煤炭的广泛使用为工人提供了新的权力。大量的煤炭从矿井沿着固定的、狭隘的通道、铁路、运河到达工厂和发电站,这一薄弱的运输环节为工人运动创造了条件,一个环节的罢工很容易导致整个能源系统的瘫痪。由于这一新兴权力的出现,西方政府最终屈服,给予所有公民投票权,并对富人征收新的税收,为失业和工伤提供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退休金以及其他公共社会福利的改善。煤炭供应的流动和中断,推动了更加平等的集体生活的民主诉求。”[12]236
20世纪随着石油的应用,这一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随着石油生产的分散化和国际化(特别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威权政府),工人的权力不断削弱。另一方面,基于石油的工业主义以深刻的方式,全面地塑造了工人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衣服、塑料、食物、交通等。它已经成为我们所称的“帝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687-711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即便如此,蒂莫西·米切尔指出,很难想象,自由民主将最终克服化石燃料的生产主义模式。。这表明,国际团结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还是一种政治实践。也就是说,像德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的工人,应该支持或同情他国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收入的政治斗争。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必须有这样的集体和个人的认知,即个人的生活水平基础部分是建立在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之上的。
当然,从绿色左翼的视角出发,我们需要走得更远:我们需要提出倡议和方案,并推动相关的政治斗争,以挑战资本的控制,挑战资本主义将全球劳动力置于永久的竞争地位、牺牲他人和自然的发展逻辑。
第三,从绿色左翼的视角出发,我们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是如何提出一种超越帝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或者说不以他人和自然为代价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支持众多形式的政治斗争,并在同时推动各种解放的、生态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到目前为止,全球的发展模式注定是突出数量的经济增长,比如国家的就业和税收等。但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所驱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其主要目标是资本积累,而不是让每个人过上好的生活或关注自然。工人运动应该与环境运动相结合。因此,我们必须对旧的“社会/经济”与“生态”分野进行重新界定;环境问题比如能源贫穷、肮脏的工作环境、喧哗街区的住房、不健康的食物等,也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第四,正如在奥地利和德国所讨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变革性的左翼,来克服依然散沙般的左翼政治。这不是说要将分配问题搁置在一边,而是将它置于另一个背景之下。如果左翼力量希望对上述提出的问题做出充分的解答,那就不得不对“繁荣”概念提出进步性的理解,超越当前关于“增长和分配”的原则。在工业化国家,绝对的生产和消费量需要在很多部门中进行削减——当然不是全部部门,比如护理工作和可再生能源部门就需要增长。而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要生产更少的汽车、更少的空中交通、肉食消费,由高度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向可持续的农业模式转型。
在很多方面,政治也需要重铸。“跨界”作为一个过程,将聚集议会内和议会外的力量、改变的先驱者和进步的企业家等。总之,它将是通过多种多样的倡议,发起、实施、捍卫政党、公共机构、协会、工会、企业家及其利益集团、社会运动和普通公众的社会生态转型实践的过程。所有这些过程都会面临着跨越式发展,但也会遭遇挫折,而且它们也不会同时发生。这将会产生战略性的政治后果:为了修正上述提到的发展逻辑,使其朝着团结现代性的方向发展,一个变革性的左翼需要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冲突,不仅要以更好的方式处理分配问题,而且要干预社会(再)生产的模式,特别是在那些拥有组织良好的强大力量的地方。
6 结语
罗莎·卢森堡提出了“革命的现实政治”的概念,约阿希姆·赫希称它是“激进的改良主义”[13]157-212,而迪特尔·克莱因则将它称之为“双重转型”[14]。这其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推动改革主义的政治,以及改革社会的具体步骤,但这一政治变革需要以解放的视野来推进,在良好的社会中确保每个人的美好生活,并且不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全球绿色左翼不应该将此理解为两个连续性的阶段(今天是改革主义,明天是激进主义),而应该将改革的倡议和政治以及相关的冲突,融入具有解放潜力的现实实践之中。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却是实现人类真正解放的决定性的条件。
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新型经济体系的了解:一种超越对当前正规市场(通常被狭义地理解为资本主义市场,忽略公共部门的市场)和雇佣劳动的理解。它对解放运动而言,意义重大[15]1703-1711。在西欧和国际学术圈,围绕着“关怀革命”的主题,经济体系也是其中讨论的重点,比如一种观点就认为,经济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应该将人们的福祉、使用价值、自然的生态再生产看作是决定性要素。这就意味着,需要对社会和国际劳动分工进行重组。那样的话,必将指向当今世界由阶级、性别、种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内部分野所塑造的权力和统治结构。同时,解放也意味着各种形式的劳动分工的解放。这就表明,我们需要不同形式的知识、技能和能力。那么,我们怎样去创造这样一个社会?比如,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体系?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实现解放性的社会生态转型,需要构建一种有吸引力的生产和生活模式、重塑当前权力关系、培育当前实践的替代性选择,并进一步提出其他领域的替代性方案。当然,社会生态转型在未来依然具有某些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反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故事”可能会引发重大变革,包括生活条件的恶化;质疑当前的权力关系可能会带来混乱,当精英不再控制社会时,普通民众可能会感到恐惧。对此,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不确定性并不是一种权力机制,我们必须确保社会生态转型不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这是任何社会生态转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
参考文献:
[1] 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Crisis and continu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nature relationships: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nd the limits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4(2013).
[2]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eds.),The Communist Manifesto,Socialist Register(London/New York:Merlin Press.1998).
[3] Hans Thie,Rotes Grün.Pioniere und Prinzipien einer?kologischen Gesellschaft(Hamburg:VSA,2013).
[4] Gallas Alexander,Lars Bretthauer,John Kannankulam and Ingo Stützle(Eds.),Reading Poulantzas(London:Merling Press,2011).
[5] Antonio Gramsci,Prison Notebooks,German Edition(‘Gef?ngnishefte'),edited by Klaus Bochmann and Wolfgang Fritz Haug(Hamburg/Berlin:Argument.1991).
[6] Rainer Rilling,“Transformationals Futuring”,in Michael Brie(ed.),Futuring:Perspektiven der Tran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und über ihn hinaus(Münster:Westf?lisches Dampfboot,2014).
[7] Giorgos Kallis,“In defence of degrowth”,Ecological Economics,70/5(2011).
[8] Francois,Schneider,Giorgos Kallis and Joan Martinez Alier,“Crisis or opportunity?Economic degrowth for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18/6(2010).
[9] Karl Marx,Capital: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I,Marx-Engels-Werke 23(Berlin:Dietz,1977[1867]).
[10]Alex Demiroviĉ,Demokratie und Herrschaft(Münster:Westfälisches Dampfboot,1997).
[11]Marco Revelli,Die gesellschaftlicheLinke.Jenseits der Zivilisation der Arbeit(Münster:Westf?lisches Dampfboot.1999).[12]Timothy Mitchell,Carbon Democracy: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London/New York:Verso.2011).
[13]Joachim,Hirsch,“Politische Form,politische Institutionen und Staat”,in Josef Esser,Christoph G?rg and Joarchim Hisch(eds.),Politik,Institutionen und Staat:Zur Kritik der Regulationstheorie(Hamburg:VSA.1994).
[14]Dieter Klein,Das Morgen tanzt im Heute:Transformation im Kapitalismus und über ihn hinaus(Hamburg:VSA.2013).
[15]Adelheid Biesecker and Sabine Hofmeister,“(Re)productivity:Sustainable relations both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and between the genders”,Ecological Economics,69/8(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