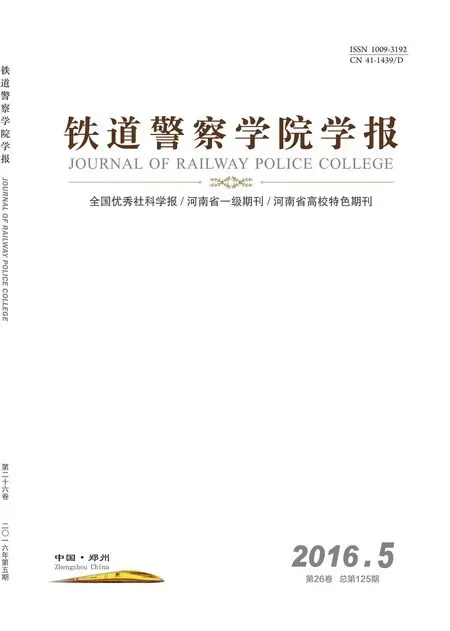网络时代的量刑制度变革
方斌
(河南警察学院侦查系,河南郑州 450046)
网络时代的量刑制度变革
方斌
(河南警察学院侦查系,河南郑州 450046)
互联网的兴起使得刑事案件量刑程序中判意与民意的冲突问题凸显。借助网络游离于审判法庭之外的民意,一方面具有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完善量刑规范化改革、消除不当司法干涉等积极机能,另一方面也极易被网络所异化,增加被告人遭受舆论审判的风险。为此,应在量刑程序中构建人民陪审团、量刑听证、法庭之友等制度,积极疏通民意进入司法场域的通道,扬其长而避其短。
网络民意;量刑程序;自由裁量权;舆论监督;制度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从李昌奎案件谈起
随着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民意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表达空间,网络舆论热议司法案件的现象也随之凸显出来。网络一方面将司法个案的有关情况传导给社会,引发公众的关注,另一方面又为公众参与讨论司法个案的裁判结果提供了平台。那么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刑事案件的量刑能否考虑网络民意?应否考虑网络民意?如何考虑网络民意?法官又该如何平衡刑事案件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妨从近年来的一起名案——李昌奎案件的讨论开始。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因婚姻和家庭纠纷将同村19岁少女王某某及其年仅3岁的弟弟一同杀害,作案过程中还对王某某实施了强奸。2009年5月20日,畏罪潜逃的李昌奎在四川省普格县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作出后,李昌奎以存在自首情节为由提出上诉。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了李昌奎的自首情节,以原判量刑过重为由将原判死刑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从“死刑”变为“死缓”,二审法院一字之差的判决书顷刻间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该案的量刑亦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大多数网民都认为,李昌奎作案手段残忍、情节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纷纷指责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量刑过轻,有失公正。而被害人家属更是打着“强奸+两条人命=死缓?”的横幅,四处质问法律何在、公理何在。一时间,云南省高级人民院陷入了一场空前的舆情危机。在强大的网络舆论压力下,云南省高院不得不对引起“民愤”的李昌奎案件启动再审程序,李昌奎的命运也在网络上一片喊杀声中显示为“待定”。
2011年8月22日,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的再审在云南省昭通市进行,同年9月29日李昌奎被依法执行死刑。这场一波三折并伴随着无数争议、抗议、讽刺、调侃的审判最终以司法判决“臣服”网络民意而终结,李昌奎的命运也在死刑—死缓—死刑的变换中定格。尽管李昌奎案件在经历一审、二审、再审程序后最终尘埃落定,然而关于其自首仍被判处死刑的讨论仍在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物理空间中继续。
近年来我国对待死刑的态度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至今,“少杀、慎杀”的理念正陆续变成地方各级法院在司法裁判中践行的原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云南省高院在李昌奎案件中,带着“司法引领民意,而非顺应民意”的“理性自负”,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以及“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两条理由,对李昌奎改判了死缓。客观上讲,这一判决并没有明显的法律问题,甚至可以说二审法院是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对李昌奎案件进行了改判。然而,为何这一法律事实原本十分清楚、判决本该非常清晰的案件,进入法院后,竟在种种网络舆论的影响下,变得如此模糊不清?究其根源,这直接涉及以网络舆论为代表的民意如何监督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二、网络时代下的民意与判意
(一)网络民意与判意的分歧
一个看似普通的案件,经过网络的发酵,随即便会演变为震动社会各界的热点事件。李昌奎案件的一波三折充分表明司法裁判正日益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重心。在网络时代的刑事司法裁判中,以网络舆论为代表的民意已屡屡突破传统“量刑酌定因素”的束缚,正日益成为左右刑事案件量刑的重要筹码。然而,不幸的是,基于观念和事实认定方面的因素,网络民意与司法机关的判意存在天然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正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首先,网络民意与司法机关的判意在观念上存在严重分歧。就具体个案而言,这种分歧突出地表现在评价标准与结果认定标准的分歧上。网民往往是基于伦理道德的立场,以社会正义和道德捍卫者的角色对司法活动进行评价。他们对于特定个案往往在案件事实的评判方面采用道德标准,而在案件的裁判结果方面则又采用法律标准。易言之,网民采用道德标准评价案件后,却要求司法机关对被评价者进行法律制裁。而司法机关通常是基于客观、中立的立场,以法律作为案件的唯一评价标准并据此得出评价结果。不仅如此,由于道德评价标准本身具有模糊性、个体性和层次性,对于相同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当网民采用不同的道德标准对具体案件进行评价时,极有可能得出不同的评价结果。而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则要求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坚持理性原则,对于相同或类似的犯罪行为作出相对一致的裁判结果。
其次,网络民意与司法机关的判意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分歧。网络民意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全面地表征案件事实,主要取决于其信息来源的具体情况。相较司法机关而言,网民对于某一特定案件事实信息的获取主要来自外部渠道,诸如新闻媒体的报道、案发地群众的议论、被害人家属的控诉等等,因此,通过网络民意表征的案件事实往往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而司法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则是建立在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之上,而且是经过控辩双方激烈的辩论后最终由法官认定的“法律真实”。
(二)网络民意影响判意的机理
纵观国内以李昌奎案件为代表的具有影响性的民意与司法纠缠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民意对判意的影响主要在于刑事案件的量刑而非定罪。具体而言,网络民意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对刑事案件的量刑产生影响。
其一,网络民意借助强势媒体和“官意”影响刑事案件的量刑。互联网的出现不仅突破了传统媒体在信息容量、传播方式以及辐射能力方面的局限,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媒体对公众意见的筛选、过滤、拦截功能。社会公众借助网络平台自由地参与司法案件的讨论并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从而为传统媒体设置议题。不仅如此,网络民意表达的对象也不仅仅限于相关的司法机关,而且还指向了各级党政权力机构,其目的在于使公众对个案的态度成为一种引起党政权力机构重视的民意,进而通过党政权力机构对司法机关施加影响。在我国司法尚未完全独立,审判机关人、财、物过度依赖地方政府的情况下,司法官员以法学家的智识和思维回应外部压力的能力还相对薄弱。尤其对于被大众媒体广泛报道并由此引起政府高层关注的热点案件,法院的围墙更是弱不禁风。因此,李昌奎案件死刑适用的变更其实只是一种表象,影响其命运的案外因素并非网络民意,而是“掌握强势话语权的新闻媒体和直接制约着司法官的政治决策层的意志”[1]。由此,网络民意影响刑事案件量刑的模式也可概括为:网络民意影响权力机构,权力机构的意志影响司法机关。
其二,法官平民化的思维方式。如果把权力机构的意志看作是网络民意影响刑事案件量刑的外部因素,那么平民化的思维方式则是网络民意影响刑事案件量刑的内部因素。客观地讲,社会公众对于法律规范本身并不熟悉,就个案判决而言,他们往往更看重判决的社会效果而非对法律规范的预期。而法官的本行是专事审判,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超出普通民众思维的法律智识活动,但在法官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难以截然分离的现实中,法官往往有意或无意地迎合社会公众对自身的角色期待,把自己视为百姓的“父母官”,把司法裁判当作管理手段,并将合乎民意的裁判结果视为政绩。在这种平民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下,法官的审判过程及其结果不得不接受以网络民意为代表的各种社会价值观念的评价,以提高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同时,法官也不得不尊重既定的法律文化传统、习俗以及伦理规范来实现个案的正义。当顺应现实成为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时,民愤便会成为法官行使裁判权的重要依据[2]。法官这种平民化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其在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时就会更倾向于裁判活动本身的目的,而非法律规范的字义表述;就会更加重视“衡情度理”,而非法律论证。而法官一旦被视为民意的代表,社会民众对司法的预期也会随之调整,试图通过民意影响裁判结果的现象也就必然会发生。
三、网络民意介入量刑的利弊
(一)网络民意介入量刑可能存在的弊端
法官的量刑必须具有客观合理性,应该首先根据量刑情节对法定刑进行修正,然后形成处断刑,最后在处断刑的范围内决定宣告刑[3]。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精神①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考虑到刑罚目的不仅仅是定罪,更包含有犯罪预防、教育等功能,以及犯罪行为人罪前、罪后情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主观恶性,此处的犯罪情节应作广义的理解,即不仅包含犯罪行为本身的情节,而且包括犯罪行为前及行为后的案外情节。参见高铭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反映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的罪前、罪后情节的民意理应成为刑事案件量刑的参考。然而,现实中民意经网络发酵后往往会发生种种异化,这些异化消减了民意表征犯罪情节的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使民意所表征的犯罪情节有可能被人为地操纵。在传统社会中,民意之众寡通常是以民众上访的规模或联名告状人数的多寡等形式来体现的,但在网络时代,民意更多地表现为网民对当前案件的“点击率”、“网帖的跟帖率”的多少。由于网络的技术性因素,如网络的匿名性、网络数据的可修改性等,点击率、跟帖率就有了被人为操纵的潜在可能性。易言之,网络民意所表征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后果、态度、目的等量刑情节存在被人为夸大的可能性。
第二,网络民意容易失真。匿名性是网络舆论传播的最主要的特点,同时也是其本质特征所在。网络的匿名性一方面使网民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使其在网络上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但是另一方面又极大地降低了网民的道德约束力和法律上的责任,因而也就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负面结果,即虚假信息的泛滥。
第三,网络使民意突破了犯罪行为地域的界限,从而弱化了其量刑评价功能。就法律本意来讲,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工作地、生活地的民意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犯罪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从而具有作为犯罪情节的量刑评价功能,但是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民意已大大超出了上述地域界限,其所反映的不过是广大网民的一般的价值观评价。
第四,网络民意可能夹带偏激的情绪。日本学者曾经指出,国民欲求中虽然包含直观正确的部分,但也不乏一些非正确的成分,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观点的片面性和个人情绪的反映[4]。显然,借助网络表达的民愤就是这种个人情绪的极端反映。作为一种从道德领域发出的非理性的集体行为,民愤本身既不能客观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亦不能客观代表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如果法官把民愤所体现的较高的道德标准法律化并把它视为量刑的依据,则会侵犯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并最终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顺应民愤的审判虽然在个案上似乎实现了所谓的“公正”,但它从根本上破坏了法治精神,终将使民众丧失对法律的信仰。
第五,网络民意中可能包含相对落后的法律观。当司法个案的处理结果与网络民意相一致时,广大网民很少会认为这是法律在民意影响下得到正确的适用,相反,他们会认为这是法外力量所产生的效果,在网民们的意识中法律是可以变化、变通,甚至是可以人为规避的,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人治化的思维方式。另外,重刑主义在我国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社会公众借助网络表达的民意显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过度倚重刑事手段,对犯罪嫌疑人从严从重适用刑罚的主观倾向。对于一些贪污腐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等关乎公众利益、民愤较大的案件,公众对于犯罪嫌疑人适用重刑的要求则更为强烈。
(二)网络民意介入量刑的合理性分析
在网络时代,以网络舆论为代表的民意介入量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这有利于审判法官对酌定量刑情节的正确适用。在刑事案件审判中酌定量刑情节的认定与适用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法院量刑工作的重大难题。在关于量刑的立法和司法中,酌定的依据往往被表述为“情节”“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后果”等法律概念,但无论如何,酌定必然是一个主观化判断,“酌”与“定”都依赖于主体的主观测度[5]。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某一特定主客观事实是否属于酌定量刑情节,不同的法官会产生不同的看法;不仅如此,即使对于相同的酌定量刑情节,其在刑事案件量刑中所占的分量如何,不同法官也会做出不同的评判。司法如果一味地让法院垄断酌定量刑情节的事实认定权,那么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情况下,酌定量刑情节的误用、滥用以及由此导致的量刑失衡将不可避免。这不仅会导致同案不同判,更会引发民意的浪潮。毕竟“法律的生命从来就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从这一角度来看,对于法律规定的酌定事由,在广泛讨论基础上形成的网络民意更注重一些不为立法所承认而依公正要求却应予采纳的情理或事理,公众的“酌定”似乎更符合生活的逻辑。网络民意介入量刑能够有效地克服法官任意使用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弊端,有利于实现个案判决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可信任度,从而也更加有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
其次,这有利于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完善。当前我国法院系统正在逐步推进的以增强量刑公开性和透明度为核心内容的量刑规范化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量刑的公正与均衡,但是,其在解决量刑自由裁量权与民意的紧张关系方面效果甚微。司法与民意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正义观念:司法侧重于理性,注重逻辑,而民意侧重于感情,注重经验;司法侧重于程序正义,注重“同等对待”,民意侧重于实质正义,注重“原心定罪”,民意既会对“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导致的“同案不同罚表示不满”,亦会对“秉公执法”下的“同案同罚”表示不解。除非将民意导入刑事司法之内,贯通两者所依所重,否则单靠量刑规范化改革难以防范也抵御不了民意浪潮,相反,司法自由裁量权越是规范,量刑程序越是公正,裁判结果可能引发的反对民意浪潮就越大[6]。
最后,这有助于法院抵御外来不当力量的干涉。司法公开化、民主化是实现司法公正、矫正司法偏差,尤其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保证。在量刑中导入民意无疑为司法公开化、民主化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使得各种信息和观点能够自由地在网络空间得到传播;同时,网络反馈的及时性和传播的互动性、参与性,又使网络媒体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形成议题;再加上网络传播突破了地域限制,也更容易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借助网络,司法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共知、共享的信息。在社会共同关注下的个案处置,基本消除了司法机构及其成员重大失误甚至营私舞弊的可能,也有助于提高人民法院抵御外来不当力量干涉的信心与能力,网络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在此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四、量刑导入民意的制度构建
民意介入司法是一把双刃剑,在网络时代司法无法完全回避民意,相反,司法的过程应当对民意开放;而民意要想在司法审判中获得承认并发挥作用,就必须以某种“法律参与”的形式进入司法场域。易言之,民意必须依托一定的形式和路径进入法律程序,通过法律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发挥自身的影响。由于民意参与司法具有广泛性和层次性,在量刑中导入民意的制度构建应是一个完善的系统而非依赖于某个单一的路径。
(一)量刑人民陪审团
在司法审判中实行陪审制度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陪审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陪审团制,一种是参审制。前者主要存在于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后者则主要存在于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我国的陪审制度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即由依法定程序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利的制度[7]。但实际情况是,囿于专业知识的限制,人民陪审员很难在案件的审理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而面对各地屡见不鲜的要求对被告人从重或从轻处罚的联名上书、集体上访抑或是“媒体审判”,人民法院如何满足人民群众不满仅于体制外监督而期待参与到体制内并对量刑发表意见的新要求、新期待,业已成为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陪审制度是将体制外民意导入量刑工作的重要机制,在陪审制度改革问题上,应以量刑改革为契机,大胆借鉴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在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构建量刑人民陪审团,以针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事实予以认定并做出是否适用的裁决。
我们所要构建的量刑陪审团与英美的定罪陪审团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区别集中体现于政治逻辑方面:英美陪审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分权制衡,其最终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对国家专制权力的防范与制衡[8],出于这种需要,定罪权与量刑权分属于陪审团和法官行使;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则侧重于体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让普通民众直接参与司法目的是弥补代议制式的间接民主的一些弊端[9]。而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是我国司法的本质属性,因此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是直接民主的体现,而无关政治意义上的分权制衡问题。当前,无论是人民群众对于参与量刑并发表意见的期待,还是刑事案件被告人对于接受公正刑罚的需求,都远较于如何定罪强烈得多。因此,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应当满足社会的这一现实需要,将陪审制度完善的重心置于量刑而非定罪。
具体来讲,构建量刑陪审团制度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环节:(1)关于量刑人民陪审团的职权。鉴于在我国的量刑实践中,酌定量刑情节在认定、适用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容易引发民意不满,量刑陪审团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独立地对酌定量刑情节进行认定并做出裁决。(2)关于适用的范围。首先,在案件适用范围上,鉴于世界各国普遍将陪审制度适用于比较严重的刑事案件,量刑陪审团应当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其次,在参与的庭审程序方面,量刑陪审团应仅限于参加量刑程序。如果开庭前被告人认罪,那么量刑陪审团可以直接参加庭审;反之,如果被告人不认罪,则量刑陪审团应仅在量刑程序开始时再参加庭审。(3)关于参与的形式。鉴于以个人名义参加以法官为中心的审判组织的陪审员容易受到法官的影响甚至操纵[10],量刑陪审团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作出裁决而非加入合议庭。(4)关于量刑陪审团的启动程序。申请量刑陪审团参与刑罚裁量是刑事案件被告人的一项法定权利,被告人对该项权利行使具有自主决定权。因此,量刑陪审团应当依被告人的申请而适用,当然被告人也可以放弃使用该权利。对于被告人放弃行使该项权利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听取民意的,则可以通过量刑听证的形式进行。(5)关于评议的规则。量刑陪审团进行评议裁决时应当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对于构成酌定量刑情节应当作为量刑参考的裁决原则上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票通过。
(二)量刑听证
量刑听证制度是我国各地法院在量刑中民意导入机制上的实践创新,典型的有浙江省安吉县法院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量刑听证,湖北省通城县法院针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刑事案件的量刑听证[11],山东淄川区法院针对缓刑裁决的量刑听证[12],以及河南省高级法院针对死刑二审案件的量刑听证等[13],其主要做法是邀请民意代表或案件相关人参与庭审或召开专门的听证会,就量刑问题征集社情民意。量刑听证可以有效弥补量刑陪审团参审范围的局限以及因被告人放弃权利而不能启动量刑陪审的弊端,因此它不仅是民意参与司法的另一重要途径,同时也是量刑陪审团的重要补充。需要注意的是,量刑听证与量刑陪审团不得在同一审理程序中并用,且量刑听证意见仅供法院刑罚裁量时参考而不具有强制力。
(三)法庭之友
“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起源于古罗马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最初发源于英国普通法,而后被移植到美国法中并得以繁荣发展。“法庭之友”是一个专门给非案件当事人向法庭陈述意见的制度,主要用于上诉审中。在该制度下,非案件当事人可以向法庭提供与案件相关的背景信息、不为法院所知的案件事实或法律意见。“法庭之友”通过提交诉状来影响法院的判决,这种诉状被称为“法庭之友陈述”(amicus curiae brief)。实行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它允许民众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庭提供意见,从而为民意开辟了程序输入的新渠道。它不仅能够提供不被法院知悉的证据事实和法律意见,为法院做出公正判决提供帮助,而且还有助于将民主精神贯彻到法院的审判活动中来,从而避免司法权运作的决定非民主化。2003年苏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引进了法庭之友的审案方式。据报道,这一举措增加了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感,促使当事人在庭审中更专业地阐述观点,从而更加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14]。我们认为,如果量刑陪审团与量刑听证主要是为区域性民意参与司法提供通道的话,那么法庭之友制度则为更为广泛的民意参与司法提供了制度性平台,这不仅有利于法院“兼听则明”,也有利于收编漫游于体制之外的“民意”,克服其负面影响。
[1]左坚卫.民意对死刑适用的影响辨析[J].河北法学,2008(2):35-37.
[2]孙笑侠.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5):47-56.
[3]冯军.量刑概说[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3):27-28.
[4]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顾肖荣,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0.
[5]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J].中国法学,2008(4):167-168.
[6]沈德咏.《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答记者问[EB/OL].(2004-12-27)[2016-02-01].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4-12/27/content-172240.htm.
[7]郭永庆.量刑中民意导入机制研究[J].法律适用,2009(11):76-80.
[8]万海峰.英美陪审团制度的政治解读[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62-169.
[9]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87.
[10]雷朝霞,郑淑霞.两大法系陪审制度之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1):121-123.
[11]李正清.通城法院试行“量刑听证”[J].中国审判,2008(9):67.
[12]王红梅,袁涛.地方法院关于量刑程序改革的尝试——山东省淄川区人民法院的实践与探索[J].法律适用,2008(4):15-16.
[13]肖智勇.“陪审团”参与死刑二审的首次尝试[J].法律与生活,2009(7):33.
[14]苏州法院:“阳光审判”出新招[N].扬子晚报,2003-06-10.
责任编辑:赵新彬
The System Reform of Measuring Penalty in Internet Epoch
Fang Bin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Henan Police College,Zhengzhou 450046,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highlights the conflicts between public opinions and court decisions. With the aid of Internet,on the one hand,popular opinion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regulating the discretion of judge,perfecting sentencing standardization reform and eliminating the improper judicial intervention;on the other hand,it is easily alienated by Internet,thereby increase the risk of defendant suffering public opinions on judgment.Therefore,we should establish several systems,such as jury system sentence hearing and amici curiae,to clear the channels for public opinions to enter the fields of justice.
online public opinion;sentencing procedure;discretion;public scrutiny;system construction
D924
A
1009-3192(2016)05-0108-06
2016-07-20
方斌,男,河南林州人,法学博士,河南警察学院侦查系讲师,研究方向:证据学与侦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