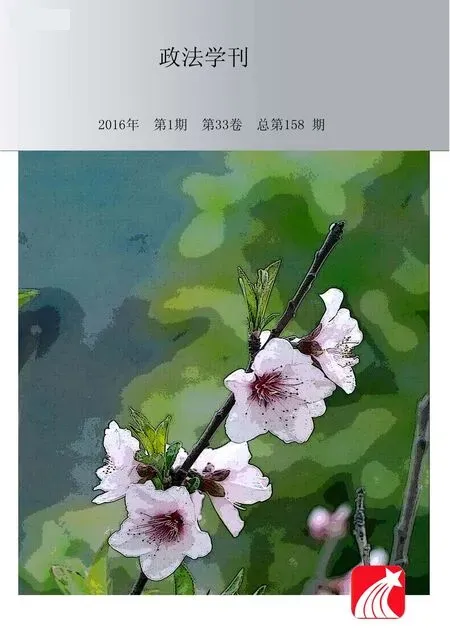浅析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警役军事与治安职能
李光迪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浅析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警役军事与治安职能
李光迪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5)
摘要:警役是中古和近代英格兰乡村的基层官员,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其职能进一步完善,成为乡村共同体的政治领袖。军事职能体现警役的“国家公务人员”性质,治安职能则体现警役之“乡村共同体官员”特性。警役在履行军事职能时遵从国家之命令,履行治安职能时则倾向于按“乡规民约”和“邻里之情”行事。警役自身体现出了英格兰王国的集权倾向和自治传统之间的妥协,这种“均衡”确保了英格兰社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英格兰;警役;军事;治安
警役是中古时期和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的重要官员,最初只是负责征兵与治安的“地方小吏”,后成为类似“村长”的乡村基层官员。关于警役问题,西方学者(尤其是英国学者)已有较为精深的研究。其中以J·R·Kent,J·Whitehead 与W·.E·Tate,T·G·Barnes,J·A·Sharp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Kent从警役职能的演化入手,着重阐发警役自身的“双重属性”。J·Whitehead 与W·.E·Tate则从警役“教区官员”的特性入手,分析警役“教俗混合性”。Barnes以萨默塞特郡为例,分析该郡警役在1625-1640年中的种种表现,并与英格兰地方自治问题相联结。J·A·Sharp对17世纪警役在维护地方治安上的表现进行了专门研究。国内学界近十余年也对英格兰乡村自治问题给予了关注,如侯建新之《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增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王玉亮之《英国中世纪晚期乡村共同体研究》、李云飞之《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同时出现了一批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普遍提及了英格兰乡村崛起之关键因素:乡村自治理念。但对于乡村政治的执行者-警役,大多只是加以辅助性说明。笔者以为,警役虽具有“国家公务员”和“自治官员”的二重性,但在履行治安职能时充分尊重“乡规民约”,这正是自治理念深入人心的表征。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从警役身上我们可探究自治理念在英格兰乡村崛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格兰王国之军事体制
从中古直至近代早期,英格兰王国之军事体制从最初的以封建骑士为主干发展到以雇佣军为主体,虽然直到近代早期(16-17世纪)仍未形成常备军体制,但军事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则是毋庸置疑的。下面笔者从军事体制之演变为角度展开论述。
诺曼征服之后,征服者威廉将已在诺曼底地区运作成熟的封建体制引入英格兰,建立起封建军事体制。如马克·布洛赫所云:“诺曼底诸公爵定居英国,是法律制度移植的众多显著例证之一:法国封建习俗传播到一个被征服的国家。”[1]309
与当时欧洲大陆孱弱的王权不同,诺曼封建体制有着较为强大的王权建构。欧洲大陆之“封君封臣”制度含义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也就意味着国王虽然依靠分封体制建立起政权,但封臣之封臣并不直接听命于国王。此种体制之弊端就在于一旦王权稍有弱势,封臣就会有强烈的分裂倾向。威廉一世则吸取了这一教训,征服英格兰后不久就要求各级封臣向其宣誓效忠,这就是所谓“《索尔兹伯尼誓约》”,随后又进行全国范围土地调查,以明确封土情况。马克垚教授评论道“索尔兹伯尼誓约更使大多数封建主均受威廉节制,便于指挥。末日审判调查则显示全国范围的封土制的建立。威廉是全国土地的名义上的最后的所有者,一切封土最终都是领自国王威廉的。在这里,可以说封建制度(封臣制)与国家制度相吻合,诺曼英国当为典型的封建国家。”[2]58-59
封臣为封君服军役是“封君封臣”制的题中之意。威廉一世控制了全国约六分之一的耕地和大部分森林,以此作为王室领地。同时将其余耕地分封臣下,臣下再将土地向下分封,各级封臣依照封土之面积大小向国王提供服军役的骑士,甚至连拥有封土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也不例外。“凭此,威廉一世组织起一支大约5000-7000人的骑士军队。”[3]37此时骑士为英格兰王国军队的核心力量。不过,封建骑士为主体的军队也存在缺陷。首先是服军役的时间问题,在金雀花王朝时期,英格兰诸王与法国频频发生冲突,贵族服军役的时间不断拉长,军费开支浩大,导致封臣苦不堪言。其次是骑士在战中自由散漫而不听统属。因此,“从亨利一世时开始即有以交钱代军役的事例发生,以后日渐发展,亨利二世时更为经常。国王每有征召,即向臣下收盾牌钱,然后另用钱雇人作战。”[3]65其实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有征召民兵参战的传统,诺曼征服之后,此习俗得以保留。历代英王也不时征召民兵,只不过由于骑士在作战中的主导作用,此时民兵主要职责是辅助作战,征召的数量也不多。
1181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军备条例》,要求所有“自由人”配备武器并宣誓时刻为国王效力。“很显然,亨利最初的目的只是要在封建兵役体制之外建立更为有效的防御机制。根据亨利的法令,即使最贫穷的人都应拥有长矛和盔甲,他们应根据国王颁布的令状,以郡而不是以封建领地为单位进行集结。”[4]68英王爱德华一世当政期间战事更为频繁,在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征服战争中,他大规模动员民兵参战。爱德华一世还颁布《温彻斯特法令》,重申了自由民对于国王的军役义务。警役(constable)一职就是在此时设立的,主要职责是动员村中民兵参战,平日里负责民兵的训练事宜。广大民兵武器自备,但国王却不愿向其提供粮饷,要求各郡自行负担,导致抗议之声四起。经过民众不断抵制和请愿,从英王爱德华三世时起,规定所有民兵自离开本郡时起,由国王支付报酬。
自14世纪起,随着英格兰王国之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整个社会开始出现巨变。正如戴尔所说:“我们无法忽视13-16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个时期里,领主与佃户、国家与臣民、农业与工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英国的社会与经济再也不会回归从前。”[5]42庄园经济开始解体,附着于其上的封建骑士军制也出现了危机。在这一时期,英格兰王国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职能日渐完善,同时,新型步兵方阵和战术兴起(所谓“步兵革命”),英王开始更多依靠民兵和雇佣军作战。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王大批征召民军,在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中,英格兰长弓手重创法国骑士军团,此役对于提升步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百年战争也极大地提升了英格兰的战争动员能力。安德森指出:“在百年战争大部分进程中,英国的优势并非来自海上霸主地位…这一优势正是来自英国封建君主政体更高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和完整性。直到战争接近尾声之时,比起法国王权来,英国封建君主运用其固有财富、动员其贵族的行政能力一直强得多。”[6]117
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之王权得到空前强化,通过宗教改革和拓展王室领地,英王获得大笔财富,一系列司法改革则削弱了大贵族势力。此时的英格兰才真正具有了“现代国家”的雏形,“都铎君主成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和英国教会的正式领袖,这种中央集权的动因将英国带入到现代时期。”[7]143不过,直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王国仍然没有常备军体制,只是常年维持着一支人数精干的王室卫队。为何无常备军?梅特兰指出“维持一支常备军要面临双重困难:一是不诉诸非法的委任状就无法维持任何军纪;二是不通过任何非法的敛财渠道就无法供养军队。”[8]180梅特兰点明了维持常备军军纪的困难和日常开销的巨大。另外,英格兰独特的地理位置(海洋屏障),也可能是无常备军的原因之一,即使面临外敌入侵,也可在得知消息后从容不迫地进行动员。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军队集结正是基于以下两个前提:地方政府(城市和乡村)有完善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广大“自由民”有足够的财力可以自行负担军事装备。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做到以上两点并不困难。
需要指出的是,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王国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召集民兵保卫国家。军队在出征时国王会给予报酬,但平日的供养、训练都掌握在地方乡绅阶层手中,征兵官由乡绅担任,训练所需费用也由乡村富户承担。这是由英格兰王权之有限性和浓厚的地方自治传统所造成的。正如安德森所言:“新的都铎王朝君主政体是在有限的基础之上运作的。这使它与欧陆其他王朝有所不同:它没有一个坚实的军事结构…都铎王朝国家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与法国、西班牙绝对主义相匹敌的军事机器。”[6]117警役作为乡村基层官员,正是在征兵和维持乡村民兵队伍上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二、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格兰王国之乡村治安管理
论及乡村治安问题,笔者以为,有必要简单阐发一下英格兰之乡村自治传统。
英格兰有着“地方自治之家”的美誉,其地方自治传统源远流长。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日耳曼人马尔克公社制度中的原始民主遗风对英格兰的乡村自治传统造成了深远影响。到公元10世纪时,已经大致形成了郡——百户区——镇区(或村庄)的地方行政结构。村庄由村长(reeve,旧译为里夫)管理。阎照祥教授指出:“村庄是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社会基层组织。村长由百户长指定或由村民推举,负责村务,诸如处理邻里纠纷,缉捕盗贼等。”[3]25此时的乡村基层官员还较为原始,往往身兼多项职能。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乡村开始了封建化和庄园化的进程,但这种古老的自治传统并没有因此中断,仍然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所谓“乡村自治”主要是体现在“乡村共同体”这个层面上,梅特兰指出“晚近的历史学家们在镇区中看到了一个比在庄园中更为古老的社区或共同体(community)-就英国的历史而言,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始的共同体:一群人或一个家庭群落,很可能是依据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依照集体农业制度耕作土地;他们是或一直是这些土地的主人…这些事务都通过一个被称为镇区法庭(township-moot)的机构得到处理。”[8]35虽然“共同体”是一个较为晚出的概念,但其所反映出的问题:英格兰乡村所具有的原始民主特性(广泛的政治参与性)和政治结构的非单一性,很早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宪政史家)。
从中古时期到近代早期(16-17世纪),英格兰乡村之政治结构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由庄园——乡村——教区三者构成。村民的身份也具有多重性,在庄园中,他们是领主的佃户;在教区中,他们都是教士之“教民”;而在乡村中,他们又是享有一定自治权力的“乡村共同体”成员。有时,一个庄园就是一个村庄,或一个大庄园下辖几个村庄,或一个大村庄内有多个庄园,情况多种多样,但以前两种情况较为常见。庄园体制更多体现一种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到都铎王朝时期,庄园制度已呈现衰败迹象,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起初只是骑士扈从的约曼阶层逐渐崛起,成为英格兰农业生产变革的中坚力量。体现宗教职能的教区也开始承担一些世俗管理职能。
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公法的分裂态势,虽然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王国之立法和司法建设有了很大进展,但主要成就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如星室法庭的设立和议会一系列法令的通过),对于地方性事务的管理仍要依靠传统惯例,在乡村层面就更是如此。对于乡村司法和治安问题,领主主要依靠庄园法庭予以管理,但这需要整个“乡村共同体”的成员参与其中,这是由庄园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乡规民约”所决定的。正如伯尔曼所述:“法庭本身由庄园全体成员组成,上至领主和管家,下至地位最低的农奴。他们全都是法官,被称作‘诉讼参加人’…关于自由人与农奴参与裁判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区别…庄园司法的运作需要全体成员之间高度的合作。”[9]320
伯尔曼所言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但乡村共同体之自治传统和“乡规民约”确实会对领主之权威形成一定制衡作用,村民对于“乡村共同体”的政治事务有广泛的参与性。英格兰王国地方政府职能单一,又没有成熟稳定的文官制度。甚至到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郡级政府都还不是常设机构,本郡事务主要在季度法庭(quarter session)召开时集中办理。 郡守(sheriff)、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 、民兵都尉(lord lieutenant)等郡级官员都没有薪金。如许洁明所述:“在17世纪的英格兰,通过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地方行政制度,主要只是一种形式…而地方政府的存在…是依靠‘业余’官员及这些官员与中央政府的合作来维持。”[10]74因此对于地方治安问题(尤其是乡村治安),中央无力单独管理(尚没有警察制度),就要依靠民选产生的“乡村共同体”官员协助处理。这些“共同体官员”在处理治安事务时,往往更注重维护“邻里之情”,依照“乡规民约”来处理纠纷。以警役为首的乡村官员对本村的管理带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他们往往和本村居民联合起来,在庄园法庭上与领主分庭抗礼,或与上级官员据理力争,“乡村共同体”的自治特性在警役处理治安事务时有着充分的表现。
三、警役之军事职能
可以说,常备军制度是一个国家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供养一支常备军需要有完善的财政体制和发达的官僚制度,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战争动员。同时,军队之征兵工作、平日的训练、以及战时的后勤补给也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战争是对国家机器运作能力的重大考验。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率先在欧洲建立常备军,并推行普遍兵役制,加之运用新式战术,使瑞典军队战斗力大增。法国也紧随其后建立了常备军。英格兰王国却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由“护国公”克伦威尔建立了一支五千人的常备军。不过,虽然英格兰王国未能效法欧洲大陆其它“绝对主义”国家建立成熟常备军体制,但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依靠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的紧密合作,仍可以在短时间内集结大量民军。在与西班牙和苏格兰的战争中,这种高效的动员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乡村警役就是这一动员体制上的关键齿轮。现就从警役职责之演变和警役履行军事职能之具体情况展开论述。
警役一职最早出现于英王爱德华一世时期,主要职责是在战时征召民兵,警役分为两种:高级警役(high constable)和低级警役(petty constable),前者是郡级官员(郡守和治安法官)的主要助手,后者则是乡村基层官员,为本文主要论述对象。此时的低级警役还只是普通的乡村小吏,并无太多职权。前文述及,英格兰乡村之政治结构具有多元属性,庄园、“乡村共同体”、教区各有一套自己的“领导班子。”庄头在庄园中具有主导地位,主要安排庄园中的生产生活和庄园法庭事务;教区则由教区执事(churchwarden)掌管各项事务,主要是各项宗教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乡村共同体”的情况要复杂一些,除了警役以外,村中还会有一干负责各项事务的官员,如征税官、济贫官、道路巡查员、巡夜者、森林和水塘看护员等等。这些官员大多一年一任,由村民选举或抽签产生,任职期间没有报酬,只能从村庄的公共资金中获取少量补助,或者以免除部分赋役作为回报。一些地区的乡村共同体还有堡长(borsholder),副堡长(thirdborough)等官员,他们主要负责村庄的治安。[11]
警役之职权经历了一个扩展的过程。到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警役之职能逐渐增多。除军事职能外,警役还要负责征税、治安巡逻、维护公共设施、处理邻里之间的各种纠纷等等,他们成为“乡村共同体”中的政治领袖,之前提及的众多“乡村共同体”官员,大多成为了警役的副手和属下,协助其处理村中的各项事务。警役的军事职能虽然有所削弱,但仍是其众多职责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就此略加论述。
警役之军事职能包含多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在战时动员村中民众组成民兵,警役一般会与民兵都尉共同负责征兵工作,并将全体民兵送至集结地域。其次,警役还要每年对民兵进行训练。第三,警役要负责民兵所需各项装备的保养工作,有时还要去采购所需武器。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警役军事职能之履行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这取决于英格兰王国是否与别国处于战争状态。当发生战事时,警役的军事职责就会大幅增加。在某些年份,尤其是在16世纪80年代末到16世纪90年代,以及17世纪20年代末到17世纪30年代,警役们十分频繁地参与军事活动,不断地征召民兵,并投身于对士兵的训练中。[12]这可能是由于英格兰当时正与西班牙和苏格兰处于交战状态,故警役之军事职责甚为繁重。
征召士兵、组织民军是警役军事职责中的重要内容。征兵工作主要是由郡政府之征兵官和民兵都尉负责,警役起初只是从旁协助。到都铎王朝晚期和斯图亚特王朝初期,乡村警役开始全权负责辖区内的征兵工作,并在征兵官前来检查时展示村庄中的武器装备。从征兵官向警役发出的授权令中可以看出,征兵官经常命令警役自己也要加入到民团中,并且要确保“乡村共同体”的应征民团阵容齐整,并且配有适度的装备和武器。[13]规模不同的村庄按照人口比重提供数量不等的士兵,在人口比较稀少的村庄,一般只要求提供2到3名士兵,如果战事紧张,所有16到60岁的男性都有义务去服役,有时警役们会起草一份村中有能力服役者的名单,并提交给征兵官,由征兵官决定谁来服役,一般来讲,有多次服役记录或年龄较大者可以免于服役。
从现有的警役向上级提交的报告书来看,他们对于征兵事务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警役们必须要确保征应征士兵的人身安全,直到他们接到命令开赴战场。有时警役们还会雇佣人员来协助自己保护应征的士兵,不过与其说是保护,还不如说是看守,因为很多农民都是被迫服役,虽然参军会得到国王给予的薪金,但毕竟上战场生死未卜,经常有人逃走,警役雇人看守应征士兵也就见怪不怪了。例如1598年,斯塔福德郡帕丁汉姆村的警役就付钱给一位村民,让他看守一位要被征召至爱尔兰服军役的人。[14]在1625年曼彻斯特的警役也雇佣了几位同乡来看守新兵,新兵在当地的小旅馆被“保护”了5天,直到他们被军官带走。1640年莱斯特郡沃瑟姆村的警役付钱给几位村民,让他们帮助保护2名被征召的士兵,其中有1名士兵整整被看守了6天6夜。1640年Carleton Rode村的一位警役也记载了看守1位应征士兵时的开销。1639年East Harling村和曼彻斯特的警役们还记录了一笔额外的开销:他们要在那些前往苏格兰的应征士兵们经过本村时提供保护。[15]
通过分析部分警役提交给上级的报告书,可以看出他们所征召的新兵和上级的要求相差甚远,完成上级官员所分配的征兵名额的压力,以及村民们对于征兵工作的抵制情绪,使得警役不时会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完成征兵任务。有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录:警役会雇佣“陌生人(非本村人)” 去服役,或者抓捕外来的人去服役。例如,帕丁汉姆村的警役就多次用“陌生人”来填补征兵名额,在1594年该村的警役报告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雇一个人去爱尔兰服役”警役共花了14先令,1596年警役又花了8先令雇一个陌生人去服役,其中有3先令4便士是他的“饮食开销”。在1598年该村警役只花了6便士就雇到了一个陌生人去服役。甚至有一次该村的警役已经征召到一名村民去服役,不过,警役却给了军官5先令让他把这名村民放了,然后用一个不知哪里找来的“陌生人”取而代之。[12]
在1607-1608年,英格兰王国对爱尔兰发动战争,此次战争规模不大,但仍从全国范围内调动了不少民军出征。在这一时期,帕丁汉姆村的警役付给一位去服役的人5先令,诺福克郡斯托克顿村的警役则花了10先令雇了一个人去服役。在1625年,曼彻斯特的几名警役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征兵名额采取了更加“非常规”的手段:警役付钱给两位同乡,让他们负责圣灵节前夕、圣灵降临节周一和周二的治安工作,自己则四处抓人当兵,依靠这种野蛮的方法他们在6月7日总共征到了20名民兵,随后将他们送到了洛支旦镇,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警役对这些强征来的士兵严加看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11]
还有其他一些资料显示警役之征兵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在郡治安法官的报告书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记录:治安法官指责警役征召的新兵有“各种缺陷”,而且士兵中有很多人都不是警役的同乡,而是所谓的“陌生人”。在1627年,莱斯特郡的治安法官指责辖区内的警役们在征兵时疏忽大意,并且威胁说,如果警役们不能征召到“能干的士兵”,就将他们自己征去当兵。不过上级的警告,似乎没有引起该郡警役的足够重视,兵源质量低下的情况仍在上演。该郡治安法官还抱怨道“警役经常通过贿赂将应服役者释放,这是在直接挑战我们的授权令,送到我们这里服役的尽是些身体有缺陷的人”。[12]
1637-1640年,苏格兰人民发动反英起义,英王查理一世派兵镇压,故这一时期征兵频繁,关于兵员质量的抱怨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南安普顿的治安法官对辖区内警役之指控最为典型:属下的警役Burton Latimer和一些乡村官员,在1639年4月逮捕了“绅士们的仆人和其他郡的有着良好素质的陌生人”,强迫他们去服役,以此“取代警役的同乡”。该治安法官还说,他已将有违法行为的警役抓去当兵,作为对他们玩忽职守行为的警示和惩罚。其他郡的治安法官也有类似的记载:1638年,剑桥郡的治安法官指控属下的一名警役,声称后者在因公外出时,逮捕了一个陌生人并勒令其去当兵。同年,肯特郡Ashford村的一位警役,也因强征陌生人当兵而被上级官员指控。1640年,康沃尔郡的治安法官指责属下的警役“疏于履行征召士兵的义务”,为此治安法官强迫警役们去当兵,为的是迫使他们“征召自己家乡中有才能的人”去服役。[15]
有时甚至会有这样的极端情况:警役利用手中的征兵特权收受贿赂,或是帮朋友逃避兵役,或是借机将自己的仇人拉去服兵役,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例如,1598年一位萨福克郡的商人声称自己和同村的警役因一件小事结仇,结果后者利用手中权力将他强征到海军服役。在1596年一份提交到星室法庭的诉讼中,两位诺福克郡的警役被指控犯有受贿罪,他们在受贿后放走了应去服役的人。此二人最后都被免除了职务,其中一人还被处以罚金。[16]
虽然在战事频仍之时,警役之征兵任务会十分繁重,但16-17世纪英格兰乡村的生活整体上还是较为平静的,警役平日的军事职责在于维护武器装备和组织民兵训练。前文述及应征民兵需要自备武器,但从16世纪起,许多乡村开始设置“公用武器”,由全体村民出资购置,武器的维护往往就由警役负责。警役还要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召集民兵进行训练,确保军容严整。[17]上级官员(民兵都尉)会定期前往各村检查,如果武器装备存在问题,整个村庄的居民都要一同受罚。
从现有资料来看,警役在采购和维护武器装备、组织民兵训练方面是颇为“尽心尽责”的。例如在维护武器方面,警役需要不时采购新武器,虽然可以获得补助,但警役有时还要自掏腰包。斯塔福德郡帕丁汉姆村的警役在购买武器方面表现的十分勤奋。从1587-1588年,该村警役采购了大量新装备,包括两把长剑、两把短剑、一根长矛、一顶头盔、四条腰带、两个剑鞘。在16世纪90年代末又进行了多次采购,1594-1595年该村警役购买了一枝步枪,在1595-1597年共购买了四把剑。1613-1616年,警役们又陆续购买了一支步枪、三把剑和剑鞘、两顶头盔。在莱斯特郡也有警役大量购买装备的记载,1613年该郡梅尔顿·莫布雷镇的警役购买了两根长矛、一枝步枪、一件胸甲、以及头盔,子弹带等等。同年,该郡沃瑟姆村的警役在采购军事装备上共花费了3镑10先令,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1614年吉辛村的警役也采购了一批“公用武器”,包括两把长剑、两把短剑,还花了8先令购置了一套盔甲。[18]1618年什罗普郡萨沃普村的警役花费26先令购买了一支步枪。1625-1626年,该郡Carleton Rode村的官员购买了几根长矛。[15]17世纪30-40年代诺福克郡的Carleton Rode村和斯托克顿村的警役采购了几批胸甲和剑,米林顿村的警役购买了一把剑和两根长矛,还有腰带、剑鞘、背包等等。[19]
在每年的某些时段,警役还要协助民兵都尉训练民军,各村的训练时间并不固定,一般是在夏秋季节,持续时间通常不超过十天。如果是人口较为密集的村子,训练就会在本村进行,若村中人口不多,就会由附近的几个村子进行联合训练。例如,斯塔福德郡帕丁汉姆村人口稀少,因此在1625-1626年该村的警役和民兵每年7次前往乌尔汉普顿村参加军事训练。同一时期诺福克郡梅尔顿·莫布雷村的警役每年进行5次军事训练活动。在1626-1627年什洛普郡布兰斯顿村的警役共组织了4次训练。1628年该郡怀姆斯沃德村的警役也组织了4次训练。至于训练的持续时间,以莱斯特郡沃瑟姆村的警役为例,1639-1640年该村警役一共4次前往Loughborough村参加军事训练,时间分别为5月6-8日,5月27-31日,6月9-11日,另有一次是在9月,几次训练活动一共进行了11天。1642年沃瑟姆村的警役在6月中旬和8月底之间一共参加了5次军事训练,每次训练的时间都不长。地点分别是6月15日在梅尔顿·莫布雷镇,6月27日,7月20日和8月11日在莱斯特,8月26、27日在Loughborough村。[20]
就现有资料来看,从16世纪至17世纪初,警役在履行军事职能方面有着较为出色的表现。考虑到当时英格兰王国并没有设置常备军,故警役履行军事职能的效率对于国家之军事动员具有重要意义。警役不仅协助民兵都尉在战时征兵,还要在平时负责武器装备的采购、维护以及民兵每年的定期训练,警役在这些事务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英格兰王国在军事动员方面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包括乡村共同体在内)的密切配合。可以说,正是以警役为首的乡村共同体官员的忠于职守,才使得英格兰王国得以在几次对外战争中迅速动员民军,有效保护了本土的安全。
四、警役之治安职能
管理乡村治安也是警役的一项重要职能。如果说警役之军事职能更多体现其“国家公务人员”的特性,那么治安职能则反映出警役作为“乡村共同体”官员的性质。英格兰“乡村共同体”之自治特性表现为全体村民对于共同体事务的广泛参与、“共同体”官员对于乡村利益的维护、乡规民约在乡村政治中的基础性地位等等。警役在履行治安职能时主要是以本村的“乡规民约”作为依据,本村之利益的维护也是他们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由警役的“民选官员”本质所决定的。
16-17世纪初,“圈地运动”正在英格兰乡村愈演愈烈,伴随而来的是乡村产权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动。正所谓“土地这一当时最宝贵、也最稀缺的资源获得了全新的配置,形成了以大地主所有制为特征的全新的产权结构组合…促成了小农经营的全面衰落…加速农民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为劳动雇工化、土地资本化和地租资本化开辟了道路。”[21]但这一进程的副作用就在于产生了大量“外来者”(outsider),也就是所谓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或充当雇工、匠人、或从事小买卖,但也有部分人干些违法的勾当或者沦为乞丐,他们对乡村治安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对“外来者”加以制裁和防范便成为警役的重要职责。
乡村共同体的村民对于“外来者”是颇为敌视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者”只是在村中短暂逗留,无法与村民“同甘共苦”,对于其中的流浪汉和乞丐则更是排斥。现有资料中显示警役经常会对“光临”本村的流浪汉予以驱逐或处罚。赫特福德郡的官员对于处罚流浪汉问题有着详细的记载。如1631年8月Broadwater百户区的官员约翰·加兰德、查理·凯撒和威廉·凯德在自己的报告书中指出:当年其辖区内已累计有125名流浪汉受到处罚。[22]在1634年4月Broadwater百户区的警役声称自从1月末以来已经处罚了38名流浪汉,其中还有9人是爱尔兰人。该地1637年3月的报告书指出自1636年6月末以来共处罚了76名流浪汉。在1634年3月Dacorum的官员报告警役共处罚了110名流浪汉,在1636年4月Dacorum的官员又报称最近六个月中各村的警役共处罚了106名流浪汉。[22]莱斯特郡也有类似的记载,在1631年,Sparkenhone村的警役报告说他们在过去几年中累计处罚了753名流浪汉。警役们的勤奋受到了治安法官的赞扬,后者认为警役已经“基本清除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流浪者”。1631年6月Framland百户区的治安法官指出辖区中有部分警役存在对流浪汉疏于处罚的情况,他对懈怠的警役处以每人20先令的罚款。治安法官的处罚效果明显,随后的文件显示,到1632年1月,该百户区总共有113名流浪者受到处罚。[11]
有时警役和村民们也会对流浪汉予以救济。例如1590年苏塞克斯郡一位警役不顾治安法官的命令允许流浪汉和“游手好闲者”在村中留宿。[23]1615年该郡East Grinstead村的一位警役因对一位流浪汉的处罚“十分轻微”而被召到巡回法庭受审。1618年在沃里克郡Preston Bago村,一位绅士将4名流浪汉移交给该村警役,但后者只是将他们短暂监禁,随后便让他们“各奔东西”。有些警役甚至“款待”流浪汉。1630年约克郡诺斯雷丁村的一位警役因将20名流浪汉带到家中饮酒而遭到治安法官的指控。[12]
除了驱逐行为不端的“外来者”,警役还需每日在村中巡视维护治安。在16-17初的英格兰乡村,盗窃罪是较为常见的,警役在处理此事时,往往按照“乡规民约”和“邻里之情”行事。若罪犯是自己的同乡,警役一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比如,1576年在诺福克郡Cley村,该村警役放走了一位有盗窃嫌疑的村民而受到治安法官的指控。1601年约克郡的一位警役被带到季度法庭上受审,因为他没有执行一份抓捕盗窃犯的授权令,法庭对其处以20先令罚金,他还因“对法庭的嘲笑,轻蔑和有损名誉的言论”被投入监狱。又如赫特福德郡布希村的约曼警役乔治·布莱克威尔,在1596年的一次巡回法庭上他供认自己释放了一位应当由他押送到监狱的犯人。诺丁汉郡的一位警役因允许被看管的犯人逃走而被治安法官召到季度法庭上接受质询,这名警役态度傲慢,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对治安法官称“会有另一个无赖去执行警役的义务”而被法庭罚款10先令。[24]有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上级官员来村中抓捕罪犯,警役不愿从旁协助,甚至加以反抗。例如,威尔特郡的几位治安法官前往Marlborough村执行逮捕命令时,遭到当地村民的袭击,该村警役却对此不闻不问。[12]
流浪汉和乞丐会遭到警役的驱逐,但对于因事外出途径村庄的人,警役和其他乡村共同体官员则有义务提供帮助。比如途径村庄的朝圣者、旅行者、从战场上返回的残疾士兵、遭遇海难的船员。郡级官员会给他们颁发通行证,并命令警役在他们路过村庄时给予帮助。他们在进入村庄时必须向警役出示通行证,若是没有通行证的“陌生人”,警役有权将其逮捕。
此外,警役还要处理村中的各种“琐事”。例如制止村民之间的打架斗殴和恶言相向;处罚酗酒闹事和聚众赌博者;拆除违法搭建的房屋;处理各种农事纠纷(在他人土地上放羊,私建篱笆等等)。例如,英王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严守安息日的法令,规定人们不得在安息日玩“不适宜的游戏”(主要是掷骰子、纸牌等赌博活动),授权警役监督村民。1625年又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民众周日活动的法令,并授权警役和教区执事对违反法令者处以罚金,还可在必要时扣押违法者的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警役在处理村中各种治安事务时,往往需要其他乡村共同体官员和村民的合作,否则,警役是孤掌难鸣的。若要对某位破坏治安的村民做出处罚(如某人打架、盗窃或赌博),庄园法庭的措辞一般如下:“经领主和佃户们的同意”或“经法庭全体成员的同意”,“对某人作出处罚。”警役向治安法官提交的报告书也会在结尾附上全体村民的签名。由此可见,管理乡村共同体政治事务是全体村民的义务,因为这涉及到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参与其中能够有效维护共同体的利益,故能引起他们的政治热情。这种参与有“乡规民约”作为依据,更体现出共同体强烈且久远的自治精神。
五、结论
警役作为英格兰王国的乡村基层官员,自身具有“双重属性”,他们既是“国家公务人员”,也是“乡村共同体”的官员。国家公共职能和地方自治职能在警役身上完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在16-17世纪初,英格兰王国中央政府之建构逐渐成型,地方政府职能也较之前有所发展,但还远称不上“成熟”。警役则由最初的乡村小吏成长为“乡村共同体”的政治领袖和利益代言人,警役之履行军事职能和治安职能充分体现出其“双重属性”。
首先,警役对于军事职能的充分履行确保了英格兰王国具有高效的军事动员能力。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王国仍没有设置常备军,仅有一支人数有限的王室卫队。每当发生战事,都要动员地方民兵参战,警役之主要军事职责便是协助民兵都尉完成征兵任务。虽然在档案中存在着警役所征兵源良莠不齐、收受贿赂使同乡免于服役、雇人顶替同乡服役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警役之征兵工作是较为出色的。而且,警役还要在平日里负责民军武器的采购和保养、定期组织训练等等,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警役有着卓越的表现。正是这些普通乡村基层官员之“恪尽职守”使得英格兰王国可在短时间内完成战争动员,集结起数量可观的民军,加之英格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军力量的成长,使战火难以危及到英格兰王国之本土安全。
其次,警役对乡村治安的维护体现出英格兰乡村的自治传统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度。英格兰乡村有着久远的自治传统,乡村管理之原始民主特性长期存在。广大村民有着三重身份:教区之教民、领主之佃户、“乡村共同体”之成员,“乡村共同体”利益之一致性要求村民们参与到乡村政治管理中来,这种参与得到了“乡规民约”的制度性保障。“乡村共同体”之官员全由民选产生,其以警役为核心管理村庄事务,在维护乡村治安的过程中,警役通常以“乡规民约”而不是国王之令状作为执法依据。这并不是说警役不注重对正义的维护,而是乡民们在自治体制下选择了更具效率的解决方式。依靠“乡规民约”和“乡村自治”有效缓解了矛盾、解决了纠纷,同时避免了执法严苛对于村民生活的干扰。广大村民对于“乡村共同体”治安维护的参与也增加了他们对于“共同体”的认同。
最后,警役身上的“双重属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格兰王国的现代化之路在地方政治上的路径。英格兰王国直到16-17世纪仍没有成体系的文官制度,中央政府机构设置也远称不上完善,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基层政府)更是“粗糙简陋。”再加之英格兰乡村之自治传统,使得国王之政令难以直接传达到乡村,故需依靠“乡村共同体”官员协助管理,后者无薪金,又是民选产生,在执行王之政令时经常以维护地方利益为基准,中央与地方之矛盾往往以双方妥协而告终。英格兰之王权无力对乡村进行全方位控制,只能在宏观层面进行管理,这就为后者的发展保留了宽松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警役竭力在集权和自治之间寻求平衡,中央与地方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促进了英格兰乡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以警役为首的“乡村共同体”官员通过参与乡村政治生活锻炼了自身,士绅阶层逐渐崛起,成为国家新生之政治力量,自治理念也由此深入人心,并被他们带入到更高一级的政治管理层次中。
参 考 文 献:
[1]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 [M]. 李增洪,候树栋,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阎照祥.英国史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 周威.英格兰的早期治理-11-13世纪英格兰治理模式的竞争性选择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英] 克里斯托弗·戴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 [M]. 莫玉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M]. 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维克多·李·伯克.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 [M]. 王晋新,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8]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 [M]. 李红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9] 阎照祥.英国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M]. 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1] William Sheppard, The Offices and Duties of Constables, Borsholders, Tythingmen, Treasurers of the County-Stock, Overseers of the Poore and other Lay-Minister, London, 1641.
[12]J. R. Kent, The English Village Constable 1580-1640, Oxford, 1986.
[13] A. Hassell Smith. Justice at Work in Elizabethan Norfolk, Norfolk Archaeology, 1967.
[14] Joel Hurstfield, Freedom,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in Elizabethan England, Cambridge,1973.
[15]Keith Wrightson, Poverty and Piety in an English Village:Terling,1525-1700, New York,1974.
[16]E. P. Cheyney, A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defeat of the armada to the Death of Elizabeth, New York, 1926.
[17]Lindsay Boynton. The Elizabethan Militia 1558-1638,London, 1967.
[18]J. H. M. Cam. Liberties and Communities in Medieval England, Merlin Press, 1963.
[19]T. G. Barnes,Somerset,1625-40:A County's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sonal Rule', Cambridge,1961.
[20] Eleanor Trotter, Seventeenth Century Life in a Country Parish, Cambridge, 1919.
[21] 王晋新,姜德福.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22] Julie Calnan, County Society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County of Hertford, 1580-1640, Cambridge University,1979.
[23] Anthony Fletcher, A Country Community in Peace and War, Sussex, 1600-1660,London,1975.
[24] Rosamond. J. Faith, Peasants, Manors, and Court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3, Jul, 1998.
责任编辑:林衍
A Tentative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 of British Rural Constable Military and Security in Early Modern Period
Li Guang-d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Constable was England's rural officials in medieval and modern period and its function was further improved in Tudor and Stuart dynasty. As a result, constable became the political leaders of the rural community. Military function reflected the "national civil servants" nature of the constable and security function showed the "rural community official" nature of the constable. Constable complied with the king's lien to perform the military function and tended to pursue "local rules"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neighborhood" to perform the security function. Constable itself reflected the compromise between British tradition of centralization tendencies and autonomy and this "balance" ensure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society.
Key words:England; constable; military; security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李光迪(1987-),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2013级世界史专业博士生,从事警察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D035.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745(2016)01-00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