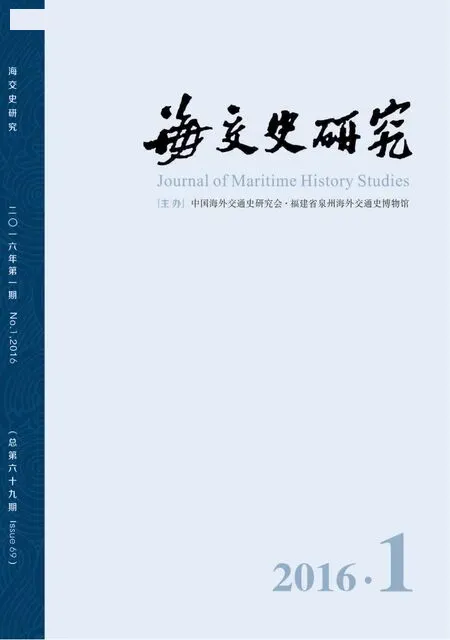17世纪法国入华传教士东西交通路线初探
——早期法国远东扩张和天主教入华传教的相互关系
谢子卿
17世纪法国入华传教士东西交通路线初探
——早期法国远东扩张和天主教入华传教的相互关系
谢子卿
〔摘要〕首位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罗历山回国后寻觅到陆方济等人,他们在罗马教廷的支持下成立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个传教团体努力探索从中东到印度洋海陆结合的路线,同时帮助法国人的远东势力扩张至暹罗,为法国传教士建立起一条通向中国的全新路线。之后在法国耶稣会士的斡旋下法国商船在17世纪末抵达中国,终于打通了法国和中国之间的海路。法国传教士为此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这一方面是出于在17世纪已很明显的民族国家意识,另一方面是希望法国可以为传教士在远东的海外传教保驾护航。
〔关键词〕巴黎外方传教会耶稣会法国暹罗
17世纪入华的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对于中西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些年来关于他们在华的传教、汉学、艺术、科技以及医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关于东西交通的最新成果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翻译出版的研究法国耶稣会士的系列专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翻译出版的这系列专著中,有关法国传教士入华通道的研究成果可参考:[法]伊夫斯·德·托玛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辛岩译:《耶稣会士张诚: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大象出版社,2009年;[丹]龙伯格著,李真、骆洁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年;[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法]李明著,郭强译:《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其他还有:[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中下卷)》(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大象出版社,2001年;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4、5、6)》(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大象出版社,2005年。[西]闵明我著,何高济、吴翊楣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大象出版社,2009年。,这些著作均对17世纪末期法国耶稣会士以国王数学家之名入华的过程有着详细论述。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以17世纪所有入华法国传教士的东西交通为研究对象的考察并不充分,这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葡萄牙远东保教权对于法国传教士入华通道的影响;第二,巴黎外方传教会开辟暹罗作为入华中转站的历史;第三,法国传教士和母国在开辟远东路线时的密切合作。针对上述三点,本文试图以他们的东西交通线路和法国的远东扩张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为切入点,将不同传教团体的法国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把早期全球化视野中当时天主教国家“传教和贸易并举”的时代特征在法国传教士身上的体现论述清楚。
一、早期法国耶稣会士的入华通道
1583-1687年间,据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法国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父所著《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的译本有两种,一种是梅乘骐、梅乘骏的译本,由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另一种是冯承钧译本,本文所查耶稣会士资料以光启社译本为准。此外,其他法国耶稣会士的传记可参考: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也可以酌情参考:[法]荣振华、[法]方立中、[法]热拉尔·穆赛、[法]布里吉特·阿帕乌编,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统计,共有20位左右的法国耶稣会士入华,他们都受葡萄牙保教权*自大航海时代起,天主教随着葡萄牙在远东的海外扩张而传播,为此罗马教廷授予葡萄牙保护传教士传教相关权益的相关规定简称为“保教权”,其中要点有:1.为殖民地的传教事业提供经费,包括神职人员的薪俸及培养费用;2.从欧洲出发前往亚洲的传教士搭乘葡国船只,葡王并为传教士们提供一定的旅费;3.从里斯本出发的传教士们,不仅要向天主教和教宗宣誓效忠,还要向葡萄牙国王宣誓效忠。可参见顾卫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3页。的庇护才得以从澳门进入中国。其中最早入华的是罗历山神父(Alexandre de Rhode,1591.3.15-1660.11.5),他于1619年4月4日从里斯本出发,大概在7月20日绕过好望角,10月9日抵达印度果阿,在当地逗留一段时日后于1622年7月28日抵达当时由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Malaque)*现在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市(Malcca),位处马六甲海峡,与苏门答腊岛相遥望,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领该地,不过在1641年被荷兰占领。。由于天气原因停留了9个月后再度启程,终于在1623年5月29日抵达澳门;原先在墨西哥传教的颜尔定神父(Partin Burgent,?-1629)于1629年横穿太平洋途经马尼拉抵达澳门;接着方德望神父(Etienne Le Fèvre,1598-1659.5.22)从里斯本出发于1630年抵达澳门;这三位神父有一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是日本而非中国,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是远东天主教传教最成功的地区,因此对传教士更具吸引力。不过无论是去日本还是中国,澳门都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当时德川幕府掀起教难使得他们不得不滞留澳门以便转往其他地方继续传教。由此,颜尔定和方德望被耶稣会的上级委派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直至去世,而罗历山在1627-1630年、1640-1645年这两段时期内先后在东京和交趾支那*东京(Tonkin)指越南北部;交趾支那(Cochinchine)指越南南部地区。传教,1630年到1640年的十年间他在澳门和广州传教,1645年12月20日他启程从澳门出发于1649年6月29日回到罗马,在罗马述职期间撰写的有关越南和中国传教见闻的著作出版后,进一步激发了耶稣会士的传教热情,由此耶稣会总会长尼格尔神父(Nickel)在1654-1655年间,先后派出四批传教士共18人奔赴远东,其中16人为法国人,他们大部分都先到里斯本,经葡萄牙保教权批准后,由葡萄牙方面全额提供经费沿着葡萄牙的远东航线抵达澳门,随后再根据耶稣会的指令前往越南、日本或者中国内地。
当时海路的凶险非现在所能想象,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耶稣会士的海难死亡率约有三成*吴孟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0年,第105页。,猝不及防的恶劣天气、险象环生的暗礁险滩、致命的各类流行病以及海盗打劫等等,使得传信部和耶稣会都试图另辟一条新路去中国。总会长尼格尔神父1654年派出的第一批法籍耶稣会士刘迪我神父(Jacques Le Favre,1610-1676.1.28)、聂仲迁神父(Adrien Greslon,1614-1695)、洪度贞神父(Humbert Augery,1616-1673.7.7)等人就没有从里斯本走海路出发,而是尝试“取道叙利亚,沿幼发拉底河道,入波斯湾,进印度洋,然后到了暹罗王国”*[法]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 年,第328页。,再北上从澳门进入内地。*据《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所述,1652年法国耶稣会士已经在伊斯法罕建立据点。而且,罗历山神父在教廷的支持下成为中东传教的负责人,他挑选苏纳和白乃心两位神父试图通过中亚进入中国,不过未能成功,因此他们二人亦只能最后走海路入华。苏纳去世后,在京的汤若望神父委派吴尔铎代替苏纳神父,和白乃心神父二人从北京出发经过兰州、西宁、拉萨、加德满都、印度阿格拉、达大(Tattah)、忽鲁谟斯、伊斯法罕、士麦拉回到欧洲。汤若望神父的继任者南怀仁神父亦同样试图探寻穿越俄罗斯的道路,不过由于中俄尼布楚战争而引起俄国警觉,17世纪90年代耶稣会士闵明我神父的努力亦失败而告终。总体来说,穿越中亚、俄罗斯或者西藏入华的陆路交通线路探索并未成功,海路依旧是法国传教士,乃至所有入华传教士的主要入华通道。可参见:吴孟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第96-136页;吴莉苇:《17世纪耶稣会士对通往中国之陆上通道的探索》,载《天主教研究论辑》(第四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54-175页。由于要穿越奥斯曼帝国、伊朗的萨菲王朝以及莫卧儿帝国三个伊斯兰国家,这条陆海结合的线路比葡萄牙的海路更危险,所花费的时间更长,不稳定因素更多;所以日后入华的耶稣会士绝大多数还是选择海路,他们乘坐的葡萄牙船至少可以在葡属远东殖民地或者商站补给,还可以躲避陆路上的打劫和宗教迫害。由此可见,若没有葡萄牙保教权的庇护,耶稣会很难进入中国,因此这一时期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为保入华通道也会为葡萄牙的国家利益效力,例如当鳌拜等辅政大臣为执行康熙元年的“迁海”和“禁海”令意欲让葡萄人离开澳门时,时任耶稣会南京住院院长的刘迪我神父就即刻进京,同汤若望神父一同商议对策为保澳门出力不少。*黄庆华:《中葡关系史》(上),黄山书社,2006年,第282-283页。
总体来看,早期法国耶稣会士入华的共性就在于他们将修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为了能入华传教,他们向葡萄牙国王宣誓效忠,得到葡萄牙保教权的许可后才得以进入澳门。因此,对于这些法国耶稣会士来说,效忠葡萄牙和效忠罗马教廷是一致的;接受葡萄牙保教权的庇护、履行他们对葡萄牙保教权的义务同维护耶稣会在远东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反过来,要保持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优势地位,他们也必须尽全力保护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地,以免耶稣会入华的交通线有被隔断的可能。尽管耶稣会为葡萄牙在远东的海外扩张贡献良多,但是葡萄牙远东帝国的衰落已露端倪。当罗历山于1645年12月20日由澳门启程回罗马述职时,他的上级就命令他“优先搭乘荷兰船去欧洲而非葡萄牙船,因为从果阿到里斯本的发船间隔太长了”*Alexandre de Rhodes, Voyages et missions du Père Alexandre de Rhod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Julien, Paris:Lanier et Cie,1854),P.343.,这恰恰从侧面反映出葡萄牙在远东的贸易地位正在下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荷兰人于1641年1月14日,从葡萄牙手中夺走马六甲从而完全支配了马六甲海峡。罗历山于1646年1月14日抵达马六甲时,同船的葡萄牙人曾告诉他说:“当时只有25人的守军在没有得到果阿援助的情况下,依旧坚持抵抗到了最后,并且围城中有一半人饿死”*Alexandre de Rhodes, Voyages et missions du Père Alexandre de Rhod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Julien, Paris: Lanier et Cie,1854)PP.340-341.,可见虽然葡方的勇气令人敬佩,但是葡萄牙的颓势已依稀可见,一方面当地守军人数明显不足,另一方面葡萄牙远东的中心果阿也未能及时给予回应,只能坐等荷兰人“垄断了苏门答腊西岸一切香料贸易和马来群岛大部分香料贸易”*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30页。。对此罗历山深有感触,他抵达马六甲的当天看到荷兰人欢庆占领日的盛大场面,加上随后他在巴达维亚(Jacquetra)*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的中心。因被怀疑传播天主教而被囚禁10个月的经历,皆让其产生出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他已经意识到葡萄牙的衰弱已不可避免,为防止天主教的远东传教会随之衰弱,就必须寻找到另一股足以抗衡荷兰和英国的力量,对于罗历山而言,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就是最佳选择。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探索入华通道
罗历山神父是首个提出天主教传教和法国远东扩张并举的传教士*Alexandre de Rhodes, Voyages et missions du Père Alexandre de Rhod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Julien, Pairs: Lanier et Cie ,1854),PP.435-436.有关罗历山神父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可参考:苏一扬著,张廷茂译:《耶稣会士罗历山:第一个在澳门的法国人》,载澳门《文化杂志》,2014年,第93期。,他于1652年回国后大力呼吁国人积极参与远东传教,除了上文提到的16名法国耶稣会士外,还有一批法国青年响应了他的号召,经罗马教廷批准后他们成立了巴黎外方传教会(the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有关巴黎外方传教会东西交通、葡萄牙保教权以及中国礼仪之争等相关问题的中文研究,可参考吴莉苇:《文化争议后的权力交锋——“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谢子卿:《17世纪法国和暹罗邦交过程中的巴黎外方传教会》,载《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郭丽娜:《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活动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韦羽:《18世纪天主教在四川的传播》,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有关巴黎外方传教会东西交通的法文史料和研究,可参考:Adrien Launay , Frédéric Mantienne, Lettres de Monseigneur Pallu: Ecrites de 1654 à 1684(Paris: Les Indes savantes,2008); Adrien Launay ,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Paris: Téqui, 1894), tome1;Relation des missions et des voyages des evesques vicaires apostoliques, et de leurs ecclésiastiques és années 1672, 1673, 1674 et 1675(Paris: Angot ,1680).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Siam,1622-1811; documents historiqlies,(Paris: Charles Douniol and Retaux, 1920).,教宗希望通过任命该组织中的三位成员担任中国和越南的宗座代牧(Vicaire Apostolique)*宗座代牧又称之为代牧主教,他是由罗马教宗钦点派往尚未建立圣统制的传教区域管理发展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最高负责人,他们直接对教宗负责,不受葡萄牙和西班牙保教权的节制。这三位宗座代牧是陆方济(François Pallu)被封为赫利奥波利斯主教(Héliopoli),“东京宗座代牧,中国云南、贵州、湖广、四川、广西以及老挝的管理者”;德拉莫特(Pierre Lambert de La Motte)被封为贝鲁特主教(Bérythe),“交趾支那宗座代牧,中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的管理者”;科托吕蒂(Ignace Cotolendi)被封为梅戴洛波里斯主教(Métellopolis),南京宗座代牧,中国直隶,山西,河南,山东以及鞑靼、朝鲜的管理者。有关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的人物档案简介,可以参阅巴黎外方传教会官网的任务资料索引库搜索查阅,见:http://archives.mepasie.org/.,以此借助法国人的力量突破葡萄牙保教权的垄断直接管理远东教务。因此,葡方绝对不会允许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从里斯本出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在任何葡属领地和商站补给,更不会让他们经澳门入华,这就迫使他们必须另辟蹊径。
三位宗座代牧首先谋划的是海路,其中之一的陆方济提议与法国马达加斯加公司联合成立一个新公司,这个公司“主要是为了荣耀上帝和拯救灵魂”*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à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Paris: P.Geuthner, 1920-1921),tome3,P.303.,而非专门从事贸易活动。他和公司签订的议定中规定:“给予陆方济20个登船名额;免费托运传教士的行李;传教士分摊首航费用;总计8万法郎预算由公司和宗座代牧平摊;宗座代牧有参与决定起航和停泊的权力……”*Adrien Launay ,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Paris: Téqui ,1894), tome1, PP.56-57.根据协议,他们决定建造一艘名为“圣路易号”(Saint Louis)的军舰,由一个名叫费尔芒(Pierre Fermanel de Favery)*他的儿子Luc Fermanel de Favery是德拉莫特的署务员,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管理会成员。的法国鲁昂军火商设计并在荷兰建造,法国驻海牙大使图(de Thou)以路易十四的名义成为所有者,不过完工后却被荷兰人扣住无法交付使用,最后“圣路易号”于1660年12月19日不幸在荷兰特塞尔(Texel)附近水域遭遇风暴而沉没*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à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Paris: P. Geuthner, 1920-1921),tome3, P.304.,这使得他们的计划暂时搁浅。
无奈三位宗座代牧只能尝试走陆海结合路线,最先动身的是德拉莫特,他于1660年7月18日在布尔热*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档案编号2:Jacques Bourge(1630.1.1-1714.8.9)他在越南传教成绩斐然,1679年11月25日被任命为东京东宗座代牧,同时册封为(奥朗主教);1686年被任命为中国传教最高管理者接替1684年去世的陆方济,不过他并未到任。的陪同下从巴黎动身,抵达马赛后同戴迪耶*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档案编号3:François Dédier(1634.9.28-1693.7.1)他和布尔热一同在越南传教,其到达暹罗而后去东京,陆方济卸下东京宗座代牧之后1679年11月25日和他一同晋封主教,被任命为东京西宗座代牧。会合,10月27日三位传教士从马赛搭船出发,次年1月11日抵达伊斯肯德伦(Alexandrette)*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靠近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地区。,然后途经摩苏尔(Mossoul)和巴格达抵达伊斯法罕,再从这里南下抵达阿巴斯港(Bender-Abbas-si)*阿巴斯市位于伊朗南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现为伊朗霍尔木兹甘省首府,是控制波斯湾船只出入的“咽喉”,中国古称“忽鲁谟斯”,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过此地。天主教传教士凡走陆路,多选择在此地搭船前往印度或者东南亚。后,坐阿拉伯人的商船去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Surate),横穿印度后再从东海岸的默苏利珀德姆(Mazulipatam)坐船,到当时由阿瑜陀耶王朝统治下的墨吉(Mergui)*现在的缅甸“丹老”,当时由暹罗统治。,穿过马六甲半岛后抵达湄南河口,最后于1662年8月22日到达暹罗首都阿瑜陀耶(Juthia)。陆方济于1661年11月8日从巴黎启程,次年1月2日从马赛港搭船去伊斯肯德伦,然后从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去奥斯曼帝国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Erzeroum),再北上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然后途经伊朗的大不里士(Tauris)抵达伊斯法罕;再从阿巴斯港(Bender-Abbas-si)出发去苏拉特然后徒步至默苏利珀德姆,之后沿着德拉莫特进入暹罗的路线,于1664年1月27日抵达阿瑜陀耶。第三位宗座代牧科托吕蒂(Cotolendi)所选路线和他们相仿,不过他于1662年9月20日在印度默苏利珀德姆8公里远的Palacol可能因感染了类似痢疾的肠道疾病不幸去世。
两位宗座代牧会合后决定由德拉莫特长驻暹罗,陆方济返回罗马述职,他于1665年1月20日启程去墨吉搭船抵达乌木海岸,然后坐英国船返回欧洲。*乌木海岸(Coromandel)是与斯里兰卡相遥望的印度半岛东海湾,具体在哪个商站登船并未提及,参见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Siam,1622-1811: documents historiques(Paris: Charles Douniol and Retaux, 1920), Tome1, P.12.1670年4月11日又搭乘法国凤凰公司的商船二度奔赴暹罗,不过刚刚绕过好望角就不幸沉没,千钧一发之际偶遇由雅各布·布拉凯(Jacob Blanquet)率领的法国首支赴印度洋的海军编队,这支舰队于1670年从法国的罗什福尔港(Rochefort)出发,拥有9艘各类舰只载有2 100名士兵和4个贸易公司共计100多人的职员,他们搭救了陆方济一行人,司令布拉凯同意带着传教士上路,于10月23日到达马达加斯加岛南部的太子堡(Fort-Dauphin)*Jules Sottas, Une Escadre française aux Indes en 1690. Histoire de la Compagnie royale des Indes Orientales, 1664-1719 , Ouvrage accompagné de gravures et d’un appendice de technique navale.(Plon Nourrit et Cie,1905),PP.43-45.。1671年9月27日,其一行人等随舰队抵苏拉特。次年2月17日,陆方济乘坐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再度出发,于4月30日抵达万丹,由于季节不利于航行且又急于上路,他于6月29日搭乘英国商船去了钦奈(Madraspatnam)*旧称马德拉斯,英译为Madras或Madraspatnam。,由于船已满载,不得不把教宗和路易十四委托其赠送给暹罗国王那莱(Phra-naraï)的礼物留在了万丹。*Relation des missions et des voyages des evesques vicaires apostoliques, et de leurs ecclésiastiques és années 1672, 1673, 1674 et 1675.(Paris: Angot ,1680),PP.94-95.其一行在8月20日左右抵达孟加拉湾,不过未能在该地进港,最后停靠在附近的法国商站巴拉松(balasson)。在当地逗留半年后,他们于3月8日搭上暹罗商船,于同月28日抵达墨吉,5月27日进入阿瑜陀耶。10月18日,陆方济等人正式觐见那莱王,之后于1674年8月20日登上一艘法国人的船去东京,但是在顺化附近海域遭遇台风被带至菲律宾群岛*Adrien Launay,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is: Téqui ,1894), tome1,P.224.另一种说法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档案3:François Pallu(1626.8.31-1684.10.29)提到陆方济此次的目的地是中国。,马尼拉方面将其拘禁,于1675年4月4日下令将其送至马德里。他于6月1日坐船去西属墨西哥,12月抵达墨西哥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Acapulco),墨西哥大主教令其暂住在大西洋沿岸港口韦拉克鲁斯(Veracruz)不远的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内,之后途经哈瓦那,于1676年11月抵达西班牙本土港口加的斯(Cadiz)。1770年1月陆方济抵达马德里觐见了国王卡洛斯二世(1665.9.17-1700.10.1在位),在法国政府和教宗英诺森十一世(1676.10.4-1689.8.12在位)的干预下,陆方济于1677年获释并赴罗马述职,由此以“环球旅行”的方式结束其第二次远东之行。同前两次相比,陆方济第三次远东之行相对顺利,他于1681年3月25日带着10名传教士登上“会长号”(Président)和 “白松号” (Blancpignon)从法国圣路易港出发,绕过好望角后在苏拉特与尹大任会合*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年,第297页。,之后又分别坐船动身,陆方济于同年7月4日抵达湄南河口。
巴黎外方传教会探索暹罗入华的过程并不顺利。第一个进入中国的是布兰多*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档案编号15:Pierre Brindeau(1636.1.1-1671.1.1)在果阿被释放后于1669年去交趾支那传教。,不过他在澳门以未经葡萄牙保教权授权而以擅自入境的罪名被捕,后被送至果阿宗教裁判所;德拉莫特坐帆船于1663年7月16日启程,不过在柬埔寨海岸附近遭遇风暴后不得不退回距离阿瑜陀耶城4公里左右远的一座小村庄,并在那里险些被果阿派来的人抓走。第一个进入内地的是陆方济,1683年暹罗国王得知其欲赴中国传教后为他提供船只,并且命令暹罗派赴广东的使节待其抵达后资助他2 000埃居的旅费*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Siam,1622-1811 : documents historiques (Paris: Charles Douniol and Retaux, 1920), Tome1, P.118.。他们一行原本会在广州登陆,不过7月8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军攻台后澎湖海战打响,他们在海上被国姓爷*ko-chinga是闽南语的音译,不过郑成功1662年就已去世,到底为何人领队带走陆方济一行人等尚待确证。(ko-chinga)的舰队俘虏,在台湾被扣近5个月,次年在厦门登陆,并且在多明我会士马熹诺(Magino Ventallol)陪同下,于1684年1月27日抵达福建漳州。
三、法国传教士入华通道的初步建立
由上可知,1680年前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入华路线基本成型,其中最重要的海路要归功于国家扶植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法国东印度公司(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成立于1664年,它和英国以及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不同,是由王室为大股东,由国家领导融资配股的垄断机构,其目的就是发展法国在远东的海外扩张事业。有关17世纪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远东的发展,可参考:Jules Sottas,Une escadre française aux Indes en 1690, histoire de la Compagnie royale des lndes Orientales1664-1719, Plon Nourrit et Cie,1905,这一过程中传教和贸易并举的特点一目了然:法国东印度公司负责运送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反之,巴黎外方传教会为公司能在暹罗建立商站居功至伟*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迪歇纳(Pierre Joseph Duchesne)于1679年途经苏拉特时成功说服法国东印度公司苏拉特商站经理巴龙(Baron)派遣三艘商船去东南亚,其中一艘“秃鹰号”(Vautour)载着迪歇纳以及巴龙委派的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布荣·德朗德尔(Boureau Desdlande)驶往暹罗并于1680年9月抵达湄南河口。如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就成功帮助了法国东印度公司在暹罗建成商站。可参考:谢子卿:《17世纪法国和暹罗邦交过程中的巴黎外方传教会》,载《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92页。,不过暹罗到中国的路线由于澳门的阻拦未有突破,待到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成立后,他们入华相对容易些,可以搭乘各国的商船,无需经过澳门直接在广州登陆即可。*顺治三年(1646)清廷施行海禁政策,但是一直未真正落实到位;平台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禁止南洋贸易,但未禁止西洋贸易。雍正五年(1727),时隔十年后清廷重新开放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西方人只可以在广州通商。这个初建的通道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法国到苏拉特;第二部分从苏拉特到暹罗;第三部分从暹罗到中国。第一部分有两条线路,其一是搭乘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绕过好望角,可在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补给后抵达苏拉特;其二是横穿中东和伊朗高原,然后在波斯湾选择港口坐船抵达苏拉特。这其中穿越奥斯曼帝国最为危险,一般情况下他们会穿上突厥人的服饰或者像罗历山一样伪装成亚美尼亚商人,跟随骆驼商队前行,不过即便如此,也很有可能会遇到强盗土匪和库尔德人武装。*Alexandre de Rhodes, Voyages et missions du Père Alexandre de Rhod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la Chine et autres royaumes de l’Orient(Julien, Paris: Lanier et Cie ,1854),PP.343-439.但是巴黎外方传教会依旧很重视这条路线尤其是返程,这是因为17世纪的法国没有能力保障远东航线的稳定性,例如盖姆(Claude Gayme)*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档案编号37:Claude Gayme (1642.1.1-1982.1.1),他于1670年2月3日动身去暹罗,根据官网档案记载,推测“东日号”的沉没时间是1682年1月1日。陪同暹罗使节出使法国所搭乘的“东日号”(Soleil-d’Orient)就在好望角附近失事,更何况法国船还时不时地会遭到荷兰人的阻击。而相对法国和土耳其重新修订《基督徒在土领事裁判权协定》(la capitulation)*这份条约旨在保护法国外交官和商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的优惠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权益。根据1604年法王亨利四世与土耳其再次修订的协议中规定:“不得有人阻碍法王的臣民以及他的友人朝圣耶路撒冷。再者,凡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Comame)暂留的基督教教士都应给予厚待和保护,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不得阻挠他们朝圣。”1673年6月5日路易十四时期重新修订协定新增如下条款:“在加拉达区(Galata)的耶稣会和嘉布遣会神父可以永久享有他们的教堂。鉴于嘉布遣会的教堂已被拆除,我们特许他们重建。所有人不得滋扰所有法国人在伊兹密尔、塞达(Seyde)、亚历山大港以及帝国境内所有通商口岸建造的教堂,也不得向其征收任何税收。”参见:Gustave Cyrille, le régime des capitulations: son histoire, ses modifications(Paris: E. Plon, Nourrit et Cie, 1896),PP.101-139.后,对于保护法籍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安全起到了更积极的作用。至于波斯,综合罗历山的旅行见闻和南志恒整理的史料来看,这段路线相对安全,这主要得益于萨菲王朝的阿巴斯看到了外交同盟关系和国际贸易的潜在利益,使得他欢迎并保护来自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美]丹尼尔著,李铁匠译:《伊朗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94-95页。
第二部分的起点苏拉特是印度半岛西岸的贸易重镇,因此传教士都将其作为旅行的中转站,莫卧儿王朝苏丹奥朗则布(Aurangzeb)批准法国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建立商站后,当地更是成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必经之路。从苏拉特横穿印度半岛抵达乌木海岸并非首选,不仅耗时过长而且环境恶劣,陪同陆方济首次奔赴暹罗的八位传教士中两个死在阿拉伯海,三个死在印度,只有布兰多和朗莫*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档案编号9:Louis Laneau(1637.5.31-1696.3.16)1661年9月从巴黎出发,1664年1月27日抵达暹罗后负责管理由德拉莫特建立的当地神学院,1673年担任暹罗宗座代牧,1688年暹罗政变,法国势力被赶出暹罗,其被囚禁。1890年获释回到神学院旧址继续传教。幸存下来,不过印度对于德拉莫特和陆方济来说另具意义,因为他们考虑过从加德满都北上翻越喜马拉雅山,然后从西藏进入中国以避开葡萄牙人对他们的阻击。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横穿印度抵达默苏利珀德姆后,再坐船去暹罗,虽然有可能会被抓住,但是“一旦抵达暹罗后找不到办法进入中国的话,至少可以重新回到印度走陆路进入中国”。*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Siam, 1622-1811: documents historiques(Paris: Charles Douniol and Retaux, 1920), Tome1, P.71.而随着法国东印度公司*1667年陆方济第一次返回法国后就试图和法国东印度公司合作,其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首相科尔伯(Colbert),表示愿意为法国远东的海外扩张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他的目的是希望法国政府也过来支持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远东的传教以保护他们的传教士免遭葡萄牙保教权的迫害和驱逐。可参见:Adrien Launay , Frédéric Mantienne, Lettres de Monseigneur Pallu: Ecrites de 1654 à 1684(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8),P.18. (257号信)陆方济于1670年致信感谢路易十四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提供津贴;(261号信)1672年1月2日在苏拉特致信路易十四;(258号信)1671年8月4日在马达加斯加致信科尔伯;(262、263、264号信)1672年1月2日再度致信科尔伯希望路易十四可以出面支持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远东可以不受葡萄牙保教权的限制,同时亦主动提出愿意为法国在印度和远东的商站提供他国情报和信息;(269号信)1672年6月4日其在万丹致信科尔伯向其汇报远东其他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情况。可参考:Adrien Launay , Frédéric Mantienne, Lettres de Monseigneur Pallu: Ecrites de 1654 à 1684(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8),PP.601-618,PP.625-627.在默苏利珀德姆(1669)、本地治里(Pondichéry)(1673)、万丹以及暹罗(1680)建立商站,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已非难事,例如从曼谷出发在万丹补给后,可以北上去本地治里或者苏拉特,也可以南下去马达加斯加或者留尼旺*当时名叫波旁岛(l’le Bourbon)。,补给后绕过好望角返回法国,反之亦然。还有一条路线是在墨吉登陆后走陆路去阿瑜陀耶,这样就可以避开荷兰人控制的马六甲海峡,1685年法暹结盟后法军驻扎墨吉控制了这条线路,不过暹罗政变后法军于1689年撤回本地因此失去了控制权。
第三部分的难点在于澳门,因为自从巴黎外方传教会进入暹罗后,葡萄牙人就对所有法国人都心存芥蒂,1665-1687年间连法籍耶稣会士都不可以经澳门入华,更不用说德拉莫特等人了。对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穿越泰国北部进入中国,第二是搭船去中国。德拉莫特选择了后者,这是因为一方面北上的路途过于艰难,另一方面纳莱王统治时期“不论在暹罗或海外的一切海上事务和商业事务都是交由中国人经理的”*[美] G.威廉·史金纳著,王云翔译:《古代的暹罗华侨》,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2年第2期,第112页。,由此就可以搭乘华侨控制的官船或者私船避开澳门进入中国*法国杂志《优雅信使》(Mercure Galant)历史悠久(1672-1965年)并享有王室特许,在17世纪主要刊登诗歌为特色的文学作品以及各地的奇闻逸事。1691年1月刊中有一篇《一封有关印度见闻的信》(lettre contant plusieurs nouvelles des Indes)披露一些关于远东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航行的相关信息。其中提到的第一点:“据大家从暹罗入华的安排以及刚刚洪若翰神父那里收到的信,大家考虑借用英国人在马德拉斯(金奈, Madras)去Emouy(可能指的是厦门)和广东的商船。”参见:Mercure galant ,1691.01,P.91.第二点:“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打仗,使得去中国的商船不得不推迟一个月出发。最后,马德拉斯的执政官还是同意我们坐上一艘名为“奥德里奇”号(Mr.Eldrich)的英国小商船。船长一开始对我们很是为难,因为有消息说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坐他们的船偷偷从广东溜进中国,于是澳门方面威胁没靠港的英国船只。不过执政官大人对我们一直很友善,他看到国王Sa Majesté(路易十四)给我们的特许状后,无谓的担心就此烟消云散了。我们于1689年3月30日登船。”参见:Mercure galant ,1691.01,PP.100-101.第三处提到:“事实上,梁弘仁主教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在马德拉斯等去中国的船有一个月,他在我们来到(据全文所述该城市叫Malaque)之后曾逗留数日。他在一由波尔多和英格兰去马德拉斯的犹太商船上,他们要去中国的Emoüy(可能指的是厦门)。和他在一起的是让·潘,他在中国曾呆了超过10年,后于1689年2月返回(罗马)。”参见:Mercure galant ,1691.01,p107-108.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Artus de Lionne,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N.78(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官方传记档案编号78);梁弘仁(Artus de Lionne)(1655.1.1-1713.2.8),1687年2月5日由教宗英诺森十世晋升为Rosalie主教,但被其婉拒;1689年入华;1693年阎当发布禁止谕令时,其认真研究过后支持其决定。祝圣后,其被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领导迅速召回巴黎和罗马参与制定传教会会规和应对中国礼仪问题,1702年10月带黄嘉略抵巴黎,并携其一同于1703年至罗马觐见教宗,在那里呆至1706年。。而陆方济及时调整了远东传教战略,他向路易十四奏报说法国东印度公司若以暹罗为远东中心,不仅可以“打通南至印尼群岛,西至印度和马达加斯加的路线;也可以有助于在越南、中国以及日本建立据点”。*Adrien Launay, Siam et les missionnaires français(A. Mame et fils, 1896),P.71.由此可见,虽然暹罗至中国内陆的航线未能成功开辟,不过由于清廷放开海禁,法国传教士可以搭乘各国船只往来东西,由此可以避开澳门,免遭葡萄牙保教权的骚扰。不过他的梦想并未实现,一方面法国东印度公司驻暹罗代表布荣·德朗德尔(Boureau Desdlande)不相信中国商人,不太愿意与之交往*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商人在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和法国人发生冲突以致于纳莱王亲自干预,参见:Pierre Margry, Relation et mémoires inéd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France dans les pays d’outre-mer, tirés des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Paris: Challamel, 1867),PP.162-166.;另一方面康熙解除海禁后3年就发生了暹罗政变,除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外的所有法国势力均被驱逐出去,因此法国开辟暹罗至中国的航线就此失败。*1688年5月暹罗的象队统帅帕·碧罗阇(Pretatcha)在纳莱王病危之际发动政变称王,华尔康被杀,法军被逐被迫退回本地治里(Pondichéry),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商站被关闭,所有未能离开的法国人都被囚禁,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当地的神学院也被查封,法国势力几乎都被清除干净,直至法军于1691年最终放弃重回暹罗后碧罗阇才将神学院归还给朗莫主教。有关法国人在1688年暹罗政变时候的情况,可参考的中文研究有:[苏联]别尔津著,陈远峰译:《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殖民者在暹罗的活动》,载《东南亚资料研究》1963年第2期;吕颖:《17世纪末法国与暹罗外交的斡旋者——塔查尔》,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谢子卿:《17世纪法国和暹罗邦交过程中的巴黎外方传教会》,载《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四、17世纪末期法国耶稣会士的入华通道
这一时期法国耶稣会士的入华路径除了经葡萄牙保教权允许由澳门入华外*他们有罗斐理神父(Philippe-Félix Carossi 1687年入华)、樊西元神父(Jean-Joseph-Simon Bayard 1694年入华)、冯秉正神父(Moyriac de Mailla 1703入华)等人。,大致分两种:第一种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路线;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的新开拓,指的是法国船“安菲特利特号”(Amphitrite)搭载两批法籍耶稣会士于1698和1701年直接登陆广州。
据费赖之的《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可查,当时有四位法国耶稣会士苏安当神父(Antoine Chomel,1669-1702)、赫苍璧神父(J.P.Hervieu,1671.1.14-1746.8.26)、隆盛神父(Guillaume Melon,1663-1706.6.7)以及聂若翰神父(Fr.-Jean No⊇las,1669.6.17-1724)穿越中东抵达苏拉特后搭船于1701年抵达广州,他们走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走过的陆海结合路线。
1687年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神父(Jean de Fontaney,1643.2.17-1710.1.16)、白晋神父(Joachim Bouvet,1656.7.18-1730.6.28)、李明神父(Louis Le Comte,1655.10.10-1728.4.18)、张诚神父(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6.11-1707.3.22)以及刘应神父(Claude de Visdelou,1656.8.12-1737.11.11)走海路入华。他们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来中国进行科学考察和传教,由于他们是路易十四委派的,所以对于里斯本而言他们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并无区别,都是葡萄牙保教权的敌人,因此他们很难经澳门入华。正当他们为入华途经担心时,巴黎外方传教会陪同的暹罗使团正在凡尔赛与政府洽谈派遣法国特使回访暹罗的事宜,于是路易十四就决定利用载法国大使的船送他们一程。*[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7页。有关法国耶稣会士东西交通的经过可参考本文开篇注释[1]所举书目。由狄考(Henri Cordier)校对的《张诚神父从北京发出的五封信》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网上免费获取,其中前三封都关于其等的航海以及在暹罗的经历,可参见:Jean-François Gerbillon, Cinq lettres inédites du P.Gerbillon, S.J., missionnaire français à Pe-King: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06.1685年3月3日他们就跟随着法国使团登上“飞鸟号”(L’oyseau)从布雷斯特启程,5月30日绕过好望角,6月19日抵达马达加斯加,他们没有北上而是一直西行停靠巴达维亚(雅加达),9月23日抵达湄南河口。1686年7月2日他们坐船启程去澳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有一篇《华人记载开辟暹罗至中国陆路交通的摘要》(Route par terre depuis Siam jusqu’à la Chine tirée des Mémoires de quelques Chinois qui en ont fait le chemin)说明在暹罗的耶稣会士也曾经研究过经老挝进入中国的方式,参见:le P.J.-B.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Pairs: P.-G. Le Mercier ,1735), Tome 1, PP.105-108.,不过由于遇到船体漏水又遇到台风他们不得不折返并于9月回到暹罗,由于缺少去中国的船只,他们不得不等到1687年6月19日搭乘“暹罗附粤商人王华士的中国帆船”*吴旻、韩琦校注:《熙朝崇正集 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342页。于7月23日抵达宁波。
这批法国耶稣会士很受康熙信任,皇帝决定委派白晋作为特使回法国招募耶稣会士来华筹建中国科学院,同时试图与路易十四建立联系。*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26页。由于他是朝廷的特使,澳门当局不敢怠慢,他从广州去澳门于1694年1月10日搭乘英国船启程,途经苏拉特后于1697年3月才抵达法国的布雷斯特。白晋觐见路易十四后请求派王室官船入华,不过法国不愿意以番邦朝贡的形式委曲求全*耿昇:《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第5-7页。,因此搭载白晋第二次赴华的“安菲特利特号”同他先前搭乘的“飞鸟号”不同,“安菲特利特号”不是官船而是法国东印度公司于1697年在白晋游说下授权给商人儒尔丹(Jean Jourdan)去中国从事贸易的商船。由此“安菲特利特号”承载着两项使命,第一是试图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第二是运送白晋、瞿敬臣(Charles Dolzé,1663-1701.7.24)、雷孝思(Jean-Baptist Régis,1663.2.2-1738.11.24)、利圣学(de Broissia)、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épare,1666.7.17-1735)、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701.7.31-1741.9.29)、颜理伯(Philibert Geneix,1665-1699.9.30)、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bille,1656-?)、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4.7-1735.12.9)和卜纳爵(Ignace-Gabriel Baborier,1663.9.4-1727.6.14)共计10名法籍耶稣会士入华。他们于1698年3月6日从拉罗歇尔港(la Rochelle)出发,6月10日绕过好望角,8月18日抵达班达亚齐*位于苏门答腊岛最西北端,是印尼穆斯林麦加朝圣的枢纽。,转入马六甲海峡后停靠马六甲,然后北上于10月5日抵达上川岛,在沙勿略墓地逗留一天后于24日抵达澳门,11月6日抵达广州。“安菲特利特号”是第一艘登陆中国的法国船。
白晋物色的另一批法籍耶稣会士搭乘德奥热(M.des Augers)指挥的舰队于1698年1月出发,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3.3.12-1739或1740)和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1664-1703.11.2)乘坐“拉邦号”(le Bon)、卜纳爵乘坐“拉泽兰号”(la Zelande)、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2-1741.7.2)和孟正气乘坐“卡斯特里肯号”(Castricon)。*[美]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第82页。他们和“安菲特利特号”在赤道和好望角两度相遇,在好望角时白晋安排卜纳爵和孟正气与之同船,剩下三人则北上抵达孟加拉湾的金德讷格尔(Chandernagor)*1688年成为法国殖民地,是孟加拉湾的贸易中心。,并遇到宋若翰(Jean-François Pelisson,1657-1736?)和罗德先(Bernard Rhodes,1645-1715.11.10),他们五人于12月乘坐“乔安娜号”(Joanne)去乌木海岸的金奈(Madras)*古称“马德拉斯”是当时英国属地,距离法属本地治里很近。,1699年1月29日又从当地搭乘英国船“乔安娜号”于4月10日抵达雅加达,5月20日傅圣泽、殷弘绪和罗德先三人转乘另一艘英国船“萨拉加利号”(Saragalley),23日抵达巨港(Palembang)*苏门答腊岛东南方面的荷兰商站,中国古称“巴林冯”或“旧港”。之后驶向马六甲,6月24日启程于7月24日抵达厦门,而其余两位也于次日搭乘“乔安娜”号搭乘顺利抵达。
“安菲特利特号”在广州逗留一年多后于1700年1月26日启程回国,8月3日回到法国圣路易港。1701年3月7日又搭载第二批法籍耶稣会士共八人再赴广州,他们是由1684年入华的洪若翰带领从圣路易港出发,绕过好望角直奔爪哇岛,然后绕过巽他海峡和邦加海峡(Banka)北上,途经西沙群岛,7月1日登上上川岛瞻仰沙勿略之墓。清朝官员坐船前来接走了卜文气(Louis Porquet,1671.4.7-1752.7.14)、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1670.3.1-1717.9.14 )、戈维里(Pierre de Goville,1668-1758.1.23)、顾铎泽(Eienne-Joseph le Couteulx,1667或1669.7.31-1731.8.8)、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11.30)、方全纪(Jérme Franchi,1667-1718.2.13)*他是意大利人,抵达中国后原属耶稣会法国传教区,后划归葡萄牙副省区。,于9月9日抵达广州。汤尚贤(P.-V. Du Tartre,1669.1.22-1724.2.25)和龚当信(Cyr Contancin,1670.5.25-1733.11.21)留在“安菲特利特号”上任执勤司铎职,随后于11月25日抵达广州*费赖之著,梅乘骐、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711页。,而这艘法国船在广州停留了四个月后于1703年8月17日返回法国布雷斯特港。
五、试评法国传教士东西交通路线的影响
(一)对远东传教格局的影响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耶稣会积极帮助法国开辟远东交通路线最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他们自己,这不仅使得17世纪下半叶成为法国传教士进入远东的峰值期,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远东传教史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1679年,先是迪歇纳*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官方档案编号65:Pierre Joseph Duchesne(1646.11.829-1684.6.17):1678年12月22日出发去暹罗。成功说服法国苏拉特商站经理巴龙(Baron)委派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布荣·德朗德尔在暹罗建立商站。不久后瓦歇*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官方档案编号31:Bénigne Vachet(1641.10.31-1720.1.2)暹罗政变后去波斯传教后回国。于1684年全程陪同暹罗使团出访法国,顺利促成两国建交,从而打通了法国通向暹罗的道路,其结果是暹罗成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势力范围,一举打破了葡萄牙保教权对远东教务的垄断。不仅如此,他们从暹罗进入越南后,在当地的势力也已经完全可以达到和耶稣会分庭抗礼的程度,例如布尔热于1672-1677年间在东京为34605人受洗,戴迪耶光1670年一年就在东京当地为1万余人受洗。1684年陆方济携阎当*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官方档案编号77:Charles Maigrot(1652.1.1-1730.2.28)他于1687年被任命为福建宗座代牧,之后发布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的《阎当训令》,是中国礼仪之争中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也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陆方济去世后在中国的实际负责人,是耶稣会传教政策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等人抵达中国后,也对耶稣会在华传教的传统地位发起挑战。
“飞鸟号”(1687)和“安菲特利特号”(1698、1701)运送入华的三批法国耶稣会士中涌现出许多对中西交流功勋卓著的知名传教士,如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马若瑟、巴明多、傅圣泽以及殷弘绪等人,他们在当时东西方的影响力和学术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持有类似见解的有耿昇《从基督宗教的第3次入华高潮到西方早期中国观的形成》的代序,[法]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7-10页。;更关键的是他们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一样绕过葡萄牙保教权,依靠法国人自己开辟的路线来华,此举势必威胁葡萄牙在远东的利益,由此直接导致了耶稣会内部葡萄牙籍和法籍耶稣会士的分裂。
因此,法国传教士开辟的新路线对于远东传教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耶稣会的优势地位因内讧而被削弱,从而转变为一种多层次错综复杂的混乱关系。对于巴黎外方传教会来说,一方面它代表罗马教廷进入远东最终目标是要从葡萄牙保教权手中拿回传教事业的主导权,此举势必和法国耶稣会士忠于本会的意愿产生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和法国耶稣会士携手合作帮助法国在远东扩张,对此他们至始至终并未能处理得当。*传信部于1678年10月10日重申了1673年12月23日发布的赦令Decet romanum 和Illius qui Caritas以及1674年6月8日的赦令Christianae religionis,要求所有远东传教士,无论任何修会和团体皆须向管辖教区内宗座代牧宣誓效忠。问题是派赴远东的宗座代牧都是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担任,这就等于是说所有远东传教修会或者团体的传教士进入代牧区都必须听命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领导,这自然会引起其他修会、尤其是耶稣会的反弹,一份1680年1月29日传信部秘书的报告显示有四位耶稣会神父拒绝宣誓,结果陆方济致信耶稣会总会长要求其召回这四位耶稣会传教士;就在同一天,一封以教宗英诺森十一世名义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则要求他立刻召回这四位神父,同时还要求今后派赴远东宗座代牧辖区内的耶稣会士要事先效忠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时任的总会长奥利瓦(Oliva)宣布召回四位耶稣会士,同时他也提到不必强迫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向他们宣誓,因为宗座代牧的权限仅限于越南和暹罗两地,他还警告说若中国和日本的宣誓问题处理不当,里斯本可能会停止资助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经费。有关宣誓问题的内容可参考:Notice bibliographique de François Pallu ,Archives des missionnaires des MEP/EDA,N.12(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官方传记档案编号12)。[法]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3页。Adrien Launay, Documents histoires relatifs à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1905, PP.89-94.
对于法国耶稣会来说,一方面他们作为耶稣会士需要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竞争以尽力维持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同为法国人却又应该携手共助法国的远东扩张一臂之力,这必然使得他们身处于修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的夹缝中左右为难;对于忠于葡萄牙保教权的耶稣会士来说,他们要面对来自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耶稣会的双重压力。因此,三方混战是造成中国礼仪之争在康熙朝后期严重激化的重要因素,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法国到中国的海路最终打通了*“1699年至1833年法国商船入粤共计141艘。”参见王巨新:《清朝前期涉外法律研究——以广东地区来华外国人管理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43-452页。,但是由于中国礼仪之争引起的百年禁教使得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人为地被暂停下来。
(二)对法国远东扩张的影响
法国传教士积极参与法国的远东海外扩张,主动探索东西交通的初衷是希望一个强大的法国可以为传教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但是随着新路线的建立法国的野心也随之膨胀,17世纪后半叶的法暹交往就是明证。荷兰控制马六甲海峡后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势力已达巅峰,纳莱王从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口中得知法国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后寄希望于以夷治夷提防荷兰对暹罗的馋涎*Adrien Launay, Siam et les missionnaires français(A. Mame et fils, 1896),PP.69-79.,巴黎外方传教会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于是引领两国建交,并且事实上在东南亚形成了法国(暹罗)和荷兰(印尼)双雄并立的局面,这对于在远东是后起之秀的法国来说可谓占尽便宜。但是,法国人并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法国传教士利用东方国家的专制王权为传教和母国利益牟利,但是权力反过来也会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法国耶稣会士塔查尔(Guy Tachard)*他原本应跟随洪若瀚于1687年入华,但是被那莱王挽留下来,因为他希望塔查尔神父可以回法国招募耶稣会士来暹罗,参见吕颖:《17世纪末法国与暹罗外交的斡旋者——塔查尔》,载《南洋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被暹罗权臣华尔康(Constance Phaulkon)*他是希腊人,原本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去暹罗开设商站,后来成为那莱王的左右手,他知道暹罗一直忧心荷兰人会入侵,所以一直向国王鼓吹和法国结盟,他撇开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特使,瞒着那莱王和暹罗朝廷,诱使塔查尔神父担任两国结盟的秘密联络人,目的只是巩固他在暹罗宫廷中岌岌可危的地位。所蒙蔽,为路易十四带去不实情报,致使法国方面做出派兵进驻暹罗的错误决定,最终引起1688年的暹罗政变使得法国人的势力被基本清除出暹罗。由此,法国失去了通往中国的中转站,“安菲特利特号”以及18世纪入华贸易的法国商船在东南亚只能停靠荷兰人的商站补给,整个东南亚都拱手让与了荷兰*暹罗政变后只有西方人中的荷兰人被允许留下经商,1703年推翻华尔康的碧罗阇去世后他的儿子又在巴黎外方传教会士西塞(Louis Champion de Cicé,1648.9.24-1727.4.1)的斡旋下重新和法国建立联系,这位新国王同意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当地在此设立商站并且给予他们同荷兰人一样的贸易地位,而这15年间西方国家中只有荷兰人被允许在暹罗进行贸易活动。西塞出发传教之日为1682年4月6日,目的地不详,只知道他曾经赴中国和暹罗传教,1700年1月19日被封为Sabule主教,管辖地为暹罗,其入华和离华之日皆不详。参见Adrien Launay, Siam et les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A. Mame et fils, 1896.,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帝国重返印度支那和中国为止。
六、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外方传教会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相互配合在17世纪中后叶开辟出法国到印度和暹罗的远东交通网络,法国耶稣会在此基础上于17世纪末更进一步打通了法国到中国的航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法国传教士对于法国远东扩张事业的起步和发展贡献良多,传教和贸易并举的时代特征在法国传教士探索入华通道的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不过他们过度参与政治以及相互之间争斗竞逐也同时破坏甚至毁灭了他们自己努力开创的传教事业。
作者谢子卿: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Abstract:Alexandre de Rhode, the first French Jesuit to China, on his return met up with Francois Pallu. They established the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in Paris, which tried to explore a route from Middle East to the Indian Sea,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lped the French to expand its power to Siam so as to open up a new route to China for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Later with the help of the French Jesuit, French merchant boats arrived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finally opened the sea route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The French missionarie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France. This was not just out of their strong sense of patriotism, but also because they wanted their country to protect them when they preach overseas.
Keywords:The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in Paris; Society of Jesus; France; Si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