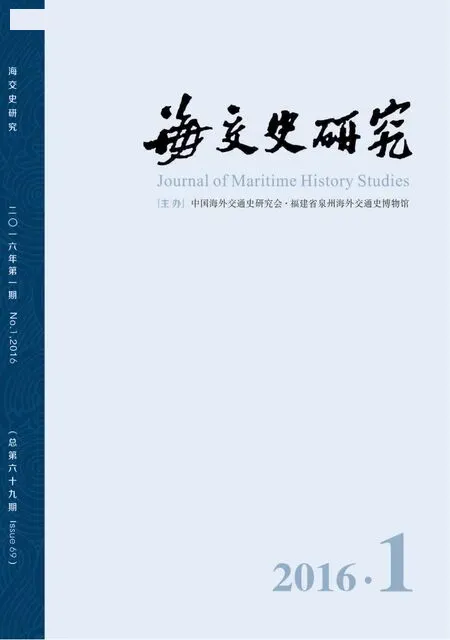泉州印度教石刻研究回顾与思考*
王丽明
泉州印度教石刻研究回顾与思考*
王丽明
〔摘要〕泉州印度教石刻自印度学者库玛拉耍弥率先向世界介绍以来,吸引了海内外许多学者的兴趣和关注,随着石刻不断被发现,相关研究文章也陆续问世。近百年来的研究, 理清了一些历史问题,尤其在石刻的图案解读、所属历史时期、文化艺术渊源、制作背景及工匠等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笔者将近百年来的这些研究文章进行回顾总结梳理,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泉州印度教印度教石刻印度教寺
泉州历史上多种宗教并存,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等都曾有流传。多元宗教构成泉州区域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为泉州留下独特的宗教雕刻艺术,成为史学界、艺术界、宗教界专家极为感兴趣的内容,尤其是印度教石刻。泉州历史上曾建 有极富特色的印度教寺和祭坛,目前已发现精美印度教石刻300多方,分别收藏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泉州开元寺、天后宫,另有一些由泉州地方史学家吴幼雄教授收藏,以及散落民间或由地方收藏家收藏。
这些印度教石刻风韵独特,吸引了许多学者,相关论文陆续问世,数量虽不多,涉及问题却不少,逐步廓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不必讳言,泉州印度教石刻的研究成果其实远不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石刻丰厚,尽管文章林林总总,但不少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有些关键问题,仍处于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究其原因有二,首先基础材料缺乏。泉州印度教寺应为石砌式,一座教寺至少有上千方石构件筑成,目前所发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很难重现当时的景象。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为我们解读和建构那段历史带来许多困难;其次我们十分缺乏兼具熟悉理解印度教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学者,只有对印度教文化与本土文化充分地理解,才能更清晰和深入地分析二者接触的诸多问题。但目前,泉州与印度之间学术交流不多,本土学者鲜有机会往印度考察。这使得古代印度教在泉州更显得扑朔迷离。这些石刻除了以自身的存在证明着印度教与泉州的交集外,它从哪里来?谁带来?怎样生存?如何发展?与其他宗教,与本土文化发生了什么?汲取了什么?迷惑重重。这提醒我们,关于泉州印度教的研究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继续摸索。然而近几年,泉州印度教石刻的研究似乎遭遇瓶颈,学术界虽然对中世纪泉州多元文化汇集,文化接触、碰撞、合作、冲突研究较多,但印度教始终有隔靴搔痒之感,流于表面,谈之不透。一些需要关怀却又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始终处于盲区。没有理清这些问题,很难说关于中世纪的泉州宗教研究是完整的。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取得什么突破,而是希望提供脉络与索引,抛砖引玉,使更多学者、机构持续关注,能有更多中外特别是中印合作的机会,以促印度教石刻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我们解开更多历史谜团。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概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Zaiton”在哪里的讨论让泉州重新赢得世界注目。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陈万里、张星烺,哲学系教授德国人艾克(Gustave. Ecke)到泉州访古考察。考察返回后,陈万里撰写《泉州第一次游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刊出),张星烺撰写《泉州访古记》(《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发表)。艾克就此与泉州结下不解之缘,1930年,他和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再次来到泉州,从此开启泉州印度教石刻的研究。
艾克博士将在开元寺拍摄所得照片及绘图寄给印度学者库玛拉耍弥(Ananda K.Coomaraswamy)。1933年,库玛拉耍弥在德国《东亚美术》(一二期合刊本)发表《泉州印度式雕刻》,成为第一个正式发表泉州印度教雕刻照片和相关论文的学者,1934年,由刘致平翻译并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印]库玛拉耍弥(Ananda K.Coomaraswamy)著,刘致平译:《泉州印度式雕刻》,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第2期。库玛拉耍弥在文中首次向世界介绍泉州开元寺内的两根印度教石柱及大雄宝殿月台下的狮身人面石刻,解读石柱上的图案故事,并考证泉州白耇庙敬字亭的两方古代印度教石刻的故事。1935年,时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的艾克,与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的戴密微合著出版英文著作TheTwinPagodasofZayton(《刺桐双塔》)*[德]艾克(Gustav Ecke)、[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该书列为“哈佛-燕京研究院专著系列”第二卷。。这是外国学者亲自来到泉州,对泉州历史文物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刺桐双塔》没有中文译本,仅见吴文良先生节译部分内容,以《泉州镇国塔佛传图石刻浮雕》刊于《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德]艾克(Gustav Ecke)、[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著,吴文良译:《泉州镇国塔佛传图石刻浮雕》,载《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1983年。艾克在此书中将印度教石刻“牛、磨盘、林伽与尊者”作为附录图版刊出,并记述“此图似乎是牛呈献乳汁给林伽;牛和林伽是表示牛为林伽解忧。现在石刻是在泉州开元寺东北方的小神庙墙上”。*吴幼雄:《泉州锡兰王裔和遗址发现记》,《泉州宗教石刻》附录,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21页。此论述当是受库玛拉耍弥的影响。1950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历史系教授林惠祥率队到泉州考古,随后在厦门大学举办“厦大历史系1950年泉州考古图片展”,在“大象与林伽”“牛与林伽”的图片注释中,他写道“泉州城内古印度人的生殖器崇拜石刻”*吴幼雄:《泉州锡兰王裔和遗址发现记》,第521页。。他撰写的考古报告称:“笔者于一九四八年到泉州考古时,瞥见这二件东西,大为惊异,知道便是印度的生殖器崇拜物。”*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载《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
艾克、戴密微、库玛拉耍弥和林惠祥,无疑都是泉州印度教石刻研究的开山鼻祖,尽管当时他们在泉州能见到的印度教石刻,只有一小部分,很难勾勒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却因此掀开了面纱,其意义当难以估量。
在张星烺等人访古泉州时,泉州宗教石刻研究奠基人吴文良正就读于厦门大学。1927年,吴文良先生回泉州任教,业余搜集、整理和研究古代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等中亚、南亚各国人和欧洲人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抗战初期,他收集或购买了大量宗教石刻,抗战胜利后又抢救了一批,其中印度教石刻近百方。1949年,他把这些石刻辑录为《泉州古代石刻集》,铅印问世,但只印数百份。1954年,吴先生将154方古代泉州外来宗教石刻捐给国家。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全书8万多字,采录宋元时期外国人遗留在泉州的伊斯兰教、古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明教)、佛教等宗教建筑遗物和墓葬碑刻图片200余幅,其中印度教石刻43幅。《泉州宗教石刻》详细介绍了印度教石刻29方(含建筑构件),石柱3根,大雄宝殿月台下狮身人面石刻及2个门框石,其中开元寺大雄宝殿后的两根石柱,及白耇庙两方石刻的解读基本遵照库玛拉耍弥的观点,并率先提出泉州元代曾建有婆罗门寺的见解。*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1958年,吴文良调任筹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以下简称“海交馆”),随后分别在海交馆油印本刊登《漫谈泉州婆罗门教寺》、《从泉州婆罗门石刻的发现谈到中印关系》,指出“宋元时代,泉州人或侨寓泉州的印度人民,筑坛以奉祀婆罗门神的,就不止一所。”*吴文良:《漫谈泉州婆罗门教寺》、《从泉州婆罗门石刻的发现谈到中印关系》,载《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1983年。1964年,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家张驭寰在《建筑理论与历史》(第二集)发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的几个问题》。
此后,我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泉州印度教石刻的研究基本停滞,仅见《晚蚕集》中收录了泉州本土学者王洪涛写于1974年的《开元寺“人面狮身”石刻》*王洪涛著,王四达编:《晚蚕集》,华星出版社,1993年。一文。王洪涛否定人面狮身的埃及来源说和希腊来源说,认为它表现的应该是毗湿奴之化身纳拉辛哈。1975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谈到,库玛拉耍弥描述的印度式石柱可能雕刻于唐代,但又因具有锡兰风格,或者也可能与锡兰王子有关*[英]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475页。。1978年,印度学者萨布拉玛尼恩(T.N.Subrahmaniam)以库玛拉耍弥发表的照片为依据,在SouthIndianStudies用英文发表A Tamil Colony in Me-dieavel China(《中古时代中国的泰米尔人聚居地》),文中翻译了泉州发现的泰米尔文碑,这篇文章没有中译版。*[印]萨布拉玛尼恩(T.N.Subzamahiam):A Tamil Colony in Me-dieavel China,South Indian Studies,Madras,1978年。
二、20世纪80年代后的研究简况
1980年代后,石刻研究向纵深发展,涉及范围逐步广泛。1978年12月,我国第一份海外交通史专题研究的期刊《海交史研究》创刊出版。1980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蒋颖贤教授在《海交史研究》发表《印度婆罗门及其传入泉州》,发问“古印度的婆罗门教传入泉州,其始于何时?其寺庙建于何处?婆罗门教主神有什么遗迹?”其后,庄为玑、杨钦章、吴幼雄等一批本土学者掀起一轮泉州印度教石刻的研究高潮,试图解答这些谜题。
1982年,《世界宗教研究》*庄为玑:《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杨钦章:《泉州印度雕刻渊源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刊载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的《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和海交馆研究人员杨钦章的《泉州印度雕刻渊源考》。庄为玑将泉州现存印度教史迹归为三处,即石笋、泉州幼儿师范学校祭坛与番佛寺,它们分布在泉州城西南与西北,其艺术源自印度本土。杨钦章则追溯了印度教传入泉州的端倪,认为这些石刻是元代建筑番佛寺的遗物,这个教寺是南印度林伽派教寺的翻版,由爪哇海道传入。同年《泉州文史》*庄为玑:《泉州印度教寺址的调查与研究》,吴捷秋:《泉州婆罗门教三石刻见知录》,载《泉州文史》1982年6.7合刊本。的“宗教史研究”开辟专栏专题讨论古代泉州印度教,除收录杨钦章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上的文章外,又刊载庄为玑教授的《泉州印度教寺址的调查与研究》,重申泉州印度教的三处遗迹,认为印度教传入泉州的历史久远,甚至可以推测到唐代以前。泉州地方史学者、书法家吴捷秋在该杂志的同一期上发表《泉州婆罗门教三石刻见知录》,校正了吴文良在《泉州宗教石刻》中关于图111、112、113来源的说法。此后,杨钦章连续撰文,于1984年在《南亚研究》*杨钦章:《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1991年在《泉州鲤城文史资料》*杨钦章:《印度教在泉州》,载《泉州鲤城文史资料》第6.7合辑,1991年。发表《印度教在泉州》,同年撰写的《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文收录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旗帜鲜明地反复强调元代泉州印度教寺源自南印度的湿婆派神庙。
随着研究的深入,泉州印度教石刻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不断显现,除本土学者外,不少国内外知名学者也见仁见智,各述其是。198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美术史论》*陈履生:《元代泉州的印度教雕刻》,载《美术史论》1986年第4期。发表《元代泉州的印度教雕刻》。作者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考察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1988年,日本学者辛岛升发表《13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元史·马巴尔等国〉》*[日]辛岛升:《13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元史·马八儿等国传>》,汲古书院,昭和63年。,对泰米尔文石碑进行翻译。1995年韩振华的《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馆研究人员丁毓玲翻译的英国学者约翰·盖依(John Guy)文章《纳格伯蒂纳姆和泉州已消失的寺庙》在《海交史研究》*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载《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John Guy著,丁毓玲译:《纳格伯蒂纳姆和泉州已消失的寺庙》,载《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韩振华在文中详解了几方印度教石刻,提出泉州印度教非传自南洋,而是直接传自印度本土。约翰·盖依以纳格伯蒂纳姆发现的中国宝塔以及泉州发现的印度教寺遗物,证明13世纪后半叶是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加强期。他还于2001年出版的TheEmporiumoftheWorld,MaritimeQuanzhou,1000-1400(《世界货舱——公元1000-1400的海上泉州》)中,发表Tamil Merchant Guids and the Quanzhou Trade(《泰米尔商人行会与泉州贸易》)*[德]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Maritime Quanzhou,1000-1400,2001年,收录1997年在荷兰莱顿举办的“宋元时期泉州地区的海上贸易和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文章。,通过对泰米尔文碑铭、印度教寺庙遗存的考察,他认为泰米尔商人与泉州社会的关系是双向的,从而强调印度教与泉州地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2011年,在宁波召开“跨越海洋:‘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严耀中在《海上丝绸之路和婆罗门教之来华》一文中,认为“婆罗门教在泉州的存在,前后至少断断续续竟长达两千年之久”*林立群主编:《跨越海洋:“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国际学术论坛文选(2011,中国,宁波)》,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9-275页。,该结论与蒋颖贤的观点正契合。
1990年代末,明代锡兰王子“世家”文物被发现,引发学术界对白耇庙属性界定的讨论。1998年泉州市温陵白耇庙理事会汇集十几年来的相关研究文章编印《温陵白耇庙》*谢长寿主编:《温陵白耇庙》,1998年。,1999年林悟殊发表《泉州白耇庙属性拟证》*林悟殊:《泉州白耇庙属性拟证》,载《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2000年海交馆研究员李玉昆带领海交馆学术团队,主持国家文物局重点研究课题《泉州锡兰王裔文物研究》,其中对白耇庙是否为锡兰王子所建印度教寺作了细致的考察。*李玉昆、陈丽华、叶恩典、曾丽民课题组:《泉州锡兰王裔文物研究结题报告》,2004年,资料保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未正式出版。
21世纪后,四部与泉州印度教石刻研究相关的巨著,将该项研究推向高潮。
2005年,泉州师院吴幼雄教授增订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科学出版社,2005年。,将几十年来泉州发现的印度教石刻进行汇总解说增补至90类,绝大多数现已发现的印度教石刻都刊录于此书,书中附录《婆罗门教的传入和泉州的印度教寺》、《泉州锡兰王裔和遗址发现记》两篇文章。附录文章简略梳理婆罗门教与我国的交集,例举存有婆罗门教遗址的地区,分析泉州元代及明代的印度教遗存,并在《泉州锡兰王裔和遗址发现记》一文中回顾泉州锡兰王裔史迹发现的历程。锡兰王裔、白耇庙、印度教三者关系颇为纠结,从已有的学术成果看,目前分歧还较大,主张白耇庙为锡兰王裔所建印度教庙,与主张白耇庙为泉州民间庙宇的各执一词。
2007年,美籍华人余得恩实地访问印度和泉州,在查阅大量印度教经典,并访问大批印度学者后撰写英文著作《泉州印度教石刻》*余得恩著,王丽明译:《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的比较研究》,载《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该著述的英文并未正式出版,作者将文稿直接投至《海交史研究》,节选其中一部分翻译成中文发表。,系统回顾泉州与印度交往的历史,更使大部分的印度教石刻图案背景故事得以解读,《海交史研究》节选其中的一部分,由海交馆研究人员王丽明翻译,2007年发表《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的比较研究》,是目前将泉州所发现的印度教石刻解读得最为详细和完整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俏梅(Risha Lee)分别考察了印度和泉州,2012年完成博士论文ConstructingCommunity:TamilMerchantTemplesinIndiaandChina,850-1281,她在第四章A Shiva Temple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中以泉州的湿婆庙(作者断定该番佛寺为湿婆庙)为重点分析例证。文中除介绍泉州在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以及泉州发现的印度教石刻,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分析这些石刻构件,重构泉州这座古番佛寺的多层级建筑形态,并用语言描述与绘图相结合的形式勾画了这座已毁的寺院。李俏梅博士的这一著作首次为我们构建了番佛寺的建筑形式,视角独特,显然对此前研究有明显突破。可惜此文尚未公开发表,也没有中文版。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邱永辉研究员出版著作《印度教概论》*邱永辉:《印度教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书中开篇第一幅图便是泉州的毗湿奴立像,在“印度教与中国”一节中她阐明几个观点:印度教的主要派别毗湿奴和湿婆派,均在泉州存在过;元明两代,泉州的印度教不仅有不同的派别,印度教寺庙、祭坛也有多处,有较大数量的印度教徒曾在泉州长期寓居;印度教在泉州与民间信仰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如石笋与当地的风水观念,同时还影响了其他宗教的发展。*邱永辉:《印度教概论》,第364页。
除此之外,也有许多美术领域的博士、硕士关注泉州印度教石刻这一选题,如湖南师范大学李江平《试析印度雕塑对元代中国雕塑艺术的影响》,暨南大学黎日晃《元代雕塑艺术研究》,苏州大学陈清《论泉州传统建筑装饰的多元化特征》等。
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无论石刻本身还是石刻背后的“印度教与泉州”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几个重要问题得到较为充分的阐述。
三、石刻图案解读
印度教石刻图案繁复神秘,充满异域风情,它以神话为母题,反映神、神话内容或某一印度教教义,表达的故事令人好奇,因此解读石刻所反映的内容,是石刻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20世纪50年代,吴文良指出,“这些石刻大多雕工精细,手法特殊,从雕刻的故事内容看来,它们都与三千年前印度的文学作品《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两部史诗有关。”*吴文良:《从泉州婆罗门石刻的发现谈到中印关系》。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同。1980年代以来,吴幼雄、余得恩、杨钦章、韩振华等陆续对石刻图像作了解释,并一致认为泉州这些石刻和印度本土的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其中,尤以亲自往印度和泉州实地考察的美籍华人余得恩的解读最为全面。
已发现的泉州印度教石刻主要有4类:石龛、石柱、立式神像和柱头、柱础、底座、石垛、雀替等建筑基础构件。目前,解读观点比较一致的有:中西合璧的开元寺印度教石柱图案,是各位学者分析最为透彻,看法最为一致的。它的图像大多取自毗湿奴各种化身的故事,余得恩还逐个与南印度同题材雕刻做了细致比较,得出二者极为相似的结论;英气飒爽的立像被认定为毗湿奴这点没有任何异议;磨盘状雕刻都被认作湿婆的重要化身林伽;“御赐佛像”石刻门楣“是一方属于婆罗门教寺的石匾额的上部”*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之所以被称“佛像”是因为“在元代的泉州,印度教的神像也被称为佛像”*杨钦章:《印度教在泉州》。;“牛和林伽”、“大象和林伽”一般延续库玛拉耍弥的解释,认为分别表现牛与大象对林伽的崇拜,仅韩振华认为分别是湿婆的牡牛和湿婆之子象头神犍尼萨。
争议比较大的有:
妙趣横生的开元寺月台“人面兽身”像。学者们普遍认为兽身为狮身,但并非印度原有元素,对其文化渊源的认定分歧较大。余得恩的观点是它刻划了南印度人头牛身的女神(Kamadenu),但创作时将躯体装饰成狮子,这与南印度朱罗时期有些神庙一样;韩振华推断此为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图像本是表现拉克希米女首象身的侍女,但象身用狮身代替,且狮身的形式是中国绘画上的常见样式;吴文良、吴幼雄、庄为玑推测源自埃及的人面狮身石像,这种造型由埃及传入希腊再至印度,然后由印度传入泉州;王洪涛则断定是毗湿奴化身纳拉辛哈。
造型类似的五个龛状石刻:1、跌坐莲花上的女神。吴文良、吴幼雄和余得恩断其为毗湿奴之妻拉克希米;杨钦章、韩振华、刘迎胜*刘迎胜在《海路与陆路》一书的《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中对此有简单的观点阐明。认为是湿婆,杨钦章解释其坐在莲花上是“不断创造生命的爱之本能象莲花一样开放”*杨钦章:《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2、兴济亭神像。余得恩认定为湿婆之妻;吴幼雄、杨钦章、约翰·盖依判断为湿婆。3、两方含有“神与林伽”图像的龛状石。吴文良、吴幼雄、杨钦章认为神像是湿婆;余得恩以为神像身份难以确定;韩振华则断定为毗湿奴。4、另外还有一方被称为“湿婆舞王”像的龛状石。余得恩、庄为玑、杨钦章认同舞王湿婆的观点;吴幼雄看法不同,认为是湿婆之妻杜尔迦,刻划其战胜巨魔的故事;韩振华也解读为湿婆,但认为非舞王之像,因为脚踩的不是巨魔而是湿婆的坐兽。
两个门框石上的图像也有分歧。对于“手执莲花的猴子”图像。吴文良、吴幼雄认为是哈奴曼;余得恩认为只是一只普通的猴子。另一“双手合十者”的图像,吴文良与吴幼雄的观点都是武士;余得恩却视其为膜拜者。邱永辉则认为两副门框石,描述的正是《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和英雄哈奴曼。
石柱上的角力图据余得恩介绍是南印度神庙的标志。吴文良、吴幼雄、余得恩判断它与克利希那(毗湿奴化身之一)的传说有关,但韩振华倾向于林伽崇拜,表达陵诃越(即移动的林伽)。杨钦章虽然也认为图中表现的是克利希那与金翅鸟在角力,或是黑天之兄大力罗摩(毗湿奴化身之一)和穆希帝迦,但因有明显的林伽存在,因此也认同与林伽崇拜有关。
仍有不少石刻缺乏有效判断,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两神像和高立的柱子,吴幼雄推测与湿婆崇拜有关,余得恩认为缺少辨认身份的明确标志,确也鲜有人涉及。海交馆收藏的多座兽面形石刻,半兽半鸟,一般解释为毗湿奴坐骑“金翅鸟”,但不少学者认为似乎牵强,余得恩判断为朱罗时期神庙里典型的龛状装饰,李俏梅认为是建筑上的避邪之物,吴文良、吴幼雄收录此兽头鸟翼图像时只作描述性的介绍并未解读。小山丛竹附近发现的狮形石雕,吴幼雄认为是渗入本地民俗的印度教雕刻,并且与锡兰后裔有关,但显然证据不足,也无其他人论及。
泉州印度教石刻的解读要求研究人员对印度教教理、图像艺术非常熟悉,但又不能局限于此。中世纪的泉州纷繁复杂,各种宗教表面上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实质上,它们同处一个城市中,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相互独立并关联着。即使从印度教自身而言,由于地域传播的遥远,大量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往返,也一定使印度教艺术的传播经历了复杂而生动的过程。这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解读这些石刻内容时需要进行大量的基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宗教间的对比研究,才能趋于准确。
四、石刻的文化艺术渊源
学界对泉州印度教石刻之文化艺术渊源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除库玛拉耍弥在只有开元寺和白耇庙石刻参照的情况下,判断“中国匠人仿印度之木刻(?)原物所制。”“其对印度或锡兰程式及作风模仿之近似,乍见几疑出自印度匠人之手”*库玛拉耍弥著,刘致平译:《泉州印度式雕刻》。外,大部分学者认为源自南印度的艺术风格。
1962年,吴文良“初步认为这些雕刻题材多出于当时在泉州侨居的印度教僧所授意,而雕刻的艺术及手法,则出于泉州地方匠工之手”。*吴文良:《从泉州婆罗门教石刻的发现谈到中印关系》。印度学者萨布拉玛尼恩更将范围缩小至南印度,“第一个将泉州印度教石刻与南印度联系起来,并作详细分析的是萨布拉玛尼恩,他于1978年在《南印度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复提及这些石刻的雕造仿效南印度雕刻,但含有当地韵味。”*余得恩著,王丽明译:《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的比较研究》。此后不少学者就此加以论述。
韩振华认为,“判断泉州印度教石刻的风格来源,应根据石刻的年代而定。如果是北宋之前的,则传自印度或南洋都有可能,如果石刻的年代是北宋之后的,则传自南洋之说,殆无可能。”因为“盖日后南洋之印度教已衰,无由再传中国。泉州的这些石刻是青石(因青石运自惠安,洛阳桥未造,远自惠安运青石不经济,故用之甚少),年代不可能早于13世纪以前,因此非传自南洋,而直接传自印度本土。”*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
庄为玑判断“泉州的印度教宗教艺术实源自于印度本土,它同印度的宗教艺术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泉州石刻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抄袭或生硬的模仿,它的雕刻艺术精致而圆熟,颇具匠心,确实达到较高的水准。”“这些精美的雕作,就其纯粹的异国作风而言,可能直接出自印度石工之手。然宋时泉州石雕技艺已极发达,倘经印度教徒授意或提供画本,本地石工亦可胜任。”*庄为玑:《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海上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
陈履生的基本立场是“泉州印度教雕刻是附于印度教建筑之上,表现印度教内容,滋生于中国土壤,盛开于特定历史时代的艺术之花”;“其艺术处理的手法有别于印度匠师的风格”,泉州印度教雕刻艺术画面简洁明了,所创造的形象和作品表现出的艺术风格与时人的审美观相适应,透露出元代的“逸品”风格和民族气息;“它和同期印度教雕刻的繁锁装饰风格与满构图的画面结构形式大相径庭”,“它的风格和印度、波斯图案的扭曲造型适合于繁密的装饰风格,自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从而显现出我们自己民族的装饰艺术及其独特的美学风格”。*陈履生:《元代泉州的印度教雕刻》。
杨钦章认为,“我们从泉州保存下来的印度教雕刻中,可以发现南印度雕刻艺术的再现”*杨钦章:《印度教在泉州》。。他的《泉州印度雕刻渊源考》更具体指出是南印度的湿婆派寺庙,“南印度象岛、奥里萨、爱罗拉、玛莫拉普拉姆等地的湿婆派寺庙充满了种种刻划入微的神祗和动植物图象,具有强有力的装饰效果,给人一种具体深刻的印象。泉州湿婆造像艺术正是发源于这条宽阔的艺术之河。”*杨钦章:《泉州印度雕刻渊源考》。他在后来发表的《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中进一步阐明,“从新发现的柱头、柱顶、龛状、横枋、嵌板石等建筑构件来看,其外露部分都以不同程度深浅的浮雕形式镌刻精美的纹样。显然它明显地体现了南印度帕拉瓦、朱罗艺术的风格。”*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
余得恩通过详细比较印度与泉州的这些石刻图像后将时间缩至后朱罗时期,或最迟也属于早期的维杰耶纳加尔时期,“证明了中国与南印度东海岸地区的历史渊源。从它们附带的中国主题和某些错误来看,泉州的石刻最可能是产生于当地工匠之手,其模型也许是来自印度的信徒提供的绘画。”*余得恩著,王丽明译:《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的比较研究》。。
李俏梅博士也肯定了印度商人雇用泉州本地工匠的可能,她认为当时的泉州是多元文化汇萃的城市,泰米尔商人资助的这座湿婆庙周边住着各国人等,石刻上有些纹饰和其他宗教石刻的纹饰很相似,也许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雇用了同一批工匠。同时她还提出,也有可能来到泉州的印度商人带来包括工匠在内的随行人员,这种情况并非首次。
研究泉州印度教石刻的文化渊源,不能单纯以图像主体作模本,还应注意对装饰细节的纹样进行考究。比之图案主体的固有印度式,纹样装饰作为配角存在往往要灵活得多,也成为石刻雕琢时个性化创作的发挥点。泉州印度教石刻的纹样分布图像各处,有的是建筑体上的装饰及各处边饰,有的是图像画面的装饰,还有的处于图像本身的服装、冠帽、佩饰等,可以说是图像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其类型丰富,从图纹来看,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等,如莲花、圣树、狮形,其中以蛇纹最为独特;从图形来看,有几何形,钟形、屋脊形、柱形、龛形等;从风格来看,有希腊式、中国式、印度式、锡兰式等。这些纹样不仅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也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寓意表达巧妙而含蓄,既反映独特的审美情趣,又传达深刻的含意。如石柱上“雀鹿蜂猴”的图像既生动和谐,又寄托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寓“爵禄封侯”),含有中国人的哲学理念。再如横梁石上的狮头雕刻,风格与气韵,迥异于中国式狮头,带有明显的西域特征,除了告诉我们其王权与威严外,也流露出他的风格源流。还有如典型的龛型浮雕,其上明显的中式屋脊,与印度式狮头同置一处,不同宗教文化艺术相互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余得恩曾分析“大象与林伽”图像中的树叶与花托的空白填充与布局,是典型的中国式艺术手法。很容易体会到,装饰的细节更能泄露艺术的渊源。因而石刻上的纹样是最值得我们考究的内容之一,但多年来学术界对泉州印度教石刻的研究多半集中于石刻故事的解读、建筑的断代等,石刻纹样基本忽视。目前仅见余得恩注意到了某些细节,并在解读石刻图像时对个别装饰作了分析。吴文良和吴幼雄对建筑构件上的图形纹饰也有些简单的介绍。除此之外,其他若有涉及者大多只是简略描述,仍亟待进一步探讨。
五、泉州印度教神庙建筑的研究
寺庙建筑作为宗教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宗教文化最典型的产物,是研究某一地区,某种宗教最直接的切入口。泉州印度教神庙留下的未知空间很大。宏观层面上,寺庙建筑的起源,建筑属性及时代特征;中观层面上,建筑的数量、选址及布局;微观层面上,建筑种类、空间构成、宗教意象、细部装饰等都知之甚少,即便是最基本的神庙数量与形制也莫衷一是。
庄为玑在《泉州印度教寺址的研究》中指出“泉州印度教的寺址不只一处,不只一座”。从已出土的石刻看,其用材、形制和风格的确存有明显不同。这些石刻中湿婆与毗湿奴的题材都不少,且雕刻风格存有差异,这留给学者不少想像空间。陈履生对这二神共存的石刻解释是:“泉州印度教雕刻是以毗湿奴和湿婆二神的混合形式出现的,这是因为此种混合形式受人崇敬”,“故在泉州寺庙里两主神都得到了表现”*陈履生:《元代泉州的印度教雕刻艺术》。,言外之意,泉州印度教寺里面同时供奉二主神。杨钦章也判断泉州只有一座印度教寺,但属于湿婆派,他解释在湿婆派神庙里出现毗湿奴是因为“他们认为湿婆和毗湿奴以二神混合的形式出现更加受人尊敬”*杨钦章:《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然而大多数学者猜想泉州不只一座印度教建筑。泉州是否有可能分别有祭祀湿婆与毗湿奴的寺庙?会有几个祭坛?由于文献上着墨太少,现存石刻的信息量仍不够丰富,场景再现模糊不清,学界至今对此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
虽然历史上泉州印度教寺数量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一座。可是这座寺庙遗留下来的石刻量毕竟不多,甚至难窥一斑。文献上关于这座寺庙,仅有“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明嘉靖抄本:《清源金氏族谱》,第51页。,“番佛寺池,在城南隅”*道光《晋江县志》卷8,《水利志·番佛寺池》。如此廖廖数语的描述。且“番佛寺”指的是否就是印度教寺,也有不同的声音。韩振华在《元末泉州伊斯兰的“番佛寺”》*韩振华:《元末泉州伊斯兰的“番佛寺”》,载《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认为那兀纳可能是东印度的穆斯林。“西域人那兀纳所创建的番佛寺,乃是南印度东海岸的注辇人(亦即达罗毗奈人)所崇奉的伊斯兰寺院。”果如此的话,文献上竟没有关于这座印度教寺的只言片语。
吴文良与吴幼雄的观点是,这座印度教寺庙可能“与印尼爪哇东部的日惹附近所见的‘婆罗浮屠塔’或‘塔婆’的形制相同的。特别是那些砌在‘浮屠塔’上的顶层及下层的大型石块和泉州所发现的半人半兽石刻、人面狮身石刻、须弥座石刻、屋脊形石刻和龛形石刻等,极相类似”*吴幼雄:《婆罗门教的传入和泉州的印度教寺》。。然婆罗浮屠建于公元8世纪,且为佛教圣塔,虽然建筑形式上有印度教元素,但这里的印度教只是不同宗教和文明间融合补充的一种表达,它表现的终究是不同的宗教主题,不足以作为泉州建筑形制的参照。
杨钦章判断当时泉州其实只有一座湿婆派的寺庙。“寺庙创建的时间虽然于史无征,但族谱和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表明该寺是建于元代,可能是十四世纪中期。”*杨钦章:《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在分析泉州印度教寺可能形制时称“中古印度的印度教建筑包括三大派:马拉他派、奥里萨派以及十世纪以后泰米尔人治理下的紧那利派。将泉州出土的建筑雕刻(如台基石、须弥座、石柱、柱础石、柱头石、石框门等)与印度湿婆派的建筑相比较,我个人认为,泉州湿婆派教寺属于紧那利派。这类建筑一般包括有:‘曼达波’,即神殿前面的柱廊或列柱厅;‘瞿布罗’,顶上建塔的门;殿堂本身,即所谓‘毗摩那’,上面建有象截了顶的方尖形多层大塔”*杨钦章:《对泉州湿婆雕像的探讨》。。中世纪是印度教神庙建筑的黄金期,各地封建国王崇尚印度教,建造了大量的印度教神庙建筑,呈现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局面,创造了不少建筑奇迹。目前对中世纪印度教寺庙分类的不同看法很多,在对建筑形式分类不是特别明了的情形下,似乎也很难对泉州的这座神庙进行归类。
如此看来,在已发表的文章中对此寺庙可能形制的判断是笼统的,缺乏专题研究。李俏梅博士在她尚未出版的论文中有一个章节谈到这座寺庙,她将该寺庙建筑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基础材料、墙和上层建筑,并指出这些寺庙构建尽管只是原建筑的一小部分,却透露了大量的建筑信息,包括布局形式和建造者,她认为建筑工人采用的是南印度的建筑技术,细节表明工匠或建筑师熟悉达罗毗荼建筑形态。她在文中描绘了这座寺院的形式,使这座已毁教寺首次得以呈现。这座印度教寺的形制样式,仍需对古印度教寺庙建筑研究造诣较深的学者深入研究还原。
六、石刻背后的印度教与泉州
学术界曾有“印度教没有传入中国”的说法,但泉州发现印度教寺石刻表明印度教曾到泉州来。中国现存的印度教遗址遗物中,保存最多、最完好的正是泉州这些石刻。因此,研究中国的印度教,无疑离不开泉州的印度教。
印度教是由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泉州的,这是学界的共识,但何时传入,尚难界定。石笋被视为重要物证,韩振华、杨钦章、庄为玑、余得恩认同石笋乃印度教的林伽。庄为玑推断“石笋为北宋以前遗物。是印度原始宗教的遗风”,“可能是唐代印度教传入中国的史迹”。*庄为玑:《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他在另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这种观点,“其传入泉州至少应该在公元八世纪的唐代,甚至可推测在唐代以前的六朝,决非夸大之词”*庄为玑:《泉州印度教寺址的调查与研究》。。林惠祥在泉州考古图片展中也认为是古印度人的生殖器崇拜,“必是宋或以前有印度人到泉州,带来婆罗门教,连这种风俗也传来”。吴幼雄“更怀疑它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在泉州的遗物,也就是说它可能是秦汉以前的遗物”。*吴幼雄:《婆罗门教的传入和泉州的印度教寺》。庄为玑在《泉州印度教寺址的研究》中谈到了泉州幼师校园内的印度教祭坛遗址,“这个古迹可能是唐初或以前走南港(即安海港,作者注)时的古迹。”然而,关于此遗址的断代研究笔者并未见其他人谈及,对于印度教在唐代就传到泉州也无进一步的证据。
目前已收集到的三百多方印度教石刻,学者们都认为源自元代泉州的番佛寺及分散的祭坛。不论是早期学者,还是后来的吴幼雄、余得恩、韩振华、杨钦章等对此都没有异议。余得恩更是首次从南印度不同历史时期起承托作用的柱头石的构造来判断石刻的历史时期,有理有据,颇具说服力。
1956年,吴文良在泉州伍堡街发现的断裂而模糊的泰米尔文石碑是石刻断代的重要依据。余得恩的《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的比较研究》、约翰·盖依的《纳格伯蒂纳姆和泉州已消失的寺庙》介绍了印度学者萨布拉玛尼恩对石刻泰米尔文的翻译。在萨布拉玛尼恩看来,这些泰米尔文字拙劣且多处错误,估计不是泰米尔人制作的。他的这篇文章并未译成中文,其碑文翻译在中文书刊中仅余得恩作了引用,余得恩认为其翻译应最为准确。*余得恩著,王丽明译:《泉州印度教石刻艺术的比较研究》。更广为人知的翻译出自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及辛岛升。1981年,斯波义信到厦门大学时,曾对碑文进行认读,翻译结果在吴幼雄的《泉州宗教石刻》中有记载,余得恩也有引用。*吴幼雄:《婆罗门教的传入和泉州的印度教寺》。辛岛升的翻译由杨钦章在《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中引用。三人对石刻内容的翻译有所不同,但几个关键点却是一致的:首先寺院供奉了湿婆,第二时间都认定为1281年,第三是在朝廷的许可下建起的寺院,第四由泰米尔人出资修建。泰米尔文石碑的出土和解读为石刻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大部分学者认为多数石刻,包括来自开元寺、东观西台、南校场、通淮门、下围村、津头埔、东门外、新门街、伍堡街、池店等处的石刻皆来自这座寺院。
但元代的印度教又是如何传入泉州呢?庄为玑推测:“婆罗门教很可能自占城入广州,而传来泉州。”*庄为玑:《泉州印度教史迹及其宗教艺术》。杨钦章认为无可靠材料说明印度教僧人直接进入泉州传教并兴建教寺,“我个人更接近于认为是间接传入的,即印度教可能是经由爪哇,再由爪哇向泉州发展”,“考虑到爪哇印度教昌盛的历史,我们有理由推测可能是居留爪哇的南印度或当地僧侣把印度——爪哇的宗教艺术带到泉州,印度教的传入泉州,爪哇曾起友好使者的作用”。*杨钦章:《泉州印度雕刻渊源考》。
印度教在元代后是否仍在泉州存在是需要解决的另一问题。北门小山丛竹附近明代所建的白耇庙作为可能的证据,多年来一直为是否印度教寺庙争议不断。吴文良先生根据小山丛竹附近发现的石卧狮、石卧牛、须弥座祭坛石刻,白耇庙敬字亭上所嵌的印度教石刻,以及《泉州府志》及其它史料的零星记载,判断“泉州白耇庙可能是一座锡兰人兴建的印度教寺庙”*转引吴幼雄:《泉州锡兰王裔和遗址发现记》。。1998年,吴幼雄、谢长寿在《温陵白耇庙》的《泉州白狗庙重修碑记》中肯定“系明代寓居泉州锡兰王裔所建印度教庙,祀印度洋山神毗舍耶,同于今印度、斯里兰卡、爪哇毗舍耶,异于泉州狗舍爷”。书中谢长寿、廖渊泉的《明代锡兰山国王裔在泉州史迹调查札记》还逐一驳斥其为非印度教寺的几种说法。但不少学者在各个场合质疑它其实是祭祀着福建民间流行的戏神田都元帅雷海青和一只称为“灵牙将军”的狗神,也就是狗舍爷。事实上,泉州市区不乏有供奉狗舍爷的寺庙,如中山路花桥宫、城南富美宫、西街奉圣宫等庙宇。1999年,林悟殊在《泉州白耇庙属性拟证》中认为:“把泉州白耇庙定性为明代锡兰王裔建立的印度教庙,从已发表的资料看,尚缺乏有力的证据。”他倾向于与印度教无关,而与琐罗亚斯德教(袄教)有联系。2000年,海交馆研究人员李玉昆、陈丽华、叶恩典、曾丽民组成课题组,在历时三年研究后,2004年,他们在课题研究报告中断定,白耇庙的两方印度教石刻其实和其它地方发现的印度教构件及石雕一样,只是元代印度教寺庙的构件,“不足以作为白狗庙是印度教寺庙的依据”,“泉州白狗庙既非印度教寺庙,也非寓居泉州锡兰王裔所建,而是和其他许多民间信仰庙宇一样,作为境主宫的民间信仰庙宇”。*李玉昆、陈丽华、叶恩典、曾丽民:《泉州锡兰王裔文物研究》课题研究报告,2001-2004年。因此元代之后,泉州是否有印度教的存在仍然存疑。
无论如何,印度教曾在泉州存在的历史毋庸置疑。从出土的石刻看,元代泉州印度教信仰的规模并不小。寺院和分散祭坛的存在,以及惊动朝廷下诏印度教寺的建立,表明城市内有一定数量的印度教信众,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这些石刻及历史上成群结队的印度教徒来泉州经商的事实,我们可以确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人在泉州定居了,出现了印度教社区。但为什么却没有留下任何印度教徒的墓碑和后裔?相比阿拉伯、波斯人在宋元时期的泉州,文献上对印度商人着墨太少。印度教商人在泉州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生活让我们好奇。他们和本地人的互动,和外来民族的互动等等,我们知之太少。他们是否有不同派别的存在,毗湿奴派?抑或湿婆派?他们是否与其他宗教发生交集?他们的寺庙有多“壮丽”?如果番佛寺为印度教寺,那么为什么作为穆斯林的那兀纳会与番佛寺有瓜葛?他们是否形成自己的印度教团体,并对当地的经济生活产生过影响?任何一种宗教在一个地方生存必然会与当地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接触与渗透。景教和伊斯兰教在泉州对文化影响持续发生,甚至摩尼教的摩尼光佛也成为一个村落一代又一代民众的保护神。宋元时期不少印度商人或来自印度教信仰地区的东南亚人,他们杂居于泉州,将自身文化带入中世纪泉州错综复杂的网络中。然而在我们现在看来,印度教与泉州文化,与同时期在泉州存在过的其他宗教间却给人一种隔绝的印象。池店印度教神像被作为观音膜拜,体现的不是认同而是民众对印度教的一无所知。难道印度教徒在泉州的宗教和信仰活动只在内部进行,没有涉及任何对外流播?难道没有任何印度商人定居并繁衍于泉州,在元代后就消失得如此彻底?印度人与泉州本地人、印度教文化与泉州本土文化,同时期的其他宗教文化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故事与碰撞,仍像谜一样地存在。是的,石刻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是文化现象的解读。通过石刻,我们想知道的远比石刻本身多得多。
作者王丽明: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泉州:362000)
Abstract:The Hindu stone inscriptions in Quanzhou have drawn the worldwid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since they were introduced by the Indian scholar Ananda Kmaraswamy. As more and more stone inscriptions were found, more and more research papers were published. The researche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have helped us solve quite a few historical issues, such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bed patterns, the origin of the inscriptions, the cultural, arts and production backgrounds, the craftsmen, etc. After reviewing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put forth her points of view.
Keywords:Quanzhou; Hinduism; Hindu Stone Inscription; Hindu Temple
*本文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课题“古代中国与印度洋海上交流”(2013-JBKY-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