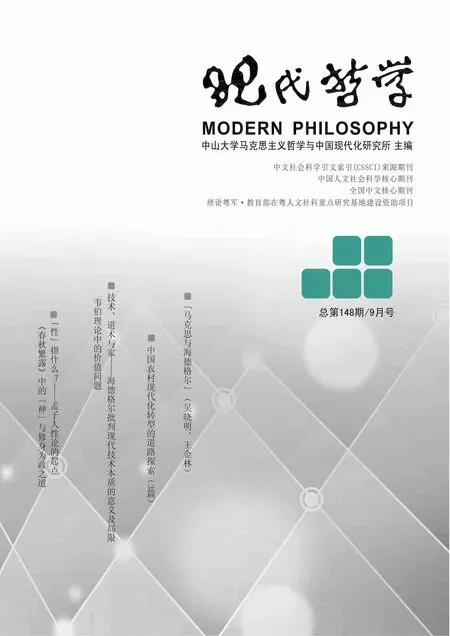《汉书·五行志》三阶一体的理论建构
吴祖春
《汉书·五行志》三阶一体的理论建构
吴祖春**
作为西汉阴阳五行思想的系统总结与集中呈现,《汉书·五行志》既记录有大量的灾异及其相关解释,也有明确而独特的理论建构。在遵天道但更重人道的理念下,《汉书·五行志》将既往的阴阳五行学说整合为以阴阳五行为内容的世界图式、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三阶一体且层层落实的解说体系,在用以解释各类灾异现象的同时,揭示了西汉时期人们独特的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思维进路。
《汉书·五行志》;阴阳五行;天人之道;理论建构
《汉书·五行志》是班固“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17页。的汇辑性作品,其价值在历代正史中得到确认。但是,自从刘知几对《汉书·五行志》所录的灾异事件,力证其不仅“错误”而且“杂驳”,质疑班固“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史通》中有专门针对《汉书·五行志》所载灾异的《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之篇。[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1页。,学界对于《汉书·五行志》的认知,便基本没有超出杨树达的观点:“古人于君主专政无奈之何,故创为阴阳五行灾异之说以恐之。汉世此说盛行,故班创为此志以记其说。由今观之,其说绝无义理,读者勿为所惑可也。”*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这实际上是在肯定它具有劝诫君主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从根本上否定了它的义理价值的存在。事实上,《汉书·五行志》作为对西汉时期阴阳五行思想的总结,一方面反映了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以其特有的理论建构,昭示了汉人用以认知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思维进路。
一、以阴阳五行为内容的世界图式
阴阳五行世界图式是秦汉时期人们对于世界(宇宙)的基本看法,也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五行志》并没有关于阴阳五行世界(宇宙)图式的完整论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五行志》透露的信息,将这一世界图式勾勒出来。
《汉书·五行志》关于阴阳五行世界图式的勾勒,仅限于引述《尚书·洪范》篇论五行的话:“经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5册,第1318页。实事求是地说,从这段并不完整的引文,我们无法看出它所做的是对世界图式的勾勒。然而考虑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后,它笼罩、统治着汉代数百年,弥漫在几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82页。,“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5页。,“在《十二纪·纪首》中,把许多事物,都组入进去,而成为阴阳与五行所显露之一体,以构成包罗广大的构造,于是使人们感到,我们所生存的世界,都是阴阳五行所支配的世界,由此而成为尔后中国的宇宙观,世界观”*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氏著:《两汉思想史》第2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不难发现,这段文字提示的正是它引而不发的世界观。
将世界看作是由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以及以之为代表的五类性质不同的事物构成,相对于单一世界本源或世界构成,无法避免地要对五行做有序化处理。就空间序列而言,虽然先秦以来对五行次序的表述存在差异*如《尚书·洪范》篇的水火木金土、《管子》和《春秋繁露》等的木火土金水、《淮南子》的金木水火土等。《汉书·五行志》虽引用了《洪范》篇有关五行的界定,但在展开讨论中却是以木火土金水为序。,但在与五方的联系上,却无有例外都以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为对应关系。这不仅使五行在空间上固定下来,也由此确立一个方位坐标。通过这个坐标,使能够与五行相搭配的项目,如五色、五味、五音、五脏、五谷等,均可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这就为纷繁世界的模式化、条理化开辟了道路。
然而,空间序列虽可视为五行的结构,却无法解释何以五行能够同五方相连,也无法说明五行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运转在五行中的反映,更无法说明依靠这样一个结构如何能够解释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五行不能只是一个简明的结构,它还要有生命,也就是使之运作起来的内在动力。
如何赋予五行生命呢?在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中,这就要使之与时间建立联系。五行与时间的关系,直到西汉,都是既清楚又说不清楚的问题。说它清楚,是所有讨论阴阳五行尤其是五行问题的文献,都对五行与时间的密切关系,以不同方式予以了肯定;说它说不清楚,是对于五行与时间该如何匹配,存在明显争议,且各种说法均有不周延之处。据可见资料,先秦至汉代,关于五行与时间匹配的方案主要有四种:一是将一年分为五季,然后与五行一一对应,如《管子·五行》和《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二是将一年分为四季,对应木火金水,以土辅四时,如《管子·四时》和《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三是将一年分为四季,以对应木火金水,但以土主季夏,如《吕氏春秋·季夏》和《春秋繁露·五行对》;四还是将一年分为四季,以对应木火金水,但是以土居夏中,如《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将一年分为五季(每季七十二日),虽实现了与五行的一一对应,但与通用的四分法存在明显错位;肯定四季划分而以土为四时之辅,虽以突出土的重要性化解了四时与五行无法一一对应的矛盾,但也不得不牺牲金木水火土原本并列的关系;以土居夏中或季夏,同样存在着否定五行间平等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淮南子》和《春秋繁露》中都没有确定的、前后一致的五行与时间的对应方案,而是采取了便于调和的数说并存的做法。《五行志》作为对西汉阴阳五行思想的总结,不会对这一状况毫不知情,再加上其对五行、五事从“经”到“传”再到“说”的整齐梳理,以至各类灾异的有序记录,都说明《五行志》对于五行与时间的关系已经找到了更为妥当的处置方法。
表面上看,《汉书·五行志》对阴阳的论说确实不如五行,但考虑到从董仲舒到《白虎通·五行篇》,五行已完全纳入阴阳统贯之内,“言五行即是言阴阳,而较言阴阳更为详备”*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前揭书,第237页。徐复观认为,五行与阴阳的完全融合,是在《白虎通·五行篇》实现的;但笔者通过对董仲舒阴阳五行思想的仔细梳理,发现其实在董仲舒那里已经完成了这一融合,而《白虎通·五行篇》不过是对这一融合进行了再次确认。,就不难理解《汉书》何以以“五行”而非“阴阳”或“阴阳五行”名志,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名为《五行志》而实质上发展的却是阴阳五行思想了。
总之,通过对五行内涵的拓展,以及与五方建立空间对应关系,与季节建立时间对应联系,《汉书·五行志》将世界看作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尤其是以之为代表的五类不同性质的事物,按照东南中西北的空间方位依次安置,并遵从季节运行规律以实现自身循环的基本图式,这就是其阴阳五行的世界图式。这个图式中虽不乏为后人诟病的简单化和神秘化倾向,但其将世界看作动态的和立体的生生不息系统,认为通过这个具体而微的世界构成可以洞悉天道奥秘,无疑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不过,阴阳五行世界图式的建构,在这里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探研天道奥秘或呈现理论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图式,藉由人类社会是世界之一环的观念,使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能够得以解释。这就使它必然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二、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
将阴阳五行世界图式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就形成了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在这个图式中,五行已明显与其作为世界本源的一面分道扬镳,着重发挥了其作为五种不同性质之标识的一面。与此同时,五行与五方、季节间的对应关系,也在这里正式出场。
紧随五行内涵之后,《汉书·五行志》以五行所代表的五种不同性质为标准,结合秦汉以来流行的时令内容,将国家的时政纲领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进行了分类概括。具体内容如下:
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
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以妻,则火不炎上。
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
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5册,第1318、1320、1338、1339、1342页。
从内容上看,这些条目显然是从防范施政失误的角度,对时令中的施政禁忌进行的专门概括。“则木不曲直”之类,既标明了该类政治纲领所属的五行之目,又明确指出了违反禁忌必然导致的后果。至于每条由禁忌组成的政治纲领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紧随“传”之后的“说”中,有进一步解释。我们以“木说”为例:
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车有和鸾之节,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及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同上,第1318—1319页。
在格式上,五行“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木说”相对于其他四“说”,一是少了对季节的暗示之词*火为“扬光辉为明者也”、土为“生万物者也”、金为“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水为“终臧万物者也”。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5册,第1320、1338、1339、1342页。,二是多了引入观卦这一极具迷惑性的解释进路。要知道,按照京房的卦气说,观卦对应的是八月而不可能是春季。但是不管怎样,这段解释至少透露出如下信息:
第一,木在方位上对应东方,与先秦至西汉有关五行与方位配合的流行观点一致。同时回避了与时间的明确关系,转而强调如何施政以符合木的本性要求。
第二,“其于王事”是“说”的重点和主体内容。所谓“行步有佩玉之度……使民以时”,与其说在阐释应当实施的政治纲领,不如说在强调国君于行为举止上应当遵循的礼义节度。这种有意识的解释偏向,一如在阴阳五行世界图式中对五行内涵的拓展,为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向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落实,搭建了桥梁,提供了通道。
第三,同“传”中仅列政治禁忌不同,“说”中不仅阐述了各项政治禁忌的具体内涵,而且还对应当推行的政治措施有所交代。这一方面凸显了《五行志》在总体上偏重政治禁忌以及由此导致的灾异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它不是没有注意到应当正面肯定的各项措施以及由此带来的好的征兆。
即使不考虑其他四“说”对各自对应的季节的暗示,仅考虑当施之政的具体内容,那么对照先秦至西汉文献中相关部分的内容则可发现,《汉书·五行志》在木“传”与“说”中所列事项,基本没有超出其时流行的观点,即强调助长养、行赏赐、重农事,而这又毫无例外是春季当颁施之政。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木政,如《管子·四时篇》“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五行篇》“日至,睹甲子木行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2、868页。,或者《淮南子·时则训》“孟春之月……其位东方……盛德在木”*何宁:《淮南子集释》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79页。、《春秋繁露·五行顺逆》“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45页。等,都与时间建有一定之联系。也唯有这样,才能解决木政何时实施的问题——除非五行的使用仅仅是为了对政治行为进行分类。而即便只是出于分类需要,也将涉及分类依据——且不说所有政令都所出有时,是否合适也主要取决于施于何时。因此,时间之于五政都至少是个隐性存在。
至此不难看出:第一,所谓的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就是将阴阳五行世界图式落实在社会层面上,形成的对社会该当如何的基本看法,即由依照季节变换制定的政治纲领为要素组成的、按照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性质进行归纳分类、并最终在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上依次得以确定的基本图式。第二,以阴阳五行为内容的世界图式与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一方面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相依共存的关系。就其对象而言,一者为世界(宇宙)全体,一者是人类社会,本身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从抽象的世界图式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图式,不仅五行的内涵从万物所由生的五种元素,转换成了五种不同性质,并被赋予了具体的政治内涵,而且作为时间序列的季节转换,在继续标识其阴阳消长的实质外,开始以时令的面目出现,并呈现出向礼制拓展的倾向——在不同的时节颁布不同的政令,本是礼制的重要内容。第三,由于《五行志》的史书性质,它所呈现给人们的这个落实在现实政治上的阴阳五行图式,一方面缺少相应的理论论证,呈现出经验总结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明显倾向于通过违反政治禁忌的行为与灾异现象的联系,对现实中君主的政治行为给予警告和约束性限定。只是这种约束能否起作用,最终还是要看君主对礼的遵守情况。因此,《五行志》在阴阳五行图式的构建中,最终将落脚点放在国君应当遵循怎样的行为准则上。
三、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
《汉书·五行志》因袭了《尚书·洪范》篇对貌言视听思五事所做的具体限定,也认可它们各有需要遵从的礼义节目:“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艾,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5册,第1351页。不仅如此,还将“庶征”中有关休征和咎征的内容也搬用了过来。这样,但凡五事能据礼而动,即貌言视听思最终体现出肃乂哲谋圣,自然界就会冷暖风雨各从其时;如若五事违礼而作,亦即容貌狂妄,言语僭越,查视宽缓,听言过当,思虑昏乱,则天道运行必然出现异常的波动,导致冷暖风雨不从其时。
同五行“传”中对待时政纲领和政治禁忌的态度一样,五事“传”对《洪范》篇提到的举止规范以及相应的休征仅仅是存而不论,其关注的重点也是不合礼的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灾异。为行文简便,我们仅以“貌传”为例来说明:
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5册,第1352页。
学界曾有人注意到此处在天人关系上的公式化处理*冯浩菲:《〈洪范五行传〉的学术特点及其影响——兼论研究天人感应说之不能忽略伏生》,《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2期,第38页。。我们更应该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违反五事应当遵从的礼义规范所导致的灾异,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明显超出了违反以五行划分的政治禁忌所可能带来的灾异,这无疑是从一个侧面突出了君主行为守礼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二是在违反五事应当遵从的礼义规范所导致的众多灾异中,潜在地扩大了五行在社会领域中的内涵,即不仅包括五事,更包括五孽、五祸、五痾、五眚、五祥和五色等;三是五事“传”中虽没有明确指出其与五行的关系,但在“惟金沴木”之类的深入探讨中,显然暗示了貌言视听思与木金火水土的一一对应关系。
至于该如何理解五事“传”程式化的内容,还需要借助五事“说”的进一步阐释。为行文简洁起见,我们仍仅以“貌说”为例予以说明:
凡草物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虫豸之类谓之孽。孽则牙孽矣。及六畜,谓之祸,言其著也。及人,谓之痾。痾,病貌,言浸深也。甚则异物生,谓之眚;自外来,谓之祥。祥犹祯也。气相伤,谓之沴。沴犹临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时则”以绝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后也。*[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5册,第1353页。
“说曰”的内容,显然是在具体解释“传”中的关键词。透过其对孽、祸、痾、眚、祥等的解释不难发现,在对灾异描述的次序上,明显受了董仲舒的影响。董仲舒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6页。灾异出现有先后次序。《五行志》与此稍有不同,它以“时则”突出了各种灾异出现的可能性与或然性。这样,灾异的出现就不再是上天对君主的仁爱,反倒是对君主违礼行为的容忍度降到了最低——只要君主行为不合礼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这无疑加强了对君主行为的监控与约束性。“说曰”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五行在这里已不再是单纯的五种世界构成元素或五种不同性质,而成了五种不同性质的气。正是透过五行之气,五事才与五行建立了相应的联系。
从《五行志》的行文看,五事“说”与五行“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五行“说”对五行“传”的解释比较一致——唯一出现的引申就是在水“说”中对京房《易传》的引用,而五事“说”对五事“传”的解释则意见相对杂驳。因此在貌“传”进行解释的“说曰”之后还专门附有一段文字,对这种驳杂的情况进行了说明。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对于仪容体貌方面的限定,也就是“肃”“敬”,《五行志》有专门的解读,其强调的重点是既要君主做到内心的“恭”,还要其做到外在的对人和物的“敬”;二是在对咎征的具体解释中,《五行志》直接以阴阳消长和季节变换,来解释何以貌言视听思不合礼而所罚不同,相对于《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中以肃主春、乂主秋、哲主夏、谋主冬以与季节相连的做法,显然巧妙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五行志》并非不言阴阳,同时也指明了貌言视听思与季节的隐性对应关系。
这样,在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落实为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的过程中,不仅五行的内涵沿着礼的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以五行为标识划分的时政纲领,转变成为以貌言视听思为内容的五事,并以五行之气维系着二者间的直接联系;而且季节的内涵也沿着五行划分时政纲领时体现出来的礼的规定性一面继续发展,凸显了礼的制约性和支配性;唯有通过五行之气得以确立的五方,维持着其不变的地位。于是,阴阳五行图式最终从世界图式,经由社会图式,最终落实在了君主行为准则上,形成了以五事为基本内容、五方为空间序列、季节为隐性时间序列、礼为实质的个人图式,揭示了西汉时人们对外在世界尤其是社会(政治)现象的观察与认知路径,以及服务于君主专制的理论归趣。至于与“五事传”内容相仿的“皇极传”,则不过是对其理论归趣的进一步强调。
关于阴阳五行的世界图式,《汉书·五行志》不是第一个论证者,也不是论证最完善者,但却是最直接、系统而有特色者。一般而言,世界图式作为对世界的理解和重现,不管它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逻辑的还是直觉的,其对世界的把握和认知,都毫无例外是宏观的、抽象的、概括的和凝练的。以遵循天道运行规律并最终转化为遵循人间礼制规范为理念,《五行志》建构了一个从世界图式到社会图式,再到个人图式的系统的层层落实的阴阳五行图式。这一庞大而整齐的图式,不仅系统地展示了天、地、人三者间的动态关系,诠释了西汉时人理解的天人之道的具体内涵,而且昭示了当时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思维进路,并对此后中国人认识外在世界的模式产生了莫大影响。
(责任编辑 杨海文)
吴祖春,河南南阳人,哲学博士,(广州510225)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B234.99
A
1000-7660(2016)05-01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