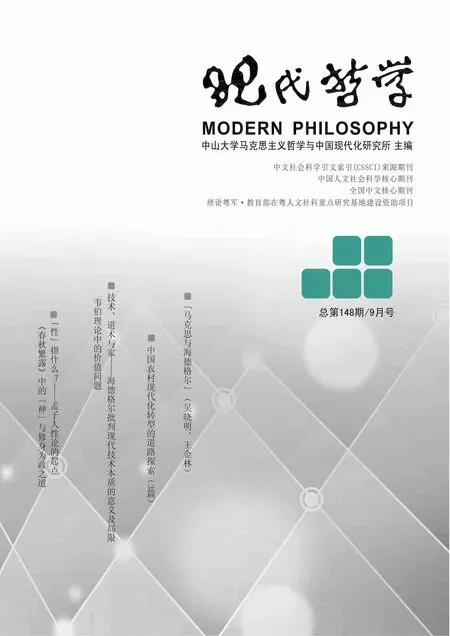《春秋繁露》中的“神”与修身为政之道
翟奎凤
《春秋繁露》中的“神”与修身为政之道
翟奎凤**
《春秋繁露》中的神,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作为祭祀对象的神(鬼神)、作为变化之道的神(化神)和作为生命主体的神(心神)。在董仲舒天人同构的观念下,天是最大的神,天子祭天有着绝对的神圣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懈怠荒废。通过祭祀,可以见到平常见不到的神。作为君主还要尊神、贵神,这里所说的神是讲最高统治者的修养,是化道之神,无形无象无声,是形而上的整体的一,它能主宰形下世界的变化。《春秋繁露》还讨论心神之义,认为只有平意、静神才能养气长生,这种虚静体神聚精的思想受到道家的一定影响。在董子看来,养生与治国是一个道理,身为国,心为君,这种身体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董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天之春夏秋冬相应,是天道自然,只可顺调无滞,不可制止。
天;尊神;贵神;静神;神气
“神”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主要有鬼神、神化、心神三个义项*详细讨论,参见翟奎凤:《先秦“神”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9—135页。。《春秋繁露》约出现84次“神”字,其意义也不外这三个方面。在具体讨论上,《春秋繁露》则有其独特的意义结构。下面主要从祭祀之道、为君之道、养生之道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春秋繁露》中的神。
一、天、百神、小神与祭祀之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是早期中国政治的重要议题,对此《春秋繁露》也有大量讨论。毫无疑问,“天”一直是中国古人信仰的最高神,而且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天。除了“天”,中国人祭祀的神灵还很多,“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早在先秦就有“百神”的说法。关于“天”和百神的关系,董仲舒明确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义第六十六》)*本文参考的是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的《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如非特别讨论,原文征引只注出篇名。,又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郊语第六十五》)。“天”是大神,相比之下,其他的神都是小神,祭祀的时候要先祭“天”(郊祭),然后才能祭其他的神,这样才符合“礼”。董仲舒说:“故《春秋》凡讥郊,未尝讥君德不成于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逆于礼,故必讥之。以此观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独卜,郊祭最大也。”(《郊祀第六十九》)甚至,不祭祖先,也要祭天,以表示天尊于人之义,“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郊事对第七十一》)。
祭祀的根本义谛在于“见”到“天命鬼神”。董仲舒说:“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谓也。善乃逮不可闻见者,故谓之察。”“祭之为言际也与?祭,然后能见不见。见不见之见者,然后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后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祭义第七十六》)综合来看,“察”与“际”应该都是“见不见”的意思,进入祭祀状态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存在,即天命鬼神。“天命”对应于祭天,鬼神对应于一般的祭祀。如果留意《礼记》关于祭祀、神明的问题,我们会看到在《礼记》中更多地用到的是“交于神明”,如《礼记·祭义》中说“孝子将祭……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恍惚以与神明交,庶或饗之”。在祭祀之道上,我们不得不说,这是董仲舒与《礼记》的一个重要区别,“恍惚以与神明交”侧重与神明的感通一体,有种“迷醉”“忘我”的意味,而“见不见”“知天命鬼神”似乎有了更多的清醒、理性、知性、分别和边界意识,这种意识其实也体现在“察”与“际”二字的字义之中。
知天命鬼神,就可以明了祭祀的实质,这样就会重视祭祀活动。董仲舒接着说:“重祭事如事生,故圣人于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独任,事之而不专恃。恃其公,报有德也,幸其不私与人福也。”(《祭义第七十六》)这里的逻辑性很强,而且有着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祭祀——畏、信、事——鬼神——正直——福报,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德福一致的观念。德性、内心的圣洁虔诚是祭祀的关键,董子说“德在天地,神明休集”(《正贯第十一》),有大德者,神明皆来护佑。当然,“德在天地”主要来讲也是对天子的要求,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逻辑下,天子的心灵德行与上天有着直接的感应,因此,天子祭天有着至高的神圣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荒废或懈怠祭天,“对天的祭祀即郊祭是封建统治者最大最重要的活动,给其他神祭祀之前必须先祭天,人民生活苦难、诸侯在丧期中,都不能停止祭天活动”*周桂铀:《董仲舒论祭祀——兼论儒家论天的宗教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90页。。
《春秋繁露》中讨论祭祀的名目很多,其中还有关于求雨的祭祀,论及了春、夏、季夏、秋、冬五时神:“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鸡七。”“季夏祷山陵以助之……其神后稷,祭之以母五。”“秋暴巫尪至九日……其神少昊,祭之以桐木鱼九。”“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求雨第七十四》)其对应关系可简括如下:春——共工;夏——蚩尤;季夏——后稷;秋——少昊;冬——玄冥。而关于五时神,代表性的文献《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的记载是:春天,主东方,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天,主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天,主西方,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天,主北方,其帝颛顼,其神玄冥*详细讨论,参见杨华:《上古中国的四方神崇拜和方位巫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13页。。对比来看,《春秋繁露》的说法与此出入较大,共工、蚩尤、少昊为帝,以少昊帝配秋与《礼记》一致,季夏后稷与后土相类,只有“冬,其神玄冥”与《月令》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求雨第七十四》篇,两次出现了“神宇”这个词语,如春天求雨部分有说“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豭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夏天求雨也又说“取三岁雄鸡、豭猪,燔之四通神宇”。“神宇”一词似不见于先秦文献,这里当为首次出现,一般认为这里的神宇是灵室,即祭堂*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7卷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第862页。。
二、尊神、贵神与体国为君之道
上面主要讨论了作为祭祀对象的神。《春秋繁露》中“神”的意义是多面的,除了祭祀之神,作为变化之道的“神”在《立元神第十九》有比较集中体现。如说:“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则君尊严而国安;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莫见其所为,而功德成,是谓尊神也。”这里的尊、神是并列词,并不是动宾结构。“尊”体现的是对权利、名位的敬畏,又具体表现在要任用贤能。而这里的“神”结合上下文,当是变化之道,与《易传·系辞》所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意思比较接近,宋儒张载《正蒙》所说“一故神,两故化”是对“神”这一含义的很好揭示。作为化道之神,这里具体说的是政令治道、化民美俗、天下太平,能做到这一点要靠众多贤能的同心协力、一心一意,这样才能入神化民,能够“莫见其所为,而功德成”,这是“尊”“神”的目的。当然,作为变化之道的神,似又可分为客体、主体两种,《易传》所说当侧重于客体的化道之神,而《立元神篇》似侧重于主体的化道之神,具体来说是天子要化天下需要入“神”及“同”“一”的工夫和修养。董仲舒接着又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盛其精而壹其阳,众其贤而同其心。壹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后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立元神第十九》)这里“天”对应于“圣人”,圣之“贤”即天之“精”,天之日月星辰即圣人之爵禄,可见这里所谓的“圣人”就是指君主。天要“盛其精而壹其阳”才能致其“神”,圣人要“众其贤而同其心”才能“致其功”,我们看这里“心”与“阳”也是对应的。综合来看,这里的“神”的特点一是能“化”,二是“莫见其所为”。
除“尊神”外,《立元神第十九》提出“贵神”说:“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声。声之不闻,故莫得其响,不见其形,故莫得其影。”与“尊神”不同的是,这里的“贵神”是一个词,是以神为贵的意思,但两者所说的神,意义是一致的。“神”无形无声,看不见、听不到,但是董仲舒又强调:“所谓不见其形者,非不见其进止之形也,言其所以进止不可得而见也。所谓不闻其声者,非不闻其号令之声也,言其所以号令不可得而闻也。”可见,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并不等于无所作为、不进不退,只是其所以进退的道不能见到,其所以号令天下的道听不到。接着董子又说:“不见不闻,是谓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关于此处标点,张世亮等人译注的《春秋繁露》为“是谓神人”(第199页)。这是不准确的,“人”字应与下句连读为“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从这里看,“神”不见不闻,是冥昏、幽深的意思,但正是只有能做到冥昏,才有明彰,这与《荀子·劝学篇》所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的意思是一致的。当然,董子这里所说的神一方面可以说是体现了天道变化之功的内在机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来说明天子的修养。他还说:“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向阳,恶人见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为人君者,执无源之虑,行无端之事,以不求夺,以不问问。吾以不求夺,则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则彼费矣。吾以不问问,则我神矣,彼以不对对,则彼情矣。故终日问之,彼不知其所对;终日夺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则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阴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这里的“阳”和“神”都有让人难以琢磨的意味,就是说君主的思想和内心不能让臣下轻易知道,否则容易为臣下所制,这套君王术有其一定道理,但容易给人感觉有流于黄老权谋与申韩之术的意味。冯契认为:“董仲舒讲人君的‘建治之术’在于‘贵神’,实际上也近乎黄老的阴谋权术”,“故弄玄虚,耍手腕,令人莫测高深。这完全是黄老和申韩的语言”*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8页。。实际上这套君王心法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金春峰的评价比较平和一些。他认为“这完全是《老子》以‘不争为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思想的运用和发挥”,“他把《老子》的权谋思想和阴阳天道结合起来,对黄老思想是一种发展”*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立元神”三字,“元”是君主。董子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又说:“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君化若神”,可以理解君王要像“天”神一样高高在上、不可琢磨,这样来看这种“神”有点“鬼神”之神的意味。但综合来看,《立元神篇》所说“神”应该更多的是一种化道之神的意味,“一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阳”“一”是化道之神的重要特征,可是这种神又有幽深、昏冥之意味,神者深也,这又有着阴的特征。《易传·系辞》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又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董子《立元神篇》所说的神,神有阳的一面也有阴的一面。仔细分析,董子此节论神,似有些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强调神与精、阳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说“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似神又以阴为体,以阳为用。依此推理,阴、冥当是无形的,所以“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向阳”“人君居阴而为阳”,但又说“阴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这样人君当是尚阳。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又说:
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故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也;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考实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其君。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刚坚然后阳道制命。
这里强调“神”的冥昏、无形的特征,而且也是与“阳道”对应。天“藏其形,所以为神也”、人君“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立元神篇》所说的尊神、贵神,其主要意思可以从《易传》所说化道之神来理解。《立元神》还说:“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这里的“神”是心神的意思,《春秋繁露》有多处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神。下面我们具体讨论心神之神。
三、平意、静神、养气与养生之道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七》基本上是讲人如何法天之道来养生的,天人之道贵在中和,这也是养生的关键。具体而论,养生又重在“爱气”,“民皆知爱其衣食,而不爱其天气。天气之于人,重于衣食。衣食尽,尚犹有间,气尽而立终”。在人的生命系统中,气与神、意、心密切关联。董子说:
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之谓意,意劳者神扰,神扰者气少,气少者难久矣。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身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陵,固守一德。”此言神无离形,而气多内充,而忍饥寒也。和乐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内充也。外泰不若内充,而况外伤乎!忿恤忧恨者,生之伤也;和说劝善者,生之养也。君子慎小物而无大败也,行中正,声向荣,气意和平,居处虞乐,可谓养生矣。(《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这里是论心神之义,应该说“气”是天然客观存在的,所谓“气从神而成”,这是就个人而言,能摄取多少“天气”(精气)为其所用,主要取决于其神的状态(静),“神从意而出”,也并不是说神是由意生出来的,而是说神的本然状态功能的展现要由调整意来实现。“心之所之谓意”,意是内心的趋向。如果意念纷乱,神就会受到干扰,神被扰乱,能摄取稳固的天气、精气就会很少,气少就很难长寿。因此,君子要减少欲望、断绝恶念,来最大限度地平静心意,心意平,神才能静,神静才能养气聚气,神气才能相融,气多身体才能康健有力,这样就得到了养身的关键。“神无离形”,形神合一,这样内气就会充实,这也是道家的养生要诀。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控制好不良情绪,内心中和,恬愉向善。
《循天之道篇》还说:“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气到底是从“神”还是从“心”呢?其实从神也就是从心,因为神从意,而意为心之所之,神可以说是心的整体状态。关于精、气、心、身的内在关系,《通国身第二十二》也有详细论述:“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形体无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致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因此,董子养生说中的气指的是精气(气之清者),也可以倒过来说,其所言之精为气之清者,是生命能量之源,是生命力的象征。所谓“虚静其形”、“形静志虚”,主要还是强调虚静其心、其意、其志,“虚静以致精”与“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的主张是一致的。董子的这些养生思想,有学者认为“较多地吸收了庄子关于恬淡虚静与全神守气的养生思想”*方勇:《庄子学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3页。。
“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董仲舒论身心关系,经常拿国与君的关系来类比。《天地之行第七十八》说:
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隐居深宫,若心之藏于胸;至贵无与敌,若心之神无与双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浊,若身之贵目而贱足也;任群臣无所亲,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上下相承顺,若肢体相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气和平,形体无所苦也;无为致太平,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而体得以全;臣贤,君蒙其恩,若形体之静,而心得以安。上乱,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为伤也;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心为之丧。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这里出现两则“心之神”,后则是与“形体之静”对举的,可以理解“心之神”为心的神明、神灵、神圣,与“静“相对,这里的神似为形容词。“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可以与《正贯第十一》所说“德在天地,神明休集”相互诠释。《郊语第六十五》也说“天地神明之心,与人事成败之真,固莫之能见也,唯圣人能见之”,这种神明不是特定的神灵,而是天地之心、天地之精神。“若神气自通于渊也”,这里的神气是说心神之气。“致黄龙、凤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陈槃认为:“《繁露》所言黄龙、凤皇、玉英、芝英、玉女皆瑞应事物。以神仙玉女为瑞应,秦汉间则然。”(氏著:《古谶纬书录解题附录(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1页)张世亮等人译注的《春秋繁露》认为玉女、芝英当指“气功导引中所达到的高妙成果与境界”(前揭书,第635页)。,这里的神明也当指心神。黄俊杰认为“董仲舒在上文中论述国君与百官的功能时,是诉诸具体的人的身体中‘心’之‘神’之有无或四肢是其否发挥作用”,他认为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身体政治论”*黄俊杰编著:《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8年,第265页。。王健文解释这段话说:“董仲舒的文字分喻君臣、上下、心体,对偶而述,只有一个地方不是很相称:‘上乱,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为伤也。臣不忠而君灭亡,若形体妄动而心为之丧。’若依对称原则,上句当为‘君乱,臣被其患,若心不神明而手足为伤也’。但是现在所见的陈述形式,显然别具用心,刻意维护君的尊严。上乱,只能是耳目不聪明,而不是心不神明,换言之,只是君之近臣不贤,责任不在君(心)。叔孙通所谓‘人主无过举’,汉代阴阳不调则罪在三公,大致都是在类似的思想氛围下的产物。这样为君上维护的曲折解释,事实上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极为深远。凡是施政不当,臣民多还是为皇帝开脱,认为是奸人蒙敝(耳目不聪),继续忠于皇帝,造成政治认识上的盲点。”*王健文:《国君一体:古代中国国家概念的一个面向》,氏著:《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122页。刘畅认为“在此,共找出了‘心’与‘君’的十五处相同之点进行类比,其重点在于论证君主治理国家的种种道理和技巧,可视为对先秦以来心君同构思想的一种经典性总结。亦可看出,论证心君同构的思想归宿,在于为王权政治提供另一种理论依据”*刘畅:《心君同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原型范畴分析》,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在董子看来,国与身相似,天与人也相似,有着同构相应性,他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人副天数第五十六》)这里的“神气”当指“天气”或具体来说指春夏秋冬之气,与上段“若神气自通于渊也”之神气不同。实际上,把心之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之气相关联,《春秋繁露》曾反复论及:
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号也。(《为人者天第四十一》)
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类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故可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阴阳义第四十九》)
人有喜怒哀乐,犹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乐之至其时而欲发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时而欲出也,皆天气之然也。其宜直行而无郁滞,一也。(《如天之为第八十》)
这种理论施之于养生,会把喜怒哀乐看作人的天然情绪,就像天有春夏秋冬一样自然,难以避免,可以顺势节制,不可以克除,而且宜“直行而无郁滞”。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气要循环流通,不能长时间滞于某种情绪。明末刘宗周把喜怒哀乐看作心体的天然四德,与天之春夏秋冬四气交替一样自然,他反对“未发为性,已发为情”的说法,认为“以是分配性情,势不得不以断灭者为性种,而以纷然杂出者为情缘”*[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33页。。显然,刘宗周以喜怒哀乐为心体四德是为了把儒学与佛教严格区别开来,这种思想与董仲舒“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的观点非常类似,可谓渊源有自*《荀子·天论篇》说:“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荀子也把喜怒哀乐看作人的天然情感。。
综上所述,《春秋繁露》述及的“神”是对先秦以来“神”观念的综合继承与发挥。董仲舒的神观念既有先秦儒学与《易传》的影响,同时吸收了庄子及黄老道家的养生思想,其“神”观念体系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把祭祀、养生之神与治国理政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奇特的身体政治学是中国古典哲学特殊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
(责任编辑 杨海文)
翟奎凤,安徽亳州人,哲学博士,(济南250100)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B234.5
A
1000-7660(2016)05-0115-06
*本文系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