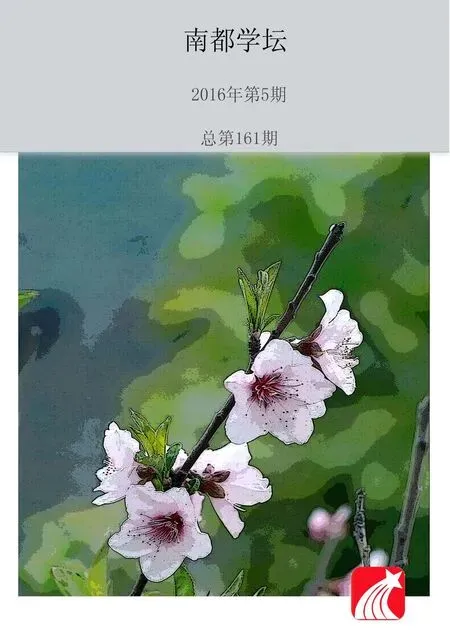于亦北亦南中更重南曲
——王骥德《曲律》之“南戏论”
王 辉 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于亦北亦南中更重南曲
——王骥德《曲律》之“南戏论”
王 辉 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王骥德《曲律》虽然是北曲与南曲并论,但因其重点在南曲(戏),而成为明代继徐渭《南词叙录》之后的又一部“南戏论”著作。《曲律》之于南戏的论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着眼于音乐的角度,将南戏的起源与上古时期的“南音”结合考察;二是主张“本色与文采”兼用,“法与词两擅其极”;三是对南戏格律学的建立;四是重视南戏创作与舞台表演。王骥德的这些南戏认识及其所获,对当时的南戏创作与其后的戏曲学研究,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徐渭;《曲律》;格律学;南戏论
在《南词叙录》的作者徐渭死去的第八个年头,即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徐渭的弟子王骥德在友人的催促下,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也完成了一部戏曲理论著作*《曲律》卷首附有二序,一为冯梦龙《叙》,一为王骥德《曲律自序》,前者的落款时间为“天启乙丑春二月既望”,表明其作年为公元1625年,后者则署为“万历庚戌冬长至后四日”,表明其作年为公元1610年,二者相隔15年。以冯序之“而伯良《曲律》一书,近镌于毛允遂氏”云云,勘之王序落款的时间,可知王序本为《曲律》的初刻本,冯序本则为《曲律》的再刻本,或者为翻刻、翻印本 。对此,吕天成《曲品自序》中的“今年春,与吾友方诸生剧谈词学,穷工极变,予兴复不浅,遂趣生撰《曲律》。既成,功令条教,胪列具备,真可谓起八代之衰,厥功伟矣”一段文字,又可为之佐证,因为其中的“今年”,勘之吕序“万历庚戌嘉平望日”的落款,知为公元1610年。吕序既与王序作于同一年,而吕序于其中又有“遂趣生撰《曲律》,既成”云云,则《曲律》之成书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也就甚为清楚(按,“遂趣生撰”的“趣”,古通“促”,“遂趣生撰”即“遂催促徐渭撰”之意,而其“既成”又在“今年”,合勘之,知徐渭撰著《曲律》的时间实际上不足一年)。又,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曲律》之《曲律提要》可知,《曲律》现所存见之最早刻本为天启四年本,其较之冯梦龙所序本(天启五年本)而言,无疑是属于另一种刻本的。如此,则知《曲律》的初刻本问世后,坊间是多所翻刻与重印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对于提高《曲律》的社会知名度,显然是极为有利的。,这就是被时人称之为“法尤密,论尤苛”[1]第四集,37、“厥功伟矣”[1]第六集,207的《曲律》。《曲律》凡四卷四十节,所涉门类详备,论析精辟,组织严密,而又自成体系,是公认的明代戏曲论著的代表作。此书虽然是北曲与南曲兼论,但因王骥德受乃师《南词叙录》及当时有关南曲著作的影响,使得其所论重点乃为南曲,而且,其所论之南曲又主要表现在“南散套”与“今之戏文”方面。“南散套”又有“南套”“南曲套数”之称,一般只用同一宫调所属的曲牌,在这方面与“今之戏文”密切相关;“今之戏文”又名“南曲戏文”,其实就是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称之“南戏”。所以,《曲律》所论之南曲,实际上是与南戏甚为关联的,因之,称《曲律》为继《南词叙录》之后的又一部“南戏论”著作,也就甚为符合明代戏曲论著之发展实况*《曲律》将南曲(戏)列为论述之重点者,其“总论南北曲第二”之文末自注已有所载:“北曲,《中原音韵》论最详备。此后多论南曲。”又“论名调第三”于“视古乐府,不知更几沧桑矣”下有注云:“以下专论南曲。”凡此,均为《曲律》中视“南戏论”为重点之证。而据《曲律》全书可知,王骥德在撰写是书之前与之时,还曾参考过蒋维忠《南九宫十三调词谱》、沈璟《南词韵选》等有关南曲的著作。。此则表明,王骥德的戏曲认识观,特别是对于南戏的关注与重视,与徐谓乃是甚为一致的*关于徐渭的戏曲认识观,以及对南戏的倾力关注,具体参见拙作《南戏“论著”的第一人——论徐渭〈南词叙录〉》一文,载《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4期。又,在徐渭《南词叙录》之前,对南戏批评予以涉及者,虽首推何良俊《曲论》一书(主要为《琵琶记》等“九种戏文”,且甚简),但其之所论因主要为北曲,故与《南词叙录》《曲律》之“南戏论”不属一个系列。关于何良俊《曲论》及其所获,具体参见拙作《论何良俊的戏曲学理论——以其〈曲论〉为研究中心》一文,载《阅江学刊》2013年3期,第142—148页。。
王骥德一生著述甚丰,除诗文集《方诸馆集》外,另有散曲《方诸馆乐府》二卷,传奇《题红记》,杂剧《倩女离魂》等五种,在戏曲论著方面,则有《南词正韵》《曲律》《古杂剧》(选编)等,并校注《西厢记》《琵琶记》二种。其中,最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的,即为《曲律》四卷。《曲律》所关涉的戏曲学内容,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源流论、作法论、艺术论、表演论。而其中之所论所析,又以南戏为多,因之,本文旨在着眼于“南戏论”的角度,对《曲律》中有关南戏的种种论述,作一具体透视。
一、关于南戏起源的认识
大凡论及南戏者,首先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之起源进行讨论,这在徐渭《南词叙录》是如此,于王骥德《曲律》也是这样,二者所不同者,是徐著专论“南戏史”,而王骥德于《曲律》中则是北曲与南曲(戏)兼为。徐渭《南词叙录》认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1]第三集,239其中所言“宋光宗朝”,为宋光宗赵惇绍熙年间(1190—1194),也即南宋初、中期之际,这与“或云”之“盛行则自南渡”基本一致。《南词叙录》中的这一“南戏起源说”,曾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所接受,认为“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2]109。
王骥德《曲律》之于南戏起源的认识,所藉以切入的角度,与徐渭《南词叙录》大相区别,即徐渭论南戏的起源,依据的是南戏的剧本实例,如《赵贞女》《王魁》等,而王骥德则主要是以生成史为着眼点,将其上溯到先秦时期的“曲”与“乐”,然后再从上古而下溯至金、元、明诸朝,并由此及彼地对北曲与南曲的发生、发展进行了逐一梳理。所以,王骥德在“论曲源第一”中认为:
曲,乐之支也。自《康衢》《击壤》《黄泽》《白云》以降,于是《越人》《易水》《大风》《瓠子》之歌继作,声渐靡矣。……金章宗时,渐更为北词,如世所传董解元《西厢记》者,其声犹未纯也。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胜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杂胡语,其声近噍以杀,南人不习也。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于是美善兼至,极声调之致。始犹南北划地相角,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1]第四集,55-56
在这段文字中,王骥德指出,北曲“渐更”于金章宗时期(公元1190—1208年),“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且“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因为南曲的繁荣兴旺,而致使“北词几废”,则南曲在“我明”的发展势头之迅猛,已不言而喻。
在“总论南北曲第二”中,王骥德又就南曲之起源进行了再讨论,并依序引录了胡鸿胪《侍珍珠船》、左克明《古乐府》、吴莱《乐府类编》、王世贞《曲藻》等之所载,以作为其立论的依据。如引录胡鸿胪《侍珍珠船》所引刘勰《文心雕龙》后认为:
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关西胡鸿胪《侍珍珠船》引刘勰《文心雕龙》,谓:涂山歌于“侯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于“飞燕”,始为北声。及夏甲为东,盘庚为西。古四方皆有音,而今歌曲但统为南北。如《击壤》《康衢》《卿云》《南风》,《诗》之二《南》,汉之乐府,下逮关、郑、白、马之撰,皆北音也;《孺子》《接舆》《越人》《紫玉》、吴歈、楚艳,以及今之戏文,皆南音也。[1]第四集,56
这实际上是曲、戏并论,只不过是曲先戏后而已。首先,王骥德以“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10字进行“总论”,意在表明南曲的历史久远、渊源悠长,并就所引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之所言为据,对南曲的“渊源史”进行了简略观照,认为“古四方皆有音,而今歌曲但统为南北”。之后,则以排列之法对北曲与南曲进行了“二元”归类,认为“今之戏文”与古之“《孺子》《接舆》《越人》《紫玉》”等,乃皆为“南音”之属;而“《诗》之二《南》,汉之乐府,下逮关、郑、白、马之撰”等,则皆为“北音”。这一“南”一“北”,虽然壁垒森严,阵线分明,但在王骥德看来,其无论是北曲抑或南曲,甚至是“今之戏文”,都是与上古时期的“四方皆有音”密切相关的。
综合上述,可知王骥德之于《曲律》中对南曲(戏)起源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将北曲与南曲的起源进行了比观,认为其皆具有历史悠久之特点;二是在具体的论述中,乃是由曲而戏,进而曲、戏并论;三是指出盛行于“我明”的“今之戏文”也即南戏,亦为“南音”之属,其与上古时期的《越人》《紫玉》等在音乐方面属于同一“乐源”;四是认为“南音”的起源虽然可上溯至夏、商时期,但其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今之戏文”,则是在“我明”之际。其中的第三、第四两点,实际上是借助“南音”这一特殊的音乐支点,将南戏的起源推向了上古时期的夏、商之际,即认为南戏的肇始与发展,主要源自于上古时期的“南音”。王骥德在“总论第一”与“论曲源第二”中所勾勒的,实际上是南戏由《越人》等上古的“南音”至“我明”之“今之戏文”的一条音乐发展脉络,其所反映的则是南戏之产生,主要是受先秦“南音”的影响而导致。
从戏曲发展史的角度言,王骥德之于《曲律》中对南戏起源的上述认识,较之徐渭《南词叙录》的“南戏起源说”虽然着眼点不同,但二者的内核却是基本一致的。《南词叙录》认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云云,指的是南戏具体剧曲之始,而《曲律》认为“今之戏文”与上古时期的《孺子》《接舆》等相关联者,主要是立足于“南音”发生、发展的角度,也即是就其音乐的渊源关系以论,所以,二者实际上并不矛盾。至若《曲律》认为“迨季世入我明,又变而为南曲”者,是指“今之戏文”在“我明”的繁荣发达之况,与《南戏叙录》之记载更相契合。因为据其所载,朱明代蒙元未久,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即曾对高明的南戏之作《琵琶记》大加肯定,认为其“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关于朱元璋对高明《琵琶记》的赞扬与肯定,具体参见拙作《朱权与〈太和正音谱〉——兼论〈琼林雅韵〉及“南曲韵书”说》一文,载《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5期,第7—12页。。朱元璋对《琵琶记》的这种赞扬,对于“今之戏文”在“我明”时期的发展,无疑是极具助益的。
二、对沈、汤之争的评判
在王骥德生活的万历年间(1573—1619),由于南戏在当时的兴旺发达,而导致了戏曲批评的空前繁荣,使得各种不同观点之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沈、汤之争”。“沈”即沈璟,“汤”即汤显祖,二人一为“吴江派”的领袖,一执牛耳于“临川派”,均于南戏创作的繁荣与其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王骥德则以其深厚的戏曲学素养,担当了这场论争的评判者与理论总结者,而其之于南戏的种种认识,亦皆因此而得以凸显。
“沈、汤之争”是南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双方所争论的核心,主要表现在“词与法”“本色与文采”两个方面,而“词与法”又为其关键所在。所谓“词与法”,又称之为“辞与声”“文与律”,其所指实际上就是戏曲作品中内容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也即在一部戏曲作品中,究竟是以内容(思想)为第一还是以艺术(形式)为第一的问题。朱明时期对戏曲之“律”(“声”“法”)予以高度重视者,何良俊堪称第一人,其《曲论》在论及《拜月亭》等九种南戏时,曾如是写道:“此九种,即所谓戏文,金、元之笔也,词虽不能尽工,然皆入律,正以其声之和也。夫暨谓之辞,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叶。”[1]第四集,12何良俊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律”(“声”)而不是“辞”(“文”“词”),从审美的角度言,要求戏曲作品中的“辞”(“词”)能“皆入律”者,显然是一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但因其忽视了“辞”的重要性,而无法使之“文律并重”“辞法双美”。所以,何良俊所提出的“宁声叶而辞不工,毋宁辞工而声叶”,实际上就是一种“艺术至上论”。而何良俊的这种“唯艺术论”的认识,即成为了“沈、汤之争”的导火索。当时的情况是,沈璟对何良俊“宁声叶而辞不工,毋宁辞工而声叶”的认识进行了全盘接受,因而认为:“何元朗(良俊),一言儿启词中宝藏。”(《词隐先生论曲》其一)而汤显祖针对沈璟的这种认识,则予以坚决反对,认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语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3]1337由是,“沈、汤之争”即因此而始。对此,吕天成《曲品》乃略有所载:
此二公者,懒作一代之诗豪,竟成秋之词匠,盖震泽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光禄(沈璟)尝曰:“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奉常(汤显祖)闻之,曰:“彼恶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防拗折天下人嗓。”此可以观两贤之志趣矣。[1]第四集,213
沈璟认为,戏曲作品最重要的就是“律协”,其次才是“词工”,如果因为“律协”而导致了“词不工”,甚至是“读之不成句”,那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针对沈璟的这种“唯律论”认识,汤显祖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其是沈璟“恶知曲意哉”的一种具体反映,因而认为,“予意所至,不防拗折天下人嗓”。 二人之所争所论,既针锋相对,又各不相让,以至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骥德则于《词律》中对此进行了评价:
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珠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咋舌。……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吕吏部玉绳(吕天成之父)以致临川,临川不怿,复书吏部曰:“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防拗折天下人嗓子。”其意趣不同如此。郁蓝生(吕天成)谓临江近狂,而吴江近狷,信然哉![1]第四集,165
这一评价,主要是着眼于比较的角度而言。王骥德认为,沈璟严守戏曲的格律,本属正确,但其却忽视了剧本的内容;而汤显祖虽然重视剧本的内容,但却又忽视了戏曲的格律,即二者均有所偏颇。既言二人之所长,又揭二人之所短,评价颇为公正。
从总的方面讲,王骥德对于沈璟与汤显祖各自的文学才华,以及二人表现在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方面的成就,乃极为钦佩的,如认为沈璟“于曲学,法律甚精,泛澜极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殁”;而于汤显祖则谓其“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曲律·杂论》)。均敬重有加。但对于二人传奇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王骥德则于《曲律》中进行了既严肃而又一针见血的批评。如评沈璟云:
词隐(沈璟)传奇,要当以《红蕖》称首,其余诸作,出之颇易,未免庸率。……生平于声韵、宫调,言之甚毖,顾于己作,更韵、更调,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晓耳。[1]第四集,165
这一评价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沈璟的戏曲创作进行了品鉴,指出其“传奇”只有“《红蕖》称首”,其余则“未免庸率”,原因是“出之颇易”;一是就沈璟的戏曲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进行了批评,认为其一生于“声韵、宫调”等虽然“言之甚毖”,但于己作之“更韵、更调”,却“每折而是,良多自恕”,即认为其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几乎完全脱钩。又如认为“汤奉常之曲,尽是案头异书”,并说:
所作五传,《紫萧》《紫钗》第修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然无奈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类,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又视元人别一溪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使其约束和鸾,稍闲声律,汰其剩字累语,规之全瑜,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1]第四集,160
这是依汤显祖戏曲作品的创作时间所进行的评价,认为其“五传”虽具有后来者居上(即愈写愈佳)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语多琐屑,不成篇章”“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剩字累语”颇多、声律不协等,若能对此一一改正,则其传奇即“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既进行了批评,又寄予了希望。
在“本色与文采”方面,虽然沈璟与汤显祖都崇尚“本色”*沈璟与汤显祖对“本色”的崇尚,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多有涉及,如认为沈璟“《双鱼》而后,专尚本色”,汤显祖“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本色)三昧”等,即皆为其例。为省篇幅,以下只对王骥德之于二人“本色”的批评略作讨论,特此说明。,但二人对“本色”的认识却是颇具区别的。“本色”与“文采”相对而存在,因之,沈璟乃认为,那些非“文采”的“庸拙俚俗之曲”等,都极为“可爱”,都属于“本色”的范畴。王骥德则就沈璟的这种认识,提出了极严肃的批评:
词隐……至庸拙俚俗之曲,如《卧龙记》[古皂罗袍]“理合敬我哥哥”一曲,而曰“质古之极,可爱可爱”。《王焕》传奇[黄蔷薇]“三十哥央你来”一引,而曰“大有元人遗意,可爱”。此皆打油诗之最者,而极口赞美,其认路头一差,所以己作诸曲,略堕此一劫,为后来之误甚矣。不得不为拈出。[1]第四集,160
王骥德认为,沈璟对那些属于“打油诗之最”者“极口称美”的举措,完全是对“本色”的一种歪曲,为避免贻误后学,故乃将其《卧龙记》等作中的“庸拙俚俗之曲”一一拈出。汤显祖对“本色”的认识,由于较沈璟要高明许多,故而为王骥德大加称道,认为“其掇拾本色,参诸丽语”,颇具“境往神来,巧凑妙合”之特点,并说“于本色一家,亦唯是奉常(汤显祖)一人”(《杂论第三十九下》)。一批评,一称道,则王骥德之于沈、汤二人“本色”的评价,泾渭之分明,于此即可见其一斑。
而值得注意的是,王骥德通过对“沈、汤之争”的评判,其于“词与法”“本色与文采”的认识,亦因此而得以充分体现,此即“本色与文采”兼用,“法与词两擅其极”。王骥德的这一认识,不仅纠正了两家的偏颇,而且使之辩证统一,相互兼顾,极具戏曲学的审美特点,而且也丰富了其戏曲认识观的内涵,因而颇值称道。
三、对南戏声律学的创建
在王骥德《曲律》问世之前与之时,专论南戏的戏曲论著,主要有徐渭《南词叙录》、蒋孝《南九宫谱》、沈璟《南词韵选》、吕天成《曲品》等,但这些论著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都不曾对南戏(曲)的声律进行过具体研究,更无以使之与“学”相关联者。声律之学,虽有诗、词、曲之分,但其基本点则是一致的,即三者都讲究四声、平仄、对仗、用韵、字法、句法等,所不同的是,其各有因体裁之异而产生的具体要求之别,如近体诗只能押平声韵,词、曲则不仅可押仄声韵,而且还可平、仄声通押,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曲作为一种艺术品类,虽然有散曲与剧曲之分,但就其声律而言,二者实则是甚为一致的,因为一部剧曲无论有多少折或者多少本,都是由若干套数(宫调)所组成,所以,散曲(不含小令)的声律要求,也就自成为剧曲的声律要求。
王骥德《曲律》所论曲之声律,虽然是北曲与南曲均有所涉,但南曲(戏)的声律却为其论述的重点,而正是因了这一重点,才使得其成为专论南曲声律的第一书。《曲律》全书四十节,与曲之声律相关者,主要有“论宫调第四”“论平仄第五”“论阴阳第六”“论韵第七”“论闭口字第八”“论务头第九”“论声调第十五”“论句法第十七”“论字法第十八”“论衬字第十九”“论对偶第二十”(以上卷二)“论用事第二十一”“论险韵第二十八”“论尾声第三十三”“杂论第三十九上”(以上卷三),以及卷四之“杂论第三十九下”,共十六节,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二。这一实况表明,《曲律》之于曲的声律,乃是相当重视的,而此,也是《曲律》之所以将书名取为“曲律”的重要原因。虽然,从汉语格律学的角度讲,“论句法第十七”“论字法第十八”“论衬字第十九”“论对偶第二十”“论用事第二十一”等,乃皆属于格律的范畴,但其于“律”却是多有关联的,因之,将其归之于声律之“律”者,也就并无大碍。所以,从总的方面讲,《曲律》对“律”之所论所析,实际上就是对“南戏声律学”的一种创建,目的则是为了使南戏的法度规矩,更具有声律体系方面之特点。
在上所列举之十五节“曲律”中,“论平仄”“论阴阳”“论韵”“论声调”“论句法”“论字法”“论衬字”“论对偶”“论用事”,则为其“律”之关键所在,故王骥德于其之所论所述,不仅皆具体细致,而且深刻独到,锱铢必较。下面以“论平仄”“论韵”为例,以窥王骥德创建“南戏声律学”时所获成就之一斑。在“论平仄第五”一节中,王骥德于论南曲之入声时,乃如是写道:
北音重浊,故北曲无入声,转派入平、上、去三声,而南曲不然。词隐(沈璟)谓入可代平,为独洩造化之秘。又欲令作南曲者,悉遵《中原音韵》,入声亦止许代平,余以上,去相间,不知南曲与北曲正自不同,北则入无正音,故派入平、上、去之三声,且各有所属,不得假借;南则入声自有正音,又施于平、上、去之三声,无所不可。大抵词曲之有入声,正如药中甘草,一遇缺乏,或平、上、去三声字面不妥,无可奈何之际,得一入声,便可通融打诨过去,是故可作平,可作上,可作去;而其中作平也,可作阴,又可作阳,不得以北音为拘:此则世之唱者由而不知,而论者又未敢拈而笔之纸上故耳。[1]第四集,105-106
这段引文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王骥德论南曲之平仄,是与北曲之同类情况进行比较后而言,因之结论可信;其二是在对沈璟“谓入可代平,为独洩造化之秘”予以肯定的同时,于其所主张的“悉遵《中原音韵》,入声亦止许代平”的认识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应根据南方语言有别于北方语言的实况,以保留入声字在南曲中的独立地位;其三即认为入声字在南曲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缺,因为其能起到调和声调、声律的作用。综此三者,可知王骥德之“论平仄”,完全是着眼于南曲(戏)的实际情况以为,这对于南戏剧本的创作而言,显然是极具助益的。
南曲的用韵,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声律学内容,故王骥德在“论韵第七”中,对其进行了深邃而又独到的论述。“论韵”之所论所析,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指出“独南曲类多旁入他韵”的弊端;二是认为南戏之“更韵”不可取;三是认为何良俊对《西厢记》“失韵”所“訾”不当;四是对周德清《中原音韵》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五是主张南曲应用“南韵”而非“北韵”;六是对沈璟“欲别创一韵书”的举措予以赞许。其中,又以第四、第五之所论尤为重要。王骥德对周德清《中原音韵》的批评,所涉亦相当广泛,如认为:“韵中略疏数语,辄已文理不通,其所谓韵,不过杂采元前贤词曲,掇拾成编,非真有晰于五声七音之旨,辑于诸子百氏之奥也。”这是指周德清未能从“五声七音”的角度编纂《中原音韵》,而只是“杂采元前贤词曲,掇拾成编”而已。如又认为:
周江右人,率多土音,去中原甚远,未必字字订过,是欲凭影响之见,以著为不刊之典,安保其无离而不叶于正音哉!盖周之为韵,其功不在于合而在于分;而分之中犹有未尽然者,如江阳之于邦王,齐微之于归回,鱼居之于模吴,真亲之于文门,先天之于鹃元,试细呼之,殊自径庭,皆所宜更析。而其合之不经者,平声如弦、轰、兄、崩、烹、盲、弘、鹏,旧属庚、青、蒸三韵,而今两收东离韵中。[1]第四集,111
举出具体的例子以进行批评,表明《中原音韵》确实是存在着“而分之中犹有未尽然者”之弊端的,而其“合之不经者”,亦如是。对《中原音韵》类似之批评,在“论韵第七”中还有很多,兹不具述。这些例子表明,《中原音韵》作为一部“作北曲者守之,兢兢无敢出入”的韵书,其无论是“合”还是“分”,都是存在着许多问题的。正因此,王骥德即根据南曲(戏)的语言特点与创作实况,提出了“南曲当用南韵”的主张。认为:
且周之韵,故为北词设也;今为南曲,则益有不可从者。盖南曲自有南方之音,从其地也,如遵其所为音且叶者,而歌龙为驴东切,歌玉为御,歌绿为虑,歌宅为柴,歌落为潦,歌握为杳,听者不啻群起而唾矣!……今之歌者,为德清所误,抑复不浅。[1]第四集,112
其中的“盖南曲自有南方之音,从其地也”云云,不仅是一种很有见地的认识,而且还由此催生出了一部专供南戏创作之用的《南词正韵》。所以,王骥德于“论韵第七”之末乃认为:“余之反周,盖为南词设也。而中多取声《洪武正韵》,遂尽更其旧,命曰《南词正韵》,别有蠡见,载凡例中。”在明代万历前后众多的戏曲论著作者之中,能如此而“为南词设也”,王骥德则堪称“南词第一人”。
四、南戏创作与舞台表演
《曲律》自“论剧戏第三十”至“论讹字三十八”,共用了九节的篇幅对“剧戏”进行了论述,其所论又可大致分为两部分,即一为剧本创作,一为舞台表演,且其几乎皆以南戏为主。所以,这九节的内容,即成为《曲律》中的“南戏作法论”与“南戏表演论”,而其中,“南戏作法论”又乃为大端。
《曲律》论南戏之作法者,主要有“论剧戏第三十”“论引子第三十一”“论过曲第三十二”“论尾声第三十三”“论落诗第三十六”“论讹字第三十八”,共六节,表明王骥德对南戏的做法乃是相当重视的。综观这六节之所论,其实际上就是指如何在剧本中处理好“剪裁”“锻炼”“引子”“过曲”“尾声”等方面的问题。从文学写作学的角度审视,“剪裁”与取材密切相关,“锻炼”则是指对语言的烹炼,但王骥德之所论,却是将其与南戏的“各人唱”互为结合的。因而认为:
各人唱则格又有所拘,律有所限,即有才者,不能悉肆于三尺之外也。于是:贵剪裁,贵锻炼——以全帙为大间架,以每折为折落,以曲白为粉垩、为丹艧;勿落套,勿不经,勿太蔓,蔓则局懈,而优人多删削;勿太促,促则气迫,而节奏不畅达;毋令一人无着落,每令一折不照应。传中紧要处,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又用宫调……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作可也![1]第四集,137
这段文字之所论,虽含有表演的成分于其内,如“毋令一人无着落,每令一折不照应”等,但更多的则是关于南戏剧本写作所应注意的事项。在王骥德看来,“北剧仅一人唱”,而南戏则为“各人唱”,因之,南戏的剧本即应根据这一实际情况,进行多人物唱词的写作,且应与“宫调”“当行”“本色”等相关联,否则,所写就会成为“案头之书”,或者“张打油”之类的俚俗诗。又如“论引子”一节:“盖一人登场,必有几句紧要话说,我设以身处其地,摹写其似,却调停句法,点检字面,使一折之事头,先以数语该括尽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谛。《琵琶》引子,首首皆佳,所谓开门见山手段。”所谓“引子”,就是“一人登场”后所说之“紧要话”,其于南戏的作法则称之为“开门见山手段”。王骥德认为,“引子”写作的关键点,是要求作者“设以身处其地,摹写其似,却调停句法,点检字面使一折之事头,先以数语该括尽之”,即既要求“摹写其似”,又要做到言简意赅,便于表达。凡此,均为南戏剧本写作之应注意者。
据上引“论戏剧第三十”之所言,北剧是“一人唱”,南戏则为“各人唱”,此则表明,南戏的舞台表演较之北剧而言,乃是要复杂许多的,所以,王骥德在《曲律》中即对南戏的有关表演之况进行了讨论,此即“论宾白第三十四”“论插科第三十五”“论部色第三十七”三节。这三节之所论,依序为南戏的“宾白”“插科”与“部色”,且各具特点。如“论部色”一节,作者先引任蕃《梦游录》、陶宗仪《辍耕录》、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之所载,对北剧的“部色”进行了描述,然后则针对南戏的表演实况,就南戏的“部色”进行了介绍。认为:
今南戏副净同上,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装孤。……今南戏副净同上,而末泥即生、装孤即旦,引戏则末也。一说:曲贵熟而曰“生”,妇宜夜而曰“旦”,末先出而曰“末”,净喧闹而曰“净”,反言之也;其贴则旦之佐,丑则净之副,外则末之余,明矣。……今之南戏,则有正生、贴生(或小生)、正旦、贴旦、老旦、小旦、外、末、净、丑(即中净)、小丑(即小净),共十二人,或十一人,与古小异。古孤即装官,《梦游录》所谓装孤即旦,非也。[1]第四集,142-143
“部色”一词,唐宋时期指的是两种音乐体系,即“乐部”与“执色”,此之所言,则为戏曲中的人物角色。在朱明一代的戏曲论著中,对南戏的人物角色予以如此关涉者,《曲律》之“论部色第三十七”堪称第一文。其中的“今南戏”云云与“今之南戏”云云,为王骥德将南戏“部色”与北剧“部色”比较后之所言,自是真实可靠。而“古孤即装官,《梦游录》所谓装孤即旦,非也”的认识,则是对《梦游录》关于“装孤即旦”所做的订正,颇令人信然。由是而观,可知《曲律》对南戏“部色”之所论,于南戏的角色定位与舞台表演,不仅具有较为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戏曲史料学价值。
南戏的剧本创作与舞台表演,与北剧相比,虽然有着某些方面的相同,但更多的则是相异,对此,王骥德自是十分清楚的,故乃于《曲律》中以九节的篇幅论述之,且不乏灼见。正因此,《曲律》的问世,对当时的南戏创作与其后的戏曲学研究,以及明代南戏批评的理论建构等,都将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
[1]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八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汤显祖,著.徐朔方,校笺.答吕姜山[M]//汤显祖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李法惠]
2016-06-10
王辉斌(1947—),男,湖北省天门市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佚学研究与乐府文学批评。
I207.37
A
1002-6320(2016)05-00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