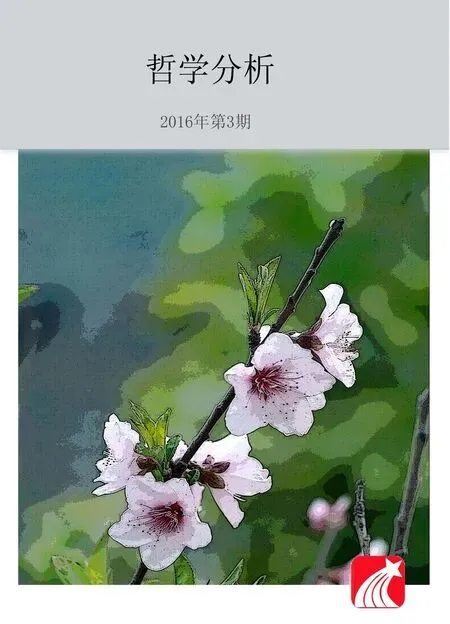身体意识:串联现象学、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的博罗米恩结
——兼评陈巍著《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
陈劲骁
身体意识:串联现象学、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的博罗米恩结
——兼评陈巍著《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
陈劲骁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曾以“博罗米恩结”(nudborroméen)来描述其所阐述的想象界(l’imaginaire)、符号界(lesymbolique)和实在界(leréel)三者之间的拓扑学结构,并以“核心症状”(sinthome)作为串联起前三者的关键第四环。根据他的观点,一个博罗米恩结至少需要三个圆环组成,但这样的基本结构并不牢固,其中任意一个圆环的脱落都会使整个博罗米恩结散架。拉康用这一诗化的隐喻意图说明他的精神分析主体性观点: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主体,但任一界域的缺席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主体性的崩塌,即产生精神病。在拉康看来,锁住主体的博罗米恩结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在此基础上套上第四环,即核心症状,以串联和加固由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组成的主体的拓扑学结构*需明确的是,这里的症状应严格区分于临床心理学意义上的症状,它意指一种主体享乐(jouissance)的核心。因此,分析的结束并非对症状的消除,而是分析者真正识别自身的核心症状。。
这一饶有趣味的精神分析式的隐喻同样适用于描述当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相互摩擦、相互碰撞的壮烈景况。现象学和精神分析作为人文哲学的突出代表,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热点和前沿的神经科学一直被认为是无法兼容、分庭抗礼的矛盾学科。相较于科学,哲学被认为无法量化和标准化;相较于哲学,科学被认为过于机械化而缺少了应有的人文关怀。相互的攻击挞伐使得知识的博罗米恩结随时面临坍塌的危险。
事实上,建立起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连接这种做法早不新鲜,但往往都停留在对彼此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借鉴和使用,每当涉及对某个共同问题的集中讨论,哲学和科学两大阵营就往往会由于彼此立场和背景的差异而无法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沟通交流。那么,哲学和科学是否有进一步建立联结的空间和区域?又或者说,是否存在一个能够同时串联起现象学、精神分析以及认知神经科学这三门学科的博罗米恩结?对此,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巍博士的新著《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给出了部分解答。本书以意识问题为核心,在现象学和神经科学之间搭建了一座坚固的桥梁。然而,笔者认为,如果能将这种意识进一步发展为一种身体意识,那么,以身体意识为中心,我们或许就能够找到一个真正串联起现象学、精神分析以及神经科学组成的博罗米恩结的第四环,从而实现哲学和科学之间的一次全新的沟通对话。
一
事实上,哲学与科学自诞生始就不是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早在古希腊时期,无论是泰勒斯、德谟克利特,还是亚里士多德,其哲学思考无一不是指向世界的本原和宇宙万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的知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考中早就孕育了现代科学精神的种子。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哲学和科学这两门“本是同根生”的学科之间的分庭抗礼,相互挞伐?这一“因缘”从“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一哲学基本概念问世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悄然埋下。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形而上学这一概念,旨在在物理学(physics)之外分离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形而上学。正如《易经·系辞》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物理学面向的是人的感觉经验,是上手(zuhanden)的器具(Zeug)。它是一种“还原论”(reductionism)的思想进路,简言之,万物必须还原到一个不可分的,最后的单元或者最小的颗粒,德谟克利特将其命名为“原子”(atom)。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还原论路径基本上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路径,是一种朴素的自然哲学。
在追问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形而上学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它不是在时间或空间上对具象的事物进行回溯或还原,而是采用一种抽象的路径来直接追问事物的本原,致力于剥离出一切经验现象背后的本质,亦即胡塞尔所谓的“纯粹逻辑”(reinelogik)。这是一种追求和论证超验的“存在”即超越经验的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本体论”(ontology)。因此,形而上学立足的前提条件是,一切现象之外都有一个终极的实在或本体,而世间万物都是这个永恒、终极的本体派生出来的产物。
经验与超验,现象与本质的区分不仅造成了哲学史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还直接诱使了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分离出来,乃至在某种意义上取代哲学重新成为衡量世界运作的真理和标准。随着黑格尔将绝对精神发展至顶峰,哲学的使命也似乎一度走到了尽头——既然对事物的描述可以得到更加精确的经验数据支撑,那么大堆庞杂的哲学本体理论存在的意义何在?哲学家们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要不就抛弃黑格尔而重新回到康德,重新为现象界和物自体划上一条严格的界线,要不就另辟蹊径,重新开辟一条非理性的哲学道路。前者随着不断发展逐渐衍生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不同形态,在语言逻辑的层面上捍卫着现代科学,成为检验科学命题意义和价值的一道审查机制。后者则显现出一种更为蓬勃的姿态,对非理性的拓荒让他们重新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哲学疆土。无论是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还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抑或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无一不在昭告着哲学精神的重新回归——至少在那些科学尚无法解释的混沌领域,哲学还有着无可替代的解释效力。
然而,在科学与哲学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人仍怀着哲学与科学一脉相连的美好愿景,即便是将潜意识理论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弗洛伊德,也终生向往着精神分析走向科学化的一天。在他看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是能够相互兼容的,他在《科学心理学大纲》(ProjectforaScientificPsychology)一书详细论述了这种观点。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致力于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即“用可规定的物质粒子的定量决定状态去描述心理过程。”*S. Freud, “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 inTheStandardEditionoftheCompletePsychologicalWorksofSigmundFreud, edited by J. Strachey Vol.I, London, UK: Hogarth Press, 1966, p.295.在这个观点中,弗洛伊德凭借其天才般的直觉已经隐然认识到了神经元存在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由于其所处的年代神经科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足以对一般心理现象进行客观描述,因此弗洛伊德并没有找到正确建立起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有机联系的有效途径,其生前构建心灵的神经学模式的尝试也并没有成功。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弗洛伊德的天才构想正在逐渐走向现实*神经精神分析已于1999出版学术期刊《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Neuropsychoanalysis),并于2000年成立了国际性的学术机构“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协会”(The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oanalysis Society)。。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仅在各自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开始意识到了跨学科交流的必要价值,顺应于这种时代潮流,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之间也开始尝试相互沟通对话,神经精神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便是由此催生出的一门新型学科。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哲学运动中,还有另一支哲学大军显得异常瞩目:它脱胎于现象学,并同样吸收了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澄清并回答当代认知科学的如下困惑:我们如此丰富绚烂的意识经验(conscious experience)或心智生活(mental lives)是如何从一小块果冻状的大脑组织的神经冲动中涌现而来的?它们究竟是在大脑中的何处产生?又是以何种方式出现?如何借助现象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洞悉、描述并解释我们的主观经验或感受本身?一种精心打磨的(fine-grained)现象学分析如何有效地融入那些以探索大脑产生意识经验为目的的神经科学研究之中?又如何将其运用于意识经验障碍的干预与治疗之上?这种将现象学分析融入神经科学实验的做法能否拓展到对主体间意识经验的考察上,从而为理解他心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强健认识论立场?最终,这一神经科学与现象学联姻的产物能否有效地救治“身心问题”(body-mind problem)这一笛卡尔时代遗留至今的形而上学难题?刻画上述宏伟蓝图的新式学科被智利著名认知科学家瓦雷拉(F.Varela)命名为“神经现象学”(Neurophenomenology)。
二
神经现象学和神经精神分析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传统人文科学对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一次响应,都试图用认知神经科学来弥补传统意识哲学在解释身心问题上的短板和局限——最大不同之处或许仅仅在于,神经现象学面对的是纯粹意识,而神经精神分析面对的是压抑在意识之下的蓬勃的潜意识。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现象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亲密联系。法国当代著名现象学家Michel Henry曾专门撰文论述现象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现象学和精神分析作为当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运动,能够共同激发对人类关系的多重性反思*M. Henry, “Phénoménologie et Psychanalyse”, inPsychiatrieetExistence,edited by P.Fédida Grenoble: Millon, 2007, p.95.。而另一位法国现象学家,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教授Guy-Félix Duportail则认为,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具有相同的拓扑学结构,而肉身(chair)则是它们汇聚的场所。据他所言,主体性的内在图式通过肉身这一媒介在外在世界得以显现,而其显现的方式被拉康称之为“核心症状”,梅洛庞蒂则将其命名为“复杂概念”(implexe)*G-F. Duportail,AnalytiquedelaChair. Paris: Cerf, 2011, p.34.。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出于对主体意识共同关照,现象学和精神分析的最终落脚点都会停留在身心的关系问题上。事实上,胡塞尔从研究纯粹意识的逻辑结构转向关注生活世界的现象学也能体现这一点,而梅洛庞蒂致力于对身体知觉的现象学研究则是最好的佐证。在中文语境下,身体(corps)和肉身的概念往往容易被混为一谈,但两者应该得到明确区分。肉身对应于德文leib一词,意指活生生的身体,仅应在身体的物质性层面使用;身体对应于德文cörper一词,它更常用于指代主体对自身身体在心理层面的感知,因而是一种身体意象(imageducorps)。在传统的哲学观点中,物质性的肉身一直被认为是精神的桎梏和枷锁,因而往往得到贬抑,即便在文艺复兴时代得到短暂的颂扬,也不免沦为感觉主义的肉欲狂欢。而身体由于被误认为等同于肉身,因此也“诛受牵连”,长久地遭到了遗忘和忽略。
当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将心理主义从现象学中驱逐出去的那一刻起,身体意识的概念也正式宣告回归。胡塞尔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可以显示其对身体意识在现象学地位的摸索和权衡——尽管他这种探索并不是直接立足于身体概念本身,而是通过“生活世界”和“意向性”等概念来引入身体意识。胡塞尔认为,为了面向事物本身,必须悬置一切成见,这也就意味着意识必须意向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这种意向性是意识的本质特征。同时,意识在指向某个对象的同时必须立足于某个意识主体,这意味着,该意识主体本身也具有意向性的结构。但是,先验性的意识和经验性的身体之间始终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如何从封闭的自我世界走向开放的生活世界是胡塞尔主义现象学无法克服的最大难题。当然,胡塞尔已经隐约意识到了身体和肉身在概念上的差异性,但他却并没有明确指出意识的主体就是身体本身。现象学的身体意识是由梅洛庞蒂最终完成的。为了回归到前逻辑的意义发生地,即身体知觉,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对唯理性主义展开了强烈批判,并认为意识应该被还原到先于任何判断的感觉事物本身的意义上。梅洛庞蒂赋予了身体两种不同的意蕴。其一,暧昧(ambiguïté)的身体。具体来说,身心关系并不是笛卡尔所描述的那种身心平行论,而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暧昧关系,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为此梅洛庞蒂提出了“身体图式”(schémacorporel)这一概念,以试图消除长久以来横贯于身体和心灵之间的鸿沟。其二,“交互身体性”(intercorporéité)的身体。具体而言,主体能够象征化自身的身体,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身体与世界相互交融,从而接触和理解这个世界,发现世界的意义。这种观点相较于胡塞尔现象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胡塞尔虽然也曾强调过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在身体构建主观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却始终没有将身体摆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因此,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识的交互主体性。相反,梅洛庞蒂则将胡塞尔所谓的纯粹意识严格限制在主客体的关系之外,并用身体的意向性取代意识的意向性,从而用交互身体性取代交互意识性。在这个层面义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现象学。由此,身体—意识的鸿沟也终于被打破。
三
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身体和意识的关系也始终困扰着精神分析家和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首先试图抹除身体和心灵的界限。在《冲动及其命运》(pulsionsetdestindespulsions)一文中,弗洛伊德认为,冲动(pulsion)是横贯于身体和心灵的边界,它始终流通游走于身体和心灵之间*S. Freud,PulsionsetdestindesPulsions, Paris: Payot, 2002, p.109.。拿躯体性神经症来说,某些躯体症状实际上是由于主体心灵受挫,流动于心灵的冲动在身体上做出破坏性举动,以试图找到合适的出口。因此,身体实际上是负荷冲动流动的场所,同时具有心理和肉身层面上的意义。而在另一位精神分析家拉康看来,冲动的失缰借由各种症状(symptme)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本身就是主体存在的一种常态。简单来说,人人皆有症状。因此到了拉康那里,身体和心灵的边界实际上已经基本被抹除,身体不再仅仅是承载主体冲动,或者说是主体表达欲望的肉身场所,它本身就是主体存在于世的外在表征。
无论是现象学在意识问题上对身体—意识关系的分析,抑或是精神分析对潜意识冲动在身体上的症状表现的探索,我们都可以看到,身心关系在当代哲学中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哲学显现的那样相互拮抗,难以调和,而呈现为一种渐趋融合的趋势。人们也渐渐认识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交流也并非不同主体之间的生硬碰撞,而是存在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主客体之间绝非楚河汉界那样界限明晰。同时,身体也不再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对象抑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各器官的简单组合,不仅身体的各部分得以相互交融,身体与世界的视域也得以相互融合,从而成为一种活的整体。从此,身体不再是柏拉图和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那个封闭不动的阿基米德点,而能够在时间的长河和空间的旷野中不断铺展、流动。
然而问题在于,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对身心间鸿沟的消解是否能够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一种共识?又或者说,这种共识立足的基点在哪里?至少在哲学和科学长期隔离对立的漫长历史岁月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各自发展使双方都意识到,只有彼此“握手言和”,才有可能弥补自身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和不足。或者说,康德在现象和物自体之间划分的界限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绝对孤立,至少在某些领域,例如身体意识问题,是存在相互沟通对话的可能的。神经现象学和神经精神分析都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中孕育而生的全新学科,旨在通过现象学和精神分析使用的第一人称方法与认知神经科学与神经动力学等第三人称方法有机结合的方式来重新探索人类的意识经验和潜意识经验。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转变成为,为现象学和精神分析插上神经科学的翅膀是否必要?又是否可能?
事实上,身体—意识的关系问题从来都是认知科学的热点研究领域。科学认知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离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到“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过程。传统认知主义认为认知是可计算的。具体来说,大脑的认知过程与计算机的符号加工过程在功能上是类似的,都表现为一种“计算”的过程。大脑和计算机实际上都只是一种对符号和信息的处理、操纵与加工的形式系统,而区别仅仅在于两者的结构和动因不同。具体来说,计算机通过人工设定的逻辑规则进行相应的符号运算,大脑认知过程的运作则来自于其先天或后天的各种理性规则。这种观点的最大危害在于其抹杀了身体在主体认知过程中的重要功能。根据这种观点,主体认知的运作虽然必须通过身体才得以展开,但其功能却始终与身体相互独立。作为第二代认知主义的具身认知则将身体的概念重新引入到认知过程当中。具身认知认为,心智和认知必然以一个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因此,最初的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身的心智,而最初的认知则始终与具身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载《科学学研究》2006年第2期。。即,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身体形式积极参与到主体的感觉经验的建构当中。诚如Shapiro所言,具身认知所强调的是身体在有机体认知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L. Shapiro,EmbodiedCogn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338.。具体认知的观点很明显打破了第一代离身认知主义的黑箱传说,而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呼应着现象学和精神分析的身体意识观点。我们也能因此大胆断言,现象学、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之间的对话是完全必要,也是可能的。
四
陈巍博士在这本书中细致地追溯了神经现象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试图找到神经科学与现象学汇聚的结点。作者显然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意识的概念在现象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中的特殊位置,而在本书的开篇就将被心理学“扫地出门”的“意识”重新“请回”了认知心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在作者看来,意识问题的研究远没有随着行为主义操作化定义的兴起而丝毫显得过时,相反,它应该是为人类所关注的永恒主题。作者的这种考虑显然是基于意识问题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复兴盛况。芬兰意识科学家Revonsuo曾经对意识问题的价值给出一种精辟的解释:“研究意识是研究存在的本质,但却并非是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研究的那类存在——因为它们研究的是诸如原子、星系、海洋、细胞、时空等客观存在——而是研究我们存在的根本性质,我们的主观存在,作为一系列主观经验之我们的生活。”*A. Revonsuo,Consciousness:TheScienceofSubjectivity, Hove and London, UK: Psychology Press, 2010, p.20.这种鲜活的主观经验与主体的每一个意识活动都息息相关。例如当我得知亲人去世时伴随而来的胸口沉甸甸的压抑感。由此看来,意识问题的价值性在于它具有的浓厚的人文关怀,研究意识同时也是在叩问存在本身。
然而,科技的发展史同时也是存在的遗忘史。科学技术的极速发展不仅在物质的层面上为人们提供了更加精细的生活模式,还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模式。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一种对确定性的服从和敬畏。事实上,无论是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古典哲学,又或是从中脱胎而来的现代自然科学,无一不是将理性置于感性之上,将概念凌驾于经验本身。在他们看来,经验是零碎的、片段的、不可靠的,对感性经验的依赖容易束缚住理性的光辉和灵魂的澄明。这种概念化的思维模式在一方面对现代科学实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确定性和精确性的保证,另一方面也将包括意识在内的主体经验打入了更深的囚牢。借助意识,人们能极大地突破物质肉体所能感触到的既有时空,然而其无定形的流动性特质同时也意味着它绝不会受概念框架的掣肘,因而也无法得到操作化定义的精确描述。
因而,意识问题的研究无疑成为现代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大难题,甚至成为诸多研究者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因此,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意识的神经科学的理论或取向都在意识主观性这一“困难问题”(hard problem)面前折戟臣服,这诱发一些研究者反思,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正在敦促当代认知科学必须“理解经验与大脑中的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D. Platchias,PhenomenalConsciousness: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ExperienceandNeuralProcessesintheBrain, Durham: Acumen, 2011, p.7.。换言之,“当代认知科学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即是构建一个能同时阐明意识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及其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纲领”*E. Thompson, A. Lutz & Cosmelli, “D.Neuro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for Neurophilosophers”, inCognitionandtheBrain:ThePhilosophyandNeuroscienceMovement, edited by A. Brook & K. Akins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0.。
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瓦雷拉等提出了“神经现象学”的全新方案。作者准确地从定义上对神经现象学进行了界定。在作者看来,神经现象学是一项联合了神经科学和现象学,在强调人类心智的具身—生成条件的基础上,旨在通过现象学还原、内省与佛教沉思训练等第一人称方法(first person methods)与认知神经科学与神经动力学等第三人称方法(third person methods)的有机结合来探索人类意识经验或主观经验的跨学科运动*陈巍、郭本禹:《神经现象学运动二十年:辨析与厘定》,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神经现象学的横空出世无疑昭告了意识主观性向认知科学的重新回归。而本身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以研究意识经验问题为核心的现象学,由于插上了第三人称研究方法的翅膀,其原本面对科学的四面夹击而自顾不暇的尴尬境地也随之缓解。
在本书中,作者正是借助意识这一可靠的支点,试图架设一条从现象学通往神经科学的路径。然而,意识是否能够因此继续成为串联起现象学、精神分析以及神经科学这三门学科的一个更为结实的博罗米恩结?笔者认为并不足够。事实上,梅洛庞蒂已经对现象学的未来发展出路做出了一个十分明晰的指示,即意识最终的落脚点在于身体。精神分析对于症状和身体关系的研究也在另一个维度上呼应着这一点。因而,笔者据此认为,身体意识才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串联起现象学、精神分析以及神经科学的博罗米恩结。
五
实际上,本书在探索神经现象学的具身—生成取向时已经隐然埋下了身体意识的种子。作者认为,神经现象学进一步将认知神经科学的具身认知论发展成为具身—生成论,并用具身—生成取向来概括神经现象学的心智观。这种概括方式充分说明作者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区分“具身”和“生成”(enactive)之间差异的重要性。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作为具身与生成认知的提出者的瓦雷拉,或是Thompson, Lutz都经常在很多场合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如“生成认知科学”或“具身认知科学”。因此,具身认知与生成认知在一些场合往往被等同起来,或者说生成认知是由具身认知进一步发展而来的*Menary, R.RadicalEnactivism-Intentionality,PhenomenologyandNarrative.FocusonthePhilosophyofDanielD.Hutto,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57.。作者很明显意识到了这一误区,他特别强调,要从严格意义上区分开认知的“具身”与“生成”的内涵。这是因为“具身”与“生成”两个概念各自侧重强调不同的方面。“具身”侧重对大脑、身体与环境在认知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静态地描述。“生成”则侧重解释具身认知活动的产生与运作的动态机制*陈巍、郭本禹:《具身—生成的认知科学:走出“战国时代”》,载《心理学探新》2014年第2期。。
然而,作者的真正问题在于,“具身—生成”的概念还不足以指出身体意识在意识领域中的特殊位置。换句话说,一个寓于身体的意识仍然停留在普遍的主体意识的层面上,只不过更加明确了身体作为意识的寓所而已。但实际上,精神分析在身心关系的问题上早已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完全抹除了身体和意识的界限。也就是说,身体不再只是意识(在精神分析的话语中,这种意识是一种流动不居的“冲动”)寓居的场所,而是与意识一道构筑起了主体的存在。因此,意识只能充当连接现象学和神经科学的桥梁,却不足以串联起现象学、精神分析和认知神经科学这三门学科。而真正抹除了身体和意识界限的身体意识才能堪此大任。我们也可以说,精神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现象学从梅洛庞蒂重新带回到了海德格尔,并重新找到了被遗忘的身体意识的存在。因此,这本专著的最大遗憾之处正在于,作者将现象学发展的洪流停贮在了“意识”这一被认知科学长久遗忘,却始终是传统哲学“老生常谈”的基本命题,而没有真正借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之手,彻底打通从胡塞尔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的回溯之路,从而发现“身体意识”这一足以再次盘活现象学运动的源头活水。当然,瑕不掩瑜,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本专著中,作者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即从研究人类的意识经验入手,在现象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之间开创性地搭建了一座互为裨益的桥梁。这也为探索身体意识这一串联起现象学、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的博罗米恩结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毋庸置疑,作者在书中对神经现象学的这次全面回眸不仅是对哲学传统的忠实守望,更是对科学前沿的殷切向往。
(责任编辑:肖志珂)
作者简介:陈劲骁,巴黎第七大学精神分析学院博士候选人。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认知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3JZD00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项目编号:15CBZZ02)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