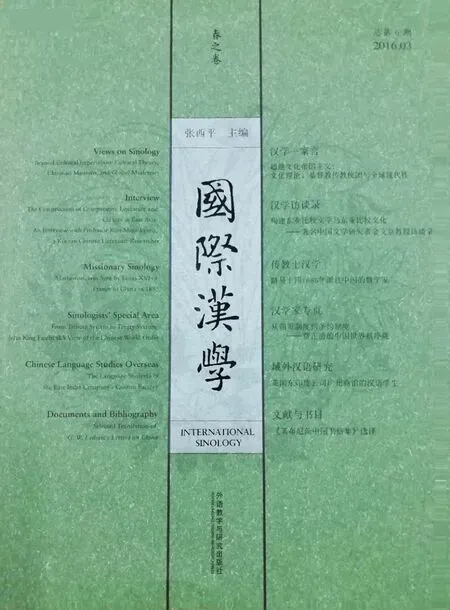从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费正清的中国世界秩序观
□ 陈国兴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在其191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描述了清代的“贡赋”制度和对外交往中的朝贡礼仪制度。他认为“贡赋”是中国早期朝代税赋的主要形式,是亚洲式政府(Asiatic government)的一个固有特点。贡物以实物,特别是粮食为主,太平天国之后,一些省份也可采取折现的办法纳贡,但是原来运送贡粮的船只费用依然摊派如故,反映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财政上的政治保守主义。他依据《大清会典》对清代的朝贡国进行了列举:周边定期朝贡的国家,南掌(Laos,即老挝)、缅甸十年一次,苏禄(Sulu)五年一次,朝鲜四年一次,暹罗(Siam)三年一次,琉球(Loochow)三年两次,安南(Annam)两年一次;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等国则不定期派来使节。他认为这些抱着开拓贸易想法的欧洲使节在华的屡次失败,源于中国人的朝贡礼仪观念,“这些使臣前来是为了朝贺和进贡的,其责任是接受命令而不是谈判订约的”。①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0, pp.31-33, 50, 43.在这里,马士显然将朝贡制度作为一种保守、落后的对外关系制度,认为它妨碍了条约制度的推行,并必然为后者所取代。但他并没有从更深层次上阐明清代对外关系中朝贡制度保守、落后的原因,也没有看到这种制度与国内贡赋制度的内在联系,因而他所做的只能算是一种粗略的研究。
在欧美学界,第一个对中国朝贡制度进行深入剖析和系统化研究的当属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费正清是从外交史研究进入中国学的,他继承并发扬了马士有关朝贡制度的研究。他认为,朝贡制度作为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基于国内儒家等级制度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延伸,与欧洲基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相比,是一种封闭、落后的外交制度,必然会在代表主权平等的条约制度的冲击下瓦解,中国的外交因此得以进入近代国际关系网络之中。费正清的这种见解成为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遭到佩克(James Peck)、柯文(Paul A.Cohen)等人的激烈批评,但他在朝贡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依然是影响至今的一种主流思潮。
一、费正清对朝贡制度的最初理解
费正清对中国朝贡制度的论述始见于他1936年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的扉页上写着“In Grateful Memory of Hosea Ballou Morse”,可见马士对他的影响之深。文章第一章论述了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前中国传统的外贸管理方式:由政府建立或授权的垄断部门控制的对外贸易,在理论上是一种与接受附属国朝贡相联系的特权。尽管中国商人、官员乃至朝廷从中获利巨大,但在官方看来仍然是一种朝贡贸易,而非平等的贸易关系。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海上朝贡贸易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中国舰队出访这些国家以建立皇帝在这里的宗主权,而来到广州进行贸易的15个国家,像暹罗、爪哇(Java)、柬埔寨(Cambodia)、婆罗洲(Borneo)、苏门答腊(Sumatra)、孟加拉(Bengal)、锡兰(Ceylon)等都具有附属国的地位,由政府在口岸设置的市舶司来监管他们的贸易和朝贡事务。1517年,葡萄牙第一次派使团来华,企图在广州开展贸易,他们给皇帝带来了礼品,因而不能说中国没有赋予他们属国地位。①John King Fairbank,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1850—1858,” D.Phil.diss., Balliol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1936, pp.1-5.
在费正清看来,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人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中仍然延续了这种传统的对外关系的观念和政策,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与这些周边属国一样,乃化外之民。他引述马士学生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的话:
中国人的确习惯上把欧洲人称为并看作是“蛮夷”,指那些“来自野蛮、不文明的国度,道德和智力有待开化的民族” ……那些有直接机会对我们的习俗和文化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把五个口岸都加在一起,在3.6亿人口中约有五六千人,除此以外,大多数都把我们看作是在道德和智力上不如他们的民族。至于那些与我们没有直接接触的中国人,我的确不记得同他们交谈过。但我同这样一些人交谈过,他们先前对我们的观念和我们对野蛮人的观念类似,当他们了解到我们也有姓氏,也明白父亲、兄弟、妻子、姐妹等不同家庭关系,或者说当了解到我们并不是像一群牛一样生活时,如果说他们没有感到惊愕,也总是觉得诧异。②Ibid., p.69.
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这种态度部分源于对西方的不了解,对西方的蔑视主要源于文化优越的传统,这种传统构成中国人生活观的一部分。在早期,中国文明周围是野蛮的部落,并不时遭到他们的围攻,这些夷狄构成了他们认识世界的一部分,有关夷狄的传统在文献和普通人的脑海里建立起来。由于中国文化中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以及中国人对这种观念的不断强化,所以面对西方的入侵,这种观念不仅得以存活而且变得更加强烈。在咸丰时期的文件里“夷”是用以指涉西方人的通用字,而且一些野蛮部落的特征也都被堂而皇之地归结到西方人身上。在中国人看来,行为缺乏理性和不可预知性是西方人类似野蛮人的一个主要特征,因此在中国的官方文件里,常可以看到“夷情叵测”“夷情诡谲”这样的字眼。另外,在中国的社会等级中商人是处于最底层的,中国人对西方人唯利是图的做法嗤之以鼻,所以条约口岸西方人昭然若揭的贪婪只能引起中国人的厌恶。此外,官员和文人学士迟钝的思维惯性也造成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和隔绝。可以说,中国文化优越的传统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极少是一种虚妄的东西,通常代表了一种最强的力量,在19世纪50年代体现为驱逐外国蛮夷的刺激性情感,但也严重妨碍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对外交往,只有像林则徐、曾国藩等少数官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所以在外交行为上中国人是“防范性”的、“不动声色”的、害怕“另生枝节”的,由此而产生的对外国入侵的担心,使清政府把对外交往主要限制在广州这个尽可能远离首都的南方城市。英国人利用条约进一步扩大贸易的想法,与中国人的这些传统观念处处抵牾,因而造成了早期条约制度的失败,而1858年建立的外籍税务司制度为双方的共治搭建了一个平台,并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的瓦解。①Ibid., pp.70-81.在这篇博士论文中,费正清主要论述了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建立,朝贡制度只是被作为一个背景,通过其中所折射出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旨在说明这种共管制度建立的艰难历程。因而,他对朝贡制度的描述更多是一种粗略的感性认识,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观点。
二、费正清对朝贡制度的界定
1941年,费正清与邓嗣禹(1906—1988)合著的《论清代的朝贡制度》(“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第2期(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 No.2),这是费正清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把朝贡制度问题抽出来,第一次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全文长达112页,共分8个部分,对清代朝贡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
文章先从四个方面对朝贡制度加以界定:
1.朝贡制度是中国早期先进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明清之际朝贡制度的制度化源于中国文化优于四夷的悠久传统,从商代起,中国文化像一个岛屿卓然于四夷,在与北方、西方的游牧民族以及与南方土著民族的接触中,中国人逐渐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中国优于四夷,主要在于文化而非政治,在于体现在儒家行为准则和文字系统上的生活方式而非武力,夷狄之所以为夷狄,不在于他们的种族和出身,而在于他们对中国生活方式的非依附性。因此,四夷要想“来化”,分享中华文明,就必须承认中国皇帝作为天子的至高无上的威仪。这种对皇威的承认显然是要通过三拜九叩的礼仪和土特产的朝贡体现出来。实际上通过这种体现了各种繁文缛节的朝贡制度,这些非中国的四夷地区在无所不包的中国政治和道德体系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2.朝贡制度在中国统治者看来具有自我防御的政治目的。在此,费正清引述了蒋廷黻的论述:新儒家的教条认为,国家的安全只能在孤立中才能实现,并规定,任何国家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都必须按照属国的方式行事,必须承认中国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即宗主国—附属国的关系,附属国必须像中国人一样接受中国的道德伦理,这样就排除了国际交往中的平等原则。这种教条不是为了征服和主宰,而是为了寻求和平和安全。此外,那种认为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利的看法是不对的,中国回赐礼品的价值要远远大于贡品,因此难怪中国19世纪晚期以前的政治家们会对国际贸易能增加国内财富的观念持嘲笑的态度。中国允许贸易主要出于两种目的:一是为了彰显帝国的慷慨,二是为了保持四夷对中国的臣服。②T.F.Tsiang, “China and European Expansion,” Politica 2 no.5, Mar.1936.A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费正清由此认为,贸易与朝贡实际上是对外关系制度的一体两面,中国统治者注重的是朝贡的道德价值,而四夷则看重贸易带来的物质价值,这种平衡使得双方都十分满意,从而维持了两国的关系。
3.在实践上,朝贡制度有着重要的商业基础。在中国与四夷的交往中,商业关系与朝贡是密不可分的。贸易是由陪伴贡使来到中国边境甚至首都的朝贡国商人来进行的,有时朝贡使团成员也充当了商人的角色。在澳门和广州,由于欧洲人过度关注商业带来的物质利益而把理应进行的朝贡礼仪忘得一干二净。
4.朝贡制度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媒介。在中国人看来,所有外交关系都属于朝贡关系,因而所有的国际交往,如果涉及同中国的关系,都必须纳入朝贡制度。中国遣使查明敌情或寻求结盟,外国使者来华谈判之类的外交事务都要在此框架下进行。如中国皇帝会遣使参加朝贡国国王的葬礼,以表达对属国的关心,同时也可以借此了解新的国王,并对该国事务施加压力。如果外国使臣在京逝世,中国会给予国葬。
其次,费正清还依据《万历会典》《大清会典》等对晚明到清代朝贡国遣使来华的周期及起伏变化、机构设置、宾礼制度等做了较为翔实的分析。明代设置了主客司负责朝贡国事务,郑和航海前后,朝鲜、琉球、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罗、西藏等地的朝贡较为频繁且呈现出周期性。1421年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与此同时随着郑和航海的结束,原来通过南海海路而来的供使逐渐减少,来自西部内陆的供使出现上升趋势,到16世纪,贡使来华的总量呈明显下降趋势。清代在明代基础上,除继续把来自东、南部的朝贡国归入主客司管理外,1638年又在原来处理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的基础上增设了理藩院,用以管理北部和西部贡国事务,仍以蒙古事务为主,也包括欧洲事务。随着清代统治者对西、北各部族的征服,这些地区的情况已不同于明代的朝贡与贸易的关系,这些地区的贡使不再充当贸易交流的角色,理藩院管辖下的这些地区成为区别于东、南朝贡国的藩部,但是理藩院在处理满—蒙关系时依然延续了传统朝贡制度的做法。
另外,费正清还论述了清代朝贡制度下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明代,在与中国的多次冲突中,葡萄牙人获得了名义上的朝贡国地位,被允许居住在澳门这个固定的地方,并可以定期到广州进行贸易;清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被局限在广州进行贸易,甚至到1858年以后也仅仅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他指出这是中国政府传统朝贡制度的自我防御心理使然。费正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这种封闭状态是被来自海洋的贸易逐步打破的。在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的帆船贸易有所发展,与中国进行帆船贸易的国家被列为互市国,因为从陆地而不是海洋发展起来的朝贡制度在中国强大的时候可以对内陆边疆的贸易进行有效控制,通过贸易的媒介使这些贸易国成为朝贡国。但是,海洋贸易由于远离边境,使中国政府很难形成有效的控制,中国消极的海洋政策也很难吸引海上贸易国愿意成为中国的朝贡国。到19世纪初,朝贡贸易被贡使以及朝贡国乃至中国商人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所利用,贸易与朝贡的连带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分裂。但是19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诸国纷纷来华寻求贸易开拓,清廷依然固执地采用这种古老的朝贡制度,加之对欧洲国家认识的缺乏,于是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时便出现了种种障碍。①John King Fairbank and S.Y.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 (1941): 135-246.
1942年,费正清再次撰文《朝贡贸易与中国对西方的关系》就朝贡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文章除了重复上述《论清代的朝贡制度》中有关朝贡制度的四个特点外,着重强调了朝贡制度的文化起源和中国人面对西方入侵时的无知与愚昧。在长期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无论是北方的游牧部落还是南方的土著对中国人的先进文化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作为这种先进文化象征的文字书写系统和儒家的行为准则,以及中国人崇高的德行、中央王国在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这些四夷无法抵御的诱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渴望更加强化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中国人对夷狄的判断也主要是通过文化而不是种族或民族的因素。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精神(spirit of culturism)。他认为这种文化主义来源于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人认为人必须顺从自然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人与自然对立的西方观念是不同的。由人与当下自然的和谐推断出现在与过去的延续性,因为每一代人都会与看不见的自然力量一起影响当下人的生活,因而便产生了敬祖的做法,于是敬祖和服从自然都构成了当下人的行为准则。皇帝作为天子是人与这种看不见的自然力量的协调者,为此他必须代表万民举行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安康,皇帝在仪式中的作用以及他高尚的德行构成了他权威的基础。孔子认为,一个人良好的德行在于他对礼仪和社会规范的遵从,即所谓臣忠子孝,当然在上天面前代表子民的皇帝必须是所有人的典范,并以此建立他的权威和影响。孔子的教条成为皇帝践行政治权威的道德基础。因此,皇帝与夷狄的关系是一种文化中心的中国与四夷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认可构成了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来化”的夷狄必须承认中国皇帝作为天子的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并通过贡品和各种礼仪体现出来,而皇帝则以“怀柔远人”的德行彰显他的宽大仁慈,在这种朝贡和怀柔的双边活动中中国皇帝统御万邦的权威得到很好的体现。
基于这样的文化主义,中国人没有兴趣了解西方,也不愿意与他们接触,作为商人的蛮夷他们不屑一顾,作为武力的蛮夷他们唯恐避之不及。因而,前来开拓贸易的西方人往往被局限在几个固定的口岸,即使在口岸也被孤立在一个封闭的区域。其次,中国政府为避免与这些西方商人直接打交道,通常由当地商人、买办、翻译人员、银行业者间接来进行,这些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交流中使用的洋泾浜英语也不利于传达思想。而传教士也因人数和传教地域的局限性,加之中国政府的禁教限制,很难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凡此种种,造成了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与愚昧,面对西方商业的入侵毫无思想准备。①John King Fairbank,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2 (1942): 129-149.
这些早期朝贡制度的观点为费正清日后条约制度的论述做了很好的铺垫。他认为,对19世纪中国的对外政策只能在传统的朝贡制度框架下才能理解,朝贡制度作为东亚的儒家世界秩序直到1842年以后才被英国的条约制度取代,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53年,费正清在其博士论文以及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一书,在该书中他把博士论文中外籍税务司制度建立这一事件推溯至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原来成为他论文结局的这个事件不再是他的焦点,而仅仅构成了西方侵入中国这个大格局中的一个环节,共管体制成为该书的核心。他已经从博士论文有关中英外交的纠葛中摆脱出来,赋予了这些事件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作为共管体制重要标志的外籍税务司制度成为了解中国过去和未来的窗口:“如同是‘使条约制度平稳地为外国人运转的润滑油’,这个机构对中西关系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重要性,而作为条约制度成功运转的关键,它又为朝贡关系的消灭和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创立铺平了道路”。②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罗苏文等译:《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费正清已经开始搭建日后闻名的“冲击—反应”框架,作为这个框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朝贡制度在这本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第二章,他从共管体制的角度对朝贡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19世纪满汉对西方作出的反应,是由一种从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继承而来,并在朝贡制度中制度化了的设想、期望和评价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结构所注定的。朝贡是一种华夷共守的制度,它是在华夷边境上由双方共同创造,并在数世纪中作为中外交往的媒介双方共同实行的制度。这种朝贡关系的意识形态在汉—满民族思想中所占据的位置,无异于民族主义和国际法在西方人头脑中所占据的位置。朝贡思想与儒家君主制那种令人惊异的特性密切相连,即夷狄入侵者常常可以承袭这种制度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只是目光短浅的西方政治学家所看到的那些东西。儒家君主制是一种独特的非民族的制度(non-national institution),虽以儒教中国的社会文化为基础,但也能为中国的反叛者和夷狄入侵者所掌握并加以利用,实际上有时他们利用得更容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中国的儒家君主制本身已成为华夷共治的制度。
面对近代西方的冲击,中国仍以这种三千年来在与游牧民族交往时形成的朝贡制度及先入之见来应对工业化的西方,显然会误入歧途,终致悲剧的发生。“虽然朝贡制度无法成功地应对西方,但这是中国唯一的防御方式,因为它是儒家君主制与外国列强打交道的既定方式”。③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23, 25.
1965年9月,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的专题研讨会,费正清于1968年把这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是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HUP,1968.)一书。书中共收录相关论文13篇,其中费正清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国的世界秩序:一种初步的构想》(“The Chinese World Order:A Preliminary Idea”)对中国的朝贡制度做了总结性的论述。他认为,中国与周围地区以及“非中国人”的关系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向外的示范,因而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在东亚形成的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与欧洲的国际关系不同,是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以中国为中心世界秩序:
可以分为三大圈:第一是汉字圈,由几个最临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即朝鲜、越南,它们的一部分古时曾受中华帝国的统治;还有琉球群岛、日本在某些短暂时期内也属于此圈。第二是亚洲内陆圈,由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从属部落所组成,它们不仅在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而且处于中国文化区以外或边缘,它们有时进逼长城。第三是外圈,一般由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包括最后在贸易时应该进贡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其他国家,以及欧洲。
中国的这种世界秩序“同欧洲那种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传统大相径庭。近代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难以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费正清在这本书中另一篇文章《中国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体系》(“The Early Treaty System of Chinese World Order”)再次考察了19世纪朝贡制度的解体,作者认为通商口岸最早为外国领事负责的特区,当最惠国条款施及所有缔约国时,清廷不再宣称居于西方人之上。在随后的20年里清朝再也无法把西方人纳入其权力体系之中,从而导致了陷入危机的朝贡制度的最终瓦解。①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一种初步的构想》,见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16—17页。
本书收录其他人的文章分别就中国世界秩序的产生、发展以及清代的状况进行了探讨。如杨联升的《中国世界秩序的历史诠释》、王赓武的《明朝早期和东南亚的关系:背景探析》、法夸尔的《满族蒙古政策的起源》、全海宗的《清代中朝朝贡关系考》、弗来彻的《中国和中亚:1368—1884》、韦尔斯的《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史华慈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过去和现在》等文章基本上都是按照费正清的上述理路来论述的。费正清在此书中提出的“中国世界秩序”的理论框架把朝贡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许多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朝贡制度”“朝贡贸易”等词语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领域的常用术语。
三、西方条约制度及费正清对条约制度的理解
在费正清文化诠释的框架中,中国在被外族统治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华夷共治(Sino-barbarian Synarchy)的国内政治架构,在清代即是满汉两头政治(Manchu-Chinese Dyarchy)的共管制度。夷族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皈依,投射到对外关系上就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而形成的等级制的朝贡制度,这是一种与西方以民族国家和主权平等为基础的条约制度截然对立的对外关系制度,朝贡制度代表了一种非理性、保守、落后的对外关系,条约制度则代表了近代理性、开放、先进的国际关系准则,因而前者构成了后者顺利进入中国的障碍。他认为,西方人(主要是英国人)要打破这种障碍,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了中西共治的折中办法,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廷的脸面,尽管它有悖于西方国际关系的概念,但可以使条约得到有效执行,“对外国人而言,海关成为一种使条约制度顺利发挥作用的润滑剂”;在清廷方面,满汉两头政治管理的惯性作法使它很容易过渡到华夷共治。但双方的看法是相互颠倒的:西方试图通过这种办法将中国纳入到民族国家和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网络中,而清廷则试图将西方纳入到它的儒家君主制的世界秩序中。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费正清把1860年之后的这种从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的过渡称之为“满—汉—西共治”(Manchu-Chinese-West Synarchy),清廷“把外国入侵者纳入其国内权力结构的手段……实在是太方便易得了。它盲目地、毫无准备地引领着中国人民进入了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崭新时代”。②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pp.464-465, 468.这样,条约制度逐步渗透并瓦解了朝贡制度,最终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费正清所谓的平等的条约制度是建立在近代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过程中诞生的国际法基础上的。1618年至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导致了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和政治共同体—王朝(dynamic realm)的分裂,居住在某一地区的人在本地区传统的语言和部族等基础上,依据新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一个个民族国家。战争催生了民族国家,国家又继续发动战争,面对欧洲战争频仍的局面,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提出了“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说,试图从中探索战争的根源以及寻求社会安宁的解决办法。他认为,人按照自己本性生活的状态就是“自然状态”,人的本性是保命(self-preservation)、自私的,总是企图无限地实现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从而导致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状态。人们为了避免战争,就必须放弃企图占有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通过相互契约,把大家的权利交给一个人,把大家的意志变成一个意志,通过一种公共权力机制来实现管理和保命。这个被人们通过契约赋予权力的人是君主,这不同于原来古典时期的君权神授→君主→臣民的纵向共同体,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横向缔约权利向君主的转让。君主代表的是人们的集体意志,他就是国家的本质,霍布斯把这样的国家比作《圣经》中力大无比的海兽“利维坦”。国家的建立,结束了自然状态。在他看来,每个人之上都有一个超越一切的权力—国家政权,可以使契约获得有效性,从而使社会得到安宁,和平得到保证。在他看来,君主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是一切法律的制定者和纠纷的仲裁者,臣民只能绝对服从君主,不能有任何的不满和反抗,因为反对君主就等于反对契约、反对自己。君主在国家内部建立的政治权威形成了内部主权,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就出现了相互承认的主权概念,这为国际法的诞生提供了前提。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把国际法看作是国与国相互交际的法律,是维护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保障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正像一国的法律是为了谋求本国的利益,国与国之间的法律谋取的非任何国家的利益,而是各国共同的利益。这就是格劳秀斯所谓的国际法。
三十年欧洲宗教战争结束后,在1648年召开了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和会,与会各国依据格劳秀斯提出的国际法原则签署了一系列和平条约—总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ies of Westphalia),该和约把对主权源泉的追溯从内部统治的合法性正式转向了外部承认的关系,确立了每一个缔约国的合法地位,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以条约体系为形式的国际关系准则。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被视为中世纪权力重叠的宗教—王朝共同体与近代单一政治秩序的民族—国家的分野,代表了中世纪神权法与近代理性自然法的分野。
这种在主权平等的国家间以条约形式构成的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初主要局限于欧洲国家,近代理性自然法也只是欧洲的一种“国家间法”(laws between nations)。启蒙运动的历史视野及其自然法观念为形式主义的主权概念提供了普遍主义的基础,即当欧洲国家与其他地区的国家签订条约时,也预设了在这些地区某种主权国家的存在,实际上这种预设的主权国家概念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没有描述实质的国家关系,它把国际法看作是人道主义(所谓人道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体现,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现代现象。这种形式的对等关系体现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关系,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扩张,这种预设的主权和国际法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行。
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的朝贡关系是一种国内关系向外的延伸,他否认中国与这些朝贡国之间的主权关系,因而也就否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概念,由此他将朝贡制度贬低为一种落后的对外关系体系,而把以主权为基础的条约制度褒奖为一种先进的体系,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19世纪的清朝是一个自主的政治实体,其主权概念源于内部统治的合法性,儒家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法律体系构成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基础。它不仅存在着多数学者都承认的朝贡制度,同时还具有复杂的行政权力、法律体系、领土权和国际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中俄分别于1689年和1727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19世纪中叶,当英国等欧洲国家与清廷签订条约时,实际上完全忽略了中国国家主权的实质存在,只是将其作为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这种形式平等的主权概念背后是在武力威胁下的不平等,并最终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因此,这里存在一个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一方面西方列强强迫中国设立海关、通商口岸,割地赔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同时在形式上又赋予中国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费正清在最初的分析中,只看到了条约制度对朝贡制度的瓦解和对近代化的促进作用,而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这种霸权逻辑。只有当这些被殖民、被侵略的国家接过了启蒙主义的普遍权利的口号,通过反殖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实现民族自觉和国家独立,才赋予了形式主义的国际法和主权概念以世界范围的实质内容。①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696—702页。
此外,费正清还认为朝贡制度缺乏平等尊重的概念。实际上满族入主中原,最初为了得到各民族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承认,主张夷夏相对化和内外无别的说法,如今文经学对大一统的讨论,这其中都蕴含了民族平等的观念。在处理与朝贡国的关系时也主要采取一种“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的宽容态度:允许朝贡国之间通商并与他国缔结条约、尊重朝贡国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处理与蒙、藏等民族以及与俄国等国家的关系时,也存在着朝贡与条约制度交叉、并用的情况。但从平等关系的角度把朝贡制度与条约制度对立起来,是一种简单的做法。到清朝后期,朝贡国与西方国家缔结条约也是造成朝贡制度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于西方对中国的冲击。
把清朝官员和士大夫对西方国家的无知愚昧作为闭关锁国、排斥外来文化的原因也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在康熙时期,就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出任钦天监正来推算历法,在他的举荐下大批传教士得以出入北京朝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后,东南沿海开禁,并允许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和江南云台山四榷关对外通商,对荷兰、暹罗和其他国家实行免税和减税政策;《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设立恰克图为两国通商地,允许俄国向北京派遣教士。的确存在清朝官员和士大夫对西方的不了解,但是清廷关注的焦点在西北的内陆边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军事压力主要来自西北,同时由于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猖獗加上郑成功部的袭扰,清廷对沿海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来自沿海的西方侵略问题才成为清廷关注的焦点。
费正清把民族—国家看作是与传统帝国相对立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家思想早已成为国内各民族赖以聚合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甚至是构成朝贡关系网络的基础,加上满汉共治的清政府不断强化大一统思想和儒家法统而形成的“官方民族主义”,因此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把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则强加给中国,是对中国文化共同体的纵横向的切割,即否认儒家传统和儒家文化的聚合力,是一种把中国纳入西方殖民体系分割宰治的做法(如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地建立殖民地以及划分势力范围)。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恰恰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诞生的,比如梁启超提出的反对列强侵略的大民族主义和反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小民族主义。但是,民国以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小民族主义又让位于大民族主义。②同上,第614页。所以,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与帝国传统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不是像费正清所言,“西方观点的实质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初期的国家看待。……条约规定一切民族国家一律平等,即使这些条约造成了不平等的局面”;他还以美国“门户开放”为例再次强调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外来性,“中国的‘完整’,它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独立以及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已成为美国政策的实际的习惯用语。……如果这些深深植根于西方思想中的西方期望能起作用,那么与西方的接触就必然给中国带来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英国通过条约帮助中国建立了新的制度—平等的民族国家,而美国则保持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说西方的入侵刺激了民族主义的话,也是间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应是,一直将这种灾祸归咎于清政府的无能,而不强调外国侵略的因素”。①费正清:《条约体制下的共管》,载陶文钊编选,林海、符致兴等译《费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86、88页。
至于晚清的自强和改良运动,在费正清的眼中也完全是西方冲击的产物。他认为,无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都是“为表达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以淡化了的方式参与共治而创立的基本理论”。按照这种两分法,满族天子可以继续他的儒家统治,西方人参与整个近代化进程,包括海关和租界的建立,及其由先进的城市管理产生的贸易法和条约口岸体制。但他认为这只是向近代化过渡的一种折中的办法,“接受任何西方的事物都被证明是一种单向驱动器,它只能进一步使这个儒教国家脱离它的传统基础”。魏源发展军事工业的想法,必然会摧毁传统的儒教国家及其由税吏管理的农业经济,从而促进中国的近代化。②同上,第90—91页。我们不应该否认西方侵略的同时带来的西方近代思想和先进技术对中国的促进作用,但费正清在这里再次回避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内部成长的民族主义因素,冯桂芬、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面对西方的入侵不断地将这种外来的压力转变为内在制度的变革和“自强”的诉求,制度的变革在于重新树立在西方冲击下岌岌可危的政治权威,对传统的强调在于强化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意识,学习西方在于加强反对外国侵略的军事力量,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才能有效地获得国际承认并抵御外敌侵略。
结论
总而言之,我们在看待朝贡制度和条约制度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割裂开来,这是西方二元对立、线性社会发展的简约化思维逻辑。我们既要看到条约制度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条约制度后面彰显的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既要看到朝贡制度保守落后的一面,也要看到这种长久形成的制度积极意义的一面。在当今国际关系领域,由于霸权主义、扩张主义造成的冲突、杀戮、掠夺每天都在上演,被费正清指责为不平等、落后的中国朝贡制度实际上完全可以用来建构一种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关系理论。中国的朝贡制度是一个有序的世界秩序,不是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的诸国林立、互相倾轧的无序战场。中国的朝贡制度所包含的“天下观”中的“天”的概念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物质性概念,更是一个社会、精神和道德的概念,体现了一种和谐互系的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是自然与人文、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交汇的空间。这种空间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就像向水中投入一枚卵石产生的一圈圈的涟漪,随着不断延展的涟漪,中心不断地被淡化,从而消弭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存在的只是远近、亲疏的距离和礼仪关系。同时它又是一种差序包容的关系,一方面,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差序关系保证了体系的和谐与稳定;另一方面,居于中心的中国对附属国是怀柔、包容的,它不是西方强权维持下的紧张的国际关系,而是一种互系的、和平的国际关系。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差序是一种正常存在的结构,但是近代形成的平等政治观念是所有国家的诉求,只要大国有责、小国有序,是可以构建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的。③秦亚青:《全球视野中的国际秩序·代序》,载秦亚青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12—14页。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