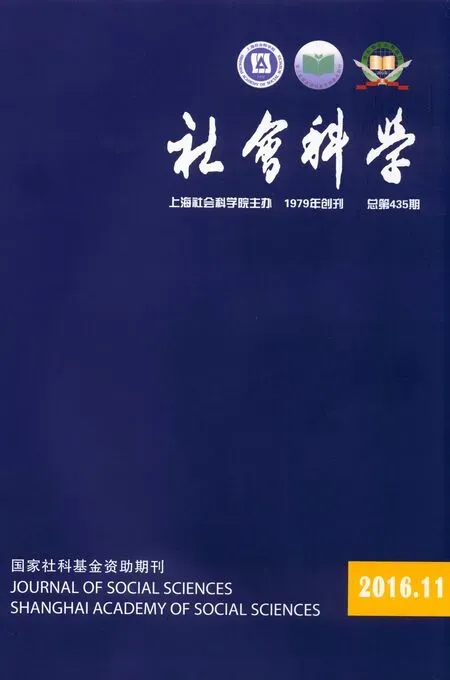谢尔曼·阿莱克西《飞逸》中的反暴力书写*
邱 清
谢尔曼·阿莱克西《飞逸》中的反暴力书写*
邱 清
美国印第安裔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在《飞逸》中以族裔和超族裔的视角探讨暴力冲突的复杂成因和当代危机。小说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演绎印第安混血孤儿的身份问题和艰难处境,控诉了美国的强权政治使得“以暴制暴”成为被边缘化印第安“他者”的“集体无意识”。以移情视角为关照点,通过对比不同暴力主体的心理活动,阿莱克西不仅批判对暴力的错误认知和定势思维,还叩问暴力事件中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责任感。最后,小说将暴力冲突延展到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中,透视出模糊身份界限,寻求对话和沟通的良性机制才是化解民族和种族矛盾,终结暴力的有效策略。
谢尔曼·阿莱克西;《飞逸》;反暴力书写
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1966-)是当代美国印第安裔英语文学中最卓越的作家之一,被《纽约时报》誉为“这个时代最动听的抒情声音”*Nancy J. Peterson(ed.), Conversation with Sherman Alex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p.XX.,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诗歌集、剧本,荣获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大奖。《飞逸》(Flight)发表于2007年,是一部集科幻元素、历史叙事和成长小说于一体的上乘之作。题写在扉页上的“叽—啁—叽—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Sherman Alexie, 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预设了《飞逸》与战争之间的联系。作为一部经典反战小说,《五号屠场》通过鸟儿“叽—啁—叽”的啼叫声控诉战争暴力给人类造成了难以言说的伤害。阿莱克西坦言“电视上不停播报的伊拉克战争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而《五号屠场》给了他叙事策略上的启发*Rebecca Roberts, “Author Sherman Alexie Talks Flight” Interview, “Talk of the Na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April 11, 2007, n.p.,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517855, 2007-04-01.。从列宁预言的“充满了暴力的二十世纪”*[美]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到本世纪伊始,和平的进程依然令人堪忧。具有族裔身份的阿莱克西尤其关注多元文化语境下由民族和种族问题引发的暴力冲突。《飞逸》并不局限于只探讨当代的热点问题如9·11事件、领养体制中的种族暴力等,还将视角延伸至历史的维度,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美国历史上其他“不可思议的暴力时刻”,并致力于探求暴力事件持续发生的原因*Rebecca Roberts, “Author Sherman Alexie Talks Flight” Interview, “Talk of the Na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April 11, 2007, n.p.,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517855, 2007-04-01.。学界对小说的研究无法绕开“暴力”这个主题词汇,评论家柏兰德(Kerry Boland)说“易于理解、包含人性之光的反暴力寓意是小说最明显的特征”*Kerry Boland, “‘We’re All the Same People’? The (A)Politics of the Body in Sherman Alexie’s Flight”,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Vol.27, No.1, 2015, p.71.,学者科隆布(Joseph Coulombe)认为小说致力于挖掘“暴力和恐怖活动的根源、语境及后果”*Joseph L. Coulombe, “The Efficacy of Humor in Sherman Alexie’s Flight: Violence, Vulnerability, and the Post-9/11 World”, MELUS, Vol.39, No.1, 2013, p.1.,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反暴力是阿莱克西执意探讨的重要主题。《飞逸》展现了主人公从信奉“暴力正义说”到颠覆对暴力的错误认知再到探寻和平生存之道的认知成长轨迹。与故事本体层面平行并置的是作家对暴力冲突背后心理、政治、道德等多层面的审视与诘问。通过描述当代印第安混血孤儿在都市的艰难处境和身份危机,小说控诉了美国的强权政治给印第安人带来无以复加的创伤,难以抚平的创伤又使得“以暴制暴”成为被边缘化“他者”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揭示暴力产生的社会政治动因是其反暴力书写的首要步骤。由于引入时间旅行的超现实主义写作策略,小说再现了真实的暴力历史场景。以移情视角为关照点,通过对比不同暴力主体的心理活动,阿莱克西不仅批判对暴力的错误认知和定势思维,还叩问暴力事件中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责任感。最后,小说将暴力冲突延展到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中,透视出模糊身份界限,寻求对话和沟通的良性机制才是化解民族和种族矛盾,终结暴力的有效策略。
一、 强权政治: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
在当代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下,少数族裔难解的身份危机是透视暴力恐怖活动的重要视角。因此,《飞逸》以戏仿经典名著《白鲸》首句的形式“你就叫我青春痘(Zits)吧”*Sherman Alexie, 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1.开篇,学界认为小说从一开始就颇具新意地将“身份问题推到明显而中心的位置”*Nancy J. Peterson(ed.), Conversation with Sherman Alex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p.170.。“青春痘”既是主人公印第安混血儿的绰号,又是内涵丰富的象征符码。红肿、流脓、结痂的青春痘在主人公并不白皙的脸上和背上星罗棋布、泛滥成灾,成为创伤的隐喻和耻辱的身份标签。主人公认为光洁透明的白皮肤才是美国社会合理身份的评判标准,将自我身份定义为有别于白人的“他者”,认定父亲的印第安基因才是一切厄运的罪魁祸首。他有暴力伤人的冲动并时常梦见自己“撕破他人的肚子和胸膛,吃掉肾和肺,敲开他人的头颅,喝脑髓”*Sherman Alexie, 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26.。同时,文本还影射青春痘患有精神萎靡、幻听幻觉、暴力梦魇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
主人公饱受创伤的暴徒形象符合印第安文学评论家南茜·斯蒂凡黛(Nancy Styvandale)提出的“跨/历史性创伤(Trans/historical Trauma)”研究范式。斯蒂凡黛认为西方主流创伤理论并不适用于被边缘化的印第安“他者”,不能从后殖民语境完整呈现印第安人的创伤经历,而“跨/历史性创伤”的概念准确地表达了“印第安人的创伤起因并不呈单一性,而是各类事件穿越时间和空间不断重复叠加,进而对印第安人产生累积性和增生性的持续破坏作用”*Leon Lewis(ed.), Critical Insight: Sherman Alexie, Pasadena: Salem Press, 2011, p.345.。也就是说,印第安人的创伤问题与美国的内部殖民进程相生相伴,是一个延续的、不断推进的过程,任何对印第安人不利的、非正义的举措都会导致创伤的形成。以青春痘为代表的印第安混血孤儿的创伤问题绝非起因于某一件重大的、非同寻常的暴力事件,而是受到整个强权政治体制持续性地侵害和压迫。小说用清楚明晰的笔触阐明了主人公是如何走上从幻想暴力到言语暴力直至实践暴力的“以暴制暴”之路。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阿莱克西塑造的孤儿形象是为了隐喻当代印第安人被强行割裂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后,被迫“寄养”于美国主流社会,陷入“文化位移”的后殖民牢笼中*Nancy J. Peterson(ed.), Conversation with Sherman Alex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p.171.。《飞逸》的主人公青春痘从出生开始只与印第安人存在血缘上的关系,并未确立印第安的文化身份。小说着力凸显了美国领养体制看似民主实则强权的伪善性。在青春痘的身份归属上,毫无疑问,他拥有印第安血统,然而美国种族政策“一滴血原则(one-drop rule)”并未给他一个“官方”的身份,他的肤色和体貌特征又使他不能与白人孤儿享受同等权利。他成为被“异化”的怪胎,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被随意安置,辗转于二十多个领养家庭。小说通过主人公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压抑痛苦的叙述着力渲染了领养体制内无所不在的可怖冷暴力。养父爱德加因不满青春痘在飞机航模赛中打败自己,当场愤怒地砸碎所有飞机,用一种“家长式的”狂暴作风吓唬他震慑他;患有恋童癖的养父将他带到地下室强行性侵;还有的养父以他作为筹码骗取政府抚恤金,克扣他的基本衣食住行;警署、孤儿院和其他过渡性政府机构到处都是充满恶意的工作人员。青春痘无法在领养体制内找到生存空间,被分配到第二十一个家庭时,他怒火中烧地喊道:“是的,这就是我的生活,一系列凶残的混蛋和飞机坠毁事件。二十架小飞机都坠毁了。我就是一架着火的飞机,撞向每一个领养家庭。”*Sherman Alexie, 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11.这句话中飞机的隐喻修辞与“9·11事件的意象甚为吻合。”*Joseph L. Coulombe, “The Efficacy of Humor in Sherman Alexie’s Flight: Violence, Vulnerability, and the Post-9/11 World”, MELUS, Vol.39, No.1, 2013, p.2.将青春痘比作愤怒的恐怖分子,领养家庭比作双子塔,阿莱克西除了声讨当前领养体制中的种族主义恶行,更力求还原暴力心理的形成过程。因为无法承受身体、心理、精神的迫害与创伤,青春痘只能幻想通过暴力途径发泄不满与愤怒,寻求公平和正义。对于“无能为力的被殖民者”来说,“他们共同的无意识就是杀人这一蠢念头”*[法]氟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译林出版2005年版,第21页。。解密暴力实施主体行为背后的社会动因是阿莱克西反暴力书写的首要步骤。
失去亲人的孤儿在主流文化中逐渐沦为被边缘化的“他者”,处于漂泊无依的无根状态,这早已成为后殖民文学的经典母题。阿莱克西在长篇小说《印第安杀手》中描述了被强行从保留地抱养到城市的约翰无法在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之间找到自我身份定位,成为都市“迷途的小鸟”*Nancy J. Peterson(ed.), Conversation with Sherman Alex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p.28.,掀起了种族间暴力对抗的风暴。《印第安杀手》是《飞逸》的姊妹篇,与前者刻意宣泄种族仇恨的情绪,隐含暴力对抗的企图不一样,后者侧重探寻暴力产生的根源,揭露社会政治体制的强权本质,反对将印第安人视为“本质邪恶”的观点。青春痘从十岁进入领养体制的五年间逐渐陷入被殖民化的逻辑辩证法中,将自我身份定义为有别于白人的“他者”,不断滋生与强权政治(警察局、孤儿院、福利院等机构)对抗的情绪。民族国家的民主体制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宗旨,以消除暴乱,建立合理秩序为目的,却以霸权思维的逻辑在“立法的暴力”和“护法的暴力”中培育暴力的温床*[德]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陈永国、马海良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333页。。
除了遭受领养体制的残暴虐待,电视成为主人公走向暴力诉求的助推器。电视是阿莱克西所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体现了作家对以电视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的关注。标准化、商业化模式下的大众文化将印第安人千篇一律地做“类型化”处理,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论方式呈现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关系。毫无疑问,这种强权主义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模式并不能使印第安人接触到历史的真相。青春痘深受其害却浑然不知,他常想“我从不能理解那些说电视不好的人”*Sherman Alexie, 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11.。阿莱克西用反讽的修辞手法表明:对于尚处人生观塑型阶段的青春痘来说,以电视为载体的大众文化蒙蔽了他理性思考和正确认知的心智。同时文本还暗指电视在青春痘暴力心理的发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通过电视熟悉各种枪支;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主演的西部战争片崇拜有加;津津乐道于印第安人和白人历史上的暴力纷争和战争冲突。正如让·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战争已经变得电影化和电视化了,媒介中的影像使战争以其他方式延续…暴力影像提供原始的快感,并具有不受美学、道德、社会和政治束缚的野蛮诱惑力,所以也是非道德的。”*Jean Baudrillard,The Evil Demon of Images, trans. Paul Patton and Paul Foss, Sydney: Power Institute of Fine Arts, 1987, pp.17-28, http://courses.arch.ntua.gr/fsr/130155/jean%20baudrillard.PDF.“影像的恶魔”使青春痘丧失理性判断的能力,以电视中的暴力为模仿对象,逐渐滋生“以暴制暴”的幻象。
由上可见,小说以身份问题为切入点,再现了主人公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体制中遭受无法承受的创伤和误导后如何走上暴力诉求的心路历程。那么,阿莱克西是否以此为暴力正名?暴力是否可以成为伸张正义的手段?正如法农为暴力辩解:“对于被殖民者来说,只能通过绝对的暴力进行诉讼。”*[法]氟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译林出版2005年版,第5页。或如萨特所言:“暴力像阿喀琉斯的长矛,能使长矛刺的伤口结痂。”*[法]氟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译林出版2005年版,第31页。然而,从后续的情节发展来看,阿莱克西并非鼓吹“正义的暴力”,相反,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论者。首先,主人公用言语的暴力攻击他人时遭遇失败。当被养父母强令用合乎规矩的“早安”来回应并不真诚的问候时,青春痘言辞激烈地三次使用恶毒的语言,强硬地对抗父权制威严。但是语言暴力并未换来宽容和尊重,几乎引爆了一场惨烈的肢体冲突,他也因此被警察带走。其次,青春痘在银行持枪制造恐怖袭击案时,阿莱克西并未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真实的暴力场景,甚至并未确切表明持枪扫射是否执行,而是重点描写主人公开枪时癫狂迷失、惶恐不安却又欲罢不能的心理体验,营造出亦真亦幻的虚幻景象。在分析暴力心理时,约翰·基恩(John Keane)说:“暴力可能是欺骗,但与之相悖的是,正是那种欺骗提供了一个抵挡自我所遭受的连续打击的安全庇护所。”*[英]约翰·基恩:《暴力与民主》,易承志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与基恩的观点不谋而合,阿莱克西力图揭示创伤与暴力之间充满悖论:暴力会引发创伤,创伤又会滋生暴力对抗的情绪,但暴力最终只是提供逃避创伤的虚假幻象而已。因此,如何打破暴力幻象并获得对暴力的正确认知成为小说主体部分要探讨的关键问题。
二、 移情:暴力主体的能动性
《飞逸》不仅从当代政治文化体制的角度追责暴力产生的根源,还试图在多重语境下探讨暴力冲突的复杂成因。小说的主体部分采用时间旅行的叙事策略,主人公在银行持枪射击时突然穿越时空,依次见证五幕暴力事件的发生,情节指涉19世纪末直至21世纪初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暴力事件,包括印第安民权活动分子阿奎什(Aquash)的分尸案*Lydia R. Cooper,“Beyond 9/11:Trauma and the Limits of Empathy in Sherman Alexie’s Flight”,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Vol.42,Issue 1, 2015, p.143.、大小角战役、伤膝谷惨案*Steven Salaita,“Concocting Terrorism off the Reservation: Liberal Orientalism in Sherman Alexie’s Post-9/11 Fiction”,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Vol.22, No.2, 2010, p.33.以及9·11事件*Lydia R. Cooper,“Beyond 9/11:Trauma and the Limits of Empathy in Sherman Alexie’s Flight”,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Vol. 42, Issue 1, 2015, p.123.。如此大幅度的时空跨越和多层次的暴力言说交织成一个复调表征空间,而贯穿始终的是阿莱克西对人性和暴力问题审慎的思考。小说摒弃历史宏大叙事,聚焦个人情感维度,在主体部分更侧重从人性的层面考虑道德领域中主体的能动性。凭借具有超现实主义特征的时光飞行,主人公附身他人,回到历史现场,获得“语境化”和“亲历性”的直观感受*刘克东:《恐惧带来的思考——谢尔曼·阿莱克西的后9/11书写》,《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同时,作为每一幕暴力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主人公可以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再现真实的暴力场景,探知被附身角色的复杂心理活动,然后再以第一人称视角加以评述。双重叙事视角重合并置,既为反暴力书写营造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又为呈现暴力主体的移情能力架构了有辨识度的认知空间。
《飞逸》中的暴力历史书写与民族和种族仇恨盘根错节、相互纠缠。通过展现复杂万象的暴力事件,阿莱克西致力于颠覆关于“本质邪恶”的暴力本体论思想。美国少数族裔如黑人、印第安人往往被视作具有野蛮和凶残的天然基因,9·11事件后又有针对伊斯兰人的极端恐慌情绪。以此关照历史,必将得到关于暴力的错误认知。因此,小说通过引入移情的视角诠释人性残暴的本源不取决于民族和肤色,而在于个体的移情能力。“移情(empathy)”理论有助于从心理认知层面阐释人性暴虐与暴力生成之间的关系。剑桥大学西蒙·巴伦—柯恩(Simon Baron-Cohen)教授在《邪恶的科学阐释:论移情与残暴本源》一书中指出“移情发生在人们停止思维的单一聚焦,而采用双向思维模式的时候……移情是指能够理解他人所思所感,并用恰当的情感回应他人”*Simon Baron-Cohen, 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New York: Perseus Group, 2011, p.16.。巴伦—柯恩用图示的方法呈现移情能力的高低之分。移情能力越高,越能对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容易形成利他的观念。移情能力越低,越容易产生暴力倾向。当出现“零度移情(zero empathy)”时,有可能直接引发暴力犯罪*Simon Baron-Cohen, The 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New York: Perseus Group, 2011, pp.19-27.。五幕暴力叙事在不同程度上皆体现了巴伦—柯恩从移情视角关照暴力心理的形成,而尤其以表征战争暴力的大小角战役和伤膝谷惨案最为明显。
大小角战役和伤膝谷惨案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印第安人和白人战争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以其为原型的暴力历史书写中,小说完全消解荣耀、胜利、英雄主义等词语在战争中的高尚含义。印第安人在大小角战役中成功击溃卡斯特将军,然而阿莱克西并没有站在族裔的立场上为印第安人的胜利喝彩,宣扬正义之战,而是将“大小角战役”称为“全错之战”*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70.。在惨绝人寰的伤膝谷大屠杀中,白人士兵没有完全被妖魔化,盖斯/青春痘和小圣人(Small Saint)不惜违抗军令解救印第安弓箭男孩(Bow Boy)。由此可见,小说将对暴力的认知置于更复杂和含混的空间,不断编织暴力叙事之网,又不断解构关于暴力的定势思维。在横尸遍野、满目苍夷的战争现场,主人公通过不断提升的移情能力,逐渐理解暴力事件中行凶者和受害者的不同处境,甚至用实际行动反对和阻止暴力的发生。同时,文本还着重刻画了第二类人物形象,他们毫无移情能力,冷酷无情,沦为极权体制下的杀人机器,卡斯特、莫斯塔斯将军和众多士兵可归于此。两股力量相互抵制,使文本中的暴力和反暴力叙事充满矛盾和张力。
根据巴伦—柯恩的图示法,主人公的移情能力是一个动态建构、不断上升的过程。首先,大小角战役“快速而残暴”的杀戮场面不仅使他感觉从身体到灵魂都不舒服*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72.,而且他立即联想到曾经制造的银行恐怖袭击案。通过将自我的暴力罪行投射到残酷的杀戮场面,青春痘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开始忏悔曾经的恐怖行为,并醒悟暴力恶行将带来无以复加的后果。其次,附身印第安失语少年后,青春痘处于双重受害者的角色。当面对束手就擒的白人士兵时,经过痛苦而矛盾的心理挣扎后,青春痘用理性的思考战胜感性的杀戮冲动。“难道这个士兵因为其战友割掉我的喉咙就应当被处死吗?如果我杀死他,我是否应该被他的家人和朋友处死?难道仇恨是一环套一环再套一环的无限循环吗?”*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77.从青春痘的评论可以看出,他已经跳出个人爱恨情仇的狭隘视野并用推己及人的谅解心态思考是否可以终止暴力的恶性循环。再次,作者在伤膝谷惨案中刻意凸显参战白人士兵大多都是十多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睛看上去凹陷而空洞,贫瘠而无神,好像能吃到足量的食物却得不到到真正的开心”*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82.。青春痘心生怜悯之情,再次联想到自己的经历,不禁发出振聋发聩的责难之声:从古至今,不分民族、种族、地域和国家,孩子都是被战争操控和利用的工具,战争背后是险恶的政治企图,战争暴力是强权的本质体现。移情是同情产生的先导,只有移情才能产生利他主义的观念。青春痘终于缓解种族仇恨的情绪,用同情之心悲悯所有饱受暴力侵害的孩子。最后,青春痘突破意识的束缚,成功控制盖斯的身体,与小圣人一起不惜违抗军令,成功解救印第安弓箭男孩。在阴郁而灰暗的战争色调中,青春痘的移情能力达到顶峰,从情感到意识到都摆脱了被操演的角色,用实际行动为反暴力涂抹最鲜亮的色彩。
与主人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卡斯特和莫斯塔斯为代表的白人将领们。他们处于“零度移情”水平,不会进入“他者”的心灵进行换位思考,是战争中冷血无情的刽子手,是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的典型。他们消除宗教信仰和道德顾忌,并不愚蠢却缺乏思想,从个人的晋升等实际利益出发,使“脱离现实和无思想性的平庸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恶的本能”*[美]汉娜·阿伦特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小说解构卡斯特在白人历史中的英雄形象,将其塑造成刚愎自用,以歼灭印第安人来攀爬政治仕途的杀人狂魔。莫斯塔斯将军在极权体制下毫无自我判断力,完全接受了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与印第安人交战是美国的“天赋使命”,是“文明”对“野蛮”的临幸和驯化,是神圣而光荣的正义之战。因此,他在军队集合时发表极富煽动性的演讲,宣称“我们要给印第安人迅速而致命的正义之摧”*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85.。他绝不放过任何屠杀印第安人的机会,麻木地参与到暴虐行动中,为屠杀而屠杀,将人性的残暴表露无疑。卡斯特和莫斯塔斯作为庞大的极权体制中的一份子,将个人的道德责任感托付给组织,完全泯灭了个体的自我判断力和主观能动性。
阿莱克西把对个体残暴人性的诘问巧妙地融于暴力历史书写中,通过对比不同主体在暴力现场的移情能力,小说颠覆了以民族、种族和宗教为判断标准的暴力“本质邪恶”论,肃清关于暴力的定势思维和偏见。凭借不断提升的移情能力,主人公完成暴力认知和创伤治愈之旅,逐渐从暴力的幻象中全面苏醒,不断醒悟暴力的罪大恶极,慢慢产生同情和谅解的心态,并用身体力行的方式证明暴力的正义性假设只是一个伪命题。
三、 顿悟:暴力终结的启示
揭示暴力产生的社会根源显然不是小说的终极意图,强调暴力主体的能动性还不足以建立让人信服的暴力终结说,而这两个层面的话语都是为了指向阿莱克西最终建构的美好家园。在谈及《飞逸》的创作时,阿莱克西坦言:“结局就像是祈祷。也许我是用自己的方式祈祷更乐观更有希望的未来。”*Rebecca Roberts, “Author Sherman Alexie Talks Flight” Interview, “Talk of the Na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April 11, 2007, n.p.,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517855, 2007-04-01.由此可见,小说的结局蕴含着作家最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走出暴力困境的未来展望。而且从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来看,主人公青春痘在结束时光飞行的认知之旅后,必然实现意识上的飞跃,因而,文本做了“顿悟(epiphany)”的艺术化处理。在文本的第十九章,主人公重新回到银行枪击现场。就在他返回自我身体的那一刻,五幕时光飞行连成一个整体,顿时生发出深奥的意象。当他用“精神的”眼睛扫视熟悉的银行场景时,一切都调整并汇合到一个“焦点”,于是他产生“刹那间的心领神会”,也即“精神的顿悟”*Kim Sharon, Literary Epiphany in the Novel, 1850-1950: Constellation of the Sou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2.。仔细咀嚼主人公顿悟后的行为和语言,可以寻迹阿莱克西反暴力思想地形图的出口。
银行在小说中不仅是主人公制造恐怖袭击的案发现场,更是一个隐喻的社会空间。“我就站在西雅图市中心的这家银行,我身边大概有五六十个人,肤色各异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我听到了四五种不同的语言。我想这些人应该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p.34-35.从文本铺陈的细节可以看出银行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象征场域”*Kerry Boland, “‘We’re All the Same People’? The (A)Politics of the Body in Sherman Alexie’s Flight”,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Vol.27, No.1, 2015, p.70.。再次置身这个空间的青春痘发出顿悟后的感慨:“也许我们都是孤立的。也许有些人也在穿越时空见证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也许我们正在共同经历这一切。”*Sherman Alexie, 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158.“我们”,这个称谓体现了模糊族裔与非族裔界限,超越本质主义的立场。但“我们”又是孤立的,这说明人与人之间或者说文化之间缺乏沟通和交融,是彼此隔绝的。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提出“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 monoculturalism)的概念,意指多种文化并存但是文化之间却处于分离和隔绝的状态*[印]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森指出多元单一文化主义往往形成僵化和排他的身份划分标准,造成对峙的局面,容易诱发暴力冲突。因此,要化解种族问题和身份危机,必须模糊界限,倡导多元化的身份归属和对话机制。
不难看出,阿莱克西早已将多元身份归属的理念编织进文本中,并随着主人公的五次时光飞行逐层揭晓。青春痘首先化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汉克对印第安民权活动分子执行残忍的枪决。小说有意打破单一而僵化的身份观,除了将汉克塑造成残忍的种族分子,还强调了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他有上百个不同的自己,而只有一种身份是杀手。”*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58.印第安叛徒霍尔斯和埃尔克坚持按照传统仪式埋葬同胞,所以也并非完全泯灭良知、一无是处。大小角战役中的印第安人以自我防卫的方式获得胜利,但是疯狂亵尸的行为有悖人伦。伤膝谷惨案中的小圣人除了是白人士兵,还是解救印第安孩子的真勇士。恐怖分子阿巴德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但他是聪明机智的好学员、好丈夫。在第五次时光飞行中,当亲生父亲怒斥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心白人帕玛和保罗时,青春痘评价说“白人(white)”和“白人性(whiteness)”*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136.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以肤色一概而论。由此可见,阿莱克西试图在不同的语境下呈现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反对将人按单一的、唯一的、先在的方式进行分割。“身份”在小说中逐渐生成为流变而多义的能指,不断颠覆“程式化”和“固定化”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范式。
主人公最终跳出种族仇恨的狭隘视域,用更包容的态度和更开阔的视野从新定义自我身份。他配合警员调查,与大卫警官推心置腹,不再以自我封闭和不加区分的态度抵抗一切。当今的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在于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更应该倡导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本质主义的漩涡,缓解仇恨对峙的局面,走出暴力的困境。青春痘去警局缴枪自首时说道:“也许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去杀戮。不管是谁指使你,不管你有多好或多坏的理由。也许你应该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的。”*Sherman Alexie,Flight, New York: Black Cat, 2007, p.162.这句话是小说中意义最明晰的反暴力宣言,是对“暴力正义说”最坚定的否决,彰显了普世的人文情怀。阿莱克西的多部作品都借用犹太人大屠杀来类比印第安人的悲惨遭遇。无独有偶,美国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曾提出“人人都是犹太人”的主张*Harold Bloom(ed.), Modern Critical View: Bernard Malamud,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p.156.。两位作家都从本民族的苦难来审视其他民族和人类共同的处境,体现了超越族裔立场,将暴力置于人类共同体的命运中。不管是行凶者、暴力鼓吹论者、受害者、漠视者都是暴力传递锁链中的一环,都将承受暴力带来的创伤和危害,这是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
与阿莱克西此前的作品相比,《飞逸》的结局更为清晰明朗,洋溢着着理想化的诗意色彩和乐观精神。主人公最后选择重新回归领养家庭,接受罗伯特一家的照顾,结局与开端首尾呼应。领养家庭再也不似曾经的暴力坟场,而是充满友善与关爱的“希望之乡”。主人公脸上象征着创伤的 “青春痘”得到了养母玛丽专业的医疗护理,可能焕然一新的皮肤预示着个体在意识升华后脱胎换骨般的重生。尽管无法改变肤色,但是偏执、单一、唯一的身份观和仇恨思想已不再能主导其意志,暴力的虚假幻象被彻底打碎。当然,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并不意味着暴力将就此销声匿迹,但是暴力终结论会成为文学永不停息的主旋律,因为和平是全人类共同的福祉。
结 语
阿莱克西对暴力题材的兴趣和敏感源自于他的切身体悟,因为充斥着暴力斗殴的保留地成长经历给他的童年生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持续升温的区域战争、重大暴力恐怖活动、校园暴力事件等都促使他从社会的层面探寻暴力背后的强权政治和霸权思维。通过聚焦个体的情感维度,小说也强调了暴力事件中主体的能动性和道德责任感。而终结暴力则必须摒弃本质主义、原教旨主义等僵化和排他的观念,共筑人类共同体。《飞逸》是阿莱克西时隔十年后出版的第三部小说,在其创作历程中具有重要的转向意义。他曾说,“我变得越来越不以印第安为中心…9·11事件之后,我谈论穷人、谈论处于劣势地位的人…谈论如何消除部落主义的消极性…”并致力于探讨如何建构一种“超越种族、区域、国家”而更关注整个劣势群体的世界主义观念*Nancy J. Peterson(ed.),Conversation with Sherman Alexi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9, pp.129-130.。正是作家开阔的超族裔视野使得作品的反暴力书写彰显出普世的人文情怀和希望之光。
(责任编辑:李亦婷 潇湘子)
On Anti-violence Writing in Sherman Alexie’sFlight
Qiu Qing
In his novelFlight, American Indian Writer Sherman Alexie probes into complicated causes and contemporary crisis of violence from and beyond minor-ethnic standpoint. The novel presents identity problems and harsh conditions confronted by contemporary Indian mix-blood orphans with deep humanity, discloses how the American hegemonic political systems bring up the notion of “violence revenging against violence” in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of marginalized “others”. By light of “empathy” theory and through comparing different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lexie not only criticizes stereotypical and falsified ideas about violence but query the agency and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violenc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novel extends violence into the fate of human community, and indicates that blurring identity borderlines and dialogical modes ar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relieve national and racial revenge and to end violence.
Sherman Alexie;Flight; Anti-violence Writing
2016-01-20
*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外语联合项目“创伤视域下的谢尔曼·阿莱克西作品研究”(项目编号:14WLH14)的阶段性成果。
I106.4
A
0257-5833(2016)11-0184-08
邱 清,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学院讲师 (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