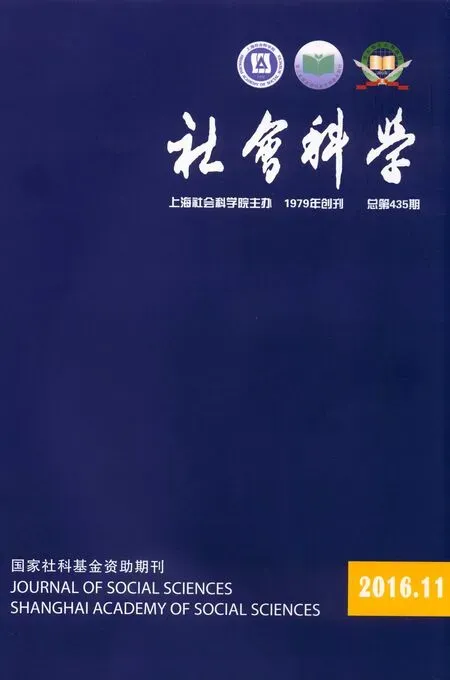斯宾诺莎与认知的动力机制*
吴树博
斯宾诺莎与认知的动力机制*
吴树博
惊奇时常被西方思想家视为哲学(甚至一般知识)的开端,这一点在近代早期欧洲哲学中亦有鲜明体现。然而,同为近代哲学的代表,斯宾诺莎却对惊奇做出了激烈批判并消除了以往人们为之赋予的认知价值。在他看来,人的根本认知动力并不是人心所感受到的惊奇,而是应当首先在作为实体的神之中去寻找,是由作为生产力量的神的思想属性所提供。只有确立这种视域之后,我们才能谈及由神所产生的、作为有限样式的人心的认知问题。而在人心层面上,认知动力的最直接来源乃是人心保持自身存在的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使人心不断地保持和提升自身的实存力量和思想力量。这同时说明,在斯宾诺莎那里,认知动力理论,甚至是一般认识理论,皆以存在论为前提。
惊奇;神;观念;心灵;力量或努力
一
在西方哲学史上,以“惊奇”作为哲学(甚至一般知识)之开端是一种得到很多哲学家赞同的观点。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曾明言:“惊奇感是哲学家的特征。除了惊奇,哲学没有其他根源。”*Plato, Theatetus, 155D, translated by J.H. McDow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他们先是惊奇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奇的人,每自愧愚蠢;为脱出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982b14-20。。因此,正是惊奇将人天生的求知之欲调动起来。而这种观点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后世哲学中的支配性影响而广为传播。虽然在希腊化时期,尤其在以神学为核心视域的中世纪时期,惊奇的地位曾一度被弱化甚至受到强烈压制,*就惊奇与理论好奇心在希腊化和中世纪时期所受之压制,可以参见H.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lated by R. Walla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3, Part III, “The ‘Trial’ of Theoretical Curiosity”, Chapters 2-5, pp.263-324.但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特别是随着以知识问题为核心议题的近代早期哲学的发展,惊奇的作用重新受到严肃对待并得到深入发挥,尤其在笛卡尔那里,惊奇的意义变得更为紧要。
在笛卡尔看来,惊奇(admiration)与爱、恨、欲望、快乐和痛苦一起构成人心中六种最基本的激情,*R. Descartes, Les Passions de L’me, Partie II, Article 69, Oeuvres de Descartes, ed. C. Adam & P. Tannery, T. XI, Paris : Vrin, 1974.而惊奇又是首要的并最先得到探讨,因为我们所具有的大多数激情都是在我们知道某个对象对我们有利或有害之后才出现,可是在我们知道某个对象是否于我们有利之前,我们就会对之感到惊奇。凡是首次遇到的事物总会使我们感到奇怪,我们认为它是新的或者与我们以前所认识的东西或我们设想必然存在的东西完全不同,这时我们就会对之感到惊奇或惊讶。*③ R. Descartes, Les Passions de L’me, Partie II, Article 53; Partie II, Article 74-75.在这种背景下,惊奇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在认知层面,而不是道德层面,得到表现:正是惊奇激发了心灵的注意和反思,使我们察觉到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并将其保持在记忆中,从而强化和延续了心灵中的思想;若无惊奇,这些思想很容易模糊,而那些对惊奇没有任何自然倾向的人通常都十分无知。③因此,惊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求知的原动力。这一点得到很多近代哲学家的赞同,而惊奇感也成为近代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Cf. L. Daston and C. Park,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New York: Zone Books, 1998, Chapter VIII, “The Passions of Inquiry”, pp.303-316.
可是,同为近代哲学之代表,斯宾诺莎在有关惊奇的问题上却另有见地。这在他于自己的早期著作《神、人及其幸福简论》(KV)*文中对所涉及的斯宾诺莎著作的引用遵循当前国际通行的缩写和引用格式,其中《神、人及其幸福简论》缩写为KV, 然后是部分和章节数,如“KV, 2,3,2”指该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2节;《伦理学》缩写为E, 具体内容的缩写形式为A(公理)、App(附录)、C(绎理)、D(证明)、Def(定义)、P(命题)、Pref.(序言)、S(附释),如“E2P11C2D”指该书第二部分命题十一绎理二证明;《神学政治论》缩写为TTP,然后是章节数,如“TTP, 6, 1”指该书第六章第1节,由于中译本没有分节,所以附注中译本页数。斯宾诺莎著作的外文皆依据Spinoza, Opere, a cura di F. Mignini e O. Proietti, Milano: I Meridiani, 2007;中译文参照相关中译本:《神、人及其幸福简论》,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中对惊奇做最初考察时就有所体现。与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当时也把惊奇视为最基本和最先被考察的激情。这种作为激情的惊奇出现在以第一种[认识]方式(即意见)认识事物的人身上:既然这种人是从某些特殊事例引出普遍结论,所以在看到跟他们的结论对立的东西时,他们就感到惊奇。例如,一个只看过短尾羊的人,在看到长尾羊时就会感到惊奇。而这种事情在许多哲学家身上也时有发生。(KV, 2, 3,2)同时,由于意见来源于泛泛经验和传闻,本身没有任何确定性,并且总是屈从于错误,(KV, 2, 1-2)所以,由意见所引发的惊奇并不是哲学的起源和哲学家的独特标志,凡是得出真实结论的哲学家都不会感到惊奇。(KV, 2, 3,3)因此,虽然斯宾诺莎遵循笛卡尔的思路把惊奇视为一种基本的激情,但他对惊奇的地位及其认识价值的评价却明显与笛卡尔有别。
而随着斯宾诺莎思想的发展,尤其在《伦理学》(E)里,他对惊奇的看法与笛卡尔有了更加深刻的差异。首先,他不再把惊奇视为激情(更不是基本激情),而是视之为我们关于某物的想象。*在斯宾诺莎那里,想象和情感都是思想属性的样式,都是人心的特定活动。但作为两种不同样式,想象和情感又有区分:想象乃是人心觉察和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而情感则是身体的感受和这些感受的观念(Cf. E2P40S2&E3Def3)。由于这种个别的想象与其他想象没有任何关联,心灵就一直被固定在其中,而不会过渡到关于其他事物的想象。当我们最初碰到一个新奇或反常的事物时,我们的心灵无法把它跟其他事物的形象按次序联系起来,无法进行连续的思想,从而感到惊奇。所以,惊奇表现了心灵本身的分神,这并非起于一种将心灵的注意力从别的事物转移出来的积极原因,而仅是由于没有任何原因可以决定心灵从对一物的考察过渡到对他物的考察。(E3App.Def.4)作为一种突发事件,惊奇就如同心灵活动中的死亡时刻。而我们之所以感到奇怪,是因为我们不能为所发生之事赋予意义。当心灵惊呆了并似乎被剥夺了认识力量时,这个惊奇的心灵就被拘禁在自身之内,停滞了思想。心灵本身的因果性联想机制由此被打断,而惊奇本身又无力使心灵摆脱这种状态。因此,笛卡尔赋予惊奇的力量,在斯宾诺莎这里,恰恰是它所缺乏的。除了心灵在感受惊奇之前所使用的力量之外,惊奇并不具有其他任何力量。*L.Vinciguerra, Spinoza et le Signe: la Genèse de L’imagination, Paris: Vrin, 2005, p.44.这种作为心灵之停滞状态的惊奇也就不是认知动力的真正来源。
其次,惊奇及其导致的结果不仅无法推动心灵求知,反而成了我们求取真知的障碍。这一点由惊奇与迷信之间的紧密关联得到鲜明体现,斯宾诺莎也在这个层次对惊奇展开了更深入的批判。在《神学政治论》(TTP)序言里,斯宾诺莎描述了“迷信”在人的心理层面的生成史。他认为,人天生就易于迷信,而导致迷信的根本原因是恐惧。由于人们时常陷于异常艰难的处境而无以形成任何行动规划,同时由于他们贪恋运气所给予的不确定的好处并对之做毫无节制的渴求,以致他们总在希望与恐惧之间徘徊。如果他们看到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却又无法用寻常事物进行解释,他们便会充满惊奇,并相信那是一桩奇迹。它展现了神灵的愤怒,须用祭祀和祷告来使之平息。(TTP, Pref.1-2,中第9页)在这种情况下,惊奇非但没有引发大众去求知,反而使之陷入盲信和对权威的依赖,并最终放弃对反常之物的自然原因的探究。而相比于探究奇迹的自然原因,大众更愿诉诸于神的意愿和超自然的力量。“在看到人体的精妙构造时,人们会感到一种可笑的惊奇。由于不知道一件如此精美之作品的原因,他们就断言人体的结构不是如机械一般造成,而是由一种神圣的或超自然的技艺创造。因此,要是有人想探究奇迹的真正原因,像智者一般热切理解自然事物,而不像愚人那样对之大惊小怪,那么他就很难不被大众所信赖的自然和诸神的解释者指斥为渎神的异端。”(E1App.)因此,以无知作为根源和标志的惊奇非但不是求知的动力,反而因其引发的恐惧使人陷于迷信,并导致人进一步的无知和无力。
然而,在大众、惊奇与无知之间却有一种极为悖谬的联系:“大众总是更愿意保持对自然原因的无知,他们唯独渴望听到那些无法为他们所理解的东西并由此激发他们最大的惊奇。”(TTP, 6,1,中第89页)正因如此,惊奇变成很多宗教人士控制教众的手段。早在古希伯来先知们发预言和圣经作者撰写圣经文本时,他们就已注意到惊奇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联。“毫无疑问,圣经中所叙述的一切事件都是自然发生的,然而它们却被归诸于神,这是因为圣经无意通过自然原因来解释事件,而只是叙述那些可以触动想象的事件。在这样做时,它使用了特定的方式与风格,以便最有助于激发惊奇,从而在民众心中引发虔诚。” (TTP, 6,13, 中第99页)而这种手段日后在各大体制化宗教中得到普遍运用。掌握宗教权力的人通过激起信众的惊奇和恐惧来为宗教的教义和法规奠定合法性基础,反过来,他们又利用这些教条把群众牢牢束缚在迷信和无知之中,以便稳固自己的统治。他们非常清楚,“愚昧一旦被揭穿,愚蠢的惊奇一旦消失,他们用来论证和维护自己权威的唯一手段也就被消除了”。(E1App.)所以,对那些以自然原因来解释事物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异常敌视。在此恶劣处境下,惊奇不可能展现任何认知价值,反而成为闭塞民智、推行暴虐统治的手段,而斯宾诺莎对惊奇的批判在此达到了顶峰。
二
既然斯宾诺莎对惊奇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剥夺了以往为之赋予的认知价值,那么人的认知动力又源于何处呢?对此,斯宾诺莎在其著作中未曾明言,然而,透过他的具体表述,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相关的信息——只不过他的观点需借重构性推导才能得到展现。
作为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诺莎与其他理性主义者分享了许多共同的思想前提,但也彰显了他的反常之处。近代哲学通常被人们视为一种“意识哲学”,它从笛卡尔的“我思”获得最初基础。然而,当笛卡尔从心灵出发之时,斯宾诺莎却以神为最初的出发点。*L. Stein, Leibniz und Spinoza: Ein Beitrag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eibniz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 Verlag von Georg Reimer, 1890, S. 283.他的这种做法既与当时哲学的一般特征相关,也与他的哲学的内在特性相联。
一般而言,17世纪是欧洲启蒙运动肇始和初露端倪的时代,但此时哲学跟神学和宗教并未彻底划清界限,哲学家们仍不停地谈论上帝,斯宾诺莎亦是如此。*G. Deleuze, Cosa può un Corpo? Lezioni su Spinoza, a Cura di Aldo Pardi, Verona: Ombre Corte, 2013, p.67.然而,与其他哲学家不同,斯宾诺莎彻底抛弃了传统人格化的上帝观念,转而持有晚期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自然神观念,而且比那些文艺复兴前辈走得更远:他把作为其形而上学之核心的实体直接称作“神或自然”,并借此确立了一种彻底自然主义的视域,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G. Gentile, Giordano Bruno e il pensiero del Rinascimento, Firenze: Vallecchi Editore, 1920, p.126.在他看来,神乃是与自然同一的、绝对无限的存在者(E1Def6)。一切具体事物(亦即神的样式)都在神之内,都是神依自身的本性必然性把它们生产出来。*实际上,神把具体的样式或事物产生出来的过程就是神依照自身的本性必然性来活动和改变其自身之样貌的过程,换言之,神在产生和理解其自身之时,也同时把事物生产出来。这两种生产在神那里是完全同一的。(Cf.E4Pref.)没有神,任何事物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被设想(E1P15)。这不仅适用于有形事物,也适用于非形体的事物。
而作为事物之内因,神又是通过他自身的属性(attributus)把事物生产出来。就其本质而言,属性乃是理智就实体所知觉到的、构成实体之本质的东西。神就是由无限多的属性所构成的实体,其中每一属性各自表现一种永恒无限的本质。(E1Def4&6)因此,属性对神而言既是构成性的,也是表现性的,而这种构成和表现都是相对于神的本质而言。既然神的力量(potentia)就是神的本质自身(E1P35),那么属性就构成和表现了神的力量,属性本身也要从力量的角度得到规定。可是,在构成和表现神的本质的无限多的属性中,能为人的有限理智所把握的只有思想和广延这两种属性。我们只能从这两种属性出发来认识神、世界和我们自身。人的心灵、观念、欲望、意愿等具体样式都隶属于神的思想属性,都必须依据思想属性才能产生并得到阐释。
而在思想属性的生产活动中,观念占据着首要地位。“思想的各个样式,如爱、欲望以及其他以心灵的情感之名被命名的任何样式,除非在相同的个体中具有所爱、所欲(等等)之对象的观念,否则这些思想样式便不能存在。但即使没有其他思想样式,却仍然可以有观念。”(E2A3)而在无限多的观念之间,最初的观念乃是为神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神的观念”,这是一切关于观念之叙事的出发点。具体而言,“在神之内必然有一个观念。此观念既是神的本质的观念,同时也是一切从神的本质必然而出的事物的观念。”(E2P3)斯宾诺莎把这个唯一的神的观念称为神的无限理智(E2P4D)或由神的思想属性所产生的直接无限样式(E1P21)。任何个别的和有限的观念都被包含在这个唯一的神的观念之内并由之产生。
而在构想观念(甚至是一切样式)的生产和实存之时,斯宾诺莎严格遵循范畴的一致性,严格贯彻属性之间的平行论原则。虽然神的本质由无限多的属性所构成,但是诸属性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更不会相互混淆。每一种样式只能由它所隶属的属性——而不能由其他属性——来产生和解释。(E2P6)因此,“观念的形式存在以神为其原因,只就神被认作能思想的东西而言,而不是就神为别的属性所阐明而言,这就是说,神的各种属性的观念以及个别事物的观念都不以对象本身或被知觉的事物为其动力因,而是以作为能思者的神为其动力因。”(E2P5)作为思想属性的样式,观念只能由思想属性来产生和解释,而不能由其他属性,尤其不能由广延属性来产生和解释。正因如此,斯宾诺莎认为不能以对象或被知觉的事物为认识的动力因。在他的思想属性与广延属性的平行论模式下,身心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不可能的:“身体不能决定心灵,使它思想;心灵也不能决定身体,使它运动、静止或处在其他状态之下”。(E3P2)因此,认知活动的前提、动因及其结果都必须在神的思想属性之中来寻找。而斯宾诺莎的相关论述也始终以此作为出发点,并严格排除近代主体性哲学以“自我”和“心灵”为出发点的做法,相应地,人的心灵也没有认识上的优先地位*在斯宾诺莎看来,就存在论层面而言,人及其心灵并不比其他存在者占据更卓著的地位,相反,从神的观点来看,或者说就一切存在者都由神所产生而言,万物莫不等同。(Cf.E4Pref.)。
然而,尽管神可以被视为认知的最终出发点,但更为具体的认识过程或个别观念的形成过程也应当得到解释。就此,斯宾诺莎写道:“一个现实实存的个别事物的观念以神为原因,并非就神是无限的而言,而是就神被认作被另一个现实实存的个别事物的观念所分殊而言;而后一个观念之以神为原因,乃是就神为第三个观念所分殊而言,如此类推,以至无穷。”(E2P9)由此可见,虽然斯宾诺莎在“神的观念”层面上规定了一切个别事物的观念都由神所产生并处在神之内,但就个别观念的生成而言,一个个别观念却是由另一个个别观念所产生,前者是结果,后者是原因,而后面作为原因出现的观念同时也是一种结果,它需要由另外一个作为原因的观念把它生产出来,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其实就意味着,在微观层面,个别观念的产生和存在同样遵循因果性的生产次序并形成严密关联,任何个别观念的直接“存在因”只能是另一个个别观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依然要有神作为原因的参与,但这时神不是被视为绝对无限的存在者,而是被视作被特殊观念所分殊,此时神将自身具体化为每一个个别的观念并以个别观念作为其载体而展开生产活动。
可是,如果观念是纯粹由思想属性所产生或者更具体地说个别观念是由其他个别观念所产生并形成因果链条,那么观念与其对象如何一致呢?斯宾诺莎认为,“观念自思想属性而出与观念的对象自其所隶属的属性推演而出,其方式是相同的,并遵循同样的必然性”。换言之,“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E2P6C&P7)。从神的角度来看,由思想属性所产生的观念与由广延属性而出的观念对象(即具体事物)必然严格一致,这由思想与广延这两种属性之间的平行共构来确保。然而,这种外在的符合却从更深层次上源于一种内在的同一,即“思想实体和广延实体其实是同一个实体,不过时而通过这个属性,时而通过那个属性去理解罢了。同理,广延的一个样式与这个样式的观念亦是同一个东西,不过由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E2P7S)。可是,当斯宾诺莎说广延样式与该样式的观念是同一个东西时,并非就个人而言,而是就神而言的,因为在人心的层面,个别观念与它的对象并非直接同一,只有在神那里二者才真正同一。既然在神之内,观念与其对象是同一的,那么就不存在二者是否符合的问题。
总体来看,《伦理学》第二部分(“论心灵的本性和起源”)的前十个初始命题根本没有涉及人和人的心灵,而只是在神以及神的思想属性层面考察认识机制。所以,此阶段之论述彰显的不是人的心灵在认识,而是神在认识;这种神的视角贯穿斯宾诺莎知识理论的始终,而认知的终极动力也被定格于神以及神的思想属性本身。
三
通过对认知的终极动力的界定,斯宾诺莎排除了以“被知觉的事物”或“人的心灵”作为阐释认知动力之出发点的做法,同时也断绝了主体性哲学的通路。*É. Balibar, “A Note on ‘Conscientia/conscience’in the Ethics”, Studia Spinozana, Könighausen & Neuman, 1992, p.37.然而,他在《伦理学》中又明言:“人的最高幸福和至福就是在生活中尽可能地完善我们的理智和理性,因为至福不外是由对神的直观知识而产生的心灵的满足。而完善理智不是别的,只是去理解神、理解神的属性以及理解由神的本性必然性而出的诸行为。”(E4App.4)而为达此目标,我们所依靠而且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知识,是作为有限思想样式的人心所能获致的知识。所以,“我们必须考察那些犹如手牵手一般引导我们达到关于人心及其最高幸福之知识的东西”(E2Pre) 。由此,考察人心的本质及其获取知识的途径就不可或缺,而人心的认知动力问题自然也包含于其中。可是,在展开具体探讨之前,我们需首先对人心的本性做进一步说明。
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的心灵是一种表现了神的思想属性的有限思想样式,“最初构成人心的现实存在的东西不外是一个现实实存的个别事物的观念”(E2P11)。而这个构成人心之观念对象的东西,只是某种现实实存着的广延样式,亦即人的身体以及身体的诸感受(E2P13)。所以,人心实质上就是它的现实实存的身体的观念。那么,心灵如何具有关于身体的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心灵本身如何成为身体的观念呢?既然心灵作为一种观念只是样式而非实体,所以它根本不可能通过身体的诸情状对它的直接触动而具有身体的观念,况且斯宾诺莎的属性平行论彻底断绝了这种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同时,心灵之为身体的观念,并不意味着心灵主动地对身体形成观念,因为作为一种有限样式,心灵本身并没有绝对的权能(potestas)来对某个对象形成观念。当斯宾诺莎说“观念是由心灵所形成的心灵的概念”时,这个“形成”更多是隐喻意义上的,而不具有实在价值。*F. Mignini, “Spinoza’s Theory on the Active and Passive Nature of Knowledge”, Studia Spinozana , Walther Verlag, 1986, p.47.而且心灵之为身体的观念是不能唯独通过心灵自身来解释的,而是依然要参照着神才能得到阐明。“人的心灵是神的无限理智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说,人的心灵知觉到这物或那物之时,我们不过是说,神具有这个或那个观念,但不是就神是无限的而言,而只是就神为人心的本性所阐明或就神构成了人心之本质而言。”(E2P11C)因此,心灵之所以是它的身体的观念,首先是因为在神之内有关于它的身体的观念,其次是就神构成了人心的本质而言(这是就神被个别心灵所分殊而言)。同样,我们对身体的诸情状之所以具有观念也依照这个模式得到解释:“在构成人心之观念的对象中,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必定为人心所觉察,换言之,在心灵中必然有关于所发生之事的观念。”因为“在任何观念的对象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在神之内都必然有关于此发生之事的认识,但这是就神被认作为同一对象的观念所分殊而言,也是说,只就神构成某种事物的心灵而言。所以,在构成人心之观念的对象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在神之内必然有关于此发生之事的认识,这是就神构成了人心之本性而言,换言之,在心灵之中必然有关于此发生之事的认识或者说心灵觉察到了它。”(E2P12&D)因此,人心所具有的观念(包括身体的观念、身体一切感受的观念,甚至一切事物的观念)最终都必须通过神才能得到解释。
在上述的讨论中,斯宾诺莎已触及人心的具体认识问题,但他依然没有对人心的具体认知动力展开探讨,甚至以知识理论为核心的《伦理学》第二部分也没有对此做出直接阐述,而只是对三种知识*斯宾诺莎将知识区分为三种形态:想象或意见是第一种知识,它是从泛泛经验和迹象得来;第二种知识(或理性)是从对事物的特性所具有的共同概念和充分观念得来的观念;第三种知识或“直观知识”是由神的某些属性的形式本质的充分观念出发进而达到关于事物本质的充分知识(Cf.E2P40S2)。的本性、特征和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对人心的认知动力的具体考察则被融入于《伦理学》后三个部分对情感和伦理生活等问题的分析之中。这是因为斯宾诺莎对知识的探讨与他对人的情感和伦理生活的分析有着内在关联——唯有通过知识,我们才能获得自由并达到伦理上的幸福生活;此外,只有到了第三部分他才引入对具体存在者而言至关重要的存在论法则,即“自我保存原则”。后者是斯宾诺莎哲学中继第一重基础——即绝对无限的神——之后被明确提出的第二重基础。*A. Negri, L’anomalia Selvaggia: Saggio su Potere e Potenza in Baruch Spinoza, Milano: Feltrinelli, 1981, pp.176-188.而对由具体样式构成的世界进行阐释恰恰更依赖于第二重基础。
在由神所产生的个别事物层面,斯宾诺莎一开始就提出了死亡的外在性原则,*[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页。亦即“若不通过外因,任何事物都不能被消灭”(E3P4)。换言之,“任何事物,就其自身来看,莫不努力保持其自身的存在”,因为“个别事物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表现了神的属性的样式,这就是说个别事物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表现神据之存在和活动的神的力量的东西。因此,任何事物,就其自身来看,都尽可能努力保持其自身的存在”(E3P6&D)。而“一物竭力保持自身存在的力量或努力(conatus),不是别的,只是那物自身既定的或现实的本质”(E3P7D)。既然就其本质而言,“任何事物,不论其完满程度如何,总是能够依据它由之开始存在时同样的力量以保持其自身的存在”(E4Pref.),那么,作为有限样式的个别事物,无论它的实存,还是它的本质,都必须从保持自身存在的力量或努力这个角度得到界定和理解。当神依其自身的本性必然性把具体事物产生出来以后,事物就负载了积极肯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也就是神的力量本身。(E4P4D)正是这种现实力量赋予事物以实在地位并彰显出其实存的自发性和肯定性。同时,也正是这种力量使事物具有生命——无论是神还是作为有限样式的个别事物,它们的生命都是由鲜活的力量得到根本规定,而不以灵魂或心灵作为生命之本原。*S. Zac, L’idée de vi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pinoza, Paris: PUF, 1963, pp. 93-103.然而,这种“保存自身存在的努力”并非单纯惰性的保持,更具有积极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事物追求的不是仅仅延续自身单调的持存,而是不断追求力量的提升和自身实存的完满。*E. Curley, Behind the Geometrical Meth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15.正是依据事物的这种不断保持和提升自身之实存力量的倾向,我们才说斯宾诺莎在有限样式的层面延续并深化了他在实体层面所彰显的动力性原则。
而以上从一般层面就有限样式所说的一切同样适用于观念和作为观念的人心。一旦被产生出来,人心就具有了现实的实存,既有自身之本质,也具有在时空中不确定的绵延;同样,在生成之时,心灵也具有了把它生产出来的神的力量,并据此力量来保持其自身的存在。因此,虽然人的心灵并非自在自为的实体,亦不具备绝对的直接性和自主性,但是由于人心是由神所产生并分有神的力量,从而也就具有自身的生命、活力和肯定性——只不过这些必然在一定限度之内来理解。因此,“无论心灵具有的是清楚明晰的观念,还是混淆的观念,它都努力在不确定的绵延中保持其自身的存在,并意识到它的这种努力”(E3P9)。既然心灵的努力或力量就是心灵的本质,并且同其他任何事物之本质一样,心灵的本质只确认心灵自身之所是与心灵自身之所能为,而不确认心灵自身之所不是与心灵自身之所不能为,所以,心灵仅仅努力想象足以确认或肯定它的活动力量的东西(E3P54D),并在这种肯定的过程中,不断追求自身力量和完满性的提升。但是,由于心灵乃是现实实存的身体的观念,所以心灵的这种肯定和追求并非简单对准自身,而是以身体作为直接的对象:“我们心灵之努力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倾向就是要肯定我们身体的存在,任何否定我们身体之实存的观念都违反心灵之本性”(E3P10D);既然“任何提升或降低、促进或阻碍我们身体的活动力量的事物的观念都会提升或降低、促进或阻碍心灵的思想力量”(E3P11),所以“心灵总是尽可能努力去想象足以提升和促进身体之活动力量的东西”(E3P12)。正是借助这种途径,心灵肯定和提升自身的实存与活动力量。而心灵的这种努力实质上就是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认识力量并不断增加自身的知识,因为心灵的力量仅仅为知识所决定。(E5P20S)因此,在具体实存过程中,人心最初的认知动力正是来源于它自身固有的这种肯定性的努力或力量。
四
然而,作为一个具体的实存物,心灵及其保持自身的努力不会单纯局限在其原初的生成状态,而是必然进入具体的实存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人心保持自身的努力首先在“想象”中展开自身,亦即心灵总是努力想象足以提升和促进身体之活动力量的东西。因此,求知动力首先表现在心灵的想象之中。可是,既然斯宾诺莎对作为想象的惊奇进行了严厉批判,而此处我们把认知的动力重新引入到想象之中,这难道不构成矛盾吗?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惊奇只是想象的一种形态,却不能穷尽想象之全部。虽然惊奇被排除于认知动力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想象本身也完全被排除。相反,在斯宾诺莎的认知理论中,最初的具体认知动力正是在想象的范围内运作。人心保持其自身存在的努力首先就表现为它想象着足以提升和促进身体之活动力量的东西,也就是想象足以提升和促进自身活动力量的东西。
而这里所说的想象并非心灵本身所进行的随意联结(例如构造出“飞马”、“金山”等意象),更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尽管它们也是想象,但却不构成想象的根本规定形态。在斯宾诺莎那里,想象的形成和运作始终与人体受外物作用后形成的感受(affectio)——斯宾诺莎称之为“事物的形象(imago)”——紧密相关。而人体之感受的观念总是将外物呈现为即在当前,当心灵以此方式考察事物时,我们就说心灵在想象。(E2P17S)而当心灵努力想象足以提升和促进身体之活动力量的东西时,它并非随意地构造,而是同样遵循因果决定机制,始终以身体之既有的感受或既定的事物形象为前提。想象的活动是一种联系或联想的活动,它力求把自身中的观念与实存事物之形象的观念按照因果机制结合起来,以便形成观念之间的连锁,构成合乎逻辑和法则的观念形态。而实质上说,任何知识或知觉都是按照观念之间的因果决定机制构成的:“对结果的认识有赖于并且包含了对原因的认识。”(E1A4)此外,虽然想象保有了那种从神的力量而来的保持自身存在的努力从而具有自发性,*S. Zac, L’idée de vi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pinoza, p.109.但它却不具有绝对的自主性,而是始终处在被决定的状态,而这种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心灵之外的原因。具体而言,虽然心灵总是竭力想象足以提升和促进身体之活动力量的东西,但究竟哪些东西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却非心灵先天就能知晓,而是需要在现实的绵延和实存过程中,通过与外物的遭遇才能把握,因此,在想象时,心灵并非以自身之本性作为全部的或充分的原因,而只以之作为部分的或不充分的原因,由此,处在想象之中的心灵就是被动的,它所具有的乃是被动的情感或激情。(E3Def2)作为被动状态,想象更多地由不充分的观念——即片段的和含混的观念——所构成,并因此成为错误的来源或原因。(E2P41)但是,斯宾诺莎却并未因此全盘否定想象的价值,因为“心灵的想象,就其本身来看,并不包含错误,换言之,如果说心灵犯错误的话,这不是因为它想象,而是就它缺乏一种观念而言——这种观念足以排除它想象着呈现于它面前之物的实存。如果当心灵把不存在的事物想象为如在当前,同时,又能够知道那些事物并不现实实存,则心灵反将认这种想象为其本性的才德,而非缺陷”(E2P17S)。因此,虽然想象可以是错误的原因,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求知动力的源发和表现之地,况且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知识本身并不必然为真,而是既有真知识,也有错误的知识,而即便是错误的知识也必然有其原因。
与此同时,作为不充分知识的想象也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G. Deleuze, Spinoza et le Problème de L’expression, Paris :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8, p.268.是我们最原初的现实生活状态。或者说,想象就是我们所知觉的直接的世界,是我们在想象的统治下生活于其中的直接世界,正是想象构成了后者的本质。*L. Althusser, “The Only Materialist Tradition: Part I: Spinoza”, The New Spinoza, ed. W. Montag and T. Stolz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6.因此,想象乃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初方式,是我们对世界、事物和我们自身取得知识的初始途径。在想象的支配下,人心对事物及其所遵循的法则并不具有充分的或清楚明晰的知识,而是始终受运气和偶然的支配;所以,并非所有的想象对我们的生活来说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想象都能成为我们进一步求取知识的动力,因为有些想象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使我们感受到剧烈的痛苦,*例如欲求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东西、在想象中跟一个比自己强的人进行比较,等等,都会引发痛苦。而痛苦本身就意味着人心从较大的完满向着较小的完满过渡(E3P11S),意味着心灵自身之实存和思想力量的降低。因此,任何引发痛苦的想象非但不是认知的动力,反而使心灵失去它原有的力量。
当然,并非所有的想象都会引发痛苦,相反有很多想象给心灵带来了快乐。而快乐就是人心从较小的完满过渡到较大的完满 (E3P11S),此时心灵具有了更多实在性和力量。尽管处在想象之下的快乐是被动的情感,而且这种被动的快乐可能会过度(乐极生悲!),但就其源初的生成和实存机制而言,这种快乐却是好的,因为心灵在感受快乐之时,它不仅感到自身力量的肯定,也体验和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和实存力量的提升。这种作为心灵之情感而呈现的快乐同时也标示了身体层面的一种良好的遭遇机缘,是我们的身体在与外物遭遇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契合。我们在想象之下感受到的快乐,首先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和外物之间具有共同的东西或一致之处,从而能够进入到一种良好的组合关系之中。*[法]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第22页。正是这种快乐的情感推动我们获取关于事物的知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愿意去认识那些与我们相一致并给我们带来益处的东西,而那些与我们相异质并带给我们伤害和痛苦的东西,我们最初更多地选择逃避,这恰是依照想象来生活的人最常采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因此,从想象的视角来看,只有那些带来快乐的想象才能成为推动我们进一步去求知的动力,正是这种形式的想象可以将观念和心灵内在的力量发挥出来并使之在因果机制下构建观念之间的联结与组合,从而形成新的观念或知识。
然而,想象和快乐情感的作用决不止于此,实际上它们还是使人心从不充分的观念过渡到充分的观念并使人心从依靠想象来生活过渡到依靠理性来生活的关键。当心灵因具有快乐情感而觉察到身体与外物之间的共同之处或共同特性时,它同时也具有了关于这种共同特性或契合关系的表象或观念,这些观念就是“共同概念”(notiones communes),而后者正是理性的基础。(E2P44C2D)与处在想象之中的不充分观念不同,共同概念是充分的。这种充分性源于共同概念之对象的共同性,换言之,作为共同概念之对象的共同特性同等地处在事物的部分和总体之中;而“当某种东西为一切事物所共有且同等地处在部分和全体之内时,它必然充分地被构想”(E2P38)。所以,共同概念本身就是充分的和真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自然之中的普遍性。*M. Gueroult, Spinoza (II, L’me), Paris: Aubier, 1974, p.326.当想象只对那些带来快乐的事物具有探索和求知的欲望时,理性则力求对一切自然物(包括那些会对人造成伤害的东西)都有所认识。所以,理性所进行的是一种完整的把握,是一种真正的理解。此时,心灵不再按照自然的通常秩序来考察事物,也不再从个别性来考察事物,而是从某种永恒的形式下来审视整个世界,并把握自然的永恒法则,但归根结底,这种转化的基本前提和动力依然是心灵保存自身存在的努力。*就共同概念和理性本身的具体生成过程,参见笔者在《论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理性生成论》(《现代哲学》2015年第2期)一文中的详细讨论。
综上所述,在作为有限样式的人心层面上,认知动力源于事物保持自身存在的力量或努力,后者不仅是一条存在论原则,也是一条认识论原则,更是斯宾诺莎的认知动力理论的最基本原理。而想象则是人心保持自身存在之努力的最初表现形态。通过想象那些足以肯定和提升身体之活动力量的东西,心灵同时肯定和提升其自身的思想力量,也就是肯定和推进自身的认识。如果这种想象能够产生良好效果,给人带来快乐,那么它必然体现人的良好遭遇机缘,使人心体验到自己与外物之间的一致之处。也正是这种快乐推动着依靠想象来生活的人愿意去认识给他带来快乐的事物,并同时为从想象过渡到理性准备前提条件。
(责任编辑:周小玲)
Spinoza and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
Wu Shubo
Wonder has often been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philosophy, even of the knowledge in general by western philosophers, which is also clearly manifested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However, as one of the famous representatives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Spinoza makes a fierce critique of wonder and eliminates its cognitive values. For him, the essential dynamic of cognition should been firstly sought in the nature of God and his attribute of thought as productive power. Only after establishing this horizon, we can speak of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 in the particular minds produced by the attribute of thought in God. And on the level of human mind, the ultimate dynamic of cogni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conatus of human mind’s preserving its own being. It is this conatus that makes the human mind preserve and enhance its own power of existence and that of thought, which is the most immediate impetus for the mind to pursue knowledge. Therefore,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 and even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in the whole take the ontology as their foundation.
Wonder; God; Idea; Mind; Power or Conatus
2016-07-10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斯宾诺莎伦理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5YJC720028)的阶段性成果。
B563.1
A
0257-5833(2016)11-0125-09
吴树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092)
——从纳德勒的评价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