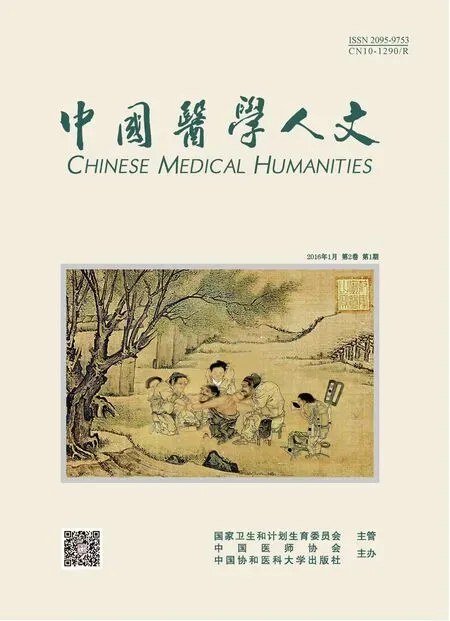那年 他19岁
文/陈 阳
那年 他19岁
文/陈 阳
作者单位/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时间过得很快,研究生生涯的一半快要过去了。我离开了病房,开始着手我的课题工作,回想在门诊和病房里一年多的时间,见了很多病人,但有一个人,我始终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见他,是我刚刚上手临床工作,开始独立管病人。那天,导师说新收了一个疑诊白血病的年轻人,让我做主管医生。一进病房,看见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因为贫血,皮肤和嘴唇有些苍白,但精神很好,也不聒噪,很有礼貌,并配合问诊和查体。我心里默想,这么年轻的小伙,但愿不是白血病,问了病史,做完体格检查,需要给他做骨髓穿刺术,来协助诊断。一听要骨髓穿刺,他妈妈有些害怕。而他倒不怕,还让我做完之后给他看看骨穿针。他看了看骨穿针,惊呼:“骨穿针真粗!”那表情像是完成了一项挑战一样,充满着骄傲,还说要拍下来给他的高中同学看看。我不禁哑然,是啊,他只是个19岁的高中生,还是个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病,有多严重,还一心想着出院后向同学展示自己的勇敢。
很快,大部分的检查结果都回来了,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我没有太多的惊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的父母决定暂时不告诉他病情,我亦这样想,他还如此年轻,这样的结果很难承受。确诊之后,首先是化疗,如果化疗期间一切顺利,病情缓解,才有机会进行骨髓移植治疗。我一直害怕他问我有关病情的事情,可他一直都没有问。化疗过程还算顺利,结束后出现了骨髓抑制,免疫力低下,合并严重的肺部混合感染。抗生素都用上了,但体温每天都在38摄氏度以上,我每天都去看他好几次,可唯一能做的只是摸摸他的额头,鼓励他,希望能熬过骨髓抑制期。有一天,他很虚弱地躺在床上,比刚来的时候瘦了很多。我和平日一样,安慰地摸了摸他的额头,嘱咐多喝些水。他突然问我:“陈医生,我是不是治不好了?”我有些猝不及防,但马上说:“你想什么呢,坚持过骨髓抑制期就好了,你很快会好起来的。”他笑了笑说:“我以后也想当医生,就像你一样。”过了一周后,他体温控制住了,精神也好了很多。
有一天晚上,我在值班,他妈妈过来和我聊天,说着说着,她哭了,我才知道这孩子在4岁时父母便离异了,一直跟着爸爸生活,因为生病,妈妈才过来陪护。为了给他治病,爸爸妈妈的房子都卖掉了,但问题是他姑姑想让他妈妈和爸爸再怀一个孩子,给他做胚胎移植用,这让他妈妈很为难,所以过来向我咨询胚胎移植的事情。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无助的母亲,且不说伦理是否允许,但一个胚胎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只能告诉她这个计划行不通。后来,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等感染控制了,用爸爸的骨髓做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又过了些天,骨髓抑制期已过,血细胞都恢复正常,但因为合并有肺部真菌感染,还得继续输注抗生素,定期复查胸部CT。因为病房里重病人比较多,容易交叉感染,且在这种三甲医院里费用也较高。他们的家不在这儿,陪护也不太方便,所以最终决定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他便出院了。
过了大概一个月,需要进行第二个疗程的化疗,他比之前胖了些,精神好很多。我为此感到高兴,希望可以尽快做移植。但事情却没有那么顺利,胸部CT显示肺部有一个很大的结节。活检提示是个真菌结节,需要手术切除。在胸外科会诊后,医生认为风险比较大,不支持手术治疗,建议保守治疗。抗真菌的药物一天就要一千多,但也很难使得这个感染灶完全吸收。每天例行查房时,他总会目光穿过层层人群,对我笑笑,师姐为此还调侃过我,可我很替他难过。我也为自己,为当前医疗水平的局限性感到愧疚,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化疗结束后,他便出院了,之后再也没有来住院,也没有来门诊复查。
过了很久的一天,我突然看见一条新闻,标题是山西高三男生患恶性白血病签遗体捐赠申请,我的心开始突突地跳,会不会是他呢?我点开一看,真的是他,新闻还配了照片,他带着口罩躺在病房上,爸爸站在旁边,一脸的疲乏与苍老。是他,就是我的那个年轻患者,顿时心中百感交集!感动?敬佩?惋惜?不!更多的是心疼,心疼他多舛的命途,心疼这个本该在篮球场、在课堂、在知识的海洋里肆意遨游的年轻人。不知道他可曾有过钦慕的姑娘,现在却只能在病床上忍受病痛、直面死亡。噢,不!我应该是敬佩,敬佩他勇敢面对残酷命运的勇气;敬佩他积极战胜病魔的坚强;敬佩他在面对命运极大不公后,仍拥有的巨大仁慈。我感觉喉咙那儿有什么东西堵上了,说不出话来。我木然地坐着,想着他,想起初见时的神采,想起每天查房时对我的会心一笑,想起对我的信任,想起那份乐观和坚强。
后来,我在门诊遇见他的姑姑,知道他做了肺部手术,正在北京的某家医院准备做移植,我真心感到高兴,只是在想,那些难熬的日子,小小的他是如何熬过来的。曾经看过席慕蓉的一段话: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一个人单独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对他,我唯有祝福一切顺利,对我,我想不为别的,就为了这样的患者,也应该励志做一名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