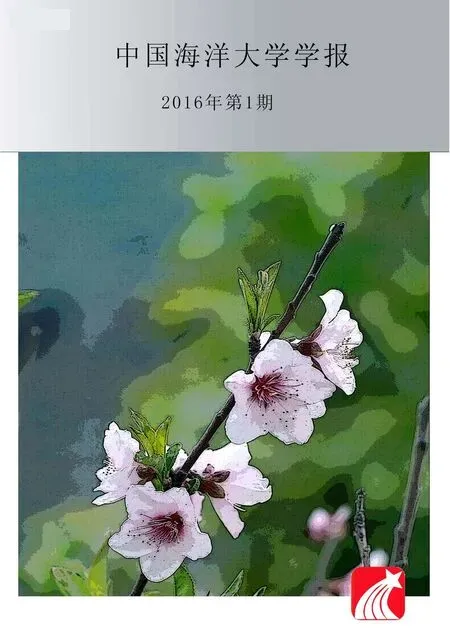论新历史主义兴起之文化语境与理论意义*
卢 絮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广东 广州 528200)
论新历史主义兴起之文化语境与理论意义*
卢絮
(华南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广东 广州 528200)
摘要:在名目繁多、杂语共生的理论批评时代,新历史主义能脱颖而出,并从最初的饱受争议和响应者众多,到世纪末的相对沉寂,再到最近几年来研究热潮的回归,证明新历史主义有其自身的理论优势和适应时代和理论发展的能力。对于新历史主义兴起之初的文化语境的回顾和分析,挖掘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与当代意义,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运用这一理论。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文化语境;理论意义
新历史主义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美国文学研究者们对于统领文学批评领域将近半个世纪的“新批评”感到沉闷而乏味,其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使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和历史,陷入狭隘、封闭的纯文学内部世界;而7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潮以其极端的解构思维和“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简单武断又把文学研究推向了一个虚无境地和纯粹的能指游戏中。美国的文学批评研究处在了一个相当微妙的十字路口,要不继续德里达解构主义思路朝着传统、现实甚至未来开炮,质疑、颠覆和解构一切包括自身,显然这条道路越来越让人心存疑虑;还有便是回到过去形式主义的老路上,进行文本细读和抽象的形式结构分析。
一、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经历与学术环境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显然两条路都不愿选择,这点我们可以从格林布拉特的学术历程看出。上世纪60年代他在耶鲁大学接受了严苛的形式主义学术训练,对于自30、40年代就在美国开始流行,以威廉·威姆斯特和克林斯·布鲁克斯为代表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文本内部分析的学术方法了然于心却不以为然。60年代中期,格林布拉特有机会在英国剑桥留学,当时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学研究中引入的经济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让他大开眼界,之后他广泛涉猎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阿尔都塞、本雅明的作品,这无疑使他得以窥探文学文本以外的世界,并采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视角。70年代,格林布拉特在伯克利任教,经历了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理论界的流行,哈特曼和保罗·德·曼等文论家对他不无影响。期间,米歇尔·福柯也来到伯克利工作,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历史谱系学的研究方法,其权力话语分析和非连续性历史观念,对一切整体化、中心化、科学化及真理的质疑无疑给格林布拉特以及后来的新历史主义者们极大的启发和影响。
格林布拉特的个人学术经历恰恰反映了新历史主义诞生之前美国文论的发展动向。如果我们把视界再扩大至整个西方理论界,时间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条以语言论为核心建构的西方文论线索就会浮现出来。对语言本身的兴趣,对文学词语、形式和结构的关注成为20世纪文学甚至哲学问题的中心,围绕着语言研究而派生出来的文论流派相继产生:从现代主义文论到俄国形式主义,从英美新批评到心理分析和结构主义文论,随后从对这些文论的初步反思和反拨,即解构主义文论到阐释接受文论,无不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带着语言乌托邦的耀眼光环。“飘扬在彼得堡上空的旗子”成为这种语言乌托邦的象征,表达着文学独立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自由理想。然而,在罗兰·巴特和符号学解析和德里达对语言延异的无穷追问中,这种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受到彻底怀疑和解构。语言的不确定性,阅读中不可避免的误读和曲解,都不断赋予主体以新的阐释权力和能动创造性。对主体的重新发现预示着西方文论逐渐走出“语言的牢笼”,回归历史和文化语境。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历史是文学的最终能指,正如它是最终的所指。”[1]文学与历史这种长久分离的状态必然要得以纠正,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文论发展的隐秘逻辑,也是西方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和理论革新运动带来的直接后果。
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性解放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席卷欧美各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人生观都成了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出现了反对主流社会,反对性别和种族歧视,反对一切中心和权威,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潮流。政治家们疲于压制和应对动荡的时局,而激进的理论家们则空前活跃,各种足具反叛意味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出现井喷状态。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种种新的理论流派相继出现,新历史主义也是其中一员。新历史主义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代表者路易斯·蒙特罗斯曾说:“文学研究的重新定位至少始于1980年代早期,大部分批评者的价值观形成是在文化试验和政治动荡的1960年代,那时他们还是大学生。而197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给这一代批评家们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制度和知识层面的影响,当时他们大多正在摸索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当然,受时代影响的总体情况因人而异,因特定的性别角色、个人观念和所处的亚群体而异。总体上,这一代批评家顺应了1980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气候。”[2]正是这种动荡的社会文化环境滋养和促生了新的文学理论,它们分享的共同原则是:反对传统文学中审美、道德和本体论原则;开始从本质、内在的永恒规律追寻转向建立历史、语境和突发性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任何封闭性、总体性和普世性原则,对既定的文学价值和文学边界产生质疑。实际上,多元并存且更迭频繁的理论局面是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而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美国文论界与历史的绝缘状态也成为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催化剂。现实要求美国文论界在自我反思中寻求理论的更新与突破,而恢复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和历史维度成为学者们首先思考的问题。
二、历史观念的全面革新与新历史主义的应运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变迁带来的还有一个后果,便是人们历史观念的革新,历史进步和历史理性受到质疑,历史规律和原则被颠覆。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到波普尔“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从巴尔特“作者之死”到历史学者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终结论”,历史哲学从一种整体上理解历史,把握支配历史的基本原则及其隐含意义的方法受到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大写的历史”被“小写的历史”取代,“国王和英雄的历史”被“平民日常生活的历史”取代。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关照下,重新梳理历史哲学的基本线索,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诸多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齐美尔、汤因比、科林伍德、克罗齐等,都认为历史是各种各样关于过去事件的记载,至于历史真实不过是对于这些事件的不同的评判标准,而优秀的历史学家必定同时也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克罗齐曾说“历史只能把拿破仑和查理大帝,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和意大利统一,当做具有个别面貌的个别事物再现出来。”[3](P514-515)波普尔则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想象力的贫困。”“历史决定论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把历史解释当做学说或理论……他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4](P103,120)当历史与想象力挂钩,与主体选择和解释挂钩,那么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也就不再明晰。
实际上,历史与科学的分野同时也拉拢了历史与文学的距离,20世纪人文学科内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更是把历史学家的目光集中到了对历史认识本身的反思,和对历史叙事的语言性的强烈关注。传统历史主义把语言当做透明体,认为历史叙事和历史真实可以直接划上等号,而历史叙事学将语言视为历史真实与意义表述之间的中介。海登·怀特是历史叙事学最坚定的捍卫者,他的成名作《元历史》(1973)被看作是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扛鼎之作。海登·怀特把历史作品看做是“叙事性散文结构的一种,称它们一般而言是诗学的,具体而言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在修辞和比喻的层面取得沟通”。[5]他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构成了任何一部史学作品那种不可还原的‘元史学’基础”。[6]在他看来,任何历史都是一种修辞想象,历史是被构建的,而且是被诗意地构建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历史不过是作为修辞和文本的历史,其叙事过程和模式取决于叙事者的修辞态度、方式、阐释角度和价值立场。海登·怀特显然不是唯一的历史叙事学者,德里达断定:“只有关于书写本身的历史,只有‘符号化真理系统’的历史。”[7]福柯认为:“断裂是任何历史阶段思维的主导方式,话语结构是任何历史形式的终极所指。”[8]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也不得不同意:“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而我们也只有通过事先的文本化和叙事化才能接近历史真实。”[9]同时,詹姆逊还不忘强调“只有在追寻不被中断的叙述轨迹时,使历史中被压抑和掩盖的事实回归文本表层时,政治无意识的信条才能得以贯彻和体现其必要性。”[10]后现代主义学者汤姆森·威利则宣称导致“历史书写的将来只能是诗学的形式,除了想象力以外并不能反映任何历史或者现在。”[11]
历史叙事学几乎成为了当代历史学主流,也刷新着当代人的历史观念,即对过去某种权威的历史说法和唯一绝对的历史叙事的怀疑。当然,新历史主义也秉承着这样的叙事历史观或称之为语言历史观。格林布拉特不止一次提到他对想象力的重视,“文学研究者应该把他们所有的想象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对于历史叙事,他问道:“存在对历史事件的单方面的正确的解释么?人们曾经相信这种唯一的宏伟的历史演进模式,但是现在还有人真正相信这个么?任何对自己负责的人都应该承认这种改变!”[12]可以说,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之所以与传统历史主义有根本的区别,前提便是两者历史观的迥异。历史观念的彻底革新、历史叙事学的兴起和流行,福柯式知识考古学和历史谱系学的后现代解构历史思维,这些都促使格林布拉特和新历史主义学者们重新审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导致了文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向,即“历史转向”。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无疑是美国批评界勇敢站出来提出“历史转向”呼声的第一人。1982年,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权力》一文中第一次使用“新历史主义”一词,用来总结这些论文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也与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原则大相径庭的理论和实践特征。“新历史主义”无疑可以代表美国文论研究领域恢复对于文化、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关注的趋势,反映了理论家们走出语言与符号的象牙塔,重新投入文化、历史批判的时代洪流,并介入当下社会生活的强烈愿望。就如蒙特罗斯说:“人文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纠正学生们认为历史一去不复返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即生活在历史中,历史的形式和压力在他们主观的思维、行动、信仰和欲望中清晰可见。”[13]由于长期形式化思潮的主导,人们的历史意识已经空前匮乏,因此,重新唤醒人们的历史意识,重新划定文学的边界成为新历史主义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例如,1986年在现代语言学协会的主席致辞中,希利斯·米勒略带沮丧,甚至夸张地说:“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几乎是整体性的转向:从具有方向性意义的理论指向了语言本身;相应地,转向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性别状况、社会语境和物质基础。”[14]珍·霍华德说:“突然间,对历史的冷漠被一种狂热的兴趣所代替。文艺复兴研究的期刊里充斥着的是把弥尔顿、多恩、斯宾塞的作品放在历史语境中研究的论文。……而这种趋势只是体现了从后结构主义转向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的,一场规模更大的批评运动的一部分。”[15]保罗·康托尔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评价:“格林布拉特的作品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典范。……八十年代初,新历史主义在迅速席卷文艺复兴研究领域后开始向其他领域开枝散叶,到目前为止,几乎文学研究的每个时段,如果不是由其主导,也深受其影响。”[16]爱德华·佩驰特更是在文章中声称:“一个幽灵正出没于批评界——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幽灵。”[17]
新历史主义当然不是幽灵,不过这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却真实地反映出这一理论潮流在刚兴起时在美国文学界掀起了极大的风波。据记载,1993年3月,格林布拉特被纽约时报杂志评为“学术巨星”(academic superstar),称他正处于文学批评领域的“炙热的中心”(red-hot center)。[18]迄今,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早已被熟知和应用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领域的各个层面。
三、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贡献与当代意义
新历史主义走过三十年,缘起于对新批评形式主义的不满,到重构历史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再到纠正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虚妄之途,使文学研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从整体性、目的性宏大叙事转向探寻地方性知识、历史的细微末节处和弗兰克·兰垂契亚所说的“最坚实的和最贴近地面的生活肌理”[19]中,新历史主义以其始终秉持的理论开放态度和广阔视野,以及脚踏实地的实践研究精神,为所谓的历史虚无论、理论终结论、文化危机论等各种乌托邦论调敲起了警钟,并预示着“一个更为伟大的理论革命的开端。”[20]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尼尔·陆登庭在任命格林布拉特为人文学科大学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职位中的最高荣誉)时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没有人能像格林布拉特那样改变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整个方向……他的真正贡献远远超出了方法论的意义。”[21]总的来说,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有以下几点理论贡献和当代意义。
首先,新历史主义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理论之间互通有无,平等对话的可能,即建立多元性理论对话空间的可能。新历史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受到了当代各种主流理论的有力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在博采众长、吸取各类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拥有了宽阔的视野。如前文提到格林布拉特早年熟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让他跳出了形式主义的牢笼,开始关注文学中的政治、社会、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同时对历史和文化的物质性加以思考;新历史主义积极吸取福柯的历史断裂观念和权力话语理论,把历史的非连续性、事件性和偶然性因素纳入文学研究的视域,对最边缘处和最隐蔽处的权力关系条分缕析,重新建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适应了历史观念的时代革新,认同关于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抵达历史的观点,但他们反对解构主义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极端观念,在肯定历史和文化的文本性质的同时,也不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存在;新历史主义采用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观念和“厚描”的研究路径,重视文化塑造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和自我塑型过程。
其次,新历史主义使当代文学理论成功走出语言学转向后的结构主义、新批评、解构主义等总体上属于形式主义分析的文论金字塔,重新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维度。但这绝不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或作家、作品背景分析的简单回归,即有些学者认为的社会中心-作者中心-作品中心-读者中心-社会中心新的轮回。实际上,文学作为某段历史、文化时期的“反映物”或者“装饰物”的性质已经被彻底否定,文学的主体性功能得到极大张扬,文学和历史的二元对立关系被一种相互指涉、复杂交织的关系所代替,文学不仅是成为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推动者和建构者。至此,文学不再是高居于文化神坛之上不可企及的精神贵族的专属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从艺术殿堂中走出来,变成了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新历史主义学者眼中的文学史也不是仅仅包括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的历史,因为“文学的历史是体现个人或体制意愿的历史”,“文学史永远只是使文学成为可能的历史”,“文学史终究有缺憾。”[22]文学和非文学的边界要重新修订,或者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在建立与消亡之间不停摆动。就如,文学总是处于想象与真实的交汇处,虚构与现实的循环往复中,或在怀疑与信仰间不停争斗一样。
第三,新历史主义主张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视角,把文学置回历史文化语境,在这一过程中,新历史主义对于主体的历史地位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格林布拉特不止一次谈到,“新历史主义的中心点就是对主体性的质疑和历史化。”[12]格林布拉特并不相信有全然独立于历史文化结构之外的所谓自由主体,“在我的全部文本和资料中,我所能说的是:没有纯粹的时刻和没有约束的客观性,确实,人类主体本身开始似乎就非常不自由,不过是特定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的产物。”[23]这种主体观和西方现代性发生以来对主体的原发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肯定和宣扬是有区别的,同时也和形式主义文论中把文本当做唯一独立、自主的主体截然相反。实际上,新历史主义反对主体和客体,或主体和结构二元对立的关系,认为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提倡一种主体间性的理念。对主体和自我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新历史主义研究的重点,但是它显然反对那种普遍性的超然的主体存在,而更乐意突出主体的不稳定性、可塑性(fashioning)、历史性和协商性(negotiation)。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积极能动地参与社会能量的融汇、流通和交易,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同社会文化的权力系统进行谈判和协商;另一方面,文学本身具备塑型功能,对于文学创作者、阐释者和阅读者而言,文学扮演着引导、塑造、完善、或分裂自我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完成“自我塑型”(self-fashioning)的过程。尽管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主体的产生绝不是自觉、自动的完全自我塑造过程,而是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合力的产物,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新历史主义对于自由、独立的主体是抱有幻想的,对于主体的阐释和建构功能是满怀信念的。就如格林布拉特所说:“……放弃自我塑型就是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就是放弃对自我的固执守护(尽管这个自我有可能是虚构的),就是死亡。……我觉得完全有必要保持这种幻想,即自我还是我自己的主要建构者。”[24]
四、结语
如果把新历史主义放到文论史的角度来看,是对文本批评“向内转”之后的重新反拨,是一次历史回归。我们看到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而且在更多的人文学科领域,研究者们沿着新历史主义开辟的道路,在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中,在偶然遇到的零星文本中,在不为人知的被时间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了历史的真实和文学能带给我们的所有“共鸣与惊奇”。特别是在后现代充满消极、颓丧、怀疑和绝望的“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文化氛围中,新历史主义以其特有的实用主义功能、开放包容的学术情怀和搁置理论空谈的实践操作品格获得了许多研究者的青睐,成为被寄予厚望的新世纪批评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之一。(致谢:感谢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项目(14SK10)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M]. Verso, 1978: 24.
[2] Louis Montrose, New Historicisms. Stephen Greenblatt.&Giles.Gunn, ed.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1992:392.
[3]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 (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
[7] Derrida Jacques,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M]. Newton Garver,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141.
[8] Michel Foucault, The Foucault Reader[M]. Paul, Rabinow. ed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65-75.
[9]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35.
[10]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
[11] Willie Thompson,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y[M]. Hundmills: Palgrave, 2004:24.
[12] 生安锋.透视文化、重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缔造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访谈录[J].当代外语研究,2010,(3):1-6.
[13] Louis Montrose, New Historicisms. Stephen Greenblatt.&Giles.Gunn, ed.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1992:393.
[14] Louis Montrose, New Historicisms. Stephen Greenblatt.&Giles.Gunn, ed.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1992:394.
[15] Edward Pechter,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Its Discontents: Politicizing Renaissance Drama[J]. PMLA, 1987,102(3):292.
[16] Paul A. Cantor, Stephen Greenblatt's New Historicist Vision[J]. Academic Questions, Fall, 1993:21-22.
[17] Edward Pechter,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Its Discontents: Politicizing Renaissance Drama[J]. PMLA, 1987,102(3):292.
[18] Paul A. Cantor, Stephen Greenblatt's New Historicist Vision[J]. Academic Questions, Fall, 1993:34.
[19] H. Aram Veeser., The New Historicism. In 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M]. H. Aram Veeser ed. London: Routledge,1994: 4.
[20] Noel King, The Restless Circulation of Languages and Tales: interview with Stephen Greenblatt[J]. Harvard University. Textual Practice, 2006,20(4):710.
[21] N.Rudenstine, Greenblatt Named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In Gazettle, The Harvard University , Http://www.hno.harvard.edu/gazette/2000/09.21/greenblatt.html, 2011.11.12.
[22] Stephen Greenblatt, 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J]. Critical Inquiry, Vol. 1997, 23(3): 469-470.
[23] 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256.
[24] Stephen Greenblatt, The Improvisation of Power. In The New Historicism Reader[M]. H. Aram Veeser ed. London: Routledge,1994:76.
责任编辑:高雪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ising of New Historicism
Lu Xu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eg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28200, China)
Abstract:In a varied and complex theoretical criticism age, new historicism has become prominent and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field from the initial controversy to a relative silence in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n to the return of the research fever, which proves that new historicism ha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the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new times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ise of new historicism, we find it helpful to dig out its uniqu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or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Key words:new historicism; Greenblatt; cultural contex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6)01-0117-05
作者简介:卢絮(1979-),女,湖南湘乡人,华南示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