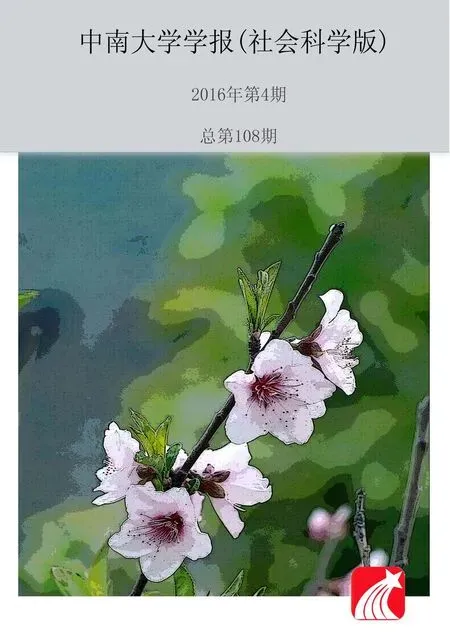关于五代“山后八军”的几个问题
李翔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关于五代“山后八军”的几个问题
李翔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山后八军”作为五代“山后”地区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史料记载出入处较多,存有概念混淆、内涵及外延不明等情况。五代“山后八军”,实乃唐末幽州刘仁恭首设于山后地区,源自八个具有防御性质的军镇,名称上沿袭幽州东北的“八防御军”而来。五代“山后八军”与宋“山后八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概念。
五代;山后八军;山后八州
五代为典型的武人政治时期,“尚武”是此时代的主调,对五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军制无疑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山后八军”作为此时期北方边地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夹杂了行政区域及军事制度变迁、边地军事特点等方面因素,并在史料中频繁出现,重要性不言而喻。胡三省在《通鉴释文辩误》中对此有过详细解释[1],今人任爱君也曾撰文论述[2],不过他们看法各异。笔者通过查阅史料发现,关于“山后八军”,存有一些不同提法,尤易与“山后八州”混淆。基于前人研究,进一步考辨五代“山后八军”的含义及澄清相关误解,便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山后八军”设立大致时间及所在区域
“山后八军”这一历史名词,两《唐书》均未见记载,最早见于《旧五代史·李承约传》和《新五代史·李承约传》中。
李承约,字德俭,蓟州人也。曾祖琼,蓟州别驾,赠工部尚书。祖安仁,檀州刺史,赠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赠太子少师。承约性刚健笃实,少习武事,弱冠为幽州牙门校,迁山后八军巡检使。[3](1188)
李承约字德俭,蓟门人也。少事刘仁恭,为山后八军巡检使,将骑兵二千人。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承约以其骑兵奔晋,晋王以为匡霸指挥使。[4](527)
幽州自中唐以来便是河朔割据藩镇之代表,广明大乱后更是游走于梁、晋之间,无异于一地方割据政权。据上述两段史料可知,山后八军巡检使乃幽州所设,盖无疑问。李承约虽有列传记载,个人履历还不够明了。其为蓟州人,曾祖出任蓟州别驾,祖、父分别担任檀州刺史、平州刺史,三州均为幽州节度下属州,可见承约家族在幽州属于有一定地位者,承约“弱冠”能为幽州牙门校亦可理解。
从承约“少事”刘仁恭,且“弱冠”出任幽州牙门校,后迁山后八军巡检使来看,承约很大可能是被幽州节帅刘仁恭表为山后八军巡检使。另,《光绪顺天府志》明确提出:“仁恭所置山后八军。”[5]参《唐方镇年表》可知,刘仁恭于乾宁二年(公元895)至天祐四年(公元907)担任幽州节度使。[6]但无其他材料可进一步确定“山后八军”的设置时间。鉴于此,笔者揆以为“山后八军 ”为唐末刘仁恭所设。
关于“山后八军”的所在区域,笔者通过爬梳史料,也能大致确认。唐末五代,飞狐口是连通幽州和河东的重要战略关隘。“庄宗攻刘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将兵三万别出飞狐,定山后,取武、妫、儒三州。”[4](54)有关这段史实,《资治通鉴》载“晋李嗣源分兵徇山后八军,皆下之”[7](8769),这里的“分兵徇山后八军”正可与上段材料“定山后”互证。可见,“山后八军”大致位置应与武、妫、儒三州有一定重合。
胡三省对“山后”的解释使这点得到确认。《资治通鉴》卷二六〇在述妫州高思继兄弟为山北之豪时,下有注“妫、檀诸州皆在幽州山北,亦谓之山后”[7](8465);同书卷二六六载“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二千”,下出注“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7](8672)。有研究者据此条,指出五代时期的山后在今北京西北,宣化至密云之地,山指燕山。[8]此说尚有修正的空间。
清代史料对“山后八军”的大致位置有了进一步解释。清乾隆年间编修的《通鉴辑览》指出其位于“居庸关古北口地”[9]。《通鉴辑览》史料价值有限,然此处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五代“山后八军”的具体位置。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檀州近古北口地,今密云。[10]可见,此说具备可信度。又,清末编修的《光绪顺天府志》认为“山后八军”在怀来、宣化地界。[5]同样,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知,武州、新州及妫州大致位于上述区域。[10]
综上,笔者认为五代“山后八军”大致处于今河北西北部至北京东北部近居庸关一线。这里的“山”有特定含义,仔细观察上述两段材料中胡三省对“山后”的解释,见其均加以“幽州山北”或“卢龙”的限定。那么,“山”应该指卢龙境内山脉,理解为今燕山、燕都山及太行山脉北段更合理点。
为什么胡三省要有此限定呢?笔者在《通鉴》胡注中又发现了“山后”的一段不同解释。《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载天福八年(公元943)十二月,契丹主集山后及卢龙兵伐晋,下有注:“山后,即妫、檀、云、应诸州。”[7](9256)参《中国历史地图集》,大致为幽州北部及晋东北,今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10]“山后八军”也处于这大区域内。
严耕望精于唐代地理,对这段地区有过详细的考证。“今山西北部,河北北缘,自西而东有管涔山,恒山,太行北段、军都山、燕山诸山脉,如链相接,为中国北方之一天然障塞,亦为中国北出草原交通之阻。”并指出此段“障塞”中有著名三关,太原之雁门关居西、定易之飞狐口居中、幽州之居庸关居东,均为天下险关。[11](1491)安史之乱以来,此区域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融合的中心区域,栖息着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其地理位置重要,民众大都骁勇善战,历来被各路军阀所窥视。
石敬塘在立国之初,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交好契丹,至此,中国北方的天然障塞尽失。契丹伐晋时的“山后”,大致为严氏所言障塞之北,故胡三省有如是解释。可见五代“山后”的概念因史实不同而有所变化。源于此,五代“山后八军”的真实含义宋以降难被世人明晰,并与“山后八州”混淆,下文将对此展开阐述。
二、五代“山后八军”之内涵分析
“山后八军”为唐末刘仁恭首设于幽州,其诸多问题还有待考证。上文提及,胡三省对“山后八军”有一段注解:“卢龙以妫、檀、新、武四州为山后。”[7](8672)这在《通鉴释文辩误》中有更为详细的阐述。现全引如下:
史炤《释文》曰:山后八军,谓涿、营、瀛、莫、平、蓟、妫、檀,皆属卢龙节度使;卢龙,乃幽州范阳郡也。(海陵本同。)余按涿、营、瀛、莫、平、蓟、妫、檀,此卢龙巡属八州,非山后八军也。涿、营、瀛、莫、平、蓟皆在山前,惟妫、檀在山后。又有新、武二州,与妫、檀为四州,置八军,以备契丹,河东故有山后八军巡检使。[1]
此段最后一句句读或有问题。上文已指出山后八军巡检使为幽州所设,从所处地理位置上来看,与契丹、河东镇交界,所防备的应为此二者。另有《光绪顺天府志》提出山后八军之设置不仅防契丹,亦防晋。[5]据此,后一句应为“置八军,以备契丹、河东,故有山后八军巡检使”。
不过,胡三省明确指出“八军”为四州下所设置的八个军,给予笔者极大的启发,对于进一步明晰“山后八军”诸问题提供了可能。又,《旧五代史》卷九〇载:“(李)承约性刚健笃实,少习武事,弱冠为幽州牙门校,迁山后八军巡检使。”[3](1188)
这段材料的解读就显得极为重要。
“牙”通“衙”,李承约曾在刘仁恭衙内任职,当然可看成是刘仁恭的元从。刘守光篡父位自立后,“名儒宿将经事父兄者,多无辜被戮,(李承约)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3](1188)由此可见,李承约身为“宿将”,在外是有领兵权的,史言:“(李承约)少事刘仁恭,为山后八军巡检使,将骑兵二千人。”[4](527)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认为,唐末五代时期,各藩镇把其军队分至各州县,即是在交通要道、战略要地、经济要地等重要区域常设军队,以自己的亲信担任镇将,这些军队被称为外镇军,或巡镇军,其所管辖的区域即为镇。[12](154)此其一。
唐末五代,军镇也可称之为军、镇,胡三省所解释的“军”正是此意。李承约本为刘仁恭亲信,后“握兵在外”,担任“山后八军巡检使”,很可能身为“外镇军”的统帅。由此推之,“山后八军”应类似于军镇。此其二。
“巡检使”一职也可反映“山后八军”的军镇性质。巡检使自唐以来开始设置,五代应该是延续下来了,但还未走向制度化,可到了宋代已经很普遍,尤其是地方上,“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均见巡检之设置。[13]这类巡检也正是日野氏所云“巡镇军”。学界关于五代巡检使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现可参考的有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她认为北宋时期的巡检制度多少有因袭五代之处,巡检的设置主要是在州县、京师和留都、军镇、还有一些沿边的交通要道,巡检大都由武将担任,仅是差遣性质。[14]巡检使的设立肯定为了便于协调对契丹及河东的防御。此其三。
初步可断定,“八军”指的是八个军镇。幽州在“山后”地区设置山后八军巡检使,其渊源还是能得到考证的。《资治通鉴》在记载公元917年“山后八军”的一次叛乱后,又有下面一段史料: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比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7](8812-8813)
《通鉴》胡注还指出“渝关入营州界及平州石城县界”[7](8812),“平州之东乃渝关”[7](8813)。从上段材料来看,“八防御军”处于营、平两州内的渝关至海之间的狭长要道上,为塞外少数民族入内之要道。另,参之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营、平二州均位于幽州东北边,平州临海。[10]而“山后八军”位于幽州西北边,近居庸关一线。
其实两者是有联系的,《通鉴》把这两段史料放在一起自有其独到之处,此段开头之“初”便是探寻两者联系之钥匙。东晋以来,一些政权习惯把战乱时期沦陷地区的移民迁徙至新地区,并为其重建郡县,沿用原有名称。这种政策在中国古代是很常见的,尤在战乱时期更为明显。比如唐初以来为了对契丹各部落进行拉拢和有效控制,便采取了羁縻州政策,之后又有了在内地州县设置的入内侨置羁縻州。[15]“初”正体现了两者之衔接关系,“八防御军”处于契丹入内要道,唐朝以来便一直设置,刘仁恭任幽州节帅时期,为了在西北边防晋、契丹,延其名在“山后地区”设置八个防御军镇亦能理解。换言之,“八防御军”是“山后八军”名称上的前身,实际含义则略有差异。
但“山后八军”具体指哪八个军,司马光及胡三省均无法指出,后人考证也困难重重。《旧五代史》载:
九年(公元912),周德威讨刘守光,嗣本率代北诸军、生熟吐浑,收山后八军,得纳降军使卢文进、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献。幽州平,论功授振武节度使,号“威信可汗”。[3](710)
从这段材料来看,山后八军恐涵盖纳降军及武州。胡三省指出山后八军所处四州中有武州,而张温在武州刺史与山后八军都将两者间来回迁转,亦是旁证。史言:
庄宗伐邢台,获之,用为永清都校,历武州刺史、山后八军都将。从庄宗袭契丹于幽州,收新州,历银枪效节都指挥使,再任武州刺史。[3](798-799)
纳降军亦同理,初步可判定其为“八军”之一。《新唐书》解释纳降军“本纳降守捉城,故丁零川也。”[16]查阅《唐代交通图考》,纳降守捉在武州西边,处于上文所考之“山后”区域。[11](1512)同时,周边还有天成军、清塞军、宁武军等,笔者怀疑上述诸军与“山后八军”有所关联,但并无充足史料可佐证,只能暂存疑。
“山后八军”设立之初,军镇性质已经明晰,而其兵员之特性,在一次军乱中也体现出来了。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庄宗征兵于山后,却导致了兵乱。《旧五代史》卷九七《卢文进传》(《新五代史》卷四八《卢文进传》同)载:
庄宗与刘鄩对垒于莘县,命存矩于山后召募劲兵,又令山北居民出战马器仗,每鬻牛十头易马一匹,人心怨咨。时存矩团结五百骑,令文进将之,与存矩俱行。至祁沟关,军士聚谋曰:“我辈边人,弃父母妻子,为他血战,千里送死,固不能也。”[3](1294-1295)
《资治通鉴》卷二六九也载:
甲午,至祁沟关,小校宫彦璋与士卒谋曰:“闻晋王与梁人确斗,骑兵死伤不少。吾侪捐父母妻子,为人客战,千里送死,而使长复不矜恤,奈何?”[7](8812)
可见,军士以“边民”自称,并不愿意为他人战,晋梁争霸与己无关,仅自卫乡土而已。日野开三郎指出,唐代藩镇的军队构成除了厅直军、外镇军外,还有乡军,乡军多是地方组织,自凑兵粮,独立防御,多不具有野战的任务。但是为了更好地协调防御,也需要外镇军和厅直军的配合,藩镇才慢慢侵蚀原有乡兵的独立地位。[12](150-152)
除此之外,史料中的“团结五百骑”,应指团结兵、团练、乡兵、义兵。“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7](7245)团结最大特点就是属于地方武装,兵农合一。张国刚指出,团结兵包括“征行”团结兵和“镇防”团结兵,镇防团结兵在自己家乡组织起来,保卫特定的边州和要害之地,不属于地方军队,但是委于地方官训练,像边兵一样被边地军事长官所领导。[17]庄宗征调的明显属于后者,这种团结兵是具有乡兵性质的,“并令刺史自押领,若须防遏,即以上佐及武官充。”[18]
综上来看,“山后八军”设立之初,是幽州设置在边地、具有防御性质的八个军镇,主要防备契丹和河东,为模拟东北边的“八防御军”而来,目前可知的军镇有纳降军,士兵大多本地自募,自卫乡土,独立性和战斗力都较强。幽州时期,刘仁恭派李承约统“山后八军”,只设置了差遣性质的巡检使,应是乡兵色彩还较为浓厚之缘故,类同于“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7](8813)。
三、“山后八军”与“山后八州”之辨析
首先,需措意《辽史》中还有“山北八军”之说。史载:
神册元年(公元916)……攻振武,乘胜而东,攻蔚、新、武、妫、儒五州,俘获不可胜纪,斩不从命者万四千七百级。尽有代北、河曲、阴山之众,遂取山北八军。[19](396)
公元916年,晋新州兵叛,杀统领山后八军的新州团练使李存矩,拥立卢文进,并反攻新、武二州不利,归于契丹,而正是此时,卢文进引契丹入寇。[3](1294-1295)但是契丹并未长期占有此地区。《辽史》又载:
奉圣州,武定军,上,节度。本唐新州。后唐置团练使,总山后八军,庄宗以弟存矩为之。军乱,杀存矩于祁州,拥大将卢文进亡归。太祖克新州,庄宗遣李嗣源复取之。[19](510)
很明显,《辽史》中“山后”与“山北”多通用,所记“山北八军”当是“山后八军”的别称。后世史料所出现“山北八军”处都是关于这段史实,应是因袭而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中都未出现过“山北八军”,大概是因为《辽史》修撰过程中多据辽朝《实录》。由此可推测,“山北八军”仅是“山后八军”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
任爱君认为,“山后八军”“山北八军”与“山后八州”并无区别,都是指“山北”地区。[2]实际并非如此。
“山后八州”最早见于一首名为《城北》的边塞诗中,作者刘挚为北宋中期文人。
寒门秋色阵云飞,雉堞烟青昼角悲。
河坼波涛含赵魏,星分毕昴半华夷。
太原玁狁当征日,瀚海单于欲战时。
六十万兵闲饱死,谁怜山后八州儿![20]
此诗第二句正是引典故,讲述李存勖于魏州登基。“初,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昴,太史奏:‘毕、昴,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其后四十九年,帝破梁军于柏乡,平定赵、魏,至是即位于邺宫。”[3](403)而“太原”和“玁狁”当分指五代的河东政权与契丹。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史料均不见“山后八州”的记载,在关于宋代的史料中却屡有提及。比如《宋史》载:“(章衡)归复命,言辽境无备,因此时可复山后八州。不听。”[21](11008)又,《续资治通鉴长编》言:“既以兵守四关口外,西山有后来新开父牛铁脚猪窠二口,敌人以通山后八州之路,然皆险峻,不容车马。”[22]笔者揆以为,“山后八州”是入宋后才出现的名词。此时,“山后八军”却基本不再出现,可能是因为此地早陷于契丹。
然而宋以降,诸家对“八军”的解释偶与“八州”混淆在一起。典型有南宋史炤的解释:
山后八军,谓涿、营、瀛、莫、平、蓟、妫、檀,皆隶卢龙节度。[23](卷二八,第1叶B)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是目前可见除“胡注”外唯一的《通鉴》全书注本。南宋时,除史炤本《释文》外,还有司马康本《释文》,这在《通鉴释文辨误》中称为“海陵本”。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只收录司马康本,未收入史炤本。[24]《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将史炤本及司马康本均收入其中。[21](5092)有学者提出,史炤本成书在司马康本之前,且司马康本乃托名之作。[25]不过,司马康本未见流传,如今可见的《资治通鉴释文》仅为史炤本。
史炤提出的 “山后八军”为卢龙辖下八个行政州的说法,已被胡三省否定。胡氏指出“八军”并非指八州,而是指四个州下设的八军,笔者对此表示认同,并在上文考证出“八军”实乃军镇。
又,任爱君提出八州是幽州管内的妫、蔚、新、武四州和并州管内的云、应、朔、儒四州,亦称为八军。[2]“山后八军”原为幽州所设,不可能包括并州管内的四个州。任氏此说应是沿袭顾祖禹的观点。
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寰、应、朔、蔚也。《通释》曰:“幽、蓟、瀛、莫、涿、檀、平、顺为山前八州,新、妫、儒、武、云、应、朔、蔚为山后八州,平州先没,寰州后置,故十六州有寰州而无平州。”[26]
此为《读史方舆纪要》关于燕云十六州的解释,“山后八州”直指燕云地区的八个州。疑惑的是,顾祖禹明确表明,他是直接引用《通释》的记载,但史本无此说法,笔者颇怀疑顾氏所引为司马康本。此处暂不深究《通释》说法的正确性,径将其视为宋人对“山后八州”的一种解释即可。而顾祖禹沿袭宋人提法,当无疑问。
较之《唐代交通图考》,笔者发现燕云十六州下新、妫、儒、武、云、应、朔、蔚八州,确实都处于以太行山为首的障塞之后,[11](1512)这应代表了宋人对“山后八州”的主流看法。
同时,在其他史料中也可找到“八军”或“八州”为燕云地区一部分的证据。如:
(端拱)二年(公元989),将讨幽蓟,诏群臣各言边事。琪上疏谓:“……王师可于州北系浮梁以通北路,贼骑来援,已隔水矣。视此孤垒,浃旬必克。幽州管内洎山后八军,闻蓟门不守,必尽归降,盖势使然也。”[21](9123-9124)
此为宋初宋琪关于收复幽蓟的上书。宋琪为五代入宋时期的人物,其本燕人,燕云地区割给契丹后,中契丹进士科,被幽州节帅赵延寿辟为从事,“以故究知蕃部兵马山川形势”。[21](9125)虽然不明宋琪所指“山后八军”①是否为八个行政州,但确指燕云地区的一部分,此应成立。
又,北宋中期的章衡明确提出了伐辽,收复“山后八州”。史载:
(章衡)使辽,燕射连发破的,辽以为文武兼备,待之异于他使。归复命,言辽境无备,因此时可复山后八州。不听。[21](11008)
“复山后八州”很明显地表达了收复失地的意思,直指燕云地区。北宋初曾有过收复燕云地区的姿态,[27]所以大臣还能提出攻略。而章衡是北宋中期的人物,此时朝廷彻底安于自保,其建议自然不会被接纳。
然北宋依然念念不忘燕云十六州,宋徽宗时期与金联合灭辽,得以短暂收复燕云地区。这在《宋史·地理志》中出现了一种“山后九州”的提法。史载:
云中府,唐云州,大同军节度。石晋以赂契丹,契丹号为西京。宣和三年(公元1121),始得云中府、武应朔蔚奉圣归化儒妫等州,所谓山后九州也。[21](2251)
奉圣、归化两州乃石晋割让的新、武二州。据《辽史·太宗下》载,会同元年(公元938),后晋遣赵莹献十六州图籍,“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19](45)那么,“山后九州”中的武州又是如何而来?其实这是辽人新设的州,下辖神武县,在大同府西南方,与归化州(石晋割让武州)并无联系。[19](41),[28]赵铁寒认为,宋人对此不够明了,拉上新设武州才有“山后九州”之说。[29]除去辽人新设的武州,其余八州正好与顾氏所引《通释》“山后八州”吻合。
笔者认为,宋时期出现的“山后八州”与五代“山后八军”了无联系。“山后八州”大多情况下指的是燕云十六州下“山后”的八个州。后唐末,石敬瑭以十六州为代价换取契丹支持,当然也包括原来“山后八军”所在区域,这在《辽史》中记载为“山北八军”。[19](510)入宋以来,太祖、太宗两朝也曾有过收复燕云地区的军事行动,但惨遭失败,真宗朝“澶渊之盟”后,便逐步固疆自守。由于历史日渐久远,加之对“山后”的理解也随之变化,关于这段史实的回忆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赵铁寒指出,北宋虽离石晋不远,但宋人对十六州之原委多不明晰。[29]在如此重大史实前,宋人且有各种含混不清,比如后来的“山后九州”生硬扯上辽人所设置的武州。那么,年代相对更为遥远,且重要性远逊于燕云十六州的“山后八军”,宋人难以明晰其含义也不难理解。
注释:
① 宋琪为五代入宋时期的人物,那时可能还留有“山后八军”的提法。从“洎”字的解读来看,“幽州管内”与“山后八军”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名词。刘仁恭所设“山后八军”是处于幽州管内的,这里的“山后八军”则为另一种含义,可能也属于文中所论“八军”“八州”混用的情况。
[1] 胡三省. 通鉴释文辩误[M]. 北京: 中华书局,1997: 172.
[2] 任爱君. 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J]. 北方文物,2008(2): 59-65.
[3] 薛居正. 旧五代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6.
[4] 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5] 周家楣,缪荃孙等. (光绪)顺天府志[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6391.
[6] 吴廷燮. 唐方镇年表[M]. 北京: 中华书局,2003: 573-575.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1997.
[8] 李鸣飞. “山后”在历史上的变化[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35-39.
[9] 傅恒,等. 历代通鉴辑览(第三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74.
[10]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M].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84-85.
[11] 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 河东河北区)[M].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
[12] 日野开三郎. 东洋史学论集(第二卷五代史の基调)[C]. 东京:三一书房,1980.
[13]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541.
[14] 刘琴丽. 五代巡检研究[J]. 史学月刊,2003(6): 34-41.
[15] 任爱君. 唐代契丹羁縻制度与“幽州契丹”之形成[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1): 8-17.
[16]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 1019.
[17] 张国刚. 唐代兵制的演变和中古社会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2006(4): 178-189.
[18] 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1992:157.
[19] 脱脱. 辽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4.
[20] 刘挚撰,裴汝诚,陈晓平点校. 忠肃集[M]. 北京: 中华书局,2002: 419.
[21]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22]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1992: 3649.
[23] 史炤. 资治通鉴释文[C]// 四部丛刊初编本.
[24]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 郡斋读书志校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229.
[25] 林嵩. 南宋〈通鉴〉注考论[J]. 古代文明,2007(1): 74-81.
[26]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276.
[27] 孙建民. 燕云十六州与宋初宋辽的军事策略[J]. 河北学刊,1989(4): 90-94.
[28]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10-11.
[29] 赵铁寒. 燕云十六州的地理分析[C]// 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宋辽金史研究论集. 台北: 大陆杂志社,1960: 53-62.
[编辑: 苏慧]
Some questions about “the Eight Armies in the back of T’ai-hang Mountains” in the Five Dynasties
LI Xia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 Communication,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The Eight Armies in the back of T'ai-hang Mountains” were some important military forces in the Five Dynasties. There are a lot of discrepanc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ources,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conceptual confusions and unclear meanings. “The Eight Armies in the back of T'ai-hang Mountains,” designed by Liu Jen-Kung who was the supreme executive for Yu-chou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derived from eight military regimes which wer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for defense,and were named after “the eight defensive regimes” in the northeast of Yo-chou. Moreover,the present essay concludes that “the Eight Armies in the back of T'ai-hang Mountains”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ight Chou in the back of T'ai-hang Mountains” in the Sung Dynasty were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oncepts.
the Five Dynasties; the Eight Armies in the back of T'ai-hang Mountains; the Eight Chou in the back of T'ai-hang Mountains
K24
A
1672-3104(2016)04-0187-06
2016-02-25;
2016-05-26
宁波大学人才工程项目“唐宋幕府及文士研究”(F01285144702)
李翔(1988-),男,江西吉安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唐五代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