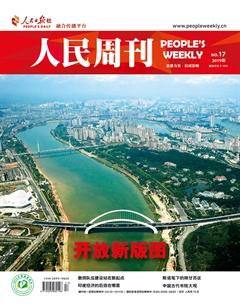身份、记忆、变迁:从墓志看隋唐时期的幽州
蒋爱花
近年来,从长时段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群成为学术热点,“长安学”“洛阳学”等研究已蔚为大观,学者们倡导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和更广阔的学科视野来关注古代城市群的整体变迁。这既仰赖于长安、洛阳地区丰富的传世文本,也得益于层出不穷的考古发掘与出土文献。与之相比,学术界对幽州的关注起步较晚,目前逐渐形成了相关研究梯队,研究层次显著提高,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也逐步推进。
一
幽州为古九州之一,《禹贡》曰:“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幽其一也”,《周礼》记载为“东北,曰幽州”。幽州所辖的范围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动,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天津以及辽宁部分地区。幽州“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唐以前,中原王朝关注的重心在西北关中;唐以后,逐步转移到东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体对中原王朝造成震荡、首当其冲的地区,也是唐朝灭亡后重新建构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从西向东甚至向东北方向转移且次数频繁,王朝的边防重镇也渐次由西北转移至东北,使处于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过渡区域的幽州地区逐渐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区域特色。从隋唐历五代十国直至元大都的建立,幽州的戍边角色悄悄发生了巨变:从胡地、戎墟演变成了中国古代后半期多個统一王朝的都城。治中国史前半期的学者较多关注当时的两京,对于幽州关注的目光停留在军事边防、藩镇割据以及以北京、河北、天津等现代区划为核心的区域史层面,或者是针对某一地区考古个案的解释。究其原因,幽州并不属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重心,史料记载与出土文物的相对缺乏也限制了学术界作出更多的解释。安史之乱后,幽州地区的形象被“河朔藩镇”的阴影遮盖。其实,幽州的发展史是一部辽以前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史,此地孕育出中国古代后半期多个统一王朝的都城绝非偶然,从边鄙之地到权力核心的演变过程值得探讨,而近年来地下实物——墓志的大量出土,为研究幽州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
二
从墓志角度关注幽州社会的历史变迁,具有厘定官修史书、正本清源的作用。笔者通过对隋唐时期15000余方墓志的拣选,从中释读出幽州地区的墓志约200方,加之收藏于各文物部门的墓志实物约50方,共计20余万字。从数量上来看,幽州墓志的数量仅次于两京地区,而多于“北都”太原府。幽州地区的墓志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志主在幽州地区做官,如“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1956年,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附近出土);二是志主死后埋在幽州地区,如“唐故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陇州诸军事、行陇州刺史、上柱国、南阳县开国伯张道”窆于幽州良乡县阎沟山;三是间接与幽州相关的隋唐时期墓志,如“唐故恒王府司马、幽州节度经略军兵曹参军太原王府君”的父亲王思“以营田授勋,终幽州昌平县尉”。
幽州墓志文本中的个人表达、历史记忆、民风描绘值得仔细解读。比如,在中古时期,人们素有“归葬(洛阳)邙山”的情怀,但幽州地区出土的墓志却存在着与之迥异的“归葬”“迁葬”现象。在个案研究方面,2013年1月,北京市房山区发现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志吸引了研究者较多的目光。在刘济墓挖掘初期,曾经出现金代的钱币,学界一度怀疑是海陵王的墓葬,随着刘济夫妇墓志的相继出土,使我们认识了刘济这位正史中寥寥数笔、墓志中却饱满立体的人物。刘济的生卒年、官职履历、军事活动、死因等清晰可见:虽在藩帅的承袭上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独霸性,财政上则向中央“屡输忠款”;在军事上虽拥重兵,却无抗衡中央之行为且多次承担抗击北方入侵之责,参与镇压地方叛乱,尽到了中央政府要求的“义务”,表现出“恭顺”的一面。这与此前学术界认为的幽州地区所属割据型藩镇类型大相径庭,由此看出幽州试图在戍边与保持自身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自身的安全需求与得失取舍才是幽州地区的治理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三
隋炀帝修通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后,幽州成为运河的北起点,在军事上成为征伐契丹、渤海国等地的后勤基地。安史之乱后,幽州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幽州墓志体现出一些时人普遍的礼法要求。隋唐时期,人们十分重视归葬祖茔,幽州墓志也可印证这一点。举例而言,唐代高行晖(691—759年)终任官为怀州别驾,去世于乾元二年(759年)怀州官舍,其妻大历元年(766年)终于幽州私第。直到元和二年(807年),夫妻俩才被合葬于潞县,相隔近50年。据记载,高行晖夫妇相继去世后,其子高崇文(746—809年)正征战于长武、宁州(今陕西、甘肃)等地,等到元和二年才回到幽州故里。出于合葬父母的礼法要求,高崇文将父母之墓由怀州迁回潞县(今北京通州区),迁葬后两年(809年),高崇文病卒。高行晖曾为尚书,其子高崇文哪怕迟至半个世纪也要将父母归葬故里,这符合“周礼之制”的做法,堪称“至孝”。再如,唐人张道昇曾在幽州为官,终任官为陇州刺史,卒于长安私第。墓志明确记载,其子在张道昇死后“泣血扶护还乡”,由长安迁回幽州安葬,两者相距约两千余里。
幽州墓志中还提到了不少“官于燕地,因家徙此,遂为蓟人”的现象:墓主人或为驻守北地的将领,或担任幽州辖区州县的官员,或为入朝蕃将的后裔。这也是幽州地区民族迁徙与融合的缩影。比如,吐蕃人禄东赞曾担任松赞干布时期的大相,其后裔论博言“咸通乙酉重五(865年),聘东垣回,暍疾于路,迄秋分永逝于蓟城……夫人,防御军使检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刘騽长女,先于公殁十余年,墓于幽都之西三十里新安原”。论博言于咸通六年(865年)在蓟城析津坊病逝,其妻刘氏先于丈夫去世,被葬于幽都县的新安原,而其子最终将亡父亡母合葬。值得关注的是,论博言家族从曾祖父论弓仁(墓志中记为“布支”)开始归唐,祖父论惟贞、叔祖父论惟明参与了唐德宗时期平定“泾原兵乱”的战争,均被封为“奉天定难功臣”。到论博言时,已在中原定居达四代之久,成为入朝蕃将,近百年的入华历程使其家族高度汉化。论博言娶汉人之女、其子对父母行合葬之仪,他们的日常生活、丧葬习俗也已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此外,幽州地区的墓志也有独特之处,官员墓志是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幽州的官员倾向于在幽州镇的范围内迁转不休,却极少与中央及其他藩镇之间互动,形成了独立的官员任免、迁转体系。多方使用伪朝年号的墓志,反映出幽州地区民众“动摇不定”或“随遇而安”的心态,这与长久以来胡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幽州与两京之间的向心力逐步淡化,幽州内部的商业繁荣以及独立的赋税体系,使之奠定了唐末五代时期幽州最早脱离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隋唐时期,幽州所牵涉的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北部活跃着突厥、回纥(鹘),东北活跃着奚、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民族之间的战争与融合体现在数次迁徙中: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被唐军打败后,大量降众被安置在幽州境内定居;随之,粟末靺鞨也迁入燕州(今北京怀柔、顺义);新罗人迁入良乡广阳城,唐置归义州统之。开元四年(716年),契丹弹汗部迁入幽州东北,置归顺州(今北京顺义);开元二十年(732年),奚人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被安置在良乡县。可以说,幽州南边属于“内轻外重”的中央王朝,北边则承担着御边的任务,虽然在唐玄宗时期有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但割据的状态很快得到了调整。如果我们将眼光拉长,可以看到幽州区位特殊性的源与流,其“源”可追溯到汉代以来的东北亚格局,其“流”也不止于五代时期的地方政权纷争。北宋初年,地方治理中“文臣作知州、转运使管理财政”的措施只是暂时画上了割据的休止符。辽金与宋朝的战争、和议、朝贡、互市,无不反衬出幽州在历史时空中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