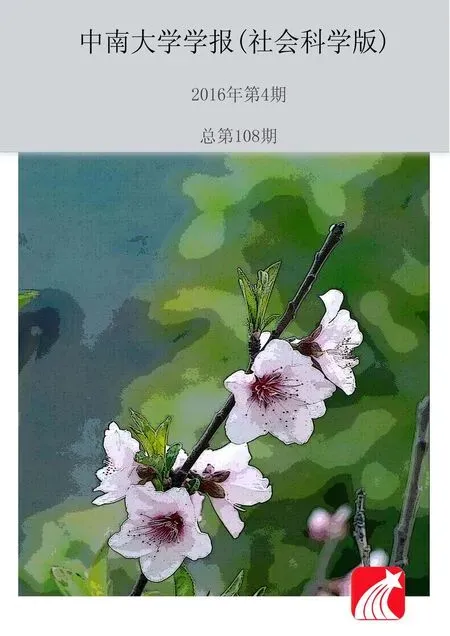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体系化构造
熊亚文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体系化构造
熊亚文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上,二者的混同已然导致了一系列水土不服的现象。事实上,基于中外刑法犯罪论体系、共同犯罪理论及立法的差异,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与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存在本质区别,二者乃处于不同层次的两个不同概念。必要共同犯罪实际上仅相当于必要共犯分类下“纯正的必要共犯”,至于“不纯正的必要共犯”则应属于任意共同犯罪范畴。若依此对必要共同犯罪概念进行体系化构造,则可使其司法适用难题迎刃而解。
必要共同犯罪;必要共犯;对向犯;聚众犯
一、现状及问题
在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根据共同犯罪是否能够任意形成的标准,可以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如此分类的功能在于:一是方便对共同犯罪予以类型化研究,二是用以区别二者的法律适用方式。事实上,刑法理论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进行类型化研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根据二者的不同特性,对二者的法律适用方式予以区别,进而指导和规范整个共同犯罪的立法与司法。通说认为,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的法律适用方式不同:对于任意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刑法总则共犯规定和刑法分则罪刑规范定罪量刑,而对于必要共同犯罪则应当排除刑法总则共犯规定之适用,仅根据刑法分则相应的罪刑规范处理即可。基于如此分类功能,刑法理论和实践理应严格界分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并在此基础上对必要共同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予以特别规定与适用,使必要共同犯罪满足“只需直接根据刑法分则相应规定处理即可,而无需再行适用刑法总则共犯规定”之要求。如此方能指导和规范整个共同犯罪立法与司法,凸显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之分类应有的刑法价值。
然而,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之分类功能一直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以至于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上。对于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所含具体犯罪类型及其与任意共同犯罪之界分,学界均直接援引德、日刑法必要共犯与任意共犯之分类理论,普遍忽视了中外刑法犯罪论体系、共同犯罪理论及立法存在的本质差异。从主流刑法教科书以及绝大部分相关论文的介绍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学界基本都将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与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相混同。即便有部分学者明确使用了“必要共同犯罪”之概念,但实际上仍旧是在直接照搬德、日刑法共犯理论中必要共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可谓“换汤不换药”。尽管到目前为止,有少量文献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指出必要共同犯罪概念与必要共犯概念的内在不同,但却未对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做进一步体系化构造。
以必要共犯概念代替必要共同犯罪概念,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无疑会导致水土不服的现象。因为必要共犯所对应的共犯类型是任意共犯,其属于最广义的共犯概念,二者的区分并不完全具有区别法律适用方式的功能。换言之,对于必要共犯并不必然得出其仅需根据刑法分则的相关罪刑规范定罪处罚而不能适用刑法总则共犯规定的结论。德日刑法理论承认、司法实践也认可并存在必要共犯适用总则共犯规定定罪处罚的情形。然而,在我国刑法中,将共同犯罪划分为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最终是为了区别二者的法律适用方式,这不仅是理论上通行的观点,也是实践中认可的做法。在此前提下,倘若以必要共犯概念代替必要共同犯罪概念,则必然导致诸多在德、日刑法中可以适用刑法总则共犯规定定罪处罚的必要共犯,在我国刑法中却无法适用刑法总则共犯规定定罪处罚。
具体而言,按照当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行的观点,必要共同犯罪包括对向性共同犯罪、集团性共同犯罪和聚众性共同犯罪,其内涵和外延基本等同于德、日刑法中的对向犯、集团犯和聚众犯。根据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的分类功能,将会出现如下司法适用难题:①对于刑法分则未规定处罚的必要参与者,主要是对向性共同犯罪中刑法未规定处罚的实施对向性参与行为的一方,不能适用教唆犯或帮助犯等共同犯罪一般规定定罪处罚。这必将导致超出“最低必要参与程度”范围且具备刑事可罚性的违法与责任的单罪对向犯相对方存在入罪障碍。②对于同罪对向性共同犯罪主体的刑罚裁量,不能适用刑法总则共同犯罪关于主从犯之规定对其区别主从作用而予相应量刑。这将导致同罪对向性共同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裁量无法实现规范性与均衡性,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③对于聚众性共同犯罪中刑法规定单一罪刑单位的情形,不能适用刑法总则基于犯罪人作用不同而实行主从有别处罚原则的共同犯罪一般规定对其区别主从作用予以量刑。这也将导致刑法规定单一罪刑单位情形的聚众性共同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裁量缺乏规范性和均衡性。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将必要共犯概念与必要共同犯罪概念彻底混同,是导致当前我国必要共同犯罪上述司法困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倘若能够基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体系,严格把握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那么,尽管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源自于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我们仍能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严格界分必要共同犯罪概念与必要共犯概念,可使当前我国必要共同犯罪的司法困境从根本上迎刃而解。因此,将必要共同犯罪置于我国刑法理论体系加以系统化审视,使其与必要共犯概念严格区分,在此基础上重新划定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之外延,对于必要共同犯罪乃至整个共同犯罪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完善均至关重要。
二、中外刑法必要共同犯罪之概念辨析
(一) 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法中的必要共同犯罪概念源自于德、日刑法共犯理论中的必要共犯概念。据考察,早在1805年,德国学者Stubel就提出过“实质性”必要共犯概念,此后,德国学者Heffter首次明确使用了“必要共犯”一词,经德国学者Schuetze、Kries等先后对必要共犯理论进行专门探讨,必要共犯概念才真正得以确立和认同。[1]当前,关于必要共同犯罪的概念,中外刑法学界形成了两类存在本质差异的观点。
1. 功能性概念说
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Kries关于必要共犯的最初定义——“在概念上以数人的加担为必要的犯罪”,是必要共犯的通行概念。例如:德国学者李斯特认为,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需要多人共同参与的是必要共犯。[2]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和托马斯·魏根特认为,倘若一个犯罪构成要件的实现必须要数人共同参与,那么它就是必要共犯。[3]约翰内斯·韦塞尔斯认为,倘若对构成要件之理解从概念上看,必须以数人参加为前提条件,那么它就是“必要的参与”。[4]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认为,有些犯罪只能由二人以上的行为构成,这就是“必要共犯”(reati a concirso necessari),或者更正确地说,就是必须以多个主体为存在前提的“必要的多主体构成”(le fattispecie plurisoggetti necessarie)。[5]日本学者野村稔认为,根据预先设定的构成要件,只有复数的人才能实行的犯罪,就是必要的共同犯罪。[6]山口厚认为,必要共犯是犯罪构成要件以数人的共动、加功为本身或前提的犯罪。[7]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对必要共犯概念之界定,普遍持与德、意、日刑法学界相同的观点。例如:林钰雄认为,有些犯罪只能由复数行为主体违犯,此即为必要之参与犯(即必要共犯)。[8]黄荣坚认为,所谓必要共犯,是与任意共犯相对应的概念,此类犯罪之构成以数人共同参与为要件。[9]此外,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有陈子平等等。[10]
可见,在构成必要共犯是否要求两个以上参与者均成立犯罪的问题上,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必要共犯是在构成要件上以数人的参与为必要的犯罪,其仅要求具体构成要件在形式上的实现必须有数人共同参与,而不要求两个以上参与者均成立犯罪。此类观点,笔者称之为必要共同犯罪的功能性概念说。
2. 实体性概念说
在我国大陆地区刑法学界,由于犯罪构成理论及共同犯罪理论与德、日刑法存在差异,必要共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引进时被大大限缩,由此形成从属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体系的必要共同犯罪概念。我国大陆地区刑法理论普遍认为,必要共同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立法规定只能由二人以上构成的犯罪。例如:马克昌、高铭暄教授等认为,某些分则立法规定了二人以上才能构成的犯罪,这种情况属于必要的共同犯罪。[11]陈兴良教授认为,只能由二人以上构成的犯罪即为必要共同犯罪。[12]林亚刚教授认为,必要共同犯罪是指必须以二人以上的行为为构成犯罪必要条件的犯罪,这种犯罪的成立模式就是共同犯罪。[13]
相应地,在构成必要共同犯罪是否要求两个以上参与者均成立犯罪的问题上,我国大陆地区刑法学界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必要共同犯罪是指只能由二人以上构成的犯罪,其不仅要求具体构成要件的实现在主体上必须有二人以上共同参与,还要求二人以上共同参与者均成立犯罪。此类观点,笔者称之为必要共同犯罪的实体性概念说。
(二) 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观点评析
笔者认为,必要共同犯罪的功能性概念说与实体性概念说之所以存在实质性差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中外刑法犯罪论体系的差异是导致分歧的根本原因;其二,中外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及立法的差异是导致分歧的直接原因。
首先,就犯罪论体系的差异而言。
在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大多数学者所主张。根据“三阶层”体系,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成立犯罪需经过三个层次,只有同时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行为才是犯罪。对此,有学者指出,大陆法系“三阶层”体系最为突出的优势在于,其是以一种“阶梯递进”的方式来判断犯罪成立。[14]其中,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阶段,由于独立于违法性与有责性判断,“只是一种形式的事实判断,而不是对事实的实质的价值判断”。[15]这意味着,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最终有可能因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而不成立犯罪。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共犯理论从属于构成要件理论。[3](775)因而,德、日刑法学者对共犯的研究是从犯罪成立判断的第一个阶段即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开始的,人们往往是从构成要件是由多数人实施还是由单数人实施来区别共犯与单独个人犯罪。[16]这使得德、日刑法中共犯的成立,不要求两个以上参与者最终均构成犯罪。必要共犯作为共犯的一种类型,是与任意共犯相对应的,其仅强调构成要件的实现在主体上必须有数人共同参与,这是一种行为意义上的主体复数,而不是犯罪意义上的主体复数。
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不同,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标准。它实际上内涵了“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有关犯罪成立的全部内容,是某一行为成立犯罪的所有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如此犯罪构成乃是判断某一行为成立犯罪的唯一标准。”[17]可以说,我国大陆地区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不仅是实质判断与形式判断的统一,还是犯罪成立的消极要件与积极要件的统一。因此,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共同犯罪必须是两个以上“合格行为人”[18]共同实施的犯罪,其内含两个以上的犯罪人。相应地,必要共同犯罪是只能由二个以上主体构成的犯罪,它强调的是一种犯罪意义上的主体复数,而不仅是行为意义上的主体复数。
其次,就共犯理论及立法的差异而言。
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共犯”概念在不同层次上使用具有不同内涵,由此产生了“共犯分层理论”。根据共犯分层理论,“共犯”概念可以在最广义、广义和狭义三个层次上使用。所谓最广义的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现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最广义的共犯可分为必要共犯和任意共犯。其中,任意共犯的具体情形,即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又被称为广义的共犯。所谓狭义的共犯,则特指帮助犯和教唆犯。[19]我们所称的必要共犯与任意共犯,都是在最广义的共犯概念下来划分的。由于最广义的共犯概念仅强调具有多数人实现了构成要件,不问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能力、是否具有相同的罪过形式、是否最终均成立犯罪等,因而统一于最广义共犯概念下的必要共犯与任意共犯概念也仅指行为自然意义上的主体复数性。与此相应,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没有在总则中规定共犯的概念,其共犯的相关规定也没有共犯人主观方面的内容。①如此一来,必要共犯理论与德、日等国刑法立法之间也就不存在冲突。
不过,由于我国《刑法》第25条明确规定了共同犯罪的含义,所以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一致认为,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犯罪人。因此,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同犯罪与德、日刑法理论中的共犯存在实质性差别,前者是一个后犯罪判断的概念,后者是一个前犯罪判断的概念,后者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前者。我国刑法学界在引入德、日刑法理论中的必要共犯概念时,为了使必要共犯概念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体系相契合,必然要将“必要共犯”概念改造成“必要共同犯罪”概念。因为统一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体系的必要共同犯罪概念,其前提必然要求两个以上参与人均构成犯罪,如此便缩小了德、日刑法共犯理论中必要共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三) 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应然立场
鉴于中外刑法理论及立法存在以上客观差异,笔者承认并尊重如下事实: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与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一种后犯罪判断的、刑法学上的实体性概念,它内含两个以上的犯罪人;后者是一种前犯罪判断的、技术意义上的功能性概念,它仅指行为在自然意义上的主体复数性。二者完全处于不同层次上,不能相互混同。
倘若仅承认必要共同犯罪的实体性概念而否定其功能性概念,则会导致如下问题:其一,将会使绝大部分传统上被认为是必要共犯的情形被排除在外,大大缩小必要共犯概念的外延,从而导致中外刑法学界丧失关于必要共犯理论的交流平台。例如,日本刑法中的贩卖猥亵文书罪属于必要共犯,若仅承认必要共同犯罪的实体性概念,便会将这种情形排除在外,这对于德、日刑法学界而言完全不可接受。其二,将会使必要共犯概念丧失存在的基础,其刑法价值将大打折扣。[20]因为任意共犯是对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正,它扩大了刑法打击范围,从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21]而立法者通过必要共犯的刑法分则立法,对必要的复数参与者进行一定筛选后予以刑罚处罚,从而限制了刑法打击范围,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所以若否定必要共同犯罪的功能性概念,其刑法价值无疑将大大减损。
倘若仅承认必要共犯的功能性概念而否定其实体性概念,则将无法使必要共犯概念纳入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体系之中,造成共同犯罪理论研究无法细致深入地展开。即便仍勉强将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划分为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也无从凸显如此划分的刑法功能,从而使共同犯罪最为典型和重要的类型划分丧失应有意义。
事实上,必要共同犯罪的功能性概念和实体性概念具有不同的刑法功能。必要共同犯罪的功能性概念是与任意共犯概念相对应的,其刑法功能在于区分共犯类型,但不必然区分二者的法律适用方式。因为必要共犯与任意共犯是从行为自然意义上的样态对共犯进行划分,是一种前犯罪判断,所以必要共犯最终并不必然存在两个以上的犯罪人。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将必要共犯进一步划分为纯正的必要共犯和不纯正的必要共犯,前者是指按照刑法分则明文或者默示规定,所有参与者都应受到刑事处罚的必要共犯,后者是指刑法分则只规定处罚某些或者某个参与者的必要共犯。[5](299)对于纯正的必要共犯,直接适用刑法分则的规定处理即可,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共识;对于不纯正的必要共犯,能否适用总则共犯规定处罚法律未规定处罚的必要参与者,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7](339-342)与之相对,必要共同犯罪的实体性概念是与任意共同犯罪概念相对应的,其刑法功能在于区别二者的法律适用方式。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必要共同犯罪概念必然内含两个以上的犯罪人,其相当于德、日刑法共犯理论中的“纯正的必要共犯”,对于必要共同犯罪只需直接适用刑法分则规定处理即可,而无需考虑是否适用刑法总则共犯规定。
三、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之外延重构
既然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与德、日刑法必要共犯实际上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那么必要共同犯罪所含具体犯罪类型当然不可能等同于必要共犯。由于必要共同犯罪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必要共犯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因而必要共同犯罪的外延无疑要小于必要共犯,许多必要共犯类型并不属于必要共同犯罪范畴。因此,有必要在德、日刑法必要共犯的概念框架下,根据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任意共同犯罪的分类功能,对当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行的必要共同犯罪类型进行检验,以重构必要共同犯罪的应然外延。
根据当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行的观点,对向性共同犯罪、聚众性共同犯罪和集团性共同犯罪被认为是必要共同犯罪的三大基本类型,其内涵和外延基本等同于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下对向犯、聚合犯(包括聚众犯和集团犯)的内涵和外延。集团性共同犯罪作为最典型的必要共同犯罪,理论和实践对此均无争议。故接下来,仅针对对向性共同犯罪和聚众性共同犯罪进行探讨。
首先,就对向性共同犯罪而言。
由于当前我国刑法中的对向性共同犯罪是根据德、日刑法中的对向犯改造而来的,只不过基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的要求,将对向犯限定在成立共同犯罪时的情形,因而对向性共同犯罪所含具体犯罪类型与对向犯基本相同,即同罪对向犯、异罪对向犯和单罪对向犯。
对于同罪对向犯,如重婚罪,其是否真的如当前我国刑法理论通说所认为的那样,属于必要共同犯罪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根据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内涵,只有必须由二人以上才能构成的犯罪才是必要共同犯罪,那种可以由一个人构成也可以由二人以上构成的犯罪应属于任意共同犯罪的范畴。以重婚罪为例,当相婚者被欺骗或者被胁迫而与他人重婚时,由于缺乏责任要素而不可能构成重婚罪,此时便只有重婚者一人构成重婚罪;当重婚者与相婚者均具有重婚的犯罪故意时,且在具备违法与责任要素的情况下,二者便成立重婚罪的共同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显然与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相冲突,而恰恰与任意共同犯罪概念相契合。②此外,根据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的分类功能,对于必要共同犯罪只能根据分则的相应罪刑规范定罪处罚,若以此标准来逆向检验同罪对向犯是否属于必要共同犯罪,恐怕也只能得出否定结论。因为当重婚行为双方均构成重婚罪的情况下,二者无疑属于重婚罪的共同犯罪,由于重婚罪的刑法分则立法没有对重婚双方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因而需要结合主犯、从犯等总则共犯规定对二者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区分,实现罪刑均衡。因此,同罪对向犯虽然属于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的范畴,但却不属于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范畴。基于同样的理由,异罪对向犯和单罪对向犯虽属于必要共犯的范畴,但也不是我国刑法中的必要共同犯罪。那种认为“当对向犯双方均构成犯罪的时候,就属于我国刑法中的必要共同犯罪;当对向犯双方仅一方构成犯罪的时候,便不属于我国刑法中的必要共同犯罪”的观点,不仅没有尊重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内涵,还将人为造成对向犯在我国刑法中的定罪量刑障碍,因而并不可取。③
其次,就聚众性共同犯罪而言。
探讨聚众性共同犯罪的前提是认识聚众犯罪。[21](352)关于聚众犯罪之概念,学界大致有如下三类观点:①聚众犯罪是指“聚集多人实施犯罪”[22]。此类观点从词意本身来理解聚众犯罪,含义最广,只要是以聚众的方式实施的犯罪均被认为是聚众犯罪。由于如此界定聚众犯罪并没有实际意义,因而此类观点不为我们所取。②聚众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立法明文规定以‘聚众’为构成要件的犯罪”[23]。此类观点从构成要件来理解聚众犯罪,含义最窄,只有刑法分则立法明确规定“聚众……的”才被认为是聚众犯罪。由于此类观点机械地把“聚众”一词视为聚众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使聚众犯罪成为“聚众……罪”的个罪总称,从而忽略了法律规定的其他几种聚众犯罪情形,因而也不为我们所取。③聚众犯罪是指“刑法分则立法规定必须以聚众的方式实施的犯罪”[24]或“刑法分则立法规定需要由首要分子组织多人共同聚集实施的犯罪”[25]。此类观点一方面以刑法分则立法的明文规定为前提界定聚众犯罪,不至于导致聚众犯罪的外延无限扩大,另一方面又把握了聚众犯罪的核心要素,且不拘泥于“聚众”之概念名词,因而是本文所采取的聚众犯罪概念之观点。
在我国刑法中,分则立法规定“聚众行为”的条文共有以下三种类型:①仅有“首要分子”而无“聚众”。该类型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必然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分裂国家罪、组织越狱罪、暴动越狱罪和武装叛乱、暴乱罪;④二是可能成立单独犯罪的情形,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②“聚众”和“首要分子”均有。该类型的犯罪包括:聚众斗殴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哄抢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聚众冲击军事禁区罪,聚众持械劫狱罪。③仅有“聚众”而无“首要分子”。这类条文具体包括:聚众“打砸抢”行为,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聚众赌博行为,聚众强制猥亵、侮辱妇女行为,聚众闹事破坏监管秩序行为。根据上述界定的聚众犯罪之概念,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聚众犯罪应仅限于第①和第②类型的条文所规定的犯罪,第③类型的条文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均是以聚众的方式实施一般的犯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聚众犯罪”。
据此,可将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属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对于此类聚众犯罪,刑法规定处罚所有的必要参与者,其结果只能是由二人以上构成,不存在单独个人构成犯罪的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属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武装叛乱、暴乱罪,组织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暴动越狱罪,共6个罪名。二是属于任意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对于此类聚众犯罪,可能由单独个人构成,也可能由二人以上共同构成。换言之,刑法仅规定处罚此类聚众犯罪的部分必要参与者,只对部分罪行严重的必要参与者设置了相应法定刑,而不处罚其他必要参加者。当刑法仅规定处罚首要分子时,若首要分子为二人以上,则成立任意共同犯罪,若首要分子仅有一人,则属于单独犯罪。当刑法规定处罚积极参加者和首要分子时,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若积极参加者或首要分子为二人以上时,则成立任意共同犯罪,若只有一个首要分子,且不存在积极参加者或多次参加者时,则属于单独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属于任意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包括: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聚众哄抢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聚众斗殴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聚众冲击军事禁区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秩序罪,共12个罪名。⑤
根据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的分类功能,对于属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当然要排除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一般规定之适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属于任意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也并不意味着必然统一适用刑法总则共犯规定。因为根据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原理,完全可能存在因刑法分则有特别或者例外规定而排除总则一般规定适用的情形。所以对于属于任意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理论完全可以借助意大利刑法学家帕多瓦尼的观点,即将必要共犯划分为“纯正的必要共犯”和“不纯正的必要共犯”。如此一来,在必要共犯的三种具体类型即对向犯、聚众犯和组织犯中,对向犯无疑属于不纯正的必要共犯,组织犯无疑属于纯正的必要共犯,聚众犯中如果刑法规定处罚所有必要参与者的,就属于纯正的必要共犯,如果刑法规定只处罚某些或者某个必要参与者的,就属于不纯正的必要共犯。再进一步,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的外延,实际上仅指德、日刑法必要共犯分类下“纯正的必要共犯”的外延,至于“不纯正的必要共犯”在本质上应当属于任意共同犯罪的范畴。据此,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的外延仅包括集团性共同犯罪和部分聚众性共同犯罪,至于其他所有犯罪,包括对向性共同犯罪和其余部分聚众性共同犯罪,都应属于任意共同犯罪的范畴。
四、结语
诚然,我国刑法中的必要共同犯罪概念源自于德、日刑法中的必要共犯概念,但融入于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体系的必要共同犯罪概念却与必要共犯概念存在本质区别。必要共同犯罪是一种后犯罪判断的、刑法学意义上的实体性概念,它内含两个以上的犯罪者;而必要共犯是一种前犯罪判断的、技术意义上的功能性概念,它仅指行为在自然意义上的主体复数性,二者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上。一直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并未对必要共同犯罪与必要共犯的如此本质区别予以重视,从而普遍存在以必要共犯概念代替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现象,这是导致当前我国必要共同犯罪定罪量刑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既然必要共同犯罪不同于必要共犯,那么必要共同犯罪所含具体犯罪类型当然也不可能等同于必要共犯。事实上,必要共同犯罪的外延要小于必要共犯,其仅包括“纯正的必要共犯”而不包括“不纯正的必要共犯”。在严格区分必要共同犯罪与必要共犯,继而严格划定必要共同犯罪外延的基础上,若再以必要共同犯罪与任意共同犯罪的分类功能为视角,来审视当前我国必要共同犯罪的司法实践,那么其存在的诸如刑法分则不予处罚的对向性参与行为的入罪障碍、必要共同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裁量不规范、不均衡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注释:
① 例如,日本刑法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者,皆为正犯”;第61条规定:“教唆他人实行犯罪者,科以正犯之刑。”如此等等,均未涉及共犯人的主观方面。
② 再如,串通投标罪也是典型的同罪对向犯,但却不是我国刑法中的必要共同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串通投标罪确实是以共同犯罪形式出现的,但在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操控不知情的多家公司围标时,可能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构成串通投标罪(参见孙国祥.串通投标罪若干疑难问题辨析.政治与法律,2009(3):48-52)。
③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对向犯不应属于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范畴”之观点,已经成为一种有力学说。具体可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增订十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60.周铭川.对向犯基本问题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20-125.孙国祥.对合犯与共同犯罪的关系.人民检察,2012(15):6-12.等等。
④ 对于分裂国家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有论者认为通常是共同犯罪,但不完全排除单独个人成立犯罪的可能(参见赵秉志,时延安.略论中国内地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为视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53-61.);也有论者认为属于必要共同犯罪(参见钊作俊.论分裂国家罪的几个问题.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29-33.)。笔者认为,从分裂国家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状表述和刑罚设置上来看,刑法不仅规定了“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方式,更区分了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并配置了相应的法定刑,这充分表明立法者处罚所有必要参与者的态度,因而属于必要共同犯罪。
⑤ 此类聚众犯罪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成立共同犯罪,但是,正如情况各异的司法实践案例表明,完全可能存在单独个人成立此类聚众犯罪的情形。因此,此类聚众犯罪应当属于我国刑法中的任意共同犯罪而非必要共同犯罪。
[1] 佐伯千仞. 共犯理论的源流[M]. 东京: 成文堂,1987: 271.
[2] 弗兰茨·冯·李斯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M]. 埃贝哈德·施密特,修订. 徐久生译. 何秉松校.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0:360.
[3]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 徐久生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847.
[4] 约翰内斯·韦塞尔斯. 德国刑法总论[M]. 李昌珂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 333.
[5] 杜里奥·帕多瓦尼. 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M].陈忠林译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99.
[6] 野村稔. 刑法总论[M]. 全理其,何力译. 邓又天校.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379.
[7] 山口厚. 刑法总论(第2版)[M]. 付立庆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39-342.
[8] 林钰雄. 新刑法总则[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67.
[9] 黄荣坚. 基础刑法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88.
[10] 陈子平. 刑法总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22.
[11] 马克昌. 犯罪通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502.
[12] 陈兴良. 共同犯罪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31.
[13] 林亚刚. 刑法学教义(总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13.
[14] 陈兴良. 犯罪构成论: 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个学术史的考察[J]. 中外法学,2010(1): 49-69.
[15] 张明楷. 外国刑法纲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74. [16] 张忠国. 试论德、日刑法中的必要共犯理论[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2): 132-136.
[17] 黎宏.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J]. 法学研究,2006(1):32-51.
[18] 谢望原. 共同犯罪成立范围与共犯转化犯之共犯认定[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4): 80-88.
[19] 大谷实. 刑法总论[M]. 黎宏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296-297.
[20] 李涛. 必要共犯概念之探讨[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6):153-156.
[21] 张明楷. 刑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1: 348.
[22]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6.
[23] 姜伟. 犯罪形态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4: 240.
[24] 张正新,金泽刚. 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J]. 法商研究,1997(5): 76-80.
[25] 邹江江. 聚众犯罪与聚众性之解构[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85-90.
[编辑: 苏慧]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joint crime
XIONG Yawen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the knowledge of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joint crime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still stays at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joint offense in German and Japanese criminal law. In fact,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systems,the theories and legislations,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in that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at different levels. Essential joint crime is actually equivalent to “pure essential joint offense,” which is a category under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joint offense,while the “impure essential joint offense” should belong to any common crime. If we construct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joint crime in this way,its problems of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can be solved successfully.
essential joint crime; essential joint offense; mutual offense; mod offense
D914
A
1672-3104(2016)04-0032-07
2016-02-29;
2016-03-29
熊亚文(1990-),男,安徽宿松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