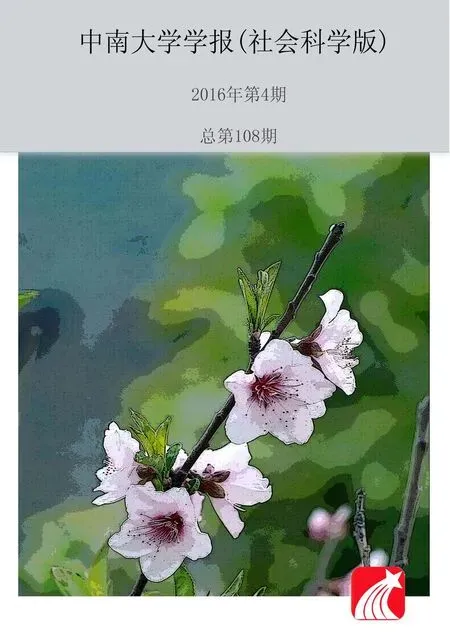净影慧远佛性观对其净土思想的影响
林啸
(北京大学哲学系 宗教学系,北京,100871)
净影慧远佛性观对其净土思想的影响
林啸
(北京大学哲学系 宗教学系,北京,100871)
南北朝晚期地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净影慧远,他对佛性的阐释是以如来藏思想诠释佛性思想的。对慧远《观经疏》《大乘义章》等论著的研究发现,他在论述净土思想时的语言表达、思维模式、论证形式都与他对佛性思想的讨论接近,甚至一致。慧远以“佛性之因”论证“三土差异”,以“性之四门”描述“四门往生因”,以“二门体状”讨论“染、净关系”,以“不善阴等四门”疏解“五逆十恶”等,不仅推动了佛教解经学的发展,而且赋予净土思想更多的义理色彩。
净影慧远;佛性;如来藏;念佛;净土
一、引言
魏晋时期流行的主要佛教思想,是通过“格义”来比附中国哲学的诸多概念而形成的“般若学”。鸠摩罗什来华后,翻译出不少中观类的经典,引发了大众对佛教“空性”的热烈讨论,之后随着涅槃类经典的译出,这种倾向逐渐转向了对“佛性有”的关注①。净影慧远(523-592),是南北朝中后期的论师,亦是地论南道学派②的集大成者。慧远对于佛教义理的理解常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著作丰富,述理宏深,许多著述不仅为后人所广泛引用,也促进了当时佛教解经学的发展。目前国内关于净影慧远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其“佛性”、“净土”等方面,对其不同思想之间的继承性和关联性的研究略显不足。本文以慧远《大乘义章》《观经疏》《无量寿经疏》为主要文献参考,辅以慧远其他著作,来考察慧远佛性观对其净土思想的影响。
二、南北朝佛教背景与净影慧远的佛学倾向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密不可分。梁启超说:“(佛教)中分二期,一曰输入期,南北朝是也;二曰建设期,隋唐是也,实则在输入期中,早己渐图建设,在建设期中亦仍不怠于输入,此不过举其概而己。输入事业之主要者,曰西行求法,曰传译经论。建设事业,则诸宗成立也。”[1](11)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是与中国文化磨合、碰撞的阶段,该时期掀起了一股佛经翻译的高潮,佛教义学理论蓬勃发展。而思想领域,古代中国思想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最解放、最自由的一面,儒学一家的统领局面被打破,佛教与中国本有的文化互相碰撞、激荡、相互学习借鉴的过程中稳步发展。南朝继承东晋重视义理的传统,理论上多有继承与创新,而北朝的佛教偏重功德事业与修行禅坐,义理基本局限于戒律一隅。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受所在地文化环境的影响,佛教被接受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这种动乱割据的局面下,空宗一派的僧侣向南方迁移,鸠摩罗什所传的空宗思想也就随着流传过去。而有宗经典的菩提流支等人立足北方,形成南“空”、北“有”的局势。同时,南方的学说偏重佛教义理,着重义理辨析和经典传持,而北方的学说倡导有系经典,即提倡实修、禅定戒律之学。“南北朝佛教哲学发展的主要三个特点就是在慧学上注意有系佛学、在定、慧三学中比较重视实修、盛行判教、对当时佛学诸派的问题和诸多问题都广泛探讨,精微入理,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2](258)慧远的思想自然也受同时代社会状况和佛教思潮的影响。前秦与东晋的战乱、吕光对西域边境的拓展所带来的动荡,前秦覆灭、后秦建立,后凉内部分歧及同后秦之间的纷争,加之南北朝诸国之间的没有停歇的各种征伐,在这种不停的战争、动荡、分裂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心理承受着身、心双重的摧残,极需一个和平、富足、美好的理想国度作为精神籍慰与依靠。因此,正是当时的社会现状推动着慧远对净土思想高度关注。
慧远生平的佛学研究,在道宣撰《续高僧传》中提到“初学《涅盘经》,顿尽其致”[3](608c),其所注解的《涅槃经义记》,更被僧界奉之为圭臬,足见慧远涅槃学理论之高明;“复向洛下从献公听《法华》、《华严》”[3](608c),《法华》和《华严》的理论,既属于如来藏系的经典,又同时涉及判教、成佛、修行等诸多思想,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尤为丰富,是最能体现佛教圆融思想的二部经典,通过这二部经典的学习,也奠定了慧远思想中圆融无碍的思想特质。书中同时提到“大、小经论普皆博涉,随听深隐特蒙赏异”[3](608c),可知慧远不仅对大乘经典十分熟悉,对小乘经论也多有研究。慧远以地论师的身份来注解诸大乘经典,但从慧远的著作和注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排斥或者特别推崇某一家学说。汤用彤提到:“(法)上之弟子慧远,齐隋之间,推为泰斗。则为地论而兼涅槃之学者……其大乘义章,常归宗涅槃也。”[4](461)慧远晚年还向昙迁学习《摄大乘论》。综观其一生博通诸教,兼具大、小乘思想背景,深谙一乘之微妙,圆融会通诸宗经典,旁征博引,注解了包括《涅槃经》、《观经》《起信论》、《维摩诘经》在内的数十部经论,[5](81)实难定于某一家之论说。实际上这既是慧远本人对于时代命题所做的积极响应,又是他自己学术历程的必然归趣;既是对印度佛教精神的继承,又是结合时弊之困和民众喜好而做出极富中国化的尝试与创新。正如赖永海所说:“战争频发,人人自危,这一切使得人间充满着世事无常,人生如寄之悲戚。既然佛教的般若学不能够度人出生死苦海,谈玄说妙也不能够避免朝不保夕的命运,涅槃佛性说的解脱思想自然成为陷于绝境中人民的唯一希望。”[6](239)慧远对涅槃学的理解和研究也是精深入微,他认为《观经》高于《涅槃经》,而隋唐时期不同宗派的僧人都有把“涅槃佛性说”与“往生净土”等同起来的思想倾向,认为在往生的同时就实现了涅槃“常、乐、我、净”四德。除此之外,考慧远诸论著,我们发现其引用的论著种类,除了一般所熟知的经典外,有系一类的经典的引用也十分频繁,包括《阿毗达摩杂心论》③和晚出的《起信论》④等。地论师虽以《十地经论》为主要研习经典,但也兼通说一切有部毗昙学。据刘元琪考证:“在北朝时期毗昙学兴盛,被称为毗昙孔子的智游传给慧嵩,而慧嵩与慧远在时间、所在地点上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慧远受毗昙学的影响较深,且慧远在论述大乘义章的某一问题的时候,也首列毗昙直说,也可以看出一二。”[2](258)吕澂认为:北方毗昙思想的盛行,从学术思想的渊源上来看,可能与北方一开始就有《地持论》的翻译有关,以后又有《华严》、《十地》以及《摄论》、《唯识》等书的译传有关,而毗昙学派的思想是与上座部有系是接近的。[7]慧远的佛学思想广博宏富,和他受有系、如来藏系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从他关于真、妄和合的心识思想、佛性之体等论述中就可以看出来。而上座部有系即是说一切有部。慧远在分析佛性体义和净土思想时的论证模式,就与有部关于诸法实有的分析十分接近⑤。当然,这是受《起信论》影响还是有系经典影响更多,也不好下定论。而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对净土思想的构建和完善也启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三世实有”的说法使净土往生成佛和菩萨道的行化问题得到了解决。笔者认为,从思想渊源和影响上来说,这也是慧远对净土经典进行阐发、注疏的其中一方面因素。
慧远一系的地论学派深受印度如来藏系统的影响⑥,而慧远作为南派地论师的主要人物之一,以如来藏系经典的“真心学说”来构建其主要的思想构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佛性的定义和疏解,同时也影响了慧远净土思想和其自身修学实践倾向的形成。南、北二道争论的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佛性的本、始问题,也就是当、现问题。从慧远的角度来看,本有的佛性,实际上是因为真、妄合和的觉性随缘集起,才无法显现;所谓始有,在慧远的佛性理论中更接近于报佛性层面,也就是修学实践的部分。而慧远的心识思想以如来藏思想的真心思想为基本,融合了瑜伽行派的心识思想,认为佛性是本有的。⑦在如来藏经典《宝性论》中提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时,解释其中的一种意思就是法身遍满义,《观经》中的“诸佛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正是表达了这种法身遍一切处、诸佛与众生不二的概念。《观经》中“是心是佛,是心作佛”[8](533b)的论述可以说与如来藏系统的心性说是一致的,强调了自心本具成佛的可能性。以自利利他、提倡六度万行的菩萨修行伴随着本愿思想的产生,为净土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托,这与同属如来藏系经典的《涅槃经》,在思想上有相似性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符合慧远自身涅槃佛性说的导向。这种真心本觉思想和慧远提出的佛性内涵、真识心概念等极为契合,从而引发了慧远对《无量寿经》和《观经》进行了注疏和阐演,这就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这里就不作详述。
三、净影慧远净土思想的佛性观印记
“伴随着晋宋之际般若学逐渐向涅槃学的转换,南朝佛教教风、僧人学风也发生巨大的变革,其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因素。”[9](32-56)此次转变以一股全新的思潮,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方向,佛教学者从原先“注重义理”的讨论转向对“解脱实践”的追求,并结合自身修证为其进行充分的论证,形成多个佛教学派。慧远作为地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限于自身所学,而是广泛注疏各类经典,尤其是对净土经典的重视和判释,影响了同时代其他学派对净土思想的看法,也从侧面体现了慧远兼容并包、圆融无碍的思想特色。对慧远思想进行研究,必须从他作为僧人的角度去理解,因为无论他对佛性的演绎、对心识的疏解,亦或是他的判教理论和净土思想,毋庸置疑都是为他与当时的佛教界提供精神依托,为其修学实践进行论证。
(一)“宣说佛性之因”与“三土差异”论
“为令众生不放逸故,宣说佛性,若不说性,总心自轻,谓己不能成大菩提,无心趣道,多起放逸,故说众生悉有佛性定必当成,令舍放逸随顺趣向。《宝性论》中:“所为有五,一为众生於己自身生怯弱心……二为轻慢余众生故,宣说佛性,彼当作佛,云何可轻……以知众生有佛性故;三为妄执我众生故,宣说佛性,不同情取……四为执着虚妄法故,宣说佛性,不同所取;五为诽谤真如佛性……”[10](477c)慧远引用《宝性论》中的内容,谈到了需要为其宣说佛性的五类众生,肯定了宣说佛性对众生的重要性。在慧远看来,如果不为众生宣说佛性,众生会以为自己不能成佛,就不断放纵自己,无心修道,最后堕落在恶道,这种思想倾向也表现在他对净土是报土亦或是化土、凡夫是否可入报土的看法上。他在《大乘义章》中认为,净土不是佛所独居,而是佛与凡夫共住。虽然佛与凡夫共居,但净土的类别又不一样,可分为事、相、真三种净土。慧远认为凡夫,声闻、缘觉分别对应事土和相土,认为唯初地以上菩萨和佛居于真净土,而“真净土”又分为真土和应土,“真土”是从法身层面来理解,即以法界为身,而法身所对应自身的真实法性,则有相应所居之土即“真土”。“应土”指方便善巧所现之土,释迦牟尼示现在人间,故人间也称为应土,别称“圆应土”。而真土就是佛自受用身,为显涅槃妙德之功用的依报庄严之处所。法性土、实报土由真土所开显,圆应土即是化土,而这三土又与佛的三身一一对应。至于“化土”,有善、恶与染、净之别,是为度化众生而方便示现的。简而言之,化土不是佛自受用土,是受用法乐之地,度化众生之所。慧远认为弥陀净土的染、净,是因为凡夫之心有漏,故心识有差别,这就产生业感的不同。凡夫流被慧远归为临终仍持有漏心,虽发出世之愿,但只能往生事净土,慧远对此认为:“言事净者,是凡夫人所居土也。凡夫以其有漏净业得净境界,众宝庄严饰事相严丽名为事净,然此事净。”[10](834a)慧远将事净土又分为二种,一种求有漏之业,为三界所摄之土;一种以求无漏业,超出三界外之土。慧远从心识的角度认为弥陀净土中诸宝林树和种种亭台楼阁的庄严景象,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故弥陀净土依报所缘之境亦是无漏,但从他对佛性的理解来看,又认为众生只要修出世善法或者菩提道,还是可以往生第二种事净土,只是与真土还有实质性差别。他在《义疏》中说到:“弥陀佛国,净土中粗,更有妙刹,此经不说,《华严》具辨。”[12](182c)虽然如此,慧远至少将凡夫往生的境界拔高了不少,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范畴。通过慧远对净土的分类可以看出,他认为不同类型的净土都是由众生自身的福报、智慧与业力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的智慧就是指众生心识差别而产生所缘境之不同。从上文对比可知,慧远对凡夫往生的去处和净土的等级虽已有自己的见解,但基本上还是和他宣说佛性思想的初衷是一致的,着重以凡夫发心、起信为首,以一切众生皆能得度为根本出发点。
(二)“性”之四义与“四门往生因”
慧远认为佛性不同,是因为“性”的表义不一,据此慧远提出“种子因义、体义、不改义、性别义”四种。其中种子因义就是“一者种子因本之义,所言种者,众生自实如来藏性……云何名性,性者所谓阿耨菩提中道种子”[10](472a)。慧远据《涅槃经》认为“性”就有种子的意思即成佛种子,是众生本具之如来藏性。对于体义,慧远认为:“说体有四:一佛因自体,名为佛性,谓真识心;二佛果自体,名为佛性,所谓法身;第三通就佛因佛果,同一觉性,名为佛性……第四通说诸法自体,故名为性,此性唯是诸佛所穷,就佛以明诸法体性。故云佛性,此后一义,是所知性,通其内外。”[10](472a)第一,佛因自体,慧远认为就是真识心,他在《涅槃经义记》中说,“如来藏者是真识心”[13](693b)“如来藏者,佛性异名,论其体也,是真识心”[13](692c)。第二,佛果自体,就是法身佛。所谓法身佛,慧远在《大乘义章》解释到:“法者所谓无始法性,此法是其众生体实,妄想覆缠……名为法身……法身体有觉照之义,名法身佛。”[10](837c)第三,通于佛因佛果的觉性自体,参考慧远的论著,我们大致可知此觉性是内化于佛因、佛果中的一种存在,隐为佛因,显为佛果,因无明遮蔽故有所分别,但觉性自体不易。第四,诸法自体,即佛能遍入、遍知一切事物和众生之体性,前后四种囊括有情、无情所有众生。不改义即在上述四种体义下所衍生:“一因体不改,说之为性……此就因时,不可随缘……就体以论,故名不改;二果体不改,说名为性,一得常然,不可坏故;第三、通就因、果自体不改名性,如麦因果麦性不改,以不改故,种麦得麦,不得余物……在斯第四,通说诸法体实不改名性,虽复缘别内外染净,性实平等湛然一味故曰不改。”[10](472b)一是佛因自体不改,这其中又分为随缘不改和得果不改,慧远认为作为佛因的真识心有随缘而染的集起作用,如“向虽在染,而不作染,今与妄合,缘集起染,如水随风波浪集起”[10](530a),认为真识心本来是清净无染的,只是因为受外在染法的影响,与无明结合,才集起生死种种染法,如水波之喻,但是这种染污又不会更改他的本性:“第八真识,体如一味,妙出情妄,故说为真。又复随缘种种,故异变体无失坏,故名为真。”[10](525b)二是而得果不改,就是说在佛因和佛果之间转换以及证佛果的同时还不会有生灭变化;佛果自体不改也就是一证永证,不会退失。三是说无论在众生界还是佛界,这种作佛因,成佛果定当不改。四是诸法自体不改,就说真识心随外缘起染法的同时,虽然表面上有内、外,染、净的不同,其实体性是没有分别的,平等一味。慧远的这四种义涵盖了有情、无情众生,包含了很浓厚的修行实践色彩。种子义说明了众生应该相信佛所说言教真实不虚,相信自身本具如来藏性,接着才能引发接下来的体义,佛因自体为众生本具之真识心。而佛果自体“法身佛”,是众生祛除无明遮蔽后所显的状态,这种不变的真识心就是如来藏性,在佛因时就已得佛果,二者是一种以果修因、相即不离的状态,这种以前观后、以后观前的相续状态,就需要一个切实可靠的行门用于发显。通过对比慧远的著述,我们发现慧远在《观经义疏》中论述往生方法和手段的时候,也是围绕对“性”之体的理解所展开,开头就说到往生极乐的因:“依大品住宣说般若空慧为因,修空慧除灭罪障故于净土欲生即生,依《涅槃经》一切善业皆净土因不可具列……依往生论五门为因。”[12](183b)慧远认为往生净土的因,若依《大品般若》所说是空慧;依《涅槃经》所说是修戒、修施、修慧和护法;依《维摩经》所说是饶益众生等八种法;依《往生论》所说是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这五种门。慧远总结后分为四门:“一修观往生,观别十六备如上辨;二修业往生,净业有三亦如上说;三修心往生。一者诚心,诚谓实也……二者深心,信乐慇至欲生彼国。三者回向发愿之心,直尔趣求说之为愿挟善趣求说为回向。愿有二种,一愿生彼国,二愿见彼佛,所行所成亦尔,此是第三修心往生。四归向故生……自虽无行善友,为说佛法僧名,或为叹说弥陀佛德……于中或念或礼或叹或称其名悉得往生。”[12](183a)第一门“修观”,即是修习十六种观想,发愿往生,这就如种子义一样,必须先认可佛所说真实不虚,才能发起观想,慧远将此观列为“定善”“定”就是不可或缺的意思,这和对种子义所说众生本具如来藏性的说法一致。第二门“修业”,其中说到 :“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8](663a)经中认为此三福为三世诸佛之正因,即众生明白本具如来藏性后,需依此修学,让发显的佛性成就果德功用。而慧远在谈到性之体义的时候,也用到了相似的概念,就是佛因自体、佛果自体,前者指真识心,由于心识受外缘所集起的染法,故被遮蔽。通过对三福的修习能够祛除无明的遮蔽,这与上面论述真识心发显的模式和径路也是一致的。通过一段时间的熏修,真识心就减少外缘的依附而产生对六根的诸种影响,这样被无明烦恼所遮盖的佛果自体才能够显现而见诸佛,此处见佛特指见阿弥陀佛,而《义疏》中说:“一明见前阿弥陀佛身相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二明由见一切佛故即得具足念佛三昧。”[12](180c)这里说到见一佛即是见诸佛,因为诸佛体同,实际上和佛性义中诸法自体无所不在是一致的。第三门“修心”,主要从从个人心识上加强对弥陀的认识、厌离娑婆和欣求极乐的决心,进而将因地所修之功德用来庄严果地,这与慧远对佛性体义中佛因自体和佛果自体之间关系的论述也是一致的。第四门“归向”,慧远认为此类人虽无善行,但得诸善友赞叹三宝之妙,赞叹诸圣和净土之庄严,故一心归向,或以心念,或以身体拜之,或以声赞叹之,或以口称唱其名字,由此皆得往生极乐。实际上这种论证模式又回到为众生宣说佛性的原因上来,还是给不同层次的人都予以机会和希望。慧远所举出诸往生之因,全部都是具体的实践方法,结合他对于佛性的论述来理解,就能够更加清晰明朗。
(三) 佛性之二门体状与“染、净”“佛身”
佛性的体状,慧远解释说:“一约缘分二,缘有染净,染谓生死,净谓涅槃,生死涅槃,体皆是性故。”[10](180c)佛性有染、净二门即觉性与染法合和,它有生起染法的作用,便有生死的一面,反之亦然;另外还有体、相二门,佛性本身是恒常一如,没有分别相的,这是佛性的体。但是当其随缘的时候,呈现出清净、染污的各种相状,就有用的一面,如:“体用分二,废缘论性,性常一味,是其体也,随缘辨性,性有净秽,是其用也。”[10](472c)佛性还有能知与所知:“三能、所分二,一能知性,二所知性,能知性者,谓真识心,以此真心觉知性故,与无明合,便起妄……所知性者,谓如法性、实际、实相、法界……皆是所知性也,此所知性,该通内外。”[10](472c)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慧远将能知与真识心相对,所知与诸法实相对应。最后慧远论述了法佛性与报佛性不一不异的关系,法佛性与上文对净土种类的判释相关,认为法身佛就是众生本具之觉性发显,从而成就佛身。而关于报身佛,慧远说到:“报身佛者,酬因为报……又德聚积亦名为身,报身觉照,名之为佛。”[10](838a)慧远认为报身就是修行功德所感得的实在性聚合体,故称为身,因具有觉性作用,故又称为佛。慧远认为无论是法身佛还是报身佛,二者的觉性都是源于众生本具之真识心,当真识心不被烦恼遮蔽时,便是法身佛。随着真识心显露,烦恼相逐渐消失,外在的功德和内在所积聚的功德实体,就构成了报身佛。慧远还引用黄金与矿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认为法身佛的体性只有显、隐之别。通过不同层次的修行,可以生起如佛般真实德性的功德,亦如黄金,虽无体,但金从矿中出土后,却能形成各种由黄金所作之物。从以上可知,慧远的法佛和报佛皆作为如来藏来定义,即觉性,慧远亦称此如来藏作为第八真识心的别称:“八识心体是法佛性,彼心体上,从本已来,有可从缘生报佛义,名报佛性。”[10](843c)慧远将法佛与报佛的问题又转回到了真识心开显问题上来,而真识心的开显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佛性的当常、现常问题即本觉、始觉,冯焕珍认为:“慧远直接将真识心视为众生本具的正因佛性,而将此心得二种净用分别等同于从中分出去的法、报二佛性问题,随缘显用义对应法佛性,其随缘作用义则对应报佛性,这样就顺利地将《起信论》和《摄论学》的心识观与当时的佛性论贯通起来。”[5](270)慧远对凡夫往生净土类别的判定,完全是以心识的有漏、无漏作为依据。慧远在论述心识问题的时候,更是借《起信论》说到:“前六及七同名妄识……迷于因缘虚假之法,妄取定性,故名为妄。第七妄识,心外无法,妄取有相故名为妄。第八真识,体如一味……如一味药流出异味而体无异,又以恒沙真法集成,内照自体恒法,故名为真,真妄如是。”[12](525b)他认为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和的,在流转过程中无论是背觉合尘亦或是背尘合觉,都不失其清净自性本心,也就是真识心,实际上这种表述更倾向于北道派。换言之,阿赖耶识其实是“真识心无始以来受到根本无明的熏习,所形成的‘生死之根源’”[5](219)。
慧远在论述到佛土相状的时候,也常用染、净关系来论述,如《大乘义章》中“诸佛菩萨实证善根所得之土,实性缘起,妙净离染,常不变故,故曰真净,然此真净因无缘念”,“土虽清净应与染合”,[10](835a)慧远从诸法本然安住、实相无相出发,认为由内心显发的性相常住不变,所感、所证的土也离染而真净,但又认为诸佛之真净不碍与染合,这和慧远真识心染、净合和的观点可谓是一致的。慧远对佛土种类之间的关系,也使用佛性体状、体、用的方式,其中说到:“其应土者,随情现示有局别,染净躯分形殊,善恶诸相庄严事别各异,应土如是。”[10](845b)慧远认为真土虽然是没有染污,但是在随各类众生和因缘相互接触时就呈现出净、染各种形殊之相状。而对于佛性的能知与所知,在慧远论述净土能净与所净的关系中也可以看见类似论证模式:“有二种,一是相净……二自在净,犹如净珠……所现无碍,故曰自在……一切国土平等清净,净相之土,彼秽此净,不名平等,自在净者,染净圆通,法界齐等,故曰平等,此二土体,庄严净者。”[10](845c)慧远认为能净(相净)还不够彻底,因仍有与秽土相对的相,故不称为真实平等,而所净(自在净),是能够圆融染净的诸法体性,这与佛性所知相的第一义空的概念是同一个意思。上文提及佛因自体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法身佛,如果结合上文慧远的佛身观来看,慧远对往生人群的界定,很大程度与其佛身观有密切关系。而慧远的佛身观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其真识心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汲取《摄大乘论》中对于佛三身的论述,将早期在般若经典中提到的佛身观内容进一步深化。这里的法佛性就对照于真土中的应土,而报佛性就对照那个唯佛受用的真土,通过众生不断修习所感功德而聚合而成的实际存在,成为沟通法、报二佛性的桥梁,这样使法、报二佛之间的关系紧密起来,与慧远对佛性有法佛性、报佛性的论述是一致的。
(四) 佛性“不善阴”等四门与“五逆十恶”往生
除此之外,慧远对《观经》还给予评价:“此经乃是菩萨藏收。”[12](173a)慧远认为《观经》属于大乘菩萨藏经典,而不是小乘经典,并且认为净土法门乃顿教所收,但这其中又表现出慧远思想的一个矛盾,既然慧远判弥陀净土是凡夫可往生的事净土,必然不是声闻、二乘的相净土,也不是初地、佛住的真净土,为何又将净土经典判为菩萨藏所摄呢?修学此经观法的凡夫是否可被称为菩萨呢?结合上文来看,慧远承认凡夫可往生弥陀净土,但降低了弥陀净土的层次,这恐怕是慧远在修行方式上过于注重自力的原因,忽略了他力(佛力)的作用。从学理上无法接受弥陀净土是报土,弥陀是报佛、凡夫可往生报土的理论,但若从慧远佛性理论的构建来说,他还是希望凡夫可以往生,通过往生达到转凡成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慧远在《观经义疏》中判净土法门为顿教所收,因为这与慧远的判教理路是一致的。从某种层面来看,判教是时代所驱,是对追求无有众苦佛国的期冀,是对一种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时代背景紧紧相连。慧远认为大乘经典无论是从哪方面来进行阐释佛教义理或者修学法门,在表述上或有不同,但在最终目的上是殊途同归,并无绝对的深、浅,优、劣之别。慧远对《观经》中“唯除五逆不得生”和《无量寿经》中“五逆十念得生”也做了一个解释:“于彼观经之中,说五逆等皆得往生。今此经中言不得生,此言何论?释有两义:一约人分别,人有二种:一者久发大乘心人,遇缘造逆,如闍王等。此虽造逆,必有重悔,发心求出,能灭重罪,为是得生,观经据此;二者先来不发大心,现造逆罪,多无重悔,不能决定发菩提心,为是不生,此经据此。二约行分别,行有定散,有人虽复造作逆罪,能修十六正观善根,深观佛德,除灭重罪,则得往生,观经据此。若人造逆,不能修习观佛三昧,虽作余善,不能灭罪,故不往生,此经据此。”[12](107b)这和慧远在论述佛性性状的不善阴的内容和看法是一致的。慧远在《大乘义章》说到:“不善阴者,佛性集成外凡五阴,……阴即是性,言果阴者,佛性集成佛果五阴……唯有方便可生之义,或说为四,如涅槃说,一阐提人有,善根人无。”[12](473a)慧远认为凡夫的五阴虽有漏,却是真识心随染缘而起,从真性而言,佛性本无染、净。他说到:“言理性者,废缘谈实……真体一味,非因非果,与涅槃中非因果性,其一也。四中初一阐提人有,善根人无,第二善阴,善根人有,阐提人无,第三果阴,二人俱无,第四理性,二人俱有。”[12](473b)他认为理性是剔除了随缘染、净的分别,就实体而论,亦是自觉而得自体。所以从这一点看,佛性不但善根人有,一阐提也有,这种思想自然影响了慧远对往生人群的看法。慧远认为五逆之人只要临终至心忏悔,还是能灭罪得生,不得生之人不限于五逆之人,只要是生前造恶,临终没有发起忏悔的念头,一样不能往生,所以经文中矛盾的主要目的是要警戒修学之人,不要造下五逆之罪。肯尼斯·k·田中也通过对慧远论著的分析,认为慧远将明明不是圣人的三品众生(善趣以下的众生)都判为圣人,旨在激励修行者和信众发愿往生到最高的品位。[14]慧远对一阐提是否有佛性及能够成佛的看法,很明显与他佛性体状中“不善阴”等四门论证方式一致,限于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作赘述。
四、慧远佛性观对其净土思想影响的特征与意义
佛教晋宋之际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的转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讨论和会通,从最初“南方重义学、北方重禅门”的分界格局到后来南、北佛教统一时“禅定实践与义理兼弘”的模式,如方立天所说:“般若空”到“佛性有”的转变过程,也是中国佛教吸收印度佛教、消化佛教义理的时期[16](346)。慧远对此也谈到:“经多说空,破诸法性,说诸法空,今此何故宣说佛性?”[12](447c)他回答到:“然彼清净法界门中,备一切义,诸法缘起,互相集成,就空论法,无法不空,据性辨法,无法非性。”[12](109b)慧远从他对佛性的看法出发,认为诸法性空,但是佛性之觉体不碍染、净,随缘所成,互为依凭,认为从法义上来说,一切法当体是空,从性义上来说,一切法又皆依性住,此种佛性观所衍生出的结果必然就导向了实践层面的为学倾向。他在《义疏》却说:“释迦正法有五百年,像法千岁,末法万岁,一切皆过,名为灭尽。我以慈下,明已留意。佛以慈悲怜愍众生。故法灭后,独留此经百岁济度,以此经中开示净土令人求生,故偏留之。《大涅槃经》显示佛性,教圣中深,圣人先隐,为是先灭,此经教人厌苦求乐,济凡中要,为是后灭。法随人别,故灭不同,其有众生值斯经者所愿皆得。”[12](116a)慧远以佛教信仰者的视角,认为《涅槃经》宣说佛性是以深奥的义理先接引部分圣人先到达彼岸,而《涅槃经》会随着末法时期的到来而提前消失。而《观经》因为教人往生,是以实际的事用来接引凡夫到达彼岸,一个直说佛性,一个以果显佛性的存在。二者看似类似,但慧远认为《观经》比《涅槃经》来得更重要,因为《观经》将佛性落实到了具体的实践范畴。如义疏中说 “末后一偈,教令定去,设满世界火,必过要闻法,决意定去,会当成佛。广济生死,明去所为,会当成佛”[12](109b),“彰彼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明寿长远,无有中夭,除愿为物余国受身”。[12](109b)慧远认为众生成佛无疑是对众生皆有佛性的最好论证,故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对比,将涅槃佛性论导向了往生净土说。据木村泰贤《大乘佛教思想论》所言:“中期大乘佛教相关理论及经典传译及发展,是为要完成龙树时代所留下的三个任务:(一)关于真空妙有最终根据之说明的不足;(二)一切众生成佛的心理及其理论根据之说明的不足;(三)关于佛陀论尚未完全,尤其是法身观尚未完成。”[15](385)以龙树为代表的初期大乘佛教虽然也谈念佛,但仍将其作为万行中的一行而已,并没有特别的突出与强调,仍然站在般若类经典的立场下破“有”谈“空”;而到了中期阶段,虽然其它大乘经典也逐渐兴盛和传播,但是般若“诸法性空”思想,仍是所有大乘思想的理论基石。慧远以其极富理论特色的佛性说,对净土思想进行了诠释,使净土思想以真空不离妙有、妙有依赖真空的模式出现,若从心识的开显和共业的形成来审视的话,西方净土清净庄严的环境,当体即空,此则非有,缘生无性故空,空而常有,二者相互交彻,两相无碍。正如赖永海所说,“佛教之最终目的是成佛,但成佛是靠自悟自度,抑靠诸佛菩萨的慈悲普救,这也是佛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亦即悟与救、自力与他力的问题”[6](22)。这也就是说“佛性”虽然是理论层面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若离开了实践层面的重视,那么也将失其根本宗旨。慧远运用自己丰富的佛学思想,圆融、处理了真空与妙有之间的关系,既彰显了佛性理论的多重内涵,也反应了其在实践层面的为学倾向。
净土法门因其本身缺乏思想,所以当时并没有受注重“谈玄论理”的佛教界太多关注,僧人对净土经典的阐释、发挥也不多,直到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南北朝社会在经过动荡、分裂后,佛教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扶持,一方面通过与儒、道二家在不同领域的碰撞、融合,迈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慧远深受地论南道系的影响,根据《摄论》的心识理念,结合《起信论》的真心本觉思想,构建了一套以佛性观为线索主线的净土思想修学体系,集中体现在“心识所对应的净土类别”、“四门往生因与四性义”、“佛性之二门体状与佛土染、净”、“不善阴与五逆十恶往生”四个方面:第一,确立了慧远净土思想的境界论,厘清了凡夫往生的类别及对净土性质的界定,指出二者皆由其心识开显程度所决定;第二,明确了慧远净土思想的修行论,确立了净土法门基本理念与行持方法;第三,明确了慧远净土思想的主体论,慧远借用真识心随缘集起染法的方式,来论述了净土的能净和所净的关系,且结合佛身观指出众生通过修行是如何实现如如不动的觉性在佛因自体与佛果自体、法佛性与报佛性之间的转换;第四,慧远延续了关于道生以来对“一阐提”是否有佛性的讨论,并在净土经典中为“一阐提”成佛找到依据,通过佛性不善阴等四门,论述了五逆十恶往生的确定性,继承和发展了道生以来的佛性论和顿悟成佛说。慧远的净土思想,不仅注重体系的理论构建,而且还注重学人修学倾向的根本旨趣,同时又不离社会生活的人心需求,认为真正的往生净土,还是离不开对于如来藏性的体察、重视真识心的开显和无明的祛除。慧远的净土思想虽然与后代的净土思想比起来较为重视自力,但是并不影响其对后世净土思想的影响。往生净土的人群到底是凡夫还是圣人?这无疑关系到净土信仰者的信心及其传播程度,慧远的判释不仅使净土思想的理论构建更加完善,扩大了往生人群的范围,而且对净土宗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慧远对净土的相关论述也被后代僧人广为借鉴和引用。慧远从“以业摄识”的角度,认为内心清净才能够感得国土清净,实际上这也迎合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中国传统思想。慧远以真识心问题来阐发和演绎其净土思想,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颇有“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味道,只是慧远对往生和净土还是持肯定态度。慧远将思辨高深的理论与务实的修学结合起来,站在当时学界所关注的“佛性”问题上来会通净土思想,不仅是圆融处理南、北佛学之间矛盾的一种积极尝试,更是在对中、印二种文化碰撞、不同哲学概念、范畴相互冲突的部分进行融合与会通,进行适当的选择与改造,使空、有,染、净,能、所等关系皆能够很好地进行解释与运用。若从佛性论与解脱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所有宗派都无一例外地是在讨论和论证这两个问题,而慧远的净土思想同时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从以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慧远的净土思想处处彰显其佛性学说,且还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其真识心、判教等思想,充分体现了慧远注重修学实践的为学倾向。通过本文的对比,对于了解净土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宗派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的意义。
注释:
① 张雪松认为涅槃佛性的出现,解决了般若智慧与现实之脱离,认为涅槃佛性的概念统合了本体与妙用、般若与方便等一些列问题,见张雪松著《唐前中国佛教史稿论》,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202页。
② “关于慧远是否属于地论宗的说法,吉津宜英认为并没有相关足够的证据说明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在自己的著作宣称自己属于什么宗”,见《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研究纪要·31·关于地论师的考证》,驹泽大学出版社,1973出版,第307-323页。“后代大多以其法统或者著作来进行判定,肯尼斯·k·田中认为把其称为“法上系统”更为合适”,详见所著,冯焕珍,宋婕译《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净影慧远的〈观经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③ 《大乘义章》中引用《杂心论》多达137次之多。
④ 日本学者吉津宜英和望月信亨都怀疑《起信论义疏》的作者,包括《起信论》真伪问题也争论不小,印顺在《起信论评议》一文中认为:“起信论无论是中国或是印度造的,它所代表的思想,在佛教思想中有它独到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见印顺《中国佛教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第303页。)
⑤ 一切有部关于诸法实有的分析,显然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法的真实本质,即法性、法体即本体的层面,一是作用的刹那显现,也即现象的层面。三世实有的法,本体是真实存在的,而它在不同时空的流转,会依据不同情况,产生不同的结果,可于一世摄三世之事,亦可于三世中摄独有一实体之法,由本体存在的发显而决定其变化的最后结果。我们发现慧远对净土思想的论述,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特别是法佛性和报佛性两者关系的问题,这种真识心的开显承载了展现法佛性的本来面目及转换成聚合实在报佛性的部分。
⑥ 廖明活认为慧远师承法上,而法上又师承慧光,慧光属于南道系的地论学,地论学为印度瑜伽行学派在中国的延续,这通过慧远以心识思想为骨干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印度瑜伽行系统也重视心识的概念);又在印度佛教发展中,以心识思想为核心的宗派,除了瑜伽行派外,还有如来藏一系所流传的经典,通过慧远学术背景可以看出他深受此系经典的影响,因为其心识思想以如来藏系经典的“真心学说”为基本,并融合瑜伽行心识理论而形成。参见廖明活:《净影慧远思想述要》,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出版,第19页。
⑦ 廖明活认为慧远对八识义的看法,以《起信论》、《涅槃经》等经论的佛性思想来统摄《楞伽经》、《摄大乘论》等经论的唯识学,会通性、相二宗;慧远的《大乘起信论义疏》会通性、相二宗,是历史上最早用“起信论”观点解释瑜伽唯识思想的著作,这对唐代的法相唯识宗具有一定的影响。见其著《净影慧远思想述要》第40-47页,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出版。
[1] 梁启超.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2] 刘元琪. 净影慧远《大乘义章》佛学思想研究[C]// 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三辑·第23册. 台北: 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
[3] 道宣. 续高僧传·卷8[C]// 中华藏·第61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96.
[4]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冯焕珍. 回归本觉——净影慧远的真识心缘起思想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 赖永海. 中国佛性论[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7] 吕澂.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8] 畺良耶舍译.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卷1[C]// 中华藏·第18册.北京: 中华书局,1996.
[9] 任继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10] 慧远. 大乘义章·卷1[C]// 大正藏·第44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1] 菩提流支译,世亲造.无量寿经优波提舍·卷1[C]// 中华藏·第27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96.
[12] 慧远. 观无量寿经义疏·卷1[C]// 大正藏·第44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3] 慧远. 大般涅槃经义记·卷3[C]// 大正藏·第44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4] 肯尼斯·k·田中. 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净影慧远的《观经义疏》[M]. 冯焕珍,宋婕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5] 木村泰贤. 大乘佛教思想论[M]. 演培译. 台北: 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16] 方立天. 魏晋南北朝佛教[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编辑: 颜关明]
Influence of Jingying Huiyuan’s Buddha-nature view on his pure-land thought
LIN Xiao
(School of Philosophy & Relig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Jingying Huiyuan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Ground School in lat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and his interpretations of Buddha natur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ypical interpretation of tathagata-garbha thoughts.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on Amitayurdhyana Sutra and Essay on the Meaning of Mahayana,we find out that when he was explaining pure-land thought,the language,modes of thinking and ways of argument he used are similar to,even the same as those he used in the process of explaining Buddha nature. For example,Huiyuan used “the reason of buddha nature”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of lands,” “four aspects of nature” to describe “four aspects of future life,” “two symptoms” to discus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ean and the dirty,” “no good aspects” to demonstrate “Anantarika-karma.” This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ddhist exegetics,but also endows pure-land thought with more theoretical colour.
Jingying Huiyuan; Buddha-nature; tathagata-garbha; pray to Buddha; pure land
B948
A
1672-3104(2016)04-0015-08
2015-10-28;
2016-01-02
林啸(1988-),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佛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