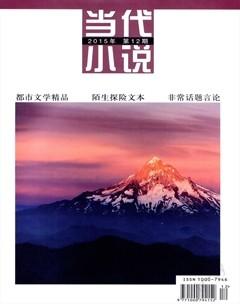寻找自由天空的文学之鹰
李君君 张丽军
自由这个古老而又美丽的字眼,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在为它做着不懈的奋斗。人们不断地做着关于自由的美梦,由此衍生出一篇篇动人心弦的诗篇。自由也成为一个响亮的号角,让人们打破城堡坚硬的壁垒,将那些独享自由的独裁者彻底放逐。我们的五四先辈们在当时蒙昧一片的中国率先举起“自由”的大旗,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性的实现。未来被他们寄予了无数美好的期待和热烈的期盼,然而我们必须遗憾地承认,在以自由精神为基本精神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因为现实中的种种琐碎恰恰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回顾这个季节的文学期刊,作品着重探讨的正是现代人这种被各种“锁链”所束缚住的不自由状态。
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自由而鲜活的人,在现代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被生活的庸常、荒谬挤压得变了形的、枯萎的人。杨遥的《鹰在天上》(2015年第4期)中,网销员朱青因整天对着电脑高度紧张地工作导致年纪轻轻浑身上下都是毛病,只有倒立才能缓解他的病痛,让他能够重新思考。“我”在好友陈克难的单位偶然看到了倒立的朱青,从此对他发生了兴趣。不久,朱青突然辞职不知去向,“我”和陈克难大为纳罕。为找出朱青辞职的原因,陈克难接替了朱青的职位,通过网页浏览记录陈发现朱青辞职是为了去捕鹰。“我”得知后立刻前往老家代州寻找朱青,那是个唐时盛产雄鹰的村落,如今却不见一只鹰的影子,村民也早已遗忘了这段历史,过着千篇一律的凋敝的灰色的生活。辗转多处,“我”终于在建设银行的自动服务区见到了朱青,近乎流浪的他还在读克尔恺郭尔《非此即彼》。与他分别后,“我”读他读过的书,也患上了类似朱青的现代病。后来,陈克难和祖上曾以捕鹰显赫一时的少年翔同朱青一起去捕鹰。几次失败后,他们终于捕到一只鹰,可最后又认为为了自己的好玩而去捕捉这种自由的生灵是不对的,一致同意把它放了。此后朱青去乡下种地,试图种出理想的粮食,而少年翔则在北方碧蓝如镜的江里养鱼。当朱青为种地焦头烂额,艰难收获的粮食又被村民大量偷盗时,少年翔的渔民梦也因石油泄漏在江里而破灭了。这时的朱青感到自己现在和原先在单位时同样的疲惫不堪,两个试图打破束缚,回归自然的乌托邦构想无疾而终。在这部作品中,“鹰”这种自由而有灵性的生灵成了朱青这些“笼子中的人”所向往的自由的象征。朱青在倒立时弄明白了自己因为工作的束缚而变得不自由,他想要的生活是无拘无束地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而现在的工作却让他一天二十四小时精神高度紧张地集中在电脑上。想要的生活和正在过的生活是相反的,这种现实境遇的悖谬让人撕裂,让人堕落,于是便需要救赎。对“鹰”的追寻是人试图回复原初,回到本我的修复尝试,然而鹰在天上,它们已经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天空了。
民啸的《我对这个世界没看法》(《百花洲》2015年第4期)述说的也是这样一个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却终被另一种堕落所俘获的故事。摄影师马东有自己的理想,他想做一名好摄影师,拍他想拍的题材,可为了生活他却在一家广告杂志做摄影师,每天为了公司、客户的需求像一个焦躁的公交车司机一样永无止境地驾车、停车。昏天黑地焦头烂额的业务让自己的创作时间被挤压得可怜。为了做回自己喜爱的人文摄影,马东辞了职,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昂贵的徕卡M9兴奋地拍摄这座城市。然而,作为一个无名的摄影师,自己拍摄的照片根本无人问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当五万元的相机落入富春江时,马东也将自己出卖了。他不再摄影而是与一名离异的广告公司老总——群姐,建立了一种类似包养的关系。生活就像一张网,密密截获那些企图飞往蓝天的翅膀。王祥夫的《交界处》(《星火》2015年第5期)则讲述了大学毕业生林加春为凑足父亲的手术费而跨越自己一直坚守的那条“界限”在夜晚敲开了模特队的头胡丽的门的故事。西北狼的《杀刺嘎依》(《广州文艺》2015年第9期)在表达对战争的反思之外,也表现了报社记者陈小兵与同事冯家明在职场令人生厌的纠葛,最终陈被迫离开自己钟爱的记者行业。陈离的《如梦记》(《百花洲》2015年第4期)表现了当下高校教师为评职称、分房子的辛酸苦辣。同时表现现实与自由人性相悖,使美好人性萎顿的作品还有李治邦的《辞职》(《长江文艺》2015年9月上)等。
现代化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了恶果。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商业化了,被物质化了,这也导致人凡事必讲功利。当人们“自由”地去追逐金钱和利益,传统的亲情、爱情、友情在利益大考验中如何?如果这些曾经将我们紧紧维系的传统价值观念被击溃,谁还能扶正它,人该如何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文学无声地记录了这些正在挣扎或已沉落的灵魂,否定了他们所在的非人性世界。
中国传统的家本位观念在经济大潮中遭遇史无前例的冲刷。冯慧的《好大一个家》(《长江文艺》2015年9月上)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农村大家庭如何被金钱冲散的故事。菜农玉珊一家兄弟姐妹众多,大哥是令全家人骄傲的大学生,多年来在北京打拼已小有一番成就,彻底脱离了土里刨食的日子。大姐玉淑早已嫁到邻近湾子,大姐夫也是个勤扒苦作的老实人。二姐玉娇是三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的,提亲者络绎不绝,可她一心要找个城里人,彻底摘了菜农这顶帽子。后来她果真如愿地找到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田老鼠”,搬进了城市里的“鸽子笼”。老幺玉珊则嫁给了工人小秦,小秦是个外乡人,夫妻俩婚后也就一直住在玉珊家。一家的纷争由修建老宅起,老宅年久失修,老娘召集家庭会议,提出集资修宅一事。大姐因造屋欠债,实拿不出钱,老二玉娇和大哥则推脱拿不出钱。老娘因此立下“谁照顾老娘,老房给谁,谁盖新房也不许扯皮”的字据。玉珊和小秦起早贪黑终于盖起了新房,上梁那天一阵风单把“和睦家庭万事兴”的下联吹走,似乎预示着以后的家庭纷争。大哥因充满回忆的祖宅盖上了新房而对老娘心存怨恨,连她去世也不曾回家。多年后,曾经满口不要老房的大哥二姐在听到老房拆迁的消息纷纷赶回家来争抢,兄妹闹得不欢而散。但是得到了拆迁补偿款的玉珊、玉淑过得并不舒心。大姐的儿子染上毒瘾,没多久就将名下的房子败光。二姐玉娇家的鸽子笼多年过去更显破败狭窄,然而就是这摇摇欲坠的鸽子笼也因拆迁引夫家姐妹争抢,侄子三十多岁因没钱没房眼看就要打一辈子光棍,生活实在窘迫。小秦则因争房风波误伤了门卫,损失了三十多万元。后小秦坚持回到自己家盖了一套房子,了结了心病。好大一个家,如今却因利益而冲散了,玉珊感慨万千,最后决定将自己家的房子分给二姐一套,践行老娘 “兄弟姐妹有难要互相帮助” 的遗嘱。传统的宗法血亲使一个大家庭根枝相连,可当利益纷争出现,兄弟姐妹反目,就让人感到根枝撕裂的痛苦。当人们试图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念去追逐金钱时,人就亲手给自己戴上了另一副枷锁。
霍君的《左转弯,右转弯》(《星火》2015年第5期)讲述了小艾一家的故事。这一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痛和心病。小艾从小就梦想着住上有抽水马桶的房子,过上城里人体面的生活。如今这套两居室的房子算是圆了她的梦,可是在丈夫得子的戏谑下,她在卫生间里看到了父亲清晨忘冲的马桶,那种羞愤像一个尖锐的麦芒让她原本的鼓胀的满足感一下子泄了气。从此小艾都会在清晨准时醒来,在听到父亲按下抽水马桶的声音后才能再次安心入睡。丈夫得子是个摩的司机,不体面的职业让妻子和儿子都感到尴尬。儿子严禁得子去校门口接他,可是得子每天还是冒着儿子的鄙视在校门口一百米处等他。得子一直有某种模糊的期待,期待生活中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让快要馊透了的日子重新变得鲜灵起来。一张包皮手术的广告单让他看到了新鲜的希望,然而手术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有出息的男人。正是这种在家庭这个小窗口里缩小了的性的压抑和社会地位的压抑成了得子的心结。当小艾在酒店大堂里高声指使他“给王局长打电话”时,他的脑子轰的炸开了。他疯了。小艾的父母亲一直在家里活得小心翼翼,生怕给女儿女婿带来麻烦。父亲一直对女儿心存愧疚,他想到小时候小艾在麦茬地里摔倒割伤了手腕,他明明极其心疼可却违背本意地打了她一巴掌,这成了他的心病。当孙子亲手戳到了小艾的痛楚让她在客厅里吐血晕倒时,老人毫无征兆地下定了决心。那天清晨,他来到自己上班的地方,当看到一辆奥迪车驶来时,他扑了上去……老人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赔偿款来让女儿过得幸福。
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现代爱情观在现代社会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查一路的中篇小说《天亮以后》(《四川文学》2015年第9期)就讲述了一个爱情中掺杂了物质后逐渐变质的故事。名校毕业生李亘毕业后不仅没能出人头地,甚至没能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他自己开了个小电脑工作室谋生。日子不紧不慢。女友小艾一直为自己的低门楣自卑,与其说她是在城市里急功近利地奋斗,不如说她是在向昔日生活中所承受的异样目光复仇。当女友赤裸裸地鄙视他准备的不要钱的浪漫时,他决心振作起来,为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而奋斗。可是,正当李亘顶着极大的困难打拼时,小艾却靠“奖金”自己买了房子。她已经和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发生了关系。一个人的经济基础变了,她的基本面也会跟着改变。爱情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像爱情了。当李亘痛苦地明白真相时,他开始自暴自弃,放纵自己与一个黑帮老大的情妇堕落下去……麻烦接踵而来。作品清醒地表现了爱情在现代社会中现实境遇。
城市青年的爱情遭受冷遇,而进城民工也有自己烦恼。黄荣才的《找一个人代替》(《四川文学》2015年第9期)讲述了长期夫妻分离的进城务工者的苦闷。他们长期的寂寞使他们不自觉地希望“找一个人代替”自己心爱的妻子。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种关系纯属互相取暖,有开始没有未来。梁开荒最后对家庭的回归使作品的色彩温暖起来。
任珏方的《星期六晚餐》(《福建文学》2015年第9期)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关于付出、关于对珍贵肆无忌惮地破坏的故事。“我”的亲生父亲韩瑱得了重病,临死前让我把他送回望道村,我百般不情愿但还是按他的意思做了。后来“我”才得知这个坐过两次牢的别人口中偷梨贼都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是在利用和践踏韩瑱的爱与信任来获得利益和好处。自始至终韩瑱的付出都毫无怨言,可母亲却对他怨恨至深,对他提防敌视,生怕他来破坏自己现在的生活。申剑的《太平天下》(《山花》2015年第9期)中早该在十五年前死去的袁如海却成了儿子追名逐利的武器,为了自己的名利,袁小海让他的父亲靠医疗器械不人不鬼地活着。在追逐利益的道路上,爱与信任遭遇危机,一切美好人性都可以作为置换的砝码随时放上利益的天平。谁来扶正这已失衡的天平?也许人们应该回到“望道村”,找回那个亲密的人性世界。
自由精神是每个现代人不应失却的品质之一,可当人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个性,按照他人的期许来修剪自己的枝条,那就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梁鸿的《好人蓝伟》(《上海文学》2015年第9期)就塑造了一个像阑尾一样,无用还害人的妥协主义者——蓝伟。他是人人认可的好人,但也最是个坏人。他内心空虚,随波逐流,怎么都行,为取悦别人毫无目的地做事,按照别人的要求塑造自己的个性。他时刻在表演,演出别人值得夸赞的样子,最后这虚伪竟让他自己也信以为真。只有曾经见过他意气风发的人才惊诧于他现在的消极和无为,一个人何以在盛年时只能在沙滩上帮人看沙?他已丧失了人的自由意志并且毫不自知。
当底层人寄希望于已经飞黄腾达的底层人,最终却发现别人做出的承诺不过是欺骗和利用时,这愤怒就像燃烧的火焰会毁掉一切。余同友的《画火的人》(《广州文艺》2015年第9期)就讲述了火车上一个神秘的画火男子梦魇一般的往事。王祥夫的《噗的一声细响》(《红岩》2015年第5期)讲述了农村妇女北花在受到刘继红的欺骗和侮辱后对其进行惩罚的故事。李黎的《还债》(《红岩》2015年第5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为挣钱而欠债而又始终在借钱还债的暴发户陈尚龙。
女性主题永远是文学的母题,可传统社会中的旧观念在今天依然让女性不自由。郭庆军的《与鹤共舞》(《四川文学》2015年第9期)中王女女没有别的爱好,她只爱听“唱瞎腔的”唱戏,把这些近乎流浪的艺人接到家里,让他们吃顿好饭,睡个好觉就是她的心愿。可是,没男人的女人不光最易受恶邻的气,也最易成为自己儿女的撒气筒。她的两个儿子像看守一样管制着她。最终残翅灰鹤舍己为人,帮助它的女主人达成了心愿,女主人的真心让这些艺人一辈子觉得温暖。
人类源自海洋,人类苦咸的眼泪保留着对海洋的回忆。也许当人们在现代社会里受伤后,只有回到海洋的怀抱才能得到治愈。赵世菊的《台风季》中年仅13岁邻家女孩小青因想在婚礼前见她的祥利哥最后一面,在铁道旁等候时被人强奸。怀孕的她只得远走他乡,“爸爸”何良的被枪毙使亮亮从此不再说话,直到亮亮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才再次开口。当心爱的海豚丢失后,亮亮再次开口说话:他要去找那条海豚,于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大海。亮亮的失语是现代社会中的伤痛造成的,而海洋却让他得到治愈。
人的意志应是绝对自由的,但作为时代最敏锐的触角文学恰恰敏锐地捕捉到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种种不自由的姿态。或为庸常的生活、无聊的工作所困,或沦为金钱的奴隶,戴着名利的枷锁劈杀亲情、爱情、友情。文学无声地记录了这些正在挣扎或已沉沦的灵魂,否定了他们所在的非人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