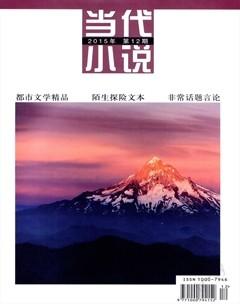九月叙事
方格子
秋天到来。走出门外,兆吉忽地感到凉意。虽然喜欢南方温润的凉,但当他瞥见路边被丢弃的台历时,心底一惊——怎么又是一年了呢?
电瓶车行驶在达夫弄,风顺着耳边行走,呼呼地响。这条路因了一位作家而命名,他记得第一次读他的小说是初中,睡在上铺那个阴郁的同桌总是于熄灯之后,打手电看书。兆吉被他的勤奋好学搅得心慌,趁上铺去厕所,偷偷翻开他的被窝,却是一本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兆吉自认不钟情文学,但与大多数从懵懂光阴走过来的青春男女一样,满满的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让他迅速获得这本小说的阅读资格。忧伤,挣扎,沉迷于某种时代的气息。兆吉发现,自己骨子里是有那么一点情愫的,只是他不耽于此,只愿意记住这个名字。
大学里,兆吉学的是农学,兼修植物科学与技术,对于植物的喜爱,源自于他与生俱来的天然喜好。偶尔他会想,我就是一株生长在良溪岸边的凤阳树,石榴树,或者也可以是新年的竹子。“总之是植物。”他说。他记事开始,祖父便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认识那些生长在山涧边的草,饭团草,小鸡米草,酸枝根,生地黄。12岁那年,他曾经在一株歪脖子的冬青树上挂一根杜英的枯枝。第二年,带米粒去山上,看到那树枝依然挂着,他笑了,仿佛有了某种默契,互相对视。米粒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熟悉山中树木的,后来,米粒在幼儿班给孩子做游戏时,总要带他们去田间地头,山湾,熟悉花草树木,熟悉农事。
临毕业时,谋取一份工作成了同学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有黯然,有喜悦,还有踌躇满志,一心要展翅飞翔。兆吉说,快快毕业吧,我要回良溪。
上铺同学第一时间抨击兆吉,兆吉,你是不是发昏了,良溪那些山,那些花草树木,你什么时候去照看过它们,它们不是照样生长得这么葱茏。兆吉愣了愣,想辩驳几句。上铺说,心虚了吧。你们良溪村真不缺你一个,你得留在省城,再不济也得是个县城吧。
你得出去。
你得出来。
内心少了坚定,在这喋喋不休的规劝中,兆吉没有回良溪。
兆吉留在外面了?良溪人总是这样问他的家人。
母亲每每报以最安慰的笑容,是啊,出去了,出去了。
兆吉你出来了?在城里遇见良溪人,都会这么问,他们总是不由分说地替兆吉高兴。
兆吉在达夫弄一家园林公司谋到一份工,像是有某种隐秘的暗喻,初中时代阅读小说的那些碎片式的时光,重新回到他内心,达夫弄。让他恍然觉得这条安静的街巷有着与植物最亲密的关系。他想,他是可以在远离故土的县城安排那些需要被安置的树木的。虽然他的工作是坐在电脑跟前,设计某个小区的绿化方案,为新建的公园拿出一套最妥帖的绿色景观。但是,因了这些都可以与他的专业有关,他也是欢喜的。
兆吉不是一个爱挣扎的人。
周末回家时,兆吉去了米粒家。
米粒,达夫弄旁边有家幼儿园。兆吉说。
米粒正在做书签。米粒跟兆吉是邻居,从小跟她奶奶住,但兆吉从未看到过米粒父母。事实上,米粒自己想不起父母的模样,良溪村偶有人闲散地说起,说着说着就把米粒的身世带出一些来。大致是,米家媳妇去镇上,回来时,怀里多了一个婴儿,瘦弱,病恹恹的。大家都说这个毛毛头怕是养不活了,良溪村人对婴儿的样貌皮肤有深切的了解,谁家生的女囡子,谁家生了男小子,他们从未看到过像米粒这样出格的。出格在哪里,一下子说不清,“就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一样”,有个人这么总结。他们得空就去米家看看,他们关心这个神秘来客,他们围着米家媳妇怀里的婴儿,进行过多次对于生命存在的朴素探讨与惋惜,甚至超过了对女婴身世的打探。
是兆老先生给了你一条命。兆吉曾经听米粒奶奶这样说,那是米粒10岁那年。
兆老先生就是兆吉的祖父,祖父出生在良溪,一辈子躬耕于农田,他不关心时政,不关心良溪村以外的事。年轻的时候,人家在他面前议论东家长西家短,他安静地听,说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一样安静地听。万一有人毁谤他人时,他突然说,你走吧——毫无预兆。
兆吉曾经跟祖父问起米粒的事,问,是你给了米粒一条命?祖父从一个装满了银杏叶的竹筐里抬起头来,说,没有这回事。
米粒,达夫弄旁边有家幼儿园。兆吉说。
米粒做完最后一枚书签,用的是香樟树叶,她递给兆吉,站起来,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地喝完。再倒一杯,递给兆吉,兆吉也咕咚咕咚喝完。然后,米粒说,兆吉,我不想被连根拔起。
兆吉一愣,转而有些迷糊,说,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能扎根。
关于扎根这个说法,只有米粒才懂兆吉指的是什么。从他们俩懂得探寻山路捉迷藏开始,米粒的身世被他们提到了一定的高度。这要从一次偶尔的耳闻说起。说米粒原本出生在县城,三四个月开始,一直病痛不断,父母四处求医,终不得要领。某一天,过路的道士先生见到襁褓中的孩子,摇头叹息说,不该落在此地。米粒母亲追问,何出此言?道士先生说,这女囡从泥土来,终将回到泥土中去。父亲闻听,要动粗,说道士出言不吉。道士轻声道,命定了的。
后来,米粒奄奄一息,却又不决然离去,好像有什么牵绊着她,留不得走不了。这一天,搁放在围墙上的花盆掉落,泥土四溅,正巧散落在摇篮里。米粒得了那意外而至的泥土,居然有了生机。这似乎是米粒离开都市来到良溪的本因,事实上,谁都无法探究清她的来路。
再后来,兆吉跟米粒有过比较深刻的讨论,比如,从泥土来,到泥土去。是宿命还是偶然。虽然没有答案,但这种神秘的说法已经让兆吉对泥土产生特殊的情感,格外迷恋。他总是带着一些古怪的念头对待那些植物,那些从泥土中生长起来的物种。有一次,公司接了一个单子,要为处在江畔的高端小区进行整体绿化,布置成园林的格调。兆吉不关心那里住了谁,从事什么工作,收入,家庭,喜好——他的工作是在电脑前拿出一份适合不同趣味的实景图。公司再组织花木工人去完成种植,栽培,养护。有时,兆吉特别想去看看那些植物从哪里来,长得怎么样,那些叶片脉络的走向怎样,工人又是怎么来安顿它们的。有一次,他跟主管说,我想参与现场。
主管觉得兆吉的要求匪夷所思,终不被允许,兆吉便会在下班后去小区,公园,植物园。那些树被移栽到都市,有的长势良好,葱茏的样子。可兆吉却总能从树干枝叶上看到一些萎靡来。它们跟我一样,是被移栽了的。这么想想,他便想念良溪,良溪有米粒,幼儿园里响起的风琴声,总叫他向往。有一天,他借了部脚踏车,从县城骑车回到良溪,足足六个小时,在家睡了三个小时,抽空去米粒家门口看了看,又骑车回到县城,赶在上班前还了脚踏车。
有一次兆吉休息回家,米粒看出他有心事,问了他也不说。他跟米粒去山湾走走,挖竹笋,掏树根。米粒说,兆吉,要不你回良溪。话一出口,两人都怔了怔,他们清晰地记得兆吉那次偶尔回乡的遭际。
那天,兆吉身体不适,跟公司请了假,坐上回良溪的中巴车。中巴车上只有三个人,兆吉都认识,村头的阿根泥水匠,开小店的洪发,还有司机强华。兆吉有些讶异,问强华怎么坐车的人那么少,他记得自己上初中时,中巴车总是挤满了人。他偶尔从镇上学校回一趟良溪,都没有座位,只得坐过道上的小板凳回家。
都出去找活计,良溪只剩下两条溪了。强华说。
下了车,刚好是放学时间,三五个孩子背着书包从学校出来,迎面看到兆吉。有个孩子问,兆吉哥哥,你爷爷死了吗?
兆吉生气,盯着孩子看,孩子嗫嚅地说,我们老师说,良溪村出去的人都不愿回家,只有死了人,才会回来。
兆吉很快被提拔为组长,虽然设计组只有四个员工,不曾想,也就过了三个月,兆吉便辞职离开。待他走出公司,主管在身后赶上来,一只手搭在兆吉肩上,偷偷塞给兆吉一张名片,说,兆吉,我们同事一场,你替我保密,我是隔段时间就要去他那儿,我觉得你也需要。
兆吉看名片,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联系方式,他把名片塞还给主管。主管说,我是真心希望你好,兆吉,你是个有才华的人,可是,你知道,有才华的人也会犯病。
兆吉算是失业了,他没打算回家,每天窝在出租房里,也没出去找工作。过了半个月,主管打电话来,说,有家公司在招人,让兆吉过去看看。
兆吉,你不该荒废才华。
挂了电话,思绪有片刻的游离,似乎又一次来到那个高端小区。那一次,一车灌木从卡车上卸下,那是上好的金边黄梁。按照兆吉的设计样式,工人开始陆续地铺排开来。兆吉看着这些草本灌木密密地排列起来,居然有了别样感受。他脱下外套,从一堆工具里捡起一把镢头,蹲下来挖坑,他知道栽种黄梁木的土坑要多宽,多深,两棵之间的距离。一镢头下去,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兆吉有些激动,以至于手机响了好几声他才反应过来。
主管让他回公司,“有些变动。”主管说。
居住在这个小区的住户都是人物,政商都有,有个住户不喜欢黄梁木。“改种红花。”主管说。“冬青树也得换,改种其他树。”兆吉惋惜,他告诉主管,这批货不错,来自县城东面的苗木基地。兆吉曾经去过那地方,苗圃主人是个年轻人,大学毕业贷款创建了一份事业。年轻人还给兆吉打过一个电话,说起做苗圃的各种艰辛。
兆吉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组长,没有任何权力来决定一单生意,他只跟主管说,以后多照顾一下苗圃。
别担心,我们不退货,只是不用这些了。新货隔两天到。年轻人创业当然不容易,政府是有扶持的,免税,免息贷款,免费试用土地,这些都是对新毕业大学生的优惠政策——扶持会被写进年终总结,是相关部门的年度成绩。
那么,是公司亏钱了?
不是。
那这些苗木?
“你让工人找个僻静的地方,给处理了吧。”主管说。
兆吉问是否调配给别处,怎么处理,刚想问,主管说,烧了。
兆吉以为听错,有些发愣,呆呆地看着堆在地上的树木,他想象不出蓬勃的绿色被一把大火烧了会是怎样的景象。它们叶子蜷曲,枝条萎缩,迅速分泌出汁水——米粒有一次问兆吉,树木会流血吗?
谁的主意?
你别管。
我想知道。
兆吉,别犯晕了,你以为你是谁呀?那东西,不就是一堆乱柴火,哦,柴火都算不上,公司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单子,别大惊小怪。
你们就是这么糟蹋植物的吗?
“你疼吗?”
兆吉不说话。
“烧的是政府的钱,管你什么事?兆吉,要不是看在你有才华的份上,我还不愿提醒你,你真的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兆吉沉默。他想起有一次跟米粒去山上,见一株杉树被砍了一个口子,插上一根木头,当做挂钩。
杉树疼吗?米粒问。
很疼。兆吉说。
兆吉成了一个无所事事游荡在县城的良溪人,消息传得很快,良溪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好在大家习以为常。很多良溪人在外面都会遭遇这样的情况,“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重新找到工作,总不能回良溪待着吧。”
兆吉是后来才得知父母也出来了,去的是临县,在一家塑料制品厂打工。兆吉给母亲去电话,言语中多有责备,他心疼父母,六十多岁了,还出去打工,家里经济不至于拮据到这地步。母亲说,在良溪,没有什么能做了。种了菜吃不完,想送都找不到人。
“总不能在家等死吧。”父亲抢过母亲的手机,吼了一声,兆吉慌乱中挂了电话。
不久,兆吉听说良溪将建造新农村,整体规划,成为本县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本。他在达夫弄碰到一个良溪人,背了包裹去车站。说,兆吉,你怎么不回去,上面拨了一大笔钱给我们村,家家户户的房子都要重新造,良溪要大变了。
家家户户?
“家家户户。我算了笔账,米粒家最划算,她奶奶那房子你知道的,是清朝手里的破东西,修修补补撑到现在,现在好了。米粒也能住上新房子了。”